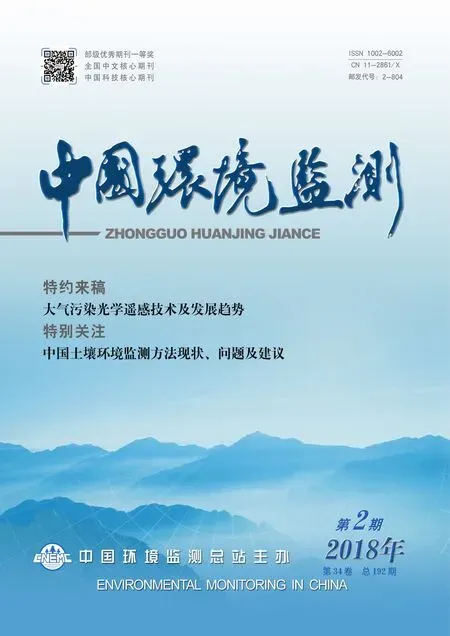環境監測技術服務社會化的政策文本研究
鄢德奎,陳德敏
1.重慶大學法學院,重慶 400045 2.重慶大學西部環境資源法制建設研究中心,重慶 400045
環境監測社會化指政府直接向社會提供的部分環境監測公共服務事項轉由具備條件的社會環境監測機構承擔。近年來,地方政府相繼出臺環境監測社會化發展的政策文本。筆者運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梳理各地環境監測社會化政策的異同,結合中國環境監測社會化發展現狀,提出改進建議,為環境監測社會化健康發展提供參考。
1 分析框架與研究樣本
1.1 分析框架
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政策文本中的共同要素包括4個方面:市場準入、監測領域、運行管理和監督制裁。筆者以這4個維度作為分析框架,比較研究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對策。
1)市場準入是社會化環境監測機構提供環境監測服務的最低能力要求。準入方式大體可以分為2種:資質認定和名錄制。資質認定是社會環境監測機構申請環境監測業務能力認定,申請通過后才能從事相關環境監測業務。名錄制是政府對環境監測服務庫進行公開招標,并以統一的考核指標對社會監測機構評估打分,依據分數高低進行排序入庫,將原來政府承擔的部分監測業務,委托給入庫社會監測機構。
2)監測領域可分為環境監測服務領域、環境監測公益性領域、環境監測監督性領域。環境監測服務領域主要包括排污單位污染源自行監測、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環境損害評估監測等環境監測活動;環境監測公益性領域主要包括環境質量監測、環境預報預警監測等環境監測活動[1];環境監測監督性領域主要包括環境執法、環境質量目標考核等環境監管中的監測活動。
3)運行管理是指環境主管部門對社會環境監測機構進行全過程的質量控制和質量監督,確保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出具的數據客觀準確。筆者不僅梳理分析環境主管部門對社會環境監測機構采取的資質管理和名錄管理2種質量管理方式,還分析環境監測質量控制制度之外,環境監測報告制度、信息保密制度和禁止分包制度。
4)監督制裁是規范和引導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有序發展的重要舉措。筆者依據各地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政策文本的內容,主要考察各地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制裁事項和責任追究方式。
1.2 研究樣本
1)樣本采集。研究主要是對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發展地方立法實踐經驗進行研究,研究選取的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政策多集中于地方省級和市級層面。在獲得46份相關政策文本中,剔除有關聯但并未直接規定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的文本,最終確定29份研究樣本。
2)樣本構成。樣本的政策文種主要分為4個類別(辦法、方案、意見、規定),樣本的發文層次可分為中央級、省級、市級3個層次,樣本的發文主體都為環境行政主管部門,樣本的發文時間跨度自2009年11月1日—2016年3月16日。
2 政策文本分析
2.1 市場準入
各地對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的市場準入進行規范的主要內容包括2個方面:一是市場準入方式;二是市場準入條件。其中,市場準入方式分為名錄制和資質認證兩大類,大部分省(市)的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的準入方式是資質認證,約占75%。所有的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政策都包括工作場所、隊伍建設、準入期限這3種準入條件。為了進一步細化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的準入條件,江西、新疆、湖南并未“一刀切”地將準入條件界定為一種標準,而是分梯次地規定準入類型。如江西省規定了環境監測甲級機構、乙級機構和自動監測運維機構的工作場所、人員規模的不同規格。
2.2 監測領域
多數省(市)都具體規定了環境監測服務事項。為了減輕環境監測部門的繁重監測任務,幾乎所有省(市)都允許排污單位污染源自行監測、企事業單位排污狀況自主調查監測、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清潔生產審核監測等4項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個別地區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承受能力以及實際需求,開放了一些特有的環境監測服務事項(如深圳市的輻射監測等)。根據環境監測服務的領域不同,吉林省、湖北省、平涼市等將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分為2個階段,首先是全面放開的環境監測事項,其次是因地制宜地有序逐步放開的環境監測事項。這一規定與環境保護部《關于推進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的指導意見》的政策精神相一致,即全面放開服務性監測市場和有序放開公益性、監督性監測領域。
2.3 運行管理
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制度除了名錄管理和資質管理之外,還有監測報告制度、信息保密制度、質量控制制度等。名錄管理只在個別省(市)中施行,它是一種動態的管理方式,進入名錄的社會監測機構需要實時更新自身的環境監測服務信息,以便于環境主管部門考核。為了保證社會環境監測機構監測數據的真實有效,多數省(市)都規定了質量控制制度,但該制度具體內容并不統一。環境監測質量控制制度大體有2種模式:一是全過程質量管理,從環境監測點位的設置、采樣頻次、時間和方法到數據傳輸等整個環境監測過程都需要監測質量控制;二是內外部質量控制,如山西省規定社會環境監測機構應積極參加質量控制考核、能力驗證、實驗室間比對等外部質量管理活動,并采取密碼樣、明碼樣、空白樣、加標回收和平行樣等方式進行內部質量控制。除了環境監測質量控制制度之外,環境監測報告制度、信息保密制度和禁止分包制度也被多數省(市)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政策文本所青睞。
2.4 監督制裁
監督制裁是環境監測社會化管理的重要事后監管手段,依據研究文本中部分省(市)的政策內容,制裁方式和制裁事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環境監測社會化末端管理的強度和重點。就制裁方式而言,為了制裁違規的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多數省(市)規定了吊銷資質、通報制度、從業禁止和黑名單制度。除了上述4種制度以外,有些省(市)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規定了差異化的制裁方式(如禁止或限制違規的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參與政府購買或委托項目、損害賠償、暫停各類環保專項資金補助等)。雖然各省(市)界定的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制裁事項大相徑庭,但都無一例外地將篡改、偽造數據等弄虛作假行為、超能力認定范圍開展監測活動等作為制裁的必要選擇項。
3 政策評價
從上述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各地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政策的具體內容雖有所差異,但均對市場準入、監測領域、運行管理和監督制裁等方面作出規定,為推進各地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部分省(市)的相關規定還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使以往混亂的社會環境監測服務市場進一步規范化。在肯定各地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政策的同時,也要看到這些政策文本的不足之處。
3.1 市場準入條件苛刻
多數省(市)對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的工作場所、隊伍建設、準入期限等設立了過高的準入門檻。具體而言,除了江西、新疆、湖南以外,其他各省(市)并未較好地顧及環境監測領域的實際情況,均將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準入條件設為一項標準,最終造成有能力監測某些領域的企業因無法滿足準入條件而被排除在社會環境監測服務行業之外。此外,工作場所作為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的準入條件也與地方保護主義有關。目前,除了西藏以外,其他各省(市)都有自己的能力認定標準且不承認外省的資質認定結果。這類苛刻的市場準入條件限制了許多有能力的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使得能開展環境監測服務的機構大量減少,最終導致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成本過高、市場無法優化配置環境監測資源等難題[2]。
3.2 監測領域有待放開
各地在監測領域開放范圍方面千差萬別,但整體上監測領域都過于狹窄。多數省(市)明確規定的環境監測領域不超過5項,如貴州省僅規定企事業單位排污狀況自主調查監測等3項監測領域,并且所開放的環境監測服務事項并不是當前環境監測服務的重要領域。以環境監察執法監測為例,作為環境監測中使用最為頻繁的一項監測服務,僅有山西、湖北2省將其作為有序開放的監測領域。而現實中,長期以來作為中國開展環境監測活動的唯一主體——環境行政主管部門所屬的環境監測部門卻無力滿足越來越多的環境監測需要。限制社會環境監測機構開展環境監測服務,既是對社會環境監測機構提供服務積極性的挫傷,也是對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政策的消解。
3.3 運行管理模式僵化
當前,環境監測質量控制制度是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的最主要制度。該項制度的實施主體是環境行政主管部門,旨在保證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出具的環境監測數據真實客觀。然而,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模式無法保障環境監測服務市場公平公正,因為在缺乏外部控制的情況下,政府環境監測部門在環境監測服務中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種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模式的弊端還表現在環境監測信息保密制度方面。這項制度要求社會環境監測機構為所從事的環境監測數據保密,設立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政府環境監測信息權的自由行使。政府可以有選擇性地公開或不公開環境監測信息數據,這便與公眾有權獲得環境質量數據相悖,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公眾的環境知情權,更無從保證公眾參與環境監測管理監督。
3.4 監督制裁手段單一
各省(市)對于社會環境監測機構的違法行為采用較多的制裁手段是吊銷資質,既無法達到制裁的目的,也無法激勵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嚴格守法,究其原因:①社會環境監測機構的違法行為多種多樣,違法的嚴重程度、影響范圍都不盡相同,對任何違法行為都一律吊銷資質將造成“輕罪重判”的制裁不公現象發生,制裁也就無法達到正向激勵的作用[3];②將吊銷資質作為主要(甚至是單一)的制裁手段,嚴重的環境監測違法行為既可能觸犯《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也可能觸犯刑法的相關規定,而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政策文本中并無相關援引條款,也就無法指引執法人員和涉事企業的行為,更不可能達到有效的反向制裁效果。
4 政策建議
4.1 放寬市場準入條件
各省(市)應根據自身情況,因地制宜地放開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的準入條件,充分激勵社會監測機構供給監測服務。首先,各地可根據社會環境監測服務行業的發展情況,設置多層次的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的準入標準,形成大、中、小各層次均衡發展的社會環境監測服務行業生態。當然,社會環境監測機構的層次越高,監測服務事項越多,對社會環境監測機構能力要求越高,準入條件也就越多。其次,全國范圍內循序漸進地推進社會環境監測機構資質互認體系。最后,各省(市)應逐漸取消異地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必須在當地具備諸如工作場所等硬件設施的要求。
4.2 有序開放監測領域
當前環境監測市場并不成熟,為引導環境監測市場規范化,應當有序開放環境監測領域。環境監測領域有序開放的基本原則是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必須享有所從事環境監測的數據知情權。在此基礎上,結合當前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的程度,因地制宜地全面放開服務性環境監測領域,循序漸進地逐步開放公益性環境監測領域,禁止開放監督性監測領域。具體而言,積極引導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參與排污單位污染源自行監測、環境損害評估監測、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等服務性環境監測活動。對于公益性環境監測領域應逐步開放,如盡量委托社會環境監測機構開展環境質量監測,不完全依賴社會環境監測機構開展突發環境污染事件的應急監測。由于受到環境監測信息公開范圍的限制,現階段對于諸如生物多樣性及身體安全等監督性監測領域應禁止開放。
4.3 構建多元管理模式
以政府為主的單中心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模式無法有效回應當前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出現的難題。構建政府主導、行業協會協同、公眾有效參與的多中心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管理模式是保障環境監測服務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4]。在推動環境監測社會化發展方面,作為環境監測的環保部門與監測機構計量資質認證的質檢部門應整合資源,強化環境監測監管的合作治理,并依靠大數據和信息技術平臺,建立健全環境監測機構信用評價體系,依據信用等級實施動態的差異化管理。除了加強行政監管之外,還應成立行業協會,制定行業準則、行業內等級評價、糾紛處理等制度,助推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良性發展。同時,社會環境監測機構應嚴格遵守信息披露制度,及時公開企業及相關環境信息,便于公眾參與監督。
4.4 完善監督制裁體系
強化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過程中違法行為的責任追究,建立健全環境監測監督制裁體系是基本前提。摒棄單一的制裁方式,構建以警告、責令整改、黑名單制度、通報制度、從業禁止、吊銷資質等制度為主的多元制裁體系。在行政主管部門對環境監測服務活動中不規范環境違法行為進行制裁時,可視違法行為的危害程度而裁量選擇恰當的制裁方式。除了上述制裁手段之外,在環境監測活動中,對環境污染或生態破壞造成損失且負有責任的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應承擔連帶的民事賠償責任;對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的社會環境監測服務機構還應對其負責人進行按日計罰[5]和行政拘留;構成犯罪的,需追究刑事責任。
參考文獻(Reference):
[1] 蔡守秋.中國環境監測機制的歷史、現狀和改革[J].宏觀質量研究,2013,1(2):4-9.
CAI Shouqiu.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nvironmental Monitor Mechanism[J].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2013,1(2):4-9.
[2] 何瑾.建設項目竣工環保驗收監測全程質量管理[J].北方環境,2013,25(1):147-151.
HE Jin.The Whole-Course Quality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Check and Acceptance Monitoring of Completed Construction Project[J].Northern Environment,2013,25(1):147-151.
[3] 唐忠輝. 論環境損害賠償中的強制監測義務[J]. 政治與法律,2009(12):19-28.
TANG Zhonghui. Mandatory Monitoring Obl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J].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09(12):19-28.
[4] 孫麗,唐曉青,張明華,等. 中國臺灣地區環境監測市場化經驗[J].中國環境監測,2016,32(4):39-43.
SUN Li,TANG Xiaoqing,ZHANG Minghua,et al.Experience of the Marketized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aiwan,China[J].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2016,32(4):39-43.
[5] 鄢德奎,陳德敏. 《環境保護法》按日計罰制度適用問題研究——基于立法與執法視角[J]. 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6):146-152.
YAN Dekui,CHEN Demin.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Daily Penalt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Based on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J].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6(6):14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