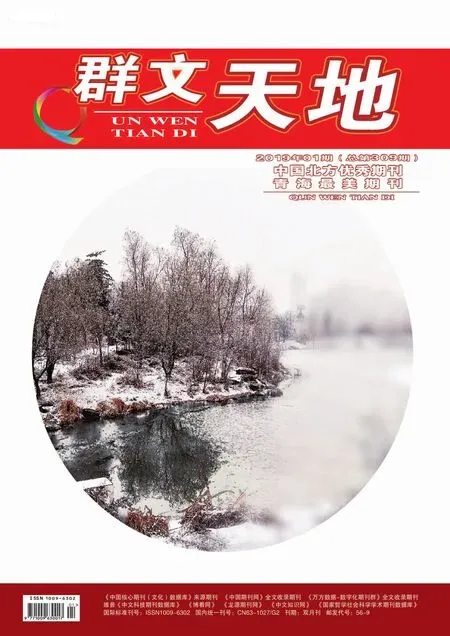河湟春秋(一)
張得祖 李健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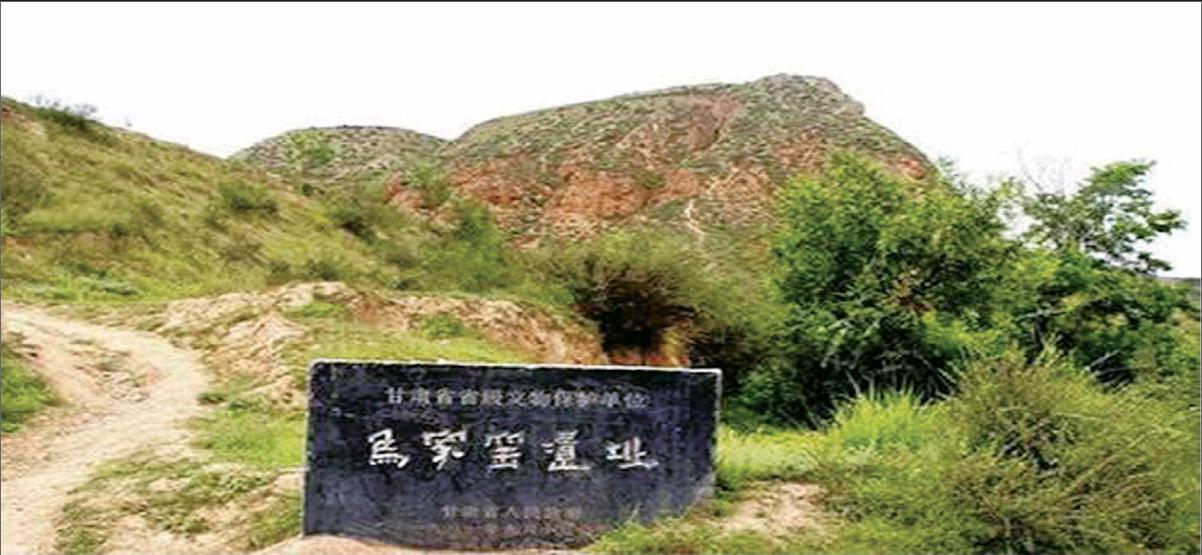
河湟地區是我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拉乙亥遺址的發掘說明早在中石器時代,人類已扎根于此;馬家窯文化時期輝煌燦爛的彩陶文化,在人類史前文明史上獨樹一幟;齊家文化時期,河湟地區已進入青銅文化階段。
河湟地區本為羌戎故地,西漢中期以來,隨著中央王朝勢力的進入,此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兩漢以來,中央王朝在河湟的行政建置、移民屯植等活動,使這一地區邁向內地化的歷史進程。魏晉時期,五涼政權先后統治河湟,使當地成為民族文化融匯之所。隋及唐前中期,中央王朝對河湟實施有效統治。安史之亂后,河湟為吐蕃吞沒。兩宋時期,青唐政權控制河湟。元明時期,中央王朝復又控制河湟。清朝雍正年間,政府通過行政改革,使河湟納入府縣(廳)體制,從而加速了河湟內地化的步伐。
從趙充國屯田始,諸多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深刻地影響著河湟地區的社會歷史文化;羌、鮮卑、吐蕃、回紇等民族,在這片熱土上書寫下民族文化輝煌燦爛的篇章;近代以來,河湟兒女與全國人民一道保家衛國,使河湟也融入了現代化的歷史潮流之中。一部河湟春秋,就是一部河湟開發史,是一部民族文化交融史,也是一部民族邊疆與中原內地一體化的歷史篇章。
第一章 輝煌燦爛的史前文明
第一節 早期人類活動遺跡
青海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存,如同青海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長江、黃河的發源地一樣,也是我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據考古發現,青海地區有從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有銅石并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文化,文化序列如此完整和齊全,除中原關中地區外,在全國其他地區實屬少見。
一、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1956年七八月間,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趙宗溥先生等在青藏高原進行地質普查時,在柴達木盆地南緣格爾木河上游三叉口、霍霍西里等地采集到十幾件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和礫石等工具。根據石器的種類、打制方法和石銹,可推斷它們應是舊石器時代的遺物。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隊在共和縣曲溝地區的托勒臺又采集到一大批打制石器,研究者認定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物。1982年7月,中國科學院鹽湖研究所、地球化學研究所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生物地理地貌系組成的鹽湖和風成沉積考察隊在柴達木盆地小柴旦湖東南岸的湖濱階地上采集到一批舊石器。1984年6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至同一地點,在高出小柴旦湖湖面8米一13米的古湖濱沙礫層中找到了與石器共存的原生層位。在這里先后采集到的石器有112件,其中包括雕刻器、刮削器、尖狀器和砍砸器等41件。據碳14測定和地層對比,這批石器的年代距今大約3萬年。從石器以刮削器為主的組合和制作技術上看,具有舊石器晚期華北兩大系統中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的特色,說明西北與華北古人類在文化技術上著密切的聯系。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多處多次發現打制石器,說明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這里并不是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而是古代人類勞動、生息、繁衍的地方。以上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雖在青藏高原腹地,但與東部河湟地區的古代文明有著密不可分的傳承關系。
二、中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1980年7月,青海省文物考古隊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組在海南藏族自治州進行考古調查時,在貴南縣拉乙亥公社附近的黃河沿岸階地上,發現一處中石器時代遺址,包括六個地點(編號為8021、8022、8023、8024、8025、8026)。拉乙亥遺址位于共和盆地中部,西南距西寧市約200公里。遺址所在地海拔為2580米,埋藏在茫拉河與沙溝河之間的黃河河谷階地中,即在黃土狀砂質土層內。發現有灶坑、紅燒土等遺跡與石器、骨器等遺物。出土文化遺存共1489件,其中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裝飾品2件。石器以打制為主,種類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研磨器、琢背石刀和調色板等。其加工技術達到一定的水平,除直接打擊法和間接打擊法外,還出現琢修技術,而琢修技術是中石器時代制作技術的最大特色,這表明拉乙亥遺址是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文化遺存。研磨器是用于加工谷物的古制工具,它的出土表明至少采集農業已經出現。骨器的加工制作亦達到相當水平,發現的骨錐和骨針等,原材料經過仔細選擇,磨制精細。特別是骨針,器身細長,尖端銳利,有針眼,其技術已經相當成熟。證明當時的人們已用獸皮之類縫制衣服。拉乙亥遺址發現三十多座灶坑遺存,與灶坑伴出的還有一些動物骨骼,能鑒定出種屬的有羊、狐、環領雉、沙鼠、鼠兔、喜馬拉雅旱獺等,還有一些寬大的肋骨,可能屬于馬或牛。有些骨骼尚保留有砸擊或火燒的痕跡。同時,還發現一枚智人的上乳犬齒,屬于尚未成年個體的牙齒,年齡在10歲至13歲,牙齒磨損嚴重,可推測當時食物是比較粗糙的。
拉乙亥遺址出土的木炭經碳-14測定為距今6745±85年,當時的社會形態大致處在母系氏族社會中期階段。
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考古學分期中將使用磨制石器、出現陶器的時代稱為新石器時代。青海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是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因最早(1932年)發現于甘肅省臨洮縣馬家窯村而得名。爾后在甘、青、寧等地區發現的文化遺存,其文化性質與馬家窯所出相同者,都叫做馬家窯文化。因為馬家窯文化源自中原仰韶文化(1921年首次發現于河南澠池縣仰韶村而得名),且當時甘、青、寧同屬甘肅省,過去曾有人稱為甘肅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的地理分布比較廣泛,東起甘肅涇、渭上游,西至黃河上游共和、同德縣境內,北人寧夏回族自治區清水河流域,南抵四川岷江流域阿壩藏族自治州汶川縣附近。在青海境內主要分布在湟水流域的民和、樂都、平安、湟中、西寧、湟源、大通等地和黃河河曲地區的循化、化隆、尖扎、貴德、貴南、同德、共和、同仁一帶。其分布比較集中的有民和、樂都,其次是貴德、貴南和同德。截至1990年調查登記的有917處。已發掘的主要遺址和墓地有:民和縣的陽洼坡、核桃莊、陽山、馬廠塬,樂都區的腦莊、柳灣,大通縣的上孫家寨,貴南縣的尕馬臺,循化縣的蘇乎撒,互助縣的總寨,西寧市的牛家寨,同德縣的宗日等。據碳-14測定,馬家窯文化的年代為距今5800年—4000年。依地域的差異和時間早晚的不同,又分為4個類型,即石嶺下類型(1947年首次發現于甘肅武山縣石嶺下村而得名)、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1924年首次發現于甘肅廣河縣半山村而得名)、馬廠類型(1924年首次發現于青海民和縣馬廠塬而得名)。這四個類型是相互聯系、各具特色的文化類型。endprint
馬家窯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普遍出現了彩陶。眾所周知,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彩陶的國家之一。尤其是馬家窯文化,其彩陶數量冠諸遠古文化之首。這種彩陶既是先民的實用生活器具,又是豐富人們精神生活的工藝美術品,它在我國偉大的藝術寶庫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973年,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在大通縣上孫家寨清理馬家窯文化墓葬M384時,出土了一件內壁繪有舞蹈圖案的彩陶盆。這件彩陶盆為泥質紅陶,器高14厘米,口徑29厘米,最大腹徑28厘米,底徑10厘米,內壁以剪影式平涂手法繪有三組五人手拉手的舞蹈圖案,體現了青海東部地區原始農業民族用載歌載舞的巫術活動,來祈求“豐產豐育”的生動場景。1995年同德縣宗日遺址再次出土了舞蹈紋彩陶盆,繪的是24人分兩組集體舞蹈的畫面。這兩件稀世珍寶均為馬家窯類型時代的產物,即出自距今5000年前的先民之手。據考證,這兩幅舞蹈紋圖是我國最早的成型舞蹈圖案,它們在我國美術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彩陶的主要紋飾有三角紋、草葉紋、花瓣紋、平行條紋、漩渦紋、水波紋、鋸齒紋、葫蘆形紋、圓圈紋、菱形紋、網格紋、棋盤紋、變形蛙紋和波析紋等。一般來說,石嶺下類型的彩陶圖案多見平行條紋、圓點紋、弧邊三角形、波浪紋等,含有較濃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1956年在河南陜縣廟底溝發現而得名)的因素。馬家窯類型彩陶的主題紋飾是水波紋、圓點紋和用連續S形構成的漩渦狀帶紋等,線條粗細均勻,奔放流暢,有強烈的動感。半山類型的彩陶紋飾習見網紋、波折紋、方格紋、葫蘆形紋,大多數紋飾的邊沿葉鋸齒狀,整個圖案顯得繁縟細膩、富麗堂皇。馬廠類型彩陶最流行的紋飾為四大圓圈紋、蛙紋、菱形紋和回紋等,大處簡練粗獷、小處細致人微,觀之回味無窮。總之,馬家窯文化各個類型的彩陶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形成既有相對統一的主題風格,又有層出不窮的變化形式的彩陶藝術,給人以強烈的感染力。
馬家窯文化的居民以經營原始的旱地農業為主,粟和黍是當時人們的主要食物來源。在柳灣馬廠類型墓葬的夾砂紅陶甕內,普遍發現有粟的顆粒和皮殼。農業生產工具有石鋤、鏟等逐耕工具和石刀、鐮等收割工具。狩獵業和飼養業占有一定的比例。墓葬中發現了不少石球、骨鏃等與狩獵有關的工具和豬、狗、羊、牛等家畜骨骼。民和馬廠塬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件塑有動物(狗)的彩陶壺。
馬家窯文化中交換生產品的現象已經比較普遍,墓地中常有出于不同產地的陶器同時出現。民和陽山部分陶片經中子活化分析,微量元素成分含量與其他陶片有明顯差異,表明原料產地不同,其花紋與外觀形態更接近于洮河流域巴坪墓地的遺物。另外,不產于青海的海貝、蚌殼、綠松石等在馬家窯文化墓葬中出現,且越到晚期數量越多,考古學界視這些現象為交換存在的證據。
馬家窯文化的房屋一般為半地穴式,平面形狀有圓形和方形兩種。墓葬有豎穴坑墓和豎穴墓道洞室墓兩種,洞室墓出現于馬廠類型時期,常帶有梯形或長方形墓道,并用一排或數排木棍封門,葬具有木墊板,用木板榫卯結成的木棺和獨木棺等。半山類型墓葬中有二人或多人合葬現象,最多的達六人。合葬情況比較復雜,有兩個成年同性合葬,有成年與兒童合葬,也有兩個成年異性合葬,還有多個成年同性合葬或多個成年異性合葬,其中男女合葬墓被學術界認為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態確立的標志。
隨葬品中,男性多隨葬石制的斧、錛、鑿等生產工具,女性多以紡輪為主,反映出兩性間社會分工的差異。隨葬品的數量、質量、種類,各墓間差別較大。如民和陽山墓地中,一般墓有5件—10件隨葬品,M23有隨葬品38件,其中陶容器34件,另有陶鼓、大型石斧、石球、紡輪各1件。又如樂都柳灣馬廠類型墓葬,少的只隨葬一兩件器物,如M8只1件陶盆,M38僅1件石錛。而最多的達90多件,如M564共隨葬器物95件,其中91件是陶器,還有石斧、石刀、石鑿、綠松石等,陶器中有80件是精美的彩陶,1件大陶甕中還裝滿了粟。同期同墓地出現這種隨葬品多寡懸殊的現象,表明這些墓主人生前處于不同的經濟地位,過著完全不同的經濟生活,貧富分化已比較明顯。
馬家窯文化中大量隨葬品的存在,反映出人們對于現實生活的留戀。民和陽山墓地中祭祀遺跡的出現,說明祖先崇拜意識已經存在。大通后子河河東村墓地出土的女性泥塑像陶甕、樂都柳灣墓地出土的裸體人像陶壺、民和巴州發現的有女陰的泥塑蛙紋壺和大量的蛙紋彩繪是當時人們生殖崇拜的一種表現。
關于馬家窯文化的社會形態,一般認為在其早期的石嶺下類型和馬家窯類型時期,仍處在母系氏族晚期階段,中期的半山類型時期,開始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到了晚期的馬廠類型時期,已處于母系氏族制日趨崩潰、父系氏族制基本確立的時代。
第二節 發達的青銅文明
繼馬家窯文化之后,青海及其河湟地區進入青銅時代,出現了齊家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等青銅文化。
一、齊家文化
河湟地區的齊家文化(1924年在甘肅省廣河縣齊家坪首先發現而得名)與馬廠類型文化關系密切,反映了從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的文化形態。柳灣墓地的考古發現說明,從墓葬形制、葬具、葬式、隨葬品的組合以及陶器器形和紋飾的演變等方面都反映出齊家文化與馬廠類型在文化面貌上的連續性和繼承性。
齊家文化的地理分布比較廣泛,東起涇水、渭水流域,西至青海湖畔,南抵白龍江流域,北入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鹿團山附近。青海境內經調查登記的齊家文化遺存約430處,經過考古發掘的遺址和墓地主要有貴南縣尕馬臺、大通縣上孫家寨、樂都區柳灣、民和縣清水泉、西寧市沈那等。齊家文化的陶器以質地細膩、部分器物表面打磨十分光滑而著稱。雙大耳罐和折肩籃紋壺是最典型的器物。制陶工藝有了新的突破,開始采用慢輪修整法。貴南縣尕馬臺25號墓出土了一件銅鏡,該鏡直徑9厘米、厚0.4厘米,器形規整,背部有鈕,飾有七角形幾何紋圖案,邊緣穿有兩個小孔,制造工藝精美,已采用合范鑄造手段。經快中子放射分析,銅錫之比為1:0.096,屬青銅器。它的發現在我國古代冶金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結合甘肅齊家文化遺存中出土有青銅器的情況看,齊家文化晚期已進入青銅時代。endprint
齊家文化房屋四壁均抹白灰,為四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地面鋪有0.5厘米厚的白灰,不僅美觀,還有防潮的作用。房屋面積一般十幾平方米,適合人口較少的個體家庭居住。墓葬以豎穴土坑為主,合葬墓中以男女合葬較為普遍,表明一夫一妻制已經成為社會主要的婚姻形式。柳灣314號墓的墓主人是一個成年男性,仰身直肢葬于木棺內,另有一青年女性,卻在棺外側身屈肢葬,并有一條腿壓在棺下。女性極有可能是為墓主人殉葬的奴隸。
齊家文化仍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成分,遺址中除發現石鐮、石刀、石鏟等生產工具外,還常可以見到石磨盤、石磨棒等加工糧食的用具。在青海湖濱的沙柳河遺址中,有大量的魚骨和鹿、大角羊的骨骼,以及盤狀器、網狀、骨鏃等捕魚和狩獵的工具,表明這時環湖一帶漁獵仍是重要的輔助經濟。
1981年發現的喇家遺址位于民和縣官亭鎮喇家村,這是齊家文化的一處中心聚落,經測定其年代距今約4000年前。在2002年6月中國考古學會杭州會議上被評為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05年被國家文物局列入全國100處重點遺址保護項目。喇家遺址發現的史前災難性遺址,在全國罕見,被喻為“東方的龐貝古城”。喇家遺址保留下來的齊家文化時期的地震和黃河泛濫及山洪襲擊等多種災難遺跡,反映了距今4000年左右因地震和洪水造成聚落毀滅的災變過程,為多學科交叉研究黃河上游地區環境考古提出了新的課題。目前清理的多處房址中,充滿黃土和顆粒不均的沙礫、紅膠泥土等,并發現死亡的人骨遺骸。各房址中發現的人骨數量不同,他們的年齡性別也不同,以4號房址為例,共發現14具骨骼,以少年兒童為主,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其中年齡最小的僅2歲左右,28歲—45歲的4具。由于死亡時突遇無法抗拒的災難,這些遺骸表現一剎那的驚異姿態,有的屈肢側臥,有的匍匐在地,有的上肢牽連,有的跪踞在地,其中女性懷抱幼兒,跪在地面,相互依偎,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表現出無助和乞求上蒼的神態令人動容。喇家遺址的地層關系表明,這次災難地震在先洪水在后,從而導致了遺址的毀滅。喇家遺址內還發現了深6米—8米、寬10多米的環壕,供人們集中活動的小型廣場,結構獨特的窯洞式建筑,土臺以及祭祀性墓葬等重要遺跡。出土了大量陶、石、玉、骨器等珍貴文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反映社會等級和禮儀制度的“黃河磬王”、玉璧、玉環、玉刀、玉斧、玉錛等玉器。特別是喇家遺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面條狀食物,反映了當時農業發展水平和人們的飲食狀況,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興趣。
二、卡約文化
卡約文化是于1923年在青海省湟中縣云固川卡約村首次發現而得名。“卡約”為藏語地名,意即山口前的平地。卡約文化是青銅時代青海境內的土著文化遺存,與齊家文化關系密切,應是齊家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卡約文化是青海地區古文化中分布面積最廣、持續時間最長、遺址數量最多的一種青銅時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東至甘青交界地帶,西達柴達木盆地東緣,北到祁連山南麓,南至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內的黃河沿岸和玉樹藏族自治州境內的通天河地區。已調查登記的文化遺存1766處,據已有的碳-14測定數據,卡約文化的絕對年代為距今3500年—2690年。但在不同地區,卡約文化延續時間長短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延續到漢代末年。
卡約文化的經濟形式因地而異,河湟谷地農業較為發達,高寒地區、草原地帶則牧業所占比重較大,青海湖沿岸又以漁獵業為主。卡約文化的陶器多為手制,以夾砂陶為主,多夾雜有紅膠泥。器形有雙耳罐、四耳罐、杯、甕、鬲、盆、碗等,彩陶不多,花紋有三角紋、網格紋以及羊、鹿、狗等動物紋樣。同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相比,卡約文化的陶器制造業趨于衰微,不僅數量少,制作也日趨草率,而裝飾品制造業則空前發達。隨葬品中陶器數量不足10%,裝飾品數量可達90%以上,有銅質、石質、骨質、金質裝飾品以及牙飾、海貝、綠松石、瑪瑙、琥珀等,種類繁多,反映當時人們的審美意識大大提高。其中又以銅質裝飾品最引人注目,成為人們炫耀財富的象征。潘家梁47號墓中有隨葬品229件,其中銅質裝飾品竟多達140件。銅器制造業代表著當時手工業的最高成就。湟源大華鄉中莊墓地出土的犬戲牛鳩杖首、四面銅人、鳥形銅鈴等造型逼真、工藝復雜。犬戲牛鳩杖首是在鳩頭狀杖銎之上,一端塑鑄一條昂首張口翹尾的猛犬,另一端塑鑄有一頭聳肩奮力的母牛,牛犬相向而立,作欲斗狀。母牛腹下又有正在吮乳的牛犢卻神態安然。此件構思巧妙、造型生動,可能系用多范合鑄而成。無論從制作工藝還是從造型藝術看,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出卡約文化時期人們的青銅鑄造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卡約文化時期人們居住的房屋以半地穴式為主,也有地面式房屋遺址。房內地面上常鋪有一層紅膠泥面。居住地一般選擇在河岸臺地上,也有些構建在高山和形勢險要的地方。墓葬形制有豎穴土坑和偏洞墓兩種,大多數豎穴坑墓有二層臺,有木棺,葬式以二次擾亂葬為主。二次擾亂葬即在尸體埋入地下一段時間后,重新挖開墓,并將尸骨攪亂的一種葬俗,這種葬俗與當時人們的某種宗教信仰有關。幼嬰、小孩則采用母子合葬或甕棺葬。
在卡約文化墓地中,人殉、人祭、牲殉、牲祭現象大量出現。湟中縣潘家梁墓地中,人殉的墓葬占發掘墓葬總數的10%之多,一墓中人殉一般一至三人。用來祭祀的人常被捆綁成跪伏狀,埋人挖好的坑內,其上部放置一件四耳大罐。有的殉人骨骼的肢骨和脊椎骨上往往留有繩子綁縛過的痕跡。殉人的旁邊常放有一段家畜骨骼和一個花邊口的小罐。殉人的出現說明當時已經存在家內奴隸。循化阿哈特拉墓地殉人墓葬多為男性,都有大量隨葬品附葬,并在墓主棺板上和二層臺上放置大量羊角,被認為是財富的象征,用牛、羊殉葬和祭祀的現象也比較普遍。
1959年柴達木諾木洪等地發現后命名的諾木洪文化,目前僅發掘塔里他里哈一處遺址。發掘的房屋有圓形和方形兩種,用土坯砌成,抹以草拌泥。附近有飼養牲畜的圈欄,出土有大量馬、牛、羊、駱駝骨骼,還出土了大量毛布、毛條、毛帶以及皮靴、骨笛、骨哨等。考古資料顯示,諾木洪文化的居民過著穩定的定居生活,其經濟生活以畜牧業為主,而較多的骨耜和石刀的出土以及麥類作物痕跡的發現,又證明農業也在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諾木洪文化的陶器,無論陶質、陶色和形體均與卡約文化關系密切。因此可以認為諾木洪文化與卡約文化同屬于一個文化系統,諾木洪文化是卡約文化的分支。經碳-14測定,諾木洪文化其年代為距今2905±140年,屬西周時期,下限可能延至漢代以后。諾木洪文化的冶銅業也較進步,出土的青銅器有斧、刀、鏃、鉞等,制作也較精致。還發現煉銅用具和銅渣等,表明銅器是本地制造的。在遺址圈欄入口處還發現殘木車轂兩件,表明當時已在使用木車,它可能是畜力挽拉的木車。木車的出現,標志著青海的古代交通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endprint
三、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1924年在甘肅省臨洮縣辛店村首次發現而得名)是分布在甘青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在青海局限于西寧、同仁、循化以東,主要集中在湟水中下游的樂都、民和一帶。已調查登記的遺存97處,已發掘的地點有大通縣上孫家寨、樂都區柳灣、民和縣核桃莊等,以核桃莊的發掘資料最為豐富。據碳-14測定,辛店文化的年代為距今3235年—2690年。辛店文化時期人們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生產工具除石制的斧、鏟、刀、錛、杵、磨谷器等外,多見用動物肩胛骨或下頦骨制作的骨鏟。手工業有制陶、紡織、冶銅業等。陶器以夾砂粗陶為主,紋飾有繩紋、劃紋等,彩陶紋飾多為雙勾紋、寬帶紋、回紋、太陽形紋、S形紋等。銅器有小型工具、銅容器及各種裝飾品等,冶銅業比齊家文化時有一步的發展。辛店文化與卡約文化大體同時代并存,二者關系比較密切,社會發展階段也大體相同。
第三節 舜“遷三苗于三危”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記載,堯在位時,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后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亦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兇,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這說明,在我國的傳說時代,曾有舜“遷三苗于三危”之事。
“三苗”是我國古老民族,又稱“苗民”“有苗”,主要分布于今洞庭湖和鄱陽湖之間,即長江中游以南一帶。傳說,堯時,“三苗”作亂,堯發兵征討,作戰于丹水,打敗“三苗”,其首領驩兜臣服于堯,整個部族成為堯為首領的部族聯盟國家的南方族眾,然而,“三苗”仍叛服無常,堯將驩兜放逐于崇山,把“三苗”部分族眾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
舜“遷三苗于三危”的時期,恰好處于我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所謂傳說時代,指的是既無直接的文獻材料又無確切的考古資料為佐證,僅以神話傳說中附帶的史實來加以了解的一個特殊時代,堯、舜的時代就是典型的傳說時代,當時,以華夏族為核心建立起來的部族聯盟控制著中原地區,生活在華夏族勢力范圍周邊的少數民族,或臣服于華夏,或長期與華夏作戰,彼此間的競爭與交融成為后來建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基礎。據傳說,舜為有虞氏之首領,國號為“有虞”,為帝顓頊的六世孫。堯將天下禪讓給舜后,為平定周邊部族,舜可能與一些部族發生過戰爭,并以流放族眾的方式對其進行懲戒。
從《史記·五帝本紀》的相關記載看,當時已有“北狄”“南蠻”“西戎”“東夷”諸種稱呼,即已經有了明確的族與族和界限,這顯然是后世的假托,未必吻合傳說時代的具體情形。然而,上述記載并非沒有任何根據,特別是舜“遷三苗于三危”的記載,與考古學材料的確有印證關系。
研究表明,青藏地區是人類最后占領的陸地,而非最早的人類發源地。晚更新以來,史前人類有3次向青藏高原東北部遷移、擴張的歷程,其中,全新世大暖期時期,馬家窯文化人群自東向西經河湟谷地進入青藏腹地的過程,即是東部人群西向發展的一個典型,而末次冰消期進入青藏腹地的人群則在馬家窯文化人群到來之時已成為當地土著。從考古學材料看,馬家窯文化的早期類型深受仰韶文化影響,可稱為仰韶文化的西北類型,馬家窯文化人群自東向西遷徙的過程恰恰與馬家窯文化類型中出現越晚的類型分布越靠西的考古證據不謀而合,這說明距今五千多年前,從關中平原西部,即涇、渭水上游地區向西遷入西漢水,以至洮河、湟水及河曲之地的人類遷徙路線一直是存在著的,這條遷徙路線可能也是人類占領青藏高原的必經之地。
如前所述,堯、舜的時代是我國傳說時代,大約距今4500年,恰好處于馬家窯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半山、馬廠類型的西向發展及其與之后的齊家、卡約文化的內在傳承關系,都印證出人類在青藏高原東北邊緣,即河湟地區遷徙、適應、生存、發展的歷史畫面。《后漢書·西羌傳》記載,舜所放逐“四兇”,將其“徙之三危”,并稱“三危”即“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說明當時舜放逐“三苗”族眾的具體地點即是“河關之西”,為“南羌”之地。
漢代人所謂“南羌”,并非指南方羌人,因兩漢時與中原民族形成競爭關系的主要民族——匈奴,處于北方,受其脅迫羌人往往從河西、河湟一帶自西向東侵擾中原,其所處的地理位置恰好在匈奴以南,故稱之為“南羌”。據《后漢書·西羌傳》,羌人所在地“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說明羌人的地望即為“賜支”河,而“三苗”流放之地為“河關之西”,指的是今甘肅臨洮以西的黃河河谷,而湟水又是這一帶黃河的最大支流。綜合上述分析可知,位于“河關之西”的“三危”,就處于今天的河湟地區。
總之,舜“遷三苗于三危”的傳說表明自古以來河湟地區與中原之間就有著密切的聯系,在與中原的文化與政治的互動過程中,河湟地區逐步走向文明時代。(未完待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