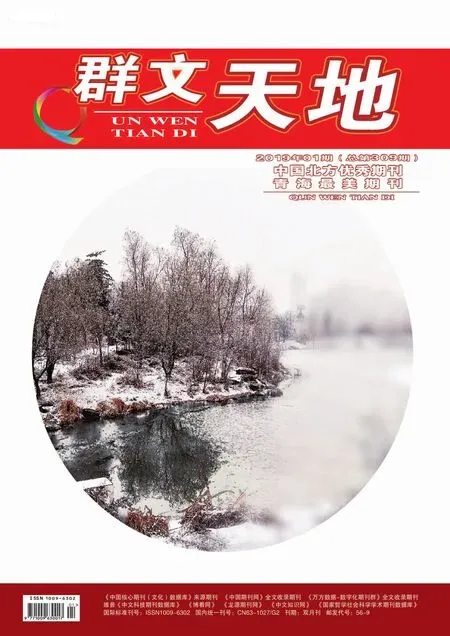“花兒”繁榮背后值得深思的幾個問題
魯占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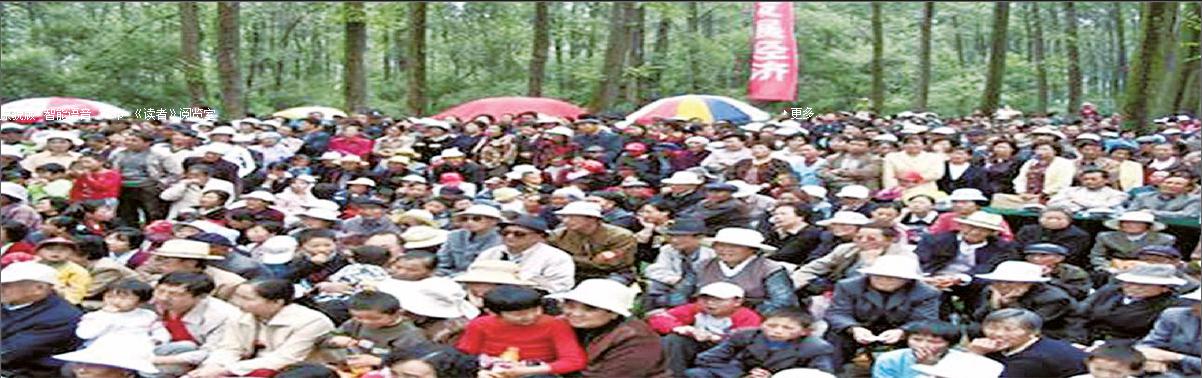
在青海,有一種民歌幾百年來在漢、藏、土、回、撒拉、東鄉等諸多民族中廣泛傳唱流布,經久不衰,它就是被稱為大西北民歌之魂的“花兒”。進入新世紀以來,“花兒”在青海邁上了新臺階,第一次有了它應有的文化地位,大大提升了它的文化品位,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我省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視,在“花兒”看似繁榮的背后卻顯現出一些不得不深思的問題。
一、“花兒”歌手與素質:整體演唱水平亟待提高
縱觀我省各地舉辦的大小“花兒”會,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經過數十年來的培養和打造,我省“花兒”歌手的整體演唱水平比以往有了明顯進步和提升,演唱實力普遍有了新的提高和增強,但部分“花兒”歌手的素質依然低下,亟待提高。尤其是“花兒”歌手個人應具備相關文化知識,有一定的藝術修養。我們在與一些“花兒”歌手的交談中感覺到,他們對文化知識的渴求愿望如饑似渴,他們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卻又很低(大部分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僅靠自學是遠遠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的,因而他們對文化知識的學習和掌握還是捉襟見肘。良好的藝術修養是歌手個人素質的重要體現,是享用一生的財富,它需要在長期的學習中逐漸培養和鍛煉起來。
瑕不掩瑜。雖然有些“花兒”歌手在舞臺上的表現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遺憾,但也給人們帶來了愉快的心情和享受。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通過努力可以使自己不斷地進步。唱“花兒”如此,個人素質的提高也是如此。如今,“花兒”歌手更多的是面向市場、面向社會,他們需要有較為出色的藝術表現力和個人素質,這樣才能吸引人、打動人、感染人。“花兒”歌手的表現力和個人素質中的魅力或氣質也很重要,在多數情況下是先天性的,但也可以通過后天的教養獲得。“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先天素養是包括“花兒”歌手在內的所有人成才的前提和基礎,需要得到后天進一步的開發、培養、訓練、學習,才能有所作為、綻放光芒。“花兒”歌手從社會經驗中習得和養成的某些能力,如對“花兒”歌詞的領悟能力、舞臺表現能力和即興發揮演唱能力等。筆者以為對今天的“花兒”歌手來說,個人素質具體表現為: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識、能領悟一首“花兒”歌詞所表達的思想內涵、選擇適合自己的舞臺著裝、即興發揮編詞演唱的能力及舞臺表現能力。換句話說,一個“花兒”歌手的素質有多高,他的藝術生命相應就有多長。“花兒”歌手要多看點書,懂點當地歷史,了解點民情風俗,掌握些文化知識。因此,文化部門舉辦的“花兒”培訓、講座,要從文化普及和歌手個人素質提高的角度人手,更要側重于他們的文化知識的增加、音樂欣賞能力的提高,以及個人素質的增強等方面,以使他們習得和養成較高的綜合素質,這是我們應該更加重視的。
“花兒”藝術要求得生存、求得保護、求得傳承、求得發展,必須要有較高素質的“花兒”歌手來推動。具備較高綜合素質,無論對“花兒”歌手本人,還是對社會大眾,無論對一臺演出,還是對社會大眾的“花兒”欣賞,都有現實的積極意義。
二、“花兒”推介與傳承:應走普通話與方言演唱同步推進的路子
近年來,在我省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各地文化部門的積極主導,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下,各種形式的“花兒”演唱活動,從省、市到縣、鄉、村,不分季節,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花兒”的發展得到了長足進步,為豐富和繁榮城鄉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逐漸成為青海主流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業態。然而,隨著“花兒”藝術的繁榮發展,“花兒”在文化繁榮的大道上與時俱進的同時,與它的生長環境產生了不容忽視的矛盾沖突,與它生長的原生態土壤愈行愈遠,在各種形式的包裝、創新下,“花兒”的本真遭到了挑戰。諸如所謂的“搖滾花兒”、電子琴伴奏,以及一些花樣翻新的“創新化”的音樂伴奏,還有不土不洋的“花兒”,嚴重脫離了“花兒”演唱的泥土。有些新創“花兒”唱詞與曲令不合,生搬硬套,群眾無法接受,這種現象比比皆是。在鄉村舉辦的一些“花兒”舞臺上,經常看到僅僅會唱幾首“花兒”的民間歌手,穿戴亂七八糟,服裝搭配混雜,觀之很不雅觀很不舒服,不講究個人舞臺形象不說,還時有耍大牌“風范”的能事,一上臺一張口就用所謂的“青普話”演唱,甚至滿嘴低俗之言,久而久之,觀眾也就習以為常了,“花兒”也就變了味,歌手也就著了“魔”。這種既不像“花兒”又不像通俗歌曲的怪胎演唱風格,將“花兒”特有的演唱風格葬送殆盡,使“花兒”的民族性、地域性、獨特性以及本真性遭到了極大破壞。有不少觀眾紛紛坦言:“現在的‘花兒唱的什么,根本聽不懂!”幾百年來,“花兒”一直以其獨一無二的演唱風格和曲調特色盛開在青海高原這塊廣袤無垠的土地上,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厚愛,而今的“花兒”離我們的鄉愁、離我們的家園越走越遠。
筆者以為,“花兒”作為一種大眾化的文化形態,推介、交流、創新和發展固然很重要,但保持其原真性更是重中之重。對于“花兒”,政府文化部門時刻要做到“兩手抓”,一手抓“花兒”的推介、交流與發展,一手抓“花兒”的挖掘、保護與傳承。從“花兒”的推介、交流與發展來看,“花兒”演唱基本都純用當地方言,也有地區方言,還有一種“風攪雪”“花兒”(漢語與某少數民族語夾雜)等,這種演唱方式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外地人對“花兒”的了解和認知,如果演唱時沒有字幕的介紹,僅憑唱腔是很難聽懂唱詞的,所以為了有利于“花兒”的對外推介宣傳和傳播,用普通話演唱“花兒”是必要的選擇。我們知道,過去盛行在農村的廟會或“花兒”會,都是各地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民間活動,在農村有著悠久的歷史,影響廣泛而深遠,歌手演唱的“花兒”曲令絲毫沒有摻雜“添加劑”,是一種很自然的來自于山間田野的原生態美妙曲令。因此,對于那些民間老“花兒”藝人、“花兒”傳承人、草根“花兒”歌手來說,他們就要守護好這一方家園,養育好這一方水土,傳承好這一方傳統曲令,更多地肩負起挖掘、保護與傳承傳統“花兒”的擔當使命。傳統“花兒”要靠這些人去保護和傳承,政府文化部門要大膽鼓勵和培養他們用當地或地區方言演唱,以使“花兒”豐富多彩的曲令、唱詞受到保護與傳承;高等院校的藝術系、音樂系,對于如何推進普通話演唱“花兒”,要積極地探索和實踐,摸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普通話教學“花兒”的路子,以使“花兒”在各種學術論壇、文化交流活動中被廣泛認知,積極培養一批用普通話演唱、教授“花兒”的專業骨干人才;專業文藝院團的專業歌手或聲樂演員,理應承擔起用普通話演唱“花兒”的使命,讓專業歌手更多地學會用普通話演唱“花兒”,這樣,一來便于“花兒”的對外交流傳播,二來便于外地人認識和了解“花兒”,以促進“花兒”在更大范圍內的推廣和認知。同時專業院團要以“走出去”的理念,汲取當地其他優秀的民族民間藝術品種與“花兒”藝術相結合,創作打造一些具有濃郁時代氣息和創新意識的舞臺“花兒”劇,促進與省內外、國內外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使“花兒”在更高的舞臺空間大放異彩,以推動和活躍“花兒”藝術的舞臺。endprint
三、“花兒”講座與培訓:使“花兒”歌手將走向千人一面、千人一曲的死胡同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將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發展提到議事日程。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指出:“在五千多年文化發展中孕育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突出優勢,對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以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培養各地文化骨干為主要目的的“三區”文化建設項目相繼在各地落地生根,有效地推動了當地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工作,也培養了一大批民族文化骨干人才。
“花兒”作為具有幾百年傳承歷史的傳統優秀文化,得到了我省各地政府的極大關注和重視。“講座花兒”“培訓花兒”,以及一些媒體舉辦的“大擂臺花兒”等,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甚至“花兒”已走進校園,其初衷都是為了挖掘、傳承“花兒”藝術,培養“花兒”人才。殊不知,參加這些“花兒”講座、培訓、大擂臺的聽眾或參與歌手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甚至有的根本不識字,而主辦方邀請的授課、點評老師和評委基本上都是高校或某一領域的教授、專家、學者或音樂家、作曲家等等,他們講座、培訓的內容不外乎就是學院派的發聲技巧和理論觀點。這樣一來,對于受訓的歌手來說,他們不僅似有“牛刀宰雞”的感覺,甚者將他們推向同一條死胡同:千人一曲、千人一面的境地。
由政府參與主導的“花兒”講座和培訓給城市群眾文化帶來了一股“新鮮血液”,對帶動城市經濟社會和諧發展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對推動“花兒”的繁榮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作用。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花兒”講座和培訓卻在無意中脫離了“花兒”生長的土壤,剝奪了“花兒”多樣性發展的空間。因而對“花兒”藝術的傳承與保護也僅僅停留在理論化的文字或口頭形式上,這一現象將使“花兒”的曲令與演唱風格走向單一,扼殺了“花兒”的多樣性特點。一些教授、專家、學者講授的內容更多地集中在歌手們似懂非懂的聲樂專業知識方面,諸如歌唱呼吸練習、自然聲區訓練等發聲方法上。這雖然對一些發聲困難的歌手有一定的幫助,但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專業的發聲講授,致使“花兒”的豐富性遭到嚴重破壞,“花兒”從多樣性進一步趨向同一性。如果我們的“花兒”講座和培訓,一直以這種聲樂專業知識的講授方法將“花兒”講座和培訓持續下去,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花兒”歌手不管在發聲方法上,還是在曲令的掌握與演唱方法上,都將出現千人一面、千人一曲的不良現象。不同“花兒”歌手唱出的“花兒”風格、曲令和基調基本都一致,同出一轍、千人一口,“花兒”也將最終走向死胡同,直至消亡。
筆者知道的我省老一輩某著名“花兒”歌手,曾擁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是青海“花兒”歌手中的佼佼者,后來進入音樂學院深造之后由于深受學院派理論和演唱方法的影響,后來基本不會唱“花兒”了,唱的“花兒”不土不洋,在“花兒”演唱上難有作為,最終從“花兒”的舞臺上徹底消失了。本來一位很優秀的“花兒”歌手,卻將自己先天性的好嗓音,葬送在了專業聲樂知識的束縛中。還有青海“花兒”電視大擂臺等一些“花兒”比賽,人們對此也褒貶不一,不管怎樣,它在“花兒”新秀的選拔和推出優秀歌手方面做出的成績是不能否定的,但也無可避免地存在很多問題。從基層海選到決賽,一直是那幾位不變的評委,觀眾對此頗有微詞不說,更多的還是難逃刻板化、程式化、武斷化、人情化等。“花兒”講座和培訓,評委專家以學院派的音樂理念來講授、評判、點評,使“花兒”越來越走向所謂“民(花兒)通”化的路子,與“花兒”的傳統元素背道而馳,越走越遠。未能達到發現人才和傳承、保護“花兒”的初衷。
“花兒”本是田野之風,散發泥土氣息,是一種自然的原始的天籟之音,如果一味地灌輸聲樂的專業發聲方法,久而久之將脫離“花兒”的原始土壤,成為一種既不像“花兒”又不像通俗歌曲的另類歌曲,結果將“花兒”自由發展的空間和原生態元素摒棄,甚至抹殺,使一些掌握原始傳統“花兒”曲令的歌手也被同化,呈現出“花兒”歌手演唱或掌握的曲令重復而且單一的現象,最終出現千人一面、千人一曲的現象。筆者以為,作為官方的“花兒”講座和培訓等,盡量請一些“花兒”老藝人,言傳身教,將“花兒”最傳統、最本質、最原始的東西,講授好、保護好、傳承好,再請一些中學語文老師或大學中文系、地理系、歷史系的老師,更多地從“花兒”歌手文化程度低的角度出發,有針對性地進行識譜、文學常識、地理、歷史知識等方面的普及。只有這樣“花兒”才能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保持多樣性。
四、“花兒”品牌與實踐:探索符合“花兒”可持續發展的路子
國家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戰略為“花兒”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怎樣去繁榮發展“花兒”藝術,怎樣把“花兒”保護好、傳承好,并推向省內外、國內外,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艱巨而緊迫的任務。如何在時代發展中發揮自身優勢,發揚光大“花兒”藝術?我省有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實踐。
“花兒”雖然普遍受到青海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但由于它長期生長在民間傳統而保守的土壤之中,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傳統觀念、傳統倫理道德規范等的束縛,難以突破窠臼,進而阻礙了“花兒”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花椒樹上你嫑上,你上時樹枝權掛哩。莊子上到了時你嫑唱,再唱哈阿爺們罵哩”,這種對“花兒”既喜愛又懼怕的思想在民間根深蒂固,“花兒”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地開放在山野之間,很難登上藝術的殿堂。進入新世紀以來,中華傳統文化有了空前的繁榮與發展,2006年我省以大通“老爺山花兒會”、互助“丹麻土族花兒會”、民和“七里寺花兒會”、樂都“瞿曇寺花兒會”為代表的四大“花兒”會相繼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花兒”列入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為了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認定、記錄、建檔等措施予以保存,對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花兒”在這一歷史文化背景下插上了飛翔的翅膀,如今,就青海來說,真正讓“花兒”登上大雅之堂的非西北五省(區)“花兒”演唱會莫屬。endprint
2004年,西北五省(區)“花兒”演唱會對“花兒”的打造、對歌手的培養、對“花兒”品牌的樹立,可以說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探索和實踐。當年,青海省文化館力排眾議,通過多種渠道,將首屆西北五省(區)“花兒”演唱會放在具有悠久“花兒”演唱歷史的西寧南山舉辦。盡管一開始他們已經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實施中還是要面對經費不足、歌手缺乏、理念落后等諸多難題。如何讓“花兒”走出田野,在青海主流文化中生存并贏得發展機遇,成為他們面臨的兩大考驗。后來,在省廳的大力支持下,他們緊緊圍繞轉變觀點、突破思想、引資打造、培養歌手和加強管理等,依據“花兒”的自身特性和廣大群眾喜愛“花兒”的實際需要,在打造“花兒”品牌活動上,大膽創新,在內部建立了以目標管理為主要內容的“花兒”工作部,以傳統“花兒”與創新相結合、以老歌手與培養新人相結合的管理模式和運作方式,在三個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一是成立“花兒”工作部。按照“發展花兒,助推群文”的基本理念,在全省范圍內篩選“花兒”歌手,以傳承人、優秀歌手帶動活動,推出“花兒”新秀,全館上下一盤棋,有效地組織實施了首屆至第十三屆西北五省區“花兒”演唱會,為打造“花兒”品牌總體目標奠定了基礎。二是探索性地推行了歌手簽約制。按照用工不養人的辦法,推動歌手以“花兒”創收致富,走出山村走進城市,通過積極不懈的努力,當年就核定在冊歌手達三十余人。三是初步建立了與“花兒”發展相適應的發展模式,一個以“花兒”演唱、“花兒”理論研究和“花兒”應用研究為前提,依靠“花兒”老歌手帶頭、積極培養優秀歌手、大力挖掘“花兒”新秀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模式和運作方式基本形成。截至目前,西北五省(區)“花兒”演唱會在冊歌手達兩百余人,培養歌手近千人。
“花兒”品牌建設經過近十幾年來的探索和實踐,大大激發和提高了廣大歌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煥發了“花兒”演唱的生機和活力,開辟出了一條“花兒”致富的新途徑。省城西寧的“花兒”茶園,不僅解決了農村務工人員的就業問題,也有效地推動了“花兒”的傳承和發展。西北五省(區)“花兒”演唱會充分發揮出中心城市向全省示范、引領和輻射的作用,已成功舉辦了十三屆,成為西北地區參加歌手最多、演唱曲令最多、演唱水準最高、規模最大、人氣最旺、最具影響力的“花兒”演唱活動,可以說是青海“花兒”創新發展的里程碑,為“花兒”藝術的繁榮發展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有近百萬群眾參與活動,規模空前,在西北乃至國內久負盛名,“花兒”品牌實踐使“花兒”有了歷史性的文化新地位。先后推出了索南孫斌、才仁卓瑪、彭措卓瑪、汪黎英、向國安、雙虎妹等一大批有實力的新生代“花兒”歌手;“花兒”理論研究工作不斷推進,業內有老中青專家學者出版了《青海花兒大典》《青海花兒論集》《青海花兒藝術志》《河湟花兒大全》《青海花兒曲令大全》等一批“花兒”研究專著以及音像制品300余個品種,填補了青海“花兒”研究的空白,使“花兒”藝術從底層的民間行為,登上大雅之堂,上升為學術層面,促進了“花兒”的進一步發展;“花兒”的舞臺劇創作也呈現出高端化和多元化,先后推出了《六月六》《雪白的鴿子》《山水相依花兒情》和正在編排之中的《阿哥的白牡丹》等一大批“花兒”舞臺劇優秀作品,使“花兒”藝術從田野走向舞臺,走向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這一切使“花兒”增加了新的藝術沖擊和感染力。截至目前,青海省有國家級“花兒”傳承人5名,省級“花兒”傳承人14名,在冊“花兒”歌手300余名,其中在省內外頗具影響力的歌手有30余名。
如今,以西北五省(區)“花兒”演唱會為主導的“花兒”演唱活動,在青海大地上如雨后春筍般崛起,我們欣喜地看到,青海“花兒”演唱活動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空前興盛,遍地開花。各地每年舉辦的大小“花兒”演唱會達百處,也相繼成立了青海紅興“花兒”藝術團、互助縣白氈帽“花兒”藝術團、互助縣丹麻土族農民“花兒”藝術團、青海玉葵“花兒”藝術團、西寧百姓大舞臺“花兒”藝術團、大音“花兒”合唱團等數十個“花兒”團隊。“花兒”在新的時代有了新的地位,歌手的演出場次和收入逐年增加,提升了“花兒”在海內外的影響力。創作、研究、演唱形成了老中青齊頭并進的良好局面,他們在傳承發展“花兒”藝術、活躍和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的同時,帶動了各地旅游業的迅速發展和地方經濟的快速崛起。
魚、青蛙和漁夫
一
漁夫來到河邊捕魚,青蛙嚇得往水里跳。
水中的魚一見了,心里說:“這個人在岸上,大概準備捕捉青蛙了。”
漁夫把網撒到了河里,魚和青蛙都被網住了。漁夫把魚一和青蛙都丟進了漁簍里。
漁簍中的臺一自言自語說:“真是太不幸了,我是受到了青蛙的牽連才被捕進網里的。”
自以為是,其實不是。很多事情發生在身上,自己看上去覺得是偶然的,其實是一種必然。
二
漁夫來到河邊捕魚,青蛙嚇得往水里跳。
水中的魚說:“青蛙真聰明,跳進水里,可以無憂了。”
漁夫把網撒到了河里,魚和青蛙都被捉到,丟進了漁簍里。
青蛙嘆息說:“原來以為岸上不安全,想不到河里也不安全。”
自以為是,其實不是。逃難的地方,不一定就平安無事。
三
漁夫來到河邊捕魚,青蛙嚇得往水里跳。
魚說:“河里真是個好地方,青蛙也躲進水里來了!”
魚和青蛙都被漁夫捕捉到了。
魚說:“水里也不是很安全的,我為什么要生長在水里呢?”
青蛙說:“水里也不是很安全的,我為什么要往水里逃呢?”
漁夫自言自語說:“不是水里和岸上決定你是安全,還是不安全,而是你所處的角色,決定你是安全還是不安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