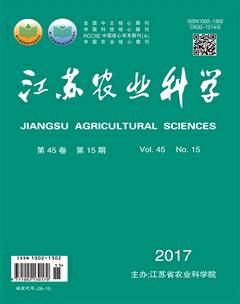雜交水稻種子萌芽與稻穗萌芽的內源激素變化
周述波 賀立紅 賀立靜
摘要:對雜交水稻親本金23B和V20B進行實驗室種子的發芽與田間栽培誘導稻穗萌芽試驗,研究2個發芽率差異顯著的品種在不同階段種子發芽與稻穗萌芽過程中其內源激素的變化。結果表明,種子萌芽與稻穗萌芽生理差異不是受內源激素中單一激素赤霉酸(GA3)與脫落酸(ABA)在種子內的絕對含量決定的,而是種子內多種內源激素協同作用的結果,(GA3+IAA)/(GA3+IAA+ABA)(其中IAA為生長素)越大的品種越易萌芽,易發芽V20B的比值大于金23B,而ABA/(GA3+IAA+ABA)越大的品種,越易抑制萌芽,不易發芽金23B的比值大于V20B;田間稻穗萌芽內源激素的變化及其他生理過程比實驗室種子萌芽的生理過程更為復雜。
關鍵詞:雜交水稻;種子;稻穗;萌芽;內源激素;生理差異;協同作用
中圖分類號: S511.01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15-0054-03
種子萌發是植物生長發育的開始,雜交水稻種子的萌發需要的外界環境條件是適宜的溫度、光照、水分、空氣,可近年來,隨著育種工作者對新品種選育的加快,在雜交水稻制、繁育過程中,經常可見田間稻穗萌芽的現象,尤其在南方,遇高溫多雨天氣,水稻稻穗的萌芽,會引起種子產量降低,品質下降,年平均稻穗萌芽率在2%~5%,有時高達60%以上[1-2]。許多研究者認為,此現象歸因于雜交水稻親本在制、繁種過程中內源激素的變化打破了種子休眠,導致田間稻穗萌芽。本研究通過選取發芽差異顯著的金23B與V20B保持系種子進行田間栽培與浸種發芽試驗,觀察在人工模擬陰雨環境下誘導稻穗萌芽過程中與實驗室條件下種子發芽過程中內源激素的變化,通過內源激素含量的比較,以探索不同階段不同品種間與種子發芽難易程度相關的內源激素變化規律,以期為農業生產上尋找抑制稻穗萌芽的植物生長調節劑提供理論與應用基礎。
1材料與方法
1.1材料
選取由湖南農業大學雜交水稻研究所提供的發芽差異顯著且生育期接近的2個雜交水稻親本品種金23B和V20B,前者為不易稻穗萌芽品種,后者為易稻穗萌芽品種。
1.2試驗方法
1.2.1室內種子萌芽材料的培養
選取充實飽滿、大小一致的金23B、V20B種子,用3%次氯酸鈉消毒15 min后,蒸餾水沖洗5次,在25 ℃條件下于暗處浸種處理24 h,然后挑選50粒種子,置于墊有含濕潤濾紙的培養皿中,重復3次,在型號為RQX-300的人工氣候光照培養箱[溫度(30±1)℃,相對濕度85%±5%,光照度93.6 μmol/(m2·s),光照時間 12 h]中培養,分別于浸種24 h后、培養24 h(浸種后48 h)和48 h(浸種后的72 h)時取樣進行內源植物激素的測定。
1.2.2大田稻穗萌芽材料的培養
試驗于2015年在湖南農業大學雜交水稻研究所試驗基地的稻田中進行,選取 7.52 m2 作為一小區單位,4月28日移栽于大田,每個小區植稻苗225穴,行株距為20.0 cm×16.7 cm。小區隨機區組排列,3次重復,采取同大田生產相同的管理方式。
齊穗后27 d,隨機選取田間水稻移栽于RQX-300的人工氣候光照培養箱[溫度(30±1)℃,相對濕度(90±5)%,光照度93.6 μmol/(m2·s),光照時間12 h]中進行培養,為讓水稻模擬處于陰雨環境中,每天共補噴750 mL清水,每次250 mL,分早中晚3次噴灑,共培養72 h,研究培養24、48、72 h 時稻穗萌芽中內源植物激素的變化。
1.2.3內源植物激素的測定
植物激素提取與測定參照王若仲等方法[3]。
2結果與分析
對V20B與金23B于實驗室內進行種子發芽試驗與田間培育后進行模擬陰雨環境稻穗的萌芽試驗,可知2個階段種子內源激素含量的變化。
2.1內源GA3含量的變化
由圖1、圖2可知,田間稻穗萌芽階段在培養的48、72 h 內源GA3含量遠遠大于種子萌芽階段培養24 h(即浸種后 48 h)與48 h(即浸種后72 h)的GA3含量。不同品種內源GA3含量變化規律比較,種子萌芽階段,V20B內源激素的含量在浸種的24 h與培養的24 h均小于金23B,其變化呈不斷上升趨勢;而在稻穗萌芽階段的內源GA3含量在培養的24、48 h 均大于金23B,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變化規律,金23B在2個萌芽階段中內源GA3含量變化均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變化規律。
種子與稻穗萌芽率見表1:實驗室內萌芽率在培養 24 h(即浸種后48 h)與48 h(即浸種后72 h)遠遠高于田間稻穗在培養48、72 h時的萌芽率,稻穗種子內源激素GA3含量卻不低于實驗室內種子;不同品種比較,V20B實驗室與大田2個階段萌芽率均大于金23B,而內源GA3含量在2個不同階段則不一樣,表明種子萌芽難易程度與萌芽率不是受內源GA3含量單因素作用,應與激素間平衡作用有關。
2.2內源IAA含量的變化
由圖3、圖4可知,實驗室內種子的發芽與田間稻穗萌芽在這2個不同時期比較,發現2個品種的IAA含量變化規律不同,V20B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變化趨勢,金23B則呈不斷上升的趨勢;V20B材料中IAA含量在實驗室條件下浸種24 h與培養24 h、大田條件下培養24、48 h均高于金23B,表明IAA含量與不同品種發芽差異、種子發芽難易程度有一定的相關性。
2.3內源ABA含量的變化
由圖5、圖6可知,種子萌發階段內源ABA含量呈不斷升高的變化規律,而稻穗萌芽階段,V20B內源ABA含量不斷降低,金23B則呈先升后降的變化趨勢。金23B的內源ABA含量在種子萌芽階段明顯大于稻穗萌芽階段,V20B在種子培養的24、48 h比稻穗萌芽培養的48、72 h階段也要高。許多研究認為,抑制種子萌發的主要物質與種子ABA含量密切相關;而本研究發現,稻穗萌芽階段中金23B種子的ABA含量反而比實驗室離體種子萌發的ABA含量低,可知稻穗萌芽比種[CM(25]子發芽過程更復雜。不同品種在2個不同階段比較發現,endprint
除種子萌芽階段培養48 h外,其余時間V20B內源ABA含量均低于金23B,可知不同品種間種子發芽難易與內源ABA含量有很大關系,ABA含量高的品種不易發芽。
2.4內源激素的比率
植物激素對植物的生長發育起十分重要的調節作用,而同一種植物激素在植物生長發育中起不同的作用,不同植物激素對植物的生長發育起促進與拮抗作用,植物的生長不是單一激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受多種激素的協同作用[4]。
由表2、表3可知,在種子發芽階段與稻穗萌芽階段,并非種子中GA3含量越高,或IAA含量越高種子越易萌芽,而是取決于(GA3+IAA)/(GA3+IAA+ABA)的大小,V20B在實驗[JP2]室和大田條件下種子萌芽率均大于金23B,2個時期中(GA3+IAA)/(GA3+IAA+ABA)前者均大于后者,而ABA/(GA3+
IAA+ABA)則前者小于后者,表明不同品種種子萌芽難易程度取決于促進型的植物激素或抑制型的植物激素占種子內激素總量的比值,促進型植物激素(GA3+IAA)所占的比例越高或抑制型內源激素ABA含量越低的品種越易發芽。
3結論與討論
種子萌芽受內外因子共同作用,外因主要有溫度、光照、水分含量與氣體等多因素的外界環境條件,內因主要為種子的特性如種皮、胚等[5]的休眠,種皮物理性阻礙、不透水透氣、種皮中發芽抑制物質存在等,胚未完成生理后熟、胚中發芽抑制物存在等。田間稻穗種子的萌芽更是受多因素的調節,其生理變化過程比種子萌芽更為復雜,稻穗萌芽除有種子萌芽的生理規律,還受稻株母體的生理代謝與調控影響,與穗部結構對種子的萌動等[6]均有關。
朱美榮等認為,小麥穗萌芽在生理上主要歸因于籽粒內部長時間存在較高濃度的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較高活性與種子萌發相關的酶如α-淀粉酶多酚、氧化酶、過氧化物酶等,以及高內源GAs含量、低ABA含量等特征。其中,α-淀粉酶活性與內源激素含量對穗萌芽與種子發芽起決定性作用[7]。
本研究發現,內源植物激素對不同品種、不同階段的種子萌發起重要的調節作用,種子萌發受內源激素影響,但不是單一激素含量在種子中起作用,實驗室條件下V20B種子萌芽率比金23B高,但是內源GA3含量在前期2個檢測時期V20B低于金23B;實驗室條件下種子的萌發與田間稻穗萌芽期相比,萌芽率種子萌芽階段高于稻穗萌芽階段,而GA3含量稻穗萌芽階段卻不低于種子萌芽階段,這與李銘等認為解除種子休眠、促進萌發與GAs含量密切相關[8],馬煥普通過對蘋果種子層積后期解除休眠、讓其萌發過程中發現有大量GA3累積結論[9]不一致。這可能與不同品種種子對GA3敏感性有基因型差異,小麥籽粒胚乳對GA3不敏感的品種不易形成穗上發芽,對GAs敏感的品種容易發生穗上萌芽有關[6],Griffiths等研究發現敲除GAs受體GID1A、GID1B、GID1C后種子不能萌發[10],表明GAs與種子萌發相關,但并非是其在種子內的含量多少而決定種子萌發的難易程度。而在雜交水稻親本種子萌芽與稻穗萌芽過程中內源激素GA3與IAA的含量之和的比率卻是引起不同品種種子在不同階段萌芽難易程度的主要原因。
ABA對種子萌發主要起生理抑制作用,許多學者認為ABA對誘導休眠起正調節作用,Matakiadis等通過對擬南芥的ABA代謝缺陷型突變體的研究發現,編碼ABA 8′-羥化酶的基因CYP707A1、CYP707A2失活會增強種子的休眠性[11-12],Kucera等發現內源ABA含量下降可解除種子休眠[13],一定濃度的ABA可抑制GAs在種子內所起的生理作用,能抑制α-淀粉酶基因的表達和其酶的活性,并誘導特殊蛋白如α-淀粉酶抑制蛋白的形成[7],ABA對未成熟胚或休眠成熟胚中α-淀粉酶-1的表達能起抑制作用[14]。徐成彬等認為,穗上發芽率與籽粒內源ABA含量之間的相關性不顯著,種子休眠與萌發是脫落酸、乙烯、赤霉素和細胞分裂素等植物激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5]。本研究發現,種子萌發與稻穗萌芽過程不是由1種激素含量決定的,而是受激素間的平衡與協調相互影響,品種間發芽難易程度取決于種子內促進型植物激素GAs與IAA之和占種子內激素比例或ABA所占的比例大小。
參考文獻:
[1]張靜,林澤川,曹立勇,等. 水稻種子穗發芽與休眠性遺傳研究進展[J]. 核農學報,2013,27(8):1136-1142.
[2]王麗萍,彭欣怡,程琴,等. 水稻穗發芽與種子休眠研究現狀[J]. 農業研究與應用,2015(4):49-53.
[3]王若仲,蕭浪濤,藺萬煌,等. 亞種間雜交稻內源激素的高效液相色譜測定法[J]. 色譜,2002,20(2):148-150.
[4]蕭浪濤,王三根. 植物生理學[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
[5]謝坤,白靜,王效睦,等. 水稻種子休眠性的研究進展[J]. 作物雜志,2015(5):6-10.
[6]楊麗娟,盛坤,董昀,等. 小麥新品系抗穗發芽特性研究[J]. 華北農學報,2015,30(4):145-149.
[7]朱美榮,張如標,王蓓蓓,等. 小麥穗發芽生理及調控途徑研究進展[J]. 金陵科技學院學報,2010,26(2):49-54.
[8]李銘,陳曉麟. 單穗升麻種子的后熟與萌發研究[J]. 重慶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2,19(1):62-65.
[9]馬煥普. 用GC-MS檢測蘋果種子層積過程中內源MeJA、GA3、GA4和GA7的變化[J]. 植物生理學報,1996,22(1):81-86.
[10]Griffiths J,Murase K,Rieu I,et al.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GID1 gibberellin receptors in Arabidopsis[J]. The Plant Cell,2006,18(12):3399-3414.
[11]Matakiadis T,Alboresi A,Jikumaru Y,et al. The Arabidopsis abscisic acid catabolic gene CYP707A2 plays a key role in nitrate control of seed dormancy[J]. Plant Physiology,2009,149(2):949-960.
[12]Okamoto M,Kuwahara A,Seo M,et al. CYP707A1 and CYP707A2,which encode abscisic acid 8′-hydroxylases,are indispensable for proper control of seed dormancy and germination in Arabidopsis[J]. Plant Physiology,2006,141(1):97-107.
[13]Kucera B,Co H A,Leubner-Metzger G. Plant hormone interactions during seed dormancy release and germination[J]. Seed Science Research,2005,15(4):281-307.
[14]孫果忠,張秀英,閆長生,等. 葡萄糖和ABA對小麥胚萌發過程中α-淀粉酶表達的調控[J]. 華北農學報,2009,24(1):44-48.
[15]徐成彬,吳兆蘇. 小麥收獲前穗發芽的生理生化特性研究[J]. 中國農業科學,1988,21(3):14-2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