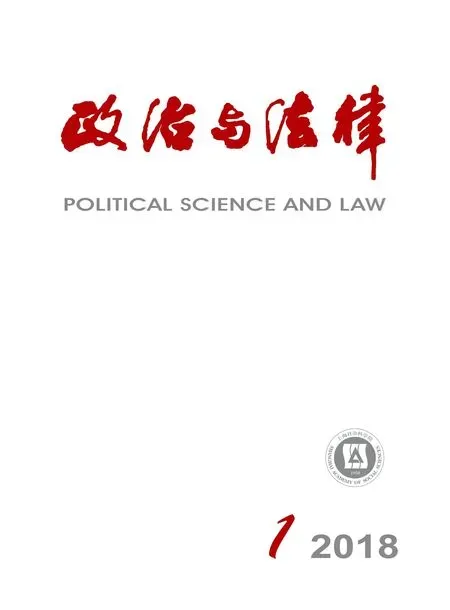論公共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及其適用困境消解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論公共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及其適用困境消解
賀大偉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對公共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法律屬性的認識是厘定航空運輸合同糾紛中承運人責任的重要問題。我國法并未明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對此存在不同的觀點。應從“條件”的法律涵義與航空運輸合同的法律結構等角度出發,合理認定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鑒于運輸總條件具有格式條款之特征,結合國內運輸條件中所慣常規定的航班延誤及取消、客票超售等特別條款備受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爭議,以及國際運輸條件中存在的承運人單方指定合同適用準據法等情況,此類條款是否對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效力構成法理障礙,應當予以論證。應當利用我國《民用航空法》正在修訂的寶貴契機,適時在法律中明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是航空運輸合同的主要內容這一法律屬性。
公共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特別條款;客票超售;公約排他適用條款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民航業的快速發展,公共航空運輸服務領域的法律糾紛日漸增多,做為航空法領域特有的概念,公共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受到司法實務界和法學理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在實踐層面,航空運輸服務合同案件的數量在航空法律糾紛中的占比持續提升,*中國民航運輸協會法律委員會對近年來針對國內航空承運人的近千例航空糾紛案例進行歸類、總結和分析,編寫了《中國民航法律案例精解》一書,在其精選的86個案例中,航空運輸合同履行中產生的合同之訴(包括航空旅客運輸合同和航空貨物運輸合同)和侵權之訴(主要包括航空運輸旅客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共計48個案例,占比高達55%。參見中國民航運輸協會法律委員會編著:《中國民航法律案例精解》,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特別是航班延誤、客票超售、行李破損或遺失等問題幾乎成為航空承運人與消費者之間的“死結”,此類糾紛主要涉及運輸總條件對各方權利義務的事前調整,承運人往往舉證其運輸總條件以對抗對方的請求,各法院對其法律效力的認定并不一致,更未形成統一認定標準。在學理層面,對于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若干基礎性法理問題仍未完全達成共識,包括由航空承運人單方發布的運輸總條件在航空法、合同法上應如何定性,其與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ICAO)主導的“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系列國際公約,*國際民航組織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1944年為促進全世界民用航空安全、有序發展而成立,總部設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是191個締約國(截至2011年)在民航領域中開展合作的媒介。2013年9月28日,中國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的國際民航組織第38屆大會上再次當選為一類理事國。以及與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IATA)發布的運輸條件之間應當界定為何種類型的適用關系;*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是一個由世界各國航空公司所組成的大型國際組織,1945年12月18日在加拿大正式登記注冊成立,總部設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執行機構位于日內瓦,其目標在于統一全球各航空公司經營中的技術、商業、監管等共同事項。作為市場主體的承運人發布的運輸總條件與作為行業主管者的中國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中國民航局)發布的四項運輸規則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認定;*這四項運輸規則指中國民用航空局(原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發布的四件部門規章:《旅客、行李國內運輸規則(2004年修訂)》(CCAR-271TR-R1);《旅客、行李國際運輸規則(1998年生效)》(CCAR-272TR-R1);《貨物國內運輸規則(1996年修訂)》(CCAR-275TR-R1);《貨物國際運輸規則(2000年生效)》(CCAR-274)。對于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中航班時刻、航班延誤及取消、客票超售、拒絕和限制運輸、承運人責任限制等特殊規定與航空消費者權益保護之間的沖突應如何規制等。這些問題的核心均在于清晰界定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進而為航空運輸服務活動、司法實踐乃至民航業立法提供理論支撐。
二、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法律屬性之厘定
公共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在學理上又稱“運輸共同條件”、“一般運輸條件”等,實踐中各航空承運人的表達也并不盡一致。*參見《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國內/國際旅客、行李運輸總條件》、《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國內/國際運輸條件》、《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國內/國際運輸條件》。筆者認為,運輸總條件一般是指由公共航空服務提供者事先制定的規范承運人與消費者因公共航空運輸服務而產生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文件。僅就名稱而言,“運輸總條件”應當作為一種泛稱而存在,且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做更進一步的區分。根據航空承運人提供運輸服務的不同類別與屬性,運輸總條件可以區分為航空旅客、行李類運輸條件(以下簡稱:旅客/行李運輸條件)和航空貨物類運輸條件(以下簡稱:貨物運輸條件);根據航空承運人提供航空運輸服務的不同航段,運輸總條件可以區分為航空旅客、行李/航空貨物國內類運輸條件(以下簡稱:國內運輸條件)和航空旅客、行李/航空貨物國際類運輸條件(以下簡稱:國際運輸條件)。*“國際航空運輸”與“國內航空運輸”的區分由《華沙公約》(1929)即被確立,但是全球范圍內的城市國家理論上只存在國際航空運輸活動。我國《民用航空法》第107條明確區分了“國內航空運輸”和“國際航空運輸”,由于法律制度上的差異,我國大陸飛往我國港、澳、臺地區的航班事實上按照國際航空運輸規則處理。
(一)關于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法律屬性的主要觀點
長期以來,學理界與司法實務界對于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及其適用一直存有不同的觀點。
1.合同說
在航空運輸實踐中,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常由航空承運人事先統一擬定,并在其與旅客/貨主正式簽署航空運輸服務合同之前以特定方式告知對方。*筆者于本文中所稱的“貨主”為行業內的泛稱,包括航空貨物托運人、收貨人及付款人等,而非僅指航空貨物所有權擁有者。在航空承運人的相關聲明之中,多數承運人一般都將運輸總條件視為航空運輸服務合同的組成部分,賦予其合同的地位及屬性。在航空法學界,部分學者針對司法裁判中的爭議,積極主張在立法層面賦予運輸總條件以航空運輸服務合同(或其主要/核心內容)的法律地位,*參見郝秀輝:《論“航空運輸總條件”的合同地位與規則》,《當代法學》2016年第1期;趙勁松:《航空運輸總條件法律地位路在何方?》,載楊惠、郝秀輝主編:《航空法評論(第4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1-97頁。但是,對于運輸總條件與航空運輸合同之間的關系,仍存有一定的爭議。主張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合同說的學者大都認為運輸總條件構成了航空運輸合同的主要內容,但是對于客票的地位和航空運輸合同其他內容的界定并無完全一致的認識。
在主張合同說的研究者中,有一部分人持部分條款無效觀點。持此觀點者基本以承認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合同地位為前提,同時認為總條件由承運人單方面事前發布,屬于格式合同,對于其內容有屬于我國《合同法》第40條所規制的免除提供格式條款者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等格式條款的,應屬無效。例如,國內多家承運人在其運輸總條件中所規定的“退票僅限原出票處辦理”的機票不能異地退票規則就曾為理論界和實務界所批判;*由于民航業內承運人對代理人管理乏力,為避免代理人借旅客退票的方式侵害航空承運人的利益,此類條款被絕大多數承運人吸納進入其運輸總條件中,甚至還引發過要求旅客跨國退票的糾紛與訴訟。此外,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還曾對某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中關于規范旅客支付與承運人出票行為關系的“系統產生票號后即為支付成功”的條款判決無效。*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25394號民事判決書。目前,我國民航行政主管部門對于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管理,采取國內運輸條件需經批準并公布方可生效、國際運輸條件需經備案方可生效的制度,那么,對于履行了中國民航局報批與備案程序而生效的運輸總條件中的部分條款經由法院做出無效判決后該如何處理,值得探討。
2.業務文件說
我國《民用航空法》等民航領域的立法并未明確界定公共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致使國內部分航空承運人以中國民航局先后發布的四項運輸規則為藍本來制定其運輸總條件,并將其視為承運人內部管理過程中的一種業務文件來對待,這樣,運輸總條件僅成為承運人業務操作規則的文本匯編,無法發揮規范航空承運人與旅客/貨主之間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功能。之所以有觀點將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作為一種業務文件,與我國民航業多年的改革背景密切相關。1949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航業歷經了從“軍隊領導為主”到“軍轉民、企業化”、從“政企合一”到“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從“機場與航空公司分設”到“航空公司重組與機場屬地化管理”等一系列改革,航空承運人在真正轉變為市場主體之前,曾做為政府的生產部門而存在,中國民航局發布的四項屬于部門規章性質的運輸規則,也先后在此背景下出臺,并為國內航空承運人所廣泛采納。這樣,部分承運人至今仍將其運輸總條件視為企業自身為落實中國民航局四項運輸規則的內部業務文件。
3.國際商業慣例說
持國際商業慣例說者認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特別是超售、拒載等特別條款)系經由國際航空運輸實踐形成的商業慣例,且為各國航空公司和旅客/貨主所認可并遵循,主要體現在IATA版本的運輸條件中。作為國際航空公司間的行業性民間組織,IATA在履行“統一國際航空運輸規則”的職能中,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制定運輸條件(conditions of carriage)范本供會員采用。為了彌補1929年《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以下簡稱:《華沙公約》)的不足,*《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于1929年10月12日簽訂于華沙,于1933年2月13日起生效,習慣上稱為《華沙公約》。《華沙公約》共分5章41條,主要規定了發生飛行事故之后的賠償責任,對國際運輸的定義、運輸憑證和承運人責任作了明確的規定。該公約規定,在運輸中由于承運人的過失使旅客、托運人或收貨人遭受損失,承運人應承擔賠償責任。IATA先后發布了多個版本的運輸條件,目前最新的版本是1986年IATA承運人服務會議(passenger service conference)通過的“建議措施(recommended practice)”第1724號文件,即《運輸條件(旅客及行李)》,*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IATA先后提出過多個版本的國際航空運輸“標準條件”。在旅客運輸方面,1927年IATA制定出了第一個版本的《維也納條件》;1933年修訂后成為《安特衛普條件》,1949年制定出新的《百慕大條件》,1953年在檀香山又加以修訂。內容涉及客票、行李、票價、定座、值機、拒絕與限制載運、航班時刻、退票、行政手續等。這一文本雖無強制性的法律約束力,但鑒于IATA在全球航空業界的廣泛影響力,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航空承運人均廣泛借鑒了該版運輸條件的相關內容。這也使得各承運人的運輸總條件常被視為全球航空業界的商業慣例而存在。
有部分學者認為,鑒于目前各國法院對于運輸總條件的認識停留在彈性合同條款階段,在裁決航空運輸案件時,仍然是有選擇性的適用,因此,解決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法律屬性的問題的路徑在于將IATA發布的運輸條件上升為剛性國際慣例,而非停留在目前的建議版本階段;其具體的路徑在于通過制定運輸總條件標準范本,在行業內廣泛推廣適用,使其最終走向剛性國際慣例。*參見前注⑧,趙勁松文。
4.回避適用說
在我國,有部分法院在審理航空運輸合同糾紛案件中,對于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采取回避認定其法律屬性的態度,通過直接援引我國《合同法》或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方式回避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存在,*參見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川民申字第1955號民事裁定書。該案系因航班延誤引起,歷經一審、二審和再審程序。在該案件審理中,四川航空公司做為承運人向法院舉證其運輸總條件之相關內容,法院在裁判中并未采納,法院直接援引我國《合同法》之相關規定進行裁判。甚至對于中國民航局發布的《旅客、行李國內運輸規則》(CCAR-271TR-R1)、《旅客、行李國際運輸規則》(CCAR-272TR-R1)、《貨物國內運輸規則》(CCAR-275TR-R1)、《貨物國際運輸規則》(CCAR-274)等行政規章也采取回避態度。*參見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5181號民事判決書。
(二)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合同屬性的初步厘定
目前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對于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功能的認識尚不盡一致,尤其對于其法律屬性仍存有較大爭議,筆者認為,從航空運輸總條件的實踐功能及其內容的法律特征分析,將其定為航空運輸合同的主要內容較為合理。
1.從“條件”的法律涵義分析航空運輸總條件
在大陸法系民法理論中,“條件”做為法律行為之附款而存在,即當事人對于法律行為效果之發生、中止或消滅所加的限制。傳統民法上,法律行為之附款包括條件和期限,分別構成了附條件的法律行為和附期限的法律行為,因此,大陸法系民法理論中的條件,“謂構成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之一部,使其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系于客觀的不確定的將來之事實”;*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頁。換言之,此處條件的內容是將來客觀上不確定的事實,效力在于決定法律行為之效力。具體到合同領域中,當事人依自由意志創設彼此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條件制度則是在此基礎上對合同風險進行分配的一種方式,構成了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限制。以附條件合同法律制度為例,條件的成就與否視為確定合同效力發生、中止或消滅的關鍵。在大陸法系民法理論中,條件有多種類別,如明示條件和默示條件、先決條件和解除條件、肯定條件和否定條件等;違法的、不符合社會公共秩序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條件一般無效。
合同法中常有所謂“合同交易條件”之概念,此處的“條件”是否即為傳統大陸法系法律行為理論中之“條件”,理論上存有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作為契約內容的“交易條件”應與作為法律行為附款的“條件”相區別,前者如買賣契約中關于標的物、價金、清償時間及地點等條款。*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頁。大陸法系合同法中所使用的“交易條件”或“一般交易條件”與“格式合同”的稱謂相通,具體而言,其在德國法中稱為“一般交易條件(Allgemeine Gesch?ftsbedingungen)”,在法國法中稱為“附合契約(contract d’ ad-hesion)”,*同前注,史尚寬書,第14頁;王澤鑒:《債法原理(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頁。在日本法中稱為“普通條款”,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中稱為“定型化契約”,在英美法多稱為“標準條款(standard article)”或“格式條款/不公平契約條款(unfair contract terms)”。在立法例上,德國曾于1976年制定《一般交易條件法》,其內容涉及對一般交易條件的界定、一般交易條件納入具體合同的要件、對一般交易條件內容的法律控制、該法的適用范圍以及一些過渡性規定等。2002年1月1日,隨著《德國債法現代化法》的正式生效,《一般交易條件法》被廢止,其主要內容被納入《德國民法典》“債法編”,成為該編第二章“以一般交易條款形成意定債務關系”(置于“債法編”原第二章“因合同而產生的債的關系”之前)。*參見陳衛佐譯注:《德國民法典(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頁。可見,此處所指的“一般交易條件”與作為法律行為之附款的“條件”并非指同一概念,前者實質為格式合同本身,后者為限制法律行為之效力的一種將來客觀上不確定發生的事實。
筆者認為,“條件”這一概念雖為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立法廣為采納,但卻源自普通法,且在英美法上常作為合同中已明確的條款內容而存在。英美法中的合同系由當事人雙方的各種聲明和承諾所構成,其性質和重要性各有不同,這些已被明確為合同條款的聲明和承諾可以依當事人的主觀意愿以及違反時的效力區分為兩類,即“條件(condition)”與“擔保(warranty)”。其中,條件被視為對事實的陳述或承諾,此種陳述或承諾是合同不可缺少的條款,且為當事人高度重視,如果陳述不真實或者承諾得不到履行,則無過失當事人可將違約當做拒絕履行,并可使自己免除進一步履行合同的義務,甚至可以解除合同并請求損害賠償;相對而言,擔保處于次要的地位,意指當事人對某事加以明確或隱含的陳述,這種陳述可以成為合同的一部分,或者雖然是合同的一部分,但對于合同的明確目的而言是次要的,并且無過失當事人在對方違反擔保的情況下,無權拒絕履行合同,只能要求損害賠償。由此可見,在普通法上,條件構成合同之“基礎(root)”,擔保僅為合同中次要的條款。*參見楊禎:《英美契約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版,第289頁。
進一步而言,英美法上條件制度所包含的范圍要比大陸法更為廣泛。英美法系對于條件之于合同作用的認定有所謂“對流條件(concurrent condition)規則”或“共存條件規則”,即合同一方的履行被推定為另一方履行其義務的先決條件;換言之,通常意義上的條件是一方當事人承諾履行合同的重要前提。在這一意義上,條件承擔著類似大陸法上履行抗辯權的功能,*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頁。此處所謂的條件也被稱之為“承諾的條件”。*[英]A.G.蓋斯特:《英國合同法與案例》,張文鎮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頁。在特殊情況下,條件才具有了“附屬的條件”的特征,即合同的生效與否取決于條件是否得到履行,此時的條件才具有了與作為大陸法系“法律行為之附款”的條件相通的功能與涵義。從這一意義出發,將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中所述之“條件”歸入“承諾的條件”更為恰當。
本質上,“條件”在英美法系合同法中的地位與其在大陸法系法律行為理論框架內的不同功能,也與兩大法系早期對于合同屬性的不同認識密切相關。大陸法系學者對合同的屬性秉持“協議說”,認為合同是意定之債的主要發生原因,*同前注,王澤鑒書,第6頁。本質上是當事人之間合意的結果,是一種協議。英美法系對合同屬性持“承諾說(允諾說)”,*比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1條規定:“合同是一個允諾或一系列允諾,違反該允諾將由法律給予救濟,履行該允諾是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所確認的一項義務。”轉引自韓世遠:《合同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合同被視為是一種承諾或允諾,合同法所規范的乃是包含一個或者多個允諾的交易,此種承諾或允諾為一方向他方當事人作出負擔某種行為或不行為的義務的表示,進而引起受允諾人的信賴。*作出允諾表示的人是為允諾人(promisor),接受允諾表示的人是為受允諾人(promisee)。將合同視為是一種允諾,最早是由英國的歷史習慣和訴訟程序所決定的,*在中世紀的英國法中,并沒有形成合同的概念。最早出現的,只是所謂的“允諾之訴”,即當允諾人違背其允諾時,受允若人有權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執行諾言。參見王軍:《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同時也與英美法將不當得利與無因管理等關系作為“準合同”對待的做法有聯系;從強制執行允諾的本質來看,無論是“作為履行的強制執行”還是“作為激勵的強制執行”,*[加]本森:《合同法理論》,易繼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都表明此種允諾并非是一種單純的允諾,而是建立在交易基礎之上的允諾。由于“允諾說”容易導致將合同視為單方允諾的誤解,因此,一些英美法學者也開始完全采納大陸法關于合同的見解,將合同視為一種協議,*英國《牛津法律大辭典》將合同定義為“二人或多人之間為在相互間設定合同義務而達成的具有法律強制力的協議”。參見《牛津法律大辭典》,牛津法律大辭典翻譯委員會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頁。由此,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兩大法系在合同的概念上有逐步接近的趨勢。*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2.從航空運輸合同的法律結構分析航空運輸總條件
從航空運輸合同的法律結構分析,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契合航空運輸合同的基本要素,發揮著系統規范因航空運輸活動產生的私法關系的積極功能,為航空運輸服務合同的核心內容。
現行我國《民用航空法》并未規定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亦未界定“航空運輸合同”的內涵與外延,其第111條、第112條和第118條分別規定了客票是航空旅客運輸合同訂立和運輸合同條件的初步證據、行李票是行李托運和運輸合同條件的初步證據、航空貨運單是航空貨物運輸合同訂立和運輸條件以及承運人接受貨物的初步證據。然而,學理上在討論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地位時,常視其為航空運輸合同的主要內容或核心內容,但是對于航空運輸合同的具體構成卻存在爭議。*主張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合同說的學者大都認為運輸總條件構成了航空運輸合同的主要內容,但是對于客票的地位和航空運輸合同其他內容的界定并無完全一致的認識。參見郝秀輝:《論“航空運輸總條件”的合同地位與規制》,《當代法學》2016年第1期;吳建端:《航空法學》,中國民航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頁。我國《合同法》第288條規定:“運輸合同是承運人將旅客或者貨物從起運地點運輸到約定地點,旅客、托運人或者收貨人支付票款或者運輸費用的合同。”比照這一規定,狹義的航空運輸合同可以被界定為航空承運人將旅客或者貨物從起運機場運輸到約定機場,旅客、托運人或者收貨人支付票款或者運輸費用的合同。*廣義范圍內的航空運輸合同除涉及起降機場之間的航空運輸服務外,還包括承運人或其代理人通過自有或第三方物流體系所提供的門到門等物理距離上的延展服務等。
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合同法立法例中,運輸類合同作為一種重要的合同類別,一般不以承運人與每位旅客/貨主簽訂正式的運輸合同為必要形式,而常以承運人向旅客/貨主交付客票/航空貨運單為運輸合同成立要件。這是基于交易效率和交易便利的考量。航空運輸雖然不簽訂具體的協議,僅通過旅客購票和托運人通過承運人填寫貨運單來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之間不存在航空運輸合同。應當說,航空運輸合同至少由運輸憑證、承運人發布的運輸總條件、其他相關法律文件等三部分內容構成。
首先,航空運輸憑證作為航空運輸合同訂立的初步證據而存在。航空運輸憑證是航空運輸中使用的來確立旅客、托運人、收貨人和承運人及其代理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文件。以航空旅客運輸合同為例,我國《民用航空法》第111條規定:“客票是運輸合同訂立和運輸合同條件的初步證據。”該條明確了客票的性質、法律地位以及承運人違反客票規則的法律后果,它是參考1955年關于《修訂1929年華沙公約的議定書》(以下簡稱:1955年《海牙議定書》)第3條第2款的規定和我國航空運輸發展的實際情況擬定的。*1955年《海牙議定書》對1929年《華沙公約》做了部分修訂,修訂后的《海牙議定書》第3條第2款約定:“在無相反的證明時,客票應作為載運合同的締結及載運條件的證據。客票的缺陷,不合規定或遺失,并不影響載運合同的存在或效力,載運合同仍受本公約規定的約束。如承運人同意旅客不經其出票而上機,或如客票上并無本條一款(三)項規定的聲明,則承運人無權引用第二十二條的規定。”航空旅客運輸合同一般于旅客購入客票時即告成立,客票只是此項合同訂立的初步證據,而不是合同本身。初步證據是普通法中的概念,普通法把證據分為初步證據(prima facie)和最終證據(conducive evidence)。初步證據又稱表面證據,它表明了對其所證明的事務的基本肯定,其作為證據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即證明力已經達到法院可以據以認定事實、進行判決的程度,但是如有相反的、更為確鑿的證據予以相反事實證明時,初步證據可以被推翻,因此,初步證據的證明力是初步的,而不是最終的。最終證據的證明力是完全充分和有效的,其他證據不能否認最終證據的證明力。兩相比較,最終證據可以否認初步證據,初步證據不能否認最終證據。
其次,承運人運輸總條件集中載明了航空運輸合同各方當事人的主要權利義務。我國《合同法》第293條規定:“客運合同自承運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另有交易習慣的除外。”然而,客票等運輸憑證并非運輸合同本身,因為它缺少對旅客與承運人等合同當事方之間權利義務內容的規范。運輸總條件集中載明了航空運輸合同當事方的具體權利與義務,以及違反合同時當事方(尤其是承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為航空運輸這種特殊的、典型的交易事件創造了一個固定的“法律框架”,從而避免每次訂立同類型的單個合同時總是去重新確定合同的內容和樣式,實質上涵蓋了航空運輸合同的主要內容。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作為一種格式的“一般交易條件”,因此為航空公司提供了一個履行航空運輸合同給付的統一的“法律基礎”,進而公司載明此類內容的聲明成為嗣后訂立的各個航空運輸合同的組成部分。*參見前注,郝秀輝文。
再次,其他相關法律文件構成了航空運輸合同的重要補充。如果說客票是航空運輸合同訂立的初步證據、運輸總條件是航空運輸合同的主要或核心內容的話,運輸合同究竟還包含哪些法律文件,也需進一步厘定。有學者認為,在“航空運輸總條件”之外,航空運輸合同還包括其它可適用的重要規定和條件,其中包括特殊旅客的運輸規定、電子設備的限制使用規定、在飛機上引用酒精飲料的規定等。*參見前注,郝秀輝文。筆者認為,在航空運輸合同中,除客票、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之外的其他法律文件,不應僅僅局限于上述文本,從類型化的角度分析,應當包括可以引起航空法及航空運輸當事人民商事法律關系產生、變更、中止、終止的特殊法律文件;此種特殊法律文件所調整的事宜并未由承運人運輸總條件所規范,并且既可以是承運人與旅客/貨主之間的特殊民商事性質的約定,也可以是相關的法律、行政法規等。從這一角度而言,構成航空運輸合同重要補充的此類特殊法律文件是動態變化的,并且需由個案具體認定。
此外,有學者認為在航空運輸合同所涉的系列法律文件中,“運輸條件”與“合同條件”也不盡一致。*參見前注,吳建端書,第160頁。航空運輸中的合同條件一般是指機票(指紙質客票、非電子行程單)背面和貨運單背面規定的條款,確立了航空承運人與消費者和顧客之間的基本合同關系,而運輸條件所涉及的內容則要廣泛得多,也構成了航空運輸合同的組成部分。以IATA決議為例,IATA除了通過第1724號決議(即“運輸條件”)之外,還曾發布過文件名為《旅客機票——通知與合同條件》的第724號決議,該決議規定了機票上必備的各種通知和合同條件。筆者認為,鑒于現行我國《民用航空法》并未單獨使用運輸總條件的表述,而只是于第111條、第112條和第118條分別就客票、行李票及航空貨運單對于運輸合同及合同運輸條件的證據效力做了規范,且第118條雖然使用了“運輸條件”的表述,但從文義解釋的角度看,應與第111條和第112條所使用的“合同運輸條件”做并列理解,可見,現行我國《民用航空法》并未嚴格區分“運輸條件”與“合同條件”。
(三)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核心內容應由國內立法確立
由于運輸合同是附和合同,其條款一般是由承運人一方擬定而不是由當事人雙方協商確定,旅客/貨主只在是否訂立合同上有自由選擇權。為了防止承運人一方將不公平條款強加給旅客/貨主,國際航空運輸公約和各國立法基本都把運輸合同條件法定化。“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有關合同雙方權利義務的條款在法理上屬于締約國之間法定的國際航空運輸合同條件的核心內容(包括國際公約轉化為國內立法中有關合同雙方權利義務的規定),在IATA運輸條件廣泛影響之下由各承運人自行發布的運輸總條件之合同屬性理應為立法所認可。
當前,我國《民用航空法》正在修訂過程中,作為突出承運人在民航市場中的主體地位、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重要方式,從立法角度賦予航空運輸總條件以合同地位正當其時,我國《民用航空法》應當在我國《合同法》及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運輸合同、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法律規制的立法體例基礎上,明確厘定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通過運輸總條件平衡承運人與旅客/貨主的權益,構造符合航空業慣例的新型契約關系,并鼓勵承運人通過優化其運輸總條件的方式來推動民航市場承運人之間的良性“制度競爭”,*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制度是經濟領域的一個內生變量而非外生變量,制度在長期經濟增長的分析中至關重要;人類的理性選擇(在具體的約束條件下)將創造和改變諸如產權結構、法律、契約、政府形式和管制這樣一些制度,這些制度和組織將提供激勵或建立成本與收益,最終這些激勵或成本與收益關系在一定時期內將支配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進而言之,在市場競爭及競爭法領域,市場主體之間的制度競爭較其行為競爭更為重要。參見[美]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載[美]羅納德·H·科斯等著,《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劉守英等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75-184頁。以進一步推動民航業的市場化發展以及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的現代化。*2016年8月8日,中國民航局發布了《關于〈民用航空法〉修訂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并于此版《民用航空法(修訂征求意見稿)》第107條規定:“本法所稱航空運輸合同是航空運輸承運人將旅客、行李或者貨物從出發地點運輸到目的地點,旅客、托運人或者收貨人支付票款或者運輸費用的合同。公共航空運輸企業公布的運輸總條件是航空運輸合同的組成部分。”
三、“特別條款”適用困境的消解:以“客票超售條款”為例
從學理乃至立法層面明確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是航空運輸合同主要內容的法律性質,所面臨的現實難點問題之一就是各承運人在其運輸總條件中對航班超售、航空旅客黑名單、航班延誤及取消等是否與合同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制格式條款以及保護消費者知情權等規范相沖突。在學理層面,此類問題凸顯了航空運輸與傳統運輸方式之不同;在司法實踐中也是爭議的熱點和難點。從類型化角度考慮,筆者于本文中擬將運輸總條件中的此類條款統稱為“特別條款”,并擬就此類特別條款對于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為運輸合同主要內容之法律屬性的影響做探析。
(一)特別條款對運輸總條件法律效力的影響
做為對“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航空承運人責任認定規則的重要補充,各航空承運人發布的運輸總條件所調整的內容一般涉及航空運輸服務鏈條的全部程序,以旅客運輸條件為例,內容一般涉及客票、票價與稅費、定座與購票、航班超售、乘機、行李運輸、航班時刻、航班延誤及取消、拒絕和限制運輸、退票、客票變更、旅客服務、第三方服務、航空器上的行為、行政手續、連續承運人、損害賠償責任等。其中,航班超售、航班延誤及取消、拒絕和限制運輸、行政手續等條款頗具特殊性。一方面,盡管我國《合同法》將運輸合同單列為一種有名合同予以規范,同時,鑒于民用航空業高風險、高科技含量、高成本、高敏感度、低收益的獨特產業特征,決定了包括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在內的航空運輸合同與傳統運輸合同存在著若干重要差別,這往往是航空法與合同法邊界之所在,當客票超售、黑名單等有別于傳統運輸合同的事件發生之時,如何通過運輸總條件平衡承運人與消費者之間的契約關系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合同法上格式條款的產生對于增進交易、便利消費者至關重要,同時,因其由優勢企業一方所擬定而限制了合同自由,所以強制締約義務的產生可謂是對合同自由的一次修正與保護,即為了保障消費者的需求得到滿足和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法律規定,除非有正當理由,否則,格式條款提供者不得拒絕消費者的締約請求;具體到航空運輸服務中,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對于航班超售、黑名單等問題的界定是否屬于“法律規定的正當理由”的范疇,應慎重考量。基于此,如何認定此類特別條款的效力,對于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合同屬性的認定頗為重要。
(二)特別條款的適用困境
一般而言,在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中,客票超售條款往往作為特別條款之一為承運人所單方面設置。客票超售是目前國內實踐中約定俗成的說法,其英文是“overbooking”,中文譯意為“超定座”,指為了避免航班座位的虛耗、滿足更多旅客的出行需求,航空承運人往往會在某些容易出現座位虛耗的航班上進行超過航班最大允許座位數適當比例的客票銷售行為。
航班超售是為了避免座位虛耗。座位虛耗的原因主要包括:(1)旅客原因,又如由于旅客通過航空訂票的周期較長,在購買機票并訂好座位后,往往存在少量旅客最終未按約定時間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的情形,也即航空法上的“NO-SHOW”,或者旅客可能同時與多家機票代理聯系購票,各家代理都定座,無意中造成重復等;(2)代理人原因,比如航空公司代理人的虛假訂座等;(3)其他原因,比如旅客由于乘坐另一航空公司或同一航空公司的航班,由于航空承運人或天氣原因延誤而錯過銜接航班,或者航空公司不要求旅客“再證實”座位等。
航班超售具有一定的經濟合理性,被視為“飛機經濟學”的典型例子,但對于航空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極易造成侵害。一方面,各航空承運人都會實行一定比例的超售,規模越大、管理越先進的航空公司的超售范圍越廣,超售收益也越大;這些航空承運人會通過相關數據分析系統抽取歷年定座和離港數據,同時參考前期被延誤行程人數和補償費用,以決定是否對航班進行超售以及超售數量,且必須權衡合理超售和拒載兩者之間的利弊,找出一個既有效利用空位又能將拒載登機損失壓縮到最小的平衡點。*參見前注,吳建端書,第165頁。另一方面,由于超售極有可能造成航班旅客的溢出,致使部分旅客無法登機,在補救措施無法滿足溢出旅客需求的情況下,甚至產生承運人拒載等一系列問題。
基于此,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于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中超售條款的合理性始終存有爭議,其可以概括為“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觀點。“肯定說”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幾方面。首先,在產生原因方面,超售源自航空承運人為避免座位的虛耗以及滿足更多旅客出行的需求,而非基于承運人之主觀惡意,航空承運人基于市場競爭、運營成本、客源流失等考慮,對航班進行超售也符合國際航空業的售票慣例,且法律上對超售行為未予以明令禁止。其次,在控制措施方面,全球民航業對于適宜超售的航班及超售的比例都有明確的行業限制,而非承運人不受控制。再次,在補救措施方面,超售一旦發生后,承運人需針對溢出旅客及時采取尋找自愿者、盡快安排下一班航班、現金補救等措施,且此類補救措施需作為明示條款與超售條款一起列入運輸總條件中。最后,在責任認定方面,對于自愿接受補償金的溢出旅客,承運人一般會提供《非自愿棄乘及免責書》,其中載有“把賠償金視為棄乘而引起或可能引起的一切索賠要求、費用支出及損失的最終解決”等類似條款,從而在旅客與承運人之間形成了一份新的認定雙方責任的協議。*參見前注,吳建端書,第165頁;王立志、楊惠:《航空旅客權益保護問題與規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36頁。
“否定說”又可細分為“欺詐說”和“違約說”。“欺詐說”認為,航空承運人在旅客購票之時并未告知消費者關于客票超售情況,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進而影響了消費者的締約意愿,并客觀上造成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違背真實意愿訂立合同,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構成欺詐,因此應按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規定的“退一賠三”的罰則處理。*2010年11月,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工商管理分局對國內某航空公司開出關于機票超售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認為其對旅客黃某一行八人中兩人的機票超售行為違反了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誠實信用原則,剝奪了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賦予旅客的知情權,同時違反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第51條第15項的規定,構成了以欺詐方式超售機票的違法行為,責令該航空公司改正違法行為,并處以罰款5000元。此案是我國機票超售行政處罰的第一案。“違約說”認為,旅客自購票之時其已與航空承運人之間達成運輸合同,航空公司未按客票載明的時間和班次運輸旅客,即使已根據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但無法阻卻遲延運輸違約責任的構成,也屬于未按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應承擔承運人的違約責任,賠償因違約給旅客造成的經濟損失。*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滬一中民一(民)終字第1946號民事判決書。
由此可見,在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中,以航班超售為代表的特別條款,無論在學理上還是在實踐中,極易遭遇適用上的困境,這既源自航空產業與航空法相對于傳統運輸行業及其法律規則的特殊性,也與立法缺失和行業導向的模糊性有關,由此導致了此類糾紛案件司法裁判的非一致性。
(三)特別條款訂入運輸總條件的規制方式
應當承認,特別條款所規范的超售、拒載等是航空運輸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合法實踐,*參見美國運輸部消費者保護處的“Fly-Rights A Consumer Guide to Air Travel”,轉引自前注,吳建端書,第169頁。無論是IATA版本的“運輸條件”與“合同條件”,*IATA第724a號決議明確了該協會會員可以在機票上適用的有關超售的相關規則。還是“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的國際公約,都明確認可了航空運輸過程中客票超售、航班拒載、延誤及取消等行為作為航空業慣例的客觀性。從航空運輸合同角度來看,存在爭議的是此類行為作為特別條款載入運輸總條件的過程中,如何在保持條款合理性與必要性的同時,亦能有效維護航空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并通過運輸總條件在航空承運人與消費者之間構建平衡的契約關系。誠然,這一方面有賴于立法與行業主管機關的指引與規范,以及航空消費者對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相關規則的事前審查機制,另一方面也需進一步規范承運人在制定運輸總條件過程中的各項實體義務和程序義務。前者包括科學、合理制定各項條款尤其是特別條款的義務,后者包括承運人的告知義務等。具體而言,筆者認為,對特別條款訂入運輸總條件予以規制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方面。
1.立法對于特別條款擬約定事項的規制
在對客票超售、航班拒載、延誤及取消等特別條款具體規制規則的設置方面,立法的作用至關重要。應當在充分了解此類問題的法律屬性基礎上,廣泛借鑒歐美等航空業起步較早的國家和地區的立法規則,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規范,引導承運人在運輸總條件中合理設置特別條款,使承運人與旅客之間的格式合同兼顧我國《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的要求和航空運輸產業的特殊性。目前,在超售等行為的規制領域,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14篇第250節所規定的“超售規則”(14 C.E.R Part 250-OVERSALES)和歐盟《關于航班拒載、取消或長時間延誤時對旅客補償和協助的一般規定》(以下簡稱:歐盟261/2004條例)最具代表性。
美國的民航運輸總量長期居于全球首位,其航空法律體系由國際公約、國會立法、司法判例、行政規章等構成。在國際公約層面,根據美國最高法院判例,適用公約的航空運輸,排除國內法律的適用(包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另外,由于國會的立法具有較強的原則性,美國運輸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美國聯邦航空運輸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等行政機構制定了更為詳細的行政規章,以使國會立法具體化,并確保其有效執行。DOT于1978年就發布了專門調整有關超售和拒絕登機的規則,并沿用至今,即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14篇第250節之“超售規則”(14 C.E.R Part 250-OVERSALES),適用于因持有經確認的定座和客票的旅客超過航班實有座位,致使航空公司無法全面提供原先確認預定的座位的情形。DOT超售規則重點對于非自愿拒載登機遴選程序(priorities procedure)中旅客權益的保護和航空承運人的義務做了重點規范,細致規定了遴選自愿者與非自愿者的程序和方法、補救的措施、補償的標準、支付的方式、補償資格的獲得等一系列具體規則。同時,DOT對于超售規則的實施情況也予以監督,要求航空承運人如實報告超售和拒絕登機情況,并將其匯總在航空旅游消費者報告(Air Travel Consumer Report,ATCR)中。美國機票超售規則自1978年生效以來能沿用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確立了超售規則的基本框架外,還建立了賠償金額的通貨膨脹自動調整機制等。*賠償金額通貨膨脹自動調整機制,指由DOT每兩年對賠償金額進行審查,并根據城市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增長來計算最高賠償額的增幅。此外,DOT在執法方面也體現出了與航空承運人良好的互動性。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雖然超售規則在美國已實行多年,但是關于航班超售的合理性問題始終存有爭議。2017年4月,美聯航UA3411航班超售并暴力驅客事件發生以后,*2017年4月,越南籍旅客David Dao與妻子乘美聯航UA3411航班,由芝加哥飛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在航班登機后、起飛前David Dao被強行拖下飛機,致使其鼻梁骨折,失去了兩顆前牙,并有腦震蕩情況。事件發生后,全球航空業與消費者組織嘩然,關于航班超售合理性與否的爭論再起。最終,David Dao與美聯航達成和解協議,協議的具體內容和涉及的金額保密。有關機票超售的話題又掀起了新一輪爭論。然而,即使如此,由于美國航空運輸的法律體系相對較為完善,盡管航空公司的旅客運輸總條件中約定了極具爭議的客票超售等條款,但是一般而言,旅客在選擇航空承運人出行之前,需要根據法律的規定先了解和閱讀其“旅客須知”,如果旅客選擇購買了一家航空公司的機票,那么雙方合同達成,航空公司和旅客都要承擔自己的義務,以最終促使航空運輸市場的自由競爭。*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本土的許多低成本航空機票價格非常便宜,但出現超售不僅沒有補償,而且也無后續航班安排,從而在航空市場上實現多樣化的選擇與競爭,以使航空市場的旅客運輸交易更為公平且自由。
歐盟的航空業發展水平及其航空法也始終走在全球前列,在航空法律體系方面,除國際公約優先適用外,亦采取單獨立法的體例。在機票超售方面,歐盟早于1991年就頒布了《關于在定期航空運輸中建立拒載賠償制度的規定》(以下簡稱:歐盟295/91條例),之后,為了更好地保護航空旅客的權利,歐盟于2004年新修訂了歐盟261/2004條例,并完全取代了歐盟295/91條例。歐盟261/2004條例的主要內容是在旅客被拒絕登機、航班取消以及長時間延誤的情況下,確立如何對其進行賠償和協助的具體規則。該條例適用范圍為歐盟成員國境內機場出發的旅客,也適用于從第三國出發、前往歐盟條約適用的歐盟成員國內的機場且承運人為歐盟成員國內的承運人的旅客,除非該旅客在第三國內收到益處、賠償或獲得幫助。該條例將客票超售的后果即拒載劃分為自愿拒載和非自愿拒載,并規定了承運人的告知義務以及拒載后補償金的額度、標準與支付方式等,體現了歐盟對于航空旅客優先保護的強烈色彩。*除了歐盟261/2004條例之外,歐盟對于航空旅客權利的保護還包括:EC Regulation 1008/2008,要求航空公司在網站上對價格進行透明化公示;EC Regulation 2111/2005,要求承運人告知旅客航班實際承運人;EC Regulation 1107/2006,對殘疾旅客及其他行動不便旅客的保護等。然而,歐盟261/2004條例的內容因為與歐盟成員國在之前條約中的義務相沖突,并且與“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有關航空承運人責任中的第三國義務相沖突,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國際爭議。IATA曾就此提起訴訟,雖然最后訴訟結果是歐盟維持該條例的合法性,但國際航空業界尚未放棄重新審查該條例的努力。*The Queen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European Low Fares Airline Association v.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Judgment of the Court(Grand Chamber)of 10 January 2006,Case C-344/04.
截至目前,在航班超售問題上,我國民航法律體系內尚未有直接對其進行規范的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中國民航局消費者事務中心曾于2014年發布過作為行業標準的《公共航空運輸航班超售處置規范》(行業標準號:MH/T 1060-2014),并于2015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為國內首個直接針對航班超售問題而制定的文件,但由于該處置規范為推薦性行業標準,盡管對于各航空承運人具有參照意義,但實際上并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盡管如此,對照2006年我國機票超售第一案中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議函》,*2006年7月21日,旅客肖某以1300元的價格購買了南航CZ3112航班(北京-廣州)機票,在旅客到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南航告知由于機票超售的原因,CZ3112航班已經滿員,原告無法乘坐,于是南航為旅客肖某辦理了簽轉手續,但隨后簽轉航班也發生了延誤,南航方面又將旅客喚回,將其轉簽至南航CZ3110航班,并免費為其升艙至頭等艙(頭等艙機票價格2300元),當日22時39分,原告乘坐CZ3110航班頭等艙離港,此時距其原定起飛時間已過了近3小時。2006年9月,旅客肖某將南航訴至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最終判定雖然南航方面的行為并未構成欺詐,但未盡到告知義務,并判以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同時,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向當時的中國民航總局(現為中國民用航空局)和南航發出《司法建議函》,建議中國民航總局作為行業主管部門,能夠承擔起制定規則的責任,盡快制定航空客運機票超售的規章制度并指導航空運輸企業適用。這已是明顯的進步。如果我國《民用航空法》能夠以本次修訂為契機,在行業基本法中增加關于規范超售等行為及責任的相關條款,進一步明確承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將對完善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合同地位并且在維護航空消費者權益與保護航空業商業慣例之間做出理性平衡大有裨益。
2.承運人就運輸總條件特別條款的告知義務
2.1 出血型甲狀腺囊性結節新型硬化劑聚多卡醇微創治療后隨訪結果 15例結節術前平均體積(17.41±13.84)mL,治療后 1周、1個月、3個月超聲復查甲狀腺囊性結節的囊腔體積變化,囊腔逐步縮小,結節平均體積分別為(8.20±5.97)mL,(1.88±1.66)mL,(1.18±1.51)mL,術后 1個月及3個月復查,囊腔體積均較術前明顯縮小,兩者與術前囊腔體積比較,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在司法實踐中,承運人的告知義務往往成為法院對于運輸總條件中特別條款效力認定的爭議焦點,*參見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2014)官民一初字第1745號民事判決書、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法院(2015)歷城商初字第1082號民事判決書、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6762號民事判決書。基于此,筆者認為,在確認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為合同主要內容這一法律屬性的前提下,合理界定承運人的告知義務,對于運輸總條件中特別條款適用困境的消解尤為重要。
我國《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釋、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分別規定了格式合同提供者和經營者的告知義務,雖然二者在告知義務的范圍和違反告知義務時相對方的救濟途徑方面存在差異,*萬方:《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經營者告知義務之法律適用》,《政治與法律》2017年第5期。但是,相對而言,這兩部法律較之我國《民用航空法》對承運人告知義務的規定遠為充分,后者只規定了承運人就責任限額進行告知的義務。有鑒于此,建議在我國《民用航空法》修訂過程中,應當合理、科學界定承運人告知義務的邊界。
其一,告知的時間。從告知時間來看,航空承運人的告知義務主要集中在訂立合同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董念清:《論航空承運人的告知義務》,《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一般而言,航班超售、拒載、延誤等運輸總條件特別條款所約定的事項往往發生于合同履行之中,此時航空承運人固然需要承擔及時、合理的告知義務,并且立法及行業慣例對于此時的告知均給予了較為詳盡的規范,*以歐盟261/2004條款為例,該條例特別要求承運人在航班延誤等情況下就旅客的權利進行告知,具體為承運人應保證在值機柜臺以清晰易讀的方式展示包含如下內容的通知:如果旅客被拒載或旅客的航班被取消或延誤至少兩小時,請在值機柜臺或登機口索要權利書,特別是與賠償(補償)金和幫助有關的內容;承運人拒載或取消航班,應給受其影響的每位旅客提供一份包含本條例賠償金和幫助內容的書面通知;承運人也應向延誤至少兩小時的旅客提供同樣內容的通知;以書面的形式向旅客提供(本條例第16條規定的)國家指定機構的聯系資料等。此外,對于盲人和視力受損的旅客,承運人也需以合理的備選方式來告知。但此種告知在性質上屬于承運人就特別條款所規定事項的補救義務,相對而言,從航空運輸合同證成的角度分析,承運人在訂立階段就運輸總條件尤其是其特別條款的告知義務對于航空運輸爭議的定性往往更為重要。
其二,在告知的范圍方面,盡管航空承運人在其運輸總條件生效之后,往往會將其公布于所屬各售票場所、訂票網站等,并在客票/貨單背面記載其全部或主要內容,以履行承運人的基本告知義務,同時,旅客通過購買客票與承運人簽訂航空運輸服務合同之際,被承運人視為已接受運輸總條件之全部內容。但是,一旦圍繞特殊條款所約定的事項發生爭議,法院往往會以承運人對特別事項的告知“欠缺明確性和指向性”為由,*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6762號民事判決書。認定承運人未充分履行經營者的告知義務。筆者認為,所謂“欠缺明確性和指向性”,核心的指向為承運人告知范圍的特定性。我國《合同法》第298條明確將承運人的告知義務界定為“有關不能正常運輸的重要事由”和“安全運輸應當注意的事項”,前者與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中特別條款之事項較為契合,但也并非完全重合。筆者對于特別條款的界定側重于影響正常航空運輸的事項,但是對于廣義范圍內的航空業慣例(比如特價客票等不屬于上述兩項事項的特別事項)的告知范圍及其程度,在司法實務界仍存在不同認識。較為妥當的處理原則是,其一,僅根據行業慣例或者交易習慣,不能直接推定消費者對相關信息明知;其二,告知作為經營者的一種法定義務,不能僅因為消費者的知情而被豁免;其三,若以行業慣例之方式履行合同而免除或限制己方責任,則法院會要求經營者履行特殊的告知義務,即以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該等條款并按消費者的要求加以說明。*參見前注,萬方文。
四、承運人國際運輸條件中“公約排他適用條款”的法理依據
與國內航空運輸不同,國際航空運輸合同涉及到準據法的適用問題。我國《合同法》及我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對于我國涉外民商事合同的法律適用均采取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主、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為補充的原則。我國《民用航空法》第188條規定:“民用航空運輸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合同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這為我國國內航空承運人設定涉外航空運輸合同的準據法適用方法和模式設定了基本規則。我國絕大多數航空承運人均在其與旅客/貨主的國際航空運輸合同中明確約定了準據法。在航空承運人國際航空運輸條件中,這一適用模式常常被表述為“根據本合同進行的運輸,應遵守某某公約”。*參見《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國際旅客、行李運輸總條件》第16.13條、《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國際運輸條件》第17.4條、《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國際運輸條件》第19.4.1條。此即所謂“公約排他適用條款”。
在航空實踐中,目前國內絕大多數航空承運人在其國際運輸條件中選擇的準據法為1999年《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以下簡稱:《蒙特利爾公約》)。以對航空承運人責任體系中的賠償責任限額為例,我國多數航空承運人均要求約定“在旅客、行李運輸中,有關損害賠償的訴訟,不論其根據如何,是根據所在國法律、根據合同、根據侵權,還是根據其他任何理由,只能依據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規定的條件和責任限額提起”等類似內容。*參見《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國際運輸條件》第19.4.1條。問題在于,國內航空承運人在涉外航空運輸合同中單方面約定強制性適用《蒙特利爾公約》,是否對于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是一種違背,進而是否影響對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合同屬性的認定。相應地,承運人單方面在運輸總條件中約定排他性地適用《蒙特利爾公約》的法理基礎等問題也有待進一步探討。
(一)航空承運人單方面指定合同準據法的合理性
筆者認為,我國國內設立的航空承運人在其國際運輸條件中單方面指定適用某一公約,對當事人在合同準據法選擇方面的意思自治并不構成實質性法理障礙。現代航空運輸業為高度發達的規模化產業,承運人單方面提供的格式條款大大提升了交易效率,消費者與其以個別磋商的傳統締約方式已不適應,更無法就涉外航空運輸合同所適用之準據法進行單獨談判,因此,從交易習慣角度分析,旅客一旦付款并購得機票,即視為接受航空運輸條件并訂立航空運輸合同,也理應視為雙方當事人對選擇本合同適用的法律達成了一致。這一規則也為國際民航業所廣泛接受,并且在民航運輸實務中,雙方當事人對合同適用的法律另行協商選擇的情況很少發生。*按照IATA統一的票樣要求,承運人在客票上載明“根據本合同進行的運輸,應遵守某某公約”,旅客購得機票即視為接受承運人之運輸總條件,也視為雙方當事人選擇了該運輸合同適用的法律為某某公約。
(二)《蒙特利爾公約》排他性適用的法理基礎
目前國內多數航空承運人在其國際運輸條件準據法適用方面唯一指向性地適用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既是因為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原本就是對“華沙-蒙特利爾體系”承運人責任規則的重要補充,更源于“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國際公約排他適用的獨特性。
1.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系對“華沙-蒙特利爾體系”承運人責任規則的重要補充
回顧航空法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作為國際航空運輸規則體系在航空私法領域的重要成果,是航空承運活動中商業慣例規則化的體現。早在1903年萊特兄弟制造出第一架飛機“飛行者1號”并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成功首飛之前,作為人類探索“管理空氣空間的使用并使航空、公眾和世界各國從中受益的一套規則”的努力就已經開始。*Diederiks-Verschoor:An Introduction to Air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edition(October 1,2001):2. 事實上,早在1784年4月,法國即頒布過警方指令,規定除非事先獲得批準,否則航空活動不允許進行,以直接和排他性地針對蒙哥爾費兄弟的氣球試驗。這被視為航空法之濫觴。1889年,歐洲19個國家在法國巴黎召開了第一次討論航空法的國際會議。此外,法國法學家福希(Fauchille)于1900年就建議國際法研究院(The Institute Droit International)制定一部國際航空法典,成為“為數不多的法律進程走在技術之前(指1903年萊特兄弟首飛成功)的例子之一”。參見[荷]I·H·Ph·迪德里克斯-范思赫:《國際航空法(第九版)》,黃韜等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商業性航空運輸活動與各國航空立法活動的蓬勃開展,航空法無論作為國際法還是國內法,均具有了自己的獨特個性,并逐漸成長為新的部門法。與此同時,國際航空法的統一化運動也得到持續推進,統一航空運輸規則的成果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以1944年《國際民用航空公約》(《芝加哥公約》)為代表的航空公法,*《國際民用航空公約》于1944年12月7日在芝加哥締結,為國際民用航空的憲章性文件,也是包括國際航空運輸法在內的現行國際航空法的基礎,是目前國際上被廣泛接受的公約之一。《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巴黎公約》)的基礎為1919年《關于管理空中航行的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Aerial Navigation)》,以及1928年《泛美(或美洲國家間)商業航空國際公約(Pan-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ommercial Aviation)》(《泛美公約》)。《巴黎公約》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涉及國際民用航空活動的國際航空公約。解決了諸如空域主權、航空器國籍、統一規則便利空中航行、航空事故調查、遇難救助等方面的問題,形成“芝加哥公約體系”;*“芝加哥公約體系”還附屬了包括針對航空器上犯罪、非法劫持航空器及其它危害民航安全的數個國際公約。二是以1929年《華沙公約》為代表的航空私法,解決了諸如運輸憑證、航空損害賠償責任制度、航空運輸糾紛的關系法院和訴訟時效等,形成“華沙公約體系”。*“華沙公約體系”含《華沙公約》名下的一系列議定書,包括1955年《海牙議定書》、1971年《危地馬拉城議定書》、1975年《蒙特利爾四個議定書》等,此外,一般認為還應包括1961年《瓜達拉哈拉公約》、1966年《蒙特利爾協議》等。
1929年《華沙公約》旨在建立與詮釋一種主要原則來處理關于航空承運人對造成旅客、行李和貨物以及航班延誤損失所進行賠償的問題,以便使旅客/貨主進行航空旅行時可以知曉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統一規則來規制承運人的責任,與此對應的是承運人在知曉其自身責任承擔的前提下,可以對可能造成的損失做好事先安排。*參見前注,I·H·Ph·迪德里克斯-范思赫書,第109頁。然而,《華沙公約》僅涉及航空運輸規則的一部分,并不能覆蓋旅客/貨主與航空承運人在航空承運活動各個環節的所有規則。因此,由IATA主導的運輸條件對華沙體系提供了大量且重要的補充,以此作為彌補承運人以及旅客/貨主之間的合同安排規則。由于IATA從組織形式上是一個全球航空企業的行業聯盟,屬于非官方性質組織(實際上已具有半官方屬性)。其發布的運輸條件雖然并不必然具有強制性的法律適用力,但因IATA在全球航空業具有的廣泛影響力,其運輸條件也為全球范圍內的航空承運人所廣泛借鑒。
1999年5月30日,作為長期努力及各方利益妥協后的重要成果,ICAO于其總部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爾通過了《蒙特利爾公約》。作為《華沙公約》的最新發展,《蒙特利爾公約》在積極吸納華沙體系有益成果與國際共識的基礎上,旨在以其“現代化”后的責任規則“取代”支離破碎的華沙體系,在協調承運人與旅客利益的同時為當前國際空運實踐的發展提供法律保障。*董念清:《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對中國的影響》,《中國民用航空》2004年第1期。《蒙特利爾公約》目前已在包括中國在內的締約國之間取代已適用70余年的《華沙公約》及其議定書,進一步規范、統一了國際航空運輸私法領域的各項制度和規則。IATA于1986年通過的運輸條件也隨之做出了更新,截至目前已更新過多個版本。
2.“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國際公約排他適用的獨特性
航空承運人責任規則作為“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各公約的核心內容之一,一般涉及承運人的責任與義務范圍、責任人、“事故”術語、可賠償的損害、責任期間、責任的免除、損害賠償限制等內容。作為“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公約的共同、重要特點之一,該體系項下的公約規則具備有別于其他非公約規則的重要適用特點,即“排他適用屬性”,其基本含義是公約訴由、公約責任規則與公約管轄權規則在其規定的事項與范圍內具有一律排除適用國內法規則與使用其他任何規則的屬性與效力,從而使“華沙-蒙特利爾體系”下的公約規則得以獨占支配承運人賠償責任的認定。*鄭派:《國際航空旅客運輸承運人責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頁。在該書作者看來,“公約規則”涵蓋1929年《華沙公約》、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等七項公約文件項下的責任規則與管轄權規則,“非公約規則”包含通過納入承運人運輸條件而發揮作用的承運人間協議以及歐盟261/2004條例等國內立法中規定的承運人責任規則。“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國際公約排他適用的獨特性,具體體現于1929年《華沙公約》第24條、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第29條之規定。*1929年《華沙公約》第24條規定:“一、如果遇到第十八、十九兩條所規定的情況,不論其根據如何,一切有關責任的訴訟只能按照本公約所列條件和限額提出。二、如果遇到第十七條所規定的情況,也適用上項規定,但不妨礙確定誰有權提出訴訟以及他們各自的權利。”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第29條以“索賠的依據”為標題,規定:“在旅客、行李和貨物運輸中,有關損害賠償的訴訟,不論其根據如何,是根據本公約、根據合同、根據侵權,還是根據其他任何理由,只能依照本公約規定的條件和責任限額提起,但是不妨礙確定誰有權提起訴訟以及他們各自的權利。在任何此類訴訟中,均不得判給懲罰性、懲戒性或者任何其他非補償性的損害賠償。”這一規則的確立,既是基于國際航空運輸不斷發展的實踐對于國際航空運輸承運人責任規則統一化、一致性的客觀需求,也是“華沙-蒙特利爾體系”項下國際公約得以落地的必要保障,進而為國際航空運輸領域內公約訴由、承運人責任規則與管轄權規則等國際私法規則統一化建構奠定了基礎。
以國際航空承運人責任規則中的賠償責任限額為例。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是指發生重大的航空事故時,作為責任人的承運人可根據法律的規定,將自己的賠償責任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賠償的法律制度。這是對民法中一般民事損害賠償原則(即按照實際損失賠償的原則)做出的特殊規定,其目的在于促進航空運輸業和航空保險業的發展。我國《民用航空法》制定于1995年,彼時對于國際航空運輸中承運人的具體限額是參考1955年《海牙議定書》規定的以金法郎為單位的數額,以及1975年《蒙特利爾第2號附加議定書》規定的以特別提款權為單位的數額制定的,并體現于我國《民用航空法》第129條。我國于1999年加入《蒙特利爾公約》,《蒙特利爾公約》與我國《民用航空法》所規定之賠償責任限額制度的具體數額與計算規則均有不同,在我國《民用航空法》未修訂之前,國內航空承運人可依據我國《民用航空法》第184條之規定,通過在承運人國際運輸條件中以合同約定的形式適用《蒙特利爾公約》規定之賠償限額標準,來調整承運人與旅客/貨主在國際航空運輸過程中關于雙方權利與責任之相關約定。
五、結 論
做為規范航空運輸活動中承運人與旅客/貨主之間法律關系的重要載體,航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理應被立法尤其是我國《民用航空法》賦予相應的法律地位。盡管目前學術界和司法實務界對于運輸總條件的法律屬性仍存在不同的認識,但是將其定位為航空運輸服務合同的主要內容這一法律屬性具有相當的合理性。通過對承運人國內運輸條件中普遍存在的類似于航班延誤及取消、客票超售等特別條款的分析,以及對國際運輸條件中準據法適用條款合理性的論證,可以發現,盡管運輸總條件中的許多規則系承運人單方事先擬定,對于承運人與旅客/貨主的合同權利義務都具有重大的影響,但其具有相當程度的合理性,且需要立法或行政手段的同步規制,因此,對于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合同屬性的證成沒有實質性的法理障礙。同時,應利用我國《民用航空法》正在修訂的寶貴契機,適時在法律中明確承運人運輸總條件的合同屬性,以利于統一指導司法實踐。
TheStudyonLegalNatureofPublicAirCarrier’sGeneralConditionsofCarriageandtheResolutionofDifficultiesinItsApplication
He Dawei
For defining the carriers’ responsibility in air transport contracts’ disputes, keeping a clear-sighted view of the legal nature of public air carrier’s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is vitally important. However, the existing Chinese laws do not clearly regulate such legal nature, which caused many debates in academia and juridical practice. The legal nature of carrier's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shall be reasonally determined in light of legal connotation of conditions and legal structure of air transport contract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enjoy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ard terms, combining the situation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sputes in academia and judicial practice over special terms usually set out in the conditions of domestic carriage such as delay, cancellation of flight and overbooked passenages’ tickets and the applicable law is unilateraly appointed by the carrier in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carriage, discussion shall be made regarding whether such terms impose judicial barrier to legal effectiveness of the carrier’s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China sha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important opportunity of amending Civil Aviation Law to clarify the legal nature that the carrier’s geveral canditions of carriage are the main part of air transportation contract.
Public Air Carrier;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Special Clause; Overbooking; Exclusivity Clause of the Convention
DF934
A
1005-9512-(2018)01-0134-16
賀大偉,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專業博士研究生。
徐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