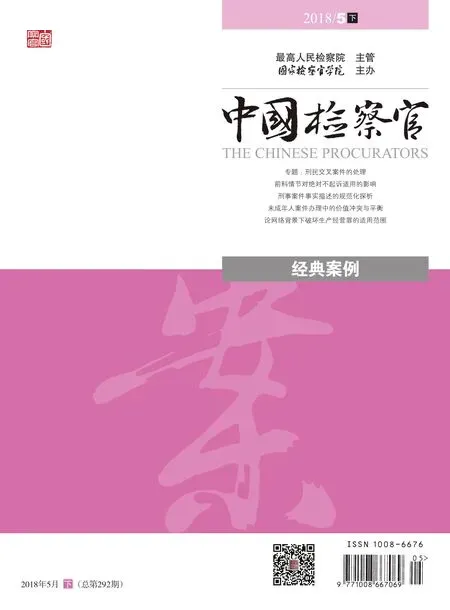美國環境公益訴訟: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
——以“自然資源保護協會訴迪克森郡案”為切入點
文◎李潔偉
田納西州迪克森郡(Dickson)因三氯乙烯(TCE)等工業化學品不斷傾倒,致使當地水源受到嚴重污染。2008年3月,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依據美國 1976 年《資源保護和回收法》(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規定的“公民訴訟”(Citizens Suits)條款,起訴田納西州迪克森郡政府及相關公司(以下簡稱“迪克森郡案”),2011年12月原被告雙方最終達成和解。[1]在美國環境公益訴訟中,此類訴訟案例以往并不常見。[2]就我國而言,近年來我國環境公益經歷了迅速的發展。根據《環境保護法》第58條、《行政訴訟法》第25條,只有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和檢察院才能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個人不能提起環境公益訴訟,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審理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檢察機關訴訟地位、法院審判程序及審判職責做出規定。至此,社會組織與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框架已經搭建完畢,“迪克森郡案”對于從理論和司法實踐完善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具有借鑒意義。
一、“迪克森郡案”的背景及進程
美國田納西州迪克森郡填埋場因三氯乙烯等有毒工業化學品經年滲入地表,造成填埋場周邊幾英里范圍內的地下水不能安全飲用。美國《資源保護和回收法》規定,對“導致或正在導致已發生的重大、實質性對健康或環境的損害”,任何人均可以提起訴訟;如果廢物處置導致了“重大的和實質性的危害”,可以通過提起“公民訴訟”來加以抵制。[3]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認為,迪克森填埋場所處理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化學物質,對人體健康及自然環境造成了重大的和實質性的危害,是迪克森郡地下水遭受污染的原因,迪克森郡政府和部分填埋垃圾來源企業應對上述污染問題承擔責任。[4]2008年3月4日,自然資源保護協會依據 《資源保護和回收法》“公民訴訟條款”起訴迪克森郡政府,之后又提交申請,追加ALP 照明產品公司(ALP Lighting Components,Inc.)、美國耐馬克公司(Nemak USA Inc.)以及州際包裝有限公司(Interstate Packaging Co.)為被告。2011年12月9日,原被告雙方在開庭前達成和解,和解協議同意設立補救基金,交由專家管理,以確保當地居民能夠獲得清潔的水源,并加強對三氯乙烯含量的監測。[5]
二、對“迪克森郡案”內容的評析
(一)“公民訴訟”條款是本訴訟案的基礎
公民訴訟,是指美國公民或團體對違反法定義務的污染者或怠于執法的環境保護行政機關,有權提起訴訟。[6]1970年《清潔空氣法》第 304條a款首次規定“公民訴訟”條款。[7]此后,美國國會將環境領域的公民訴訟條款復制到其他聯邦環境立法之中,使得公民訴訟成為美國環境立法中一項普遍適用的制度。“公民訴訟”規定在《資源保護和回收法》第7002節。[8]根據該條的規定,如果一個實體由于處置任何“固體或危險廢物”(solid or hazardous waste)而“可能”(may)對“健康或環境”產生“即將和實質性的危害”(imminent and substantial endangerment),則允許公民或團體提起訴訟。如果沒有《資源保護和回收法》中有關公民訴訟的規定,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就失去了提起訴訟的依據,只能轉而依靠其他法律實現救濟。[91]
從1976年《資源保護和回收法》生效至今,“公民訴訟”規定的內容不斷被美國各級法院的判例加以解釋和明確。在“緬因州人民聯盟訴萬靈科公司”案中,[10]法院在解釋“即將和實質性的危害”標準時,認為“合理情況是,只要因威脅而產生的傷害不是短期的,潛在的嚴重傷害不需要一定是緊急情況,并且此類威脅也不需要立即顯現嚴重的傷害后果”。同樣,在“紙業回收公司訴阿莫科石油公司”案中,法院認為“對‘健康或環境’的‘即將和實質的危害’僅需要表明存在受到威脅的傷害風險,而不是立即發生實際傷害”。[11]正如一些美國學者所言,美國法院在解釋《資源保護和回收法》“公民訴訟”條款中的一些術語時,傾向于采取寬松解釋的司法路徑。[12]
(二)環境保護與人權問題相結合
哈佛大學法學與國際發展協會(Harvard LIDS)在總結“迪克森郡案”時指出,本案與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提起的民權訴訟案存在關聯,這是案件的一個關鍵所在。迪克森郡居民多數為白人,涉案垃圾填埋場只占該郡面積很小的一部分,但居住在該區域的居民卻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主。這樣的差異使得本案一下就上升到了捍衛人權的高度,同時也為自然資源保護協會提供了強大的訴訟依據,而不僅僅局限于環境保護這一個維度。[13]
將環境保護與人權問題聯系在一起并非“迪克森郡案”的原創。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約三分之一的州憲法把環境權上升為一項基本權利,內容包括:(1)關于環境品質重要性的政策性宣示;(2)環境授權規范;以及(3)個體性的清潔、健康的環境權。[14]從理論上看,環境公益訴訟以純粹意義上的環境公益為保護對象,而環境私益訴訟系以受害人的人格權和(或)財產權因環境損害行為而受有損失作為理論依據,因而,二者并不存在交叉。而人權問題的出現,恰恰成了環境公益訴訟與私益訴訟的連接點,兩者在認定環境損害行為的成立與否方面具有共通性。
保護環境與保護人權具有關聯管轄。美國環保署(EPA)將“環境正義”作為一項公共政策,主張在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制定、適用和執行等方面,全體國民都應得到公平對待并能有效參與環境決策,而“環境正義”則是從政治上強調人權。[15]政治上強調人權通常從道德的角度展開論證,通過引起人們內心的“同類感”,而推論出保護環境的人權理論根基。[16]在美國司法中,將環境保護與人權問題捆綁在一起,將預防環境公益(繼續)遭受損害以及對已經造成的環境損害采取積極的補救措施,升華為保障人權的一部分,并與憲法權利相聯系,實際上是增強的環境問題的“可訴性”,將環境訴訟賦予執行法律、適用與解釋法律并生成新型權利、形成環境公共政策、促進社會變革等多種其他功能。
(三)通過和解實現訴訟目的
環境公益訴訟具有成本高、風險大的特征,訴訟過程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在“迪克森郡案”中,從案件發起、追加當事人直至首次開庭,已經過去三年多的時間。在“迪克森郡案”等美國環境公益訴訟中,原告謀求將爭議納入法院訴訟階段,并非希望借由法院判決實現“環境爭議”,也非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設計的初衷。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發起訴訟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借由啟動司法訴訟的方式,以司法權為后盾向對涉案政府部門、企業施加督促與威懾,促使其采取行動,以達到等同于通過法院才能夠獲得的救濟效果。[17]對于涉事的政府或企業而言,一旦作為被告進入環境公益訴訟階段,都可能因法院的不利判決而對其自身聲望和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所以也不希望啟動公民訴訟程序。2011年12月9日,原被告雙方最終達成和解,包括:(1)設立補救基金。由迪克森郡出資500萬美元設立救濟基金,以降低和消除已經發生的環境風險;(2)建立專家小組。由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和迪克森郡分別任命兩名專家組成,負責管理補救基金、劃定環境風險區、制定監測方案;(3)提供公共水源,確保所有受影響的居民能夠使用公共水源;(4)被告向自然資源保護協會支付律師費。[18]此時,原告與被告達成和解,不僅僅是相互妥協,也是實現公民訴訟產生督促與威懾效應的制度目的。
三、“迪克森郡案”對完善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啟示
近年來,由人民檢察院和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在全國各地不斷涌現。既有社會組織訴個人(如自然之友訴謝知錦案)、社會組織訴企業(如中華環保聯合會訴振華有限公司案),還有由人民檢察院針對企業、個人及政府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如徐州人民檢察院訴鴻順有限公司案)等。
(一)規范社會組織參與環境公益訴訟
社會組織與檢察機關均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適格主體。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需要政府預算加以支撐,由于公益訴訟涉及領域不同、耗資巨大的特征,又導致檢察機關在預算層面很難做出合理預期。理順社會組織與檢察機關原告主體關系時,應注重社會組織在發起環境公益訴訟時具有靈活性,可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的靈活性,鼓勵、支持其開展環境公益訴訟。在民事公益訴訟中,以社會組織為主導,檢察機關為補充;在行政公益訴訟中,應發揮檢察機關、社會組織的各自作用,并在法律中予以明確規定,社會組織可以接受檢察機關委托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前置程序,從而督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19]
社會組織參與環境公益訴訟不會引發濫訴。在“公民訴訟”條款規定之初,一些學者和社會公眾擔心此類訴訟的數量會非常龐大,法院將不堪濫訴行為的滋擾。[20]但是,從《清潔空氣法》《資源保護和回收法》以獨立條款規定“公民訴訟”的近半個世紀以來,事實證明,由公民、社會組織發起的環境公益訴訟只占美國環境訴訟總數的比例非常小。[21]究其原因在于:一是訴訟費用高。如果缺少充足的財力支持,就會大大的提高提起公益訴訟的門檻。[22]二是取證難度大。在環境污染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社會組織很難獲取相關的證據,以及證明污染排放與環境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三是敗訴的被告的賠償款被要求上繳國庫,而不能歸屬于原告,并且原告還要面臨巨大的敗訴風險。因此,推動社會組織參與環境公益訴訟對于推動環境執法具有十分現實的作用,不會引發濫訴風險。
(二)構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管理機制
《方案》“試點內容”第8條強調引入第三方機構來管理環境損害賠償基金,計劃到2020年之前建立起全國范圍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23]依據 《方案》,賠償義務人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無法修復的,其賠償資金作為政府非稅收入,全額上繳同級國庫,納入預算管理。實際上,有些案件的獲賠數額相當高,例如“中華環保聯合會訴振華公司案”一審賠償數額超過兩千萬元,[24]在“迪克森案”中,原、被告之間通過設立專家小組的方式負責監督補救基金的使用。為了落實《方案》,我國有必要出臺法規以支持設立環境公益訴訟修復基金。上述這些進展令人矚目,而相關法規方案的大范圍推廣實施還有待時日,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管理機制,將公益訴訟所得賠償款全部納入,確保專款專用,及時將環境修復執行落到實處。
(三)充分利用調解制度達成訴訟目的
美國環境公益訴訟的解決途徑包括三種方式,即法院頒發強制令、法院判決與和解。在環境公民訴訟中,大多數當事人更愿意選擇以和解的方式解決爭議,通過協商達成損害賠償和費用的分攤,使原告獲得利益,被告也會因不必承擔雙方的訴訟費用而獲益。
我國訴訟法中的調解制度與美國的和解制度類似。我國《民事訴訟法》允許原被告雙方通過調解的方式解決爭端,《行政訴訟法》第6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但是,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案件可以調解。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公益訴訟試點工作的決定》中,也沒有明確檢察機關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能否運用和解形式來結案。
調解是節約訴訟成本、發揮訴訟成效的方式。在我國現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下,行政公益訴訟調解制度的法律依據并不明晰。調解具有避免訴訟帶來的風險和降低成本的優勢,通過調解制度最終使違法行為得到糾正和懲處,實現違法者重新回到守法的軌道,從而確保環境得到有效治理。為此,應當在《行政訴訟法》第60條的基礎上,應當明確規定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進行調解,從而為行政訴訟調解提供了法律依據。
四、結論
環境公益訴訟以制度設計上的獨特性,使其成為一種非常先進的環境治理手段,從而能夠在防治污染、糾正違法行為以及保護環境方面發揮重大功能。“迪克森郡案”是美國眾多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的一例,“迪克森郡案”為完善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提供了可資參考的事例。對此,需要對《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予以修訂,通過規范社會組織參與,構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管理機制,明確環境公益訴訟調解法律依據,完善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注釋:
[1]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Dickson,No.08-0229,2011 WL 8214(M.D.Tenn.,Jan.3,2011.
[2]Herrington&Sutcliffe LLP,Harvard LIDS.“U.S.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http://www.nrdc.cn/Public/uploads/2017 -01 -09/587300dc91878.pdf.
[3]§6972(a)(1)(B)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4]First Amended Complaint for Declaratory and Injunctive Relief,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Inc.,et al.v.City of Dickson,Tennessee,et al.,Case No.08-cv-0229(M.D.Tenn.,Oct.28,2009).
[5]InterviewwithSelenaKyle,SeniorAttorney,LitigationProgram,NationalResourcesDefenseCouncil,conductedbyLIDSmembersandanOrrickattorneyonApril13,2016.
[6]李靜云:《美國的環境公益訴訟》,載《中國環境報》2013年7月4日。
[7]Robert V.Percival,et al.,“Environmental Regulation:Law,Science,and Policy”,New York:Wolters Kluwer Law&Business Pub.,7th ed.,2013:1270-1271.
[8]See Sub.(a)(1)(B)42 U.S.C.Section 6972.
[9]參見陳冬:《環境公益訴訟的限制性因素考察——以美國聯邦環境法的公民訴訟為主線》,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8期。
[10]Maine People’s Alliance v.Mallinckrodt,Inc.,471 F.3d 277(1st Cir.2006).
[11]Paper Recycling,Inc.v.Amoco Oil Co.,856 F.Supp.671,678(ND Ga.1993).
[12]James R.May."Now more than ever:Trends in environmental citizen suits at 30",Widener L.Rev.,Vol.10,2003,p.1.
[13]RCRA.“U.S.Environment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ExperiencesandLessons Learned”,http://www.nrdc.cn/Public/uploads/2017-01-09/587300dc91878.pdf(24March 2018).
[14]see Bret Adams et al.,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Provisions in State Constitutions,22 J.LAND RESOURCES&ENVTL.L.73(2002).
[15]兵臨:《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權》,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9791642.html,訪問日期:2018年3月25日。
[16]參見常紀文:《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立法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美國判例法的新近發展及其經驗借鑒》,載《現代法學》2007年第5期。
[17]參見張輝:《美國公民訴訟之“私人檢察總長理論”解析》,載《環球法律評論》2014年第1期。
[18]ConsentOrder,NaturalResourcesDefenseCouncil,Inc.,etalv.CountyofDickson,Tennessee,etal.,CaseNo.08-cv-0229(M.D.Tenn.,Dec.9,2011).
[19]馬勇:《社會組織應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重要力量》,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網,http://www.cbcgdf.org/NewsShow/4857/3812.html,訪問日期:2018年3月25日。
[20]參見齊樹潔、李葉丹:《美國公民訴訟的原告資格及其借鑒意義》,載《河北法學》2009第9期。
[21]參見李艷芳:《美國的公民訴訟制度及其啟示——關于建立我國公益訴訟制度的借鑒性思考》,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22]毛文革:《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立法與工作機制完善初探》,湖北省人民檢察院網,http://www.hbjc.gov.cn/jcyj/201803/t20180313_1262421.shtml,訪問日期:2018年3月25日。
[23]《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03/c_1117348804.htm,訪問日期:2018年3月25日。
[24]秦天寶:《大氣污染防治的法治新路徑——從全國首例大氣污染公益訴訟案談起》,載《中華環境》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