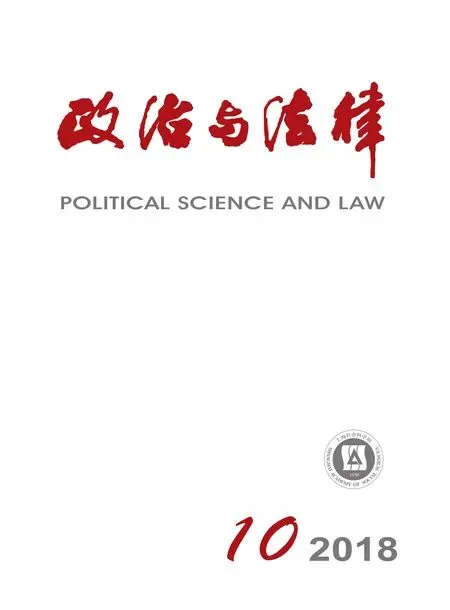金融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功能性重構*
——以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案例第40號為中心
徐凌波
(南京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00093)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及其問題
非法占有目的在金融詐騙罪中發揮著重要的界分功能。我國多個司法解釋均強調,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的關鍵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018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指導性案例“周輝集資詐騙案”(檢例第40號)再次強調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資詐騙罪區別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關鍵。然而,我國的司法實踐雖然在形式上強調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關鍵,但沒有從實體上明確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與判斷標準,而是將焦點轉向總結司法實務中形成的經驗,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具體情形。2001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總結了肯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七種情形:“(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4條則規定了八種情形:“(1)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2)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3)攜帶集資款逃匿的;(4)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的;(7)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8)其他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在理論上對于非法占有目的概念尚未形成共識的情況下,通過司法解釋從實務經驗中總結出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各種情形,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將構成要素實體內涵問題轉化為形式推定要素的程序性證明問題的做法,并非我國所獨有。普珀教授將這一類概念稱為歸屬的概念(zuschreibender Begriff)。①Puppe,Kleine Schule des juristischen Denkens,3.Aufl.,2014,S.50 f.例如,如何界定間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始終是德國以意志為本位的故意理論的難點。針對這一問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逐漸放棄了在故意殺人案件中精確界定間接故意中的“容認”態度,而是將焦點轉移到了如何證明這種態度。換言之,其通過在判例中列出能夠表征故意的各種要素來回應對何為“容認”的界定。然而,普珀教授也敏銳地指出,以推定方法取代實體內涵界定的后果,使殺人罪故意的判斷在實務中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與不一致性。②Puppe,in:Momos Kommentar zum StGB,4.Aufl.,§15,Rn.54.我國司法解釋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首先,我國司法實務長期以來將獲取貸款、集資款之后的事后表現作為推知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重要證據。例如,“將錢款用于從事非法活動”便是其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情形(《紀要》第4項、《解釋》第4條第4項)。這與我國《刑法》第384條的規定是存在矛盾的。根據該條規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從事非法活動是成立挪用公款的情形之一,國家工作人員將挪用之公款用于從事非法活動也僅僅屬于挪用,而不是以非法占有目的為成立要件的貪污。在其他以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為要件的罪名中,將事后的非法活動作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事實基礎是存在疑問的。
其次,以欺騙行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架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獨立地位,模糊了罪名之間的界限。在集資詐騙案件中,行為人虛構投資標的,偽造賬簿虛構業績,使集資參與者錯誤地相信行為人有足夠的償付能力,這本屬于認定欺騙行為的范疇,但也同時被作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據事實。例如,“周輝集資詐騙案”的公訴意見指出,周輝采用編造虛假借款人、虛假投標項目等欺騙手段集資,所融資金未投入生產經營,大量集資款被其個人肆意揮霍,具有明顯的非法占有目的。在“王某集資詐騙案”的判決理由中,法院用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事實基礎也包括被告人明知公司不具有境外上市條件,卻指使有關人員偽造報表,虛構業績,進行虛假宣傳,采用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③參見高偉、吳加亮:《集資詐騙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人民司法》2009年第10期。欺騙行為本身就是詐騙罪成立的構成要件,若再一次用于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則只要在非法集資中實施了欺騙行為就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作為獨立的構成要件要素便被架空虛置。此外,以欺騙行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可能導致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之間界限過于模糊,兩罪均以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為成立要件,通常認為其區別僅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若以欺騙行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則兩罪之界限便不復存在,原本僅能認定為構成騙取貸款罪的案件則可能被升格為法定刑較重的貸款詐騙罪。
最后,司法解釋列舉的情形是對實務經驗的總結與歸納,在這些事實經驗產生沖突時,如何分配不同證據事實在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時的權重便成為難題,尤其是在存在相反證據時,僅機械地重復司法解釋的規定,難以應對辯方提出的反對意見,無法有效地提升裁判文書的釋法說理水平。以“周輝集資詐騙案”為例,該案的辯護意見提出周輝一直在償還集資款,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集資款的故意。該案一審和二審的裁判理由與檢方的答辯意見都沒有從正面回應持續、積極的還款行為何以不能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④參見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浙刑二終字第104號刑事裁定書。只是從側面強調集資款主要用于個人揮霍,而沒有用于生產經營。集資款未投入生產經營活動符合《非法集資解釋》第4條第1項、第2項的規定,但辯護意見所強調的持續還款行動則能夠用以表明周輝并沒有“逃避返還資金”。在事實證據發生沖突時,何者具有更為優先的效力,司法解釋對此并沒有作出規定,通過機械地列舉司法解釋的規定也不能對此進行有效的說明。要充分實現釋法說理,仍然要回到非法占有目的的實體內涵解釋。
刑法上任何一個要素的證明與司法推定都不能取代這一概念在實體法上的概念界定。構成要件要素的內涵與解釋明確了證明對象的范圍。在明確證明對象的基礎上,才能夠繼續探討如何證明以及證明標準的問題。離開準確的內涵界定,司法推定的情形往往缺少體系性與統一的判斷標準,無法保證實踐中對于該要素的推定標準是一以貫之的。學理上關于非法占有目的內涵的討論往往僅以傳統財產罪(甚至僅以盜竊罪)為原型而展開,未能兼顧這一概念在實踐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也難以充分吸收實踐在這一問題上形成的重要經驗,阻礙了理論與實踐的良性溝通。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結合金融詐騙罪的司法實務經驗,重新檢討財產罪學理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一般闡釋。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學理闡釋與體系重構
(一)內涵與功能的支離: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釋困境
司法解釋僅在形式上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分功能,而在實體上放棄了對于這一重要概念的解釋,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理論上關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體系位置尚存在諸多爭議,且財產罪基礎理論所借鑒的德日教義學很難符合金融詐騙案件處理的實際需要。我國學者曾經指出,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金融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釋在邏輯起點上就是錯誤的,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以侵犯財產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理論來統攝金融詐騙、合同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解釋。⑤參見姚萬勤:《集資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論回歸——以吳英案為例的探討》,《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不過,現有財產罪理論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解讀并不能完全承擔這一功能,要有效兼顧非法占有目的內涵與功能的統一性,還需對財產罪這一基礎概念作進一步的調整與深化。
與我國刑法理論將非法占有目的視為盜竊、詐騙、搶劫、敲詐勒索等一系列財產罪共同的主觀超過要素不同,德國刑法中以盜竊、搶劫為代表的侵犯所有權犯罪與詐騙罪、勒索罪為代表的侵犯整體財產犯罪具有不同的主觀目的。前者以不法所有為目的(Zueignungsabsicht),后者則以不法獲利為目的(Bereicherungsabsicht)。⑥參見徐凌波:《論財產犯的主觀目的》,《中外法學》2016年第3期。我國刑法中,財產罪的主觀目的究竟是不法所有還是不法獲利,理論上主要存在三種傾向性意見。其一,主流觀點以盜竊罪的不法所有目的為基準來統一解釋刑法各種罪名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認為非法占有目的包含了排除所有與對財物進行利用和處分兩方面的意思。其二,較為有力的觀點認為,與德國刑法理論一樣,我國刑法不同罪名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應當根據其各自保護的法益進行分別解釋。⑦參見王俊:《非法占有目的的不同意義——基于對盜竊、侵占、詐騙的比較研究》,《中外法學》2017年第5期。盜竊罪保護的法益是所有權,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不法所有意圖,而詐騙罪保護的是整體財產,因此非法占有目的指的是不法獲利意圖。⑧參見車浩:《占有不是財產犯的法益》,《法律科學》2015年第3期。其三,極少數學者的觀點,我國刑法中盜竊與詐騙保護的法益同為整體財產,從這種整體財產法益出發,非法占有目的應當統一解釋為不法獲利目的。⑨參見前注⑥,徐凌波文。
然而,無論是將非法占有目的解釋為不法所有目的還是不法獲利目的,均無法有效實現非法占有目的在金融詐騙罪中的界分功能。
首先,不法獲利目的無法區分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不法獲利目的,指的是行為人主觀上積極地追求自己財產總量上的增加。這種積極的逐利意思與《紀要》和《非法集資解釋》中所強調的“逃避返還資金”是不相符的,后者側重于給被害人造成損失,而非積極地使自己的財產總量增加。即便是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騙取貸款罪中,行為人都存在主觀的逐利意思。僅根據行為人主觀上存在積極的逐利意思即肯定非法占有目的,將導致大多數騙取貸款、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升格為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
其次,不法所有目的同樣難以明確上述罪名之間的界限。德日刑法理論中,不法所有目的的存在有效地將輕微的使用盜竊行為排除在盜竊罪的處罰范圍之外。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使用后歸還的意思,則應當否定排除所有的意思。這種以行為人是否具有歸還意思來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思路,看似與上述司法解釋中的司法推定思路相符,例如《非法集資解釋》第4條第5項、第6項、第7項列舉了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銷毀隱匿賬目、拒不交代資金去向等多種行為人逃避返還資金的情形,用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反之,當行為人沒有逃避返還資金,具有歸還本息的意愿時,便可以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然而,在涉及貸款、集資款等金錢債權債務關系中,與債務人的還款意愿與使用盜竊行為中的原物歸還意愿并不相同。德國刑法理論中,盜竊罪的保護法益是所有權相對應的,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指的是剝奪所有權人對特定物的控制支配力。原物的返還才能表明行為人沒有剝奪所有權人控制支配的意思,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即便行為人在盜竊財物時留下了與財物價值等額的金錢作為補償,也不能就此否定行為人對于財物本身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相反,貸款、集資等金錢債務債權關系中,還款意愿是金錢債務的履行意愿,而非原物返還的意思。這種意愿并不局限于作為特定物的金錢上,而只是需要交付與債務相同數額的金錢即可。我國學者認為,在集資詐騙中,如果行為人沒有永久持續占有使用的意思,就應當否定集資人的排除意思。⑩參見前注⑤,姚萬勤文。這一觀點機械套用盜竊罪中的不法所有意思,而忽略了金錢債權債務關系中,特定錢款上的所有權在集資參與者交付集資款項時已經轉移給集資人、貸款人,行為人則負有持續支付約定利息、到期還本付息的合同義務。無論行為人是否具有最終的還本付息意思,在主觀上都不具有針對特定錢款的原物返還意思。
綜上所述,盡管非法占有目的在金融詐騙罪認定中具有重要的罪名界分功能,但事實上,無論是以不法所有目的還是以不法獲利目的來解釋非法占有目的,都無從實現這一要素在金融犯罪案件中的界分功能。司法解釋中所強調的行為人歸還貸款、集資款的意愿與能力在不法所有目的、不法獲利目的的概念中均無法獲得恰當的安置。這是導致金融詐騙罪的司法實踐與非法占有目的的學理闡釋完全脫節的重要原因。要厘清這一問題,有必要在我國財產罪保護法益的視角下重新審視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及其體系位置。
(二)排除意思的擴張:造成他人財產損害的故意
應當承認,為明確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詐騙罪與普通合同詐欺行為之間的罪名界限,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是不可放棄的。只是根據我國當前財產罪的保護法益,排除所有意思應當作適當的擴張。
從保護法益上看,排除意思作為法益侵害的核心,不應限于民法意義上的所有權。德國對盜竊罪中的排除所有意思的解釋與該罪的保護法益密切相關。在德國,對盜竊罪保護法益內涵的界定采取的是絕對的所有權保護立場。我國刑法中,財產罪的保護法益并不限于民法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是我國《刑法》第91條所劃定的公民合法所有財產。?參見前注⑥,徐凌波文。從法益指導構成要件解釋的角度出發,我國刑法中,排除所有的意思擴張為排除他人對于財產的擁有,即給他人造成財產損失的主觀認識與意欲。
在詐騙罪構造中,財產損害原本就是詐騙罪成立的客觀構成要件,擴張后的排除意思是詐騙罪故意的組成部分,而非超過的主觀故意,我國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因而并不是一個徹底的主觀超過要素。其中的排除意思在故意之內,不法獲利意思則在故意內容之外。若探討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則應當包含了排除意思與利用意思兩部分的內容,且排除意思的存在使得金融詐騙罪有效地區別于其他金融犯罪以及民商事借貸款糾紛。若僅討論財產罪的主觀超過目的,則應只包括不法獲利目的。這與德國詐騙罪的一般理論是一致的。德國詐騙罪的理論并非難以適用于我國金融詐騙罪的解釋,只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國研究者堅信非法占有目的是完全的主觀超過要素,所以在學說繼受過程中僅關注了詐騙罪故意之外的內容,并沒有注意到詐騙罪與盜竊罪因客觀構成要件不同而使兩罪的主觀目的在內容與結構上存在差異。之所以產生這種誤解,在于我國研究者錯誤地假定盜竊罪與詐騙罪作為目的犯,在犯罪結構上具有同構性,但事實上德國的財產罪理論中盜竊與詐騙具有完全不同的構成要件結構。
首先,兩罪的保護法益并不相同。盜竊罪保護的僅僅是所有權,詐騙罪關注的則是被害人的整體財產。盜竊的對象僅限于有體物,詐騙罪的對象則包括所有財產性利益。因此不法所有意思局限于個別的物上所有權,不法獲利意思則指向財產總量的非法增長。
其次,法益侵害結果在兩罪構成要件中的地位并不相同。盜竊罪保護的是所有權,但其客觀構成要件卻是破壞并建立占有(即拿走),并不要求所有權侵害結果在客觀上出現。?Vogel,in:Leipziger Kommentar zum StGB,Vor.§242,Rn.66.詐騙罪的成立則以客觀的財產損害結果為必要。德國學者蘭珀(Joachim Lampe)教授因而指出,根據賓丁的設想,刑法分則應當盡可能地僅規定實害犯,再通過刑法總則關于未遂的規定來擴張處罰實害結果未出現的情況,惟其如此才能實現罪刑均衡。從一般法理上看,詐騙罪的結構被認為是優于盜竊罪的。?Lampe,Objektiver und subjektiver Tatbestand beim Diebstahl,GA 1966,S.236.
盜竊罪與詐騙罪上述構成要件的不同最終決定了兩罪主觀目的存在結構性差異:盜竊罪的不法所有目的包括了消極的排除意思與積極的取得意思;詐騙罪主觀上則只有積極的逐利意思,而沒有消極的排除因素。盜竊罪中的排除所有意思,是主觀化了的所有權侵害結果。通過法益侵害結果的主觀化,盜竊罪將既遂時點提前到建立占有之時,而不要求法益侵害結果在客觀上實現。詐騙罪中,在客觀上已經要求財產損害結果出現的前提下,相應的主觀內容就只是詐騙罪故意的一部分,而不是超過的主觀目的。
(三)小結
我國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包含了排除意思與利用處分意思兩方面的內容,其中從財產罪的保護法益出發,排除意思在內涵上應當理解為給他人造成財產損害的主觀意思。這一主觀要素是否是一種主觀超過目的,取決于詐騙罪的成立是否以財產損害的客觀出現為必要。歸根結底,客觀構成要件決定了故意內容的范圍(構成要件的故意規制機能)。某種法定的主觀要素究竟是故意內容的組成部分,還是故意之外的主觀超過要素,取決于法律如何規定及如何解釋該罪的客觀構成要件。若財產罪的成立不以財產損害結果在客觀上出現為必要(如在德國的盜竊罪中),則非法占有目的尤其是其中排除意思的功能在于法益侵害結果的主觀化,凸顯財產罪的法益侵害核心。反之,若財產罪的成立要求客觀上存在財產損害結果,則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只能是故意的組成部分。德國詐騙罪教義學強調對于財產損害的獨立判斷,與我國財產罪罪量要素的設定相契合,也符合司法實踐重視財產損害的基本邏輯,要求詐騙罪的成立必須存在被害人整體財產的減損已經為我國學理與實務所接受。在此背景下,仍然主張非法占有目的是詐騙罪故意之外的主觀超過要素在體系上是難以成立的。
將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理解為財產損害的故意,不僅有助于厘清目前理論上關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體系位置的爭議,也能夠為金融詐騙罪的認定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客觀標準。
首先,這有助于解決盜竊罪與詐騙罪是否以非法占有目的為共同主觀目的的問題。中日兩國刑法理論上之所以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暨“不法所有目的”是盜竊罪與詐騙罪共同的主觀超過要素,一方面是受到了德國盜竊罪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刑法理論通說始終認為,詐騙罪是侵犯個別財產的犯罪,而非侵犯整體財產的犯罪。行為人在交付占有時個別財產即受到損害,并不需要單獨判斷財產損害是否在客觀上出現。這樣一來,盜竊與詐騙的客觀要件便具有了同構性。兩罪在客觀上均表現為占有的轉移,差別僅僅在于盜竊為未經他人同意轉移占有,詐騙則是因認識錯誤而主動交付占有。盜竊罪中的不法所有目的便能夠輕而易舉地嫁接到詐騙罪中。隨著主張詐騙罪是侵犯整體財產犯罪的少數觀點在日本的支持者日漸增加,整體財產減損也開始成為不成文的獨立要素時,詐騙罪的主觀目的解釋若不進行相應的調整,則在功能上會與財產損害要件發生重合。
其次,這有助于解決非法占有目的究竟屬于不法要素還是責任要素的問題。德日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論體系位置的分歧,本質上是故意在犯罪論體系中究竟屬于不法要素還是責任要素的問題,只是日本通說在邏輯上并不自洽。其一,日本通說一方面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責任要素,與法益侵害無關,?[日]山口厚:《刑法總論》(第2版),付立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頁。另一方面又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盜竊、詐騙與不可罰的盜用、騙用行為的關鍵。盜用、騙用行為之所以不可罰是因為僅具有輕微的法益侵害性,違法性尚未達到可罰的違法性程度。?[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論》,劉明祥、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頁。若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責任要素,則以責任要素界分違法性是否達到可罰程度,便存在混淆不法與責任的錯誤。其二,在所有權犯罪中,盜竊罪在實質上被視為侵占罪的未遂甚至預備階段。?Kindhuser,in:Momos Kommentar zum StGB,§242,Rn.6.在日本,即便是徹底的結果無價值論的主張者也認為,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在未遂犯中是違法要素而非責任要素。?同前注,山口厚書,第96頁。主張非法占有目的是責任要素的觀點,與其通行的未遂故意理論相左。
最后,這有助于解決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在根本上是如何認定財產損害)的問題。“非法占有目的”之“目的”這一表述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與誤導性,將理論與實務的關注焦點轉移到了行為人的主觀目的這一難以運用間接證據證明的心理事實上來,而難以容納財產損害要素認定過程中所需要考慮的因素的多樣性與復雜性。筆者以下的闡釋將表明,在法律-經濟的財產概念下,結合詐騙罪的教義學體系能夠更加系統地回答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難題,司法解釋中所強調的還款意愿與還款能力也能夠在財產損害的概念中找到其恰當的位置。
三、財產損害視角下的非法占有目的
如前所述,我國刑法理論通說認為金融詐騙罪區別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騙取貸款罪的關鍵,在于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在現有的詐騙罪解釋框架內,排除意思指的是給他人造成財產損害的意思,是詐騙罪故意的一部分。金融詐騙罪的司法認定中圍繞非法占有目的所提出的大多數問題可以歸結為財產損害的認定問題。以財產損害認定為視角,可以從教義學角度有效解釋司法解釋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各類推定因素的正當性,也可以糾正司法實踐中裁判者因機械適用司法解釋規定的推定情形所帶來的誤差。
(一)債務履行的意愿與能力是財產損害認定的建構性要素
詐騙罪財產損害的認定采取整體收支平衡原則(Gesamtsaldierung),即比較處分行為前后財產的收入與支出情況判斷被害人整體財產狀況是否發生了惡化。?Tiedemann,in:Leipziger Kommentar zum StGB,§263,Rn.159.無論是集資還是貸款,行為人與集資參與人、銀行之間都存在一個雙方法律行為,通過合同約定雙方互相負有的合同義務,即給付(Leistung)與對待給付(Gegenleistung)。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比較被害人的給付與其所獲得的對待給付各自的經濟價值大小以確定被害人是否遭受財產損害。即便給付與對待給付在紙面上的經濟價值大體相當,行為人若欠缺債務的履行能力與意愿,則該對待給付的實際經濟價值便歸于無,被害人因此遭受財產損害,德國詐騙罪理論稱之為不真正締約詐騙(unecter Erfüllungsbetrug)。?參見王鋼:《德國刑法詐騙罪的客觀構成要件——以德國刑事司法判例為中心》,《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10期。
在財產損害的認定中考慮行為人的債務履行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這一要件主觀化的色彩。這也是理論與實務始終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徹底的主觀超過要素的重要原因。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還款意愿似乎是行為人騙取取貸款、集資款的客觀行為之外需要進行獨立判斷的犯罪成立條件。然而,筆者之前的分析表明,只要承認在詐騙罪的成立以財產損害在客觀上出現為前提,那么意在使被害人喪失財產的排除意思,就只能是詐騙罪故意的一部分。對于主觀還款意愿與還款能力的強調,只是凸顯了財產損害這一要件的部分主觀色彩。財產損害要件的主觀化是由以下兩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其一,刑法意義上的財產(Vermgen)是一個事實性的概念,它區別于民法意義上的財產權。早期財產罪理論也曾經完全將刑法上的財產理解為財產權的集合(即法律的財產概念),而今通行的法律-經濟財產概念則更為強調財產的事實性。這是當今法益理論發展整體進程的必然產物。費爾巴哈所倡導的權利侵害說的主要問題,在于權利是一種形式上的法律地位,因而不具有可損性。為解決這一問題,在比恩鮑姆引入“財”(Gut)的概念之后,又發展出了可損的法益概念。?馬春曉:《法益理論的流變與脈絡》,載方小敏主編:《中德法學論壇》(第14輯下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刑法上之財產與民法上之財產權的關系,大體相當于法益與權利的關系:法益是可損的,而權利是不可損的。德國理論雖然堅持認為盜竊罪保護的法益是所有權,但嚴格來說這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上的所有權,而是基于所有權而產生的對物支配可能性。?Vogel,Leipziger Kommentar zum StGB,12.Aufl.,Vor.§242,Rn.53.盜竊行為并不會使財物所有人在民法上失去所有權,而是使其失去了基于所有權對物進行利用支配處分的可能性,刑法所要保護的正是后者。同理,當人們將債權作為財產的組成部分置于刑法的保護之下時,刑法的任務并不在于確保該債權請求權本身在法律上是否存在且有效,而在于保障該債權在事實上能夠得到實現。
其二,在權利性質上,物權是支配權,債權則是請求權。債權區別于物權的特征在于,債權是請求債務人為一定行為的權利。?參見金可可:《私法體系中的債權物權區分說——薩維尼的理論貢獻》,《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債權在事實上能否得到實現有賴于債務人的信用與配合。一旦債務人喪失履行債務的意愿與能力,債權人紙面上所擁有的債權即失去了事實上的履行可能性,其實際價值將歸于零。在民法制度上,該債權仍然存在且有效,債權人能夠向債務人主張債權請求其履行債務,直至向法院起訴,再基于勝訴判決申請強制執行。在刑法上,當債權在事實上的履行可能性受到妨礙時,便出現了刑法意義上的財產損害。如果行為人引起此種財產損害的方式符合相應的犯罪構成要件,則需要根據具體的財產犯罪罪名定罪處罰;如果缺少相應的構成要件,則僅以普通民事財產糾紛進行處理。在討論盜竊欠條等司法實務案件時,反對盜竊罪成立的觀點認為,被害人失去的僅僅是債權的證明憑證,債權本身在法律上仍然存在。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從刑法對于財產概念的事實性理解,以及從債權本身的特性來看,一旦失去唯一的債權證明憑證導致債權履行在事實上不可能時,就可以認為已經存在刑法意義上的財產損害。至于引起此種財產損害的行為是否構成盜竊罪,則仍然需要結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判斷是否存在違反被害人同意的占有轉移。?參見張明楷:《論盜竊財產性利益》,《中外法學》2016年第6期。
《紀要》與《非法集資解釋》所列舉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情形大體便可分為欠缺債務履行能力與欠缺債務履行意愿兩類:行為人肆意揮霍借款、未將集資款投入生產經營活動或投入生產經營活動與集資規模不成比例的,由于缺少持續的盈利收入來源,行為人在債務到期時必然欠缺足夠的償付能力,給債權人造成財產損失;行為人攜款潛逃、隱匿轉移資金、隱匿銷毀賬簿等情形則表明行為人雖客觀上能夠履行債務,但主觀卻逃避還款,反映其缺少債務履行的意愿。從財產損害角度看,在根據司法解釋進行推定時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虛構生產經營項目、虛構業績的事實對于財產損害的影響,并不在于以欺騙行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而是行為人并沒有實際的生產經營項目獲得盈利從而具備歸還本金、償付高額利息的能力。其二,司法解釋在非法占有目的推定中既重視資金的事后用途又強調單純的用途變更,不能當然地肯定非法占有目的。這一點可以從財產損害角度得到妥當的學理說明。不同的資金用途對應著不同的財產損失風險,關鍵并不在于資金用途的變更,而在于變更所導致的財產損失風險高低。若用途變更后面臨更高的財產損失風險(例如將集資款、貸款用于個人揮霍、非法活動或者是更高風險的投資活動)時,則可以肯定財產損害的存在。其三,刑法看重的是行為人的整體債務償付能力,因此財產的轉移只有在將明顯導致行為人償付能力下降時,才能肯定財產損害的存在。相反,若財產只是在個人實際控制的不同公司之間進行轉移,則不能當然地認為行為人具有逃避返還資金的意愿,進而肯定財產損害的存在。
(二)債務履行意愿與能力需要進行規范的綜合判斷
“非法占有目的”的表述固然凸顯了財產損害要素認定中的主觀色彩,但也高估了債務履行意愿在財產損害整體判斷中的地位與作用,在這一點上強調非法占有目的要件將證據的證明聚焦于行為人主觀意愿這一心理性的事實,不僅增加了證明的難度,從教義學上看也具有一定的誤導性。在財產損害的整體判斷中,行為人的主觀內心事實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根據法律-經濟財產概念進行規范性的限縮。
一方面,行為人雖欠缺歸還集資款、貸款的主觀意愿,提供足額、有效擔保的情況下仍能否定財產損害,排除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的成立。德國刑法理論中,法定擔保始終是財產損害認定的重要因素,因為擔保尤其是擔保物權的實現不需要債務人的自愿配合,因此即便欠缺還款意愿,也不存在財產損害。行為人既可能以自己的財產進行擔保,也可能以他人的財產設定抵押、質押或者請他人擔任自己借款的保證人。在后一種情況下,獲取他人擔保的前行為可能另行成立犯罪,例如通過欺騙手段使他人在其個別財產上設定抵押、質押或者以其整體財產提供保證的,該行為本身可以另行構成詐騙罪。然而,就借款的債權債務關系而言,即便擔保物權人、保證人存在意思瑕疵,該擔保原則上仍然是有效的。這樣,即便行為人沒有還款的意愿與能力,債權人也能夠以擔保財產實現債權,并沒有遭受財產損害。孫國祥教授正確地指出:“擔保人用于擔保的財產,是行為人償還債務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當擔保人承擔了擔保責任時,應視為行為人履行了還款責任。在擔保人已經代償債務的情況下,對行為人而言,或者認定沒有造成損失而不構成犯罪,或者認定被告人因騙取擔保而構成合同詐騙罪。”?孫國祥:《騙取貸款罪司法認定的誤識與匡正》,《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我國的司法實務也采取同樣的立場。“秦文虛報注冊資本、合同詐騙案”判決理由指出,以向金融機構貸款的方式騙取擔保人財產的,不構成貸款詐騙罪,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指導案例第352號,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一、二、三、四、五庭主編:《刑事審判參考》(2005年第4集,總第45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另一方面,在集資詐騙等典型的龐氏騙局中,即便行為人通過持續、積極的還款行動表明自己具有還款意愿與能力,這種事實上的還款意愿與能力也應通過規范的視角予以排除。這類案件中,行為人通過借新還舊的手段維系自己的對外信用,使更多的人錯誤地相信他虛構的集資項目具有較強的盈利能力,從而能夠持續地支付高額的利息。集資詐騙罪的認定難點在于,集資活動的早期參與者有規律地獲得行為人所支付的高額利息,甚至在多年的運轉中早已收回自己的本金。相關案件中辯護人也往往會以被告人此前實際償付利息為由論證被告人始終具有還款意愿,來否定被告的非法占有目的。早在2009年的“吳英集資詐騙案”中,吳英并沒有推卸自己的還款義務,大量事實表明她在舉債后積極地歸還欠款,就是辯護意見否定吳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據。?參見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浙金刑二初字第1號刑事判決書。互聯網金融的興起與發展并沒有改變這類案件的基本運作邏輯,只是利用網絡P2P平臺的集聚效應,行為人能夠在短時間內吸收更多的資金,使騙局吸收的資金規模呈幾何級增長,并能夠在更長的時間段內得到維系,造成更嚴重的危害社會后果。在前述“周輝集資詐騙案”中,周輝通過中寶投資網絡平臺非法集資共計10.3億余元,除支付本金及收益回報6.91億余元外,尚有3.56億余元無法歸還,這一組數據也從側面反映出周輝在事實上有持續償付本金與利息的舉動。這不僅關系到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而且關系到影響定罪量刑的詐騙數額究竟以集資總額10.3億元還是以最終未能歸還的3.56億元進行計算。
從法律角度看,只有得到法秩序認可的經濟利益才是刑法所保護的利益,以后續騙取的集資款為來源所形成的還款能力應當排除在行為人還款能力之外。行為人持續的還款行動本身是其維系自身對外信用的重要方式,通過積極的還款行動使更多的投資者相信行為人擁有足夠的盈利能力來歸還本息,從而使騙局得以長期運轉。我國《刑法》第224條合同詐騙罪存在類似的規定,行為人“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構成合同詐騙罪。這一規定反映了在我國刑事立法機關看來,為了繼續實施欺騙行為而實施的債務履行,并不能排除詐騙罪的成立。
從經濟角度看,早期投資者雖然有機會收回本息,但這種預期能否實現取決于是否源源不斷地有后續的投資者落入騙局之中。德國學者指出,從一個客觀觀察者的視角來看,這種獲得回報的預期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希望,即通過越來越多的集資參與者的加入,這一通過欺詐所建立的投資系統的資金鏈得以長時間地得到維系。?Schmidt,Der Verm?gensschaden im Sinne des §263 StGB bei Investitionen in Schneeballsysteme,StV 2018,57,59.因此在集資者處分自己財產之時,缺少足夠的證據計算投資者在投資時所擁有的債權請求權的實際經濟價值。將吸收的集資款用于支付本金與收益,不僅是不可預見的,而且是在經濟上無法量化的。這種完全建立在偶然性之上的回報預期不被視為具有經濟價值。
基于這兩方面的考量,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近年來在關于投資詐騙案件的判決中指出,龐氏騙局中詐騙行為所導致的財產損害數額以其騙取的投資總額來進行計算,行為人前期所支付的本息數額,不影響財產損害的認定,而只是作為事后的損害補償(Schadenwiedergutmachung)在量刑中酌情予以考慮。?BGH MStZ 2016,409.“周輝集資詐騙案”最終也以10.3億的集資總額認定詐騙數額。這說明中德兩國司法實務在該問題上存在高度的共識。
(三)財產損害的直接性原則能夠有效地區分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詐騙罪在傳統上被認為是“自我損害犯罪”,基于這一觀念,德國刑法理論原則上認為詐騙罪的財產損害必須是由被害人的財產處分直接導致的(直接性原則)。客觀歸責理論產生后,直接性原則被認為是從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保護目的中推導出來的,是詐騙罪財產損害歸責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原則要求,詐騙罪的財產損害的計算必須以處分行為為時點,處分行為之后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財產減損或增加均不能影響財產損害的認定,例如,事后產生的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通過保險而獲得的賠償、風險投資中因為意外因素所造成的財產增加,均不能計入整體財產的減損之中。?Tiedemann,in:Leipziger Kommentar zum StGB,12.Aufl.,§263,Rn.161 f.
集資詐騙與貸款詐騙中財產處分行為指的是參與集資者交付集資款、銀行批準發放貸款的行為,財產損害應當以此為計算時點。行為人自始欠缺債務履行的意愿與能力決定了集資款、貸款的交付、發放行為直接導致了財產損害。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騙取貸款罪雖然也規定了財產損失,但此種財產損害并非由前述處分行為直接造成,而是處分行為之后的其他因素(例如行為人經營失誤)所導致的。?參見黎宏:《刑法學各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頁。此種財產損失與被害人的處分行為之間缺少詐騙罪成立所要求的直接性,并不作為詐騙罪結果的財產損害。我國有學者正確地指出:“騙取貸款罪的結果是取得貸款,而非財產損失的出現。行為人對于所造成的重大損失主觀上也不一定具有故意。”?同前注,孫國祥文。我國刑法理論界與實務界通常認為,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在客觀構成要件上完全一致,僅在主觀內容上存在差異,這種觀點對于作為詐騙罪結果的財產損害做了過于寬泛的理解。
直接性原則也意味著,只有財產處分行為時的還款意愿才能影響財產損害的成立。行為人在獲取集資款、銀行貸款之后,事后產生拒不歸還意愿導致財產無法歸還的,不在集資詐騙、貸款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規范范圍之內。《紀要》與《非法集資解釋》所列舉的各類抽逃、轉移、隱匿資金或隱匿銷毀賬目等各類事后行為,雖然可以用以推定還款意愿的存在,但若有相關證據證明行為人只是在事后出于各種原因產生逃避還款意愿的,也應當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即財產損害的存在。行為人在合法取得貸款后想要逃避債務,若在逃避債務履行過程中,使用欺騙手段使被害人放棄或減少相應金額的,則屬于在履行合同中實施的詐騙行為,應根據我國《刑法》第224條的規定以合同詐騙罪論處。若單純的拒不歸還、隱匿財產逃避履行的,屬于民法調整的范疇,不構成刑法上的侵占罪。
(四)間接故意足以肯定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中“目的”二字的表述具有一定的誤導性,它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錯誤的印象,即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對于被害人所遭受的財產損害持積極的希望或追求態度,從而將非法占有目的局限在直接故意的范疇內。如果將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理解為對于造成他人財產損害的故意,則這種故意的內容顯然不局限于積極追求危害結果發生的直接故意,而是也包括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間接故意。
德國刑法理論中的“目的”概念也面臨類似的問題。通說認為,“目的”(Absicht)具有以下兩層含義。其一,作為總則中故意分類的目的。故意被分為了目的(Absicht)、明知(Wissentlichkeit)與間接故意(bedingter Vorsatz)三種類型,其中,目的指的是行為人積極追求結果發生的主觀意志態度。其二,作為分則中主觀超過要素的目的也可以指分則的具體罪名中單獨加以規定的目的,盜竊罪中的不法所有目的、偽造貨幣罪中的使用目的、詐騙罪中的不法獲利目的均屬于這一意義上的目的。德國通說認為,分則中的目的不等于總則中的目的。分則具體罪名中雖然使用了“目的”的表述,但并不一定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持積極追求的態度。尤其是盜竊罪中不法所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僅要求存在間接故意即可。?Vogel,in:Leipziger Kommentar zum StGB,12.Aufl.,§15,Rn.87.沙夫斯坦因(Schaffstein)根據盜竊與侵占之間的實質未遂與既遂關系指出,盜竊罪是侵占罪的未遂形態,因此盜竊罪主觀的不法所有目的便是侵占罪的故意,間接故意便足以成立。在行為人盜竊他人財物暫時使用后將財物遺棄的案件中,只要行為人認識到原所有人終局地喪失財物的可能性而予以放任,就可以肯定盜竊罪的成立。排除所有意思并不要求行為人積極追求他人喪失所有物的結果,而只要求其認識到喪失所有物的可能性而予以放任。?Schaffstein,Zur Abgrenzung von Diebstahlund Gebrauchsanma?ung,insbesondere beim Kraftfahrzeugdiebstahl,GA 1964,S.97,108.
當人們將排除所有意思從使原所有權人喪失所有拓展到使被害人遭受整體財產的減損以后,行為人主觀上只需對他人的財產損害存在間接故意即可肯定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金融詐騙罪中,行為人在行為時明知自己在債務到期時缺少履行能力的,并不能以自己主觀上仍有履行的意愿進行抗辯。司法解釋列舉的多項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并非建立在還款意愿上,而是建立在還款能力的基礎之上。《紀要》明確規定“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便是對非法占有目的的間接故意形態的肯定。行為人的還款意愿與能力在財產損害以及故意的認定中具有同等的地位,還款能力的缺失不僅是用以推定還款意愿缺失的證據,而且是故意造成他人損害的另一種獨立形態。
四、結 論
財產罪理論對于非法占有目的內涵的學理闡釋在一定程度上難以滿足這一要素在金融詐騙罪中的界分功能。這使得司法實務轉而尋求從司法經驗中總結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情形,將實體問題轉化為證據證明的程序問題。在程序中如何證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并不能取代在實體法上準確解釋非法占有目的的問題,離開準確的實體法解釋,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往往缺少系統的判斷標準與統一適用的根據。
非法占有目的包含排除意思與利用處分意思兩個部分。排除意思的存在是以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為代表的金融詐騙罪有別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騙取貸款罪的關鍵。由于我國刑法財產罪的保護法益是整體財產,排除意思應當擴張解釋為“排除他人財產、使他人財產遭受損失”。在承認財產損害是財產罪成立的客觀構成要件這一前提下,主觀上使他人遭受財產損害的意思是詐騙罪乃至所有財產罪犯罪故意的組成部分。利用處分意思或者說不法獲利意思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觀超過要素。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困難,本質上是財產損害的認定問題。
詐騙罪的財產損害以處分行為直接造成的整體財產減損為限,以處分行為為計算時點,比較前后財產流入與支出判定整體財產是否發生減損,在締約時主要表現為比較合同的給付與對待給付義務的經濟價值大小。若行為人主觀欠缺還款意愿,則債權人所獲得的對待給付的實際經濟價值為零,債權在事實上無法實現。我國司法解釋總結的非法占有目的推定情形的核心便在于行為人的還款意愿和能力,兩者均是被害人財產損害認定的建構性要素。作為財產損害的建構性要素,行為人是否具有還款能力與還款意愿應當在法律-經濟的財產概念的框架內進行規范判斷。在集資詐騙等典型的龐氏騙局中,行為人以騙取的集資款償付早期集資參與者的利息與本金,雖然在事實上看具有還款意愿與能力,但從規范上看,以所騙取的集資款為來源所形成的償付能力不能被認為是行為人還款能力的組成部分。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騙取貸款罪的成立及定罪量刑雖然也考慮犯罪行為所造成的財產損失,但此處的財產損失并非由欺騙行為直接造成。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騙取貸款案件中,行為人雖然使用了欺詐手段與集資參與者、銀行訂立借款、貸款合同,但其主觀上具有債務履行的意愿,對于未來的債務履行能力也有積極的預期,此時相對于行為人而言,集資參與者、銀行所擁有的債權具有經濟價值,不能認為財產處分行為直接造成了財產損害,因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騙取貸款罪中的財產損失,是犯罪情節,而非犯罪結果要件。
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強調,一方面正確地認識到了財產損害作為客觀要件具有一定的主觀色彩,這種主觀色彩是由刑法上財產概念的事實屬性以及債權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又高估了行為人的債務履行意愿在是否構成“非法占有”中所發揮的作用。行為人主觀上并不打算運用自己的財產歸還本息,但通過其他手段由他人提供足額、有效擔保的,應否定財產損害的存在。至于使他人提供擔保的行為是否成立合同詐騙罪,應當另行判斷。反之,行為人沒有明確的拒不歸還意思,但在其客觀的履行能力不足以償付的情況下與他人訂立借款、貸款合同,則仍可肯定造成財產損失的間接故意。行為人通過還款行為所表現出來的積極還款意愿需要進行規范判斷,當行為人的償付能力僅僅來源于后續的集資款時,從法律-經濟的財產概念出發,仍然要否定這種償付能力的經濟價值,肯定財產損害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