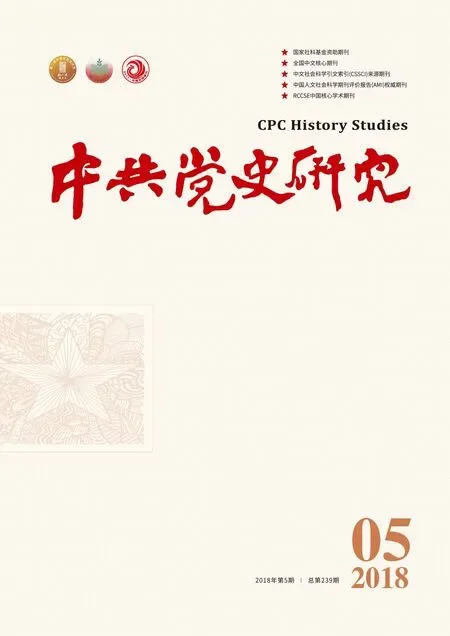重釋“社會革命”的意義
——試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問題共識”
滿 永
(本文作者 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上海 201620)
近年來,隨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介入以及學界對地方基層檔案的發(fā)掘和利用,中共地域史研究開始走出早期的根據地史研究視野,成為黨史研究擺脫某種宏大敘事的主要路徑,最直接的學術表現和成就是20世紀50年代中共地域史研究的興起。本文討論的地域史研究,就以此為主。
根據地時期的地域史研究,由于和革命的歷史進程有著高度的契合性,因此仿若自然而然之事。但是這樣的邏輯,在1949年以后的地域史研究中,表面上并不存在。因為1949年的政權更迭,意味著中共的政治統(tǒng)治從根據地時期的區(qū)域分割轉向了全國一統(tǒng)。雖然不同行政區(qū)域內的政策執(zhí)行難免有所差異,但此差異與根據地時期各根據地的相對自主狀態(tài)顯然存在天壤之別。在這種情況下,50年代的地域史研究何以可能?仍舊是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一、“調查研究”與地域史研究的可能
50年代地域史研究的可能與否,主要取決于在當時的整體歷史進程中,地方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評估地方的作用,不能不提到作為中共根本工作路線的群眾路線。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中共為保障群眾路線的落實,形成了兩個較為具體的工作方法,即調查研究和典型試點,二者都體現了中共對地方經驗的重視。在這種特殊的工作方式作用下,地方往往兼具政策起點和終點的雙重身份,這就決定了研究者若要理解當代中國的整體歷史進程,必須首先理解地方,這是地域史研究成為可能的歷史前提。
在近年來的海內外中共革命史研究中,由于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的運用,地方的重要性被不斷凸顯,甚至呈現日益地方化的研究傾向。比如在集體化時代鄉(xiāng)村中國的研究中,海外學者大多已開始在地方經驗的基礎上,強調鄉(xiāng)村相對于國家的自主性;國內學者的研究也開始走出單調的“社會主義改造”敘事,發(fā)掘在政治改造敘事下的鄉(xiāng)村自主性,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高王凌對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反行為”的研究*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劉詩古對“大躍進”前農民抗爭行為的討論*劉詩古:《退社與外流:“大躍進”前的農民抗爭》,《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4期。等。
毋庸諱言,類似研究的確讓人們看到了更多的歷史復雜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海內外學界對集體化時代中國鄉(xiāng)村自主性的發(fā)掘或強調,實際上不僅未能走出長期以來左右當代中國歷史敘事的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更有強化之趨勢。問題是,這樣的二元敘事是否完全揭示了歷史的復雜性?50年代以來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是否亦確如現有研究所揭示的,要么是政治主導的改造要么是社會自主的抗爭?當研究者從一種極端回轉到另一種極端之時,是否在無意中回避了改造與抗爭的中間地帶甚或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有學者在反思政治化的歷史敘事時就指出,警惕此類敘事模式并不等于拋棄當代中國研究中的“國家脈絡”,否則就“無法解釋1949年以后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為何如此深刻劇烈”*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8頁。。對此,筆者亦深有同感。
將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視作一種歷史狀態(tài),雖然在50年代的中國沒有問題,但研究者不能據此而將其置入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去分析,否則就有簡單化歷史之嫌,50年代的中國尤其如此。筆者以為,中共在革命歷史進程中創(chuàng)造的一些特殊經驗,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很難放入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去討論,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毛澤東在群眾路線之下不斷強調的“調查研究”工作作風。調查研究雖然肇始于戰(zhàn)爭年代的特殊環(huán)境,但在50年代以來的科層體制下,仍被塑造為中共各級機構和人員最為重要的工作作風。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共在推行重大決策之前,多會選擇某一地方做典型試點,并在取得地方經驗的基礎上再行推廣。因此可以說,“調查研究”和“典型試點”是中共政策形成的最主要路徑。而這樣的政策形成之路,也決定了多數的中共政策在其形成過程中都會滲入地方經驗。這種特殊性使得地方在理解當代中國的整體歷史進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筆者以農業(yè)集體化政策的歷史演進為例,說明地方在中共政策形成和轉變中的重要性。眾所周知,推動中國鄉(xiāng)村走向集體化之路,雖然是毛澤東在革命年代就有的訴求,但50年代初期農業(yè)集體化的正式啟動,仍與基于地方經驗的兩場爭論有關:一是1950年的東北富農問題爭論,二是1951年的山西發(fā)展農業(yè)合作社的爭論。雖然沒有經過必要的調查研究程序,但東北和山西的經驗對毛澤東決定啟動農業(yè)合作化顯然有著重要影響。因此,要理解集體化的緣起,對東北和山西經驗的區(qū)域研究就顯得相當重要。研究者至少要搞清楚,在全面合作化到來之前,這兩個地區(qū)的農村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兩地的合作化要求是鄉(xiāng)村社會的內生訴求還是地方領導的政治推動?如果沒有建立在扎實基礎上的地域史研究,上述問題將很難回答。
再比如,毛澤東1955年在合作化問題上的思想轉變,直接帶來了中央的政策調整,并改變了農業(yè)集體化的歷史進程。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毛澤東的認識轉變?他本人有過兩次較為直接的解釋:一是1955年7月15日,毛澤東在和林鐵、吳芝圃等人談合作化問題時提到,是“看到浙江、安徽都搞了好幾萬個社,我的主意變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99頁。;二是1956年11月8日晚,在和柯慶施、曾希圣等人談話時,毛澤東再次提到“合作化就是先從安徽、浙江看到新區(qū)可以大發(fā)展,又看到黑龍江雙城縣希勤村的全面規(guī)劃,才使我有可能寫出《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那篇文章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7頁。。雖然不清楚毛澤東通過怎樣的方式和渠道看到了浙江、安徽合作化的“大發(fā)展”,但從其反復的強調不難得知,兩地的合作化經驗對1955年的合作化政策轉變具有關鍵性影響。
從集體化進程的歷史轉變看,地方在50年代中國的整體歷史進程中,并不都是完全被動的適應者,同樣也是政策形成的參與者。考慮到這一點,可以認為在集體化時代的鄉(xiāng)村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并非單純的壓迫適應抑或消極對抗,也有相互融合的一面。事實上,在政治力量的強勢主導下,研究者既無法切割出一個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社會,又不能忽略社會/地方在形塑國家中的重要性。如果僅以集體化的歷史演進為例,地方甚至會在形塑中央政策的過程中發(fā)揮著關鍵性影響。
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進程,決定了研究者如果要理解當代中國的整體歷史,勢必要以相應的地方研究為基礎。
二、“社會革命”與地域史研究的共識
幾乎所有的地域史研究,都有著“以小見大”的學術訴求。但“小”中并不必然隱藏著“大”,如何“見大”一直都是個問題。
對中共地域史研究來說,一方面需要盡力從地方的層面理解整體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又不能陷入強化地方特殊性的泥沼,以致形塑出一個脫離整體歷史進程的地方來。如何拿捏二者之分寸,的確并非易事。至少從目前的研究現狀看,能夠準確把握的研究并不多見,以致多數的地域史研究,要么是宏觀歷史敘事的地方版,要么是為某種既有的結論提供地方個案,難以真正實現“以小見大”的訴求。
筆者以為,出現上述問題,首先在于當下的多數地域史研究者沒有清晰的“問題意識”,甚至數量不少的地域史研究,將作為實然狀態(tài)存在的基層政策執(zhí)行偏差視為“研究發(fā)現”,這樣的理解顯然有失偏頗。再者,迄今為止的中共地域史研究,尚缺乏必要的“問題共識”。而“問題共識”凝聚的成功與否,將是中共地域史研究能否持續(xù)的關鍵。這里所說的“問題共識”,也是地域史研究能否開展跨區(qū)域學術對話的前提。通常強調的“問題意識”,主要是指特定的研究可否歸入一個既有的學術脈絡中,并和已有的研究形成有效的對話和討論。可以想見,如果沒有相互認可的“問題共識”,這樣的對話和討論將很難開展,地域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也就終不得見。因為離開了具體材料背后的“問題”勾連,研究者將很難尋找不同地域研究之間的共通之處,對話自然無從談起。
從其他時期的地域史研究看,“問題共識”的凝聚同樣重要。比如近年來在海內外學界較具影響的華南研究,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學術的生命力,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雖然將自己的研究視野放置在特定的區(qū)域甚或某一個村莊,但其背后有著宏大且有高度共識的問題關懷。按照科大衛(wèi)的總結,他們所要探尋的就是16世紀以來的“禮儀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科大衛(wèi)著,曾憲冠譯:《明清社會和禮儀》,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4頁。。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共識性問題,才使得跨越村莊甚或地域的研究,有了對話的可能,并彰顯了地域史研究的價值所在。盡管如此,還是有學者在最近的評論中指出,有著上述“問題共識”的華南研究,仍然會面臨著如何“走出華南”的困境。比如在近代大規(guī)模社會運動興起的背景下,如何處理跨區(qū)域的革命變遷,將是華南的地域史研究必須克服的挑戰(zhàn)。*楊念群:《從“逆現代化現象”看中國歷史人類學的興起》,高士明、賀照田主編:《人間思想》第4輯,人間出版社,2016年,第47頁。從當下的中共地域史研究看,這一困境確實存在。因為和華南研究相比,中共地域史研究尚未形成必要的“問題共識”,更遑論“走出地域”了。因此,對當下的中共地域史研究而言,如何凝聚“問題共識”應是當務之急。
那么研究者能否在50年代中國研究的范疇內,凝聚出猶如“禮儀革命”式的共識性問題呢?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比如以往的革命史研究,在談及50年代的歷史時,大多都會提到“社會革命”的問題,并以此凸顯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不過由于以往的研究被注入了太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因此很少從社會結構變動的角度,討論這場革命帶給中國社會的影響所在。一旦研究者將研究的目光投入社會結構的變動上,就可以發(fā)現,發(fā)生在20世紀中期的這場“社會革命”,對中國社會的改變可能會超過16世紀以來的“禮儀革命”,因為它的影響不止于社會結構而是深入到禮儀層面。探尋這場“社會革命”的發(fā)生及其在形塑當代中國社會中的作用和機制,理應成為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宏大關懷所在。但遺憾的是,當下的多數地域史研究,并沒有這樣的“問題共識”,甚至“社會革命”都已經很少成為嚴肅的學術討論話題。
“社會革命”之所以可以成為地域史研究的“問題共識”,主要是其在結構層面帶給中國社會的顛覆性影響,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在重構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基礎上,改變了長久以來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狀態(tài)。有關傳統(tǒng)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素來都有“皇權不下縣”之說。雖然這種說法在近年來逐漸受到挑戰(zhàn),但不能否認的是,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管控和今天仍是截然不同的,它還是更多地依靠諸如宗法家族勢力等社會層面的力量,并維持了相對意義的自治狀態(tài)。雖然自清雍正中期以來,國家權力鄉(xiāng)村化的過程就已經開始,但真正改變這種相對自治狀態(tài)的還是中共推動的“社會革命”,典型表現就是50年代的“村村建支部”。雖然以支部建設為支撐的政黨權力下移,并不代表著國家正式權力的基層化,但在集體化時代的黨政一體模式下,政黨權力和國家權力的高度同構,還是意味著中共從根本上顛覆了數百年來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這種新型權力結構的構造,也是地方能夠在中共政策形成中發(fā)揮關鍵影響的體制基礎。
孔飛力在討論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時指出,近代以來的中國政府始終面臨著如何更有效汲取稅負的問題,這也成為現代國家建設議程中“根基最牢固的一部分”*〔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92頁。。杜贊奇認為,雖然20世紀前半期的國家竭盡全力,“企圖加深并加強其對鄉(xiāng)村社會的控制”,以“為軍事和民政而擴大財源”,但“贏利型經紀”的增生和“政權內卷化”現象的出現,還是表明這場現代國家建設運動的失敗*〔美〕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38頁。。如果從稅負汲取有效性的角度衡量,真正完成現代國家建設的恰是中共推動的“社會革命”。正如孔飛力所言:“土地改革和集體化在行政上的作用,不啻于國家在更為深入的層次對于農村社會的滲透,也使得國家能夠對農村實行更為強有力的汲取。”*〔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第100頁。因此,從現代國家建設的視角,可以認為中共主導的“社會革命”是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一次根本性變革,影響和意義都顯著超過了16世紀以來的“禮儀革命”。
不過和華南研究對“禮儀革命”進程的深度揭示不同,“社會革命”還沒能成為當下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問題共識”,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今后的地域史研究,如果能夠從基層權力重構及現代國家建設的角度,將“社會革命”作為“問題共識”,或可走出“自說自話”的困境。
三、“制度結構”與地域史研究的視野
如果“社會革命”可以作為地域史研究的“問題共識”,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實現了,這一點同樣可以結合現有的地域史研究趨向來談。筆者最近兩年一直在做年度中共黨史研究的分析性評述。在大量文獻閱讀的基礎上,日漸感到當下的中共地域史研究存在著一個重要誤區(qū),即不少年輕研究者將主要精力投入到運動的研究,主要興趣在討論歷史演進中的非常態(tài)過程,似乎只有這樣的研究才能歸入學術研究之列。
雖然運動在中共革命中有著重要的影響,甚至1949年以后的社會治理也被學界稱之為“運動式治理”*李里峰:《運動式治理:一項關于土改的政治學分析》,《福建論壇》2010年第4期。,但若因此而將整個歷史進程全部視為運動的過程,顯然有失全面。實際上,即便1949年后的諸多“社會革命”進程表現為運動的形式,但在非常態(tài)的歷史進程之下,是否同時蘊含著一個常態(tài)化的制度建構過程,仍是需要討論的問題。比如統(tǒng)購統(tǒng)銷制度的研究,如果只從貫徹與落實的過程看,確實有不少運動化的特征,但不能因此掩蓋運動背后的制度化訴求,農業(yè)合作化的研究同樣如此。
地域史研究誤區(qū)的出現,主要是“問題共識”匱乏所致。有了“社會革命”的“問題共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筆者認為,要擺脫上述研究誤區(qū),今后的地域史研究或可從兩個方面來著力:一是加大對政策實踐引發(fā)的社會結構變動的研究;二是在持續(xù)關注非常態(tài)歷史進程的同時,加大對制度建構與實踐等常態(tài)化歷史進程的研究。
“社會革命”的最直接后果是社會結構的變動,因此,社會的結構性變動應該成為今后中共地域史研究的重點。在結構變動的視野下重估50年代的歷史進程,有助于重新審視究竟是什么樣的政治事件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進而明確地域史研究所應著力的方向。在這個問題上,孔飛力將集體化視為現代國家建構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是頗有深意的。因為就經濟層面而言,集體化帶來的土地產權的結構性變動是土地改革無法相比的,迄今仍是當下中國農業(yè)經營模式的制度基礎;就政治層面而言,雖然集體化并未改變土改之后的鄉(xiāng)村權力架構(比如國家的正式權力體系仍然止于鄉(xiāng)一級),但為適應集體化而加速的政黨權力鄉(xiāng)村化,卻在事實上改變了鄉(xiāng)村社會的自治狀態(tài),使其被納入政黨權力的體系當中。要推動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都需要一種結構化的視野,需要研究者從表面的過程深入社會結構變動的內部。
與結構研究相伴隨的是制度研究。雖然運動在某個時期可能會成為中共治理社會的策略選擇,但運動的暫時性也使其效應的維持成為問題。事實上,當運動成為中共治理社會的常用手段后,研究者最需要思考的恐怕就已不再是運動的邏輯,而是促使運動成為一種治理機制的制度基礎是什么?換言之,研究者需要放長歷史的視野,從一個更為宏闊的歷史場景中思考運動背后的邏輯甚至運動本身的機制化問題。如果帶著制度化的視野重新考慮運動,就不難發(fā)現50年代的很多運動都有著制度化的機理,并有向機制或制度演進的趨勢。
以50年代中期的落后鄉(xiāng)改造為例,目前的研究多將其視為中共發(fā)動的土改補課運動,或者是將其與農業(yè)集體化的推進聯系起來。如果只考慮當時的情形,這樣的分析并無問題。但若將研究目光繼續(xù)延伸,就可以發(fā)現在工作推進中,將人和機構進行先進或落后的分類,成為此后中共開展基層工作的重要機制,比如1957年開始的落后社改造以及60年代初期的三類社劃分,都有相似的邏輯。這就提示研究者,如果能夠跳出單一的運動,在更長的歷史時段來觀察運動的過程,自會發(fā)現運動本身就蘊含著制度的邏輯。因此今后的地域史研究,顯然要走出單純的運動視野,從制度建構和演進的層面揭示影響歷史進程的長期因素。
總之,如果要在整體上推動地域史研究的進展,“問題共識”的凝聚和研究思路的轉向都是必不可少的。以筆者之理解,“社會革命”可以成為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問題共識”,制度和結構則可以成為揭示“社會革命”的兩條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