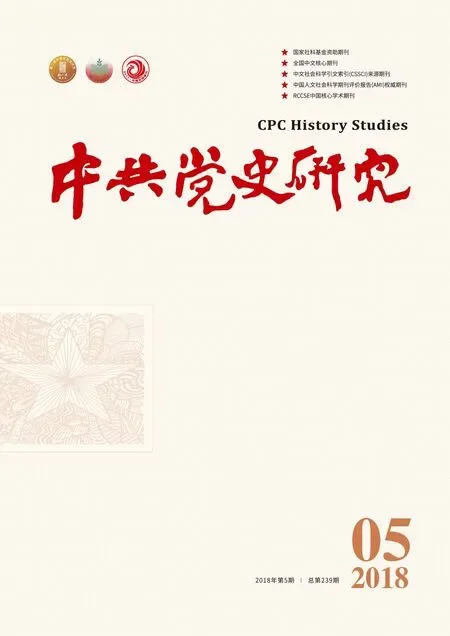關注“以城市為中心”的地域史研究取向及其意義*
金 大 陸
(本文作者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上海 200235)
自遼沈、淮海、平津以及渡江戰役以來,尤其是伴隨著“解放軍進城”,自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便有了“以城市為中心”的研究取向。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可謂政治宣言:“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1427頁。。
至此,從為啟動國家的工業化戰略而確立“城鄉二元體制”到以京滬兩大城市為策源地、以各省會城市為中心、以“城市—學生(工人)”群體為主干而展開的“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轉變,當代中國史的“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無不以“城市為中心”進行戰略布局,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無不圍繞著“城市發展”和“城市問題”(“人—物”關系與“人—人”關系)而演化和展開,其中有順風也有逆流,有經驗也有教訓,有成功也有挫折,而蘊涵著的核心問題是當中共從“革命黨”(“以農村為中心”)成為“執政黨”后,如何在適應和管理城市、建設和發展城市方面,走出一條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化道路。
然而,查詢比對現有研究文獻,即便以1949年黨的工作重心“移向城市”為標志,黨史研究領域雖有以城市居委會、流民改造、報業改革、公私合營、工人勞動生產等選題,但更多的研究還是集中于與鄉村相關的土地改革、合作化、統購統銷、公共食堂、糧食危機及城鄉社會改造等方面*韓鋼:《中共歷史的民間研究之境界》,《北京日報》2011年7月25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倡導多立足于城市,多側重于城市,即以城市的眼光去搜尋線索,發現問題,進而構筑解釋框架。城市史理應成為中共地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國內外學界圍繞“地域共同體”的討論,大致有“水利共同體”“基層市場社區”“祭祀圈”等幾種學說*孫杰、孫競昊:《作為方法論的區域史研究》,《浙江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這種以“社會經濟史”為主導的意見,實際上是強調“社會歷史發展中,由具有均質(同質)性社會諸要素或單要素有機構成的,具有自身社會歷史發展特征和自成系統的歷史地理單位”*徐國利:《關于區域史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學術月刊》2007年第3期。,“均質(同質)性”由此成為區域界定的基本條件。應該承認,這種解釋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和學術價值,甚而成為地域史定位的一般原則。
但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并不認定“一般原則”的絕對意義。所以,在地域史研究中標樹“以城市為中心”的觀點,亦不應絕對認同“均質(同質)性”原則,反而應以認同“非均質(異質)性”為準則。諸如直轄市中的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省會城市中的哈爾濱、廣州、西安、拉薩,省屬城市中的唐山、蘇州、桂林、石河子,除了可尋找自成關聯的“地域共同體”的線索,卻均有自成系統的“歷史—地理—治理”的淵源和構造。這是因為“地域史”概念在學理上的界定和在學術上的運行,不管是“均質(同質)性”還是“非均質(異質)性”的特征,終究要以“歷史—地理—治理”的時空劃分為范圍和目標,以至所謂“地域”實際就是一個“歷史—地理—治理”的空間結構、一個“歷史—地理—治理”的行政區劃。當然,此說并不排斥“地域共同體”的觀點,兩者在歸結點上并不矛盾,只是不能相互涵蓋和通約。
眾所周知,在中國廣袤的版圖上,自古代、近現代乃至當代以來,各類城市從雛形到更新、從建設到發展,除了與自然地理的“山川形變”有關,均離不開歷史地理范疇的“歷史活動主題和歷史活動過程兩個維度”,以及“時序、紀事和變遷”等要素*龍先瓊:《試論區域史研究的空間和時間問題》,《齊魯學刊》2011年第1期。。這就是說,以“城市為中心”的眼光來看“地域史”,首先要肯定城市是地理、歷史與政治治理的合體,又因城市集中了所在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資源,自然成為行政管轄的中心,且對周邊甚或更廣闊的社會流域產生輻射和影響。在此前提下,再確證不同歷史階段的“行政區劃”即一個歷史地理的單位,便不僅梳理了城市史演變的結果(含人口、建筑和社會生活等),更把握住了城市研究的根據和重心。
回到黨史研究的范疇,就可見在跨過1949年的當代史版圖上,1954年6月,政務院發文將沈陽、旅大、鞍山、撫順、本溪、哈爾濱、長春、武漢、廣州、西安、重慶等11個中央直轄市改為省轄市;1958年,國務院決定將河北省的通縣、順義、大興、良鄉、房山、懷柔、密云、平谷、延慶共九縣和通州市劃歸北京市,將北京市的行政區域拓展到16807平方公里。這一統籌和增量,正體現了以城市“行政區劃”為切入口的研究方向(歸屬與管轄)。再以上海市的“行政區劃”為例,1949年時上海市轄域面積僅為618平方公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63頁。,中央此后決定上海的功能定位就是建設“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基地”。但上海城區局促,人口密度高,哪來滿足發展兩大基地的空間呢?在中央的協調下,江蘇省于1958年將上海、嘉定、寶山、川沙、南匯、奉賢、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十縣劃歸上海市,使上海市的轄域面積陡然擴展十倍,增至6185平方公里。事實證明,這一區劃調整的決策,不僅適應了國家工業化的戰略要求,更因整體改變了“大城市、小郊區”的空間格局,對疏散人口、發達交通、促進農副業生產乃至重塑新時期上海的城市功能即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等,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此來看,考察城市管轄地域的歷史演變過程(含城市內部的調整,如上海先后在原川沙、南匯等地界建立浦東新區,將原南市區、盧灣區劃歸黃浦區,等等),就是在性質和內容上確證了“以城市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其引申出的問題構架——上至國家戰略,中至城市治理,下至百姓生活——可全面而立體地展開,此命題也就在理論規范中獲得了方向與活力。
然而,不管是直轄的北京市、上海市還是省屬的青島市、寧波市、武威市等甚或地級市、縣級市等等,面對“中央”都是“地方”——此為黨史研究的要點和側重之處。故而,“地域史”研究多應遵循“上下呼應”“以小見大”“以點帶面”“互為比照”的思路。
一看“上下呼應”。傳統的宏觀史研究多取“從中央到地方”的研究路數,因為中樞的結構與組合、決策與運作決定了這個框架是至上的、籠罩的和輻射的(可稱為“上端”)。反之,若以省區或以地縣的區劃為研究的出發點,自然屬于“地域史”的框架(可稱為“下端”)。然而,現實的問題是當宏觀史的政治傾向決定了道路和形勢的指歸,地域史的展開不可能脫離這一政治指引,但因地域的狀況各有不同,其呈現的現象、過程和結果的差異以及事態、事件和事變的特殊,往往疊床架屋、繁復多變,恰恰可以多側面、多角度地觀照和剖析來自“上端”的政治決策(傳達與告喻)與取之“下端”的政治落實(理解和執行)之間的關聯和變移。事實上,以筆者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例證來看,“上端”的政治決策也往往注意“下端”的舉措和經驗,并加以吸取、總結、提升和推廣,成為“上端”的意志和政策的體現,如大串連時期推廣大連海運學院的徒步串聯;1973年,毛澤東回復福建知青家長李慶霖的信,指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并“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77頁。,從而引導各地的知青政策有所調整;等等。在一些情況下,因“下端”的一些情態和事變,往往導引了整個政局的嬗變和走向,如1967年武漢的七二○事件,1976年上海《文匯報》的三五、三二五事件,等等。正是立足于此,整體史與地域史既是統一的、貫通的又是分流的、多元的。研究者通過“上下呼應”,把捉其間的互動和歧異,便可將地域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更通達的位序上。
二看“以小見大”。地域史的研究脫離不了整體史的大框架,即地域史的各要素不能是封閉的或孤立的,這就決定了它應具備“以小見大”的功能和責任,當然這也與目前其所遭受“碎片化”的批評有關。顯然,高端政治的每一個片斷(一個會議、一個講話、一個批示、一次會面、一次出行、一次活動等),因關系到國家的戰略布局和政策演變,以至在高屋建瓴的宏觀敘事的史學建構中,大都沒有“碎片”的感覺和認知,這是由國家宏觀史的框架和性質所決定的。而落實到地域史的研究中,因史料的內容歸宿和問題取向,均合圍在一個具體的歷史地理的區劃中,開掘它、剖析它、展示它,卻因時空的限制,便多被指認為具有“碎片化”的傾向。但問題在于,“碎片化”的特征是由地域史研究的學術定位決定的,甚或是以高層政治史的視角來指認的,以至于有學者聲稱:“中國區域史研究的碎片化趨勢不可避免,且是區域史研究的方向所在。”*高福順:《碎片化與全視野中國區域史研究的價值取向》,《史學集刊》2014年第3期。其實,歷史的演變具有地域的多樣性。所以,問題的要害不在于地域史研究本身,而在于地域史研究存在的欠缺和差失,那就是時下不少的研究論文(含碩博士論文)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傾向,即只從題目需要梳理該地域史的情況和內容,既不能放射出去,與“民族—國家”“黨政—治理”的大政方針發生勾連;又不能沉潛下去,讀透材料背后的承續和堂奧,所謂“問題意識”遭到泛化和虛設,為“問題”而“問題”,難以通過“破解/解釋”的路徑建立起“問題構架”。一言以蔽之,地域史研究中的“以小見大”,就在于能夠把握某種根本性的關系和問題,揭示出課題內含的典型價值和普遍意義。
三看“以點帶面”。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因地域史研究脫離不了時空積淀的文化類型,自然與社會史的研究存在同構關系。尤其“以城市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因輻射面極其開闊,所以除了要正視與高層相呼應的政治理路,還必須關注該行政區劃內“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習俗”等諸方面的情況和事態。具體而言,就是要用歷史演變的眼光,關注城市的發展與管理,如城區建設、交通規劃、工商金融及經濟結構、社會組織等功能;關注文化精神,如學校教育、新聞出版、文體藝術及審美風尚、文明素養等水準;關注市民生活,如民居環境、商品供應、消費水平及人際關系、社會倫理規范等狀況。就此,政治史的“點”帶動社會史的“面”,一層層地形成立體結構,做到既有立足點又有展開面,張弛有度,分合有序,自然有利于地域史研究根據課題的需要,獲得新的材料和視野。
四看“互為比照”。因“以城市為中心”的取向不絕對認同“均質(同質)性”,而取“非均質(異質)性”的地域史研究原則,故有必要強調城市之間“互為比照”的觀點和方法。其實,在中國的城市史版圖上,東南西北中各類城市的肇始和更新,其經濟和文化等均有深遠而獨特的“歷史—地理”緣由。在黨史研究領域,便可見“上青天”(上海、青島、天津等)等沿海城市與內地城市在工商業及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異;即便在知青上山下鄉時期,京津滬等城市均有知青的跨省區安排,如北京知青在延安、天津知青在黑龍江、上海知青在云南等,江蘇、廣東、福建和遼寧等所屬城市的知青則多為省內安排。由此可見,各類城市因情況復雜,地域差異性大,不平衡性明顯。通過跨地域的“互為比照”,就可以既看多樣性又看特殊性,更可在差異和類同中反觀自身的地域特征。這無疑將有助于研究者站在一個聯通的角度,針對地域史研究課題的需要,建立起合理且富有彈性的“問題構架”。
綜上所述,標樹以“以城市為中心”的地域史研究取向,應成為“跨越1949年”以來黨史研究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