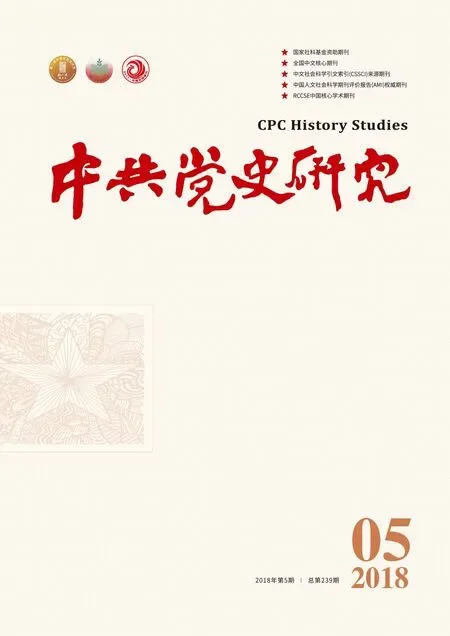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與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深化*
阮 清 華
(本文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1)
地域史研究的興起無疑是新世紀以來黨史國史研究領域較為引人注目的新動態。作為對于此前黨史國史研究中某種宏大敘事模式的揚棄和改進,地域史研究為黨史國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產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地域史研究可謂方興未艾,不僅許多黨史、國史的碩士生、博士生以地域史為研究對象,而且許多中青年教師甚至一些原本從事古代史、民國史研究的教授也開始涉獵當代地域史研究,為進一步推動地域史研究注入了新動力。但檢視目前地域史研究的相關成果,筆者發現作為地域中心的城市,在地域史研究中卻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城市史研究顯得尤為薄弱。而毛澤東時代的城市發展,無疑是當代中國城市建設史上極為重要的階段。加強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是深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一、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的成就與不足
目前學界關于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整體性的成果主要有兩套。一套是20世紀90年代由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史工作部門和中央有關單位協作編纂的《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叢書。該叢書主要收集解放戰爭后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的接管、改造和建設中所形成的重要文獻資料、當時主政者的主要文稿以及有關重要事件的回憶錄和統計資料,總體上是一套城市接管和初步改造的資料集。目前已有數十個城市的黨史研究部門收集了大量史料,完成了叢書的出版工作,但該叢書的資料利用率非常低。另一套是由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牽頭、中國城市史叢書編委會組織編纂出版的《當代中國城市發展》叢書。這套書目前已經出版了十幾個城市的專著,大多數都是從該地城市的起源開始,分門別類敘述各城市社會發展變化的歷史,下限一般都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因而對毛澤東時代城市社會的發展變化大都有所涉及,但基本上是一帶而過。
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的另一類成果是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各項政策和事件的研究。如關于城市接管政策的形成、變化與執行,以及中共主要領導人有關城市接管方面的思想和貢獻,或者是具體城市的接管介紹等;關于具體政治事件或政治運動的研究,如關于“三反”“五反”運動、底層社會改造等;或者是與城市人相關的歷史研究。目前比較新的研究成果則開始關注新中國成立后都市社會的變遷與延續等問題,為進一步理解當今中國城市社會的變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James Z.Gao,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2003; 姜進:《斷裂與延續: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張濟順:《轉型與延續:文化消費與上海基層社會對西方的反應》,《史林》2006年第6期;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中國當代史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是舉世罕見的,其敘事空間混雜著關涉歷史和現實、政治和學術的各種言說,既有嚴謹的科學之論、探微之作,也有大量因襲舊說、重復雷同、粗制濫造的讀物,還存在著許多造成誤記和誤讀的情況*王海光:《時過境未遷——關于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5期。。總體來說,中國當代史研究已然起步,“‘流水已到,渠成有待’,不遠處將會響起澎湃的潮聲”*王家范:《對當代史研究的期望》,周武主編:《上海學》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頁。。但目前當代中國史研究極不平衡,不僅存在宏觀歷史、中觀歷史和微觀歷史的不平衡,甚至還有很多空白領域無人問津,無法形成總體史的研究態勢。得益于大量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鄉村研究,許多帶有經典意義的著作的出版和流行,加深了人們對于當代中國前30年農村社會變遷和基本生活場景的了解;但對于當代中國更為重要的城市而言,相關研究卻顯得十分薄弱。作為超越“地方史”而具有整體意義的地域史研究而言,必須將城市與鄉村納入同一體系中加以研究,才能更為完整地揭示出當代中國前30年歷史變遷的基本規律。
二、加強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的必要性
加強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但目前研究現狀顯示并非如此簡單。因此,筆者認為需要在此進一步論證加強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的必要性,尤其進一步論證加強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對于促進和深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作用。
首先,新中國成立以后,城市成為中國共產黨治理的中心地帶,成為中共工作的重心所在。只有加強城市史研究,才能弄清楚當代中國前30年的社會變遷及其背后的理念與原因。城市是人類思維的創造物,是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和各種活動的聚集體*〔美〕愛德華·克魯帕特著,陸偉芳譯:《城市人:環境及其影響》,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第3頁。。正如馬克思所說:“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頁。尤其是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城市更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場所。許多中國城市的歷史非常悠久,雖然在很長時期內整個國家的城市化率不高,但城市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依然越來越大。中共雖然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也曾長期堅守農村,但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 “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移到了城市”,開始了“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城市工作由此成為中共的工作重心。
城市作為人口和各類資源集聚地,能夠更好地在短時間內集中和交換資源,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作的社會價值。中共接管城市后,黨政軍等領導機關幾乎全部遷入城市,城市無可爭議地成為各級行政中心。在以重工業化為目標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人民政府進一步將優質資源集中到城市,城市也成為各區域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可以說,中共入城以后,城市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命根子”*馮筱才:《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命根子”:1959—1961年上海的糧食緊張及應對》,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7卷“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中華書局,2013年,第223頁。,是中共新政權建立和鞏固的最重要陣地,也是中共施政的基礎。
其次,城市是理解中國社會的重要窗口。有海外學者指出:“研究中國社會,都市問題是一個關鍵。”*〔日〕斯波義信著,布和譯:《中國都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2頁。著名學者施堅雅也肯定:“(中國)城市的發展——城市的形成及其中心職能的發展——是地區發展的一個關鍵性因素。”*〔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編,中華書局,2000年,第242頁。研究中國古代到近現代社會,必須重視城市問題;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城市問題更是關鍵中的關鍵。新中國成立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改造,建立起以“生產”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會。這一被改造過的城市,既不同于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城市,也與當今中國城市社會存在巨大差異,更與國外城市具有天壤之別。以“生產基地”為目標的城市改造,將原本城市具有的消費性和服務性以及創新性和親近性等特征大部分加以消除,城市成為一個個生產單位以及圍繞著生產單位的居民組織和各種為單位人群服務的機構的集合體。像上海這樣原本國際化、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經過改造,雖然表面上“摩登依舊在場”,然而“都市迅速遠去”了*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第17頁。。“都市性”作為城市的最基本特征,在共和國城市中卻曾經漸行漸遠,但城市又的確是共和國時期最為重要的基地,所以研究者必須要通過共和國時期的城市,才能理解共和國時期的整個社會。城市作為觀察共和國前30年社會的最為重要的窗口,必須加強相關的歷史研究。
再次,從地域史的角度來說,城市是地域之中心,加強地域內城市史的研究,無疑是加強地域史研究的中心工作,更是深化地域史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施堅雅在研究中國農村基層市場時提出了著名的集市體系理論,認為中國農村集市網絡是一個包括農村集市、鄉鎮和中心城市的三級“市場共同體”。在市場共同體中,中心城市既是地理上的中心,也是市場的中心,是人員交流和物資集散的中心;而此中心城市又是更高一級城市體系的基礎,幾個中心城市共同圍繞一個更高層級的城市組成更高一級的市場共同體。*〔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編,第329—343頁。盡管這一模式受到諸多挑戰和批評,但至今無人能予以徹底顛覆或推翻,而只能不斷修正和完善它*任放:《施堅雅模式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在“施堅雅模式”中,城市無疑是地域的中心,不同層級的城市是不同規模級別的地域中心,而整個中國則被分成九大區域,形成幾個巨型城市。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建設的展開,在全國一盤棋的統一安排下,政府更多介入市場,使得原本大體有序的市場體系出現巨大變化。人口和物資的流動不再單純遵循市場運行規律,而是夾雜了更多的政治邏輯。在這一背景下,地域的界線變得更為模糊,尤其是隨著大型公共建設的開展,交通條件的極大改善,許多原本難以企及的地方變得容易到達,極大地改變了地域的范圍和邊界。但是,不管地域邊界如何變化,地域范圍如何伸縮,地域內的城市總歸仍然是地域中心。研究地域內的城市史,將城市史置于整個地域史的核心位置來加以研究,更有助于從整體上了解整個地域的發展規律,進而揭示更高級別的地域史乃至整個中國當代史的特色和發展規律。
最后,當今中國的城市化正在快速發展之中,研究共和國前30年的城市史,有可能給當今城市發展提供經驗借鑒和智力支持。1949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10.64%,經過近30年的發展,到1978年達到17.92%;改革開放后,中國駛上城市化發展的快車道,2011年的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市人口總量超過農業人口的總量*王凜然:《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中國當代史研究新課題》,《蘭州學刊》2016年第10期。。截至2017年末,中國城鎮化率更達到58.52%*《統計局:中國2017年末城鎮化率為58.52%》,新浪財經2018年1月18日,http://finance.sina.com.cn/7x24/2018-01-18/doc-ifyquixe3813845.shtml.。中國已經完成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化,中國的城鎮化率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會繼續提升。因此,急劇發展變化的城市化,需要相關科學研究的跟進,而作為諸學科最重要基礎的城市史學自然應該當仁不讓地承擔起自身的職責。就世界范圍來看,城市雖然有幾千年的歷史,但作為研究城市的學科——城市學直到17世紀至18世紀才伴隨著歐美工業化、城市化運動的步伐得以創建,專門研究城市問題的城市社會史學、城市史到19世紀20世紀之交才在城市化發育充分的美國等地開始形成,城市史取得獨立的學科地位更是要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而這些學科之所以在當時出現,就是為了回應和處理這些地區在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所面臨的各種需要解決的問題。*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論》,《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的城市化發展,盡管無論從規模還是發展的速度和方向上都存在巨大差別,但是前30年城市發展所積累的經驗以及存在的問題,可能都對當今中國城市化發展具有某種正向或反向的價值和意義。積極研究前30年的中國城市史,充分挖掘和分析前30年城市發展、變化的各類資源,總結經驗,歸納教訓,并進而上升到理論層面,可謂正當其時。即使共和國前30年的城市具有與世界各地城市很不一樣的特性,但是城市依然是集聚人口和資源的最重要空間,并隨著改革開放而越來越恢復其原本應該具有的“都市性”、服務性和創新性等基本特征,城市也終將在中國取得勝利*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早就宣布,作為“最健康、最綠色、最富裕、最宜居的地方”,“城市已經取得了勝利”。〔美〕愛德華·格萊澤著,劉潤泉譯:《城市的勝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第2頁。筆者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推進和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城市也必將在中國取得勝利。。但是這種勝利最終應該是理性和良性的,而不能重蹈西方城市發展已經歷過的各種問題,更不能繼續走中國前30年歷史已證明不良或不夠健康的城市發展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加強對共和國前30年城市史的研究,梳理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城市發展和社會變遷的基本情況,總結經驗教訓,也是歷史學回應當下中國城市快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毛澤東時代城市史研究的方向和議題
城市史應該是以城市文明興衰為主軸的專門史,但作為中共地域史研究核心的當代城市史研究,其方向和議題則與傳統的城市史研究有所不同:它既應該包括傳統城市史所關注的城市文明發展變遷過程,也必須更多地體現作為地域核心的城市在當代中國前30年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而解釋今日中國城市發展的路徑選擇。
首先,要厘清毛澤東時代中國城市的基本功能定位,即“變消費的城市為生產的城市”。不同歷史時期城市的發展必然受到其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規定和制約,因而也呈現相應的時代特色。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提出將來改造城市的基本目標就是要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基地”,強調突出城市的生產功能而弱化城市的消費功能。可以說,這個基本定位是中共城市政策的基本前提和改造城市、建設城市的所有方針政策的著眼點。明乎此,研究者對當代中國城市史上的很多問題才可能提出新的解釋,也才能理解政策初心之所在。如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持續不斷采取措施疏散大城市人口,似乎走上了一條與城市化發展背道而馳的路。但因為新政權施政的基本目標是帶領中華民族走上富國強兵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而這一目標選擇應該會自然而然地導致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如何理解這一矛盾?實際上這既是新政權集中資源建設重工業的無奈之舉,更與中共對城市基本功能的定位有關:只有將大量不直接從事現代工農業生產的“消費性人口”遷移出城市,才能保證城市的“生產基地”功能。另外,與之相關的大量中小企業、學校、醫院、文化機構、劇團等單位的外遷和疏散,雖然同樣有各自的原因,但背后也都受到城市基本功能定位的影響。
其次,要加強當代中國城鄉關系史研究。城鄉關系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對重要關系,也是中共地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打通城鄉關系的關鍵要素是移民。移民是城市人口增長的最重要動力。一般而言,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城市人口會越來越多。根據移民研究中的“推—拉”理論,人口會向著有吸引力的地方流動。近代以來中國城市具有強大的拉力,而鄉村則由于生產的衰落和破敗而具有強大的推力。這一推一拉,自然使得近代以來原本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民大量涌入城市,這也是近代中國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途徑。但是新中國成立后,城市對農村人口產生了巨大的推力,拉力雖然也在,但人為的更為強大的推力卻將農民阻擋于城市之外。同時,農村原本對人口就有一股強大的推力,但1949年后,城市人口卻大量向農村推,導致農村不僅不能推出自己的多余人口,反而要接納更多城市人口。因此農村對人口不僅有推力,實際上還有一股強大的拒斥力,希望將外來人口排除在本鄉本土之外。在人口的遷移進程中,不僅有推拉,還有拒斥與反推拉,這就導致大量人口在城鄉之間反復奔波,是為當代城鄉關系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中國的城鄉關系。這些關系如何發揮作用,如何影響城市和鄉村社會,都是黨史學界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
再次,要加強毛澤東時代城市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這也是加強中共地域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諸如《翻身》《十里店》《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林村的故事》等著作以及許多相關論文,使人們對改革開放前農村生活的基本場景已經有了很多認識和了解,對于集體化時期的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多少有所了解,但由于缺乏有分量的城市社會生活史研究,人們對同時期的城市則知之甚少。關于集體化時期城市居民如何生活和娛樂、城市里各單位內部的生產生活如何開展、政治運動如何發動、單位以外的里弄街道如何適應社會主義生活等課題,目前雖然也有一些研究,但仍然極為薄弱。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地域史研究不能缺少人們的生活史,尤其是共和國時期的地域范圍和界線大都有所變化,因而也都加入了新的因素,具有了新的特征。只有研究地域內人們的日常生活史,尤其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史,研究者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當代中國地域的整體歷史。
綜上所述,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繼續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口進入城市生活,生活環境的改變已經并將繼續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完全可以這樣說,在決定行為方面,一個人成長的物理背景和一個人居住的地方,每一點都與一個人的基因傳承或社會階級一樣重要”*〔美〕愛德華·克魯帕特著,陸偉芳譯:《城市人:環境及其影響》,“前言”第1頁。。城市的發展變化深刻地影響城市及其周邊地區每一個人的生產與生活。加強毛澤東時代城市史、城鄉關系史的研究,是深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應有之義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