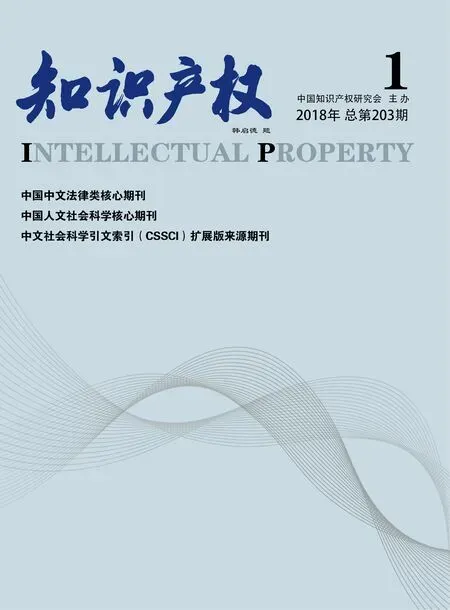論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的訴權
張 軼
一、問題的提出
除專利權人之外,我國法院還受理由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提起的專利侵權之訴。①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7)杭民三初字第108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浙知終字第83號民事判決書;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陜01民初1044號民事判決書;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陜民終89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1084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中中法民三初字第83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粵高法民三終字第229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406號民事裁定書,等等。在約定的期間和地域范圍內,獨占被許可人幾乎獨自享有源自專利技術的所有利益。而“僅僅”關心許可費收入的專利權人,特別是在許可費與許可產品銷量不掛鉤的情況下,常常會對相同市場內非法使用專利技術的一切行為熟視無睹。直接賦予獨占被許可人訴權以助其破解這一困境,似乎成為不容置疑的高效便捷手段。然而,該解決方案卻同時制造了諸多新的難題。首先,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起訴之后,作為權利人的許可方就同一侵權行為再次提起訴訟,法院應當如何處理。如果法院受理專利權人之訴,則有可能不當加重侵權人的負擔或者浪費司法資源;如果不予受理,則對真正權利人提起之訴的駁回又會明顯缺乏法律依據。其次,就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作為原告獲得的損害賠償,專利權人是否可以要求參與分配。如果專利權人有權要求參與分配,那么訴訟成本、舉證責任如何分配。如果不向專利權人分配損害賠償,那么如何合理回應權利體系內權利人之權利受到侵害的事實和法律定性。最后,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作為原告獲得的損害賠償,是否應當等于自己因專利侵權所受損失,還是可以擴展至為權利人特別設計的賠償計算規則,即等于侵權人得利,或者甚至可以采用法定賠償。前述問題均難以在保障足夠尊重現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做出滿意答案。盡管如此,知識產權立法者依然做出了明確選擇。現行《專利法》第60條授權利害關系人在專利侵權發生時起訴侵權嫌疑人。雖然該條中利害關系人的概念并不明晰,而且其適用范圍難以單獨借助法條自身解釋得以明確,②不過在一次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座談中有所提及:“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的起訴人,可以是合同當事人、權利人和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包括獨占、排他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參見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國部分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法[1998]65號)。在關于訴前程序的規范中,“利害關系人”包括了獨占被許可人,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2001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79次會議通過,法釋[2001]20號)第1條“……提出申請的利害關系人,包括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單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排他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在專利權人不申請的情況下,可以提出申請。”可能是這個原因,也有學者被迫使用,如獨占被許可人權利“間接”被侵犯之類的模糊概念,參見徐紅菊著:《專利許可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頁。但是與《專利法》第60條目的、功能極為接近的《商標法》第60條與在內容與行文方面均保持高度一致,同樣做出了允許利害關系人起訴商標侵權行為的規定。較專利領域規范更為詳盡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明確將商標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列為享有訴權的利害關系人,③該規則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如劉春田著:《知識產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頁;李明德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頁。甚至有學者認為商標權人“讓渡該范圍內的訴訟權利”,參見黃暉著:《商標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頁,然而,這種對被許可人訴權的解釋顯然與中國法律明確禁止訴權轉讓的規定沖突。并進一步在各類交易主體之間分配訴權:獨占商標被許可人可以單獨向法院起訴;排他商標被許可人可以和權利人共同起訴或在權利人不起訴的情況下自行起訟;普通商標被許可人僅在商標注冊人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起訴。學界主流觀點明確認同上述商標案件規則在專利許可領域內的類推適用,④如李明德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頁;徐紅菊:《專利許可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林廣海、邱永清:《專利權、專利許可使用權與專利許可合同——以物權法原理借鑒為視點》,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6期,第18頁;董美根著:《專利許可合同的構造:判例,規則及中國的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頁。但也有個別觀點認為在許可人不作為時被許可人享有訴權,見張耕:《試論知識產權被許可人的訴訟地位》,載《特區經濟》2005年第4期,第230頁。支持獨占及排他專利被許可人享有訴權。⑤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保護實務全書》,中國言實出版社1995年,第309頁;林廣海、邱永清:《專利權、專利許可使用權與專利許可合同——以物權法原理借鑒為視點》,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6期,第18頁。也有個別觀點不區分絕對權與相對權,一概認為知識產權人和被許可人的使用權均被侵害,見洪永洋:《解析商標侵權案中被許可人的訴訟地位》,載《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12期,第67頁。或略顯模棱兩可,參見董美根著:《論專利被許可人的訴權》,載《科技與法律》2008年第4期,第49頁,不承認用益權但認可訴權,其理由尚未涉及爭議問題本質,參見董美根著:《專利許可合同的構造:判例、規則及中國的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頁,應當指出,名為許可的轉讓是法律明確排斥的。所述解決方案利弊兼備的情況下,制度修正時應該如何權衡;《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的規定是否應當受到認同,依然值得深入反思。本文分析將從法律體系自洽和制度創新需求兩個層面分別顯示,在現行法律體系內賦予專利被許可人訴權依然屬于立法者(司法解釋制定者)和學界判斷的失誤。更佳的解決方案是,在立法論層面全面否認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提起侵權之訴的權利,修改《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特別是《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的相關規定。針對法律修改之前的被許可人起訴案件,建議就損害賠償在專利權人與被許可人之間做出符合民事法律基本理念的分配。
二、體系中的內在沖突及其解決的失敗
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的訴權無法在解釋論層面得到充分且合理的有力解釋,《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特別是《商標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的正當性受到挑戰。
(一)體系內的沖突
《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直接賦予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訴權,引發前述弊端,并非難以預料。在物債二分的民事財產權利體系中,當作為絕對權的專利權受到不法侵害時,作為債權人的
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不應享有訴權。排斥債權侵權早已作為民事法律制度的根基之一在學界形成共識。比如,特定物買賣合同標的在交付前被盜的,買受人無法以自己的名義起訴盜竊人。有權提起侵權之訴的,為合同標的所有權人。支持該制度正當性的諸多理由在此無需贅述。⑥比如誘發廣泛道德風險。與實體法相呼應,我國民事程序法,除公益訴訟等極個別被法律明確的法定例外,⑦其他特例有破產清算組織,信托特性的集體管理組織訴訟等。齊樹潔、蘇婷婷:《公益訴訟與當事人適格之擴張》,載《現代法學》2005年第5期。只允許絕對權受到侵害的權利主體提起侵權賠償之訴。⑧主流觀點僅支持絕對權權利人的訴權,常怡、黃娟:《司法裁判供給中的利益衡量:一種訴的利益觀》,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4期;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頁;張耕:《試論知識產權被許可人的訴訟地位》,載《特區經濟》2005年第4期,第231頁。又如,眾所周知,當未成年子女的絕對權(如健康權)受到侵害時,其父母也只能夠以代理人的身份到人民法院起訴,而無法以自己的名義起訴。民訴法雖然也對利益相關人提起訴訟作出細致規定,⑨肖建華:《正當當事人理論的現代闡釋》,載《比較法研究》2000年第4期。但顯然其范圍均受限于確認之訴。⑩如確認婚姻無效之訴。肖建華:《正當當事人理論的現代闡釋》,載《比較法研究》2000年第4期。由于《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特別是《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所指均為侵權損害賠償之訴,?邵明著:《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頁。獨占被許可人享有訴權的事實已經突破了合同的相對性原則,與前述民事訴訟法以及民法的原則形成鮮明抵觸。?《民事訴訟法》第119條規定的起訴條件,原告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而《商標法》第60條以及《專利法》第60條的要求僅僅為利害關系人。現有文獻中雖然不乏對域外相關規定的介紹,?董美根:《論我國商標侵權訴訟中被許可人之訴權》,載《知識產權》2015年第2期,第24-25頁;董美根:《論專利被許可人的訴權》,載《科技與法律》2008年第4期,第48-49頁;王峽:《試析商標被許可人的訴權依據》,載《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第38頁;張強強、劉仲秋:《知識產權被許可人的訴權性質探析——以二元知識產權體系為理論視角》,載《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32頁。但往往缺少對相應國家民訴基礎制度的分析。?與之相關的甚至還有實體法中的財產權利體系制度。就諸多外國法對知識產權獨占被許可人,甚至普通被許可人訴權的規定?是否享有訴權,以及肯定訴權的情況下對訴權各類可能的限制。所進行的列舉,?董美根:《論我國商標侵權訴訟中被許可人之訴權》,載《知識產權》2015年第2期,第24-25頁;董美根:《論專利被許可人的訴權》,載《科技與法律》2008年第4期,第48-49頁;王峽:《試析商標被許可人的訴權依據》,載《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第38頁;張強強、劉仲秋:《知識產權被許可人的訴權性質探析——以二元知識產權體系為理論視角》,載《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32頁。對于在中國法體系內,特別是在尚未確立德國民事訴訟條例意義上的任意訴訟擔當制度的背景之下,?即“Gewillkürte Prozessstandschaft”;“Gewillkürte Prozessstandschaft”制度的存在客觀上擴展了相關主體具備原告資格(Aktivlegitimation;Aktivlegitimation des ausschlie?lichen Lizenznehmers)的法定條件,使得利益相關的非權利人在絕對權權利受侵害時也可能起訴;德國民訴法具備任意訴訟擔當作為制度基礎,但立法者包括學界的基本態度(即使獨占被許可人處境和各方利益格局極為近似)在專利和商標領域呈現明顯差異:一方面,盡管德國專利法未作規定,學界普遍支持獨占被許可人在許可合同沒有相反約定的情況下享有訴權,而不論該獨占許可合同是否登記,參見 Kra?er, Patentrecht, 5. Auぼ. 2004,§ 36 II 1. II 2; Keukenschrijver, in: Busse/Keukenschrijver, PatG, 6. Auぼ. 2003, § 139 Rdnr. 25;另一方面,由于德國商標法(§ 30 Abs. 3 MarkenG)未予區分普通和獨占被許可人,統一規定商標被許可人僅在權利人同意的情形下才能夠提起商標侵權之訴(“Der Lizenznehmer kann Klage wegen Verletzung einer Marke nur mit Zustimmung ihres Inhabers erheben”), 獨占商標許可許可未能支撐被許可人享有訴權(慕尼黑州高級法院OLG München, Mitt. 1997, 123 - Fan-Artikel),學界中僅有部分學者認同獨占商標被許可人的獨立訴權,且局限于特定情形,如商標權人不起訴且不授權足以被認定為違反德國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Grundsatz von Treu und Glauben, § 242 BGB )之時,詳見Bühling,GRUR 1998, 196, 198; Pla?, GRUR 2002, 1029;而主流觀點與立法者態度一致,例如Schwendemann, Markenrecht in der Praxis, Poeschel Stuttgart 1988, S.87; Busse/Starck, Warenzeichengesetz, de Gruyter Berlin 1990, § 8 Rdn. 10; Müller, Die Warenzeichenlizenz, M. Dittert & Co Dresden 1940, S. 52, 61 f., 79; Heydt,Gleichzeitige Benutzung derselben Marke durch mehrere Personen und Marken von Inhabern ohne Gesch?ftsbetrieb, GRUR 1958, 457 (459); Forkel, Zur dinglichen Wirkung einfacher Lizenzen, NJW 1983, 1764 .尋求問題的本土解決方案并沒有任何現實的借鑒意義。由此,本文論證過程中也有意回避了對外國法域民事訴權基礎理論的涉入。
(二)沖突解決的失敗
在現行民事法律體系內,能為被許可人帶來訴權的途徑是被上升為對世性權利的利益的獲得。假定在許可合同的外衣之下,專利權發生了權利變動,換言之,許可人以發放許可為名行授予絕對權之實,?有學者認為獨占許可是類似用益物權的用益知識產權,參見齊愛民:《論二元知識產權體系》,載《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商標獨占許可是一部分權利的轉讓,參見李中圣:《商標侵權訴訟的主體、訴權和責任》,載《人民司法》2002年第12期,第20頁。則獨占被許可人自動享有訴權。由此假設的正確性為出發點,則《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關于被許可人得以訴訟方式禁止任意第三方使用知識產權權利客體的規定,雖然僅僅構成純粹的注意規定,甚至略顯多余,但作為對民事訴訟法和實體法原則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延續和細化,將會解決法律體系內部的沖突問題。的確,不少學者嘗試證明專利獨占許可的絕對權屬性。有學者認為債權屬性與專利獨占許可的本質特征不符。?例如,林廣海、邱永清:《專利權、專利許可使用權與專利許可合同——以物權法原理借鑒為視點》,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6期,第18頁。也有學者認為獨占商標許可是附期限的商標轉讓,但沒有進一步論證。?李中圣:《商標侵權訴訟的主體、訴權和責任》,載《人民司法》2002年第12期 ,第20頁;相反觀點,認為不是轉讓,參見張耕:《試論知識產權被許可人的訴訟地位》,載《特區經濟》2005年第4期,第230頁。在版本較舊的文獻中,明確認為許可不涉及轉讓的為絕對主流觀點,如劉春霖著:《知識產權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頁;寧立志著:《知識產權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頁;張楚著:《知識產權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頁。還有學者視承租權為用益物權,?董美根:《論專利被許可人的訴權》,載《科技與法律》2008年第4期,第47頁,但作者明確否認獨占許可為用益權;認為獨占商標許可的設立是“處分行為”,參見董美根:《論我國商標侵權訴訟中被許可人之訴權》,載《知識產權》2015年第2期,第23頁。也有觀點認為獨占許可合同直接設定了用益權,見張強強、劉仲秋:《知識產權被許可人的訴權性質探析——以二元知識產權體系為理論視角》,載《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35頁;有觀點認為訴權來源于具有對世性的“專利實施權”,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知識產權被許可人的訴權研究東方法學》,載《東方法學》2011年第6期,第36-37頁。并與許可比較:“占有事實導致承租人享有占有權”?參見董美根:《論專利被許可人的訴權》,載《科技與法律》2008年第4期,第47頁;以及董美根著:《專利許可合同的構造:判例,規則及中國的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頁,需要指明,占有只是一種事實,而非權利。以及“物在時空上的唯一性”造成了承租人得以保留“承租物物權的排他性特征”。但該進路明顯背離通說對民法現行制度的基本認知。?限于篇幅,此處不贅。事實上,不以占有為手段,而以強制性規范賦予的對他人使用的排除力來間接控制客體,同樣可以達到“物在時空上的唯一性”,但該狀態本身與絕對權的產生或轉移無關。決定因素是,“時空上的唯一性”是基于對許可人的債權請求,還是來自于類似物權性的支配。拋開較為表象的租賃類推方式,從更根本的權利構造層面分析,現行民法體系中授予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絕對權的可能途徑有且僅有兩種,即部分轉讓專利權,或在專利權之上設定對世負擔。?在絕對權意定的法律環境中,部分轉讓和用益權設定在效果上并無二致。由于法律強制要求專利權和商標權的轉讓以登記為生效要件,所以僅僅覆蓋相同地理區域的專利權或商標權鑒于不能滿足登記要件而無法進行部分轉讓。參見拙文,Zhang Yi,Der Rechtscharakter der Lizenz im chinesischen Recht《Recht der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8.2015,P486.在專利權上設定用益權,有如物權體系內設定在土地所有權上的建設用地使用權。然而,基于下列兩個原因或者事實,前述兩種途徑均無法為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在中國現行專利制度中取得對世性地位。第一,現行專利法排斥期限、地域受限的專利轉讓。帶有期限、地域限制的專利權無法被登記,而專利法明確規定專利轉讓從登記開始生效。?限于篇幅,此處不贅。如果獨占許可可以構成獨立的部分專利權且被自由轉讓,則法律為專利轉讓所設定的強制性規定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被規避。將發放獨占許可籠統地上升為權利轉讓的做法,明顯偏離立法者通過強制性條款所表達出的限制權利流通意志。第二,獨占許可的具體內容由合同雙方當事人意定。如果獨占許可構成具備對世效力的用益權,則該權利在時間、地域以及權利內容方面會具有高度隨意性。其直接后果為,不僅獨占許可,甚至普通許可也可以對任意第三人產生法律約束力,從而突破當事人之間的效力相對性。這種特性的專利用益權將在明確區分絕對權和相對權效力的潘德克吞體系內面臨嚴格批判。?參見Zhang Yi, Der Lizenzvertrag im chinesischen Schutz- und Schuldrecht, Herbert Utz Verlag, 5.2014, P32.綜上,現行法中專利獨占許可證的債權屬性難以動搖。
三、訴權賦予作為法定例外的排除
《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的規定毅然將侵權行為是否影響被許可人利益的事實判斷,上升為是否賦予被許可人訴權的法律標準。由于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是相關市場被允許合法使用專利技術的唯一主體,所以可以無須以專利權人同意為前提,獨自提起訴訟。鑒于權利人可以在同一時間、地域和范圍之內使用專利技術,所以排他被許可人只能在專利權人不起訴的情況下提起訴訟。由于普通被許可人之外大量潛在合法使用人的存在,所以普通被許可人不享有訴權。這種以各方利益平衡為主導思想的訴權分配標準,顯得不但合情而且合理,同時反映出知識產權和其他傳統民事權利在權利客體特征和權利內容構成方面的重要區別,也由此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李明德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頁;鄭成思著:《知識產權保護實務全書》,中國言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徐紅菊著:《專利許可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林廣海、邱永清:《專利權、專利許可使用權與專利許可合同——以物權法原理借鑒為視點》,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6期,第18頁。如董美根:《論專利被許可人的訴權》,載《科技與法律》2008年第4期,第47、49頁;董美根:《專利許可合同的構造:判例,規則及中國的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頁;姚芳:《試論許可合同下被許可人的訴訟地位》,載《市場周刊:理論研究》2006年第9期,第137頁;徐紅菊著:《專利許可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有學者甚至明確指出“許可使得許可范圍內所生之利益歸屬于被許可人,被許可人成為利害關系人,進而產生了其享有訴權的可能”。?董美根:《論專利被許可人的訴權》,載《科技與法律》2008年第4期,第47頁。然而,首先,該訴權分配標準僅僅在直觀上或表象上看來合情、合理,卻如前所述未必合法,并引發諸多弊端。“合情”“合理”僅是假象。法律體系要求更為精密的配合和協同運作。其次,法律從未以規制社會所有利益為己任,并非所有類型利益的不正當轉移或消滅都會成為特定利益持有主體享有訴權的充分條件。立法者對各類利益的態度差異,必須在司法實踐層面以及制度續造領域得到充分尊重。最后,客體在被無限多個主體同時使用的獨有特質所造就的復雜利益格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知識產權和傳統民事權利受侵表現形態的不同,但卻不足以成為顛覆現有民事法律體系起訴原則在知識產權領域可適用性的充分理由。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與既存民法原則構成根本沖突。為了不同條款在同一法律體系內正確搭配和協調運行,前述條款至少需要成為一項具備充分正當性的法定例外。然而,該條款所依托的利益平衡理念,雖然以“利益平衡”為依托的論證模式在知識產權領域近年來愈發具有披靡之勢,卻難以支持突破法律既定原則的迫切性與必然性。
(一)訴權賦予必要性的欠缺
授予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訴權不是立法者提供給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解決其困境的唯一路徑。即便《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的相關規定缺失,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依然受享有現有法律制度提供的充分且不引發前述弊端的保護。專利權人放任侵權發生的行為在客觀效果上等同于發放一個免費的、由《民法通則》第56條意義上的(書面、口頭形式之外的)其他形式?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2017年10月1日生效)第135條:“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采用特定形式的,應當采用特定形式”。的民事法律行為所體現的普通專利許可(默示意思表示)。該授權行為不設定權利人的積極作為義務,僅體現為表示放棄訴訟或者消除被授權人使用專利行為違法性的一種許諾。這類許可,換言之,通過放任侵權行為做出的默示,自身的存在就違反了獨占許可人負有的合同義務,?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4年)第25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2年)第3條,獨占實施(使用)許可是指權利人(讓與人、商標注冊人)在約定范圍內(期間、地域、方式),將該知識產權客體僅許可一個受讓人實施,權利人(讓與人、商標注冊人)依約定不得實施該知識產權客體(專利、注冊商標)。從上述兩個獨占許可合同的法定定義得出,許可人有義務確保在約定的期間、地域和方式僅有被許可人一個使用人。從而構成許可合同違約。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因專利侵權所受的“利益損失”,可以通過權利人承擔違約責任的方式得以彌補。本文采用的表述為“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的利益損失”,而非權利侵害。?利益,而非權利或者權益,更非法益。與之相應,支付違約賠償被僅構成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因專利侵權所受利益損失的“彌補”,而非侵權損害賠償。鑒于法律對專利侵權與許可合同違約在構成要件和賠償計算方法方面規定存在差異,即便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的“利益損失”在客觀上和一個真正的專利權人受到的侵權損害沒有任何差別,但他通過違約責任路徑所能得到的彌補數額并不當然等同于專利權人通過侵權之訴所獲賠償。該數額在具體案件中可能會大于或小于侵權賠償額。在立法者沒有對債權人的該部分利益(比如許可人在訂立合同時預見或應當預見的范圍之外?《合同法》第113條。)在立法層面給予保護的情況下,商標案件司法解釋及學界卻將該利益劃為被許可人的當然受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或者更加簡明的表述為:劃入被許可人的權利范圍。那么,立法者擔憂支持債權侵權所能引發的所有風險就會在專利許可領域成為現實。而通過承擔違約責任所達到的“保護”的力度不在所有情形下均等同于贏得侵權之訴,但該路徑顯然更加吻合現行民法體系,并不會逾越應有的,法律業已劃定的債權邊界。
(二)訴權賦予沒有增加保障功能
直接賦予訴權同樣不構成對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利益更加有效的保障。第一,專利權人賠償能力有限而有可能無法充分填補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損失的考量,同樣適用于任何一個侵權人。第二,作為責任財產的組成部分,專利權是權利人承擔違約責任的重要保障。在侵權人和許可人尚未得以具象化的立法層面,相比賠償支付能力不明的侵權人,選擇由專利權人進行賠償是對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更有力的保障。專利權的售價或執行拍賣所得低于侵權持續期間所應支付的許可費用的情形,其出現機率較小。且侵權人為取得許可所應支付的費用同樣是計算專利侵權賠償數額的方法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1條:“……人民法院可以……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當專利權人怠于維權達到惡意處分財產的程度時,如相關市場內海量侵權人免費使用行為使得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依據許可合同取得的原有競爭優勢喪失殆盡,在客觀上已經達到等同于放棄專利權的效果,自然會有保全制度介入共同對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形成救濟。因為,鑒于許可費支付義務,對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而言其實比權利人放棄專利更為嚴峻。這種情況下,債權的第三方效力可來源于合同法業已確立的債權人撤銷權制度。第三,違約責任路徑的采用可以促進專利權人維權的積極性,保證被許可人所享合同債權天然內含的合法利益。第四,即便在較為嚴峻的、許可人處于破產程序的情況下,侵權人承擔的侵權損害賠償依然可以轉化為許可人的責任財產。而且,“專業”侵權人較為常見的司法實踐狀態下,較許可人以侵權人破產為多見狀態的制度構建出發點顯然更為合理。
綜上,享有訴權使得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在維護自身利益時更加直接,因為無需借助專利權人對自身義務的履行。“利益平衡”需要在尊重現行法的框架下進行,僅在現有體系制約了對更合理或更高效的“平衡”的追求,討論框架突破或形成特例才有價值和必要。直接回避體系內業已提供的違約責任路徑,以動搖既有原則為代價尋求新的解決方案,必然導致法律體系整體運行的失調。而現行規范的瑕疵會被歸結為進行“利益平衡”的必然副產品,從而被視而不見。賦予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訴權的做法突破了既有法律框架,同時致使專利權人避免無效宣告的利益被完全忽略。因為,作為獨占許可人的專利權人,其獨占許可合同所當然蘊含的追訴侵權義務不具有強制履行性。?參見《合同法》第110條關于強制履行的規定。換言之,專利權人在對獨占被許可人承擔違約責任和侵權人申請宣告專利無效的風險之間,做出選擇的權利至少不為作為民事制度基礎性規范的合同法所否認。同樣被忽視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是,專利權人在許可合同關系存續期間積極維護專利的有效性,屬于合同法為許可人設定的合同義務。?《合同法》第349條明確要求讓與人保證自己是技術的擁有者。由此可見,直接賦予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訴權的做法不是現有法律體系內提供的最佳選擇。被考察的相關條款在制度續造中的內在體系上缺少充分的邏輯支持,難以成為法定例外。
四、損害賠償的分配原則
缺少程序法的支持,法院受理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起訴的法律依據只能是《專利法》第60條,結合《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的規定。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作為原告的侵權之訴中,專利權人只有可能作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如果法院堅持認為上述關于原告資格的諸多疑慮不足以妨礙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獲得侵權賠償,?顯然支持侵權賠償的做法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最高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2006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11次會議通過)的第1條支持植物新品種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提起訴訟;雖然依據其第6條,法院可以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判決侵權人承擔賠償損失。然而當法院依原告請求確定賠償數額時,顯然無法明確的是,被許可人被侵害之權為何權利類型。則法院至少應當,無論專利權人是否作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尊重專利法賦予專利權人的合法權利,?有個別觀點明確認為獨占許可人沒有任何經濟損失,如姚芳:《試論許可合同下被許可人的訴訟地位》,載《市場周刊:理論研究》2006年第9期,第137頁;在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獲賠范圍方面進行嚴謹界定。在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作為原告起訴的模式下,許可人和被許可人的權利組成分配區分不清,雙方往往都有損失。被許可人的損失直接來源于其市場份額的減少。而許可人的損失主要體現為因被許可人銷量減少導致許可費的下降,以及作為專利權人的其他利益的損失。因此,侵權訴訟成本的分配,證明損失的舉證責任分配,損害賠償額的計算和分配,面對另行起訴的權利人侵權人是否二次賠償,都十分繁雜而且略顯迷茫。為簡化該(因《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相關規定被無謂復雜化的)問題,回歸法律體系的原有安排,建議司法裁判中將許可人容忍侵權行為等同為免費普通許可的發放。權利人和作為侵權人抑或作為另一普通許可合同當事人的第三人在侵權或專利技術使用行為發生前是否達成合意,對于被許可人而言,不應在法律后果層面進行區別對待。為便于描述,我們構建A和B兩種情形,進行比較。在A情形中:獨占許可人,即權利人在專利權受到侵害時,為了避免侵權人提出專利無效申請,放任侵權行為發生。?《專利法》第44條允許權利人以書面聲明放棄專利權的形式放任任何人使用他的專利技術。舉重以明輕,放棄訴訟應當被認為是知識產權人的權利。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依據《專利法》第60條、參照《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的相關規定對侵權人提起訴訟,主張侵權損害賠償。依照專利法相關規定,侵權損害賠償額可由權利人損失、侵權人得利、參照許可費或法定賠償得出。
在B情形中:沒有侵權行為發生,獨占許可人發放了一個普通許可。并且在這個普通許可合同中雙方約定權利人不負有任何積極幫助義務,諸如合同法規定的交付有關的技術資料,提供技術指導?《合同法》第345條。以及維持專利權效力的義務。該許可相當于一個消極許可。?參見 Zhang Yi, Der Lizenzvertrag im chinesischen Schutz- und Schuldrecht, Herbert Utz Verlag, 5.2014, P92.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起訴許可人違反許可合同約定,要求其支付違約損害賠償。依照合同法和民法總則相關規定,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應得賠償額應等于因違約而造成的市場份額減少的損失,但該數額受到許可人在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應當預見到范圍的限制。?《合同法》第113條。不言而喻的是,該數額大小不應與侵權人得利、侵權法定賠償額或許可費產生任何關聯。在潘德克吞體系中,A和B兩種情形對于沒有任何絕對權受到侵害的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而言,并無二致。鑒于《專利法》第60條,參照《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回避了被許可人在A情形中作為原告起訴的更多規則細節,為了增強可操作性,提出權利人積極維權并提起侵權之訴的C情形作為補充。在專利獨占被許可人起訴的A情形中,其所得賠償數額,無論專利權人是否被列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不應與其在C情形中所獲數額有別。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在A情形中對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應當得到賠償額進行分析,B和C兩種情形作為分析A情形的參考。B和C兩種情形中權利人、被許可人和侵權人三方的法律關系的澄清不在討論范圍之內。具體而言,法院認定專利侵權成立后所應適用的賠償方案應當如下:
(一)傳統侵權賠償理論
法院采用傳統侵權賠償理論時,按照因侵權所受實際損失確定賠償數額,侵權人所承擔賠償額應當等于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市場銷售利潤的減少。任何情形下均不容忽略的客觀事實是,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并不是專利權人。如果原告基于自己的專利權起訴,則其損失表現為市場銷售利潤的減少以及,如果侵權人基于侵權所得市場份額大于原告基于侵權損失的市場份額,則差額部分對應原告原本期待但未能得到的許可費收益。而我們通常認為,在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獨占被許可人沒有發放(分)許可的權利。?《專利法》第12條;《合同法》第346條、第352條;參見Zhang Yi, Der Lizenzvertrag im chinesischen Schutz- und Schuldrecht,Herbert Utz Verlag, 5.2014,P42.在許可合同采用與產品銷量掛鉤的計費模式中,比如常見的入門費加提成,被許可人銷量的減少,還意味著專利權人許可收入的降低。所以,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獲得賠償后,應向專利權人補足由于侵權所少交的許可費。反之,在許可費被約定為確定數額的情況中,專利權人沒有損失,所以銷量減少的原告(被許可人)可以獨自保留所有賠償。對于C情形中作為原告提起專利侵權之訴的專利權人,本文傾向將其損失認定為許可費機會的喪失。因為一個(嚴格遵守獨占許可合同的)專利權人市場份額為零的法律原因,是許可合同中的約定,而不是侵權人的使用行為,盡管專利權人的親自使用或者許可侵權人使用的前提假設均會使專利權人遭受違約之訴的風險。
(二)許可費、侵權人得利或法定賠償理論
法院采用喪失許可費機會理論、侵權人得利或者當前最為常見的法定賠償時,專利獨占被許可人作為債權人的受保護利益應以其債權為限。換言之,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所得數額不應該超過在B情形中可得的違約賠償。其沒有在他人權利被侵害的基礎上獲得額外利益的法定理由。A情形中,法院可以支持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獲得等同于C情形中權利人所得的侵權損害賠償數額。但如果該數額超過B情形中權利人對專利獨占被許可人所承擔假想違約責任范圍的部分,則超出部分應當被返還給被追加為訴訟第三人的許可人,即真正的被侵權人。?這里指的是本文所述的“以及作為專利權人的其他利益的損失”。比如,在沒有附加入門費的單純的提成計費模式中,如果專利獨占被許可人還沒有開始進行生產銷售,則他沒有市場份額的減少或者在未來可以預見的銷量減少,所以賠償數額應當全部返還給專利權人。反之,如果依據專利侵權賠償特有計算方法得出的數額小于假想違約責任范圍,則怠于行使訴權的專利權人應當,如果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對他提起違約之訴的話,補齊該差額。
結 論
《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賦予獨占被許可人訴訟資格的做法與我國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既定的法律框架內的基本理論背道而馳。無論是將授予被許可人訴權視為一個明確設定在民法既有原則之外的特例,還是試圖否定獨占專利許可證的債權屬性的努力,均難以提高上述條款的自洽性,使其滿足最低必要限度的法律體系內在和諧需求。《商標司法解釋》第4條第2款,包括《專利法》第60條、《商標法》第60條的相關表述,至少在任意訴訟擔當制度在中國被確立之前都應予作出相應的修改。在現有法律框架內追究專利權(甚至包括商標權)侵權行為時,更符合法律內在邏輯的切入點是,由專利權人(商標權人)提起訟訴。對于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利益保護的需求,現有法律框架內的正確解決方案為:視侵權為一次普通許可發放。絕對權地位缺失的獨占被許可人僅僅可以從專利侵權賠償中取得與許可人“假想違約賠償”相當的份額。侵權賠償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被視為許可費。我國法律疏于對權利和利益嚴格區分,自然會引發相應弊端。該弊端理應在知識產權領域得到合理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