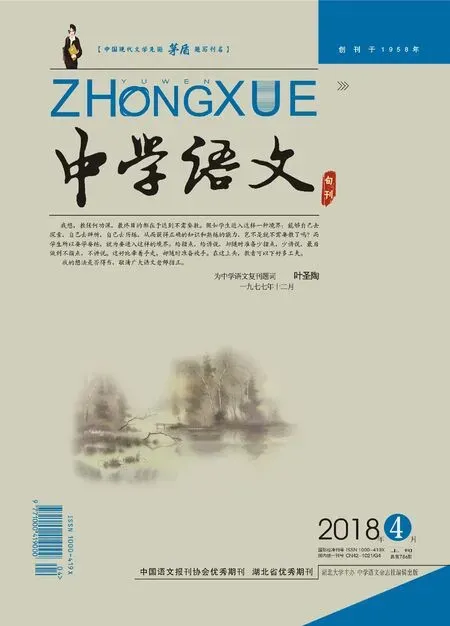閱讀教學要關注“語言”
林水生
2011年出版的 《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提出“語文課程應特別關注漢語言文字的特點對學生識字寫字、閱讀、寫作、口語交際和思維發展等方面的影響。”而2001年版則是“應考慮”,這一細微的變化說明,新版課程標準對“語言”的關注程度比原來的更高。這些課程標準要求都明確強調我們在教學過程中要關注“語言”。因此,我們要在“語言”中求索,從“語言”入手進行文本細讀,來提高閱讀教學的效率。
一、“文以載道”
宋代理學家周敦頤曾說 “文所以載道也”,他的意思是說“文”就像車子,那“道”就像車子上所裝的東西,只有通過車的運送,才能抵達目的地。他還說如果車輪車轅裝飾得再漂亮而人不坐,那只能是白白地裝飾。我們在語文閱讀教學中可以借用這個詞,從小的方面而用它,即我所說的“文”指“語言文字”,“道”指“語言文字”所構成的文本中蘊含的思想感情等。當前的閱讀教學現實情況,不管是初中階段,還是高中階段,師生共同關注點都在文章的思想情感方面,即我所說的“道”方面,相應的練習設計很少有指向“語言”形式,即我所說的“文”方面,很少探究“語言”是如何承載表達意義的設問,比如“文章是如何來表達情感的”“文章是如何來表現思想內涵的”。雖然也有品味詞語、語句的練習設計,但并不作為一個重點來對待,倒像是一種點綴。而當前的語文閱讀教學中往往忽視了“語言”,不知不覺產生了“重道”而“輕文”的現象。如果我們忽視“語言”這一根本要素,就無從談起文本細讀,也就無法有效地提高語文閱讀教學的效率。
二、語文學科特質
語文學習的目的是什么?概括起來無非有這幾點:一是讓學生的視野得到拓展,二是學生精神修養的層次得到提高,三是學生探索創新精神與能力得到培養,四是學生的審美意識與審美能力得到培養,五是學生靈活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得到培養與提高。與之關聯的也就出現不同的語文性質觀,如工具性、人文性、言語性等。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繼續追問“語文為什么是語文”,那么問題就來了,開闊視野、精神修養、探索創新、審美意識這些目的其他學科也可做到,而且有可能更突出,比如音樂美術之于審美意識,物理化學之于探索創新,政治歷史之于精神修養,社會實踐之于開闊視野。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唯有“語言”文字,方顯語文最大的本色,沒有“語言”,沒有對“語言”的品味,架空“語言”,那語文還是語文嗎?
學生語文學習是有階段性的,從小學到高中大致可分為 “故事期階段”“文學期階段”“思想期階段”,而伴隨這些階段進展的應是對“語言”品味的不斷深入,從簡單的獲取“語言”信息到深入“語言”內核,感受“語言”之美,感悟“語言”所包孕的思想,要真正讓學生具有文學鑒賞力和思想深刻性是離不開對“語言”的深入品味的。
三、文本細讀
首先,我們進行閱讀教學應指導學生立足于文本,從“語言”求索中入手,才能進行文本細讀。對閱讀文本進行“細膩、深入、真切的感知、闡釋和分析”。只有在“語言”中求索才能進行充分的細讀,品味和發掘出文本所蘊涵的情感等內涵。正如葉圣陶所說的“字字未宜忽,語語悟其神”。“從語言出發,再回到語言”(呂淑湘),并深深“沉入詞語”“穿行在多重話語之間”,去“傾聽文本發出的細微聲響”,就是“逐句摸索別人的行文思路”。只有這樣指導學生更多地體味語言文字的滋味,感受語文的魅力,才能提高語文閱讀教學的效率。
下面以兩段文字為例:
【文段1】這平鋪著、厚積著的綠,著實可愛。她松松地皺纈著,像少婦拖著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著,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著,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著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珠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透她!——朱自清《綠》
【文段2】我天天望著窗口常春藤的生長。看它怎樣伸開柔軟的卷須,攀住一根緣引它的繩索,或一莖枯枝;看它怎樣舒開折疊著的嫩葉,漸漸變青,漸漸變老。我細細觀賞它纖細的脈絡,嫩芽,我以揠苗助長的心情,巴不得它長得快,長得茂綠。下雨的時候,我愛它淅瀝的聲音,婆娑的擺舞。——陸蠡《囚綠記》
如果只是滿足于思想內容、情感態度的獲得,那么這兩段無非都是寫了“綠的柔嫩、生機、可愛等特點”這一內容,都表達了作者的“喜愛綠色”的情感。但如果我們深入”語言”,在文字中求索,則會發現:朱自清的描寫是“面上”的,是“斷面”,他對綠是“有中見異”,喜愛中更多的是驚詫,訴諸筆端一系列搶眼的比喻正是他難以抑制的喜悅之情的”語言”呈現;而陸蠡則是“點上”描寫,有“過程”,他對綠是“無中見有”,他對常春藤的生長過程描寫相當細膩,雖然常春藤的生長過程與其他藤本植物的生長并沒有明顯的不同,但作者為什么還如此不厭其煩的描寫,原因就在于他焦心等待、懷念綠色的心態,平實無奇的文字流露的是一種久違之后的喜悅和滿足。
因此,如果不指導學生進行文本細讀,不對”語言”進行分析品味,不僅會忽視”語言”之美,而且會影響我們對思想情感的深入體悟。金圣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說道他“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常常“只記得若干事跡,便算讀過一部書了”。這實在值得我們在進行閱讀教學時好好思考。
其次,細讀文本要尋找什么樣的“語言”呢?
金圣嘆指出,我們細讀文本應尋找“古人書所得意處,不得意處”之語言,應尋找“轉筆處”之語言,“乘水生波處”之語言,“翻空出奇處”之語言,應尋找“不得不補處”之語言,“順添在后處,倒插在前處”的語言,從中求索出“無數方法”,求索出“無數筋節”。切不可混帳翻將過去,將一切精妙“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后事跡”。
對于文本細讀,孫紹振先生也說過:“要從矛盾處入手,才能揭開文章密碼。”無論是金圣嘆的“筋節處”,還是孫紹振所說的“矛盾處”,都是指向那些意味豐富的文本”語言”,它們與文章的思想情感存在密切的關聯,甚至可以說就是解開思想情感的密碼。它們的呈現方式各異:或隱或顯;或簡或繁;或看似閑筆,卻直逼文意;或有悖常理,卻是情感使然。
文本的內涵只能經由“語言”文字抵達,要想抵達,必然要對“語言”中的關鍵處進行細讀,而不能任由其從細讀的視線中滑過,應對文本“語言”保持高度的靈敏度和警覺性。
捕捉文本的關鍵處必須依靠細讀才能達成,但細讀不一定就能發現,它又牽涉到細讀者個人的素養、眼力等,并沒有存在能夠讓我們輕而易舉就捕捉到文本的關鍵處的公式化的方法。
四、品味處理“語言”
怎樣處理“語言”,孫紹振先生提出“還原法”,黃厚江老師認為面對文本“語言”應問“有意思嗎”,把這些觀點變成幾個通俗的問題就是:作者為什么要用這樣的字詞句,換成別的行不行,這樣說跟那樣說有何不同等等。這些問題就是要引導我們應在語境的背景下去處理“語言”。
語境,可以是某一語句的上下文,可以是某一特定的情景,甚至可以是寫作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果說某一“語言”是局部的,那么,語境就是整體的,處理“語言”,應該立足于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上。德國哲學家狄爾泰說:“整體必須通過局部來理解,局部又必須在整體聯系中才能理解,二者相互依賴、互為因果。”因此,處理“語言”并非把“語言”從文本中剝離去作孤立的剖析,否則,必然只停留于對其本意、詞性、句法、修辭、語法等方面扁平化的分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比如魯迅《祝福》中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這句反復出現,不斷單調的重復,難道就不可以變換一下表達方式嗎?單調表達的背后說明了什么?這樣的思考就是一種對“語言”的處理,它直逼你去思考其中深層次的原因,經歷一系列打擊之后的祥林嫂,已呈現出創傷性的精神病癥狀,即存在一種揮之不去的闖入性回憶,頻繁出現痛苦的經歷,而這種表現在說話言語上就是重復性的自言自語。
再像對蘇東坡《赤壁賦》中的“而今安在哉”這一句進行分析。如果抽出孤立分析,得出的結論無非就是曹操這么一個一代梟雄難逃英雄落幕的結局,外在加上“賓語前置”的文言句法的說明。可是假如我們將其放在特定的語境下,我們就會發現蘇東坡在寫完曹操一生的征戰輝煌之后,再來這么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問,這就正好體現出了蘇東坡當時被貶黃州時所產生的人生感慨,也正好進一步證明了古代文人共同擁有的那種“人生如夢”的文化心理。無論人生再怎么繁華,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是像那一縷過眼云煙,稍縱即逝。這樣的情感落差正是同這么一句反問來達成,而這種落差又從另一角度給正處低谷期的作者以一種心理的平衡和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