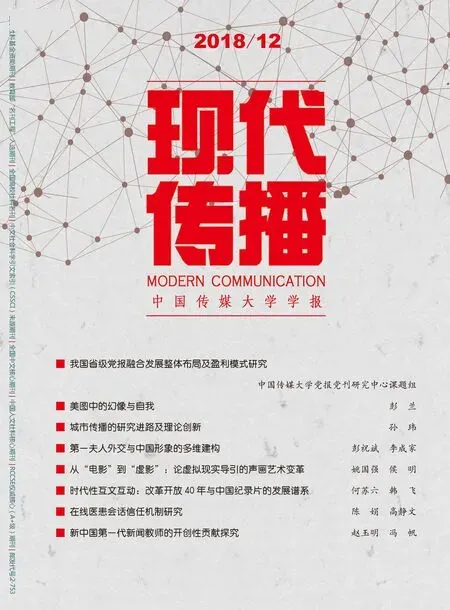時代性互文互動:改革開放40年與中國紀錄片的發展譜系*
■ 何蘇六 韓 飛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作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或許也正因為改革開放給當代中國的巨大現實影響,以及能輻射當下的思想能量,“紀念”這個詞匯在2018年顯得格外醒目。
40年,我們如何記憶?社會建構理論認為,只有通過特定的表征手段,人們才能為物質世界制造意義。紀錄影像一直被用來表現自然、歷史和社會現實,作為極具現實關照意識,且以真實性為靈魂的“影像意義系統”,它“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①,由此,紀錄片作為表征工具,無疑可成為一種凝視改革開放40年的記憶媒介。而這一文本和行業領域的發展變遷也可以成為透視和認知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展和社會變遷的一扇窗口。
一、引論:紀錄片與改革開放的“互文”與“互動”
在2018年8月舉辦的北京紀實影像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紀實影像大事記特展上,以年份為單位,展映了《潛海姑娘》(1978)、《美的旋律》(1979)、《絲綢之路》(1980)、《先驅者之歌》(1981)、《拼搏——中國女排奪魁記》(1982)、《話說長江》(1983)、《來自農村的報告》(1984)、《零的突破》(1985)、《話說運河》(1986)、《紫禁城》(1987)、《蛇口奏鳴曲》(1988)、《心靈狂想曲——第八屆傷殘人奧運會》、《沙與海》(1990)、《望長城》(1991)、《最后的山神》(1992)、《毛毛告狀》(1993)、《龍脊》(1994)、《較量》(1995)、《山梁》(1996)、《神鹿啊,我們的神鹿》(1997)、《周恩來外交風云》(1998)、《婚事》(1999)、《英與白》(2000)、《平衡》(2001)、《鋼琴夢》(2002)、《德拉姆》(2003)、《復活的軍團》(2004)、《故宮》(2005)、《大國崛起》(2006)、《昆曲600年》(2007)、《紅跑道》(2008)、《永恒之火》(2009)、《大閱兵——回首60年》(2010)、《走向海洋》(2011)、《舌尖上的中國》(2012)、《鄉村里的中國》(2013)、《瓷路》(2014)、《喜馬拉雅天梯》(2015)、《本草中國》(2016)、《輝煌中國》(2017)40部國產紀錄片。這些作品歷經歲月洗禮沉淀,每部影片獨特的美學風格下都氤氳著作品誕生年代的氣質,呈現出時代的特有表情,它們連接在一起,就是一部鮮活的改革開放史。
紀錄片相對其他視聽文本,真實客觀,且形象鮮活,可以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一個時代的民眾生活方式乃至社會發展變化記錄下來,從而成為見證國家變革、社會變遷的“歷史鏡像”。改革開放是中國紀錄片發展取之不盡的資源和立足的深厚土壤,或許也正源于此,紀錄片的發展與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脈絡呈現出一種“互文”關系。如果把紀錄片比做一條河流,我們無疑可以從這條河流的軌跡和流向中,感受這個國家40年的歷史激蕩、思想變遷、社會變革。
紀錄片的現實洞察力讓它成為社會和人類生存之鏡,與此同時,紀錄片身上所蘊藏的強大思想性和闡釋力量,讓它得以成為一把鏗鏘有力的錘子,去敲擊和叩問社會和時代,因此,紀錄片又是和時代“互動”的。40年來,從人文化時期喚起民族激情,到平民化時期體察記錄平民生存狀態,到社會化時期關注記錄社會主流現實生活,再到政治化產業時期服務國家戰略。紀錄片總是能夠把握時代脈搏,吸收社會思潮,釋放自己的多元價值和影響力。
改革開放首先是一種思想引領的力量。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更沒有40年中國紀錄片的發展變革。中國紀錄片在新時期的40年發展史,經歷了“人文化”“平民化”“社會化”“政治化產業”四個時期,每個時期的分野,都首先是一次觀念突破和思想解放。
除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不僅作為一種政治口號,更作為一種社會思潮鼓舞黨和國家、以及人民群眾從禁錮中解脫,走向現實。紀錄片作為最具現實關懷的影視文本形態,開始向本體和這個社會和時代最亟待關切的內容靠近,紀錄片人也開始擁有一種紀實主義的新觀念。紀錄片從個人式的英雄崇拜轉向反思民族命運,聚焦時代痛點,關注主流現實,從盲目的仰視開始轉向交流式的平視。這是一種求真、求是的態度。
二、譜系: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紀錄片發展四階段
1. 人文化時期(1978-1992):民族話語與精英思考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定意義上是先從廣闊的農村展開。位于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是改革開放的先驅,1978年小崗村的18位農民用一個個血手印掀起了“大包干”運動,后來才有了中國制度改革史上著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79年,時任中央電視臺編導的劉效禮被臺里派去“看看鳳陽的情況”,劉效禮到鳳陽后,看到鳳陽農民精神面貌和生活的變化,并把這一切拍了下來。回到臺里,劉效禮將素材編輯成了35分鐘的紀錄片,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體量。據編導劉效禮對筆者回憶,當時廣電部的領導審看了影片,說“中央人士對大包干的意見不一樣,你怎么會去拍這樣一部‘大片’,搞五分鐘”。領導的意思其實是要剪成五分鐘,但當時紅紅火火的大包干運動豈能是五分鐘的容量能表述清楚的。劉效禮打了個擦邊球,只剪去五分鐘。后來30分鐘的紀錄片《說鳳陽》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成為第一部反映農村大包干的紀錄片,改變了鳳陽在全國人民眼中的形象。影片播出后反響強烈,著名畫家黃永玉看了重播后,激動地給央視寫了一封長信,認為他們“拍了一部活的社會主義關于中國農民的教科書”,并送給央視一幅畫,畫中一只大大的刺猬,刺猬身上全是針。黃永玉特意在旁邊寫了一首詩為圖畫釋義,大意為“刺猬身上的針是丘比特的愛神之箭,來表示觀眾對你們的愛護”。
那是思想剛剛解禁的中國,作為知識分子精英的創作者迫切希望以紀錄片為媒介對社會現實進行主動思考和表達,紀錄片開始具有創作者主體意識。這在改革開放前,紀錄片作為一種階級斗爭和意識形態工具的時代是不可能實現的。
這是一個剛剛思想開化的年代,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紀錄片的意識形態功能依然是主導功能。精英群體力量的加入,對于民族的憂患和深思,使得這一時期的紀錄片的思考維度從“政黨-國家”框架走向民族框架。利用民族話語制造群體認同,打造“想象的共同體”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策略。民族身份的構建過程包含了一種集體歸屬感(a sense of community)的形成。紀錄片的政治性,反映出紀錄片對那些特定時期、特定地點構成(或爭取成為)社會歸屬感(或集體歸屬感)的特殊形式的價值觀和信仰,并為信仰和價值觀的建立提供一種具體可感的表達方式。②因此,就這一時期紀錄片的題材選擇上,“帶有民族象征意義的山川河流以及長城運河等,自然成為最佳的對象和載體”③。
《話說長江》(1983)、《話說運河》(1986)是這一時期的代表。《話說長江》采用了章回體結構,通過“長江”這一民族符號抒發了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靈活的創作方式和話語風格讓觀眾耳目一新,“受眾”意識的出現更是增加了觀眾黏性。《話說長江》播出時,收視率一度高達40%,播出時可謂萬人空巷,作品的主題曲至今廣為傳唱。稍后由同一團隊創作的《話說運河》也反響強烈。兩部片子的總編導戴維宇曾說,“如果說,我們在涉足長江的時候,注意力還集中于祖國山河的風貌,那么,我們在選擇運河這一題材時,則總希望通過電視節目去追溯我們民族的悠久歷史,志在表達中國人民創造東方文明的艱苦歷程,去話說運河身上所凝聚的中華民族的智慧和散發出的人情味和鄉土氣”④。可見這一時期象征民族精神的山河關照,因為主體性的顯現而體現出人文化色彩。
除了以上兩個“江河姊妹篇”,《絲綢之路》(1980)、《莫讓年華付水流》(1981)、《唐藩古道》(1987)、《讓歷史告訴未來》(1987)、《黃河》(1988)、《河殤》(1988)、《望長城》(1991)同樣表現出這一時期紀錄片中的人文色彩和精英思辨精神。哪怕像《河殤》這樣引起廣泛爭論的創作,雖然有濫用話語權力的嫌疑,但也一定程度上帶有創作群體強烈的社會責任和主體性歷史人文思考。
1991年,中日合拍的紀錄片《望長城》,成為人文化紀錄片時期的高峰。同樣作為一部宏大題材的紀錄片,《望長城》原本像長江、黃河一樣,選擇一個民族化的象征,卻自我突破,走向了生活的現場,創作者將鏡頭伸向長城沿線的人文風貌和百姓生活,以現在時態和現場體驗式拍攝,讓創作者出場,讓老百姓表達。ENG等技術的運用,使得電視紀錄片在影像語言上突破電影的束縛,長鏡頭、同期聲采訪、同期錄音成為創作特色,紀錄片自此開始有了“電視語言”,這一現象被朱羽君教授稱為“屏幕上的革命”。在《望長城》創作團隊走向現場,捕捉“長城”這一符號意義的過程中,精英反思意識走向與民眾對話,一種平民話語開始孕育。《望長城》與同時期出現的《藏北人家》(1991)、《沙與海》(1991)等作者型紀錄片,氤氳出下一個時期的中國紀錄片的話語方式。
2. 平民化時期(1993-1999):平民話語與紀實浪潮
1992年歲首,一輛專列載著88歲的鄧小平駛向南方。當時的國內,關于改革的諸多爭論、質疑聲不斷,鄧小平沿途發表了許多振聾發聵的講話,為改革開放廓清視聽、保駕護航。那是一個正處于轉型期中國,觀念的開化迅速轉化為大時代的變化,一批創作者敏感觸摸到這一時期的時代神經,把現在看來還略顯稚嫩的鏡頭,伸向周圍人、身邊事,去關注和記錄轉型期的中國表情。
1993年,一部反映安徽省無為縣5位小保姆進京務工的紀錄片《遠在北京的家》播出,編導是同是安徽人的陳曉卿。他在回家的火車上發現了這一群游走于農村與城市間的務工者,并用平實的鏡頭長期跟蹤記錄了下來。那時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讓橫亙在城市與鄉村的壁壘開始消融,農村人口開始向城市流動,鏡頭里的小保姆張菊芳,成為那個時代一個社會群體的符號表征。
這一年,還有兩個代表性的事件標志著一個新的紀錄片時期的開始。1993年2月,上海電視臺《紀錄片編輯室》開播;1993年5月,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的子欄目《生活空間》開播。兩個欄目,一南一北,見證和開創了中國紀錄片平民化時期的繁榮景象,也讓紀錄片人有了專門的展示平臺。從《紀錄片編輯室》“聚焦時代大變革,記錄人生小故事”,以及《生活空間》的口號“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里就可以得出,這一時期,老百姓成了電視紀錄片中的主角,而且紀錄片開始以一種平民話語和平視視角關注和表現普通人的生活。
轉型年代,社會快速變化,新鮮事物、新鮮的生活方式,新鮮的人,為紀錄片的拍攝提供了新鮮素材。同時,我們亦能從這些把鏡頭伸向老百姓身邊事件的紀錄片中感受到屬于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氣息:《德興坊》(1992)、《毛毛告狀》(1993)、《大動遷》(1994)、《母親,別無選擇》(1995)、《姐姐》(1996)、《四姐》(1998)、《爆炸》(1998)、《海選》(1998)等紀錄片在直面生活的同時,開始觸及社會的脈搏與痛點。
平民話語和平視視角不僅便現在對普通人的關注上,連歷史偉人在這一時期也被請下神壇,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1993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創作的12集文獻紀錄片《毛澤東》,少了乏味的史料陳列,毛澤東的形象被塑造得真實、樸素、立體,偉人的形象和他背后的歷史一起變得鮮活起來。1997年元旦,在北京301醫院,93歲的鄧小平坐在病床上看了以他命名的文獻紀錄片《鄧小平》。影片展現的不僅是一位世紀偉人轟轟烈烈的歷史功績,更是一位老人平平淡淡的真情實感。在片中,解說詞如是寫道,“在孩子們眼里,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好老頭,孫子孫女是他心中的寶貝。和孩子們在一起,他總是那樣滿足,一種盡享天倫之樂的滿足。鄧小平熱愛生活,熱愛自然,他喜歡用鮮花來裝點生活…”,細節的真實刻畫,語態和視角的改變,讓觀眾對偉人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這一時期的紀錄片發展還體現在紀實美學的興起,個體獨立創作的熱潮。
自90年代初開始,紀實美學開始在紀錄片文本中流露,從《流浪北京》(1990)、《望長城》(1991)中就已初見端倪,而《紀錄片編輯室》和《生活空間》對于日常生活和平民的內容關照使得兩個欄目對于紀實美學風格更加偏向。
紀實浪潮的興起幾乎是在體制內外同時進行的,甚至這一時期的許多體制內的作者也拍出了極具獨立風格的紀實化作品。這和這一時期西方直接電影觀念的引入和流行有很大關系。這一時期也被認為是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最為自主和激情的時代,吳文光、孫增田、段錦川、蔣樾、梁碧波、康健寧、時間等成為這一時期標志性的“作者”。《最后的山神》(1992)、《摩梭人》(1993)、《遠去的村莊》(1993)、《茅巖河船夫》(1993)、《瀘沽湖》(1993)、《龍脊》(1994)、《廣場》(1994)、《陰陽》(1995)、《彼岸》(1995)、《八廓南街16號》(1996)、《三節草》(1997)、《神鹿啊,我們的神鹿》(1997)、《回到鳳凰橋》(1997)等極具作者性的紀實化影片,將鏡頭對準一個村莊、一個部落、一個家庭、一個有符號價值的群體、一個有血有肉的個體,成為后人透視這個時代的標本。
中國紀錄片在這一時期呈現平民話語特點的另一面是作者個體話語權的強化。當人的主題確立,“意識形態的因素被人文的因素取代,紀錄片的美學、哲學意味加強,而它的社會性功能自然削減,社會責任意識自然淡化”⑤。
早在1991年,一部觀念和手法比較超前的紀錄片《沙與海》就震動了整個電視界,兩位作者,選擇了中國的西北沙漠和東部沿海兩個地方,記錄兩種生存狀態。在摘得亞廣聯紀錄片大獎的時候,國際評委對這部影片的評語如是說,“它出色地反映了人類的特性及全人類基本相似的概念”,人文關懷與哲學色彩成為影片的風格化標簽。但在這部片子播出的1991年,電視和街頭巷尾上飄蕩的是毛阿敏的《渴望》主題曲,在日益走向大眾化的電視屏幕前,這部極具哲學意味和作者性的紀錄片并沒有受到大眾關注。
如果說此前的《沙與海》的作者雖然具有一種精英式的高冷,但主題仍具有普世色彩,那么這一時期有更多的紀錄片作者沉迷于邊緣題材、自說自話和個人化實驗而不去考慮觀眾的感受,導致這類紀錄片無法進行有效傳播,紀錄片的價值和影響力也得不到體現。像所謂片比“1∶1”的頗具實驗色彩的紀錄片《北京的風很大》(1999),對于紀實美學的過度迷戀也導致紀錄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紀錄片不僅僅只是真實地記錄某一個點,更應該是真實地展示某一個面。這個“面”經常是表現為結構和關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人或者這個家庭融入整個社會,使之社會化。哪怕是一個邊緣的人,或者邊緣群體,他和他們的存在方式本身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不應該與這個社會割裂開來。⑥不過歷史即將進入下一個世紀,風向開始變了。
3. 社會化時期(2000-2009):主流現實關注與市場話語登場
世紀交替的幾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在這期間,我們迎來了香港、澳門回歸,迎來改革開放20年、建國50周年的慶典,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進一步融入世界。在這一個個歷史時刻,紀錄片人記錄下來激動人心的場面,并且用一部部氣勢恢宏的作品為時代做出腳注。
為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央視匯聚全國紀錄片精英打造了紀錄片《二十年二十人》,正是通過這部紀錄片,很多中國觀眾認識了吳敬璉、魯平、王石等改革開放的闖將。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一個個改革浪潮下的故事,以小見大,讓人們直觀感受到了改革的力量和給社會帶來的變化。同樣集中各方力量打造的《改革開放二十年》,則是一部大開大闔的史詩作品,它將二十年改革開放歷程、二十年滄桑巨變,濃縮在600分鐘的紀錄影像里。在拍攝的7個月時間里,攝制組動用了6架飛機,共飛行兩百余小時,將祖國大地進行了一次全景式航拍。
新世紀的紀錄片發展,“改革開放”依然是創作動力和創作焦點。不過中國紀錄片身處的后兩個時期,社會結構和環境走向復雜多元,中國紀錄片的發展也往往是多個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新世紀初,市場經濟的浪潮進一步輻射到電視媒體,“收視率”和“市場”成為頻繁出現的詞匯。過去作為非市場化的紀錄片行業也開始向社會主流和市場靠近。社會化時期,“市場”和“社會責任”兩個因素的引導,使得這一時期的中國紀錄片呈現出一系列變革:紀錄片開始從老少邊窮走向紛繁的現實生活,從個人化的孤芳自賞走向大眾傳播,從小作坊走向欄目化流水線,從謹守直接電影式的清規戒律走向拿來主義。市場話語權開始顯現,紀錄片的主題和表現方式更加多元。
2000年深秋,在內蒙古草原上,一部影片正在拍攝過程中。總導演金鐵木站在一輛古代戰車上,在這個將要拍攝的鏡頭中,他扮演的是一名披甲持戟的武士。這一幕正是紀錄片《復活的軍團》的拍攝現場。2004年,《復活的軍團》登陸央視,這部歷時三年拍攝的紀錄片,為觀眾還原了2000多年前的大秦帝國軍隊統一華夏的歷史進程。情景再現、角色扮演、數字特效等一些非紀實手段的運用,豐富了觀眾的視覺體驗,形成了另一種紀錄片美學樣貌。
如果說2004年《復活的軍團》的推出還是小試牛刀,2005年,《故宮》則是把技術美學運用到了極致,真正開啟了中國紀錄片的“大片”時代。80、90年代紀實化浪潮的興起導致電視紀錄片與電影分野,這一時期市場的驅動與工業化的操作模式,則讓電影的技術手法和美學樣貌重新回歸電視紀錄片。
歷史進入21世紀,中國的崛起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2003年11月26日上午,時任中央電視臺編導的任學安在車上的廣播中,聽到了中央政治局于11月24日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的新聞報道,學習的內容主要是針對15世紀以來9個主要大國的發展歷程和興衰經驗。“大國崛起”的概念在他的腦海中隨即建構而出,在想法得到了央視領導的認可后,《大國崛起》籌備迅速啟動。這一次,中國紀錄片人將視角真正投向世界。2006年,歷時三年創作的《大國崛起》一經推出便引發國內的強烈反響,一度成為熱點話題,并行銷海外。時任韓國總統的盧武鉉甚至建議所有的部長都要看一下這部來自中國的紀錄片。影片節目光盤和同名圖書在海內外熱銷,成為當時中國紀錄片市場化、國際化的重要代表。在總策劃之一麥天樞的眼里,“《大國崛起》是關心中國改革的電視人在學術界的支持下完成的一次思考”⑦。《大國崛起》的推出,成為一次中國紀錄片人在“恰當的時間,做對了的恰當事情”,也讓紀錄片以一種思想和話語的力量影響社會。
這一時期,視野的打開讓許多紀錄片人將創作目光投向浩瀚的歷史長河和廣闊的世界舞臺,歷史人文類題材重新崛起,如《晉商》(2003)、《復活的軍團》(2004)、《故宮》(2005)、《圓明園》(2006)、《再說長江》(2006)、《新絲綢之路》(2006)、《大國崛起》(2006)、《森林之歌》(2007)、《水問》(2008)、《我們的奧林匹克》(2008)、《頤和園》(2008)、《大師》(2008)、《美麗中國》(2008)、《澳門十年》(2009)等精品力作不斷推出,中國紀錄片爆發出更加強大的氣魄,以更加主流化的表達回歸主流社會。
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同樣是這一時期紀錄片的品質。《我們的留學生活》(2000)、《平衡》(2001)、《英與白》(2002)、《姐妹》(2003)、《幼兒園》(2004)、《遷徙的人》(2007)、《紅跑道》(2008)、《1428》(2009)、《西藏一年》(2009)、《歸途列車》(2009)等影片具有鮮明的作者意識,飽含社會責任和文化自覺,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紀錄片多元價值和美學探索的代表。
4. 政治化產業時期(2010-):國家話語與市場話語的博弈互動
當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中國從經濟大國向文化大國進一步邁進,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頂層設計日益明晰。中國紀錄片的發展,正恰逢這樣一個契機。在收視率大棒下被不斷排擠的紀錄片逐漸重新嶄露頭腳,“產業化”的呼聲漸起。
2010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出臺《關于加快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在中國紀錄片發展史上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以此為節點,在今后的幾年里,國家又相繼推出了有關紀錄片發展的多種政策和激勵措施,政府以產業化思路帶動紀錄片事業發展的戰略路徑逐漸確立。在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的雙重驅動下,中國紀錄片進入“政治化產業時期”。
政治化產業時期,中國紀錄片的大片創作進入常態化,《敦煌》(2010)、《梁思成 林徽因》(2010)、《公司的力量》(2010)、《華爾街》(2010)、《外灘佚事》(2010)、《走向海洋》(2011)、《外灘》(2011)、《貨幣》(2012)等影片接力和發展了上一時期的大片化氣勢,且這些單體項目大多為市場化、項目化運作。
2012年,一部展現中華美食文化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將中國紀錄片引入萬眾矚目的“公眾時代”⑧,《舌尖上的中國》在全媒體平臺熱播與口碑發酵,形成紀錄片行業的“舌尖現象”,紀錄片成為熱門話題,觀眾認知度提高。“舌尖”這一IP的成功,讓市場看到了紀錄片進行“品牌化”“季播化”“工業化”“模式化”操作的可能性,這給中國紀錄片產業帶來的意義和價值不可估量。2013年,《舌尖上的中國2》還未開拍,就已經獲得8391萬元的廣告贊助,《舌尖上的中國3》的廣告冠名費更是拍出1.18億元天價,有力提振了紀錄片產業的信心。
這一時期,產業的不斷發展,讓市場主體走向多元化,民間力量正在和政府、媒體力量形成有機互動態勢,隨著三多堂、視襲影視等民營紀錄片公司上市新三板,資本的力量開始連接和助力這些市場力量。另外,除了電視播出平臺在政策推動下的不斷擴展,新媒體和電影院線作為一種新的平臺驅動力量正在延展紀錄片的生存空間。過去談論紀錄片總是默認為電視紀錄片,就這一時期紀錄片產業的發展態勢來看,另外兩種力量已不可忽視。
根據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簡稱CDRC)的數據,2017年全網視頻總點擊量為12928.6億次,紀錄片總點擊量為90.5億次,占比0.7%。2010年后,視頻網站逐漸告別草創階段,內容質量具有較大提升,版權管理日益規范。視頻網站從單純作為傳播平臺,到現在介入自制投資,成為紀錄片傳播和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力量。近幾年,《我在故宮修文物》《尋找手藝》《假如國寶會說話》《人生一串》《了不起的匠人》等紀錄片在網絡媒體熱播,成為“新晉網紅”。新媒體平臺正在不斷創新紀錄片的觀看和消費模式,除了傳統的廣告盈利模式,隨著視頻會員付費的大勢到來,紀錄片會員付費觀看也成為新媒體紀錄片用戶的重要消費模式。目前,愛奇藝、優酷等平臺正在紀錄片付費觀看、平臺與片方分成等方面做出探索。
2017年,中國紀錄電影總票房為2.7億,這一數字是2010年的10倍,票房再創新高。2018年,更多紀錄電影登陸院線,《出山記》《最后的棒棒》《川流不息》《出路》《大三兒》等一批優秀的國產紀錄電影通過點映或公映等方式和觀眾見面,《厲害了,我的國》突破4.8億票房,繼2017年《二十二》的1.7億票房后再度刷新中國紀錄電影票房紀錄。這一時期,院線紀錄片題材和類型更加多元;紀實美學回歸;紀錄電影影像品質進一步提升;口碑引領和營銷傳播在中國紀錄電影市場發揮更大效果;紀錄電影成為國家政治傳播的抓手,成為“新主流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政治化產業時期的中國紀錄片,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在內容生產上跟政治的連接愈加密切。2010年以來,《旗幟》(2011)、《斷刀——朝鮮戰場大逆轉》(2011)、《科學發展鑄輝煌》(2012)、《信仰》(2012)、《大魯藝》(2012)《苦難輝煌》(2013)、《習仲勛》(2013)、《國魂》(2014)、《百年潮,中國夢》(2014)、《勞動鑄就中國夢》(2015)、《五年規劃》(2016)、《長征》(2016)、《長征紀事》(2016)、《永遠在路上》(2016)、《巡視利劍》(2017)等作品在政治傳播和主流意識形態建構方面顯示出較大影響力。黨的十九大召開前夕,央視聯合省級衛視集中播放了一批獻禮紀錄片,如《將改革進行到底》《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我們這五年》《大國外交》等,引發規模效應,讓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建設成就深入民心,為黨的十九大召開營造了輿論氛圍。
與此同時,紀錄片積極服務國家戰略,肩負起跨文化傳播與國家形象建構,打造文化軟實力,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與文化安全的任務。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打造,關于“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等諸多充滿中國智慧的中國方案的傳播,紀錄片也成為一個重要的闡釋和傳播場域。
以“一帶一路”為例,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簡稱“一帶一路”)后,引發了國際輿論廣泛關注,這其中既有支持和響應,也有不少質疑之聲。在中央引導和國內外關注下,“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火熱,近幾年就有如《絲路,重新開始的旅程》(2013)、《對望:絲路新旅程》(2015)、《海上絲綢之路》(2016)、《奇域:探秘新絲路》(2016)、《一帶一路》(2016)、《絲綢之路經濟帶》(2017)、《絲路,從歷史中走來》(2017)《非凡之路》(2018)等一批緊扣這一倡議的紀錄片出現,還有《世紀絲路》《共同命運》等作品正在制作。這其中既有國產作品,又有國際合拍;既有官方話語,又有民間話語、他者話語;既有大開大闔的宏大敘事作品,又有見微知著的故事化小品。它們成為講述 “一帶一路”故事,闡釋“一帶一路”理念的重要文本。
在國家話語和市場話語博弈互動的話語空間縫隙之間,許多紀錄片創作者并沒有忘記紀錄片的本性和責任,對主流現實生活進行體察和思考。筆者曾對獲得2016年中國紀錄片學院獎的現實題材影片《絕境求生》如此寫道:“影片直面國企改革這一敏感命題,多維度深入挖掘人物內心,敘事充滿力量,又飽含情感。故事在眾多線索與人物之間交織并進,剪輯張弛有度、大氣流暢,展現了國企改革中遇到的困頓與阻力,突圍時的艱辛與不易”。在這一時期,許多高質量的現實題材紀錄片如《歸途列車》(2010)、《活著》(2011)、《造云的山》(2012)、《千錘百煉》(2012)、《鄉村里的中國》(2013)、《棉花》(2014)、《高三16班》(2014)、《我的詩篇》(2015)、《高考》(2015)、《人間世》(2016)、《生門》(2016)、《搖搖晃晃的人間》(2016)、《鏡子》(2017)等佳作推出,雖然數量不占優勢,傳播渠道仍相對較窄,但新媒體和藝術院線等力量的加入使得這類作品多了曝光機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年代,紛繁變化的時代下社會與個體命運的變遷,值得紀錄片人留下注解。
整體而言,政治化產業時期的中國紀錄片,在價值上重新回歸主流;在服務和關照的觀念上兼具國家、市場與社會責任意識;在話語權和話語方式上為國家話語主導,市場話語更加開放且更具活力;在關照視點和主題表征上更加多元;在傳播對象上走向公眾化和國際化;在依托媒介上從電視一家獨大向電視、新媒體、電影院線三極傳播變革。
三、結語:中國紀錄片,新時代與新作為
40年改革開放史,中國紀錄片與時代同發展,與社會共呼吸,有對民族命運的思索,有對現實生活的洞察,有對人生百態的描繪,也有對真理思想的問道。紀錄片,無疑是時代的見證者、書寫者和闡釋者。
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身處“春天”的中國紀錄片產業也應當有新作為。新時代,中國紀錄片需要繼承和發揚改革開放精神,需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氣,“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時俱進”的追求,“求真務實”的品質。要創新利用紀錄片的特性和優勢,記錄歷史與現實,為國家和社會畫像;把紀錄片當作一種文化自信的表征,傳播先進文化,為人民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創新利用紀錄片的功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節點上為民族和國家凝心聚魂;發揮紀錄片的大眾文化產品價值,讓紀錄片產業成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以紀錄片為媒介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推動人類文明交流互鑒。這是新時代中國紀錄片大有可為之處,也是發展趨向。
注釋:
①② [美]比爾·尼克爾斯:《紀錄片導論》(第二版),陳犀禾、劉宇清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8頁。
③⑤ 何蘇六:《中國電視紀錄片史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7頁。
④ 朱羽君、殷樂:《生活的重構——新時期電視紀實語言》,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頁。
⑥ 何蘇六:《紀錄片的責任與影響力》,《現代傳播》,2005年第1期。
⑦ 徐馨:《讓歷史照亮未來——來自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的啟示》,《人民日報》,2006年12月1日,第14版。
⑧ 何蘇六主編:《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