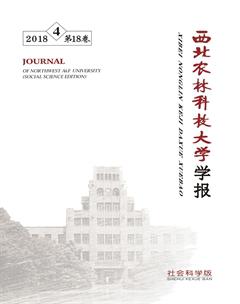“雙主體半熟人社會”: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重構
摘 要:水利水電工程建設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庫移民。通過對浯溪口水庫S外遷社區的個案研究,對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社會樣態進行了分析。水庫移民安置過程往往伴隨著移民原有村落的空間“脫嵌”以及外遷社區的空間“嵌入”。原有的移民村落是一個在差序格局主導之下的結構完整、關系網絡緊密的熟人社會共同體;而在嵌入的外遷社區空間,生成了由水庫移民與遷入地原住民組成的“雙主體半熟人社會”。首先,“社會樣態類型化”是“理想型”研究工具,“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概念建構是對水庫移民外遷社區樣態的理論化;其次,水庫移民“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社會樣態在結構維度表現為外遷移民和原住民群體組成的“事實”和“心理”同構的“雙主體”;在關系維度表現為以“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以“雙主體”間內部“熟人化”為基礎的“半熟人社會”;最后,基于S外遷社區“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空間重構中經濟、社會、政治空間的考察,認為外遷社區的空間治理需理解其社會樣態,把握社會樣態的內在機制和運作邏輯。
關鍵詞:水庫移民;雙主體半熟人社會;外遷社區;空間重構;社會樣態
中圖分類號:C912.83;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8)04-0095-08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惠及民生福祉,我國水利水電建設逐步推進,但水利水電建設又不可避免地會破壞庫區居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空間,使得水庫移民人口不斷增加。《2016年全國水利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在建的大中型水庫達到248座,開工建設安置點642個,新建集中安置住房458.5萬平方米,搬遷人口達127 589人。其中,外遷移民作為移民群體中社會關系和空間結構變遷最為劇烈的群體,需要引起特別的關注。許多學者已經對其進行了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安置模式[1]、社會整合[2]、社會適應[3]、經濟恢復[4]、社會保障[5]及發展困境[6]等方面,雖已經取得較多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已有研究雖提到水庫移民外遷社區與普通移民社區的區別之處,但沒有對外遷社區的社會樣態進行理論上的概念化;(2)大部分研究從外遷移民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忽視了外遷社區中的原住民群體,未能很好地進行“整體”上的主體性闡釋;(3)已有研究很少注意到物理空間對外遷社區社會樣態生成的影響,未將物理和社會空間統一到一個概念框架中進行分析。鑒于上述局限性,筆者從關系和結構的角度對水庫移民外遷社區進行社會樣態的分析,并提出“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概念。主要研究問題包括:(1)水庫移民外遷社區“雙主體半熟人社會”提出的理論基礎是什么?(2)水庫移民“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具體內涵是什么?是如何進行概念化的?(3)從經濟、社會、政治三個空間來討論外遷社區空間重構生成的“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樣態是怎樣的?
本文以浯溪口水庫S外遷社區的田野調查資料進行研究和分析。浯溪口水利樞紐壩址位于景德鎮市浮梁縣,S外遷社區是其中一個外遷安置點,位于浮梁縣東南面,景德鎮市東郊,是浮梁縣糧油作物的重要產區,森林覆蓋率高,礦產資源豐富,戶數370多戶,總人口大約為1 500人。移民來源于Z鎮L村X組、M組,距離S外遷社區83.2公里。L村以稻田、茶葉、務工為主,人均年收入為6 500元,其中種植業收入約占30%,山林收入約占30%,外出務工收入約占40%。
2013年6月,經村民理事會與移民戶的協商,決定搬遷到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較好的S外遷社區。2014年9月S外遷安置點開工建設,建房布局采用“組團式”布置,通過順暢的環形道路提供便利的交通。結合“三通一平”,建筑主要朝南北向。2015年土地平整、水電建設、場地硬化、社區綠化等的基礎配套設施逐步進行,房屋基本修建且裝飾完成,移民逐漸入住。2016年6月,移民基本全部入住,實際征收土地14.703畝(宅基地10.32畝,周邊旱地4.383畝),安置18戶81人。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綜述:“社會樣態類型化”的發展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一種概念工具,是一種“邏輯上的真實”。“理想類型”的運用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發現現象和問題,并預測事物的發展趨向”[7],將具體與抽象互相轉化。“社會樣態類型化”也是一種理想類型的分析,學者們基于不同的對象和視角對其進行了討論。
費孝通將自然經濟下的傳統農村社會稱為“熟人社會”[8],是一種在差序格局主導下的以血緣為紐帶的鄉土社會。“熟人社會”概念的提出為社會樣態類型化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許多學者進行了后續的研究,如“熟人社會”中的競選[9]、人情[10]、階層關系[11]、性質及特征[12]、面子[13]、“差序治理”[14]及對“熟人社會”理解的再思考[15]等。賀雪峰用二分法的方式表現了20世紀80年代我國農村的社會轉型狀況,認為傳統的自然村是一種“熟人社會”的樣態,但是現代的行政村卻是以“半熟人社會”存在的,具體表現為:村民異質性增大、內生秩序能力喪失、主體感缺失[16]。在鄉村青壯年勞動力常年外出打工,異地化的情況下,吳重慶認為這種情況已導致農村社會的日常生活有異于“熟人社會”的運作機制,從而提出了“無主體熟人社會”的概念,是空心化農村的社會運作邏輯[17]。田鵬等將就近城鎮化進程中農民集中居住區的運行機制定義為“無主體半熟人社會”,是一種“脫身不脫根”與“半嵌入”辯證作用的社區運作邏輯[18]。另外,茍天來等提出“弱熟人社會”[19],李飛等提出“類熟人社會”[20],張繼焦提出“傘式社會”[21]和“蜂窩式社會”[22],譚同學提出“工具性圈層格局”[23],徐曉軍提出“內核—外圍結構”[24],宋麗娜等提出“圈層結構社會”[25]。
通過梳理既有文獻發現,“社會樣態類型化”的研究和概念建構的發展是伴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空間重組的。透過不同的視角,學者在不同的領域觀察到了不同的社會樣態,都是一種由“實踐”向“理論”的歸納。從“社會樣態類型化”的角度來研究水庫移民外遷社區問題將為水庫移民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幫助我們了解和分析移民和原住民群體在外遷社區中是如何進行空間調配和治理的,為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共同體”再造提供理論依據。
(二)理論分析:“社會樣態類型化”關系與結構維度闡釋
深入分析學者對“社會樣態類型化”概念的建構和界定,可以發現基本上均圍繞“關系”和“結構”兩個維度來進行闡釋。費孝通的“熟人社會”,從關系維度來講是一個以宗法血緣、道德倫理為紐帶的親密性社會共同體,從結構角度來講是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水圈波紋式結構[8];賀雪峰的“半熟人社會”,從關系維度來講是一種村民之間異質性較強,關系紐帶變弱,熟悉程度降低的“半親密”型,從結構維度來講,是傳統村莊規范逐漸失效,村莊成員的生活秩序被打破,從而形成的村民主體感弱化的村莊結構[9];吳重慶的“無主體熟人社會”,從結構維度上是一種村莊主體性喪失下的空心化狀態,從關系維度上看,雖存在社會角色缺失的現象,但仍保留著“熟人社會”的關系紐帶[17];田鵬等的“無主體半熟人社會”,“無主體”從結構維度釋義為農民的物理空間區位的變化使得他們從原有的社會結構中脫離,而在新的社區中又因為農民的身份而無法嵌入到社區的社會結構中,形成了“社區里的農民”[18];從關系維度上來講,將“半熟人社會”解釋為以建制鎮為單位的“大雜居”和以行政村為單位的“小聚居”的新形成的居住格局所生成的一種社會狀態。“社會形態類型化”概念不僅為我們展現了社會變遷中農村社會所發生的不同生活現狀,而且為我們建構了重新解釋農村問題的理論框架,通過剖析各種“社會樣態類型化”的內在邏輯,可以發現關系與結構總是互相交錯、相輔相成的,比較詳實的理論研究也為水庫移民“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概念建構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見表1)。
三、水庫移民外遷社區“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概念建構
水庫移民外遷社區“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概念內涵,不僅描述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社會樣態,而且為這種樣態的描述提供一種理論建構。從關系和結構維度來看,水庫移民外遷社區“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內涵即是:基于結構維度的外遷移民和原住民群體組成的“雙主體”結構;基于關系維度的以“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以“雙主體”間內部“熟人化”為基礎的“半熟人社會”。“雙主體”結構同時存在于物理和社會空間結構之中,是在居住空間上的區位組合,也是社會空間上的關系再構。
(一)結構維度:事實與心理同構的“雙主體”
水庫外遷移民“嵌入”到遷入區與原住民群體共同組成“雙主體”結構,是從外遷社區整體而言的。“雙主體”將移民和原住民視為兩個主要的對象,既是“事實”上的“雙主體”,也是“心理”上的雙主體。吳重慶認為村落的社會角色缺失是一種“無主體”[17],田鵬等認為居民的集中上樓也造成了一種“無主體”,但是這兩種“無主體”的含義卻不相同[18]。吳重慶的“無主體”是一種“事實”上的現象,青壯年的角色缺失使得村落的真實日常生活無法完整[17];而田鵬的“無主體”更偏向于一種“心理”上的感受,是一種情感的不足導致的無主體感[18]。水庫移民外遷社區是外遷移民實際生產生活空間的遷移,在這種過程中移民的人與物進行了事實上的變化,與外遷社區中的原住民形成了社會角色上的疊加,屬于“事實”上的“雙主體”;另一方面,移民群體異地搬遷,從原有的傳統村落中“脫嵌”而出,遠離了熟悉的生產生活環境,容易產生無歸屬感,甚至邊緣化。而原住民群體平靜的日常生活也會因為移民群體的到來而發生改變,在與移民群體的互動中形成心理上的認知和身份上的感知。這樣,兩者之間不同的心理感受構成了水庫移民外遷社區“心理”上的“雙主體”。
Z鎮L村X組、M組的移民遷入到S外遷社區,進行房屋的重建和生產資料的恢復,并通過日常生活的行為以及社會交往中的各種必然或者偶然的事件與原住民群體進行互動和交流,這些都是現實存在的行動。移民“嵌入”后,外遷社區的正常運行已經不只是原住民群體單方面的事務,而是需要移民群體盡快適應遷入區的生活,進而與原住民群體共同為外遷社區的建設而努力。因此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雙主體”是“事實”上的范疇,它通過實實在在的社會行動表現并發展。另一方面,移民的外遷安置所引起的移民歸屬感、邊緣感等問題也切實存在,正如X組和M組移民從Z鎮L村外遷到S外遷社區,X組和M組移民從原有的社會結構中脫離,從熟悉的情感場域轉變為較為陌生的情感場域。這類似于田鵬等提出的農村居民集中上樓的“無主體”狀態[18],但是由于在外遷社區的空間場域中,兩者會不可避免的通過經濟、政治、社會等行動進行博弈和互動,移民群體內部心理“無主體”會逐漸被弱化。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雙主體”的“心理”范疇指的便是移民和原住民群體之間不同的情感特征,不僅僅是各自的內部情緒體驗,而且是雙方對彼此的情感認知,具體表現為移民群體的無歸屬情緒、原住民群體的疑慮情緒以及雙方彼此的防御、接觸從而接納的情緒。
(二)關系維度:內部熟人與空間布局下的“半熟人社會”
水庫移民外遷社區從關系維度來講是“半熟人社會”,是基于“雙主體”結構整體上的“半熟人”樣態。類似于賀雪峰對行政村“半熟人社會”的建構,他認為行政村是多個自然村并村而成的,這樣就從單個自然村的“熟人社會”轉變為了多個自然村構成的行政村內的“半熟人社會”[9]。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組成也類似于“并村”,但與賀雪峰的“行政并村”所不同的是,水庫移民外遷社區并不是整個移民村與遷入區的組合,而是移民村的“小組”與遷入區的組合,屬于小集體向大集體的“嵌入”。正如S外遷社區,Z鎮L村并不是整村都遷入到了S外遷社區,而是只有L村的X組和M組遷入于此,其他組分別安置到了其他社區。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家族多以姓氏血緣關系為基礎自然而然形成居民村落聚居,主要以“小組”的形式存在。進行外遷安置時,政府在政策上考慮到了移民的社會適應和社會網絡問題,所以要求外遷安置的移民至少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搬遷,不可將“小組”拆散安置,即移民群體是以“村小組”的形式“嵌入”到外遷社區的。在政策性考量的結果下,外遷社區中的移民群體由于“小組”式的血緣和地緣紐帶而處于強關系網絡結構,比如村落的宗族關系。另一方面,外遷社區的原住民群體長期的共同生活也形成了較強的關系網絡,這樣,雙主體就形成了各自內部的“熟人化”,而在雙主體整體上是一種“半熟人化”的狀態。
外遷社區的居住空間布局也對“半熟人社會”的塑造有一定的影響。S外遷社區采用的是“組團式”的空間格局來進行移民的安置,而非“插花安置”。居住空間的設計按照“一塊宅基地一戶房屋”的原則,而非單元樓式的“集中上樓”。這使得移民的居住格局從傳統村落的不規則式轉變為了“組團式”的規則格局,但卻保留了移民之間的傳統村落的“鄰里關系”。這種“組團式”的居住空間布局一方面是外遷社區空間規劃的要求,另一方面則保證了移民“小組”的鄰里完整性,保留了移民群體保持頻繁互動的可能性。另外,由于外遷社區的宅基地需要通過平整山地而形成,所以移民居住區域一般會與原住民相隔一定的距離,整體來看大致分為兩個板塊。這樣移民和原住民群體各自在物理空間上形成了“小聚居”的樣態,而兩者在整體上則形成了“大雜居”的樣態。甚至移民的“小聚居”使得移民群體外遷的“無歸屬感”得到了一定的緩解,使其內部的“熟人化”愈加明顯。這樣的“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雙主體彼此的了解和交往,總體上形成了外遷社區的“半熟人社會”。
四、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社會樣態特征
空間重構是基于空間各要素解構而再塑造的過程[26]。原先存在的空間系統主體,由于受到外部環境或者內部要素的分離作用而使得空間形態和結構受到沖擊而解構,空間系統在某種力的作用下為了繼續發展而形成了新的重構系統,這種新形成的重構空間既可能由于各構成要素的優化組合而使得新空間具備更好的運行能力,也可能由于多種力量的推動作用使得新空間需要較長的時間進行各要素的調整,水庫移民外遷社區就是一種“現代性”下,由政府、市場、社會等力量共同推動,使得移民自愿選擇外遷安置而形成的一種社區空間,“雙主體半熟人社會”樣態的生成即是外遷社區空間重構的結果。水庫建設將移民傳統的村落空間轉換為工程空間,移民群體產生并“嵌入”到外遷社區空間,使得“雙主體”的經濟空間、社會空間、政治空間等發生了重構。
(一)經濟空間
外遷社區的經濟空間主要指“雙主體”獲取生存資源的機會,具體表現為“雙主體”的耕地、水田等土地資源以及從事非農勞動獲取收入的就業資源。外遷安置點的選擇一般都會考慮到當地的資源承載力,會選取一個資源較為豐富且可以容納外來移民生存發展的區域,正如S外遷社區負責人盧某所言:
“S外遷區域經濟以農業發展為主,耕地和山林面積大,耕地資源豐富,是糧油作物的重要產區,農業發展條件整體上比水庫淹沒區好,農業機械化程度高,土地流轉程度較高,農業特色明顯,產業化程度相對較高,雖然外遷移民經歷了生產資料被破壞的情況,但是外遷區的整體條件還是不錯的,現在雖然看起來安置區有點冷清,但以后的發展肯定會好起來的。”
外遷社區較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保證移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恢復,雖然短期來看不會有明顯的提升,但是長遠來看,外遷社區自有的物質資源和水庫建成后所形成的旅游資源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移民群體的耕地和水田資源通過外遷社區的調配而獲得,主要來源于原住民群體的土地征收,是協調置換的結果。這樣,部分原住民土地空間資源通過政策性的要求轉換給了移民,原住民的土地資源減少,移民的土地資源得到了部分恢復,形成了一種經濟空間的轉移。
從土地資源上來講,移民對外遷社區不只是空間的“嵌入”,更是空間的“恢復性置換”,是政策主導下的“移民—政府—原住民”三者間的空間轉移。另一方面,在從事非農勞動已經不能滿足村民正常生活需要的情況下,移民不得不在從事非農勞動的同時進行副職就業,以獲得額外的經濟來源。移民的加入為外遷社區增加了一定的勞動力,同時也增加了外遷社區的就業競爭率,使得原住民群體的就業機會相對減少。總體上,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經濟空間表現為一種“轉移式”的樣態,“雙主體”在土地空間上經過政策中介而得到轉移,就業空間經過自我競爭而得到轉移。
(二)社會空間
外遷社區的社會空間主要指“雙主體”的社會交往和互動,具體化為“雙主體”各自的關系網絡和“雙主體”間的接觸和溝通。移民群體以“小組”的方式嵌入到外遷社區中,也就是以一個“內部熟人”的關系網絡嵌入到外遷社區中。移民群體完整的傳統村落社會關系被破壞,但更緊密的“小組”聯系保留了下來,這種聯系在外遷社區中形成一種“集體感”,也是“半熟人社會”的基礎。
“我家搬過來住了快一年多了,房子在兩年前就修好了,一年后才住進來的。搬過來之后啊,感覺就像是到了別人家似的,總歸沒有原來那個地方舒坦。大家搬過來之后壓力都變大了,可能是建房子都借了錢,需要好好掙錢還債吧。我們原來那個村現在都七零八散了,就剩下我們自己小組的人住在這里。這周圍住的都是以前我們小組的,基本都認識,現在大家都挺忙的,比以前交流少了。不過已經挺好了的,閑下來的時候也去他們家轉轉、聊聊。和他們村(即原住民行政村)沒啥聯系,住的不挨著,也不認識。”(S外遷社區Z鎮L村X組移民張某)
正如S外遷社區移民張某所言,移民群體以“小組”的形式存在,彼此處于熟悉的狀態。但是由于遷入外遷社區后經濟壓力的增加,移民不得不分出大量的時間外出勞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移民群體內部的交流減少。而且雖然小組內部熟人化保留,但生活空間的變化也切切實實使得“離土又離鄉”的移民情感受挫。筆者在對移民張某訪談時問到“您是哪里人?”王某回答的是“L村M組”,而不是S外遷社區。這說明移民的身份自我認同仍處于原村落狀態,在心理層面并沒有把自己視為“S外遷社區”的“主人”,缺乏歸屬感。移民群體由于家園喪失,賴以生存的村落空間損壞,而處于“無歸屬感”的狀態,且在一定的時期內無法在外遷社區中培養出穩定的身份認同感。另一方面,雖然外遷社區中“雙主體”的居住空間存在一定的距離,但還會因為必要的生產生活產生直接的接觸,并由于資源的爭奪而發生矛盾和沖突,S外遷社區的“河流洗衣事件”的發生就是雙主體間的一次博弈。
“我們村里有條河,雖然現在已經通了自來水,但是大家還是喜歡去河邊洗衣服。移民搬過來后也想在那里洗,可是河碼頭(即河埠頭——洗衣點)就那幾個地方,我們村的那些女人就不讓地方給移民,他們就起了沖突,不只一次呢。讓我們解決我們也不好解決啊,也就能簡單的調解一下”(S外遷社區村委方某)
“河流洗衣事件”只是“雙主體”資源博弈的一個縮影,但正是在資源博弈的過程中,“雙主體”間進行了互動和溝通。通過這些日常生活的行動,“雙主體”間不斷地產生關聯,構造著外遷社區的社會網絡。在外遷社區“雙主體”各自“熟人化”而形成的“半熟人社會”中,不可避免地會由于彼此的“不熟”而帶來空間的博弈,但這種博弈也帶來了身份逐漸認同的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事件的發生,“雙主體”間的社會空間也會不斷地進行重構,這個重構的過程也是“雙主體”間接觸、了解的過程。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社會空間樣態是在“半熟人社會”的基礎上動態式發展的,在“雙主體”間彼此的互動和社區治理活動下逐漸塑造外遷社區的社會空間。
(三)政治空間
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權力運作的基礎[27]。外遷社區政治空間指的是社區成員能依法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參與社區管理,維護自身權利。移民群體能否在“嵌入”外遷社區的同時,也“嵌入”到外遷社區的政治組織之中,對移民群體的主體性地位的塑造有關鍵性的影響。移民群體的基層權力資源隨著外遷社區的形成而受到弱化,原有的村委組織結構可能無法發揮應有的組織權力,這不僅是移民群體整體的政治權利的壓縮,也是移民個體利益訴求“歸屬”的擠壓。在雙主體半熟人的外遷社區狀態下,原住民的村委會仍保存著“熟人”的空間狀態,假如移民群體的組織力量無法接入到原村委之中,那么新形成的外遷社區的基層組織將形成一種“單主體熟人”的村委會,從而阻塞移民群體的自下而上的組織參與權利。尤其是特定福利待遇較好、村集體資產豐富的村社,如S外遷社區的移民L村X、M組,他們集體提出希望政府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新遷入移民可以享受到同等村民的福利待遇,如果移民的政治權力代表無法介入到外遷社區的資源治理,那么移民的個人利益和公共資源也無法得到保證。
“我們組全都搬到這里來了,我以前是M組的組長,到了這邊也是。已經和這邊的村委進行過了交接,把黨組織關系等都轉了過來,希望能繼續給M組村民帶來一些福利吧,讓大家在這里都能過上好生活。”(S外遷社區M組組長吳某)
外遷社區的“雙主體”在政治空間上主要體現為社區組織中的“雙主體”,即村支部和村委會中的原有組織人員和移民遷入組的負責人,是移民在外遷社區空間的政治性“嵌入”。由于原有組織人員所形成的比較成熟的村“兩委”也是一個“熟人化”的內部團體,移民遷入組負責人在村“兩委”中的“嵌入”可能會受到阻礙,形成政治性的排擠。或者移民嵌入組負責人不能擔任重要性的角色,從而無法在關鍵性的事件中為移民發聲,形成移民群體的“政治邊緣化”。另一方面,大量外遷移民的涌入也短期內加大了外遷區村委會的工作量,外遷區村委會的基層權力范圍得到延伸,需要將移民群體的政治、組織事務納入到村委會的日常治理之中。不僅移民群體基層權力資源可能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也可能造成外遷區村委會的負擔過重,導致治理不當,引發矛盾和沖突。總之,外遷社區的政治空間在雙主體上都表現出一種“壓力式”的樣態,具體表現為原住民組織的“事務性壓力”和移民組織的“邊緣性壓力”。
綜上,水庫移民外遷社區“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生成邏輯見圖1。
五、結論與討論
水利水電建設引起了水庫移民的產生,外遷安置更是一種較大的社會變遷。從費孝通先生提出“熟人社會”的概念以來,各種理想型“社會樣態類型化”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情境變遷中解釋著空間樣態的重構。本文從關系和結構變遷的空間視角分析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空間樣態和運作邏輯,提出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雙主體半熟人社會”概念,即基于結構維度的外遷移民和原住民群體組成的“雙主體”結構;基于關系維度的以“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以“雙主體”間內部“熟人化”為基礎的“半熟人社會”關系形態。水庫移民外遷社區的生成既是一種空間重構的結果,也是一種“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的形成,兩個主體在社區空間中行動,又重構和能動著社區空間。空間制約著雙主體的行動,又依賴雙主體的行動而存在。在這樣的社區運作邏輯下,應如何進行社區治理,以保證“雙主體”間的空間配置和資源治理?大量外遷移民的涌入必然加大了安置區村委會的工作量,如移民安置協調、組織和管理問題;給移民上戶和登記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問題;當地的基礎設施和社區配套服務承載能力面臨的壓力問題;移民和安置區原居民糾紛處理等等,這些給安置區村委會機構能力提出挑戰。外遷移民遷入安置區,還會對安置區原居民的社會關系產生重構,原居民不僅要經歷一個接納移民的過程,同時在互動中,重新組合自己的社會關系。如何協調移民群體和原住民群體的利益,在他們的資源博弈中尋找到一種平衡的治理方式,這都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水庫移民外遷社區“雙主體半熟人社會”不僅僅是一種概念建構,更應該為我們的社區治理服務,為外遷社區的治理提供理論支撐和指導。外遷社區的治理需理解其社會樣態,把握社會樣態的內在機制和運作邏輯,在有效的社區治理后,“雙主體半熟人社會”是否會發生進一步的轉變,移民和原住民群體是否會發生從“排斥”到“接觸”再到“接納”,從而使得“雙主體半熟人社會”發生社會樣態的轉向,比如“雙主體熟人社會”、或者“單主體熟人社會”等等,這就需要我們對現實經驗進行進一步的觀察和總結。
參考文獻:
[1] 胡寶柱, 謝怡然, 張志勇. 水庫移民社區安置模式探討[J].人民黃河,2012,34(12):112-113.
[2] 許佳君, 余文學. 水庫移民與安置區原居民的社會整合——以小浪底水庫移民為例[J].學海,2001(2):56-59.
[3] 馬德峰. 三峽外遷農村移民社區適應現狀研究——來自江蘇省大豐市移民安置點的調查[J].人口與發展,2005,11(2):62-68.
[4] 段躍芳. 水庫移民補償及其在移民社會經濟系統恢復與重建中的作用[J].三峽文化研究,2005(00):309-318.
[5] 陳華東, 施國慶, 陳廣華. 水庫移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尼爾基水庫壩區的案例分析[J].農村經濟,2008(7):96-98.
[6] 馬德峰. 中國征地外遷移民社區發展困境思考——以大豐市三峽移民安置點為例[J]. 西北人口,2006(5):6-8.
[7] 鄭晨. 韋伯的理想型式及其方法論意義[J].社會,1987(4):8-10.
[8]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9-10.
[9] 賀雪峰. 論熟人社會的競選——以廣東L鎮調查為例[J].廣東社會科學,2011(5):189-196.
[10] 賀雪峰. 論熟人社會的人情[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20-27.
[11] 李婷. “熟人社會”中的農村階層關系[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0(2):62-71.
[12] 陳柏峰. “熟人社會”變遷研究——從鄉村社會變遷反觀熟人社會的性質[J].江海學刊,2014(4):99-102.
[13] 桂華, 歐陽靜. 論熟人社會面子——基于村莊性質的區域差異比較研究[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72-81.
[14] 高名姿, 張雷, 陳東平. 差序治理、熟人社會與農地確權矛盾化解——基于江蘇省695份調查問卷和典型案例的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5(6):60-69.
[15] 劉小峰, 周長城. “熟人社會論”的糾結與未來:經驗檢視與價值探尋[J].中國農村觀察,2014(3):73-81.
[16] 賀雪峰. 論半熟人社會——理解村委會選舉的一個視角[J].政治學研究,2000(3):61-69.
[17] 吳重慶. 無主體熟人社會[J].開放時代,2002(1):121-122.
[18] 田鵬, 陳紹軍. “無主體半熟人社會”: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集中居住行為研究——以江蘇省鎮江市平昌新城為例[J].人口與經濟,2016(4):53-61.
[19] 茍天來, 左停. 從熟人社會到弱熟人社會——來自皖西山區村落人際交往關系的社會網絡分析[J]. 社會,2009,29(1):142-161.
[20] 李飛, 鐘漲寶. 農民集中居住背景下村落熟人社會的轉型研究[J].中州學刊,2013(5):74-78.
[21] 張繼焦. “蜂窩式社會”——觀察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另一個新概念[J].思想戰線,2015,41(3):77-86.
[22] 張繼焦. “傘式社會”——觀察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一個新概念[J].思想戰線,2014,40(4):54-61.
[23] 譚同學. 鄉村社會轉型中的道德、權力與社會結構[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07:222-223.
[24] 徐曉軍. 內核—外圍:傳統鄉土社會關系結構的變動——以鄂東鄉村艾滋病人社會關系重構為例[J].社會學研究,2009(1):64-95.
[25] 宋麗娜, 田先紅. 論圈層結構——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再認識[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8(1):109-121.
[26] 郁楓. 空間重構與社會轉型[D].北京:清華大學,2006:20-21.
[27] 包亞明.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