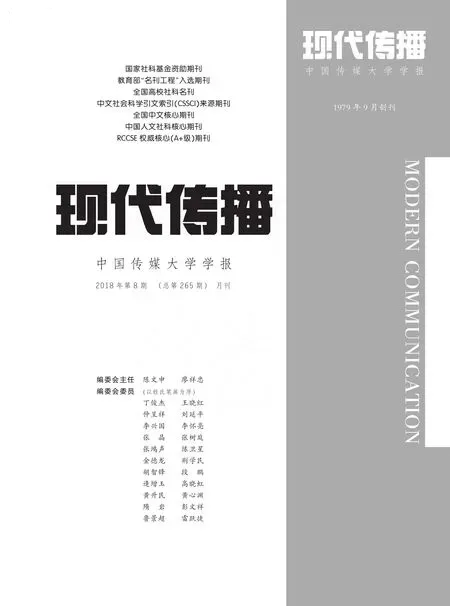在“中介化”與“媒介化”之間:社會思想史視閾下的交往方式變革*
■ 郭恩強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新傳媒技術的強力介入,“中介化”(Mediation)與“媒介化”(Mediatization)理論成為新聞傳播研究領域關注的熱點話題。特別是“媒介化”理論,已經成為當前傳播學中媒介研究的重要取向。這股最初導源于歐洲的媒介研究取向,之所以在歐美甚至全球新聞傳播研究領域蔚然成風,得益于當代諸多學者的努力。作為能夠體現媒介重要性的概念,“媒介化”術語最早出現在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學術研究中,后經北歐和德國學者的闡釋和運用,使得此概念在媒介研究中獲得廣泛關注。①“媒介化”研究關注范圍廣泛,從宏觀的媒介與社會文化的關系,到中微觀的媒介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和影響,諸多議題都在其關照之下。正是在此語境下,中國的許多研究者將這股潮流稱為“媒介化轉向”,亦或“傳播研究的中介化轉向”,認為如何理解中介化是當代傳播的核心問題,甚至斷言將傳播理解為中介化實踐,不僅構成了傳播研究的轉向,同時也是人類思潮的一種轉向,可以和語言學轉向、空間轉向、視覺轉向等突破現代性范式的學術轉向相提并論。②由此種判斷可見,“媒介化”或“中介化”思想對新聞傳播研究領域的理論意義和影響。
在已有的西文和中文研究文獻中,“媒介化”和“中介化”是兩個經常混用的概念,特別是在現實的經驗性研究中。因此,很多中外研究者在涉及這個話題時都要對這兩個概念進行學理層面的界定,③而這種區分本身,則反映出研究者背后的知識來源或理論與現實關切。典型的如潘忠黨在爬梳了西文主要的“媒介化”與“中介化”觀點后認為,與“媒介化”的概念相比,“中介化”的概念包含了對媒介力量的不同想象,同時兩者也蘊含著不同的時空想象。作為一種理論視角的“中介化”,是對人類傳播/交往形態轉換的一個概括,所有人類交往和互動都是中介了的過程,而且所有的社會生活也都有中介的機制。而經由傳媒中介的社會交往和互動,有別于面對面的社會交往和互動,凸顯于現代社會,是現代性的表現之一。④根據潘文的這一概括,“中介化”是一個關涉交往形態變革、時空意識以及現代性主題的更為一般意義的概念,如此我們似乎看到了吉登斯社會思想的痕跡。再如索尼婭·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在辨析“媒介化”與“中介化”時指出,雖然兩者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但前者主要是“日常實踐和社會關系日益由中介技術和媒介組織所型塑的元過程”,而后者則是“兩個相區分的元素、成分或過程之間的連接。”⑤這里關于社會關系與日常實踐,不同元素之間依靠中介連接和分離的思想,又帶有濃濃的西美爾形式哲學的意涵。由此可以說,傳播研究領域的“媒介化”與“中介化”理論,與西方社會思想史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聯。
盡管前述“媒介化”與“中介化”研究的代表性文獻,對與其相關的宏觀知識譜系和學術脈絡有一些介紹,但處理往往比較粗疏。本文根據“媒介化”與“中介化”相關研究文獻的提示,選取古典社會學家西美爾、現代社會學家吉登斯,以及后現代社會學者波斯特,對進路不同但與“中介化”與“媒介化”觀念有著千絲萬縷知識譜系聯系的社會思想家,對他們的相關論述進行分析,從而通過重返社會思想史,重溫媒介作為中介性機制所形塑的現代性/后現代性交往關系,并為“中介化”與“媒介化”研究提供更為寬廣的思想資源和研究視野。
二、社會交往關系的現代性轉化:西美爾的中介化思想
在以研究現代交往關系著稱的西美爾(Georg Simmel)看來,各種新的互動形式是構成現代社會最重要的要素。因為社會并非既定的“一種絕對的存在物,非得它先存在,以便讓其成員的個體關系——高低貴賤的地位、凝聚、模仿、勞動分工、交換、普通的攻擊與防衛、宗教社團、政黨的形成,諸多其他等等——能夠在其框架中發展或者由它來表征:社會只是對所有這些明確的活動關系總體的綜合或一個總的名稱而已。”⑥換言之,社會并非固定容器,其作為一種流動之物一直處于重構之中,而這種重構依賴于關系形式的改變。同時,社會交往形式并非“構成”社會交往,而就是社會交往與社會本身。這些包括心理、交往、結構/機構和形而上層面的各種形式,具體表現為語言、符號、科學、技術、制度、法律等各種類型的有形和無形的“人工制品”,它們彼此相互關聯、交錯并存,作為生活世界的人類要依賴這些相對固定的形式來展現自身。⑦西美爾的這種形式社會思想,包含著對“中介”與“媒介”因素的重視,諸多社會形式充當了人們進行互動交往的“路”“橋”“門”。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雖然西美爾甚少直接提到“媒介”這一關鍵詞,但他的研究中大量涉及了“中介”與“媒介”研究的核心議題。⑧比如他用路、橋、門等具有連接和阻斷的實物形式,來隱喻中介性形式對交往的可能和不可能。通過這些人造物中介形式,人類可以建立和跨越空間距離,從而構建出內在自我與外在之物的主客體關系。
在西美爾的社會思想中,個體間互動是社會構形的基礎。因為個人間的互動是所有社會構形的起點,也是無數新的社會構成形成的源泉。但也會有超越個體形式的其他非直接性的形式。正如他所言,“更進一步的發展創造了更高的、超越個體的構成形式,從而取代了互動作用力的直接性;這種構形以這些互動力的直接代表形式而出現,并吸收和調和了個體之間的直接關系”。⑨在這些被西美爾稱為“純粹形式”的構成中,貨幣成為現代關系基礎性變革的中介形式之一。“在貨幣交換中,把各種性質不同、形態迥異事物聯系在一起,貨幣成了各種相互對立、距離遙遠的社會分子的粘合劑;貨幣又像中央車站,所有事物都流經貨幣而相互關聯……”⑩在西美爾這里,貨幣的媒介性不僅在于其促發了交換方式的轉變,更在于導致了社會層面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根本改變,貨幣因此也成為個體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潤滑劑,為他擴展交往和生存的空間創造了便利,使得陌生人的相遇得以可能。
而“對于現代性而言,在‘中介’關系這一點上,大眾媒介和貨幣的意涵異曲同工”。因為大眾傳媒是這種構成形式之一,是一種社會交往形式,是現代性眾多關系之一。它是以宣稱民眾“直接代表”的身份出現的,并重新調和了個體的直接關系。大眾傳媒(如報刊)的出現極大地擴展了都市人行動的范圍,將以前不可能發生聯系的事件、事物與都市陌生人聯系起來。在這個意義上,媒體的內容退居其次,媒體的形式則具有了西美爾筆下貨幣的“純粹的工具”意義。與此同時,“占據著社會—文化運作中心的貨幣經濟重新組合了社會的各種質料,鍛造出現代生活平均化、量化的價值取向。它賦予事物前所未有的客觀性——一種無風格、無特點、無色彩的存在”。與此類似的是,現代大眾媒體將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與人物進行均質化處理,起到了磨平階級、性別、年齡等差異,實現了都市人格尊嚴的平等訴求。
此外,在構造西美爾所提及的各種現代性交往方式上,城市居于中介性的媒介位置。當代媒體理論家基特勒提出在本體論層面來思考媒介,他認為,在缺席與在場、遠與近、存在與靈魂的中間,所存在的正是一種中介關系,由此基特勒斷言城市是一種媒介。正是基于媒介—城市復合體這一理念,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團隊提出了“可溝通城市”的概念,將城市視為一個關系網絡的中介,從而把“中介化”思想作為城市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集中體現。毫無疑問,現代社會交往和互動的展現與展開,發生與發展在城市之中。羅伯特·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曾說:“城市是一種心靈狀態,一種風俗傳統的體現,同時還展現出隱含在這些習俗中、由傳統所傳遞的經過組織的禮儀與情感。城市不只是實體機制和人造建筑;城市更涉及了組成城市的那些人的重要歷程。城市是自然的產物,更是人性的產物。”對于由城市的中介性所導致的后果,西美爾有著敏感的覺察。在西美爾筆下,與貨幣經濟體系相關聯,城市人具有理智至上、計算的性格、傲慢厭世等特征,而在與人的關系上,還有矜持保留、自我表現的特點。
西美爾社會思想中對中介形式的強調,在后世有關傳播的“中介化”與“媒介化”研究中留下了非常顯著的印記。以研究傳播生態(Ecology of communication)和媒介邏輯(Media logic)著稱的阿什德(David Altheide)強調,“媒介化”的概念突出媒體而淡化機制,相比之下,“中介化”則更突出機制,即通過連接和協調形成一種現象或過程,并產生改造或型塑的后果。強調機制,源于作為社會學家的阿什德汲取了西美爾的形式哲學思想,同時,強調機制也與受到西美爾影響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對媒體的看法產生了呼應。同樣,也正是從西美爾意義上的社會形式出發,阿什德和斯諾(Robert Snow)開始將形式社會學引入傳播研究領域,提出了“媒介邏輯”的概念。在兩位作者看來,西美爾認為形式是這樣一種過程,社會通過它得以呈現自身。形式本身并不是一種結構,而是一種過程性的框架,正是通過它社會互動得以發生,而媒介邏輯就是這樣一種形式。后來,阿斯普(Kent Asp)將“媒介邏輯”這一概念與媒介化研究關聯起來,認為媒介化正是媒介邏輯的現實。此外,作為后來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媒介學理論中的“中介”與“媒介”思想,也與西美爾有諸多交集。在德布雷那里,媒介與中介既可以是技術—設備系統,也可以是社會機構,它們能夠成為媒介與中介的原因在于占據了特定關系鏈條中的某一位置或某一功能。中介并不是天生的命名,而是依據不同情境和關系得以確定,因此中介的位置并非是固定不變的。媒介與中介是使兩者發生關系的第三者,不只是對二者的連接,還對兩者、兩者的關系起著轉化的作用。換言之,德布雷的“中介”是一個哲學層面囊括性最大的概念,凡是建構兩者關系的都是中介。此種強調中介之物在特定的語境中起著橋梁轉化作用的關系性看法,非常接近于西美爾的形式社會思想。
三、社會交往方式的時空重組與抽離化機制:吉登斯的中介化思想
如果說西美爾關注的是早期現代社會的交往關系變革,只是通過門、橋、路等隱喻的方式揭示出現代社會肇始階段的中介化過程,那么吉登斯關注的則是晚期現代性,并且對大眾傳媒(特別是印刷)以制度化的中介形式變革社會交往方式有著更為直觀的體認。吉登斯曾坦言,自己的知識譜系特別是雙重結構化理論,與西美爾、列維-施特勞斯(Lévi-Strauss)、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人都有著緊密的知識關聯。吉登斯早年對西美爾的興趣后來導致了對戈夫曼的興趣。在吉登斯看來,西美爾將城市看作是現代性的典型,現代城市與傳統城市迥然相異,并且與遷移和交通聯系在一起,這是西美爾現代性理論的特殊之處。另外,吉登斯還認為,可以從如何穿越時間與空間而建立起人們的相互關系這個角度來看待西美爾的《貨幣哲學》。貨幣溝通的不僅僅是相互間從不了解的人,而且是從未見過的人。貨幣表現為一種媒介的功能,它原則上使人們可以與遠隔千山萬水的人進行交易,他們之間或許從來也不會謀面。貨幣也不僅僅是一種財富積累的手段,而且是現代社會賴以擴展開來的媒介,就如帕森斯后來所說的那樣,是一種交往和轉化的媒介。在這里,吉登斯關注和吸收了西美爾有關城市與現代性、貨幣與時空轉換、貨幣作為交往關系的中介與媒介等思想。關于交往方式,吉登斯還從結構理論大師列維·施特勞斯那里汲取了思想資源,認為從印刷的角度加以思考,其所代表的交往方式對于現代社會的興起極為重要,對現代民族國家的運作產生作用。再如電碼、收音機、電視、互聯網等媒介的出現,都使得人類的交往方式發生重要革命,它們不僅影響人們之間的交往,還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組織,這些都可以從施特勞斯那里得到啟示。從吉登斯在列維·施特勞斯那里獲得的啟示可以看出,在他看來,大眾媒介在現代交往方式變革中充當了非常重要的“中介化”與“媒介化”作用。無疑,吉登斯將西美爾的中介/媒介思想與列維-施特勞斯的交往方式思想進行了綜合。
那么,吉登斯是如何將上述這些有關時空、交往、中介/媒介、現代性等思考納入自己體系的呢?展開來講,在吉登斯看來,現代社會生活有三個特征或者說現代性有三大動力,即制度性反思、時空重組、抽離化機制(Disembeding,又譯作脫域)。正是由于時空重組與抽離化機制,導致現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質變得極端化和全球化,也導致日常社會生活內容和本質的轉型。
一方面,時空分離與重組是現代性的動力機制,也是抽離化的前提條件。在前現代社會,空間和地點是一致的。大多數情況下對大多數人來說,社會生活的空間維度都是受身體“在場”的支配。而現代性的降臨,“通過對‘缺場’的各種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間從地點分離了出來,從位置上看,遠離了任何給定的面對面的互動情勢。”同時,在現代條件下,地點也變得捉摸不定,“場所完全被遠離它們的社會影響所穿透并據其建構而成。建構場所的不單是在場發生的東西,場所的‘可見形式’掩藏著那些遠距離關系,而正是這些關系決定著場所的性質。”另一方面,社會制度的抽離化機制把社會關系從特定場所(地方性場景)的控制中解脫出來,并通過寬廣的時空距離,使社會關系重新組合或“再聯結”。抽離化機制又可區分為“符號標志”(Symbolic tokens)和“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兩者被統稱為“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s),西美爾筆下的貨幣可看作典型的“符號標志”。
在現代性三大動力中,大眾傳媒充當了時空分離與重組的中介化機制,成為身體“缺場”后“各種其他要素的孕育”之一種,它把空間從地點分離,通過閱讀與收聽想象重構了“那些遠距離關系”。正是在傳統社會關系向現代社會關系轉變的過程中,大眾傳媒在時空重組方面發揮著積極的影響,所以吉登斯強調:“在高度現代性的時代,遠距離外所發生的事變對近距離事件以及對自我的親密關系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普遍。在這方面,印刷或電子媒體明顯地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從最初的書寫經驗開始,由媒體所傳遞的經驗,已長久地影響自我認同和社會關系的基本組織。”此處吉登斯將傳媒看作現代性“經驗的傳遞”者,凸顯了他對媒介重構時空關系、進而重構社會關系、個人體驗的“中介化”與“媒介化”視角。比如他論證說,在個人體驗上,媒體對現代經驗的傳遞是通過將“遠距離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識中”實現的。新聞事件“也許被個人視為外在與遙遠的,但它們同等地進入日常活動之中”,從而產生“現實倒置”的感覺。換言之,“在現代性的條件下,媒體并不反映現實,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現實。”同時吉登斯強調,在現代性的語境中,傳媒影響的“要點”“不在于人們偶然地知道了發生在全世界的諸多事件,放在以前,他們對這些事件幾乎全然無知;這里的要點在于,如果不是鋪天蓋地而來的由‘新聞’所傳達的共享知識的話,現代制度的全球性擴張本來是不可能的。”這里蘊含著大眾傳媒中介了社會主體的社會交往與意義共享的思想。吉登斯在論述現代性時空關系轉變時,特別提到了尹尼斯和麥克盧漢,認為“他們都強調主導的媒體類型和時空轉型之間的聯結。媒體有助于改變時空關系的程度并不依從于它所攜帶的內容或‘信息’。而是依從于其形式和可再生產性。”在這里,吉登斯對媒介形式的重視,以及對這種媒介形式之于現代時空關系的重構,又與西美爾的形式哲學產生了呼應。
而且,盡管沒有明言,通過吉登斯的描述可以判斷,現代大眾傳媒也可看作是一種抽離化機制的“符號標志”,而媒體人則可以作為“專家系統”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形式變革的中介,大眾傳媒能將信息傳遞開來,用不著考慮任何特定場景下處理這些信息的個人或團體的特殊品質。比如,“在以往的時代中,我與社會的關系,換言之,我的社會特征受到傳統、親情和地點的制約;而今天,這種關系則要模糊不清得多。”傳統關系的模糊在某種程度上也要歸功于大眾媒體這種典型的抽離化機制。吉登斯曾說:“現代性和其‘自身的’媒體密不可分,如印刷文本和后繼的電子信號”,而今天的“印刷物仍是處于現代性及其全球網絡的核心”。由此,大眾傳媒構成了現代社會一種帶有抽離化機制的“抽象系統”。
吉登斯闡發的大眾傳媒的“中介化”與“媒介化”、雙重結構理論等觀點,對社會學者及傳播的“中介化”與“媒介化”理論學者產生了廣泛影響。如研究大眾傳播與現代文化關聯的社會學家約翰·湯普森(John B.Thompson),就具體闡發了吉登斯所強調的大眾傳媒對時空關系、社會交往的影響。傳播學者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也認為,現代性是一系列的制度形式和進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和心理環境,現代性是“以媒體為中介的現代性”。默多克強調現代性的制度形式以及媒體中介的作用,顯然受到了吉登斯的影響。再有,以斯蒂格·雅瓦德(Stig Hjaward,又譯為雅華德、夏瓦)為代表,“媒介化”理論中強調機構/制度(Institutions)研究路徑的學者,就受到了吉登斯“雙重結構化”理論的影響,主張媒介化理論要扎根于一般的社會理論。雅瓦德的“中介化”理論,最主要的觀點是媒體已成為“一個獨立制度”,它有獨特的信息和傳播功能,對于本土互動以及社會的全球結構有決定性的影響。他還根據吉登斯的思想提出了“制度邏輯”的概念,并認為它與“媒介邏輯”的觀點相融。在此,吉登斯和西美爾的思想在媒介化理論上再次有了交集。
四、后現代語境下信息方式變革:波斯特的中介化思想
相比于西美爾和吉登斯而言,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社會媒介思想更為激進。作為主張后現代理論并立志將它們引入傳播研究的學者,波斯特在知識譜系和學術脈絡上幾乎與西美爾和吉登斯沒有太多交集,這是因為他的思想來源主要得益于西方馬克思主義(這點上,可能與吉登斯對馬克思思想的吸收有交集)和后結構主義的社會思想家。波斯特對西方批判理論情有獨鐘,所以他受到以阿多諾(Theodor Adorno)、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影響尤大,同時他也對后結構主義理論和方法有著大量關注,如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的思想。之所以本文將波斯特作為典型研究對象加以討論,實因其對后現代語境下的傳播“中介化”與“媒介化”問題有著獨特看法,較早地論述了新型媒介技術對時空關系、交往方式、主體建構等方面的變革性影響。而上述這些方面,是傳播的“中介化”與“媒介化”研究重點關注的領域。
馬克·波斯特的中介與媒介研究建立在對此前傳媒研究的批判立場上。他針對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給予媒體關注不夠的現象批評說:“對媒體的探討仍是如此粗淺,以至于對媒體的性質還幾乎不存在一致看法,而對如何解釋媒介,一致意見則更少。”在這些關于媒體性質與解釋的觀點中,波斯特對只將媒介視為信號傳輸體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將“媒介只看成是工具,透明地反射著它們所傳遞的信息”的觀點,讓“人們很容易忘記媒介對交往關系的積極介入會達到何種程度。”在這里,波斯特明確地表達了作為中介的媒介對交往方式的變革作用。同時,對媒介技術的影響有著獨特敏感性的波斯特提出,此前對電子媒介的研究者只關注了新技術或新機器,關注了符號交換效率的如何提升,卻忽略了在技術革新的關頭,文化形態和社會形態對塑造新的交往模式所起的作用。他引用卡洛琳·馬文(Carolyn Marvin)的研究,認為電子交流的歷史“與其說是交流效率的演變,還不如說是人們在一系列競技場中所商談的對社會生活的行為準則至關重要的種種話題。這些話題包括:誰在場內,誰在場外;誰可以說話,誰不可以;以及誰有權威且可以相信。”例如,電話的引入不僅使人們可以遠距離交流,而且拓展了誰可以與誰交談的界限,從而危及了現存的階級關系。對電子媒介的關注由傳播效率轉換到時空關系、社會交往,以及身份意義的變革上,顯示出波斯特與西美爾、吉登斯對作為中介的媒介形式重視的一致性。
具體而言,立足于“語言學轉向”,波斯特效仿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提出了“信息方式”的理論,來對社會互動新形式中的語言學層面進行解碼。他將以符號交換形式為中介的信息方式劃分為三個階段,即面對面的口頭媒介的交換、印刷的書寫媒介的交換以及電子媒介的交換。在波斯特這里,如此劃分媒介階段,是為了討論后結構主義的一個主題,即主體是在交往行動及交往結構中被構成的。在各種信息方式中,信息保存和傳輸的每一種方法,都交織在構成一個社會的諸種關系的網絡中。為此,他著重探討了交往模式的變化是如何引起主體的變化的。在第一階段的口頭傳播時期,自我由于被包嵌在面對面關系的總體性之中,因而被構成為語音交流中的一個位置。在印刷傳播階段,自我被構建成一個行為者,處于理性與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而在第三階段的電子傳播階段,持續的不穩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換言之,在馬克·波斯特看來,每一種信息方式所形成的新的語言結構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社會關系網絡,并重新建構了它們所構成的社會關系及主體身份。
借助于后結構主義思想對語言的重視,波斯特認為需要發展一種基于語言學的交往行動理論。語言在這里充當了人們構建社會關系和主體身份的中介與媒介。因為“語言與交往行動本身有著天然的聯系。語言是交往行動的基本中介,也是人類交往的最基本的工具;而人類的交往行動則給語言提供了交流的空間,同時賦予語言現實的意義。”他用“第二媒介時代”來形容網絡時代對應于后現代主義的非理性,突出非線性、無序、不穩定、雙向互動等特質。此種媒介形式帶來了新的語言經驗和新形式的語言,從而顛覆了傳統那種穩定的、中心化的自律主體,產生了新型的主體。他把這一新主體概括為“數字主體”,從而與笛卡爾開始的理性自律的主體相區別。可見,不同介質所中介的關系所塑造的主體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波斯特以媒介為中心對信息方式的劃分,以及對不同階段媒介形式特點的概括,很容易讓人們想起以英尼斯和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北美環境學派的思想,這點連波斯特本人也不諱言。不過,他認為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即信息”雖指明了信息方式這一方向,但走得還不夠遠。換言之,雖然他們都聚焦于媒介形式而非內容對社會交往方式的影響,但波斯特以語言、符號為中介的信息方式導向了建構多元主體的哲學層面,而麥克盧漢則停留在依賴技術延伸人的感官需要的路徑分析人與技術的關系。與波斯特關注中介與技術對主體的影響類似,德布雷也強調中介與媒介因素背后人的主體性特征,特別是關注于媒介系統與通過某種社會組織來影響符號語義的環境系統間的相互作用。
五、結語
“中介化”與“媒介化”作為一種傳播的研究路徑,對以往重視傳播效率或效果的信息傳遞層面的研究起到了糾偏作用。此種研究思路使我們認識到,中介與媒介對現代社會的功能或效果不僅止于可見或可觸的經濟、政治等物質結構,也體現為構建可感或不可感的時空觀念、社會心理、情感文化、關系網絡等社會交往與意義的文化層面。基于此,本文從“中介化”與“媒介化”視角出發,通過對三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社會思想家的“中介化”與媒介化”知識譜系進行梳理,重點關注上述他們有關“中介化”與“媒介化”問題論述的社會思想史意義。回顧社會思想史我們會發現,從古典社會學家西美爾的中介與媒介思想,到現代社會學家吉登斯的大眾傳媒制度論,再到后現代社會學者波斯特的“信息方式”,進路不同但有著千絲萬縷知識譜系聯系的社會思想家,他們有關“中介化”與“媒介化”的社會思想都強調了形式的而非內容的,意義建構的而非效率好壞的層面,并且分別觸及到了早期現代性、晚期現代性,以及后現代性語境下交往關系的變革、主體性塑造等議題。由此可見,重返社會思想史的視野,不僅可以讓我們從經典論說中重溫媒介作為中介性機制所形塑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的交往關系變革,而且還可以為當代的“中介化”與“媒介化”研究提供更為寬廣、更具啟發性的思想資源和研究視野。
注釋:
③ 近年來梳理“媒介化”“中介化”概念的文獻很多,限于篇幅筆者在此不一一列舉。
⑤ Sonia Livingstone.OntheMediationofEverything:ICAPresidentialAddress2008.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9,no.1,2009.pp.1-18.
⑥ 西美爾:《貨幣哲學》,陳戎女等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8頁。
⑦⑧ 張昱辰:《論西美爾的媒介思想及其當代啟示》,《現代傳播》,2018年第5期。
(3)NFC手機支付和二維碼支付都屬于移動支付,生物識別和無感支付不需要用到手機直接支付,具有廣闊應用前景。現階段單一的生物識別很難滿足城軌快速支付的要求,上海城軌的人臉識別只是在車站門禁系統中實現應用,生物識別和電子標簽相融合的多重識別識別技術將成為今后發展方向。無感支付未來將利用手機APP把虛擬賬戶關聯實體賬戶,自動識別用戶ID,并在關聯的實體賬戶中自動扣除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