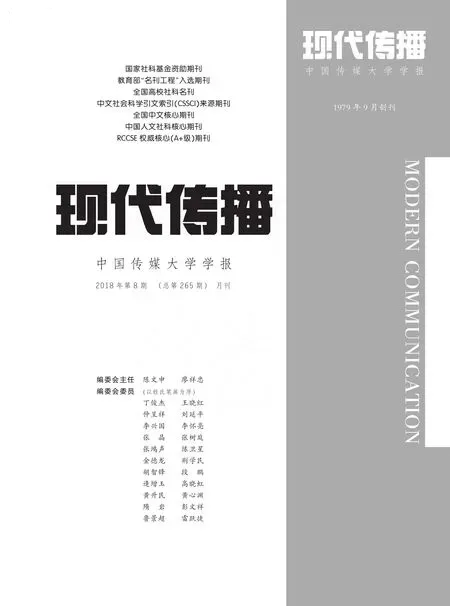主體性建構(gòu):改革開放初期節(jié)目主持人的話語轉(zhuǎn)型研究*
■ 於 春 李 娜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的主體性建構(gòu)和話語轉(zhuǎn)型,依托著改革開放初起、國家重啟現(xiàn)代化、思想文化界重申現(xiàn)代性、傳媒界重提新聞改革的時代背景。1980年北京新聞學會(即現(xiàn)在的首都新聞學會)成立,會議提出,“為了當好黨的思想中心,就要從加強實際工作和人民群眾結(jié)合抓起,從抓重大主題、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說明問題的材料入手,這是新聞改革的突破口。”①
綜觀現(xiàn)有研究,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媒現(xiàn)代性再探索乃至整個社會現(xiàn)代性再探索的新生事物、新聞改革與廣電改革的亮點,長期以來我國的節(jié)目主持人傳播研究卻鮮少深入思想文化領(lǐng)域,這不能不說是節(jié)目主持理論研究的一大遺憾。本文以現(xiàn)代性中的主體性為切入點,回望改革開放初期節(jié)目主持人傳播的話語轉(zhuǎn)型,力圖對節(jié)目主持理論研究有所推進。近年來,在電視行業(yè)斷崖式下跌的嚴峻形勢下,電視節(jié)目主持實踐也面臨深刻轉(zhuǎn)型,如何轉(zhuǎn)型?溫故或許有益于知新。
在福柯關(guān)于客體、主體和概念的話語結(jié)構(gòu)討論中,話語不僅表現(xiàn)世界,而且也在意義上說明世界、組成世界、建構(gòu)世界。②話語的建構(gòu)效果包括:社會身份建構(gòu)、社會關(guān)系建構(gòu)、知識和信仰體系的建構(gòu)。分別對應(yīng)話語的三個功能,即話語的“身份”功能、“關(guān)系”功能和“觀念”功能。身份功能涉及社會身份得以在話語中確立的方式,關(guān)系功能涉及話語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guān)系如何被制定和協(xié)商,觀念功能涉及文本說明世界及其過程、實體和關(guān)系的途徑。三個功能共存于所有話語之中,也在所有話語之中發(fā)生相互作用。在改革開放和國家重啟現(xiàn)代化、思想界重申現(xiàn)代性的時代氛圍中,節(jié)目主持人傳播開始探索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內(nèi)涵:主體性。本文即從思想史角度,鉤沉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節(jié)目主持人話語轉(zhuǎn)型的三個方面:“身份”轉(zhuǎn)型、“關(guān)系”轉(zhuǎn)型和“觀念”轉(zhuǎn)型,并分別體察其中的主體性建構(gòu),也將對這一主體性建構(gòu)的存在問題包括現(xiàn)代性的歷史局限加以反思。
二、身份轉(zhuǎn)型與主體性話語建構(gòu)
如前所述,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和國家重啟現(xiàn)代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思想文化界開始重申現(xiàn)代性。李澤厚在重新闡發(fā)康德哲學的基礎(chǔ)上,引入了“主體性哲學”這一關(guān)于現(xiàn)代性的重要內(nèi)涵。“主體性哲學”認為,人具有“能動”地改造社會的能力,人類歷史(包括人本身)是在實踐中形成的。同時,人具有認識歷史的能力,人類勞動活動產(chǎn)生的“自然合規(guī)律的結(jié)構(gòu)、形式”積淀于人類心理結(jié)構(gòu)中。因此,不管是從實踐層面還是認識層面來看,人都是歷史的“主體”。③“主體性哲學”成為中國1980年代特別是中后期新啟蒙主義思潮的主導(dǎo)性表述,這一風潮也出現(xiàn)在傳媒領(lǐng)域,先前的播音員傳播開始轉(zhuǎn)向新興的主持人傳播。
1.從播音員到主持人的身份轉(zhuǎn)型
1980年,中國中央電視臺專題部籌備一檔新聞節(jié)目,名稱是“觀察與思考”,究竟該采用什么樣的節(jié)目形式大家并不清楚,但經(jīng)歷了文革期間極左思想指導(dǎo)下播音呈現(xiàn)的“高、平、空,冷、僵、遠”的階段,節(jié)目組認為不能用類似播音員。④1980年7月12日,中央電視臺第一個新聞評論性的專欄節(jié)目《觀察與思考》開播,第一期節(jié)目名為《北京市民為什么吃菜難》,節(jié)目中有位中年男子拿著話筒四處采訪,隨后片尾打出字幕“主持人:龐嘯”,這是中國電視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主持人”這一稱謂。
“主持人”這一稱謂在今天看來或許并不出奇,但在1980年的中國,卻意味著從播音員到主持人的身份轉(zhuǎn)型。沈力是1950年代中國大陸第一位電視播音員,同時也是1980年代中國大陸第一個固定電視欄目的專職主持人。從播音員到主持人,沈力嘗試區(qū)分稱謂變化所折射的身份變化:主持人的最大特點,就是以相對個人的身份與觀眾直接地、面對面地交流,而不像先前播音員那樣以官方代表的身份宣講政策、發(fā)布命令、報告新聞。主持人以相對個人的身份出現(xiàn),就要求個性鮮明。有個性才符合生活的真實,才能夠增強節(jié)目的說服力。而體現(xiàn)個性的前提,是要有自己的見解,能夠獨立思考。⑤
沈力在對主持人的認識以及和先前播音員的區(qū)分中,力圖體現(xiàn)出主持人在身份、功能、個性、話語上最大程度的不同,特別是“以個人身份”“鮮明的個性”“獨立思考”“自己的見解”等表述,充滿了主體性話語特征和19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義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沈力認為的主持人“不像播音員那樣代表官方身份發(fā)布命令、報告新聞、宣講政策”,盡管這一認識并不一定完全準確,比如無論播音員還是主持人,都不可能脫離當時的官方背景,但當時的主持人和先前的播音員仍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相對來說,主持人的個人身份更加明顯,個性化更加鮮明,更有平等意識、獨立思考和自我見解,話語自由度也更大一些。
2.身份轉(zhuǎn)型與主體性話語建構(gòu)
1980年代從播音員到主持人的身份轉(zhuǎn)型,主體性探索在節(jié)目主持人話語中也有呈現(xiàn)。比如,在沈力主持的《為您服務(wù)》節(jié)目中“選字帖”環(huán)節(jié)的原稿為:
“前一段時間,我們收到不少書法愛好者,特別是一些青年學生的來信。他們問:現(xiàn)在出版的書法字帖種類很多,但不知哪些字帖比較適合于初學者臨摹。的確,對一個初學書法的人來說,字帖的選用是很重要的。為了幫助大家能夠選擇到一本合適的字帖,我們帶著這個問題,走訪了著名畫家和書法家董壽平先生。”⑥
作為中國大陸第一位電視播音員,同時也是中央電視臺第一個固定電視欄目的專職主持人,沈力對于時代變遷與社會變遷中發(fā)生的話語變遷相當敏感。她認為,上述編輯撰寫的原稿,仍然采用了“我們”這一先前播音員時代注重集體而淹沒個體的思維和話語特征,難以體現(xiàn)新時期改革開放與主體性再啟蒙背景下對個體、個性、人的尊重,特別是原稿仍然采用了“我們來幫助你們”這一“救世主”一般的全知全能、自上而下的恩賜意識,缺乏對觀眾的尊重、平等。于是沈力把這段話改成:
“我常有這樣的心情,每當看到別人寫字寫得很漂亮的時候,就很羨慕。我覺得字寫得好,不僅自己看著舒服,別人看著也是一種享受。在我收到的青年朋友們的來信中,很多人也表達了這種心情。他們說:很想練字,卻不知道怎么選帖。為了能使您練出一筆漂亮的字,我們特地來到了著名畫家和書法家董壽平先生的家里,請董老先生來給我們指導(dǎo)。”⑦
在沈力改動后的稿子中,主持人從“我們”變?yōu)椤拔摇薄耙詡€人身份”展開“獨立思考”和換位思考,以自己的切身體驗嘗試表現(xiàn)出親切、平等、主動、個性化、人格化的話語風格。更重要的是,主持人不是把自己和專家擺在一起,而是把自己和觀眾擺在一起,共同請專家來指導(dǎo)、學習。按照韋伯的觀點,所謂啟蒙,是一個“祛魅”過程,指的是西方社會在文藝復(fù)興前后,通過對神性至上與宗教世界主宰一切的否定與批判,從而達到對人性肯定與回歸以及世俗社會合法化。⑧沈力力圖避免先前播音員話語中某種程度上的“救世主”色彩,主持人話語中體現(xiàn)出的對人格獨立平等、個性自由發(fā)展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出1980年代從播音員到主持人的身份轉(zhuǎn)型與主體性話語建構(gòu)、啟蒙思考。
三、關(guān)系轉(zhuǎn)型與主體性話語建構(gòu)
在話語的建構(gòu)功能中,關(guān)系功能涉及話語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guān)系如何被制定和協(xié)商。1980年,與主持人這一身份確立相對應(yīng)的是,主持人與制作團隊之間的關(guān)系開始出現(xiàn)變化,主持人的主體性開始得到施展。主持人與觀眾的關(guān)系也開始出現(xiàn)變化,觀眾的主體性開始得到重視。這些變化在主持人的話語建構(gòu)中均有呈現(xiàn)。另外,“我”字的使用,也是主持人主體性的重要表征。
1.主持人與制作團隊、受眾的關(guān)系轉(zhuǎn)型
1980年以后,在主持人與制作團隊之間的關(guān)系制定與協(xié)商中,主持人開始表現(xiàn)出一定程度上的主體性。1980年以前特別是文革期間,在播音員與制作團隊的制定與協(xié)商中,播音員是比較被動的,播音員不能修改稿件,他們常常被要求逐字逐句、原封不動地播送編輯提供的稿件,很難有自己的思考、見解,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說話,常常被詬病為“話筒架子”“肉喇叭”。沈力認為:節(jié)目主持人,關(guān)鍵在“主持”二字上。從詞義上看,“主持”有“掌握”“處理”之義,而“掌握或處理”都含有一定的主動性。主持人在主持節(jié)目的過程中,需要有能力、有權(quán)力去掌握節(jié)目進程并處理相關(guān)事宜,需要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而不能只是照本宣科。主持人在節(jié)目中參與越多、滲透越多,作用就發(fā)揮越多,個性展現(xiàn)就越充分,獨到見解、觀點、態(tài)度和語言才能產(chǎn)生。⑨前文沈力修改編輯提供的稿子,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表達,正是主持人的主體性體現(xiàn)之一。
另外,觀眾的主體性開始得到重視,主持人和觀眾的關(guān)系也開始轉(zhuǎn)型。比如,沈力曾提及,先前播音員可能會照搬編輯提供的稿子說:“您懂得了膳食平衡的道理,就應(yīng)該舉一反三”,這里使用的“應(yīng)該”在語氣上比較生硬,有指令、教訓的意味。但是,主持人如果把“應(yīng)該舉一反三”改成“還可以舉一反三”就大為不同,“還可以”的語氣相對比較委婉,不是下達命令而是提供建議。再比如,先前的播音員可能會說“請您記住,以后再吃豆腐的時候,最好用肉炒。”雖然“請您記住”看似禮貌客氣,但是語氣仍然比較生硬且?guī)в兄噶钜馕丁H绻鞒秩税迅遄有薷臑椤澳院笤俪远垢瘯r,可別忘了放點肉”,語氣上更加親切、隨意、生活化,近似于朋友間的友好提醒。⑩不同于先前播音員與觀眾之間“我播你看”“我說你聽”,1980年代主持人話語中開始呈現(xiàn)對觀眾主體性的尊重,這也表明長期以來傳者與受者之間的俯瞰關(guān)系,開始逐漸向平視過渡。
2.“我”字的出現(xiàn)與主體性話語
1980年代節(jié)目主持人傳播的主體性與當時新啟蒙主義思潮中的主體性討論交相輝映,“我”字的出現(xiàn)是主體性的又一種呈現(xiàn)。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廣播推出《空中之友》節(jié)目,徐曼成為中國廣播史上第一位正式署名的主持人,第一期節(jié)目的開篇是:
“親愛的臺灣同胞,你們好!我姓徐,名曼。徐是雙人徐,曼是羅曼蒂克的曼。從我的名字,同胞們可以看出我是一個性格開朗的人。我喜歡到處有自己的朋友,我喜歡賓客聚會,在撲朔迷離的社會中,求取真理之光。今天我能有機會給諸位主持《空中之友》節(jié)目,真是感到榮幸。”
在過去兩岸關(guān)系及對臺政策的影響下,對臺廣播的話語常常是居高臨下、板著面孔、高八度、斗爭式、訓教式,很難獲得臺灣普通聽眾的好感。鄧穎超曾經(jīng)提出過不同的意見:“對臺廣播就要體現(xiàn)中國人的人情味。”1981年前后,《空中之友》提出“主持人以朋友態(tài)度”“為臺灣同胞解疑、解惑、解慮、解難”。在這樣的氛圍下,徐曼在對臺節(jié)目中語氣柔和、音色甜美,主持人話語中以第一人稱和主體意識,“采取商量的態(tài)度和探討的口吻,讓聽眾覺得是朋友之間的相互談心”。
“我”字的出現(xiàn)在中國廣播電視媒介中經(jīng)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很長時間以來,電子媒介是“階級斗爭的工具”。1980年代主持人話語中“我”字的出現(xiàn)被視為是由“媒介工具化”向“媒介人格化”的重要變革。“如今主持人每天在話筒前不知要說多少次‘我’,已經(jīng)習以為常;但是‘我’的出現(xiàn)卻是含義深遠,來之不易。不只是廣播電視學的一個課題,也是政治學、社會學的一個課題。從‘我’可以透視時代和社會。”雖然也有一些爭議,比如關(guān)于“我”字的濫用、個人意志如何與媒介意志和公眾意志協(xié)調(diào)等。但是1980年代主持人話語中,“我”字的出現(xiàn)殊為不易,其蘊含的主體性認識也難能可貴。作為傳者的主持人,不能只是“傳聲筒”“肉喇叭”,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而應(yīng)該是“主動的”“掌握或處理”“產(chǎn)生獨到的見解、觀點、態(tài)度和語言”,是具有“認識歷史”“能動地改造社會”“按照人的主觀意愿具有‘創(chuàng)造性’地、‘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實踐主體”和“精神主體”。
四、觀念轉(zhuǎn)型與主體性話語建構(gòu)
在話語的建構(gòu)功能中,觀念功能是指文本說明世界及其過程、實體和關(guān)系的途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電視傳播中更多傾向于正面宣傳、宏大敘事、解說與畫面分離,1980年代節(jié)目主持人的主體性開始萌發(fā),傳播觀念開始轉(zhuǎn)型,主持人話語中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出對理性化、世俗化、真實性的進一步追求。
1.從正面宣傳到理性化的輿論監(jiān)督
1980年代主持人話語中不再只重正面宣傳,開始出現(xiàn)輿論監(jiān)督和理性質(zhì)疑。首次出現(xiàn)“主持人”字樣的中央電視臺《觀察與思考》節(jié)目之所以受到贊揚和好評,其重要原因在于抓住民眾關(guān)注的一些敏感問題進行分析評介,并運用電視化語言加以呈現(xiàn)。另外,福建電視臺《新聞半小時》以揭露社會問題、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作用而受關(guān)注。1988年該欄目全年共播出334條批評性稿件,占總播出量45%。欄目聚焦敏感問題,包括某地干部合伙非法買賣土地,某縣拖欠民辦教師工資,某外貿(mào)倉庫進口物資長期積壓無人過問,某糧油公司倒賣化肥指標,某副縣長以權(quán)謀私、貪贓枉法,某地官僚主義使一般民事糾紛上升為殺人慘案等。節(jié)目主持人由責任編輯程鶴麟擔任,這種由責任編輯或總編輯兼任主持人的形式為后來的一些視頻新聞節(jié)目比如鳳凰資訊臺《總編輯時間》和財新網(wǎng)《舒立觀察》等欄目做出先探。
2.從宏大敘事到世俗化的民生話題
這一時期節(jié)目主持人話語中不再只重宏大敘事,開始出現(xiàn)更為世俗化的民生話題。中央電視臺《交流》欄目有一次聯(lián)系到了輕工業(yè)部部長,就當時人們最關(guān)心的話題“小學快開學了,輕工業(yè)部沒能提供足夠的紙,學生們沒有課本”進行現(xiàn)場提問,現(xiàn)場觀眾一提問,部長就得趕緊回答,“這樣一來穿靴戴帽就都沒用了”。節(jié)目結(jié)束時,主持人龐嘯說,這種交流是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歡迎各部委都來參與。上海電視臺《新聞透視》現(xiàn)場采訪搶購住房有獎儲蓄券的人們,引出住房制度改革的話題;透視交通管理不善、化妝品質(zhì)量低劣、公物被盜等現(xiàn)象;主持人李培紅在直升機上講述黃浦江上游民生引水一期工程竣工背后的故事等。盡管在早期節(jié)目中還留著明顯的時代痕跡,比如一些文革詞匯、高八度音調(diào)等等,但是節(jié)目關(guān)注民生話題及背后原因,這種質(zhì)樸與貼近讓人感到新鮮而親切。
3.從“聲畫兩張皮”到“我在場”的真實性追求
“我在場”的現(xiàn)場報道是區(qū)別于以往畫面解說兩張皮的觀念轉(zhuǎn)型,對真實性的探求隱約其中。在國際上,電視新聞現(xiàn)場報道創(chuàng)始于1960年代,其崛起與發(fā)展突破了電視新聞初創(chuàng)時現(xiàn)場畫面加后期解說的電影紀錄片式格局,開創(chuàng)了電視新聞現(xiàn)場報道的播報方式。在1980年代初期,山西電視臺新聞性述評節(jié)目《記者新觀察》中,主持人高麗萍大量采用現(xiàn)場報道,98%畫面有被采訪者出現(xiàn),并且采用現(xiàn)場同期聲,對教育、消費者權(quán)益、環(huán)境污染、廉政建設(shè)等問題進行分析評述。在一期節(jié)目中,她把自己置于日常生活場景,就“糧食搶購風”這一問題進行現(xiàn)場采訪、報道、述評,揭示其緣由及危害,并提出解決的途徑和應(yīng)吸取的教訓,對促進問題解決和社會穩(wěn)定起到一定的引導(dǎo)作用。這種蘊含著科學主義和真實性探求的“我在場”和“記者出圖像”的現(xiàn)場報道,為1990年代中后期香港回歸、澳門回歸、新千年到來等大型現(xiàn)場直播的到來和記者型主持人的出現(xiàn)做出準備和示范。
1980年代中國的節(jié)目主持人傳播觀念開始轉(zhuǎn)型,從正面宣傳到理性化的輿論監(jiān)督,從宏大敘事到世俗化的民生話題,從“聲畫兩張皮”到“我在場”的真實性追求,主持人話語中的主體性開始得到一些建構(gòu)。雖然這類新聞節(jié)目和主持人話語在理性質(zhì)疑的力度、范圍、級別上仍然有限,須經(jīng)上級批準且隨著形勢起起伏伏,世俗化的民生話題和“我在場”的真實性追求也仍然有限,但作為時代先驅(qū),他們?yōu)?990年代輿論監(jiān)督和民生新聞高潮的到來做出鋪墊,也為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等話題探討提供楔子。
五、局限與反思
正如哈貝馬斯所說,現(xiàn)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yè)”。與一些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廣播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的現(xiàn)代性探索包括主體性話語建構(gòu)在起點、階段和軌跡上有所不同,在內(nèi)容、價值訴求等方面也呈現(xiàn)出不同之處。
1.身份建構(gòu)不易,主體性有限
第一個出現(xiàn)“主持人”稱謂的新聞評論節(jié)目《觀察與思考》注重思想性、政策性和時新性,但由于公眾關(guān)心的許多“熱點”內(nèi)容還處于嚴格限制之列,“政治問題能否討論”的爭議尚未真正解決,《觀察與思考》也只能局限于為政策作注腳。1988年10月,已經(jīng)兩起兩落的《觀察與思考》第三次開播,改為《觀察思考》,肖曉琳成為固定節(jié)目主持人。在采、編、播、主持能力獲得一些獎項認可后,肖曉琳仍然堅持認為:“是的,我是幸運的。但我深知獲獎并不意味著自己就是一個出色的編導(dǎo)或是什么‘真正的’節(jié)目主持人了。我仍然主要對屏幕負責。”
主持人的身份建構(gòu)和主體性話語不可能超越體制及相關(guān)既定意志。即使是1990年代興起的具有突破性的《東方時空》這樣由相對獨立的制片人、巨額廣告收入、民間力量和國家意識形態(tài)機器共同促成的電視節(jié)目制作,一定程度上觸及了以往節(jié)目沒有觸及的社會內(nèi)容,并在影像語言、主持人風格上與以往大為不同。中國政治體制的結(jié)構(gòu)塑造了媒體發(fā)展,規(guī)定了它的基本功能。盡管一些文化產(chǎn)品對于拓展中國社會文化空間具有比較廣泛的意義,但是,由于它們一方面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空間,另一方面又是國家內(nèi)部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公共空間”并非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對獨立的調(diào)節(jié)力量,而是歷史形成的由國家的內(nèi)部空間和社會相互滲透的結(jié)果。
2.關(guān)系建構(gòu)不易,主體性受制
主持人白巖松曾反問:“過去很多事情我們不做,總抱怨環(huán)境不允許,但很多事情沒有做,障礙是不是因為自我限制?”在輿論監(jiān)督進程中,需要協(xié)調(diào)官方意志、媒介意志、民間意志等多方關(guān)系,確實會遇到邊界,這一邊界形成于各種不同關(guān)系和力量的互動中,并在不斷變化,而人們?nèi)绾涡袆邮切纬蛇@一邊界的要素之一。建設(shè)性的態(tài)度或許有益于對待輿論監(jiān)督的“能”與“不能”。在《觀察與思考》基礎(chǔ)上成長起來的1990年代的《焦點訪談》,部分實現(xiàn)或體現(xiàn)了黨/政府的意志、老百姓的心愿、媒體的利益三方關(guān)系的有機結(jié)合(即所謂的官意、民意、媒意三合為一),探索出協(xié)調(diào)三方關(guān)系的“輿論導(dǎo)向”方法,并獲得朱镕基等三任總理題詞。不過,如何將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的人格魅力和改革意向轉(zhuǎn)化成為制度性的實踐,并發(fā)展出一套實際可行的操作技術(shù),是中國新聞改革需要長期探索的一個任務(wù)。
另外,一些主持人被質(zhì)疑專業(yè)素質(zhì)和人文素養(yǎng)上存在欠缺,這成為影響其話語主體性建構(gòu)的一個因素。一些主持人被質(zhì)疑缺乏個性,而個性正是主體性的訴求之一。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主持人需要注意避免媒介尋租、政治投機。優(yōu)秀的節(jié)目主持人在能動地發(fā)揮主體性與價值判斷進行傳播時,需要將專業(yè)素養(yǎng)、政治素養(yǎng)、社會責任、價值取向融入到主持個性、語言風格、專業(yè)追求、事業(yè)品格中。
3.觀念建構(gòu)不易,主體性的歷史局限
西方文化的發(fā)展史表明,進入“主體—客體”的模式以后,曾經(jīng)理性批判、自由創(chuàng)造的“現(xiàn)代性”逐漸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性至上主義抹殺了人的意欲、情感、本能等重要方面,從而束縛了人的自由創(chuàng)造活動與批判活動的范圍;對科學的崇尚導(dǎo)致現(xiàn)當代知識的信息化、網(wǎng)絡(luò)化、媒體化,真理、知識與外在的權(quán)力相結(jié)合,常常喪失了應(yīng)有的客觀性標準,使得真理變成了非真理,知識變成了非知識。“主體性”本來是講的自由和獨立自主性,然而“主體性”走向極端成為人類中心主義,試圖極端征服自然反而抹殺“主體性”并為自然所奴役。尼采、海德格爾、福柯等相繼批判了“主體性哲學”,福柯明確宣稱“不相信”“具有普遍形式的”“獨立自主的”“主體”。
就1980年代中國的節(jié)目主持人傳播而言,由于當時處于改革開放與國家重啟現(xiàn)代化初期,尚未出現(xiàn)顯著的“現(xiàn)代化陷阱”以及現(xiàn)代性局限,但是隨著商品化、市場化、資本化、社會矛盾以及國家改革包括新聞改革的復(fù)雜性加劇,中國的節(jié)目主持人傳播在主體性探索中的問題弊端也會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在中國當代節(jié)目主持人傳播的第一個十年,具有相當權(quán)威、公信的主持人特別是新聞節(jié)目主持人尚未出現(xiàn)。同時,和當時的國家改革、傳媒改革一樣,主持人傳播中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并且一些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未能解決。但是,和改革熱情澎湃、思想英姿勃發(fā)的1980年代一樣,這一傳播現(xiàn)象讓人想念的同時,更需要客觀看待、可持續(xù)發(fā)展。畢竟,這一傳播現(xiàn)象是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fā)展、傳媒發(fā)展同時進行、利弊共擔的,沒有也不可能脫離時代。
應(yīng)該說,改革開放初期主持人話語的主體性建構(gòu)有一定意義,是區(qū)別于先前播音員傳播的破冰之舉,是改革開放在新聞改革領(lǐng)域的一項新舉措,為下一個十年即1990年代主持人傳播大發(fā)展以及隨后更長的未來做出重要鋪墊,為廣播電視人格化、輿論監(jiān)督和民生話語、直播常態(tài)化等高潮的到來預(yù)演了前奏,對于發(fā)揮廣播電視媒介的現(xiàn)實影響、推動廣播電視傳播走向現(xiàn)代化起著重要作用。
注釋:
① 童兵:《主體與喉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頁。
② [英]諾曼·費爾克拉夫:《話語與社會變遷》,殷曉蓉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頁。
③ 李澤厚:《康德哲學和建立主體性論綱》,載《論康德黑格爾哲學——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頁。
④ 陳一鳴等:《三個電視人的十年》,《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0日,第12版。
⑤⑨⑩ 沈力:《我怎樣當節(jié)目主持人》,《當代電視》,1987年第3期。
⑥⑦ 沈力:《四十年探尋》,載《中國熒屏第一人——沈力》,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4頁。
⑧ 劉正偉:《現(xiàn)代性:語文教育的百年價值訴求》,《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