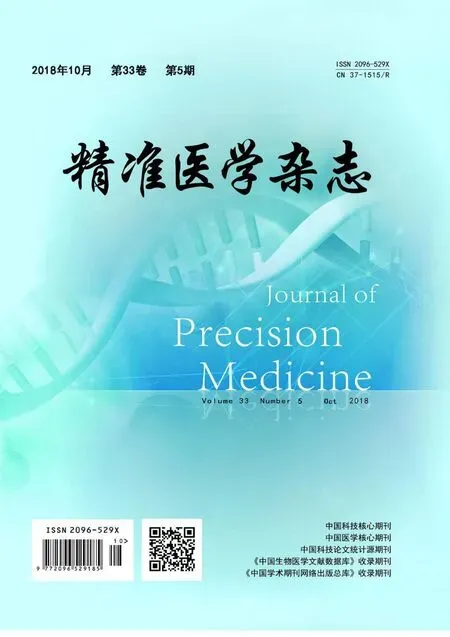非小細胞肺癌基因突變與影像特征相關性的研究進展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PET/CT中心,山東 青島 266021)
隨著分子病理技術的進步,基因突變檢測成為非小細胞肺癌臨床常規診斷手段,基于基因檢測的分子靶向治療也逐漸成為非小細胞肺癌治療的有效方法之一。傳統基因檢測會對病人產生創傷并且存在假陰性可能,因此探討非小細胞肺癌基因突變與影像特征的相關性成為當前熱門的研究方向之一。本文將非小細胞肺癌不同基因突變型與各種影像學征象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綜述,以了解研究的現狀。
1 檢測非小細胞肺癌基因狀態的意義
如今臨床上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GFR-TKI)已被廣泛用作EGFR基因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的一線、二線或輔助治療藥物,但野生型肺癌病灶對此類藥物極不敏感[1]。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突變是在非小細胞肺癌中較為常見的另一種基因突變型,CUI等[2]認為無論作為一線還是二線治療藥物,克唑替尼均可以顯著延長非小細胞肺癌病人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PFS)。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基因突變為除EGFR基因突變之外最容易發生的突變型,約占所有類型腫瘤基因突變的30%,在Ⅱ期臨床試驗中,司美替尼與多西環素聯合治療能顯著延長伴有KRAS基因突變的晚期肺癌病人的客觀緩解率、PFS以及總生存期[3]。可見基因突變的檢測對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具有重要價值。目前,組織學活檢是檢測基因狀態的最主要方法,但其具有創傷性,并且有可能產生假陰性結果[4]。腫瘤基因型的改變會影響腫瘤病灶的組織形態及生物學特征,形態學及生物特征的異質性為影像學表現的基礎,此為探討基因突變與影像學特征之間的相關性提供了可能性。
2 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與影像學征象的相關性
2.1 EGFR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形態學影像特征
現階段,國內外對于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與CT形態特征的相關性研究并未達成共識。在多數研究中,EGFR基因突變型及野生型非小細胞肺癌中磨玻璃密度病灶的發生概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LIU等[5]及HASEGAWA等[6]均認為磨玻璃密度結節(GGO)較常見于EGFR基因突變型的非小細胞肺癌。HSU等[7]對162例Ⅰ期肺腺癌研究發現,在EGFR基因突變型中,相較于單純磨玻璃樣結節,部分GGO更加常見,尤其是在L858R外顯子突變的病灶中。ZOU等[8]的研究認為,只有GGO可作為預測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的獨立CT征象,其他的征象均無統計學意義,并且純GGO或含磨玻璃密度的混合密度結節比實性結節更常見于EGFR基因突變型的病灶之中,尤其是磨玻璃密度面積構成比>0而≤50%的病灶。
腫瘤的大小作為描述病灶最基本的特征,也是預測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的重要指標。LIU等[5]針對亞洲人群中385例手術切除的肺腺癌進行的研究顯示,EGFR基因突變型腫瘤病灶常小于野生型。相關研究表明,野生型比EGFR基因突變型腫瘤體積更大,并且發現21外顯子位點突變的腫瘤病灶體積通常大于19外顯子位點突變的腫瘤病灶[9-10]。
除密度、大小之外,腫瘤的內部特征、界面特征及瘤周征象也具有一定的預測意義,但研究結論目前尚不一致,存在較大爭議。HASEGAWA等[6]研究顯示,分葉征是預測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型的主要界面特征。HSU等[9]的研究結果表明,野生型非小細胞肺癌的生長形態更加不規則,并且相比EGFR基因突變型,腫瘤病灶內部更容易發生鈣化。LIU等[5]則認為EGFR基因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腫瘤邊界更常見到毛刺征象。在對腫瘤內部特征的研究中,RIZZO等[10]及LIU等[5]均認為支氣管充氣征與EGFR基因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病灶密切相關,LIU等[5]還認為空泡征更經常見于EGFR基因突變型肺腫瘤病灶,但在HASEGAWA等[6]的研究結果中,空洞則多見于野生型肺癌病灶。如血管連接征、胸膜凹陷征等瘤周征象一直以來都作為診斷肺腫瘤良惡性的標準之一,在預測非小細胞肺癌腫瘤基因的突變時也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LIU等[5]及RIZZO等[10]研究發現,EGFR基因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較常出現血管集束征及胸膜凹陷征,HASEGAWA等[6]還認為基因突變與肺癌的肺內轉移密切相關,并且野生型非小細胞肺癌更容易發生胸腔積液。
然而,部分學者的研究與以上研究結論相反,如GLYNN等[11]認為沒有任何CT征象可以預測非小細胞肺癌的EGFR基因突變,在該研究中所有CT特征在預測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時差異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
2.2 EGFR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的代謝特征
GUAN等[12]的研究結果表明,EGFR基因突變型的非小細胞肺癌病灶的SUVmax低于野生型,ROC曲線的臨界值為8.1,預測模型的總體準確度、靈敏度以及特異度分別為77.6%、64.6%和82.5%。TAKAMOCHI等[13]也認為EGFR基因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病灶的SUVmax低于野生型,該研究中ROC曲線的SUVmax臨界值為2.69,診斷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60%及61%。LV等[14]研究發現EGFR基因突變與肺內原發病灶SUVmax、轉移淋巴結SUVmax及遠處轉移灶SUVmax較低相關,研究認為肺內原發病灶SUVmax<7.0可以預測基因突變。HUANG等[15]的研究結果則與以上結果相反,其對未經治療的ⅢB、Ⅳ期肺癌病人進行了單因素以及多因素分析,研究結果表明EGFR基因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病灶相比野生型18F-FDG攝取值更高,SUVmax臨界值為9.5。
除SUVmax之外,腫瘤代謝體積(MTV)以及腫瘤糖酵解總量(TLG)已經逐漸作為檢測腫瘤代謝活性的比較常用指標。MINAMIMOTO等[16]認為,僅SUVmax可以作為預測非小細胞肺癌腫瘤基因突變的相關因素,MTV以及TLG均與之無關。李天女等[17]則認為TLG可作為預測非小細胞肺癌腫瘤病灶EGFR基因突變的獨立因素,SUVmax、MTV以及TLG預測基因突變的最佳臨界值分別為7.99、6.09 cm3和35.08 g。LIU等[18]也研究了MTV與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之間關系,多因素分析表明,低MTV(≤11.0 m3)的無吸煙史病人,其生長于周圍肺野的腫瘤更易發生EGFR基因突變。
然而,部分研究表明,SUVmax不能作為預測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的獨立因素,不具備預測基因突變的統計學意義。通過多因素分析,LEE等[19]認為只有性別、吸煙史、組織學分型及腫瘤大小可以納入預測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的標準,盡管基因突變型與野生型的SUVmax攝取值在單因素分析中存在差異性,但在多因素分析中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SUVmax之間的差異主要取決于腫瘤組織學分型及吸煙史,而不是基因突變本身。
2.3 影像組學的應用
近年來,許多研究對腫瘤病灶提取大量的影像學信息,建立數學模型,運用影像組學的方式來獲得更為精準的腫瘤預測征象。LIU等[20]對298例手術切除的周圍性肺腺癌進行分析,每個腫瘤提取了219個3D征象,其中CT衰減能量、腫瘤主要生長方向、小波和定律規定的紋理可作為預測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的組學征象。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表明,在臨床模型中增加影像組學特征可以提高預測的效能,使AUC從0.667提高到0.709。OZKAN等[21]分析了對比度、相關、逆差距、二階距以及熵5個CT灰度紋理特征,其中二階距和熵在EGFR基因突變型及野生型非小細胞肺癌中的差別無統計學意義,19位點突變逆差距小于21位點突變。YIP等[22]應用PET相關影像組學分析了21種影像學征象,包括19種獨立組學征象和2種傳統PET影像學征象(MTV和SUVmax),認為其中的8種組學征象和2種傳統征象對非小細胞肺癌EGFR基因突變具有預測價值(AUC=0.590~0.670)。
3 非小細胞肺癌ALK基因突變與影像學征象的相關性
現階段,對非小細胞肺癌ALK基因重排與CT征象之間相關性的研究尚處于初期階段,研究結論多樣。ZHOU等[23]研究了346例肺腺癌病人,認為相較于野生型病灶,單純GGO較少見于ALK基因突變型,并且其腫瘤陰影消失率(TDR)也比較低。PARK等[24]認為ALK基因突變型的肺腫瘤體積較小,且多數為實性結節。YAMAMOTO等[25]構建了非小細胞肺癌ALK基因突變預測模型,預測因素包括腫瘤位于中心位置、缺乏胸膜尾征、大量胸水及病人年齡小于60歲,診斷的靈敏度、特異度及準確度分別為83.3%、77.9%、78.8%,他們同時對肺腫瘤CT征象與預后進行了相關性分析,認為腫瘤病灶周邊血管紊亂預示著克唑替尼治療預后不良。
WANG等[26]認為腫瘤直徑>5 cm以及N2、N3期的淋巴結轉移更常見于ALK基因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而空泡征及GGO較少見,并且ALK基因突變型肺癌病灶的TDR更低。CHOI等[27]通過多因素回歸分析顯示,分葉、N2或N3期淋巴結侵犯和通過淋巴管肺轉移更常見于ALK基因突變型的非小細胞肺癌。HALPENNY等[28]認為,ALK基因突變型的非小細胞肺癌更易發生多中心的淋巴結轉移。KIM等[29]研究了497例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多因素分析表明年輕病人、實性病灶、邊緣分葉及增強CT明顯強化是預測腫瘤病灶發生ALK基因突變的獨立因素。
目前對于非小細胞肺癌18F-FDG PET/CT征象與ALK基因突變關系的研究較少。LV等[14]針對849例中國人開展的回顧性研究中,發生于ALK基因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轉移淋巴結SUVmax較高,但在多因素分析中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PUTORA等[30]則認為ALK基因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原發病灶平均SUVmax遠高于野生型及EGFR基因突變型,并且腫瘤病灶多為中心性生長。CHOI等[31]分析了331例非小細胞肺癌病人,也認為ALK基因突變型SUVmax較高,且更易向淋巴結及遠處轉移,尤其是中等大小的病灶。
4 非小細胞肺癌KRAS基因突變與影像學征象相關性
KRAS是除EGFR之外最容易發生突變的基因,然而目前KRAS基因突變的研究多針對大腸癌,關于肺癌KRAS基因突變與影像學征象的研究較少,且結論不一。RIZZO等[10]研究認為KRAS基因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病灶多為圓形,并且在非原發腫瘤肺葉可見多發轉移結節。SUGANO等[32]的研究結果顯示,KRAS基因突變容易發于腫瘤直徑≥31 mm的非小細胞肺癌病灶,空洞、GGO和磨玻璃密度面積百分比(G/T)在KRAS基因突變型與野生型病灶中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CAICEDO等[33]針對340例Ⅲ、Ⅳ期肺癌病人進行研究,KRAS基因突變病人相比EGFR基因突變和野生型病人18F-FDG攝取值更高,應用年齡、性別、AJCC分級和SUVmean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診斷的靈敏度以及特異度分別為78.6%和62.2%。MINAMIMOTO等[16]則持有不同的看法,認為任何PET參數都不能預測非小細胞肺癌KRAS基因突變,而吸煙可以作為預測基因突變型的獨立因素。
5 展望
總之,非小細胞肺癌基因突變與影像學征象相關性的研究較多,但結論不一。將腫瘤分子生物學特征與影像特征相關聯,使研究從微觀到宏觀,為腫瘤的精準診斷與治療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與研究方向。另外,除EGFR、ALK及KRAS基因突變之外,ROS1、C-MET、BRAF等基因突變也可發生于非小細胞肺癌中,但因其發生概率小,病例數目較少,目前國內外尚未發表關于以上基因突變與影像學征象相關性的研究,這為將來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