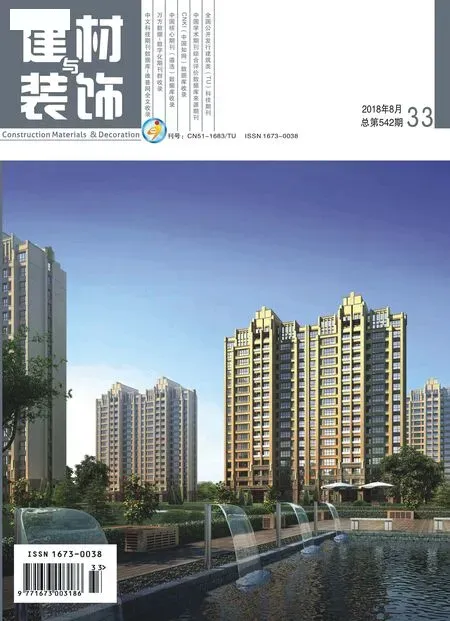卡洛·斯卡帕的建筑藝術世界
——構建記憶多重性
陳素素 林杰海
(溫州設計集團有限公司 浙江溫州 325000)
卡洛·斯卡帕(1906~1978)在意大利建筑界是絕對的殿堂級人物。斯卡帕沒有專業的建筑學位,早期不能獨立實踐,稍晚又被稱為裝飾教授,更被人認為是藝術家而非建筑師,或許這都促成了他的特立獨行。1926年取得威尼斯美術學院建筑設計教授資格,此后到1976年,一直在該校教授學生如何使用傳統材料、發覺手工制作的力量以及建筑史。哥倫比亞大學建筑史學家K.Fampton說斯卡帕的建筑史20世紀的分水嶺。尤其是其以蒙太奇手法組合多重元素的語法與實驗更是獨樹一格。斯卡帕建筑的多重性是與他的生活經歷緊密相連的。這種多重記憶既有藝術美,同時具有歷史感。
1 生活的記憶
1906年他出生在威尼斯,父親是名中學教師,母親是個裁縫。縫紉,由于它精確的剪裁和“蒙太奇”般的拼貼,是一種手工藝術作品的最初范例。童年的印象體現在斯卡帕在威尼斯雙年展杜魯茲·羅特列克畫展上,由幕布界定的空間單元,極具形式美。在威尼斯美術學院學習期間,斯卡帕接觸到新藝術運動。并在早期學得傳統威尼斯手工藝,尤以玻璃制品聞名。賴特在有次去威尼斯購得一批玻璃藝術品,后來發現竟然是出自斯卡帕之手。玻璃制作工藝的經歷為斯卡帕形成了敏銳的材料感。
斯卡帕一直以來追求建筑的一種真實,這種真實來源于自然,而自然萬物都由光來呈現,這種體驗在威尼斯,這個具有東方風情、水上漂浮的城市,尤其突出,波光粼粼的威尼斯在他記憶深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2 藝術實踐的記憶
早年,卡洛·斯卡帕就讀于威尼斯美術大學,受到古典主義熏陶,活躍在藝術家、批評家組成的圈子里。這使得他的建筑創作始終帶著濃重的藝術化色彩。在1948~1972年的跨度之間,斯卡帕多次參與了威尼斯雙年展的組織和設計。策展經歷也沉淀了斯卡帕深厚的藝術品位。斯卡帕通過他的展示設計獲取了很多建筑經驗,也逐漸的更新設計手法。他也從這些藝術大師中吸取養分,營養于自己的建筑實驗。這些大師中有塞尚、保羅·克利、蒙德里安、賴特。
3 保羅·克利與斯卡帕
3.1 對死亡的樂觀認知
保羅·克利與斯卡帕對待死亡的認知表現上存在著某種共識。克利在給朋友的信中寫到:“我并不是偶然地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我所有的作品都指向一點,并且宣稱,終期將至了。”因為有對人生、死亡的深刻理解,所以畫家從容面對,并且不失理智以及對生命最后的戲謔和幽默。
布瑞恩家族墓園的設計,斯卡帕最初的設計觀點便是創造一個綠茵遍布的花園。“我感到我要追求一個鄉村情感,就像布里諾斯所期待一樣。每一個人都會很快樂的到這里;小孩在此游玩,小狗跑來跑去。所有的墓園都應該像這樣。”而斯卡帕對波特萊爾的喜愛,也說明了他對愉悅的死亡以及憂傷下的身體抽搐暗示的有微妙的生理韻律正在醞釀。他總是提出與反向思考。這是斯卡帕對模式化墓園空間情緒和形態的雙重否定,他在設計中嘗試以全新的空間來創造墓園的新體驗,并希望為死者建造一個天堂的花園;不僅對逝者,而且為生者提供一個屬于公共的場所,大家可以在此追憶和冥想。使墓園成為“寄哀悼于沉思,化沉思于愉悅”的詩意場所。
3.2 抽象表現手法促成神秘性
克利稱自己為“線條”畫家。在主題抽象化和形象單純化的過程中,他把線條作為引領畫面的重要因素,這些線條就像音樂中的主旋律一樣貫穿于畫面。他的素描有著由自由組合、對立、搖擺和決裂組成的韻律,從而不斷向人提出詢問,賦予作品多重涵義。《通往帕納斯山》是克利的巔峰之作。它運用了點彩派的技法,色調輕松柔和,密集的小色塊增強了色彩的光感。這種閃爍不定的光感和撲朔迷離的視覺效果,正如斯卡帕在都柏林藝術展上的對于“色彩的感覺與水的主宰”的詮釋。此時的光影是夢幻的,又如此真實,自然光、環境光、燈光、水光共同譜寫著光之樂章。
“當我發現一個東西,而覺得它們是什么時,我就會將它擦去。”斯卡帕反對擬真并非說明他反對自然,而是說創作的呈現所依賴的是換語及對位的手法。這就是為什么在斯卡帕的作品中充滿著詩意,觀者可以從中讀出不同的解讀。而斯卡帕為達到這種多重性解讀就需運用一系列抽象母題:5.5和11模數、雙圓、T字型、鋸齒線腳。
(1)斯卡帕反復運用5.5×5.5位模數的線腳,這個母題不斷變換著位置與形態。對于11形態的由來,對柱也是11的體現:斯卡帕在自己多個建筑上使用過結構性或者非支撐性的對柱。以及斯卡帕在家具設計中“11”作為結構性裝飾的多次運用。
(2)T字型紋飾雕帶:斯卡帕在加里墓上使用了T字開口。那是因為T字來自希臘字母Tau,是古代基督徒用來表征通過耶穌得到永生的標記(Salazar)。T字在墓上形成了一個底座,上面的圖案,按照Norber-Schultz的說法,代表著天地宇宙樹形象。
(3)雙心圓的母題:這一形象,最初源于自于升起或落下的太陽的跳動的某種分解,或是對于雞蛋的有機分解,就像克利(PaulKlee)研究過的那樣,也是源自斯卡帕常期堅持的在圖形形式內部盡量避免在保持形式組成可讀性的點上進行交接和接縫的概念。例如,“兩個形式疊加時”不要把拱遭遇壁柱的部分切掉,交接的地方應該在這個點的上面或是下面,這樣,構造和形象的幾何感就會得到優雅和辯證的并置。對于雙心圓,斯卡帕曾說,代表著一種婚禮的習俗——在意大利的文化中,婚禮上新娘和新郎的戒指是套合在一起的以示結合;代表著圣母和圣者頭上的橢圓光環:表示出這是一塊神圣的領地;代表著女性的生殖器——生命的來源(這種設計思考同杜尚的作品給予所表達的含義和畫面構成驚人相似);代表著圖示意義中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膀胱魚的幾何圖式。
4 蒙德里安與斯卡帕
風格派對于包豪斯以及廣義的現代建筑運動都產生過重要而持久的影響。斯卡帕也很快從風格派畫家以及建筑師那里學來了一些很具體的設計手法。諸如,怎樣將傳統的盒子消解成為一個個相互成直角穿插的片——其奧秘就在轉角的切口和墻與屋面的分離上;怎樣像蒙德里安那樣,在一面實墻上用非古典、非對稱、非等級化的構圖開口子;怎樣用不同的肌理或色彩的小方塊磚,進行自由組合,砌出沒有靜態平衡感的墻面或地面;怎樣將鋸齒形的凹槽線腳切出風格派一般的韻律和節奏……斯卡帕在1978年夏的馬德里演講中,提及布瑞恩墓地的大門形式及來源于蒙德里安式構圖。
5 藝術家式的工作方式
斯卡帕創作方式與畫家相似。他的畫讓我們感受到他的意圖,是他思想的直接而真摯的反映。“我想理解,所以我要畫”,斯卡帕對待繪畫是一種思考的過程,而不是思考的結果,所以我們看不到他的建筑最終效果圖,看到的都是布滿思考痕跡、反復疊加的線條。斯卡帕的建筑可以無限深入下去,他對細節的推敲是無止盡的。他晚期的銀行設計,當他拿到這個項目時,很快就定了初步的方案,但由于對細節的苛刻,直到他去世設計還沒完工。
“上帝存在于細部之中”是斯卡帕的創作宣言。斯卡帕的對細節的追求并不是以繁為美,而是對材料的極致運用,這種細節是結構的美學的需求,是構成詩意的辭藻。如康與卒姆托都曾表達要呈現建筑材料本身想呈現的樣子。在這點上,我認為博塔并沒有超越他的老師斯卡帕,盡管能從博塔的建筑中能看出斯卡帕對其建筑審美有著很深的影響,如條形重復線型的運用,但相較其老師他的裝飾更多的是肌理的表達,而非結構的詩學表達。
6 歷史與未來的記憶
我們不能否定歷史,抹去歷史就是抹去自身的存在。歷史與未來是辯證的關系。
斯卡帕對來自過去走向未來的建筑物擁有一種更加深刻的解讀。他的建筑物材料總是可以保留時間的痕跡,老化和風化。從他的建筑中,我們能讀出時間的痕跡,穿越過去,看向未來。斯卡帕對傳統建筑和新建筑的處理方式是并置。這就如他不斷出現的母題“雙圓”一樣,這種“辯證的并置”是他對于新與舊的態度。
斯卡帕的建筑體現了路斯的理論,其建筑立面往往與傳統、環境相和諧,內部空間豐富。人們往往只能從畫冊,網絡來獲得斯卡帕建筑的局部認知,可能覺得瑣碎繁冗,但真正體驗過斯卡帕建筑的人永遠不會失望。因為斯卡帕的建筑不失無用表面的裝飾,而是深層的裝飾,是建筑結構上的裝飾,這種裝飾突出了構造的美學。而不是現代主義往往隱藏建筑節點。這解決了將豐富多變的空間內容裝入一個簡單的形體之內,在保持空間經歷多樣性的同時又不失一種統一感。斯卡帕在維諾那公共銀行(Banca Popolare di Verona)的立面處理,特意保留了時間的記憶。一版圓形孔洞下方因為雨水長時間留下了多少會形成水漬紋。或水漬紋代表著環境因素刻蝕在建筑表面上一直是西方建筑思考的重點之一,斯卡帕排水道立面處理方式輕微的誘發人們閱讀時光的意義,而一到可以被稱為純功能性的水道成了隱藏多元意義的完美線腳。而室內的節奏與室外立面是兩種不同的節奏,室外為了符合歷史文脈,處理上是斯卡帕式的詩意莊重,室內則是風格派的輕松明快。
7 日本建筑對斯卡帕的影響
“我是一位經由希臘來到威尼斯的拜占庭人”
在卡洛·斯卡帕的建筑中有類似日本庭院和合式建筑的影響。斯卡帕對日本建筑的喜愛,源于日本建筑與其建筑哲學的相似性:材料相互之間的精確組合、建筑與自然完美融合。以及他所崇拜的建筑師賴特的日本情結。布里諾墓園小教堂公寓中那兩扇看似日本棉紙窗的門,都是來自威尼斯傳統工藝“染色灰泥”,這個呈現光線條的皮層,也隱現了威尼斯的立面特征。在去向世界最東方的途中,也成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
以上的多重記憶,斯卡帕在1958-1964年間對維羅納的Castelvecchio博物館的改造對齊進行了全面的詮釋。斯卡帕用這樣的疊加使得這棟建筑能夠反射它自己的歷史,突出在時間中發生在身上的改變。
他寫道:“我想到了水體曾經環繞過古堡的外墻。這個事實讓我想到設計一種‘凹縫’”的主意。我將每個房間里的地面都進行過單獨的設計,仿佛它們都是一系列的高臺,我變化著這些臺子邊緣的材料,從石板條到一種更加輕快的石頭,為的是更好地限定方形。這樣,流動就有了模度”。這棟建筑物不止是物質地將參觀者領向這里歷史上重要的場所,它還引導著觀眾參觀展覽,去關注那些特殊的展品。有時,有些援引會用到別處或是別的什么間接性的記憶:比如,諸多的內部墻體上面都覆蓋著抹灰的板,它們會讓人想到威尼斯地區的微光處理的抹灰工藝,而這里的玻璃上,則被斯卡帕加上了類似蒙德里安繪畫上的格子。二樓的天花處理則類似于日本人的榻榻米模度。還有,下到環道盡頭處的一塊塊分開來的雙步石,很顯然是受到了日本傳統的影響。對于常規材料和形式的選擇,以及聯想的組織,都將這個博物館整合到了一種區域性的以及更加寬廣的文化背景之中,吸引著更多的參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