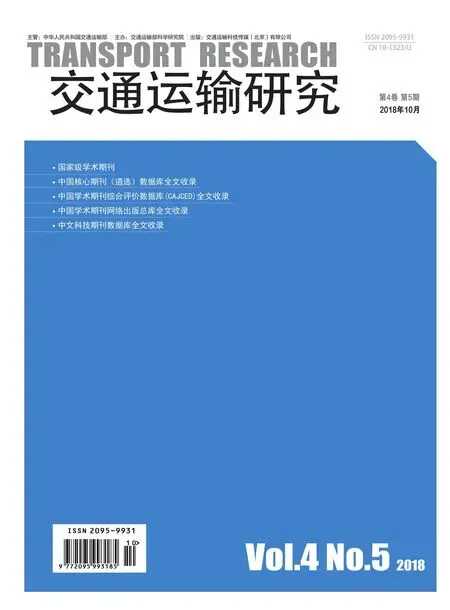概覽歷史上重大交通方略對中國發展進程的影響及啟示
張 毅
(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29)
0 引言
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交通強國”[1]開啟了建設交通強國的新征程[2]。交通運輸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先導性產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先行官”。人類文明發展的每一歷史階段,都可以看到交通進步的軌跡,反之交通進步也推動著實現文化融合、區域交往、經濟發展、國家統一。《史記》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的記載。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了持續而艱難的努力。
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踏上新征程的時代起點,回顧歷史上多次重大的交通發展標志性工程,其發展歷程宏偉、艱辛、曲折。本文擬從戰略層面分析交通對中國發展進程產生的深遠影響,探求交通與國家興衰的內在聯系規律,研究交通對國民經濟、人類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進而科學研判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中交通業的新方位和新任務,為新時代奮力“建設為交通強國”提供借鑒與啟示。
1 我國歷史上交通方略概覽
1.1 秦實現“大一統”,依交通立國
秦朝首次實現了中華大地名副其實的統一局面[3],這種統一廣泛地深入到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政令的及時下達、政權的有力鞏固、文化的廣泛融合均需要依靠與之相應的交通格局。
1.1.1 秦形成了聯絡全國、規模龐大的交通體系
秦朝在對先朝交通路線整修和連接的基礎上,以咸陽為中心,向四方輻射,修筑了以“馳道”為主的全國交通干線,以“直道”為主的軍事高速公路,開辟了面向南方以“五尺道”為代表的聯絡線,形成了通達全國的交通網絡[4-6]。
(1)干線公路秦馳道
《漢書·賈山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西方世界有“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諺語,古羅馬道路里程約6000公里。秦馳道的里程雖然沒有明確的統計,據史料和考古學界推算約有6000~7000公里[3],基本實現了“條條大路通咸陽”。
(2)軍事專用道——秦直道
為軍事用途,于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秦大將蒙恬征調軍民數十萬,用僅僅兩年多的時間,修建了相當于軍事高速公路的秦直道[7]。秦直道北起內蒙九原南抵都城咸陽,全長1000公里,這一歷史罕見的工程無論是工程規模還是實際作用都堪比長城。
(3)“五尺道”等聯絡線
秦為將長城防區貫通,建“北邊道”;為征服西南夷,修治“五尺道”,得巴蜀滇貴;為遏止嶺南,修建“新道”穿越五嶺,平定了南越。
秦朝歷時雖短,但其交通建設格局意義重大,奠定了面向中國“大一統”的交通空間格局。
1.1.2 秦統一度量衡,建立了“標準化”的交通規制
秦實施“書同文,車同軌”。明確車輛軌距標準,使更大范圍內交通往來通聯成為可能,適應了軍事工程的需要。在道路修建方面,秦實施了因地制宜的道路修建標準。《漢書》記載,秦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8],可見對道路寬度、路基設置、綠化都有相應的標準。統一的交通標準與統一的文字、統一的度量衡標準同樣重要,在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統一,對于中華文明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功績。
1.1.3 “示疆威,服海內”促進形成大一統的中國
從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依托“馳道”、渭河及黃河河道,先后五次巡視。足跡所至,北到今天的秦皇島,南到江浙、湖北、湖南地區,東到山東沿海,并在鄒嶧山、泰山、芝罘山、瑯邪、會稽、碣石等地留下刻石[9],以宣揚主權、表彰其功德。
秦將發展交通作為主要行政任務之一,交通事業在該時期有了巨大的進步。漢在秦的基礎上不斷夯實,主要交通規制在漢代得以鞏固延續,為后世交通的發展奠定了基本格局[10]。秦代建立強大的交通系統初衷是軍事上的征服與統一,但從歷史長河來看,其更大的實際性作用是技術傳播、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應該說“中國”概念的產生,尤其是統一的、被廣泛認同的“中國”概念的產生離不開發達的交通格局,離不開秦“交通立國”舉措。交通對于中國國家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1.2 漢、唐“絲綢之路”,依交通興國
自公元前2世紀中葉西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后,開通了由長安(今西安)經河西走廊沿著戈壁荒漠的邊緣,穿越西北邊疆地區,直抵中亞、西亞的馬爾罕、波斯和敘利亞[10]的商道“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暢通使中西政治、經濟、文化全方面的聯系得以實現。
1.2.1 “絲綢之路”與“草原之路”
遠在戰國時代,古希臘已經稱中國為塞利斯(Seres),意為“絲綢之國”,說明在當時東、西方兩個文明已存在實質性溝通。事實上,在漢張騫通西域之前,中國北方已存在著一條途經蒙古草原溝通歐亞的天然大道,那就是“草原之路”[7,11,12]。“草原之路”雖然更早,但與漢唐時代繁榮的“絲綢之路”有著本質區別,其作用和影響力也不可同日而語,采取不同的交通策略是形成差別的主因。
漢唐“絲綢之路”是固定線路,其沿線有驛站、集市等設施,并設立了相應的軍事郡縣行政機構。北方民族早期的“草原之路”雖然能夠實現溝通,但由于不是固定線路、沒有標志性節點,從而沒有形成經常性的商貿通道。可見“絲綢之路”并不是簡單的通達,它的諸多創舉有深層次的必然原因。
1.2.2 “絲綢之路”的重要創舉
漢至中唐歷代王朝采取了系列措施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使得絲路貿易興盛近一千余年。
(1)強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采取實用的運輸模式
絲綢之路穿越西北邊疆地區戈壁荒漠,一路并非坦途。漢、唐兩朝為推動絲綢之路的發展,注重道路及沿途驛站興建。早在西漢武帝時即沿絲綢之路修筑長城,設立亭障;東漢在絲綢之路要沖設立了不少郵亭;唐代興修驛道、驛館。絲綢之路沿線的基礎設施,發揮了保障安全、提供食宿便利、通郵、傳遞信息的作用,功能逐步完備。據考證,僅從長安到敦煌的驛館至少有40余座[12]。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在《驛館使壁記》中稱“館驛之制,于千里之內尤重”。這些驛站作為長途跋涉路線的補給節點,配合“沙漠之舟”駱駝形成非常實用的運輸模式。基礎設施的興建與實用的運輸模式,終使陸路絲綢之路保持暢達。
(2)強大的軍事、開放的民族政策、低廉的稅賦保障“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達
一方面,強大的軍事與開放包容的文化保障絲綢之路的交通暢達。漢、唐均在解除了北方匈奴勢力的安全威脅之后,在西北部絲路沿線設立相應的軍事機構,開展邊疆地區的政權建設。唐朝實行了非常開放的統治政策,尊重民族習俗和宗教信仰,同時許可胡人往來、定居中原,客觀上促進了民族融合,邊疆民族逐步融入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從軍事、文化兩方面穩固邊疆,有效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達。
另一方面,實施開放包容的稅賦政策。唐朝有專門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的律令,曾有地方官員因敲詐外商受到重刑[13]。公元834年,唐文宗頒布諭令“除舶腳(船舶稅)、收市 (政府購買)、進奉 (進貢)外,任其往來通流,不得重加率稅”,明確規定禁止重征外商,營造了平等、祥和的商貿氛圍。
(3)“絲綢之路”供給保障與商貿發展形成了良性互動
絲綢之路促進了周邊的經貿繁榮,沿線的發展也為絲綢之路提供了物質基礎。絲路沿線節點性驛站,逐步發展為貿易市場乃至城市。自漢起已在從前沿線的驛站、商貿之所設立行政管轄,絲路上的節點城市得到了極大的發展[14]。唐代在都市設立專門的接待外國貢使和商人的賓館及中外交易市場。漢唐時期來華外商除了云集于長安、洛陽之外,在天水、蘭州、武威、金昌、張掖、酒泉、嘉峪關、敦煌、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石河子、伊犁等城市也廣泛分布。這些城市節點相應的服務設施也被逐步建立起來,繁榮了絲綢之路貿易,促進沿線社會的穩定。
1.2.3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的“西部大開發”,具有改變國土空間格局的重大作用
絲綢之路是我國歷史上的“西部大開發”,具有改變國土空間格局的重要意義。如: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河西地區,西漢絲綢之路初通時,還是“地廣民稀”,以畜牧經濟為主、農業落后的地區,通過修筑道路、水利設施、實施屯墾,繁榮了商貿并引入大量移民,到東漢初,已是“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之地了。經隋唐的進一步開發,到天寶年間,河西糧食產量已占全國的三成,成為發達的農業經濟區了[15]。此外,新疆特殊的水利工程坎兒井也創始于西漢,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漢宣帝遣將率軍萬五千人屯墾,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谷[16]。此堪稱人類適應氣候變化的典范工程。
如前所述,依托交通往來,絲路上的武威、金昌、哈密、吐魯番、敦煌等城市發展繁榮起來,改變了中國國土空間發展的版圖,堪稱人類歷史上最早、最成功的交通引領土地開發(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的思想實踐。
1.2.4 “絲綢之路”使中國成為世界文化、科技交流的中心樞紐
絲綢之路在世界文化、科技交流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絲綢之路以開拓、包容的價值取向,包容的文化,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推動世界東西方文明交融發展格局的形成。唐對外輸出絲綢、瓷器、茶葉等;其輸入更是豐富多彩,馬、駱駝、牛、綿羊和山羊等家畜,大象、犀牛、獅子等野獸,毛皮、香料、藥物、寶石、金屬、珠寶、書籍甚至人口[17]。而這些輸入對中國社會、中國原有的文化又發生著復雜的、多方面的影響,其中很多逐步融入中國文化之中,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今天的中國文化同樣是歷史上的多元文化融合,既有本土的,也有外來的成分。同時,唐朝將自身的藝術、文化、技術傳給四鄰,對中世紀的整個遠東區域,尤其是對日本、朝鮮、突厥斯坦、吐蕃和安南的影響甚廣,小到木版印刷術、服裝樣式以及詩歌體裁,大到城市規劃、建筑風格,在文化技術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可以說依靠“絲綢之路”,中國扮演了將東西方的文化、技藝相互傳播的媒介角色,成為世界技術文化交流的“樞紐”,從而帶來了漢、唐興盛,是歷史上的“交通興國”。
1.3 依大運河繁榮的農耕與城市文明
水運是歷史悠久的運輸方式,從運輸經濟的角度而言有運量大、效率高、運距長、成本低的優勢。江河湖泊是大自然對交通運輸的恩賜,在生產條件相對落后的古代,其作用超過陸路運輸。除了對自然河流的利用,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開鑿了大量運河。隋、唐、五代以及宋、元均注意發展運河,疏浚、拓寬北方的淺狹河流。先秦時期已有多條史書可考的運河,其后逐步發展,在唐朝已經形成了“商旅往返,船乘不絕”的繁榮景象[18]。中國大運河幾經變遷,主要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大運河3部分,全長兩千多公里,地跨10個緯度,運河溝通了中國華北大平原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幾大自然河流水系,形成了龐大通聯的內河航行體系,其分布地區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作為中國古代交通的大動脈,至今已延續千年,是聯系政治、文化與經濟的橋梁和紐帶,對人口發展、城市的形成有著重大意義。
1.3.1 農耕、人口、城市與漕運
中國古代先民創造了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這塊土地哺育了歷代華夏兒女。從人口規模上看,華夏系統內,商周直到隋唐人口未曾超過6 000萬,有史學家認為這是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粟麥農業區所能支持的人口上限[19]。從唐朝末年開始,黃河農業衰落,中原區域高產的水稻逐步取代華北地區的粟麥,作為帝國經濟的支柱農業,重心南移,農耕的發展使得糧食富足,人口總數得以迅速超過歷史最高值,在13世紀達到一億以上(宋朝出現百萬人口的城市,人口超過20萬的有6個城市)[20];14世紀幾經戰亂,人口數量有所減少,但15世紀,到明朝中期,玉米、地瓜、土豆傳入中國,3種農作物適應性強、產量高,原本不可利用的土地變為耕地,中國出現了“土地利用的革命”,使我國明清時期的耕地面積成倍地增加,食物產量成倍地增長。在農業社會,人口數量與食物量直接關聯,明清兩代在社會安定時期人口數量也迅速增長。
農耕造就了富余人口,促進了行業細化分工,城市成為各行各業人口及貿易繁榮的匯集中心,高人口密度大城市出現,中國古代城市人口已具備相當的規模。以宋代為例,出現了百萬人口的大城市[19]汴梁(今開封),宋實行中央集權政策,集重兵于中央。政治、軍事、經濟中心重合客觀促進了城市發展,城市人口規模達到了空前水平。
城市的人口規模與糧食需求、運輸量成正比。通過水路運輸糧食的漕運,無疑是最為經濟、便利的運輸方式。反之,相對便利的水運交通又進一步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宋汴梁依托汴河(通濟渠)溝通盛產稻米的江浙等南方糧食產區及倉儲點,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都市,城內百萬人口的糧食、生活物資、原材料、生產商品通過水運往來于全國各地。從清明上河圖可以管窺當時水運與城市的繁榮發展程度。
1.3.2 中國政治、經濟重心的遷移與運河變遷
古代中心都城依托有較為便捷水系的地方而建。秦、漢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在長安(今西安),依靠的是渭水;隋唐時期修建大運河,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有永濟渠至涿郡(今北京);南通過汴河(通濟渠)、江南河至余杭(今杭州);西經過黃河、廣通渠連接關中,形成一個喇叭形的水運網絡。相比之下3條水運干線在洛陽交匯,其交通樞紐地位比關中更有優勢,秦漢至唐經濟中心也逐步由長安遷至水運更加便利的洛陽。到了北宋,重心進一步向東,向水運更為便捷區域遷移,全國各大水系在東京汴梁(今開封)交匯,以汴梁為中心,汴河、惠民河、金水河、廣濟河互相貫通,黃河連通運河,汴河連接淮河、長江,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憑此緊密相連,真正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水運網絡,各地物資實現了大交換、大匯集。南宋以后隨著都城南遷,南方得到開發,經濟中心繼續向江南方向移動,遷至蘇杭。
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王朝政治中心向北遷移,而經濟重心仍然在南方魚米之鄉,尤其是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代表,因此,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呈北南分立的格局[21]。此時,南北溝通的需求更加旺盛,而中國的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決定了中國的自然河流基本走向是自西向東,而要想溝通南北,則必須有人工運河的開辟。因此,大運河在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形成了京杭大運河典型的南北走向。京杭大運河使得南方的物質財富能便捷地輸送到北方政治中心,極大地降低了南北縱向的運輸成本,使糧食等大宗物資長距離運輸成為可能。明、清兩朝每年從南方征收北運的漕糧多達400~500萬石,漕船達9 000多艘[22]。興建北京故宮使用的龍柱、地磚等物品均是依靠水運而來。
1.3.3 運河的深遠影響
運河在古代逐步演變為最重要的聯系通道,無疑給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帶來了深遠影響。
首先,運河及漕運是古代交通追求便捷、降本增效的有效手段。農耕發展促進人口增長,進而促進社會分工、人口聚集和城市壯大,在這一過程中體現了對便捷交通、低運輸成本的追求。經濟、便捷的水路漕運運輸模式起到了關鍵作用。
其次,運河促進了沿線的繁榮發展。漕運路線繁榮了沿線城市,促進了沿線經濟的發展[23]。歷史上繁榮的城市多與水運息息相關。從運河的發展可以看到中國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順應自然的往復過程。
最后,運河線的紐帶作用實現經濟重心與政治中心均衡。從大運河的發展及走向上可以明顯看出經濟重心、政治中心的遷移。水路運輸是連接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的紐帶,是權力中心輸入養料的生命線,促進了空間融合和區域分工。漕運從秦漢時代的“東糧西運”(黃河中下游的關中、山東一帶為農業經濟發達之區,漕糧通過黃河、渭河由東向西運抵長安),到唐宋時期逐漸轉變為“東南糧西北運”,與自然河流的流向基本吻合。但到元明清,運河變為南北方向,實現“南糧北運”。運河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對于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發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時,運河也成為溝通亞洲海上“絲綢之路”和內陸“絲綢之路”的重要交通紐帶,運河開通對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起到了促進作用。
1.4 中國航海的波瀾跌宕
1.4.1 中國歷史上輝煌的航海成就
歷史上中國人特有的海洋觀念、海洋文化、海洋道路、海洋戰略,獨特而波瀾[24]。
從自然地理看,中國地處太平洋西岸,屬于海陸復合型國家,擁有綿長的、航運價值極高的海岸線,是陸地大國也是海洋大國[25]。從技術上看,中國歷史上遠洋技術、造船工藝曾幾度領先[26],船舶堅固巨大,對人類的航運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戰國石碑紀錄了當時已使用搖櫓與槳作為船舶推進的方式。宋發明水密分艙法造船技術。至元,中國航海事業逐步進入“定量航海”時代,掌握了磁羅經導航、用錨、使舵技術,掌握了海洋氣象、水文的變化規律。13~14世紀,西太平洋—印度洋已由中國掌控。
從對海洋的探索精神上看,中國曾勇于對海洋探索開辟了大量航線。秦有“徐福東渡”,東晉有“法顯西行,海路回國”,漢“開邊巡海”開辟通往朝鮮、日本的北航線和經南海通往印度和斯里蘭卡的南航線,隋唐五代中國船航跡不僅遍及東南亞、南亞而且已經拓展到阿拉伯灣與波斯灣沿岸及東非海岸,航海事業繁榮發展,“海上絲綢之路”已全面興旺。從海權上看,漢已開始巡行南海諸島,隋唐出現了專門管理海外航運貿易的市舶司[27]。中國在兩漢時已是航海大國,到唐朝又有進一步的發展[28]。宋代水軍的航跡范圍已達西沙群島、澎湖諸島。元朝海外征戰,更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次數最多的,表明其具有一定的海權意識[29]。
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在研究中國古代航海歷史后得出結論:“中國人一直被稱為非航海民族,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們的獨創性本身表現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樣[30]。”中國歷史上是輝煌的海洋大國。
1.4.2 明清海洋發展與轉折
(1)明清海洋貿易的發展
明朝鄭和在1405—1433年七下西洋,艦隊浩蕩,從航船大小、航行規模、航海技術的系統化而論,遠超過八九十年之后的哥倫布、達·伽瑪、麥哲倫等人的航行,航海事業令人驚嘆[31]。
史實證明清朝也并非是一個完全“閉關鎖國”的國家。清中期至鴉片戰爭前,海上貿易較為繁盛,清政府長期處于出超,白銀內流。根據清代海關關稅定額數字記錄,鴉片戰爭前一百年,清朝四大海關關稅呈上漲趨勢。這一時期,海上貿易的相關服務產業也發展完備,與商業貿易相關的各種產業也初步形成,如清代沿海地區發展產生的“牙行”兼顧“中介、保險、報稅、倉儲”等服務功能,類似現代的貨運代理或無車承運人,具有從運輸到物流的性質。
(2)海禁與朝貢貿易
中國歷史上,偶爾有斷絕往來之事。“海禁”又稱“禁海”,最早開始于元代,但只是偶發的臨時性政策[32]。明清兩代“海禁”越發趨緊與常規,嚴格時“片帆不得下海”,但都是有開有禁,明代有隆慶開關,萬歷時期恢復廣州、寧波二市舶司。清朝康熙、乾隆先后幾次群臣商議海禁政策,逐步解禁,也從未徹底斷絕過海上貿易,但總體是謹慎控制狀態。
明清兩代海禁政策既有關聯又有所差異,背后又有著共同的深層次原因。明代海禁因為海盜猖獗、走私泛濫,中國海盜與日本海盜勾結在一起,亦商亦盜,為患于中國沿海[33]。清代海禁則是為了“防漢制夷”。“漢”是反清復明的海上勢力,如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夷”則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順治及康熙五次頒布禁海令,三次下達“遷海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經商,進而斷絕對鄭成功的支援。海禁還體現在對民間船舶的限制。明清兩代對船舶制造有嚴格管控,船舶的形制與行政等級掛鉤,對官船、南洋船、縣船并未禁絕,對于民間沿海船只強迫改為不利遠航的平底船及嚴禁民造雙桅船(漁船不可能大到有雙桅船編制)。清在海禁開放后,對海商船的船型在長度、桅桿、載荷上還存在苛刻的管理[34-35]。
與海禁相輔相成的是朝貢貿易。明代在“天朝想象”中實施了“不征諸夷”“厚往薄來”的朝貢政策[36]。規定周邊這些“蠻夷國家”如果不主動挑釁,不許征伐。朝貢體系逐步確立為以中國為一元中心的東方世界通行的國際關系,演變成了貿易往來的主要形式,到明朝中后期,幾乎成為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的唯一方式[37]。
1.4.3 明清海權逐步弱化的反思
盡管明代有鄭和下西洋;清代長期出超,白銀內流,也并非完全“閉關鎖國”,但其海洋交通與貿易的發展與世界發展脫離,具有局限性。鄭和下西洋仍屬于朝貢貿易的體系,缺乏廣泛的民間參與,甚至明中期開始的對外政策在官方與民間兩個層次上形成對立的局面。早在宋元時期中國海商網絡已遍及東亞和印度洋水域,海外華人已有規模可觀的集聚居住之處,并逐步進入貿易和移民互動階段。而“海禁”政策禁止了中國商民從事海洋生產與貿易活動,情況發生根本轉變,尤其是在鄭和下西洋后,官方大規模的朝貢貿易,使得中國海外私商貿易無利可圖。此外,在“大一統”的天朝幻想下,鄭和下西洋還負有招撫流民的職責,對海上游民和移民打擊,壓縮中國海商的生存空間[38]。
明清政府在“大一統”的天朝幻想下,實行海洋管控的政策導向,限制民間海外自由貿易,客觀上打擊了民間對海外的開拓事業。官府管控嚴格,導致民間力量在此后逐步退出海上,中國海權也漸失于西方[36]。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鄭和七下南洋后的幾十年,西方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地理大發現的時代相繼到來。尤其是明朝的海洋技術、生產力水平在全世界一度領先的基礎上,并沒有實施海洋的擴張;同一時代,西方各國以多種形式鼓勵海洋拓展。如英國的《航海條例》,旨在通過法案保護本土民商對航海貿易的壟斷。
從中西歷史的比較中,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如何營造好開放、開拓的價值取向。在一個國家對外交流的過程中,應該是官民合力向外推進,而不應僅僅是官方的獨角戲。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如何設計并利用公平合理的制度平臺,最大程度地調動民間力量參與國際經貿活動與文化交流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這個國家的實力發展和國運興衰。
1.5 “運輸救國”與近現代交通的開端
交通運輸在民族危難時刻也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抗戰時期發生的“宜昌大撤退”,為中國挽救了民族工業精華和抗戰力量。1938年9月中國大量人員,九萬多噸的軍備、民生、工程裝備等戰略保障物資集中于宜昌及江邊時,日軍節節逼近,對人員及物資的疏解關系到戰爭成敗。盧作孚提出以40天為限做出運輸計劃,迅速克服了混亂狀態,輪船和木船在川江里來回穿梭,百舸爭流,科學調度,運籌帷幄,使之完全按照計劃順利進行[39]。可以說在運輸史上寫下了重要一筆,是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運輸業更是發揮著關鍵作用,淮海戰役車輪滾滾,百萬雄師千帆競發過大江,“組織聯絡前線與后方的軍事運輸……是對于革命戰爭有決定意義的事業。”這是毛澤東對軍事交通重要性的高度概括[40]。
近現代,人類進入了工業革命時代。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苦難卓絕的斗爭,擺脫了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民族的交通業也有顯著改善,但相比世界強國,中國交通仍然是長期落后的局面。孫中山提出《建國方略》,構想了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41],其中重要內容就是超前的大規模的交通建設:提出修建約16萬公里鐵路、160萬公里公路,形成遍布全國的交通網,連接中國的沿海、內地、邊疆乃至青藏高原;在中國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世界水平的大海港。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無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在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萬眾一心,開始了嶄新的交通運輸建設過程,諸多設想已經成為現實。
2 歷史對新時期建設交通強國的戰略啟示
2.1 新時期對交通運輸本質的再認識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貫徹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建設交通強國的戰略措施,從歷史層面總結交通強國的內在聯系規律,從理論實踐上探索交通對國民服務、人類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無疑是非常緊迫和重要的。需要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推進各項事業的建設發展。
2.1.1 馬克思明確指出了交通業改造世界的作用
馬克思指出交通運輸業是物質生產部門,“除了開采業、農業和加工制造業,還有第四個物質生產部門……這就是運輸業”[42]。馬克思指出:“社會勞動的物質變換,是在資本循環和構成這個循環的一個階段的商品形態變化中完成的,這種物質變換要求產品場所的變換,即產品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實際運動。”[43]
其一,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世界上一切都是物質的,物質是每時每刻都是運動的,變化發展的,在哲學范疇內空間位置的變化是物質運動的基本屬性,因此物質和運輸具有天然的共同屬性。
其二,物質生產的本質是使勞動對象發生物質變化,而勞動對象的變化包含了物質空間位置的變化,人類的交通運輸勞動使得物質空間位置變化。同時,運輸實質上就是勞動對勞動對象物質化的具體形式。因此交通運輸是物質生產內容,也是物質生產的勞動過程。
其三,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分析,物質的運動包括了一切領域,就像自動生產線上零部件的組合,它的生產功能是改變實物的空間狀態,以求實物在時空上的最佳配置,使他們固有的使用價值得到最充分的發揮[43],因此交通運輸實現了實物時空上的最佳匹配,從而賦予物質價值。
基于以上三點,馬克思主義認為交通運輸業是特殊的物質生產部門,交通運輸是社會生產力的組成部分,改造世界的作用巨大。
2.1.2 習近平總書記給出了新時期交通運輸的基本定位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特別關注交通運輸事業發展,總書記對交通運輸有一系列重要論述,如:2014年,總書記就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要求:“著力構建現代交通網絡系統,把交通一體化作為先行領域,加快構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聯互通綜合交通網絡[44]。”2014年3月,總書記就農村公路發展批示強調:“在一些貧困地區,改一條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給群眾打開一扇脫貧致富的大門[45]。”
“先行領域”“打開一扇脫貧致富的大門”等有關交通運輸行業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交通運輸是社會生產力組成部分觀點的進一步發揚,明確了新時期交通運輸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結合國情與國家的發展階段,進一步強調了交通運輸的功能定位,即在穩增長、服務國家發展戰略、促改革、惠民生中應當好先行,為交通運輸科學發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2.1.3 新時期要求交通運輸發展模式發生革命性變化
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這表明勞動作為人類有目的活動必須以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為前提,其中使勞動對象發生任何形式的物質變換是物質生產的充要條件。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了“人與自然是個生命共同體[46]”這一重要理念,進一步明確了人離不開自然,同時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進一步生動形象地將生態文明度量引入經濟發展要素,進一步闡明“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質變換的過程[43]”必須尊重自然,尤其是進入新時代后生產力發展水平已極大提升,物質匱乏不再是主要矛盾之后,在人的勞動生產過程中更需要自覺尊重自然。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交通運輸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在拉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發展內涵進一步豐富。既需要滿足多樣化的交通需求,同時需要尊重自然,最大幅度提高資源生產效率,減少交通運輸行業的負面外部性。因此,交通運輸必須發生深刻的變革,需要構建立體綜合的交通運輸體系,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以新時代的新要求來對標發展。
2.2 交通強國的啟示
建國初,中國一窮二白;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高速鐵路里程、高速公路里程、港口萬噸級泊位、城市軌道運營里程均居世界第一。這些偉大的成績背后,交通經略經歷了從“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再到“兩型交通”、“四個交通”;交通運輸業從逐步破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瓶頸”,實現了“總體緩解”到“基本適應”再到“適度超前”的重大躍升,經歷了幾代人不懈的努力和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邁向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征程,回顧歷史有如下啟示。
2.2.1 歷史證明強大的交通體系是國家強盛的必要支撐
歷史上強盛的時代,均有強大的交通體系支撐,秦、漢、唐均有交通格局上重大的實質突破。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曾把中國變成了東西方文化貿易的樞紐,促進了國家的強盛。歷史證明國家繁榮昌盛,必然需要強大的交通體系,交通強大是國家強盛的先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交通強國是時代之需、發展之急,是新時代的新征程、新使命。
2.2.2 歷史證明交通文明的精髓是“開拓、開發、開放”
“開拓、開發、開放”是交而后通的根本。馬克思主義認為交往對于生產力的發展、文明的交流與融合、人的全面發展等都具有重要意義。交通發展是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相互間溝通交流、商貿往來最為直接的前提,是經濟、文化溝通的紐帶。歷史上盛世時代,無不是交通有所拓展,使先前孤立的區域能夠相互銜接,進而相互交融、協調發展的時代。只有在交通發展戰略選擇上秉承開放、包容的態度,才能營造強盛國家在世界文化和經貿往來中的“樞紐”地位。反之,如果沒有一個開放通融的交通經略,終將喪失相應的權益而衰落。歷史上也有明、清兩代海洋權益逐步喪失的教訓,使得人們深知開拓、開放的重要。同時,官方與民間資本應協調發展,形成共同的國家力量,與周邊國家一起構建一個命運共同體[39],以合作、共建、共贏的方式維護好發展的多贏權益。
2.2.3 歷史證明交通格局將引領國家空間、產業格局
歷史上交通格局與國家發展格局息息相關。秦實施“車同軌”、修直道促進了中華“大一統”;陸路絲綢之路促進中國西部地區繁榮發展,促成了中國在東西方的“樞紐”地位;修建大運河降低運輸成本,在政治、經濟中心分離的情況下,促進了中國南北通融,歷史上重大交通方略無不對中國空間格局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新時期,交通運輸發揮的作用從“服務地區經濟”已經逐步躍升為“引領國家區域協調發展”“引領產業協同戰略格局”。新時期,更應注重交通的“大格局”“大視野”,提高區域及國際通道保障能力和互聯互通水平,形成便捷往來的交通格局,更好地實現交通先導。
新時期應從空間格局發展上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現實意義。我國東南地狹、人稠,經濟發展水平高;西北地廣人稀,經濟相對落后。陸路絲綢之路,幾乎與揭示了中國人口密度一直存在的東南和西北分異突變線胡煥庸線(璦琿—騰沖線)垂直。陸路絲綢之路沿線的交通建設及城市帶發展十分鮮明地體現了交通對西部區域的先導和引領作用。為此,以絲綢之路為核心,交通為先導,打造西部“三橫一縱”多層次城鎮結構,建設包昆(包頭—昆明)等陸路通道,長江黃金水道、西江通道等綜合交通運輸走廊,全方面向西輻射。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近一段時間以來西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明顯加強,東西部交通差距縮小,也必將對我國東西部空間分布不平衡的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應進一步突出交通對“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支撐保障作用,推進區域優勢互補、分工協作、聯動發展。
2.2.4 歷史證明“交通強國”有中國模式,更是世界貢獻
歷史上中國就是世界和平發展、開放進步的貢獻者與守衛者,中國曾經為世界貢獻了“指南針”、“水密分艙造船”等對遠洋產生巨大影響的發明,中國的交通經略曾使中國成為東西方文明溝通的樞紐,長期保持了大國繁榮和世界地位。新時期的強國戰略將與各國人民一道構建命運共同體,共享共贏。
同時,我國的國情決定了其發展模式與世界發達國家發展模式均有現實差異,宜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區域差異、自身特點、發展特征選擇交通發展模式和路徑。我國人均資源占有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交通資源方面也是如此,我國千人汽車保有量為140臺,美國800臺,即便未來中國具備人人購車的經濟條件,從資源壓力與環境承載力角度也不能選擇和美國等發達國家一樣的以私人機動車為主的交通模式。目前我國人均交通碳排放是美國的1/9,綠色、低碳、集約、便捷是中國交通強國必不可少的重要特征[47]。
我國倡導綠色發展理念,走出交通強國的“中國模式”。服務生態文明建設的綠色交通既是新時期自身發展的內置需求,也是和平發展的中國貢獻。我國的公共交通、共享交通體現了綠色、高效的理念;我國的高速鐵路、共享出行、車聯網及新能源汽車應用既是交通強國的標志,更是人類共同面臨的社會、環境、健康等問題的中國方案與中國貢獻。
2.2.5 歷史證明“交通強國”是融合發展,應有重大創新
交通在歷史發展進步的過程中一直呈現融合發展的軌跡,融合發展體現在公路、鐵路、水路、航空等各種交通方式的綜合一體,更體現在交通運輸與其他行業與經濟社會的緊密融合。交通運輸一頭連著生產,一頭連著消費,交通的創新實現物質財富的增值,作為人類社會活動基本需求從來都不是孤立發展的。蒸汽機的發明和鋼軌生產技術的進步伴隨著鐵路發展;內燃機的發明和工業體系的進步使人類進入汽車時代;電力工業的進步又催生電氣化交通,近現代人類工業革命無不伴隨著交通運輸的更新迭代。
如今,人類進入工業4.0時代,移動互聯網普及、人工智能技術革新使得共享交通出現、自動駕駛技術日新月異,交通發展模式正在發生變革,交通運輸業正在從重視基礎設施建設的傳統行業逐步躍升為新型科技實踐與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領域。“復興號”、“大飛機C919”、“共享交通”等是與整個交通概念相關的所有產業、科技、服務的同步提升結果,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中意義重大。
2.2.6 歷史證明人民是發展的主體,交通強國的主體是人民
人民是歷史發展的主體,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人民……是具有偉大奮斗精神的人民……是具有偉大團結精神的人民……是具有偉大夢想精神的人民”[48]。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回答了新時期交通強國建設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需要什么樣的精神力量支撐的重要問題。人民群眾所期望的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經濟的交通運輸服務正是交通強國的目標所在,需要把握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服務好人民群眾多樣、高端、個性化出行需求;實現好“降本增效”的緊迫目標,使交通成為激發人民創造力和發展活力的載體和紐帶。
3 結語
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踏上新征程的時代起點,“建設交通強國”是新時代賦予行業的歷史使命。“交通強國”要充分把握交通在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這一宏偉愿景不是一朝一夕,從長遠的戰略眼光看新時期交通強國的建設,要打好交通行業支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攻堅戰”,也要打好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持久戰”。交通必將再次助力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跨越,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好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