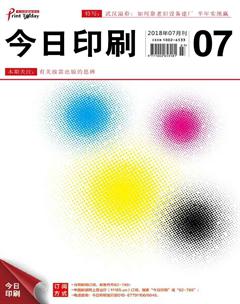影響短版圖書使用數字印刷的原因分析
潘曉東
按照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的數據:2016中國印刷產值達到了1.15萬億元,數字印刷的產值是357.9億元,占比3.1%,其中用于印制圖書的比重不得而知,但屆時全國已有20多條數字印刷生產線在出版、圖書貿易機構或是書刊印刷企業投入運行。
在《印刷業“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中,規劃制定者對數字印刷的發展目標也定得十分明確,那就是“年復合增長率超過30%”。言下之意,到2020年我國數字印刷的絕對產值應該達到654億元,是2015年數字印刷176.15億元產值的3.71倍。在這中間,最適宜采用數字印刷方式的短版圖書印刷理應占有較大的份額。
有這樣兩則數據說明了發達國家使用數字印刷方式印制短版圖書的狀況。
美國CAP Venture印刷調查公司的調查報告指出:“2009年,全球采用傳統膠印的書刊占全部書刊的94%,個性化按需數字印刷書刊占5%,電子書占1%。有人預測,到2015年美國印刷市場傳統膠印書刊量將下降46%,而數字印刷與按需印刷書刊量將上升28%,另有30%的圖書將以電子書的形式向讀者發行。”雖說實際變化究竟怎樣沒有見到后續報道,但數字印刷圖書數量的上升則是肯定無疑的。
Smither s Pira國際咨詢公司的報告指出:“2010年使用數字印刷工藝印刷圖書的比重已經有14.2%,到2020年有可能達到46.1%。”
在數字印刷圖書上,數年前即已有江蘇鳳凰率先踏入,但同發達國家比相對還是落后,關鍵是在現狀下,龐大的投資還不能為企業帶來利潤,這就讓跟進者心生疑慮。唯有弄清楚影響采用數字印刷方式印制圖書的問題所在,并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才有可能引來數字印刷在這一領域的爆發。
2016年國內圖書市場的狀況
同樣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數據:2016年,全國共出版圖書、期刊、報紙、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512.53億冊(份/盒/張),較2015年降低6.9%。其中,全國584家出版社(包括副牌社33家)出版圖書499884種(其中書籍410438種、課本89001種、圖片445種), 90.37億冊(張),增長4.32%,占全部數量的17.63%;期刊10084種,26.97億冊,降低6.29%,占5.26%;報紙1894種,390.07億份,降低9.31%,占76.11%;音像制品22122.33萬盒(張),降低24.79%,占0.43%;電子出版物29064.66萬張,增長35.57%,占 0.57%。
全國書、報、刊的總印張為2196.43億印張,折合用紙量508.73萬噸,與上年相比用紙量降低10.83%,其中:圖書用紙量占總量35.90%,提高5.28個百分點;期刊用紙占總量6.80%,提高0.11個百分點;報紙用紙占總量57.30%,降低5.39個百分點。
稍做一番計算就可以發現,2016年我國每種圖書的印刷量大致是13987本。
另有中國出版協會編制的2016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報告指出:該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總規模為701億元,較2015年的624億元同比增長12.30%。其中實體書店渠道出現2.33%的下降,網上書店保持30%左右的增幅,總碼洋超過實體書店。
在肯定圖書市場取得成績的同時,也把《中華讀書報》上的一條消息立此存照。該消息稱:“從2014年1月到2017年10月,綜合中國大陸實體店、網店及零售三個渠道數據,年銷售數量小于10本的圖書,占全部圖書品種的45.19%;年銷售數量小于5本的圖書,占全部圖書品種的34.5%。”這個數字不免有點驚人。其實,人民郵電出版社的領導同樣給出過一組數據:2016年我國出版物零售總額833億元,總庫存1143億元,每年出版的新書中55%成為絕版并退出流通。盡管這里的零售總額與中國出版協會給出的數字有著132億元的差距,原因何在,不得而知。但這兩條信息至少告訴我們:改變現有的圖書預印模式,扭轉圖書的庫存積壓現象,更多地采用按需定產的方式似乎已經成為十分急迫的事。
當然,這個改變是一個系統工程:就市場而言,牽涉到消費者習慣的改變;就出版集團而言,牽涉到考核方法的改變與圖書預印模式的改變;就圖書印刷企業而言,牽涉到最適合按需印刷的數字印刷設備和耗材有否可能在短期內走出幾乎完全依仗進口、缺乏價格話語權、最終導致產品完全缺乏性價比的現狀,因為一味賠本的買賣肯定難以為繼。說實話,這里涉及的每一項改變都不容易,但變又是必須的,好在業內已經出現了眾多不畏困難的吃螃蟹者,積累了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最終考驗的是領導者的決心。
數字印刷性價比不高是影響短版圖書使用數字印刷的最大障礙
與十來年前出版社根本就不接受數字打樣相比,現在出版社對數字印刷的接受度已大大提高,而且像人民郵電出版社、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在采用數字印刷印制圖書上都還走在同行的前列,這既是得益于數字印刷技術的進步與印刷質量的提升,也是得益于印后設備的同步發展,更重要的是出版人觀念上的與時俱進,何況數字印刷在按需確定印數、版本依對象可做適當篩選、及時修正與補充世間最新材料與數據上都有著傳統印刷工藝所不具備的優勢與能力。
影響數字印刷使用于短版圖書印制的最大障礙是現時產品的性價比不高,當采用數字印刷的圖書其銷售價格1倍乃至于數倍于傳統膠印圖書的時候,出版社會把數字印刷作為成書的首選嗎?消費者會首先挑選采用數字印刷工藝完成的圖書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推廣采用數字印刷工藝的過程中,不少傳媒集團采取的是對市場定價不變,集團內部給予補貼的辦法。這在市場推廣階段可行,但長此以往,又有哪家單位愿意如此操作?因為新工藝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成了吞噬企業利潤的出血點。
導致數字印刷在國內性價比不高的原因也有多重:
首先是設備及耗材的價格高企。迄今為止,國內使用的數字印刷設備幾乎完全被日本與美國的數個品牌所壟斷,而且耗材與設備的維護相捆綁,價格控制權完全掌握在外方手上,生產企業掙的就是供應商留下的那么丁點利潤。可能是2016年后B1、B2幅面的設備才登臺亮相的原因,現在這些設備的市場售價要遠高于同類型的四色膠印機,從效能上說,價高的還不如價低的。盡管圍繞著市場,品牌商之間也會有競爭,但參與競爭的范圍越小就越容易形成共識,不至于出現操戈大戰。
其次,較之于傳統印刷設備,數字印刷設備的折舊周期、更新周期更短,這導致引進數字印刷設備的企業每年要消化的固定資產折舊較高。有些供應商為了推進新型號的銷售往往以舊型號設備缺乏備件,鼓勵企業以舊換新的辦法,至于置換的價格當然是由供應商說了算。這也難怪不少生產企業的老總抱怨是在為設備供應商打工。
其三,設備利用率不足,設備的產能難以得到滿負荷發揮。越是大型高價的設備越是在意設備的利用率,因為這意味著成本分攤的基數不一樣,但強調滿足個性需求的數字印刷設備現時的利用率普遍較低,這就進一步拉低了數字印刷產品的性價比。為了改變這一狀況,部分企業嘗試走集中生產的道路,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如能真正形成社會化集中組織生產,那數字印刷產品的單位成本應該會有較大的下降空間。
在2017年3月展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全會上,湖北省民主促進會專職副主委唐謹就改變數字印刷設備現狀發聲,希望國家重視,加大對數字印刷的核心部件——噴頭的研發力度,像高鐵一樣走彎道超車的路。現在一年時間過去了,雖說有愛司凱等企業在發力,但國家在這方面是否有實質性的措施,這是整個行業關心的。如果數字印刷設備繼續被發達國家卡著脖子,那提高數字印刷產品性價比的想法多半還會落空,讓更多圖書采用數字印刷工藝來完成也并不現實,企業畢竟還是要講成本和利潤的。
把圖書庫存看作出版社資產降低了出版社領導的改革動力
在出版集團內,現行的把未出售圖書依然作為存量資產的做法牽制著出版社領導改變圖書預印做法的積極性。
出版社重視的是腦力勞動,為此,除了辦公用房外,出版社固定資產的投資相對較少,大量的資金都被占用在在銷圖書上。在現時,因為發行部門不承擔在售圖書的風險,基本采用出版社寄銷的辦法,由出版社墊付全部前期成本,待實現銷售后,書店留下屬于自己的碼洋扣率再行向出版社支付余額。如若圖書未能實現銷售,則由書店退還給出版社。這部分未能在一定時間內實現銷售的圖書,理論上說,他們的價值依然存在,因為還有可能實現銷售。但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圖書也是存在時間損耗的,原有圖書的價值將不復存在,直至只能當廢紙出售給造紙廠。但是現行的考核方法是,只要出版社不提出庫存圖書的報損,這部分資產在賬面就依然存在,對社長的考核就不會有負面影響,充其量加上一句“庫存量過大,存在著虧損風險”。這樣,改變長期來已經習慣了的圖書預印為由數字印刷來實現按需印刷的動力就顯得不足。
采用數字印刷方式按訂單量、多批次組織印刷圖書的好處是:不存在庫存積壓,自然也不會出現因圖書滯銷可能出現的報廢損失;非大批量預造貨,占用流動資金較少,回收周期也相對較短;省卻了庫房租賃費用與向銀行借貸資金所需支付的利息。
當然,改預造貨為按需印刷,在編印發三者的關系處置上也會產生一定的變化。以往是出版社完成前期全部工作,印制完成的圖書交書店組織銷售。改為按需印刷后,圖書的印量變成由書店(包括網絡)負責統計、下單,印刷廠按訂單組織生產并通過快遞把印制完成的圖書送上門。這樣的角色變化自然帶來工作方法的改變、利益的調整,怎樣才是最便捷、合理的?這有待通過實踐摸索。
維持還是改變,是把壓力變動力還是維持現狀減輕壓力,這是任何在位領導都回避不了的事。一般而言,上級沒有要求,自我革命難度相對大些,反之,則逼著企業走上新路,不換腦子那就只能換位子。
體制決定圖書出版必須走出版社渠道客觀上減少了社會的自費出版量
基于國情,我們國家的公民有出版自由,那些有著一定經濟條件又希望把自己的積累貢獻給社會的自費出版圖書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多。但現行的相關規定要求,作為正式出版物的圖書必須經由國家批準的出版機構提供書號、組織審讀,出版單位對圖書的質量負有不可推卻的責任。也正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一般公民的自費出版物不可能有一個數量級的突破。
自費出版給予作者的經濟壓力和發行壓力還是很大的。盡管國家對各出版單位的書號已經采取了基本放開的態度,但自費作者為取得書號還是會有一筆支出。特別是在圖書市場難以把控,出版單位要求作者包銷掉相當比重成書的時候,作者普遍還是會打退堂鼓,因為寫書就已經付出了相當大的精力,出書后不能實現暢銷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高校中不少教師寫的圖書在找不到贊助商支持的情況下就只能擱在那里不出版,這種局面應該得到改變。
迄今為止,國家對并不付諸發行的微信書還是持開放的態度,但這大多是作者用于留念,印刷的數量也十分有限。
數字印刷工藝適合于短版圖書的按需印刷,如果說現時產品的性價比不高是關鍵外因,那出版社領導對改變現狀的積極性不足就是重要內因,而自費出版在短期內難有量的突破則是客觀現狀。作為印刷人當然希望迎合社會潮流,在應用數字印刷新工藝上積極向前發展,只要再給與一定的時間,相信就會出現進一步的變化,如果有著強大的推動力,這場變化就會來得更快些。
短版圖書走數字印刷道路的前景被一致看好
短版圖書走數字印刷道路盡管至今還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出于保護環境、追求尊重、交貨迅速的考慮,它的發展前景為市場所看好。既然這是發展趨勢,那我們就應該成為動力而絕非阻力,就應該敢于面對現存的問題,有針對性地盡力主動去加以解決,而不是等所有問題都解決了我們才出來摘果子。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盡管數字印刷在印制短版圖書上有著自身的優勢,而且伴隨著設備與耗材價格的下降,數字印刷與傳統印刷在印制數量上的平衡點有可能進一步拉高,數字印刷在圖書印制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絕不是把膠印擠出這塊市場,膠版印刷還是有著自身的不少優點,膠印與數字印刷在圖書印制上都會有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至于他們在圖書印制市場上的占比多寡,全看技術的發展與市場的接受程度。
好在短版圖書采用數字印刷方式近幾年在國內已經呈現增長之勢,已經成為傳統膠印市場上的一種補充,缺少的是盈利能力,如果克服了上述關鍵難點,不再成為企業的出血點,那發展的速度必然會更快。我們期待著規模化書刊印刷企業使用數字印刷方式印制圖書的日子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