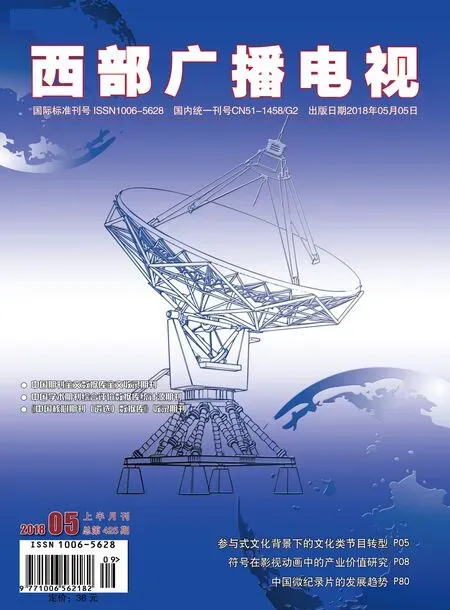自媒體環境下網絡群體意見交鋒及調和策略
翟繼業
自媒體是指傳播者通過互聯網這一信息技術平臺,以點對點或點對面的形式,將自主采集或把關過濾的內容傳遞給他人的個性化傳播渠道,又稱個人媒體或私媒體[1]。自媒體以其平民化、自主性、交互性優勢,為人們提供交際、尋求共同興趣群體、表達話語訴求的平臺,自誕生起,快速“吸粉”無數。
但正如尼葛龐洛帝所說,每一項技術或科學的饋贈都有其陰暗面。自媒體從誕生起,思想的爭鳴也伴隨著不同群體之間的紛爭,紛爭的漣漪喚起圍觀者的共情,隨之形成大規模的網絡群體沖突,其主要表現為網絡群體之間公開表露出來的敵意和對對方活動的干涉。
1 網絡群體沖突的形成
斯梅爾塞對集體行為的發生條件作了分析,指出集體行為的發生同時受六個要素的影響:結構上的有利條件;結構性緊張;概化信念的發生和擴散;誘發因素;動員參與者;社會控制機制[2]。網絡群體沖突的發生,是基于自媒體社交平臺的便利性、網絡監管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網民可以快速加入到網絡“大V”設置的個人情緒宣泄情境中,使群體沖突產生并快速升級。
1.1 內群體產生--結構失衡
網絡群體不同于現實的正式群體,各群體成員分散各地,跨越不同文化、年齡及職業等,是典型的非正式群體。內群行為是指兩個或更多個體間的互動,這些個體處于一個共同的或共享的社會自我范疇化或社會認同之中[3]。群體成員雖沒有群體規范的約束,也沒有科層制的領導體系,比較松散,內部會經常發生矛盾,但有著共同的利益需求、認知體系,一旦遭遇外群體的攻擊,會迅速地集合起來,顯示出群體的凝聚力,組建臨時的討論群,商量策略,團結一致對外,由此,從松散的大眾集合成為緊密的一體性單位。
1.2 社會分層、利益向背--偏見的根源
社會分層是當前社會結構的表現形式,社會分層是指社會成員、社會群體因社會資源占有不同而產生的層化或差異現象。這里的社會資源是指對人有價值的全部資源的總稱,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等等[4]。網絡社會亦如此,表現為不同層次群體之間互動,各個網絡分層群體都有自己的共同利益。在自媒體環境下,雖然人人握有“麥克風”,但影響力卻很小,很難引起廣泛關注,話語權仍被極少數的“意見領袖”掌控,這樣,一旦“網絡大V”發出一致對外的動員,能很快引起圈內網民的“共情”,為維護所共同擁有的訴求,傾力參與其中。
1.3 社會控制稀缺--外部監管有限
自媒體環境呈現匿名性、信息傳播快、實時監控難度大的特點,治理網絡沖突、引導網民情緒的機制還不成熟,有關治理網絡法規制度還不健全。社會控制因素缺位,外部監管有限,大多網民便心存僥幸,責任意識薄弱,個人主義觀念突出,肆無忌憚在網上抨擊。自媒體隨即出現失范現象,偏向問題滋生,大規模的網絡群體沖突一觸即發。
2 網絡群體沖突的危害
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縮影,網上的每次動蕩都會在現實社會中引起波瀾,對社會的各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2.1 政治上的危害
當前,我國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實現偉大“中國夢”而不斷探索,正處于深化結構性改革的深水區,改革不免觸及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利用捕風捉影的消息,通過網絡制造矛盾,誤導網民,引起大規模的網上群體沖突,嚴重危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破壞改革壞境,極大地阻礙了改革進程。
2.2 經濟上的危害
網絡群體沖突對經濟的危害是快速的,一旦沖突爆發,就會對某個企業經濟造成損害,特別是同質化企業之間的沖突,這種“零和博弈”,最終只會兩敗俱傷。由于自媒體個性化推薦式的“協同過濾”服務,尤其是當媒介偏向存在時,網民只看到沖突一方的觀點,作為旁觀者的網民也會形成心理偏向,特別是關于藥品、食品等關乎民生的企業信息。這樣沖突一方的企業就會陷入致命的旋渦,企業形象損害、產品銷售大幅度縮水,甚至破產。這些現象嚴重破壞市場秩序,對于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
2.3 文化、教育上的危害
據中國互聯網數據平臺(CNNIC)第40次統計,10-19歲網民占19.4%、20-29歲網民占29.7%,總比例占49.1%,占據網民比例的一半左右,是自媒體網絡的重度使用者。這一層次用戶大多是學生群體,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還不成熟,防范意識薄弱,辨別能力差,情緒控制自制力差,盲目跟風,極易被誤導。這類群體處于學習、文化培養的關鍵期,任由其參與網絡沖突,世界觀、價值觀就會有偏差,不利于主流社會認同的培養。
3 解決網絡沖突策略
網絡沖突是社會現實的反映,相比現實社會的小規模群體沖突,治理難度更大,成本更高,所以,一定要加大治理力度,同時需要各方力量協同,避免產生更大的社會危害。
3.1 健全法規,加強監管
網民參與到網絡沖突的紛爭,大多是由于沒有政策顧慮,大肆在網上造謠生非,有意惡化網絡環境,心存僥幸、法不責眾的心理現象依舊普遍。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一部分,應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兼顧社會方方面面,在法律政策上建立追究責任制,并全面開展普法教育,形成社會共識。另外,由于網絡的話語權依舊被少數“意見領袖”控制,應密切關注其言論和動向,做到有的放矢,在源頭上控制輿論方向。治理莫過于防范,在審核把關方面絲毫不松懈,加大力度依法審核自媒體、公眾號平臺,一旦發現不良苗頭,立即制止。
3.2 權威引導,防止極化加劇
群體中的成員正如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處于集體“盲目”狀態,群體沖突的雙方“零和博弈”思想嚴重,對于沖突一方的說服,會選擇性理解、逆向解讀,加上傳播隔閡現象的存在,雙方的“鴻溝”越來越大。針對這種情況,應采用第三方介入、兩面提示的策略,傳統權威媒體應積極加入,極力盡到“把關人”的職責,化“被動”為“主動”,加強輿論引導力,根據輿情監測,傳播大量的真實“信息流”,沖淡“情感流”的傳播,減輕雙方的集體“相對剝奪感”,合理引導沖突雙方修復關系,達成和解。另外,注重社區及網絡社區優勢,消除“傳播隔閡”,減少誤解,避免更大的群體極化。
3.3 加強教育,提升媒介素養
媒介素養為近用、分析、評估、創作和參與各種媒介信息提供一個架構[5]。是一個人媒介認知力、解讀力、創造力、參與力的綜合體現。當前,自媒體用戶大眾化,普及速度飛快,滲透各個階層。但媒介教育滯后,發展不成比例。當前,應根據不同年齡段、學歷層次的人群,制定相應媒介素養讀本,列入各個教育階段以及不同學科的必修課,同時,傳統媒體借助客戶端、微信公眾號等普及媒介知識,這樣形成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多方合力,提升全民媒介素養。
[1]申金霞.自媒體的傳播特點探析[J].今傳媒,2012(9):94.
[2]Neil J Smelser.Theory of CollectiveBehavior[M].New York:Free Press,1962.
[3]邁克爾·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會認同過程[M].高明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李強.社會分層十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5]榮建華.中國媒介素養教育論[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