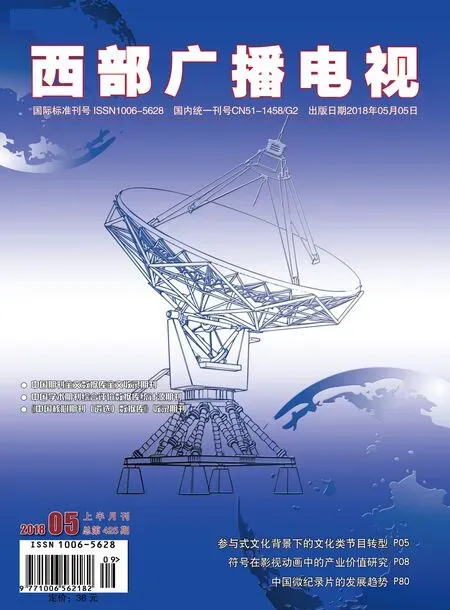淺議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的創作
付 俊
2018 年春節期間,一部以美食為主題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3》,讓無數人守在熒屏前,看得食指大動、口水漣漣。作為一個現象級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自2012年第一季首播到今年的第三季,中國美食以輕松快捷的敘述節奏和精巧細膩的畫面,向觀眾尤其是海外觀眾,展示中國的日常飲食流變、中國人在飲食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千差萬別的飲食習慣和獨特的味覺審美,以及上升到生存智慧層面的東方生活價值觀。本片給觀眾提供一個新視角看待生活藝術,讓電視從業者多了一個視角看待多元化的藝術創作。筆者對本系列片的創作總結了四個關鍵詞:“格局”“困境”“小、大”“節奏”。
1 格局
格是人對事物認知的程度,局是指認知范圍內所做事情以及事情的結果,合起來稱之為格局。不同的人對事物的認知范圍不一樣,所以說,不同的人格局不一樣。具體到《舌尖上的中國》作為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的美食類紀錄片,我們首先得解決片子的幾個核心問題。什么是主題?什么是題材?什么是選題?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的總導演任長箴歸納過一句話:“主題是價值觀,是關乎愛和真理的一句話,是靈魂;題材是片子的題目,是貫穿始終的骨頭;選題是具體的故事,是血肉。”例如,《舌尖上的中國1》的主題是“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題材是“松茸這種食材”;而第一集的具體選題是“單珍卓瑪上山采松茸的辛苦故事”。
筆者曾經是四川廣播電視臺美食節目的編導,當剛剛看到這個紀錄片時,發現此片與之前所拍的美食節目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這是一部“探討人與食物的關系”的片子。而筆者拍的片子局限于美食本身的特色、制作和歷史。
《舌尖上的中國》以美食為切入點,將鏡頭對準中國社會的普通民眾,展現了中國人的生活智慧、勤勞,熱情和追求。這個片子告訴我們能夠打動人心的真正的好紀錄片,需要的是做這個片子的人需要一個怎樣的格局,這是每個編導在做片子之前必須解決的問題,那就是想要傳遞出怎樣的主題思想。這個問題是立片之根本。
2 困境
什么是困境?字面上講應該是不順利的境遇。人生之路曲折、漫長、坎坷。走在這條路上的人們,大概都不能一帆風順,逆境經常有之。
真正的人物故事,應該是人物在實現愿望的過程中遇到的困境。身處困境,比如,《舌尖上的中國1》第一集講單珍卓瑪采松茸的故事不是講她的業績,而是講她采松茸過程中的挫敗,觀眾感動于挫敗帶來的人之共情。堅強的人總會迎難而上,或是為了生計,或是為了榮譽,等等。作為紀錄片的創作者把拍攝對象面臨困境如何找到解決困境的方法,如何在起伏的命運中把控住自己加以全面展現,這是記錄者打開創作之路的鑰匙。可以說,找到了主人公的困境就找到了好故事的引子,就找到了打動觀眾心靈和情感的鑰匙,在困境中人的三種負向情緒——憤怒、悲傷、恐懼和一種正向情緒——樂觀,都展露無疑。細膩的情感是世界性語言、是人性的表達,是普世的真理。一個好故事需要矛盾與沖突,但更需要的是在其中我們看到了歷經風雨,方見彩虹的人生真諦。從收視心理講,就是“先抑后揚”,在困境中堆積三分之二的負向情緒,最后釋放出三分之一的正能量。這種起伏變化就是一個故事,一個吸引人的好故事。最好的故事就是,人生最完美的結局,永遠屬于戰勝困境的堅強者。
3 小、大
小與大是一對相反詞,相反詞在中國文字里是一種很重要的狀態,也是中國意象化文化語境中的獨特狀態,如何在一對矛盾中體現出統一與和諧呢?放在文藝創作中,我們常會使用“以小見大”的手法,巴爾扎克曾經說過,“成功的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積驚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這里所說的“小”是指小人物、小事件、小細節、小角度;“大”的意思是指作品中體現大的情感、大的道理、大的主題、大的背景。
“以小見大”是電視工作者常用的創作方法,它往往取材于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小事件,通過小角度切入,關注人物的一言一行,描繪人物的內心活動,反映深刻的道理、重大的主題和時代背景。具體到《舌尖上的中國》紀錄片,我們可以通過每集8-10個小人物、小故事、小片段、小角度,解讀出一道道美食背后所蘊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這個是一個很高級的論述。
《資本論》第一卷指出,商品的價值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換言之,將美食的價值直指為勞動產品,這從哲學高度闡述了世界上的任何產品的形成過程中,不論使用什么工具、原材料及生產的方式,都消耗了人的體力和腦力。這解決了《舌尖上的中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紀錄片的問題,它就是人類探討人類勞動以及勞動者與勞動對象關系的共同性的電視片。因為任何商品都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放在《舌尖上的中國》這部片子中就是中國一句古詩:“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綜上所述,在《舌尖上的中國》中我們無時無刻都會看到運用以小見大的手法。一是所選小人物、小片斷、小鏡頭和生活細節,這方面創作者使用了專業微觀拍攝設備,拍攝了大量的淺景深鏡頭,從微觀特寫的角度更好地展示中華美食,極大豐富和增強了電視這種藝術獨特的表現力。二是挖掘出小中的大,借用具有典型意義的生活細節來刻畫典型形象,認真思索其中所蘊含的深刻意義。比如,松茸和蓮藕成為食材之前,它們是如何被采摘的勞動場景,就知道美食背后所蘊含的無差別人類勞動,人在社會中有不同的社會角色,但是只要是在勞動就會有共同的一面——艱辛。在勞動面前,人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因此,在片中我們感受了勞動者的可愛、可親以及片子的接地氣。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將紀錄片創作目光放在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身上,捕捉到人物在時代背景下的個性化特征,牢牢抓住塑造人物情感在藝術創作中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紀錄片所要表達的主要內容不只是一些人物的生存狀態,還要表達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情感訴求,進而揭示人性的深度,為觀眾呈現人物的生命意識中所孕育的思想情感和人文精神,這是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成功的“神”。看似一檔有關美食的紀錄片,實際上它講述的是——與美食有關的勞動者的情感故事,不僅能提高藝術作品的感染力和打動人心的震撼力,而且把人物塑造得更鮮活、更飽滿。
4 節奏
什么是節奏?筆者的理解具體到電視紀錄片,即為影片結構、鏡頭長度的處理等元素所構成的一種節律。在電視后期剪輯中,我們常常通過鏡頭剪輯,控制影片節奏,調整觀眾抑制與興奮的觀影心理,達到最佳視聽效果。在紀錄片的剪輯中對節奏的把握是至關重要的,正如摩西納克所言,“最后確定影片本身價值的那種特殊價值還是節奏”“是節奏,不然就是死亡”。
筆者對《舌尖上的中國》細節的使用而形成的節奏有較深的感受:細節畫面所產生的內部張力,比一般鏡頭更具沖擊力、感染力和表現深度。同時,細節也是調解內部節奏的重要手段。比如,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解說詞特寫化和鏡頭的細微化,解說詞內部節奏的起伏變化,能夠使觀眾的興奮點隨之抑揚跌宕,有效緩解了持續收看而引發的視覺疲勞。
同時,音樂作為聽覺元素,在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進行情感表達和交流時不失為最佳的藝術形式。紀錄片以紀實為己任,真實性為其本質屬性。抽象的表意音樂與寫實的影像相互碰撞,營造了紀錄片的藝術性和逼真性的品格。隨著紀錄片創作理念的不斷變化和發展,音樂以其獨特的藝術手段對紀錄片畫面進行渲染、烘托及深化并讓畫面留有思考空間,成為紀錄片表達中的重要元素。導演在片子中大量運用各種不同音樂以及各類特效聲,為觀眾細致地營造一種視聽氛圍。根據接受心理變化,音樂會產生一種新鮮感,使人在心理上產生一種期待;當人們持續維持在一種情緒狀況時,逐漸產生一種制約力,這種制約力則會抵消新鮮感。在這種情況下,音樂的節奏會起到一種調節作用,它通過對運動世界快慢緩急的反映,不斷破壞人們固有的心理程序,促使心理活動的增加,不斷造成人們的新鮮感。這是一個導演表達的高明之處。
5 結語
紀錄片是對一個真實事件的紀錄行為。但它同時又是作者的創作行為,它是人類的文化產品和傳播產品,本身也蘊含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在于它是以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對其進行藝術的加工與展現的,并引發人們思考的藝術形式。這里面包含真實的原生態時空和導演所理解的、并創作出的影視時空。導演是在一大堆真實生活素材里,重新構建一個為觀眾審美所接受的二度創作時空。所以,要求導演既要能還原真實,還要能表現真實。表現不是還原,表現是藝術加工,正所謂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