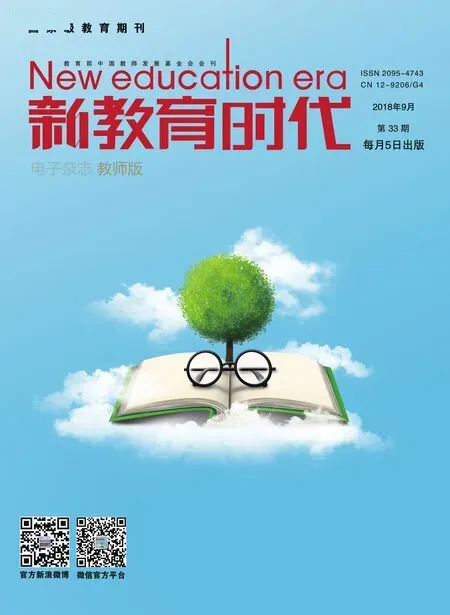幼兒同伴交往規則行為的案例分析
——以中班角色游戲為例
(合肥市榮城幼兒園 安徽合肥 230000)
一、幼兒交往規則行為的案例分析
1.交往的內隱規則行為:建立內在秩序感。
案例1:表演區里真熱鬧,幾個孩子忙著挑選喜歡的衣服,旁邊一個小男生拿著梳子和吹風機在等待著他的“顧客”,而另外一邊一個小女生端著化妝盒也在等著她的第一位“客人”,小朋友們換好衣服便找到化妝師和發型師開始裝扮起來。發型師一邊幫客人梳頭發,一邊用吹風機吹頭發;化妝師用粉撲給客人搽粉,然后畫眼影……
案例分析:游戲反映的內容是幼兒親身經歷、熟悉的或者是讓幼兒印象深刻的,幼兒根據自己對角色的理解創造性地扮演角色,往往會遵守社會對該角色的動作要求和使用物品的要求。案例1中的發型師和化妝師的角色是幼兒熟悉的,他們能夠根據角色的動作要求和使用物品要求進行表演。這種對某種角色性質的社會認同,這些內化的認知規則使幼兒建立了一定的秩序感。他們一般不允許破壞這種內在秩序。[1]
2.交往的組織規則行為:從內部走向外部。
案例2:區角游戲開始后,其他區角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是角色區里孩子們毫無進展,他們漫無目的地選著頭飾,選了好一會,有些孩子仍舊一無所獲。這時幼兒A大聲地說:“我們來玩喜羊羊和灰太狼吧!”其他孩子似乎對他的提議很有興趣,紛紛附和說:“好啊,好啊!”幼兒A得到大家的肯定后顯得特別自豪,“我來當灰太狼吧!你們誰想當喜羊羊?”有兩個孩子同時舉手都表示想當喜羊羊,幼兒A看到這樣就對其中一個孩子說:“讓他當喜羊羊,你來當厲害的村長吧!”一個個角色安排好后大家都開始準備起來......[2]
案例分析:組織能力反映出個人的社交水平,良好的人際關系是組織的前提,合理的規則是組織成功的保障。組織規則是游戲情節對角色的要求,在一角色游戲中角色怎樣分工、各角色之間怎樣合作等都需要有良好的組織規則。案例2中的幼兒A對游戲角色的規定、分配以及游戲情節的設定是該幼兒自發制定及與同伴商量的結果,這體現了良好的組織能力。
3.交往的寓教于交規則:發揮助力作用。
案例3:表演區里兩個孩子爭執起來。幼兒B:“這個面具是我帶來的,還給我。”幼兒C:“我先拿到的,所以我先玩。”幼兒B:“老師說不能拿別人的東西,這是我的,我媽媽給我買的。”幼兒C:“我玩好了再給你不就行了。”“你是個壞蛋!我以后不跟你玩了!”幼兒B生氣地說道。幼兒C的堅決不給惹怒了幼兒B,幼兒B就去搶,兩個孩子各抓著面具的兩端,誰也不愿意先讓。
案例分析:為保證區角游戲的有序、安全進行,教師總會制定許多游戲規則。在表演區里,交往規則包括:與同伴友好相處,使用文明禮貌用語,不爭搶物品,學會合作等等。案例3中的兩個幼兒因面具產生了沖突,在交往中的不恰當的表達導致了同伴關系的不愉快。教師應將這些交往規則以區角規則的形式滲透到區角游戲中,幫助幼兒提高交往的技能和水平。
二、影響幼兒交往規則行為的因素
1.幼兒的行為特點。
謝弗認為,如果一個兒童被看做破壞行為和麻煩的制造者的話,他的同伴將會拒斥他,那么這個兒童便不能形成正常社會交往技能。而為了引起別人的注意或清除自己行動的障礙,這個兒童就會作出一種更破壞性行為,以此作為加入群體活動的方式。
2.幼兒的情緒影響。
霍妮認為,兒童的基本焦慮來自人際關系的困擾。焦慮是幼兒經常體驗到的情緒狀態。當幼兒心情不好或被老師批評的時候,最容易產生違規行為。相反,當幼兒心情愉悅或收到表揚時也最容易自覺遵守游戲規則。[3]
3.家庭及媒體資源的影響
家庭和媒體傳遞的信息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幼兒的行為。加之,信息時代的今天,電視、電腦對孩子總有著無盡的吸引力,對孩子行為的影響也日益加深。偌大的信息迎面撲來,而幼小的孩子沒有辨別能力,不管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的信息全盤吸收。如幼兒對《鎧甲勇士》、《奧特曼》的喜歡,造成了對動畫情節里暴力行為的模仿,難免產生攻擊行為,影響幼兒同伴間的交往。
三、幼兒交往規則行為養成策略
1.改善認知模式,正確認識自己與他人。
中班幼兒由于自身因素的限制,對自我的認識比較片面。認知自我,包括認知風格、認知過程、認知策略。即通過對自我信息的加工、提取形成的關于自身的全面認識。知道自己的優點、缺點,知道每個人都有閃光點,都有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所以幫助幼兒改善認知模式,全面地了解自己,并知道自己與他人的區別,對于形成良好的規則行為有重要作用。
2.完善自我,增強自身吸引因素。
中班階段被忽視幼兒人數逐漸減少,而受歡迎和被拒絕幼兒的比重增加了。幼兒選擇同伴的標準越來越明確,喜歡同伴的理由是他(她)能陪伴自己一起游戲、一起活動,而不喜歡同伴的理由往往是那些消極的交往行為,即“他打我”“他罵我”“他批評我”等。事實證明,那些性格活潑、樂觀、樂于助人的孩子更容易被同伴接受,而那些沖動、暴躁、愛攻擊的孩子往往被同伴拒絕。完善自我性格,幫助幼兒增強自身吸引力,促進幼兒良好人際關系的發展。
3.設置角色游戲情境,悉心培養規則意識。
設置不同的游戲情境,尤其是包含豐富游戲規則的角色游戲,讓幼兒在角色游戲中體驗角色規則,模仿成人之間的交往,學習交往規則。如在“公共汽車”游戲里給老人讓座,在“過家家”的游戲里大人要照顧小孩,在“商店”游戲里服務員不能與顧客發生沖突等等。在活動中貫徹“不能損壞別人的物品”、“不能打架罵人”、“做錯事要道歉”等社會交往道德規則,使幼兒感悟規則的價值和意義,逐漸養成優良的規則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