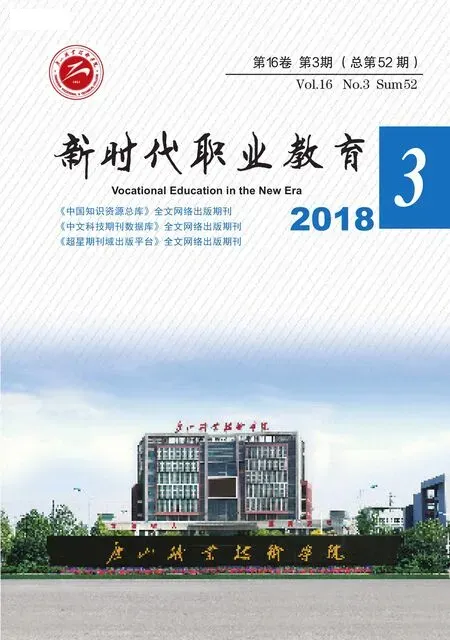從個人權利看正義
——葛德文正義思想剖析
劉 穎
(河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天津300401)
一、權利與正義的萌生與生長
從文藝復興人的發現到人們主動追求主權在民,強調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彰顯著西方國家對于個人權利的前瞻性。文藝復興強調人文主義精神,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強調個人權利,為世界帶來了光明。正如但丁所創作的《神曲》開啟了新時代的序幕。《神曲》從地獄、煉獄、最后到達天堂,也意味著但丁想通過文藝復興沖破封建的束縛,達到自由理性的世界。理性與自由,個人權利“占據”人們思想,提倡以人為中心,反對教會。這種思想并不是偶然,當時在教會和君主的管控下,中世紀歐洲文學藝術死氣沉沉,科學技術并無實質進展,人民貧困多病,這一切的情況使人們開始懷疑宗教神學的權威。邊緣人物與皇權貴族身份的落差使得他們更想爭取自己的權利,貧富與地位的差距所帶來的實質生活上的反映,也讓人們開始覺醒要為自己的權利而奮斗。人們開始探索資本主義和生產力以及進步的自由思想。文藝復興就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這場浩大且歷時長久的思想文化運動使人們開始覺醒,并意識到人的重要性。
啟蒙運動作為文藝復興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更強有力地打擊了教會和封建思想。自由民主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賦人權”等等思想啟發民智,并且對未來藍圖進行了合理展望。霍布斯認為人們那時已經有了一種正義感,亟需的是訴諸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的個人和集體,將正義與權力限制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里,用權力保障正義。面對強權,人們逐漸表現出對其的質疑與不信任,洛克提出要三權分立,對權力進行分配與制衡,才能實現對政治權力結構穩定性的控制。權利與法又是不可分割的。《獨立宣言》中提到“所有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使用這些權利是人們的自由,但同時人類又具有任性與利己的傾向,所以這就可能會發生一種情況,即人們的外在自由與他人的普遍自由發生沖突,就可能會有不義行為產生。這時候法的原則就是一種約束力。有了法的啟蒙,康德提出法權思想,將法權解釋為三種意思,即law(法)、 justice(正當)、 right(權利),分別作為一種秩序、合乎道德的事物以及一種意識主張提出來用來對抗不義行為,[1]使人們對法與權有一種恐懼感。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加上如火如荼的法國大革命,葛德文意識到正義對社會與政治的重要性,也了解到封建思想對于人們思想禁錮的危害有多嚴重。《人權宣言》中講到“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法國大革命讓人們意識到個人權利與自由的重要性,英國工業革命間接增添了貧苦大眾的苦難。現實的景況讓葛德文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通過從個人權利分析社會不平等的原因,探索解決的辦法,為苦難大眾尋求出路。
二、葛德文的正義與權利
處于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市場經濟與工業化占統治地位,倡導利益優先,人人平等。處于此時代的葛德文在《政治正義論》中這樣闡述對于正義的理解:“我對于正義的理解是:在同每一個人的幸福有關的事情上,公平地對待他,衡量這種對待的唯一標準是考慮受者的特性和施者的能力。所以,正義的原則,引用一句名言來說,就是:‘一視同仁’。”[2]從葛德文對于正義理解的“一視同仁”一詞的表面意思就可看出這時的社會相較于之前的奴隸社會—奴隸主剝削壓榨奴隸的殘忍情況不同,人們更看重平等、自由。英國法學家亨利·薩姆納·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3]。在封建家長制度中,一人高高在上,決定著一切事務,其他人只能聽之任之。身份決定著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這也突出了當時社會的極其不平等的問題。當過渡到契約型社會時,我們的出身、性別、膚色雖然不同,但是卻站在同一起跑線,有著同樣的權利,槍聲一響,可以平等地一起沖出跑道,追求自己的利益。人們對于身份的“拋棄”為的就是實現人的自由與平等。這時,人們知道了自己的平等地位與權利,為著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奮斗。伯納德·施瓦茨的《美國法律史》中也提到“契約標志著社會在實現文明和繁榮方面獲得的進展”[4]。契約是將等級制度拋出社會的一股強力,是為新時代帶來希望與光明的價值取向。舊社會的那些所謂的先天的優越性權利在擁有契約倫理的市場經濟面前毫無立足之處。在文明的發展之下,人們的思想也會隨著發展,人們對于正義與平等的認識也進一步加深。這也是社會秩序從野蠻逐漸走向規范的必要過程。
葛氏對正義的理解中不僅摻雜著功利主義思想,還摻雜著動機與效果相結合的絕對傾向。一個人對社會所造成的利益的多少,決定著我們的社會待遇的優劣。我們作為正義的受者,當為大多數人的幸福作出極大地貢獻時,社會對于我們的反饋也應該是最優的。而且,當一個人的動機與傾向都是正義的行為才能稱得上是有道德的。我們可能會對自己所熟識的人投去更多的偏愛,雖然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是人性的一種缺陷。雖合理并不代表是真理。我們每個人對于道德與正義的評判標準都是不一的,只有當把自己處于一個不偏不倚的位置看他人的行為,才是一個公正的旁觀者。
權利,自古以來就是經常與正義一同出現的一個熱議詞匯。在葛德文看來,自古這一切激烈的討論都是對于權利這一詞匯的解釋不清造成的。他認為人的權利可以分成積極的和消極的,有我們想要去做什么的權利以及可以要求他人克制或要求他人幫助的權利。道德作為一種準則,要求我們盡力去維護正義,葛德文認為人類活動的領域中,每件事情只有一種最佳解決方法,這個方法是遵從正義原則的,且最為合理。只要每個社會成員采取這種進行方式,我們的幸福生活指日可待。但現實總是不盡如人意。權利總是表現出明顯的優先性,資產階級盡力追逐屬于自己的權利,甚至于想要剝奪屬于貧苦大眾的權利,為的是奪取本不屬于自身的利益。所以,這就使權利與正義形成一種張力,相互拉扯,不能平衡。葛德文自始至終認為個人權利雖然分為消極權利和積極權利,但是積極權利似乎是一個偽命題,在他這里并不能成立。換句話說,葛氏認為并沒有從“本我”出發的權利,我們并不能自己去操控權利,應該按照道德原則的規定行使權利。按照道德的原則,為社會做出貢獻,個人權利應該是為大眾幸福與正義做貢獻(但個人權利也是不容剝奪的),權利與道德掛鉤,道德與正義的原則已經為我們規定了最正確的做法,我們必須遵從道德原則進行行為選擇,自然就無需依據自我意愿行動。“我們的一切都由不可改變的理性和正義所規定了的用途,如果我們改變這些東西的用途,我們就會給自己帶來一定的罪責”[5]。在葛德文這里,積極權利已經被正義的更高的要求所替代而宣布無效。
正所謂即使是自己的所有物也不可隨意處置。雖然葛德文的思想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卻道出了財產私有是正義問題的根源。正是由于這種錯誤的思想,守財奴積聚錢財,形成積累,造成貧富差距,大眾陷于貧困,地主卻享受這奢靡浪費所帶來的快感,從而引發了正義問題。葛德文一直倡導的就是奉獻,為社會做出貢獻,他講到若是將守財奴的那些財產服務于大眾,必定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果人們都按照道德的原則辦事,就會獲得正義。我們擁有的更多的是消極的權利,如為別人進行忠告和建議,所以并不存在私人事務,所有事務都應該受到大眾的評價和建議,這是人的一種義務。這里,葛德文預見性地注意到了一個度的問題。若一個人無休止的用愚蠢的建議來煩擾他人,侵犯了別人的思想范圍,甚至達到指揮與強迫的地步,那就相當于暴政,暴政也可能來源于評價和建議的義務。要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地方長官和君主的權利更需要控制,而且,地位高低與義務大小是成正比的,位高權重自然義務也就更大。被大眾賦予了權利就要運用到服務大眾的福利當中去。最后,葛德文指出,這些限制不僅僅應該運用到守財奴和君主身上,平民百姓也同樣適用,這樣,公平正義和道德必會如期而至。
毫無疑問,葛德文向著人權邁出了巨大的一步,人們有建議和評價的義務,人民的聲音是需要聽取的,即使是最不重要的人的意見也不應被忽視,也不應被位高權重的人的可恥的優越感所震懾。 “個人判斷的權利是其他一切權利的基礎。對于一個有理性的動物來說,只能有一個行為的準則,那就是正義;只能有一種決定這個準則的方式,那就是運用自己的智力。”[6]理性所引導的個人判斷的能力與成文制度是不可比較的,“除了根據必要的和不可改變的生存法則而采取的行動所具有的主旨之外,不應該受到其他任何的影響,而且我們不受這種影響的程度越大,道德也就越會提高。”[7]總之,個人判斷是美妙的,成文制度和法律是無法與之比擬的。在這里,他提到了法律,雖然葛德文肯定了法律的存在,也明確提出社會只能夠宣布解釋法律,并不能制定法律,稱其是“更高,更不可變的權威那里所制定的”。[8]但是,對于法律他是持反對的態度,認為這種冷酷的邏輯會與我們所追求的社會背道而馳,產生出毫無信仰與無私精神的信徒。這也使得無政府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初見端倪。
那么,如果我們現在談到簡化政府職能,在盡量少侵犯個人的獨立性的情況下維持大眾安全與幸福,那葛德文勢必會站出來維護我們的這一想法。雖然葛氏也看到獨立的個體在沒有社會組織的聚攏下也無法生存下去,政權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政權原本是為了矯正非正義而存在的,而現實卻并不盡如人意。政權將非正義的行為“合法化”和具體化了。從葛德文極力推行的理性與個人獨立性,我們了解到其對“個人”情有獨鐘,社會契約要求人們放棄一部分自我權利,進入到一個共同體中,遵循一個不可能人人都同意的約定,這無疑對于唯理主義的葛德文是無法接受的。正如盧梭所說的“凡是不曾為人民所親自批準的法律都是無效的;那決不能是法律。”[9]既然不能讓每個人都同意,它就必然對任何拒絕的人沒有任何法律效力。所以,若有人倡導簡化社會制度,回歸“守夜人”政府,葛德文則會毫不猶豫站出來跟他歸為一個陣營。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雖然使葛德文被列為空想社會主義,但卻代表了啟蒙運動到空想社會主義的過渡,迎合了發展潮流。
三、馬克思主義與葛德文正義觀比較
對于馬克思的正義思想問題,一直都爭論不休。著名的“塔克—伍德”命題就是其中一個代表。羅布特·查爾斯·塔克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是罪惡的,但卻不是不公平的。”[10]塔克認為馬克思所說的是我們不應該過度關注分配關系,而應該更多了解生產關系。如塔克一樣,艾倫·伍德也直言“馬克思并沒有以不正義之名譴責資本主義。”[11]由此,他認為資本主義并不是不正義的,當時的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并不是一種不義行為,因為這是與當時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種行為。此言論在當時引起一片嘩然。但是,當看到批判資本主義時馬克思所表現出來的譴責與悲憤的語氣時,其對于資本主義剝削與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的痛恨不言而喻。顯然,“塔克—伍德”并沒有從對的方向分析馬克思的正義觀。在現在看來,他們對于馬克思正義的學說可能會有些荒謬,但在當時卻可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如葛德文的正義學說一樣,雖有缺陷與不足,但是卻留給我們豐富的倫理與實踐價值。
首先,葛德文的功利主義的正義思想在《政治正義論》中表現明顯。這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相通的。他們所要求社會達到的最終目標都是追求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目的是一致的。其次,不同的人對于正義標準的不同理解,不可避免的受環境與個人偏好的影響等思想在馬克思那里也是可以找到相關言論的。最后,在當時,資本主義對大眾的剝削的社會下,提出無政府主義與反對暴行也是一種進步,符合時代潮流,是從啟蒙運動到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過渡。對羅伯特·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不容置疑的影響。
但是其功利主義學說(或者說當時所有的功利主義學說)對于正義的解讀還是源于道德性,是依照人們的道德進行社會的正義反饋。而馬克思曾提出,一個制度正義與否,決定于這個制度與它所處的生產關系。顯然,正義與否的問題不應該取決于是否與“塔克—伍德”命題所主張的當時的生產關系相適應,更不可能是道德這種價值判斷,而應該看其所有制本身是否正義。再有,葛德文從權利出發闡述正義的時候,將積極權利完全否定,認為道德正義已經完全規定了我們的處事方式,我們應該服從道德的決定,對自己的東西沒有隨意處置的權利。這在當今顯然是荒謬的。權利一詞本身就是對主體性的一種體現與肯定,馬克思曾說“代替那存在著各種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12]我們應該從“本我”出發,發展自己。在道德與正義的范圍內,我們有權利決定自己想要做什么。最后,葛德文作為唯理主義者,反對成文制度的約束與懲罰在現如今也會使社會無法發展下去。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法與制度的約束,權利與正義的關系無法平衡,只有將權力與正義置于法的束縛下,才能統一共存。
還有,我們一直提到的所謂“一視同仁”在當時是一大進步,但在如今看來卻還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這只是形式上的權利平等,故意遮蔽了人們的能力,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性。當忽視掉身份、能力,把所有人都放在同等的機會中,人們的能力、地位的差別反而會放大。那些富有的財者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更多的財富。中產階級會慢慢質疑自己的能力,對原有的所處地位失去信心。雖然在18世紀越來越強調人性,但是現實卻是完全卸掉了人性的概念,告訴人們權利是公平的、平等的,人與人之間沒有差別,可以隨意去追求自由和利益。
對于正義,馬克思并沒有用太多的篇幅去研究,馬克思對于他的正義思想是體現在自由、平等、博愛等相關價值取向里的。這也給了我們在新時期、新環境中創新發展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空間,以適用于當今我國的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