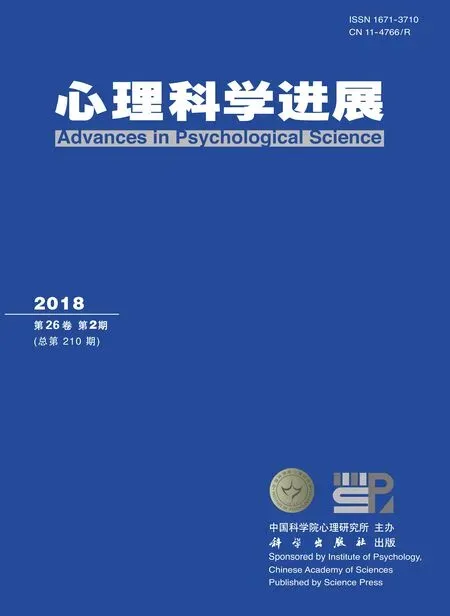兒童的社會權(quán)力認知及其與社會行為的關(guān)系*
程南華 李占星,3 朱莉琪
(1中國科學(xué)院心理研究所行為科學(xué)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101) (2中國科學(xué)院大學(xué), 北京 100049)
(3西安交通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社會心理學(xué)研究所, 西安 710049)
1 前言
社會權(quán)力(social power)一直是政治學(xué)、社會學(xué)、心理學(xué)、管理學(xué)等關(guān)注的熱門議題。Russell(1938)認為“社會科學(xué)中的基本概念是權(quán)力, 就好像物理學(xué)中的基本概念是能量一樣”, 因此社會權(quán)力存在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長期以來, 社會權(quán)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人群體, 而對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的關(guān)注較少。社會權(quán)力的差異不僅存在于成人的社會關(guān)系中, 也存在于兒童的社會關(guān)系中, 比如同伴、親子之間, 也存在著支配和被支配、權(quán)威與服從的社會權(quán)力分布。從進化的角度看, 兒童對社會權(quán)力的認知具有進化的基礎(chǔ), 準確判斷社會權(quán)力有利于個體的適應(yīng)。由于資源短缺, 社會團體中競爭時刻存在, 個體假如能夠準確判斷社會權(quán)力的相對高低, 則會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消耗與傷害(Hawley, 2016)。同時, 學(xué)步兒以及學(xué)前兒童會更加喜歡那些擁有資源的個體, 即使資源是通過強壓的、攻擊性的行為獲得的(Hawley, 2002); 他們也更喜歡與高社會權(quán)力者結(jié)成聯(lián)盟, 模仿他們、學(xué)習(xí)他們(Pettit, Bakshi, Dodge,& Coie, 1990; Roseth, Pellegrini, Bohn, van Ryzin,& Vance, 2007)。因此, 作為一種增加生存適應(yīng)性的自利策略, 早期兒童會更多地對高社會權(quán)力者表現(xiàn)出積極的偏好, 從而獲得與權(quán)力有關(guān)的社會優(yōu)勢。
社會關(guān)系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社會權(quán)力又是社會關(guān)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 正確地識別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 進而指導(dǎo)社會行為, 這是個體最基本的能力, 也是增強社會適應(yīng)的基本途徑(Hawley, 2016)。另外, 隨著近年來樸素理論的發(fā)展, 越來越多的發(fā)展心理學(xué)研究者認為, 樸素社會學(xué)(naive socialology)理論可以為兒童社會認知發(fā)展提供理論基礎(chǔ)(Hirschfeld, 2007;Rhodes, 2012, 2013)。比如, 幼兒對于人類種族間差異的推斷就伴隨著對社會類別的樸素理論的理解(Hirschfeld, 1995)。兒童的社會權(quán)力認知是社會認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感興趣于兒童早期對社會關(guān)系的樸素認識,并對社會權(quán)力影響兒童社會行為的過程加以探索。本文首先介紹社會權(quán)力的概念, 進而綜述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的發(fā)展過程及社會權(quán)力對兒童社會行為的影響, 最后展望兒童社會權(quán)力的未來研究方向。
2 社會權(quán)力的概念
社會權(quán)力的研究由來已久, 不同研究者對社會權(quán)力的界定不同。社會學(xué)研究中, Russell (1938)認為權(quán)力就是個體意圖作用的產(chǎn)物; Weber認為權(quán)力是社會關(guān)系中的高權(quán)力者在受到阻止時仍能繼續(x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可能性大小; 而 Dahl進一步明確了社會權(quán)力使得社會關(guān)系中的高權(quán)力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讓低權(quán)力者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引自Fiske & Berdahl, 2007)。這些概念反映社會權(quán)力存在于社會關(guān)系之中, 同時產(chǎn)生于社會互動的過程。社會心理學(xué)研究中, Keltner, Gruenfeld和Anderson (2003)將社會權(quán)力定義為個體通過提供或者收回資源, 實施懲罰改變他人狀態(tài)的相對能力, 是對有價值資源的不對稱控制。Fiske和Berdahl (2007)界定社會權(quán)力為對有價值結(jié)果的不對稱控制, 這里的結(jié)果不僅是資源或者是懲罰(包括了生理上的, 如健康、安全等), 還有經(jīng)濟上和社會上的結(jié)果(如社會歸屬感、共享知識、自我提升及社會信任等)。總體而言, 社會權(quán)力可以概括為在社會關(guān)系中, 高權(quán)力者對有價值資源的控制, 這個資源既包括物質(zhì)資源(如食物、金錢、經(jīng)濟能力等), 也包括社會資源(如知識、友誼、決策機會等)。
成人社會權(quán)力的研究大多依照上述定義采用“社會權(quán)力”術(shù)語進行表述, 但是兒童社會權(quán)力的研究還使用了一些其他表述的術(shù)語, 這些術(shù)語的操作定義與“社會權(quán)力”的定義大體相同, 主要包括社會支配和社會地位的部分研究。這主要是因為“社會權(quán)力”“社會支配”和“社會地位”三個概念在兒童群體中的表現(xiàn)沒有太大差異, 都是兒童對資源的不對稱控制, 以至于研究者在這些概念之間會交換使用。社會支配(social dominance)的概念最初來自于對靈長類動物的研究, 是指動物群體中個體通過強迫和鎮(zhèn)壓的方式獲得資源。后來這個概念延展到對兒童社會權(quán)力形成的研究中,指代高支配性的個體或團體戰(zhàn)勝低支配性的個體或團體, 并對他們產(chǎn)生影響(Hawley, 1999; Pun,Birch, & Baron, 2017)。社會支配常被作為權(quán)力的一種獲得方式和擁有權(quán)力之后的表現(xiàn)(Keltner et al.,2003)。比如, Hawley, Johnson, Mize和McNamara(2007)在探究 3~5歲幼兒的權(quán)力和地位對外表吸引力的影響的研究中, 將社會支配性作為兒童權(quán)力的一種形式, 并認為這是兒童獲得資源最主要的方式。另外, 社會地位也經(jīng)常與社會權(quán)力的概念在兒童研究中交換使用。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較高代表個體在社會群體中獲得他人尊重, 具有較高聲望。在兒童研究中, 通常通過同伴提名的方式進行測量(Cillessen & Rose, 2005)。有研究者認為, 8歲以前的幼兒獲得社會地位的方式是通過對玩具、游戲場地等資源的爭奪, 最后獲得資源的個體社會地位較高(Kalish, 2005; Guinote, Cotzia,Sandhu, & Siwa, 2015)。
本文中的社會權(quán)力概念在操作上定義為個體或團體對資源的非對稱的控制力(例如 Kalish,2005; Hawley et al., 2007; Guinote et al., 2015; Guinote,2017)。所以, 符合該操作定義的社會支配及社會地位的兒童研究也可納入到本綜述的范圍之中,但在表述上我們依然采用原有文獻的表達。需要指出的是, 雖然我們在綜述社會權(quán)力研究時采用了一些表述為社會地位或社會支配的文獻, 但這是由于這些相關(guān)文獻中概念所采用的操作定義與社會權(quán)力的概念類似。在以后的幼兒社會權(quán)力研究中, 我們認為對這三種概念之間的辨析及正確使用仍是非常重要的。
3 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的發(fā)展
當前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考察兒童對社會權(quán)力認知的發(fā)展:首先, 不同年齡的兒童如何基于一些線索覺察社會權(quán)力的高低; 其次, 兒童理解社會權(quán)力的獲得方式是否存在年齡上的差異。以下從這兩個方面探討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的發(fā)展。
3.1 兒童對社會權(quán)力線索的認知發(fā)展
社會權(quán)力可以通過一些線索來加以識別。現(xiàn)有研究結(jié)果表明, 盡管兒童早期經(jīng)歷的社會情境暴露以及社會互動不多, 但是他們也會通過一些線索判斷社會權(quán)力的大小。
3.1.1 權(quán)力認知的物理線索
研究表明, 1歲前的嬰兒能夠通過一些外在的物理線索來判斷社會權(quán)力的大小, 這些物理線索包括個體的物理尺寸大小(physical size)、所在團隊的成員數(shù)量多少等。通過考察嬰兒在不同情境下對物體的注視時間, 研究者可以推斷嬰兒的認知偏好。研究者給嬰兒呈現(xiàn)兩個物理尺寸不同的動畫形象爭奪同一資源的場景。結(jié)果表明, 10個月和 13個月的嬰兒在觀看物理尺寸更小的動畫形象獲得資源時比在觀看更大的動畫形象獲得資源時的注視時間更長, 而更小的 8至 9個月的嬰兒對兩種情境下的注視時間沒有差異。這說明10個月以上的嬰兒會通過個體的物理大小預(yù)期社會支配力的大小(Thomsen, Frankenhuis, Ingold-Smith,& Carey, 2011)。另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 當觀看一個所在團隊成員數(shù)量較多的動畫形象和一個所在團隊成員數(shù)量較少的動畫形象爭奪資源時, 6~9個月的嬰兒看到后者獲得資源時注視時間更長, 表明6~9個月嬰兒會預(yù)期來自于團隊人數(shù)更多的個體社會支配力大更大, 因而對超出預(yù)期的小團隊成員獲得資源時注視時間更長(Pun, Birch, & Baron,2016)。以上研究表明, 即使是6個月的嬰兒也能夠根據(jù)一些外在的線索判斷個體社會權(quán)力高低,雖然沒有更小年齡嬰兒的研究證據(jù)支持, 但是目前的研究結(jié)果足以表明一種可能性:嬰兒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對促進社會團體適應(yīng)性的社會權(quán)力的敏感性, 兒童對社會權(quán)力的認知可能具有進化上的先天性。
以上研究表明嬰兒6個月便能夠表征個體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 并且對來自不同成員數(shù)團隊的個體社會權(quán)力表征要早于對個體物理大小的社會權(quán)力表征。目前對嬰兒的研究大多通過觀察他們對不同情境的注視時間判斷他們的社會權(quán)力認知, 未來可以通過更加精確的技術(shù)手段(眼動跟蹤技術(shù))得出嬰幼兒判斷社會權(quán)力線索的權(quán)重, 比如嬰幼兒對不同面孔特征個體感知到的權(quán)力差異具體來自于哪些面孔特征。
3.1.2 權(quán)力認知的表情和姿勢線索
一些表情和姿勢線索對于我們識別社會權(quán)力的大小具有重要作用。當一個低眉順眼的人面對一個趾高氣昂的人時, 我們通常認為后者的社會權(quán)力比前者更大。一個雙手叉腰的人在面對一個向其彎腰的人時, 我們認為前者比后者的社會權(quán)力更大。近期的研究表明, 幼兒也能基于表情和姿勢線索判斷社會權(quán)力。比如, Keating和 Bai(1986)的研究表明, 4歲幼兒經(jīng)常評價眉毛較低,沒有微笑的成人相比眉毛較高面帶微笑的成人具有更高的社會權(quán)力。另一項研究表明, 5歲和6歲的幼兒僅僅通過非言語信息就能夠判定兩個成人中哪個成人的社會權(quán)力更大。這些非言語信息包括開放的姿勢、仰頭、眼神直視對方、眉毛低下、聲音低沉等等, 并且在動態(tài)的錄像中呈現(xiàn)和在靜態(tài)的照片中呈現(xiàn)效果相近。但是3~4歲幼兒需要言語線索輔助(比如高權(quán)力者需要告訴低權(quán)力者如何做)才能正確判斷兩個成人的社會權(quán)力高低(Brey & Shutts, 2015)。所以, 兒童在5歲左右便可以僅僅依靠諸如表情和姿勢線索等非言語線索判斷個體社會權(quán)力高低。
3.1.3 權(quán)力認知的社會類別線索
一些社會類別線索, 也能暗示社會權(quán)力方面的信息。比如, 由于男性經(jīng)常占據(jù)社會中較高的職位, 我們通常認為男性的社會權(quán)力比女性更大;此外, 幼兒由于經(jīng)常受到父母的管制, 所以直覺上認為兒童比成人的社會權(quán)力更低。除了個體外在表現(xiàn)的表情和姿勢等個體特征線索, 兒童也經(jīng)常采用社會類別線索思考他人并判斷社會關(guān)系,比如性別、年齡等。社會類別本身帶有很多的信息, 將個體進行分類, 兒童能夠更加有效地進行信息加工, 節(jié)約信息加工成本(Shutts, Pemberton,& Spelke, 2013)。雖然有研究表明3歲幼兒會表現(xiàn)出對于自身性別的偏好, 但是無論男生或者女生都判斷男生的社會權(quán)力要大于女生(Gülg?z, 2015),這說明 3歲幼兒能夠抑制自己的喜愛偏好, 判斷男生社會權(quán)力大于女生。3歲的兒童同時也能夠通過年齡判斷社會權(quán)力大小, 他們判斷高年齡組個體社會權(quán)力高于低年齡組個體(Charafeddine et al., 2015; Gülg?z, 2015)。
雖然目前沒有研究專門探究兒童對不同年齡和性別群體社會權(quán)力判斷的認知機制, 但是我們從資源獲得的角度推測, 3歲幼兒可能認識到男生或者年齡更大的個體身體大小及力量均更大, 所以推理他們具有更大的可能獲得資源。而 3歲幼兒、甚至更小的1歲嬰兒就能判斷獲得資源的個體社會權(quán)力更大(Mascaro & Csibra, 2012; Gülg?z& Gelman, 2017), 所以他們判斷男生以及年齡較大個體相比女生以及年齡較小個體社會權(quán)力更高。
3.1.4 權(quán)力認知的社會互動線索
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判斷社會權(quán)力的大小更多依賴于一些社會互動線索。目前的研究表明, 幼兒社會權(quán)力認知依賴的社會互動線索包括資源獲得、目標達成、下達命令、制定規(guī)則, 以及模仿等。Gülg?z和Gelman (2017)將權(quán)力有關(guān)的社會互動線索分為五類:資源獲得、目標達成、下達命令、允許/禁止他人行為、制定規(guī)則。在資源獲得線索中, 兩個孩子都想玩同樣的玩具, 最終一個孩子玩了玩具, 另一個孩子在旁邊看著, 以此暗示最終占有資源的孩子社會權(quán)力更高; 在目標達成線索中, 兩個孩子的目標產(chǎn)生沖突, 最終達成自己目標的孩子社會權(quán)力更高; 在下達命令線索中, 一個孩子告訴另一個孩子應(yīng)該做什么, 表明下達命令的孩子社會權(quán)力更高; 在允許/禁止線索中, 一個孩子能夠允許或者禁止另一個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預(yù)示著這個孩子社會權(quán)力更高; 在制定規(guī)則線索中, 一個孩子在團隊中制定規(guī)則, 要求其他的孩子按照自己設(shè)定的規(guī)則行事表明他的社會權(quán)力更高。Gülg?z和Gelman (2017)的結(jié)果表明, 對于這5個方面的線索, 兒童從3歲只能識別資源獲得與目標達成及允許/禁止他人行為的社會權(quán)力線索, 到后來 5~6歲理解社會權(quán)力的設(shè)定規(guī)則線索, 再到 7歲達到成人水平, 能夠判斷下達命令的個體社會權(quán)力更大。因此根據(jù)研究的結(jié)果我們可以推斷兒童對獲取自我利益有關(guān)(如資源獲得、目標達成)的社會權(quán)力認知要早于需要考慮他人利益的社會權(quán)力認知(如設(shè)定規(guī)則、下達命令)。
模仿也是一種暗示社會權(quán)力大小的互動線索。研究者發(fā)現(xiàn), 給兒童呈現(xiàn)一段視頻, 視頻中有兩個成人, 一個成人模仿另一個成人的坐姿、選擇圍巾的顏色、對一個物體做的動作等一系列行為, 然后讓兒童判斷這兩個成人中誰的社會權(quán)力更大, 5歲幼兒判斷被他人模仿的個體比模仿他人的個體社會權(quán)力更大, 而 4歲幼兒則不能基于模仿關(guān)系判斷社會權(quán)力(Over & Carpenter, 2015)。4歲和5歲幼兒基于模仿互動判斷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差異可能是因為5歲幼兒經(jīng)歷更多的友誼關(guān)系和更多的社會權(quán)力層級暴露。
對于更小的嬰兒而言, 他們也能夠通過社會互動中的資源獲得線索理解社會權(quán)力的大小。例如, 12~15個月嬰兒可以基于在爭奪中獲得資源以及在社會互動中占領(lǐng)他人領(lǐng)地判斷個體社會支配力更高; 并且他們能夠表征這種社會支配力為一種關(guān)系, 而不是一種個體特征, 當互動對手改變時, 嬰兒并非預(yù)期高權(quán)力者仍為之前情境中的高權(quán)力者, 而是通過新的社會情境重新進行判斷(Mascaro & Csibra, 2012)。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1~3歲的學(xué)步兒能夠在早期的互動過程中根據(jù)自己與對手的歷史輸贏情況判斷自己與他人的社會支配性關(guān)系(Hawley & Little, 1999; Pellegrini et al., 2007)。另外, 3歲幼兒根據(jù)社會互動的結(jié)果(兩次沖突爭斗中均勝利、兩次沖突斗爭最后都玩了自己想玩的玩具、獲得更多的資源)就能夠推斷誰更具有社會支配性(Charafeddine et al., 2015)。
以上社會權(quán)力線索的實證研究表明, 兒童對于社會權(quán)力不同線索的認知發(fā)展表現(xiàn)出與與人類進化一致的進程(Hawley, 1999)。兒童最開始識別更加有利于個體適應(yīng)性的早期適應(yīng)(early adaptation)線索, 比如團體人數(shù)多少, 個體身體大小, 資源獲得和目標達成等, 到后來慢慢識別有利于社會互動的權(quán)力線索, 需要表征社會道德責(zé)任以及個體間共同意圖的能力, 比如模仿與被模仿關(guān)系、下達命令、制定規(guī)則等, 因此這些社會權(quán)力方面的認知被認為是人類社會關(guān)系進化過程中相對近代的適應(yīng)機制(relatively recent adaptation;Rakoczy & Schmidt, 2013)。
綜上所述, 從進化學(xué)的角度看, 兒童認知社會權(quán)力的線索大致從早期適應(yīng)性線索(團體人數(shù)多少、個體身體大小、資源獲得和目標達成等)往后來的相對近代適應(yīng)性線索(表情與姿勢線索、模仿與被模仿關(guān)系、下達命令、制定規(guī)則等)發(fā)展。從社會關(guān)系的角度看, 隨著年齡的增長, 兒童越來越多地卷入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中, 他們更加需要理解不同場景中的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但是這些研究只是發(fā)現(xiàn)了年齡之間的差異, 并沒有很好地解釋經(jīng)驗在社會權(quán)力認知中的具體作用機制, 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究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年齡差異背后的經(jīng)驗影響機制。
3.2 不同年齡兒童對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的認知差異
社會權(quán)力可以通過支配他人的方式獲得, 也可通過贏取聲望的方式獲得(Cheng, Tracy, Foulsham,Kingstone, & Henrich, 2013)。基于支配力(dominancebased)的策略是指個體通過強制力、強壓以及暴力等反社會方式獲得權(quán)力; 而基于聲望(prestigebased)的策略則是個體通過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獲得他人的尊重, 欽佩和贊賞等親社會方式獲得權(quán)力。兒童能否區(qū)分這兩種不同的獲得方式?Gülg?z和Gelman (2017) 將社會權(quán)力效價分為惡意的和善意的社會權(quán)力表現(xiàn), 惡意的兩種社會權(quán)力表現(xiàn)是個體通過強權(quán)的方式獲得權(quán)力, 得到資源, 達成目的, 而善意的社會權(quán)力表現(xiàn)則是個體獲得資源獲得達成目的的過程包括了他人的主動謙讓以及主動達成公平。結(jié)果發(fā)現(xiàn), 3~9歲兒童對于惡意的社會權(quán)力認知判斷優(yōu)于善意的社會權(quán)力判斷, 暗示較小年齡兒童理解惡意的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好于理解善意的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
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 兒童對于這兩種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的認知會表現(xiàn)出差異, 表現(xiàn)為最初認可基于支配性的權(quán)力獲得到后來越來越偏好于認可基于聲望的權(quán)力獲得。研究發(fā)現(xiàn), 學(xué)步兒和學(xué)前兒童的社會權(quán)力絕大部分是爭奪資源中獲得,包括對物品所有權(quán)的爭執(zhí)、對游戲領(lǐng)地的占領(lǐng)等強制行為(Strayer & Strayer,1978)。雖然這些行為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強壓和攻擊行為, 但是這個年齡段的兒童認可這樣的社會權(quán)力的獲得方式, 會對通過強制方式獲得社會權(quán)力的個體更多的社會關(guān)注, 表現(xiàn)出喜歡與聯(lián)盟偏好, 并且分給他們更多的資源(Hawley, 2002; Roseth et al., 2007; Grueneisen& Tomasello, 2017)。到兒童5歲左右, 他們會面臨更加復(fù)雜的關(guān)系, 表現(xiàn)出對他人更多的關(guān)注、讓步、分享和幫助行為, 以此增加他們在團體中的支配力(Hawley & Little, 1999)。這個時期是兒童價值觀以及抽象表征能力開始形成的階段, 他們對通過強壓方式獲得社會權(quán)力的個體的態(tài)度會越來越消極。等到 8歲, 兒童對這兩種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的認知就表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兒童在實際社會關(guān)系中, 將這兩種獲得權(quán)力的策略區(qū)分開來:一些兒童通過純粹的強壓行為來獲得權(quán)力, 會變成不受歡迎的欺凌者; 而另一些兒童則會通過受大家喜愛的親社會方式獲得社會權(quán)力(Hawley & Little, 1999; Hawley, 2002)。8 歲兒童已經(jīng)不認為通過強壓的方式是一種積極的方式。因此, 那些通過支配性策略以及攻擊性行為獲得社會權(quán)力的個體會逐漸受到同伴的排斥。有研究表明, 雖然小學(xué)一年級的男孩偏愛具有支配性的同伴, 即使他們表現(xiàn)出很多的攻擊行為, 但是到了三年級, 他們和成人一樣不喜歡基于支配力策略的同伴(Dodge, Coie, Pettit, & Price, 1990; Pettit et al., 1990)。同時, 這個年齡階段的兒童更加認可基于聲望策略的高社會權(quán)力者, 研究也表明, 這個年齡階段的兒童會對受支配者(社會權(quán)力較低的個體)比支配者(社會權(quán)力較高個體)分配更多的資源(Charafeddine et al., 2016)。他們也認為基于聲望策略的獲得權(quán)力個體可以為集體帶來利益。因此對于能夠提升集體利益的高社會權(quán)力者, 兒童會分給他們更多的資源 (Kogan et al., 2011)。
綜上, 通過支配策略(強壓以及攻擊性的反社會行為)獲得社會權(quán)力可能只是年幼兒童普遍接受的規(guī)則。但是這種社會規(guī)則的有效性隨著年齡的增加而不斷降低, 而通過聲望策略(來自他人的尊重與贊賞)的社會權(quán)力在較大年齡的兒童中得到更多的認可。
4 社會權(quán)力對兒童社會行為的影響
之前綜述表明, 3歲甚至更小的嬰幼兒就能基于一些線索判斷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 那么當他們理解了社會權(quán)力之后, 能否運用社會權(quán)力信息指導(dǎo)自己的社會行為呢?目前研究主要考察了社會權(quán)力對兒童以下三個方面社會行為的影響:
4.1 選擇性信任
兒童在進行學(xué)習(xí)或者社會判斷的過程中, 當面對不同個體給出的陳詞時, 會有選擇性地采納特定個體的意見, 這就是選擇性信任(selective trust, Kinzler, Corriveau, & Harris, 2011)。研究表明社會支配性高低作為具體情境下的個體特征屬性, 會影響兒童選擇不同權(quán)力個體提出的陳詞(Bernard et al., 2016; Castelain, Bernard, van der Henst,& Mercier, 2016)。研究者通過兩個實驗情境操縱兩個人物形象的社會支配力的不同:在身體優(yōu)勢情境下, 兩個小朋友搶奪同一個玩具, 最終得到玩具的小朋友預(yù)示著社會權(quán)力更高; 在決策情境下, 兩名小朋友爭奪放置衣柜位置的決策權(quán), 一個小朋友想把衣柜放在黃色的床邊, 另一個小朋友想把衣柜放在棕色床邊, 最終擁有決策權(quán)的小朋友預(yù)示著社會權(quán)力更大。隨后在陳詞選擇階段呈現(xiàn)另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情景(一條丟失的小狗的主人尋找小狗), 上述故事情境中的兩個小朋友給出相反的兩種答案(丟失的狗去了馬路左邊或者馬路右邊), 被試選擇他們更加相信哪位小朋友的答案。結(jié)果發(fā)現(xiàn), 無論社會支配性是因為身體優(yōu)勢獲得還是從決策能力體現(xiàn), 3歲和5歲的幼兒都會更多地采納高支配個體的陳詞(Bernard et al., 2016; Castelain et al., 2016)。關(guān)于社會支配性影響兒童的選擇性陳詞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從社會適應(yīng)的角度而言, 兒童采納支配者的陳詞可能是為了迎合支配者, 同意支配者的觀點使得支配者更加喜歡自己, 因此他們傾向于采納支配者的陳詞。這類似于兒童會采納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而非少數(shù)人的陳詞, 當大多數(shù)人給出的陳詞和他們自己的判斷相違背的時候也會聽從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Bernard, Harris, Terrier, & Clément, 2015), 聽從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比聽從少數(shù)人的意見更加有利于社會適應(yīng)。另一種解釋從能力角度闡述, 兒童相信社會支配力更大的個體是因為社會支配力更大代表能力更強, 比如有研究表明兒童會判斷社會支配力更高的個體能力更強(Charafeddine et al.,2015), 因此更加相信支配力高的個體的陳詞。
今后的研究需要注意社會權(quán)力, 能力與選擇性信任之間的關(guān)系, 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 兒童首先判斷誰的社會權(quán)力更大, 然后是誰的能力更大, 再給出他們對選擇性信任的預(yù)測。另一種情況是, 兒童根據(jù)描述的場景直接判斷誰的能力更強, 誰的社會權(quán)力更大, 然后再同時根據(jù)權(quán)力與能力高低的結(jié)果進行選擇信任的對象。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在呈現(xiàn)的引導(dǎo)材料中將能力和權(quán)力區(qū)分開來。
4.2 資源分配行為
另一種研究者關(guān)注較多的社會行為是幼兒的資源分配行為。資源分配任務(wù)通常的做法是, 給幼兒呈現(xiàn)一些資源, 要求其在不同個體之間進行分配, 或者是給幼兒一些可供選擇的資源分配方案, 幼兒作為第一方角色(分配方案與自己的資源獲得有關(guān))或者第三方角色(分配方案與自己的資源獲得無關(guān))進行資源分配或分配方案的選擇。然而幼兒作為第一方角色在社會權(quán)力情境中的資源分配研究可能因為操作范式上的困難, 很難操縱幼兒自身的高低社會權(quán)力, 目前并未有研究進行實證考察。雖然在成人研究中, 研究者通常采用角色扮演(隨機分配被試為經(jīng)理人或員工, 前者為高權(quán)力者, 后者為低權(quán)力者)或者回憶法(給被試呈現(xiàn)權(quán)力定義, 讓被試回憶寫出自己對他人擁有權(quán)力的具體事件)、語義喚起(利用詞干補筆的方法,給高權(quán)力者的單詞中, 與權(quán)力有關(guān)的單詞占大多數(shù), 而控制者的單詞與權(quán)力無關(guān))等方法操縱權(quán)力獲得(見綜述:魏秋江, 段錦云, 范庭衛(wèi), 2012), 但這些方法均不適用于幼兒。但是幼兒即使很小就能理解權(quán)力概念, 也還不能根據(jù)權(quán)力概念很好地還原場景, 建立心理權(quán)力感。因此目前兒童社會權(quán)力對資源分配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幼兒作為第三方時的資源分配。
兒童作為第三方角色時, 兒童對于不同社會權(quán)力大小的個體的資源分配結(jié)果有兩種可能的假設(shè):匹配假設(shè)(Match Hypothesis)和補償假設(shè)(Compensate Hypothesis)。匹配假設(shè)是指幼兒在社會權(quán)力情境中能夠識別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 他們?yōu)榱吮3诌@種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 從而匹配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和資源分配, 也就是分配給權(quán)力高的個體更多資源, 而分給權(quán)力低的個體更少資源。補償假設(shè)則是指兒童識別了社會權(quán)力的差異之后, 認為這種社會權(quán)力的獲得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為了補償這種不公平, 他們會給社會權(quán)力低的個體分配更多的資源, 而給社會權(quán)力高的個體分配更少的資源。基于以上的兩種假設(shè), Charafeddine等人(2016)探究了3~8歲兒童在社會支配情境下的資源分配行為。研究發(fā)現(xiàn), 兒童在社會支配性情境下的資源分配模式出現(xiàn)了年齡上的差異。具體而言, 3歲和 4歲幼兒更偏好支配者, 分配給他們更多的資源, 符合匹配假設(shè); 5歲幼兒對支配者和受支配者的資源分配沒有顯著差異; 8歲兒童則分配給受支配者更多的資源, 以平衡社會支配性所帶來的不公平感, 符合補償假設(shè)。
對于社會權(quán)力影響兒童資源分配行為的發(fā)展研究, 研究者需要同時考慮他們各個心理能力的發(fā)展進程, 其中有幾個重要的社會性特點可能是社會權(quán)力認知影響資源分配行為的主要變量, 包括兒童的共情能力、公平敏感性、對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的認知、以及對權(quán)威的認知等因素。隨年齡增加, 兒童會表現(xiàn)出對于受害者(比如社會情境中的受支配者)更多的關(guān)心(Eisenberg, Fabes, &Spinrad, 2006; Malti, Gummerum, Keller, & Buchmann,2009), 同時會對公平與否更加敏感(Fehr, Bernhard, &Rockenbach, 2008; Shaw, Choshen-Hillel, & Caruso,2016), 以及他們越來越不認可基于支配的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見前文“3.2 不同年齡兒童對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的認知差異”的闡述; Hawley, 1999),因此年長兒童會分配給低權(quán)力者更多的資源。
綜上所述, 兒童作為第三方角色時表現(xiàn)出從學(xué)前期匹配權(quán)力關(guān)系, 分給高權(quán)力者更多資源,到小學(xué)期為了公平補償社會權(quán)力分配, 對較低權(quán)力個體分配更多資源的轉(zhuǎn)變。目前的研究只是基于已發(fā)現(xiàn)的年齡差異推斷兒童基于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進行資源分配的機制, 但是具體哪些因素影響兒童基于社會權(quán)力進行資源分配的過程, 還有待進一步的實驗證實。未來的研究需要更加具體地驗證, 社會性能力的發(fā)展影響兒童基于社會權(quán)力進行資源分配的內(nèi)在過程。另外, 目前的研究只是針對兒童作為第三方角色時, 在高低不同的權(quán)力個體之間分配資源的情景。當兒童自我利益卷入時, 他們會如何分配資源還不得而知。未來可以從以下方面考慮兒童自我利益卷入時, 社會權(quán)力對資源分配的影響。首先, 從權(quán)力的來源出發(fā), 探索幼兒群體中高低社會權(quán)力的操縱范式。Toffler(1990)認為, 在支撐權(quán)力的支柱—暴力、財富和知識—當中, 知識可以產(chǎn)生更高質(zhì)量的權(quán)力, 因為它不僅可用于懲罰、獎賞、勸說, 甚至可用于轉(zhuǎn)化集體生產(chǎn)力, 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因此, 通過知識能力的反饋, 研究者可以操縱幼兒的權(quán)力感。其次, 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其他影響因素的混淆,比如幼兒公平敏感性、權(quán)力角色帶來的責(zé)任感等。以資源獲得的方式操縱社會權(quán)力, 可能引入高權(quán)力兒童因為公平感補償?shù)蜋?quán)力兒童的混淆因素。比如, 高權(quán)力幼兒分配更多資源可能不是因為他們的權(quán)力感, 而是公平敏感性的發(fā)展讓他們覺得,之前是自己獲得資源, 這次需要通過輪流的方式調(diào)整資源分配(Grueneisen & Tomasello, 2017)。當分配不同權(quán)力角色給兒童時, 研究者還需要考慮這樣可能引入兒童責(zé)任感的混淆因素, 比如高權(quán)力兒童分配更多資源, 可能不是因為角色所賦予的權(quán)力, 而是角色所賦予的責(zé)任導(dǎo)致。
4.3 親社會行為
親社會行為是指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自發(fā)行為(Eisenberg et al., 2006)。從進化的角度看, 個體通過親社會行為進行社會性投資, 從而獲得聲望與尊重, 更有利于生物適應(yīng)。非人類靈長類動物的研究表明低社會地位的個體會增加社會性投資從而增大生物適應(yīng)性(Sapolsky, 2005)。兒童的研究也表明, 4~5歲幼兒的親社會行為受社會地位的影響。研究者給兩名兒童呈現(xiàn)有吸引力和無吸引力的玩具各一個, 讓兒童通過爭奪有吸引力玩具的支配權(quán)獲得較高社會地位, 然后給每位幼兒 5個貼畫作為獎勵, 并詢問幼兒是否捐贈貼畫給另一位在醫(yī)院的小朋友。研究結(jié)果表明, 相比獲得有吸引力玩具的“高社會地位”的兒童, 得到無吸引力玩具的“低社會地位”兒童捐贈更多的貼畫, 并且這種親社會行為與道德推理以及抑制控制能力無關(guān)(Guinote et al., 2015)。從進化的角度看, 低社會地位可能是一種生存劣勢, 這種劣勢需要個體通過親社會行為增加他們的聲望, 獲得更高的社會權(quán)力、社會支持以及與高權(quán)力者聯(lián)盟的可能性,從而減少自己的生存壓力。
雖然相比高社會地位個體, 低社會地位個體會表現(xiàn)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 但是當個體自己面對高地位或低地位者時, 他們的親社會行為是否會發(fā)生變化?研究者采用公平分配的范式研究他們對不同地位個體的親社會傾向, 根據(jù)兒童選擇公平方案(1, 1:表示自己得1個, 對方也得1個)的動機設(shè)置三種資源選擇情境, 親社會情境(1, 1和1, 0兩種方案, 選擇公平方案暗示兒童更加親社會)、妒忌情境(1, 1和1, 2兩種方案, 選擇公平分配表明兒童不允許對方比自己得到的更多)和分享游戲(1, 1和2, 0, 選擇公平分配暗示兒童損失自己的利益與對方進行分享)。研究發(fā)現(xiàn), 6~11歲兒童在親社會情境中, 不管對方的社會地位高低, 更多地選擇親社會的分配(1, 1); 在妒忌情境中, 兒童傾向于讓高地位的對方(校長和老師)得到更多(1, 2); 而當需要損失自己的利益時(1, 1和2, 0), 兒童卻更加愿意與地位較低的接受者(校園看護者)進行分享(1, 1) (Mcguigan, Fisher, & Glasgow, 2016)。
從上面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 不管是較低社會權(quán)力幼兒對陌生人, 還是幼兒對較高社會權(quán)力的對手, 都會表現(xiàn)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因此, 低社會權(quán)力表現(xiàn)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可能是重要的生物適應(yīng)性策略。但是研究也發(fā)現(xiàn)當面對不同社會權(quán)力高低的對手卻需要損失自己利益的時候,兒童卻表現(xiàn)出對于低社會權(quán)力者更多的親社會行為。然而, 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與親社會行為的關(guān)系目前尚且需要更多的研究證據(jù), 不管是社會權(quán)力的認知還是親社會行為本身都會隨著年齡的變化而不斷地發(fā)展變化, 而單純某個年齡段的關(guān)系并不足以得出完整的結(jié)論。目前成人的研究中,大量的證據(jù)表明社會地位, 社會階層或者是社會權(quán)力降低了個體的親社會行為(如 Guinote et al.,2015; Piff, Kraus, C?té, Cheng, & Keltner, 2010),但是兒童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更加確切的證據(jù)。幼兒社會權(quán)力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可能表現(xiàn)出與成人不一樣的模式, 同情等其他情緒社會性能力隨年齡變化上的發(fā)展差異可能調(diào)節(jié)社會權(quán)力對幼兒親社會行為的影響。
5 小結(jié)與展望
人類在嬰兒期開始便可以識別不同的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 從最初根據(jù)與生物適應(yīng)有關(guān)的物理線索和資源獲得線索再到后來發(fā)展為注重社會互動的線索, 兒童能夠越來越適應(yīng)更加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另外, 他們也對不同的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表現(xiàn)出隨年齡變化的差異, 從學(xué)前時期認可基于支配性的社會權(quán)力獲得到學(xué)齡期越來越不認可基于支配性的社會權(quán)力獲得策略。通過對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認知, 兒童能夠更好地指導(dǎo)他們的社會行為,包括更加相信高權(quán)力者的陳詞; 隨年齡增長, 對低權(quán)力者越來越多的資源分配偏好; 社會權(quán)力越高表現(xiàn)出更少的親社會行為。總結(jié)之前研究的結(jié)果與趨勢, 未來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探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考察影響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的內(nèi)在機制。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屬于樸素社會學(xué)的一部分,可能受到其他認知發(fā)展的影響, 比如兒童的樸素心理學(xué)理論(如, 心理理論)。理解社會情境下個體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 需要兒童識別不同個體的愿望與意圖以及他們是否達成目標等(Hirschfeld, 2007),這些可能需要兒童具有心理理論能力與觀點采擇能力。同時有研究表明執(zhí)行功能等高級認知能力能夠調(diào)節(jié)個體自動化刻板印象的表達(Payne,2005)。兒童高級認知能力發(fā)展(例如執(zhí)行功能等)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對于群體社會權(quán)力有關(guān)的社會認知。隨著高級認知能力的提高, 兒童對于群體的社會權(quán)力認知會超越之前的群體偏好(比如超越了對自己性別群體的偏好, 判斷男生的社會權(quán)力高于女生, Gülg?z, 2015)。另外, 兒童的個體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其社會權(quán)力認知, 比如幼兒價值觀的差異。有研究表明, 低社會權(quán)力個體比高社會權(quán)力個體表現(xiàn)出更加親社會的生活目標與價值觀(Piff et al., 2010), 學(xué)齡兒童價值觀的差異可能會影響他們對于社會權(quán)力獲得方式的認知差異。
第二, 探究社會權(quán)力對兒童社會行為的過程機制。目前針對兒童社會權(quán)力與社會行為的研究大多數(shù)僅發(fā)現(xiàn)不同的社會權(quán)力者的社會行為存在差異, 但是這個差異的過程與中間機制還不清楚。兒童對不同社會權(quán)力個體的資源分配存在年齡差異, 這些差異可能與一些兒童社會化的因素有關(guān), 比如公平敏感性、同情、權(quán)力獲得策略等。首先, 兒童公平敏感性隨年齡增加逐漸提高, 特別是8歲左右的兒童對于有利自己的不公平分配也會拒絕(Blake, McAuliffe, & Warneken, 2014)。而社會權(quán)力本身就代表著資源配置的不平等, 兒童可能會更多分配資源給資源獲得較少的社會權(quán)力較低個體(Li, Spitzer, & Olson, 2014)。另外, 同情的發(fā)展可能也會導(dǎo)致兒童更多同情社會權(quán)力較低個體, 從而給他們更多的資源或者表現(xiàn)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等(如Hamlin, Wynn, Bloom, & Mahajan,2011)。再者, 學(xué)前兒童以及青少年早期兒童獲得社會權(quán)力的方式既包括基于斗爭的支配性策略,也包括基于能力的聲望策略(見Cheng et al., 2013),之前的研究僅探究了基于支配力策略獲得的社會權(quán)力, 基于聲望獲得的社會權(quán)力對兒童社會行為的影響可能表現(xiàn)出不一樣的結(jié)果。
第三, 注重考察文化因素及兒童早期社會互動環(huán)境對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發(fā)展的影響。從社會文化因素考慮, 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公平敏感性可能會影響兒童的社會權(quán)力認知。比如, 與在傳統(tǒng)瑪雅文化中成長的 4歲瑪雅兒童相比, 在西方文化下成長的美國 4歲兒童更加注重公平(Morris,2015)。雖然研究表明相比低權(quán)力者的陳詞, 他們都更加相信高權(quán)力者的證言(Bernard et al., 2016;Castelain et al., 2016), 但是研究并沒有比較這些不同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下兒童社會權(quán)力認知的差異。從社會學(xué)習(xí)的角度考慮, 兒童早期經(jīng)歷的成人價值觀傳遞可能影響他們對于社會權(quán)力的認知。例如, 對嬰兒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嬰兒能夠理解來自成員數(shù)量更大的團隊的個體比來自小團隊的個體社會權(quán)力更大。但是成人的研究卻發(fā)現(xiàn), 在自我報告的外顯測量下, 成人會判斷更小團隊中的個體比更大團隊中的個體更可能具有高社會權(quán)力和能力, 而在內(nèi)隱測量下表現(xiàn)出與嬰兒一致的理解(Cao & Banaji, 2017)。這一結(jié)果預(yù)示著兒童隨著年齡的增加, 社會學(xué)習(xí)的不斷深入, 他們的權(quán)力認知可能會發(fā)生變化, 但是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另外, 兒童早期學(xué)習(xí)社會規(guī)則、形成價值觀的過程中, 從小接觸社會權(quán)力層級較多的兒童可能更早理解和認知社會權(quán)力, 比如在成員等級比較森嚴的家庭中長大的兒童, 多兄弟姐妹兒童等。因此可能成人和嬰兒社會權(quán)力判斷之間的差距也來自于社會價值和社會規(guī)則的不斷強化和學(xué)習(xí), 從而改變兒童的社會權(quán)力感知。
兒童早期的親子互動經(jīng)驗也可能影響他們對社會權(quán)力關(guān)系獲得策略的認知。有研究表明受虐待兒童比普通兒童在任何年齡段都更可能是恃強凌弱的欺凌者(Teisl, Rogosch, Oshri, & Cicchetti,2012)。父母教養(yǎng)實踐中體罰可能會增加他們對基于支配力的社會權(quán)力獲得策略的認可程度, 從而導(dǎo)致他們更多地采用這樣的方式獲得權(quán)力。因此,怎樣的親子互動過程更有利于兒童習(xí)得符合社會規(guī)范的權(quán)力獲得策略也值得未來的研究深入探討。
魏秋江, 段錦云, 范庭衛(wèi).(2012).權(quán)力操作范式的分析與比較.心理科學(xué)進展, 20(9), 1507–1518.
Bernard, S., Castelain, T., Mercier, H., Kaufmann, L., van der Henst, J., & Clément, F.(2016).The boss is always right: Preschoolers endorse the testimony of a dominant over that of a subordinat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52, 307–317.
Bernard, S., Harris, P., Terrier, N., & Clément, F.(2015).Children weigh the number of informants and perceptual uncertainty when identifying object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36, 70–81.
Blake, P.R., McAuliffe, K., & Warneken, F.(2014).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fairness: The knowledge-behavior gap.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8(11), 559–561.
Brey, E., & Shutts, K.(2015).Children use nonverbal cues to make inferences about social power.Child Development,86(1), 276–286.
Cao, J., & Banaji, M.R.(2017).Social inferences from group siz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0,204–211.
Castelain, T., Bernard, S., van der Henst, J., & Mercier, H.(2016).The influence of power and reason on young Maya children's endorsement of testimony.Developmental Science, 19(6), 957–966.
Charafeddine, R., Mercier, H., Clément, F., Kaufmann, L.,Berchtold, A., Reboul, A., & van der Henst, J.B.(2015).How preschoolers use cues of dominance to make sense of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16(4), 587–607.
Charafeddine, R., Mercier, H., Clément, F., Kaufmann, L.,Reboul, A., & van der Henst, J.B.(2016).Children’s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social dominance situation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11), 1843–1857.
Cheng, J.T., Tracy, J.L., Foulsham, T., Kingstone, A., &Henrich, J.(2013).Two ways to the top: Evidence that dominance and prestige are distinct yet viable avenues to social rank and influenc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1), 103–125.
Cillessen, A.H.N., & Rose, A.J.(2005).Understanding popularity in the peer system.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2), 102–105.
Dodge, K.A., Coie, J.D., Pettit, G.S., & Price, J.M.(1990).Peer status and aggression in boys' groups: Developmental and contextual analyses.Child Development, 61(5), 1289–1309.
Eisenberg, N., Fabes, R.A., & Spinrad, T.L.(2006).Prosocial development.In N.Eisenberg (Ed.),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pp.646–718).Hoboken, NJ: Wiley.
Fehr, E., Bernhard, H., & Rockenbach, B.(2008).Egalitarianism in young children.Nature, 454(7208), 1079–1083.
Fiske, S.T., & Berdahl, J.L.(2007).Social power.In A.W.Kruglanski & E.T.Higgins (Eds.),Social psychology: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pp.678–692).New York,NY: Guilford Press.
Grueneisen, S., & Tomasello, M.(2017).Children coordinate in a recurrent social dilemma by taking turns and along dominance asymmetrie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2),265–273.
Guinote, A.(2017).How power affects people: Activating,wanting, and goal seeking.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68, 353–381.
Guinote, A., Cotzia, I., Sandhu, S., & Siwa, P.(2015).Social status modulate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galitarianism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adult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12(3), 731–736.
Gülg?z, S.(2015).Developing a concept of social power relationships(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
Gülg?z, S., & Gelman, S.A.(2017).Who's the boss?Concepts of social power across development.Child Development, 88(3), 946–963.
Hamlin, J.K., Wynn, K., Bloom, P., & Mahajan, N.(2011).How infants and toddlers react to antisocial oth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8(50), 19931–19936.
Hawley, P.H.(1999).The ontogenesis of social dominance:A strategy-base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Developmental Review, 19(1), 97–132.
Hawley, P.H.(2002).Social dominance and prosocial and coercive strategies of resource control in preschool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6(2),167–176.
Hawley, P.H.(2016).Eight myths of child social development: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power, aggression, and social competence.In D.C.Geary & D.B.Berch (Eds.),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pp.145–166).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awley, P.H., Johnson, S.E., Mize, J.A., & McNamara, K.A.(2007).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preschoolers: Relationships with power, status, aggression and social skills.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5(5), 499–521.
Hawley, P.H., & Little, T.D.(1999).On winning some and losing some: A social relations approach to social dominance in toddlers.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5(2), 185–214.
Hirschfeld, L.A.(1995).Do children have a theory of race?Cognition, 54, 209–252.
Hirschfeld, L.A.(2007).Folksociology and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culture.Intellectica, 46-47, 191–206.
Kalish, C.(2005).Becoming status conscious: Children's appreciation of social reality.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8(3), 245–263.
Keating, C.F., & Bai, D.L.(1986).Children's attributions of social dominance from facial cues.Child Development,57(5), 1269–1276.
Keltner, D., Gruenfeld, D.H., & Anderson, C.(2003).Power,approach, and inhibi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110(2),265–284.
Kinzler, K.D., Corriveau, K.H., & Harris, P.L.(2011).Children’s selective trust in native-accented speakers.Developmental Science, 14(1), 106–111.
Kogan, A., Saslow, L.R., Impett, E.A., Oveis, C., Keltner,D., & Rodrigues, S.S.(2011).Thin-slicing study of the oxytocin receptor (OXTR) gene and the evalu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prosocial disposition.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8(48), 19189–19192.
Li, V., Spitzer, B., & Olson, K.R.(2014).Preschoolers reduce inequality while favoring individuals with more.Child Development, 85(3), 1123–1133.
Malti, T., Gummerum, M., Keller, M., & Buchmann, M.(2009).Children's moral motivation, sy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Child Development, 80(2), 442–460.
Mascaro, O., & Csibra, G.(2012).Representation of stable social dominance relations by human infant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18), 6862–6867.
McGuigan, N., Fisher, R., & Glasgow, R.(2016).The influence of receiver status on donor prosociality in 6- to 11-year-old children.Child Development, 87(3), 855–869.
Morris, I.(2015).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ver, H., & Carpenter, M.(2015).Children infer affiliative and status relations from watching others imitate.Developmental Science, 18(6), 917–925.
Payne, B.K.(2005).Conceptualizing control in social cognition:How executive functioning mod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automatic stereotyp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4), 488–503.
Pellegrini, A.D., Roseth, C.J., Mliner, S., Bohn, C.M., van Ryzin, M., Vance, N.,...Tarullo, A.(2007).Social dominance in preschool classrooms.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121(1), 54–64.
Pettit, G.S., Bakshi, A., Dodge, K.A., & Coie, J.D.(1990).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ominance in young boys' play groups: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6), 1017–1025.
Piff, P.K., Kraus, M.W., C?té, S., Cheng, B.H., & Keltner,D.(2010).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784.
Pun, A., Birch, S.A.J., & Baron, A.S.(2016).Infants use relative numerical group size to infer social dominan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3(9), 2376–2381.
Pun, A., Birch, S.A.J., & Baron, A.S.(2017).Foundations of reasoning about social dominance.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1(3), 155–160.
Rakoczy, H., & Schmidt, M.F.H.(2013).The early ontogeny of social norms.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7(1), 17–21.
Rhodes, M.(2012).Na?ve theories of social groups.Child Development, 83(6), 1900–1916.
Rhodes, M.(2013).How two intuitive theories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7(1), 12–16.
Roseth, C.J., Pellegrini, A.D., Bohn, C.M., van Ryzin, M.,& Vance, N.(2007).Preschoolers' aggression, affiliation,and social dominance relationships: An observational,longitudinal study.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5(5),479–497.
Russell, B.(1938).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New York:Norton.
Sapolsky, R.M.(2005).The influence of social hierarchy on primate health.Science, 308(5722), 648–652.
Shaw, A., Choshen-Hillel, S., & Caruso, E.M.(2016).The development of inequity aversion: Understanding when(and why) people give others the bigger piece of the pie.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0), 1352–1359.
Shutts, K., Pemberton, C.K., & Spelke, E.S.(2013).Children's use of social categories in thinking about peopl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Cognition &Development, 14(1), 35–62.
Strayer, J., & Strayer, F.F.(1978).Social aggression and power relations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Aggressive Behavior, 4, 173–182.
Teisl, M., Rogosch, F.A., Oshri, A., & Cicchetti, D.(2012).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social dominance as a function of age and maltreatment experience.DevelopmentalPsychology, 48(2), 575–588.
Thomsen, L., Frankenhuis, W.E., Ingold-Smith, M., & Carey, S.(2011).Big and mighty: Preverbal infants mentally represent social dominance.Science, 331(6016), 477–480.
Toffler, A.(1990).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Bantam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