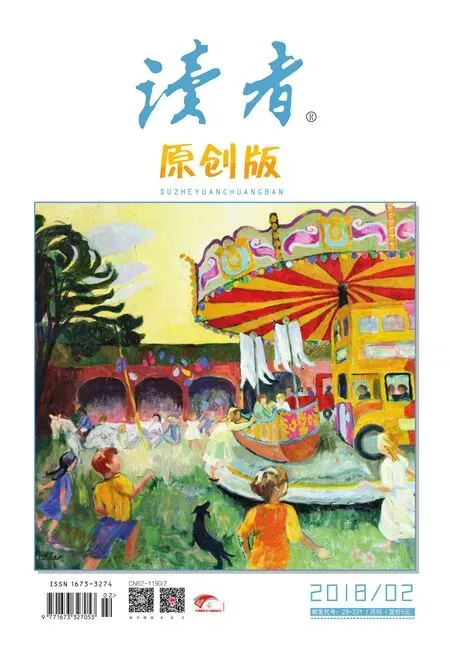嘻哈風(fēng)云
文 | 張 彰

B-Boy
紐約第三大道自北向南,從南布朗克斯區(qū)的福德姆路開始,穿過(guò)哈萊姆河,一直到曼哈頓最繁華的上東區(qū)。這條南布朗克斯地區(qū)最繁忙的主干道,在布朗克斯區(qū)內(nèi)是雙向行駛車道,出了布朗克斯,則只能北行。它構(gòu)成了對(duì)布朗克斯區(qū)的某種隱喻—這里是放逐之地,從上東區(qū)一路向北,分別住著富人、中產(chǎn)階層和窮人。如果一個(gè)人已經(jīng)往北去了南布朗克斯,他的人生想要再調(diào)頭到南方去,幾乎是不可能的。
20世紀(jì)40年代,這里住滿了猶太人和在莫里斯港找事情做的白人藍(lán)領(lǐng)。這些居民自20世紀(jì)50年代開始,便陸續(xù)搬離了布朗克斯,越富有的人搬得越靠南。他們的遷移,一方面是為了分享城市建設(shè)的紅利,搬到消費(fèi)更高、設(shè)施更完備的地區(qū)去;另一方面,可能是為了躲避絡(luò)繹不絕的新居民—那些來(lái)到布朗克斯討生活的黑人和拉丁裔居民。這場(chǎng)大規(guī)模的遷移活動(dòng)被歷史學(xué)家稱作“白人群飛”。在短短20年的時(shí)間里,黑人在布朗克斯區(qū)居民中的比重,由不足1/3上升到超過(guò)2/3。
這些新移民很快就發(fā)現(xiàn),被原有居民拋棄的,不僅僅是布朗克斯區(qū)的土地,還有房產(chǎn)、商業(yè)、服務(wù)機(jī)構(gòu)……除了設(shè)備簡(jiǎn)陋的貧民公寓,新移民很難在這里找到其他設(shè)施,當(dāng)然也找不到工作。這種情況因?yàn)闄M貫布朗克斯區(qū)的高速公路的修建而更加嚴(yán)重。為了保證這項(xiàng)大型工程能順利完工,數(shù)以千計(jì)的公寓、商店、辦公樓被迫拆遷,它們的擁有者理所當(dāng)然地選擇了更好的街區(qū)—20世紀(jì)60年代,布朗克斯區(qū)的地價(jià)還不到上一個(gè)10年的一半。毫無(wú)希望、野草一般的生活,帶給人們的只有絕望。
留給新布朗克斯人的謀生手段并不多,很多人為了騙取保險(xiǎn)金而縱火,這使布朗克斯一度成為紐約火災(zāi)發(fā)生率最高的地區(qū)。一些孩子迷上了打籃球,他們渴望像歐文那樣,飛翔在球場(chǎng)上空,拿下百萬(wàn)年薪—雖然他們出了球場(chǎng),連一份周薪90美元的工作都找不到。另外一些人做起了偏門生意—有些人賣起了海洛因,那個(gè)時(shí)代美國(guó)政府對(duì)毒品異常寬容;有些人則做起了老鴇和皮條客。做偏門生意當(dāng)然需要幫派的保護(hù),更何況,來(lái)自波多黎各、牙買加、哥倫比亞等地的黑人兄弟們也需要?jiǎng)澐值乇P。
很快,幫派成了社區(qū)的權(quán)力中心,出現(xiàn)了原始骷髏、野蠻浪人、標(biāo)槍隊(duì)、皇家巫師、七皇冠、黑桃?guī)偷缺姸鄮团伞团尚值苷袚u過(guò)市,白天和別的幫派火拼,照管自家生意;到了晚上,則要把自己這一天掙到的錢全花出去。入夜,年輕人紛紛朝163街和希望大道進(jìn)發(fā),在那里,一個(gè)名為“貧民窟兄弟”的波多黎各幫派在播放音樂。他們的設(shè)備極其簡(jiǎn)陋—裝在路燈柱子上的會(huì)議用PA音響,電吉他放大器上插滿唱機(jī)。幫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本杰·梅倫德斯,是一名吉他手,后來(lái)還組建了一支同名樂隊(duì)。
若說(shuō)“貧民窟兄弟”和其他幫派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們一直在尋求一種和平處理幫派爭(zhēng)端的方式。1971年,“貧民窟兄弟”的另一位創(chuàng)始人“黑本杰”,在阻止幫派火并時(shí)被殺,死時(shí)只有25歲。幫派的兄弟們沒有試圖為他報(bào)“血仇”(這種古老的復(fù)仇方式至今仍然在非洲沿用),而是開了一場(chǎng)“鋤頭大道和平會(huì)議”,地點(diǎn)在男孩俱樂部。這次會(huì)議召集了部分官員、警察和幾十個(gè)幫派的頭目,建立了大家都能夠認(rèn)可的談判機(jī)制,維護(hù)了街頭的和平。
之所以能夠通過(guò)談判解決問(wèn)題,并非完全由于“貧民窟兄弟”跨地區(qū)乃至跨國(guó)家的非凡影響力,而是因?yàn)椴祭士怂箙^(qū)的地盤已經(jīng)劃分完畢。無(wú)數(shù)幫派兄弟發(fā)現(xiàn),一夕之間,他們的憤怒再也無(wú)處發(fā)泄,他們苦練許久的“中國(guó)功夫”,只能運(yùn)用到舞蹈中。他們一度成了各類派對(duì)的常客。在和平會(huì)議召開之后,出現(xiàn)在“貧民窟兄弟”的派對(duì)上,于他們更像是一項(xiàng)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wù)”。這些兄弟總是冷冷地掃視跳舞的人群,在舞曲播放的間隙,下場(chǎng)去表演雜技般的復(fù)雜舞步—最初只有類似哥薩克舞的腳步動(dòng)作,后來(lái)加入了中國(guó)武術(shù)的踢技、巴西戰(zhàn)舞卡潑耶拉和瘋克舞步。舞蹈代替了拳頭,成了幫派之間對(duì)話的主要方式,這些在舞曲間隙表演的兄弟被叫作breaking boy,也就是如今人們所熟知的B-Boy。
DJ、Rap和MC
那次會(huì)議上,黑桃?guī)鸵苍凇:谔規(guī)偷睦洗蟆胺侵尥酢卑喟退貞浧鹬暗膸团苫鸩r(shí)是這么說(shuō)的:“如果你說(shuō)錯(cuò)了一句話,一場(chǎng)小型戰(zhàn)爭(zhēng)就會(huì)打響,而且會(huì)蔓延至整個(gè)布朗克斯,乃至整個(gè)紐約。一些大的幫派,如‘原始骷髏’和‘野蠻浪人’的勢(shì)力范圍很大。”20世紀(jì)70年代初期,曾有一次幫派火并持續(xù)了92天。相比之下,用舞蹈來(lái)解決問(wèn)題要文明得多。班巴塔后來(lái)成了最早為B-Boy制作Break beat(組成節(jié)奏的一系列鼓點(diǎn))的DJ,他號(hào)召兄弟們一致對(duì)外,被稱為“教父”。
另一個(gè)經(jīng)常被提及的派對(duì)地點(diǎn),是塞德維克街的一處簡(jiǎn)易公寓。女士的入場(chǎng)費(fèi)為25美分,男士的為50美分。如此低廉的價(jià)格,當(dāng)然無(wú)法讓你得到白人迪斯科舞廳里的那種水準(zhǔn)的招待,來(lái)這里的人,是沖著“酷海格”來(lái)的。這個(gè)年輕人是牙買加籍,就出生在“雷鬼之父”鮑勃·馬利所在的那個(gè)街區(qū)—牙買加首都金斯頓川奇區(qū)的貧民窟。“酷海格”13歲時(shí)來(lái)到美國(guó)。白天,這個(gè)身高1.95米的大漢是露天球場(chǎng)上兇狠的“海格力斯”(古希臘神話中的大力神);夜晚,則變成了碟機(jī)背后最受歡迎的DJ。他喜歡播放舞曲減弱時(shí)只有節(jié)奏和打擊樂的那部分,他細(xì)心地在每張唱片上做了標(biāo)記,一張放完接另一張,因此他的派對(duì)很受B-Boy的歡迎。
沒有音樂多少有些單調(diào),而且他“打碟”的水準(zhǔn)實(shí)在無(wú)法和弗朗西斯·格拉索這樣的天才DJ相比。加之跳舞的人常常需要適應(yīng)新唱片的節(jié)奏,為了不冷場(chǎng),他學(xué)著像牙買加的祝詞人那樣,用帶有煽動(dòng)性的喊話來(lái)帶動(dòng)氣氛。DJ的基本功—速混技術(shù),則要靠約瑟夫·薩德勒來(lái)完成。
“酷海格”的音響功率最大,班巴塔收藏的唱片最豐富,“閃電大師”薩德勒的技術(shù)最好,而他們的小兄弟—“大法師”西奧多·利文斯通則發(fā)明了通過(guò)摩擦碟片和調(diào)解平衡推桿制造有節(jié)奏的摩擦聲的技術(shù),也就是“搓碟”,那年他還不到14歲。薩德勒不甘示弱,發(fā)明了在節(jié)奏中短暫混入人聲和器樂的技術(shù),還第一個(gè)引入鼓機(jī)(一種音樂編輯設(shè)備),他把鼓機(jī)叫作Beat Box,也就是B-box。至此,“打碟”、跳舞、音樂,都有了,就差“說(shuō)”了。
1977年是一個(gè)糟糕的年份,這一年紐約市財(cái)政緊縮,大量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停擺,布朗克斯區(qū)深受其害,房屋無(wú)人修理,垃圾無(wú)人清掃,免費(fèi)舞會(huì)成了人們逃避現(xiàn)實(shí)的好去處。這類舞會(huì)大多在室外舉辦,有時(shí)是為了宣傳,有時(shí)是有新人要出頭,遂召集比賽。每個(gè)DJ都會(huì)請(qǐng)幾個(gè)朋友到場(chǎng)來(lái)幫忙維持秩序,“酷海格”經(jīng)常帶去的朋友是他的牙買加哥們兒科克拉·洛克。洛克的嘴皮子很溜,專門負(fù)責(zé)在“酷海格”換碟時(shí)調(diào)節(jié)氣氛,他經(jīng)常大喊:“搖起來(lái),別停下!”這句話被認(rèn)為是第一句Rap專用唱詞,洛克也被看作是第一位MC。
這一招被喜歡鉆研技術(shù)的薩德勒學(xué)去了,他找到了“牛仔”“克里奧小子”和“梅里美”做他的MC。“牛仔”的風(fēng)格更像是傳統(tǒng)的牙買加祝詞人,而后兩位則天生愛耍貧嘴,又擅長(zhǎng)模仿紐約的電臺(tái)DJ。漸漸地,布朗克斯區(qū)出現(xiàn)了越來(lái)越多的DJ和MC,他們用1977年紐約大停電那晚?yè)尩降脑O(shè)備、音響、唱片和心中燃燒的憤怒、激情、野心,從“嘻哈三杰”—“酷海格”、班巴塔、薩德勒手中,承接了一種全新的亞文化形式—嘻哈。
- 讀者·原創(chuàng)版的其它文章
- 神回復(fù)
- 交流
- 編輯有話說(shuō)
- 那些在為時(shí)代唱挽歌的人
- 段味
- 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