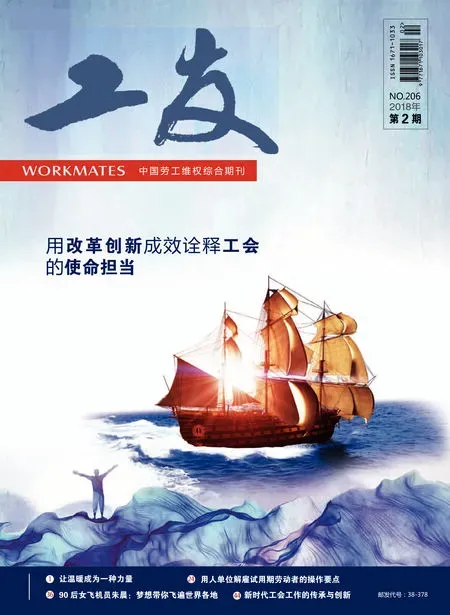家有“忙年”人
文_苗連貴

妻大眼,圓臉,天生一副笑模樣,人說這是福相,其實妻是“做”的命。妻娘家老姊妹多,她家的慣例,三十團年夜,都在大姐家聚首。那么團年飯呢?這個任務落在妻身上。妻文化不高,沒有別的專長,卻燒得一手好菜,能者多勞,自然年年就由她“代庖”了。
妻做事好喝茶,好喝那種苦澀的釅茶,常受油煙熏的人都愛喝釅茶。因此,大姐把她們單位發的好茶給她釅釅地泡上一大瓷缸,妻喝茶做事,越發不知疲累。從臘月二十六七開始,擇洗刨切,蒸煮煎炸,直到三十夜,妻的一手菜閃亮上桌,雖不能說珍饈美饌,卻也風味不同于尋常。第一道菜是燒全魚,燒得焦黃,淋了醬汁,撒著蔥花,見之使人喉頭吞津,但都不得動箸,這叫“看魚”,取“年年有余”的彩頭;第二道是丸子,有4樣:黃燜丸子,珍珠丸子,豆腐丸子,藕丸子,取四季團圓之意;接著,炸豬排,炸藕夾,爆雞丁,燴三鮮……一道道上來,堆得碗重盤疊,盡大人孩子吃,大嚼大啖,風卷殘云。
妻從不上桌,一者忙得顧不上,再者被油煙一熏沒了胃口,三來沒有上桌的習慣——平時在家,她也是往碗里夾上菜,掇個小杌子與左鄰右舍湊在一起,邊吃邊說笑——只是大家在給她敬酒時,她才站在我身后,就我的盞子抿一小口酒,吃一筷子菜“意思”一下,然后又到廚房忙她的未了之事。
一頓年夜飯吃下地,妻回家就倒在了床上,口里哼哼唧唧說這里疼那里酸。我只得給她揉肩捶腰搓背,不無埋怨:“做事悠著點,哪個像你,做起來不要命!”她口里說“不累”,但一會,便沉沉睡去,連“春晚”都割愛了。
從初一開始,我們去各家拜年,呈上禮品,姊妹們說笑一陣后,妻看時候不早,便系上圍腰,一頭鉆進了廚房。妻沒有當“坐客”的習慣,親戚們也都習慣于等妻來燴菜。于是,廚房里開始演奏鍋瓢碗盆交響曲,客廳里則麻將稀里嘩啦大合唱。如此這般,拜了東家拜西家,直至初六初七,年事才告一段落。
回到家,我說:“幾天里忙來忙去都是忙人家的,我們家自己的年還沒有過呢。”“看你嘴饞的,早給你預備好啦。”妻知道我愛喝湯,年前就貯備了藕和排骨,藕煨排骨湯,妻的廚藝一絕。我說:“以后再煨吧,你也該歇兩天了。”妻執意要煨,便連夜生起煤爐。湯宜用煤爐煨,文火慢煨,一直把藕煨到綿爛,把肉煨得與骨頭脫節,這湯才喝得有滋有味。湯要煨一宿功夫才到家,妻夜里披衣起來幾次給爐子添煤加炭。我喝妻煨的湯,總有一份感動在里頭。
我曾問妻:“你成天做那么多事不嫌煩累?”她反問我:“你每天讀書、搖筆桿子煩不煩,累不累?”在她看來,她做的與我做的一樣,是一種愛,一種享受,而且永無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