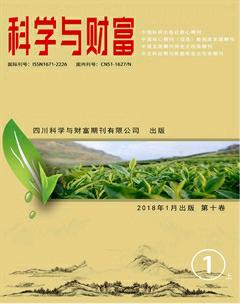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認定中的若干爭議問題
賀川
摘要: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對法律的完善程度也在進一步強化當中。職務侵占罪中的“利用職務便利”包括多個方面,是職務侵占罪必備的行為要件,同時,在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便利”的認定成為困擾司法實務部門的疑難問題。因此,文章將從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的概述切入,對其認定過程中容易出現的誤區進行區分,分析產生誤區的原因,并對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的認定進行簡述,以期能幫助司法部門對其進行準確的認定,維護社會的穩定。
關鍵詞: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問題
引言
職務侵占罪是一種經濟型犯罪,主要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其在職務上的便利,將單位財產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一種不良現象。職務侵占罪是一種比較典型的職務性犯罪,在其罪行的認定方面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應提高對其認定過程的重視程度,明確并完善其法律規定,對其進行準確的認定。
1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的概述
1.1對“職務”合法性的認識
關于職務侵占罪中的職務合法性認識,是指行為人從事一定的職務行為具有合法的依據和來源,也就是法律中明確的犯罪行為人所利用的職務是經公司、企業依合法程序授權賦予的,這是職務侵占罪職務權源的唯一狀態。職務來源如不合法,就不能成立職務犯罪,此時能否成立職務犯罪應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行為人以犯罪為目的騙取或者獲取職務的,不能成立職務犯罪;如果在騙取職務,并利用其在職務上便利實施犯罪行為的,即可構成職務犯罪,如行為人偽造履歷的目的是騙取職務,但在履職期間又產生貪污受賄故意并實施了一系列的職務犯罪行為的,且不符合“在非法占有他人財物之前即已經持有他人財物”的侵占犯罪定型性,這種情況不影響貪污受賄罪的成立,因此,不成立職務侵占罪。
1.2“利用職務便利”的內涵
利用職務便利是指行為人利用自己職務范圍內的職權和地形所形成的有利條件,及經手、管理財務的便利條件。從職務的含義來說,職務是指工作中所擔任的事情,所謂工作,就是體力和腦力的活動,因此,無論是公務還是勞務,都屬于職務的范疇。凡是因刑法中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實施的犯罪是由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從事的公務活動的便利來獲取利益的,如貪污罪、受賄罪等,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是指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工作上擁有的主管、管理、經手本單位財務的權利。
2“利用職務便利”在職務侵占罪認定過程中容易出現的誤區
2.1“利用職務便利”與貪污罪的區別
“利用職務便利”的認定與貪污罪是不同的,因此,職務侵占罪的犯罪主體是從貪污罪中分離出來的。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中的“職務便利”看似與職務侵占罪中的“職務便利”沒有較大區別,但從內涵進行考慮,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罪狀中所描述的“職務”均可理解為為公務,因其兩罪的主體都是國家工作人員,所從事的公務是帶有國家管理性質的活動,同時,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都發生在公權的行使過程中,侵犯的客體主要是公職人員職務活動的廉潔性,即公務的廉潔性,因此貪污罪的職務中不包括勞務。而職務侵占罪則不盡相同。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中的主體為單位內所有為單位工作的員工,無論聘用形式與承擔的職務,都可以成為期職務侵占罪的犯罪主體,且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在從事勞務時利用經手單位財產的便利條件,違背了工作職責的要求,同時還將財產據為己有的行為,同樣會侵占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財產所有權以及誠實信用。
2.2“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的區別
“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中同樣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利用職務便利”是利用工作的便利,而“利用工作便利”是指行為人因為工作關系熟悉作案環境,并憑借其身份進出單位,輕而易舉的接近作案目標等便利條件。為了對其進行準確的區分,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5年2月28日《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第的10條,對侵占罪客觀方面的表述為“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便利”。同時,在1997年刑法修訂時將該《決定》中的“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修改為“利用職務便利”,體現出了立法者控制職務侵占罪規制范圍的意圖。“利用工作便利”的范圍要廣于“利用職務便利”。比如,單位的保潔人員在打掃辦公室時,趁辦公室無人之機將屋內財物竊為己有的行為,雖然保潔人員承擔著為單位打掃的責任,但其竊取辦公室財物的行為并并不是打掃的職務,而是基于其為單位打掃,接近單位財物的便利,故其行為系盜竊。
2.3“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業務便利”的區別
在職務侵占罪的基礎上加重了對業務侵占罪的處罰,在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執行中確定,對罪名的規定將刑法第271條的罪名確定為職務侵占罪之前,我國也有學者認為刑法第271條的規定即為業務侵占罪。不僅反映了行為人犯罪行為與其自身工作權利、權力之間的具體關系,同時還能便于與刑法第382條中的“職務”相區別,業務可以包括一般性的勞務活動,從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外的業務侵占罪也以已合法持有的業務上的財產為成立條件,這與我國刑法規定的職務侵占罪是不同的。
2.4單位的勞務人員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
勞務,指的是單純的體力勞動或者技術勞動。勞務的內涵是勞動事務,而勞動的范圍是十分廣泛的,任何工作都可以說是勞動。有一部分觀點也有把公務與勞務進行比較的,認為公務活動的本質特征是管理性。但是,如果一種活動是在國家事務中組織、領導、協調等具有管理性的活動,那這種活動就是公務,而不是勞務。反之,如果一種活動即使屬于國家事務,但它不具有相應的管理性,那它就不是公務,而是勞務。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單位勞務人員都應排除在職務侵占罪的主體之外,因其從事管理性事務的勞務人員中很有可能成為職務侵占罪主體。例如單位的貨物押運員、倉庫保管員、出納、會計等,他們的活動是保管貨款貨物,具有管理性,但是對于像售貨員、售票員等職業的人,對于他們是否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還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如果售貨員擁有對商品價格在一定范圍內的決定權,那么他實際上對貨物就享有支配權,其工作就有一定的管理性,他就可以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但如果他對貨物并沒有支配權,只是按照定價將貨物銷售,收取顧客的貨款,然而貨款是交由出納的,這種工作就完全沒有管理性的事務,不能構成職務侵占罪。同樣,商場中的售貨員如對商品沒有支配權,一旦商品丟失,就要承擔賠償責任,但他們并沒有從事具有管理型的勞務,因此,在界定其是否構成職務侵占罪主體,就是要具體分析其是否組織、領導、協調、支配、經手某種事務、事物或財物。
3對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產生誤區的原因
3.1缺乏法律指導和制約
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作為犯罪客體,則是對財產權利的侵害。由于論者將該罪的客體僅僅理解為對財產權利的侵犯,“利用職務便利”只屬于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而非客體要件。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單一法益論”都不會從“利用職務”因素中解讀出法益職務的廉潔性或者公共權力的嚴肅性以及有效性。而由此造成的“利用職務便利”其實質與犯罪的實質客體脫節,缺乏法益的指導和制約,無法運用法益的解釋機能對其作實質的解讀和細致的框定,從而產生了誤區,影響人們的判斷。
3.2雙重法益的解讀立場
在對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的行為進行理解時,一定要在法益的指導和制約下對其作實質的解讀,不能將不具備法益侵害的行為解釋為構成要件的行為,同時,也不能將侵犯法益的行為排除在刑法的評價之外。違反前者可能會導致罪及無辜,侵犯公民自由;而違反后者會放縱犯罪,破壞社會秩序。因此,應在雙重法益的指導和制約下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作實質的解讀和細致的框定,以糾正以“單一法益論”為思維根基的誤解和誤判。
4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的認定
4.1對于主體方面的認定
對主體的認定也是職務侵占罪認定的重要依據,以此可以將其分為公務性工作人員和非公務性工作人員。根據我國所有制的性質,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應該是非國有性質的一些企業或單位。在對職務侵占罪的認定中,要根據案情的具體情況來對其主體進行界定。因此,我國現在社會的經濟發展,法律應該利用各種手段對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進行控制,從而保障國家和社會財產的完整。
4.2對于客體方面的認定
職務侵占罪的客體主要指的是那些被我國刑法所保護的,而又被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一般認為職務侵占罪的客體主要指的是公司、企業或單位的財產所有權,還包括出資人的所有權、公司的財務制度等。在對職務侵占罪客體進行界定時,一定要注意雖然職務侵占罪發生在單位內部,但是同時也影響到了社會秩序的穩定,而其對社會秩序穩定的影響并不是直接的,其犯罪主體中也并不包括犯罪行為的間接侵害或者具有威脅性的社會關系。此外,還有一些職務侵占罪,對單位的一些管理或者財務制度的侵犯具有偶然性的特點,因此不會對其造成很大的影響。
結束語
總而言之,要想準確的對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進行認定,一定是要緊扣構成職務侵占罪的各個要素,弄清職務侵占罪中的主體、客體的同時,還要嚴謹分析在職務侵占罪認定的過程中可能或已經出現的各種問題,并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來處理對職務侵占罪的認定工作,從而才能健全和完善法律的明文規定,便于國家和人民更好的行使權力。
參考文獻:
[1]盧建平,邢永杰.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認定中的若干爭議問題[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2,02:97-104.
[2]張鋒學.職務侵占罪的認定與處理研究[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6,04:127-129.
[3]劉偉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司法誤區與規范性解讀——基于職務侵占罪雙重法益的立場[J].政治與法律,2015,01:50-59.
[4]楊幗英.論我國刑法中職務侵占罪的認定和疑難問題[J].法制博覽,2015,20:22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