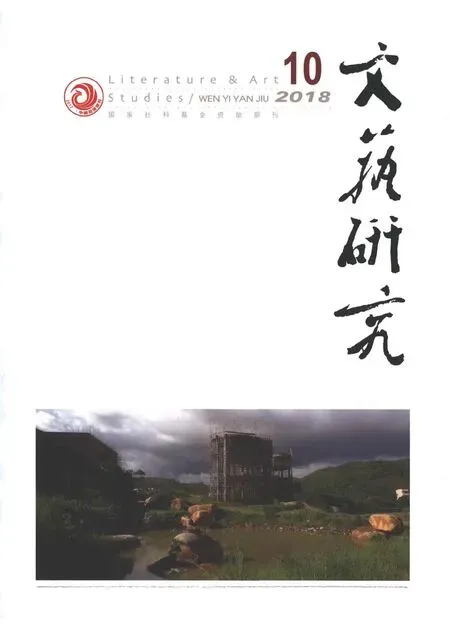論作為農(nóng)耕美學(xué)之典范的青花瓷
張 檸
引 論
瓷、絲、茶,曾是構(gòu)成西方人想象中國(guó)的三個(gè)代表性符號(hào)。本文所論青花瓷,更是一種具有典型中國(guó)特色的物品。它是一種器物,代表一種高級(jí)燒制工藝,也是一種通過(guò)白底藍(lán)花紋樣顯現(xiàn)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和趣味。青花瓷濫觴于唐宋,鼎盛于元明,經(jīng)清代康乾時(shí)期再次光大,自清末以降開(kāi)始衰落①。然而它并沒(méi)有消失,而是繼續(xù)在當(dāng)代文化和生活中時(shí)隱時(shí)現(xiàn)。在20世紀(jì)末的近三十年間,曾一度幾乎被人遺忘的青花瓷仍以三種形式出現(xiàn):第一是商品,商貿(mào)市場(chǎng)上的中低端商品(日常生活用品);第二是禮品,高端的饋贈(zèng)之物(當(dāng)代藝術(shù)瓷器);第三是古董,打著明清古瓷旗號(hào)的仿古陶瓷制品。商貿(mào)市場(chǎng)中的瓷器門市,也在用“國(guó)禮”“古董”來(lái)做廣告宣傳詞。不可否認(rèn),其市場(chǎng)前景并不樂(lè)觀。可以說(shuō),作為禮品和古董,“青花瓷”還在,而作為與日常生活相關(guān)的商品,它幾乎要在生活實(shí)踐和人們的觀念中消失。就其當(dāng)下處境而言,人們?nèi)栽谠噲D通過(guò)歷史敘述而不斷使青花瓷擺脫作為容器的一般使用功能,增加其附加價(jià)值或強(qiáng)化其文化意義。
由于當(dāng)代器物越來(lái)越趨向于物欲化、商品化、功能化,導(dǎo)致作為概念的“青花瓷”正在被工業(yè)流水線上生產(chǎn)之器物的純粹使用功能掏空。而與傳統(tǒng)的生活藝術(shù)、古老的手工印跡相關(guān)的“青花瓷”概念,正瀕臨消亡。同時(shí),曾被瓷器所淘汰的自然材質(zhì),比如木竹和金屬等又卷土重來(lái)。新型人工材質(zhì),如現(xiàn)代玻璃②、樹(shù)脂、塑料及納米材料等等,也在通過(guò)現(xiàn)代審美風(fēng)格和新穎造型,搶占越來(lái)越大的市場(chǎng)份額。更有審美趣味上的變化,年輕一代突然離“青花”而去,朝著代表宋代審美風(fēng)格的汝窯和柴燒奔去。從商品的實(shí)用性角度看,青花瓷并沒(méi)有優(yōu)勢(shì),那么,它的優(yōu)勢(shì)是在展示價(jià)值、收藏價(jià)值還是象征價(jià)值上或成疑問(wèn)。而一件物品的存在價(jià)值成了疑問(wèn),同時(shí)又無(wú)法舍棄它,那么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dòng)賦予它一種意義,這也是所謂收藏品的本質(zhì)。
大致在2010年前后,青花瓷或有一種試圖復(fù)興的跡象。這一跡象或緣于兩個(gè)偶然事件,一是歌手周杰倫廣為傳唱的歌曲《青花瓷》,它伴隨著古典婉約風(fēng)格的歌詞以及略帶憂傷的曲調(diào),將“青花瓷”重新植入年輕一代心中;二是北京奧運(yùn)會(huì)的“中國(guó)風(fēng)”表演,青花瓷的紋樣在時(shí)裝和女性瓷瓶般的身體上游移,還有在北京地鐵站和街頭展示的青花瓷裝置藝術(shù)等。國(guó)力上升和奧運(yùn)競(jìng)技的勝利,通過(guò)表演、展示和聯(lián)想,與帶有典型中國(guó)風(fēng)格的古老器物聯(lián)系在一起。大眾文化傳播事件,主導(dǎo)性審美意識(shí)形態(tài)的表現(xiàn)形式,這兩種外力能否促使青花瓷復(fù)興?這個(gè)問(wèn)題的背后,隱藏著一種歷史焦慮:歷時(shí)千年的古老器物在當(dāng)代日常生活中瀕臨消失,是不是意味著一種傳統(tǒng)的消亡?它存在于當(dāng)代生活中的價(jià)值和意義是什么?
質(zhì)而言之,青花瓷隱含著農(nóng)耕文明時(shí)代的理性智慧、審美趣味和精神符碼。它對(duì)材料的純潔性、制作工藝的精致性、制作流程的嚴(yán)密性包括燒制條件和火候等方面的要求,都是極端嚴(yán)格的;它對(duì)品相和質(zhì)地的期待也極其苛刻,如著名的“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罄”③的標(biāo)準(zhǔn)。如同鄉(xiāng)土社會(huì)對(duì)個(gè)體的道德要求一樣,總是指向一種高標(biāo)準(zhǔn)的道德實(shí)踐、統(tǒng)一的風(fēng)格學(xué)、嚴(yán)格的審美趣味,以及這些標(biāo)準(zhǔn)在日常實(shí)踐中的典范性。可以說(shuō),青花瓷的紋飾、色彩和造型也是中國(guó)傳統(tǒng)農(nóng)耕美學(xué)風(fēng)格的集中體現(xiàn),而且,這些承載文化信息的符號(hào),不是一般的繪畫(huà)圖案,它是對(duì)繪畫(huà)的二度制作,其中包含著對(duì)“青料”④的化學(xué)工藝處理的尖端技術(shù)。青花瓷,與其說(shuō)是一種硬質(zhì)的器皿,不如說(shuō)是一種凝固了的人文理想。它仿佛成了一個(gè)想象“中國(guó)”(China/china,中國(guó)/瓷器⑤)的起源神話,并為這個(gè)神話提供了考古學(xué)的依據(jù)。
對(duì)這種神話的分析,將模仿地質(zhì)學(xué)的地層分析法,自下而上(這里是自內(nèi)而外)進(jìn)行結(jié)構(gòu)和符號(hào)解析:一級(jí)結(jié)構(gòu)是作為其物質(zhì)形式所包含的自然材質(zhì)及其工藝,二級(jí)結(jié)構(gòu)是作為其文化形式所呈現(xiàn)的象征系統(tǒng),三級(jí)結(jié)構(gòu)是作為其社會(huì)形式所呈現(xiàn)的各種功能(包括美學(xué)功能及其衍生功能),最后是因功能蛻變所呈現(xiàn)的當(dāng)代征候。
一、物質(zhì)形式:青花瓷材質(zhì)的符號(hào)分析
燒制青花瓷的自然材質(zhì),是一種特殊的泥土,含長(zhǎng)石的高嶺土和瓷石粉碎而成的瓷土⑥。經(jīng)過(guò)大約攝氏1300度以上的高溫煅燒,由泥土塑造而成的柔軟器皿胚胎,轉(zhuǎn)化為堅(jiān)硬如石的、材料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凝固的特殊器皿。為解析其所蘊(yùn)涵的精神現(xiàn)象,我們先要分析泥土的意義。
作為自然物質(zhì)的泥土,其成分雜亂無(wú)章,主要是由礦物巖石風(fēng)化而成的細(xì)小沙粒,以及含有機(jī)物的粘土組成。它因“亂”而活躍,而不是因“治”而終結(jié)。所以,泥土最大的特征,就是具有生長(zhǎng)性。泥土→植物→動(dòng)物→尸體→泥土,是一個(gè)生長(zhǎng)和死亡的循環(huán)鏈條。動(dòng)物和植物死亡后,經(jīng)過(guò)生物化學(xué)作用而被泥土吸納,然后再生長(zhǎng)出新的微生物和植物。這種帶有神奇的造化力量的生長(zhǎng)性,它的吸納、包容、凈化功能,它“生長(zhǎng)—死亡”的周期循環(huán)特點(diǎn),正是農(nóng)耕文明最深刻的精神內(nèi)核,也是其相應(yīng)的價(jià)值觀念體系之所以誕生的最獨(dú)特的母體。但是,在農(nóng)耕文明世世代代對(duì)泥土和生死循環(huán)的迷戀和承擔(dān)背后,一直存在著一種超越生死循環(huán)的沖動(dòng)。其表現(xiàn)形式就是對(duì)“肉身不死”的渴望,對(duì)歷史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的追求,對(duì)永恒不變的物質(zhì)的迷戀,進(jìn)而去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它。于是,“火”這種特殊而易得的物質(zhì),成了追求超越的重要中介。在社會(huì)或歷史層面上,通過(guò)戰(zhàn)爭(zhēng)之火,消滅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的“雜質(zhì)”,以此來(lái)鞏固血緣宗法制基礎(chǔ)上的“家國(guó)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性;在身體層面上,通過(guò)煉丹術(shù)的丹爐之火,燒去自然物的雜質(zhì),提煉出永恒不變的精華,再服食而納入衰朽易變的肉體,以達(dá)到長(zhǎng)生不老的目的;在物質(zhì)層面上,通過(guò)煅燒之火,熔化和剔除泥土中易變的物質(zhì),煅造出一種恒久不變的器物。因此,對(duì)泥土的肯定和依賴,以及對(duì)泥土的否定和超越,構(gòu)成了農(nóng)耕文明的兩個(gè)重要維度。這兩個(gè)維度,是對(duì)立統(tǒng)一的矛盾,也是靜止而封閉的農(nóng)耕文明的基本矛盾⑦。
終結(jié)泥土的生長(zhǎng)性,逃避“生—死”循環(huán)的歷史宿命,發(fā)明一種永恒不朽的物質(zhì),是農(nóng)耕文明唯一的超越性實(shí)踐活動(dòng)。同時(shí),這種實(shí)踐并不是靠純粹想象力誘發(fā)的詩(shī)學(xué),而是對(duì)某些永恒不變的自然物質(zhì)的模仿的工藝實(shí)踐。這種自然物就是“寶石”(特殊的巖石)——水晶(特殊的石英)、黃寶石(黃玉)、紅藍(lán)寶石(剛玉)、鉆石(金剛石)⑧。這類特殊巖石因成分純凈、無(wú)雜質(zhì)而寶貴,因結(jié)構(gòu)穩(wěn)定、晶型單一而恒久不變,從而成為代表永生的稀有物(最典型的就是鉆石)。它們都是泥土的結(jié)晶和升華,是自然的造化,是永恒和不朽的象征。與泥土的生長(zhǎng)和循環(huán)相比,特殊巖石就是死亡和終結(jié)。實(shí)際上,其中蘊(yùn)藏著一種深刻的悖論:泥土的生長(zhǎng)性包含了死亡和衰朽的信息,巖石的死亡形式則包含了超越死亡的永生信息。用生的形式展示死,用死的形式顯示生,這種兩歧性,正是農(nóng)耕文明的深層精神密碼。
經(jīng)人工煅燒而成的器物,是對(duì)具有永恒性的巖石(寶石)的模仿。這種實(shí)踐,不是發(fā)現(xiàn),而是發(fā)明。它人為地改變了自然材質(zhì)的結(jié)構(gòu)和屬性:利用“火”對(duì)泥土的熔煉和提純,對(duì)化學(xué)物質(zhì)的熔煉和再造,使泥土的生死循環(huán)規(guī)律,終結(jié)在一個(gè)永恒的結(jié)晶上。因此,對(duì)泥土的關(guān)注和把玩,既是原初人(包括兒童)的典型游戲,也是一個(gè)古老的神話原型。玩泥巴就是一種生死循環(huán)的游戲⑨。燒泥巴則是對(duì)這種生死循環(huán)的終結(jié)。女?huà)z“摶黃土造人”的傳說(shuō),對(duì)文明而言何其重要!但它同時(shí)是一個(gè)關(guān)于誕生和泥土的神話,也是一個(gè)類似兒童玩泥巴的游戲,是女?huà)z閑來(lái)的消遣。女?huà)z“煉五色石以補(bǔ)蒼天”的傳說(shuō),是對(duì)生死循環(huán)宿命的超越性想象,是一個(gè)通過(guò)煅燒和冶煉達(dá)到穩(wěn)定秩序、終結(jié)混亂形式的工序⑩。
制陶工藝,就是對(duì)“摶黃土”和“煉五石”神話的粗糙模仿,并將兩道本不相干的、性質(zhì)不同的程序,在同一空間之內(nèi)聯(lián)成一體。在實(shí)踐過(guò)程中,通過(guò)淡化游戲色彩,凸顯技術(shù)特征,使之成為一種文明的標(biāo)識(shí)。制瓷工藝,無(wú)疑是對(duì)制陶工藝的超越。經(jīng)歷了自商周到唐宋的歷史變遷,瓷工藝逐漸成熟,抵達(dá)了農(nóng)耕文明時(shí)代陶瓷工藝的巔峰。今天陶瓷工藝的進(jìn)步,并沒(méi)有改變瓷器燒制的基本程序?,改變的只是實(shí)施這些程序的工具。比如,改燒松木為燒電,制坯的人工旋轉(zhuǎn)改為機(jī)電動(dòng)力,觀察火候的秘密經(jīng)驗(yàn)換成溫度計(jì)或電子控制的標(biāo)準(zhǔn)程序等等。
從一般技術(shù)邏輯角度看,制陶和制瓷沒(méi)有本質(zhì)差別,它們都包含了“摶黃土”和“煉五石”兩大工序。而青花瓷燒制工藝,還增加了兩道附加的工序,即“釉下彩繪”和“蕩釉”?。這兩道工序既要讓陶瓷這種器物承載農(nóng)耕文明的歷史經(jīng)驗(yàn)和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還要將這些經(jīng)驗(yàn)的符號(hào)系統(tǒng)永久固化在瓷器的表面。這一點(diǎn)將在下文論及。制陶和制瓷最大的差別在于,不同的煅燒火候(攝氏800度左右和攝氏1300度以上)與不同的自然材質(zhì)(一般的粘土和高嶺土)。高溫工藝解決了氧化硅等高熔點(diǎn)物質(zhì)的熔化問(wèn)題,高嶺土解決了粘土中氧化鐵等雜質(zhì)過(guò)多的問(wèn)題。一般泥土燒制的陶器,質(zhì)地疏松、粗糙,有微孔,而高嶺土燒制的瓷器結(jié)構(gòu)緊密、晶瑩透亮。這種凝固的結(jié)晶,將泥土的豐富信息變成了抽象的秘密,封閉在恒久的空間中,并在這個(gè)封閉形式內(nèi)部重建了符號(hào)想象的歷史。
高嶺土(瓷器之母)的發(fā)現(xiàn),為人類模仿恒久不變的自然物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對(duì)農(nóng)耕或者泥土的生長(zhǎng)性而言,高嶺土基本上是廢物,也就是所謂“不道德”的物質(zhì),因?yàn)樗`背農(nóng)耕文明追求生長(zhǎng)性的重要準(zhǔn)則。不具備生長(zhǎng)性,這對(duì)動(dòng)物和植物而言意味著死亡,但卻在農(nóng)耕時(shí)代的手工藝領(lǐng)域成了寶貝。泥土成分的雜亂無(wú)章和生生不息的品質(zhì),構(gòu)成了農(nóng)耕文明的“現(xiàn)世道德”。而高嶺土的純凈性和終結(jié)形式,構(gòu)成了農(nóng)耕文明的“超越性道德”。它們?cè)谧匀坏暮腿斯さ膬蓚€(gè)領(lǐng)域各顯神通。從超越性角度看,高嶺土是泥土的升級(jí)版,就像青花瓷是陶器的升級(jí)版、君子是小人的升級(jí)版一樣。它因此成為農(nóng)耕文明器物超越性的典范,也因此得到皇室及上層社會(huì)的青睞。對(duì)超越“生—死”循環(huán)的“超越性道德”的興趣,皇室成員要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一般人,所以,寶石、玉器、青花瓷等標(biāo)本,主要是保存在皇家空間里?。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還必須將陶瓷與玻璃、塑料、水泥等其他人工材質(zhì)區(qū)分開(kāi)來(lái)。玻璃,是一種極端曖昧的、具有現(xiàn)代性品質(zhì)的材質(zhì)。它既封閉又開(kāi)放,既接近又隔絕,既遙遠(yuǎn)又親近,既肯定又否定,是典型的現(xiàn)代“偽君子”形象,也是現(xiàn)代文化“反諷性”的象征。它是一種以不存在的形式而存在的物質(zhì)。布希亞(又譯“鮑德里亞”)說(shuō),玻璃是一種“零程度的物質(zhì)”?。也可以這樣說(shuō),它是一種無(wú)歷史的物質(zhì)。這就是凸顯功能的、無(wú)歷史內(nèi)涵的現(xiàn)代器物,與功能曖昧(不確定)的、充滿歷史和文化內(nèi)涵的傳統(tǒng)器物之間的差別。玻璃的透明性,是對(duì)內(nèi)涵的瓦解。當(dāng)它與水銀涂層結(jié)合成為鏡子的時(shí)候,就會(huì)產(chǎn)生一種類似于土地和交媾的生長(zhǎng)性的假象;特別是當(dāng)兩面鏡子相對(duì)而產(chǎn)生無(wú)限多的影像時(shí),更凸顯了其“邪惡”的特征。博爾赫斯說(shuō),交媾和鏡子都是可惡的。它是對(duì)真理的“捏造”?。類似的現(xiàn)代人工材質(zhì)還有塑料,它是一種絕對(duì)死亡的象征。塑料無(wú)論在水中還是土中或者在空氣中,它都永恒不變,一直睜著邪惡的眼睛。當(dāng)遇見(jiàn)火的時(shí)候,它采用金蟬脫殼之術(shù)化作一股黑煙向空中逃逸,把毒素留在人間。水泥,是對(duì)石頭的低劣模仿,它外表貌似石頭,卻沒(méi)有石頭的靈魂,即晶型和微弱的生長(zhǎng)性。水泥將石頭中殘存的最微弱的生長(zhǎng)性扼殺,并成為現(xiàn)代文明象征——城市的基本元素。
二、文化形式:青花瓷象征的符號(hào)分析
青花瓷,一方面終結(jié)了泥土的自然屬性及其所隱含的歷史和道德內(nèi)容,另一方面又試圖將被終結(jié)了的內(nèi)容重新激活。終結(jié)和激活,成了青花瓷的雙重文化使命。青花瓷的造型、色彩、圖案和紋飾等外部因素,在器物表層形成一個(gè)虛擬空間,并在其中對(duì)被燒結(jié)了的農(nóng)耕精神展開(kāi)再度敘述。這個(gè)空間對(duì)歷史和道德內(nèi)涵的容納方式,不同于宣紙、毛筆、煙墨等工具所呈現(xiàn)的柔性書(shū)寫(xiě)行為。宣紙和毛筆的書(shū)寫(xiě)行為,包含著儒家美學(xué)的重要內(nèi)涵,柔中有剛,剛?cè)岵?jì),以柔的形式顯示剛的力度,它要求用狼毫、羊毫、兔毫達(dá)到刀子鐫刻的效果,要求用毫毛達(dá)到“力透紙背”“入木三分”的效果。而瓷的煅燒自始至終伴隨著剛性的顛覆行為,或者說(shuō)一種暴烈的革命行動(dòng):對(duì)泥土的粉碎、蹂躪、拍打、重塑,對(duì)胎坯的高溫煅燒,瞬間將農(nóng)耕美學(xué)和道德理想鐫刻在這一封閉的器皿之中。煅燒、凝固(結(jié)晶的假象),是對(duì)泥土生死循環(huán)的宿命論的直接超越;想象性敘述和符號(hào)再造,是對(duì)死寂的永恒形式的二度超越。然而,經(jīng)過(guò)鍛燒、塑型、凝固、涂抹、描繪而浴火重生的,并不是泥土真正的生長(zhǎng)性和開(kāi)放性,而是一個(gè)再造的象征性符號(hào)體系。與泥土所蘊(yùn)含的“生長(zhǎng)—時(shí)間—?dú)v史”和“實(shí)踐—空間—道德”結(jié)構(gòu)相比,這是一個(gè)被隔離和凝固了的符號(hào)世界和想象空間。它漂浮在結(jié)晶體的表面,閃爍在透明玻璃釉的底層,游走在形體變化多端的曲線形式之中。
讓永恒而死寂的器物,承載生長(zhǎng)和變化的內(nèi)容,是青花瓷工藝在其象征符號(hào)體系內(nèi)展開(kāi)的主要工作。這種工作在二級(jí)結(jié)構(gòu)內(nèi)部,按三個(gè)遞進(jìn)層次展開(kāi)——造型,色彩,以及“紋飾—圖案”。形如女體的瓷瓶和形如地母的盆碗,是承載、接納、展現(xiàn)生長(zhǎng)和繁殖力信息的基本母體。白色和青(靛藍(lán))色,既是對(duì)自然色彩的超越,也是生長(zhǎng)和繁茂的象征。青料繪制而成的圖案和紋飾,是對(duì)自然界具體的生長(zhǎng)內(nèi)容的虛擬和想象性再現(xiàn)。在這里,農(nóng)耕文明的追求及其潛意識(shí)欲望,在符號(hào)中得到全方位展開(kāi),光滑的造型、柔軟流暢的曲線、繁茂的植物枝葉、想象中的動(dòng)物(包括真實(shí)的和虛擬的),還有可愛(ài)的戲嬰等等都得到了描繪。生長(zhǎng)性的終結(jié)所代表的時(shí)間終結(jié),在空間敘述中被重構(gòu):時(shí)間的空間化(生長(zhǎng)性被煅燒在一個(gè)特殊空間之內(nèi)),以及空間之中的虛擬時(shí)間(虛構(gòu)的敘述),是青花瓷表征空間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悖謬內(nèi)容。
青花瓷的造型,是承載象征性內(nèi)容的基本媒介。模仿自然物(比如果殼、葫蘆、橄欖等)和人體的造型,并不是青花瓷所特有的。青花瓷造型也是在對(duì)原始陶器和瓷器進(jìn)行模仿,元明時(shí)代,景德鎮(zhèn)就生產(chǎn)了大量仿造唐宋時(shí)代的瓷器,如“景德器”“宋器”等。但是,作為一種農(nóng)耕文明美學(xué)的潛意識(shí)內(nèi)容,比如對(duì)生長(zhǎng)和豐收的渴望,對(duì)肥碩母體及其生殖能力和容納能力的崇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原始陶器和瓷器等最初的器物造型,它的發(fā)生,在造型學(xué)中稱之為“象生形”,也就是對(duì)自然物質(zhì)、動(dòng)物形體,特別是女性身體的模仿。青花瓷在這一點(diǎn)上,與其他器物并沒(méi)有大的差別,都是對(duì)自然物和人體的模仿和變形,構(gòu)型時(shí)或長(zhǎng)身短腿,或長(zhǎng)腿短身。有研究者指出:“器物的比例關(guān)系,往往和人體的比例關(guān)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guó)古代的器物,尤其是陶瓷造型,其造型的各個(gè)部位的稱呼,多是擬人化的。……對(duì)于各種陶瓷器物本身的各個(gè)部位,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稱謂習(xí)慣,多是用擬人方式對(duì)待的,比如,也是把造型的不同部位稱為口、頸、肩、腹、足、底等等。……就兩種最具代表性的瓶形,即北宋以來(lái)一直流行的‘梅瓶’和清代康熙官窯創(chuàng)燒的‘柳葉瓶’來(lái)說(shuō),梅瓶……具有男人體的美感;而柳葉瓶則……有亭亭玉立的女性人體的美感。”?青花瓷的造型,無(wú)論是葫蘆型、棒槌型還是紡錘型,不管它那突出而渾圓的腹部,是在上部(梅瓶)、中部(柳葉瓶)還是下部(玉壺春瓶),它都是作為“自然物”的女體的不同變形,都是繁殖力這一潛意識(shí)的象征性再現(xiàn),都是對(duì)生長(zhǎng)性這一至關(guān)重要信息的召喚。瓷器之器型,它對(duì)自然物和人體的模仿,包含著農(nóng)耕文明最重要的信息:繁衍——對(duì)人而言就是生殖,對(duì)自然而言就是生長(zhǎng)。這也是農(nóng)耕美學(xué)的根源。在這一點(diǎn)上,青花瓷跟原始陶器有相似之處。而不同之處在于,青花瓷的象征系統(tǒng)不僅僅局限在造型,它還包含著更多其他的信息。比如,對(duì)色彩、圖案、紋飾精致性的要求,特別是對(duì)各種配料純凈性的要求。再比如,中國(guó)青花之所以優(yōu)于波斯青花,是因?yàn)橹袊?guó)陶工在制作胎坯時(shí),對(duì)原料和配料的雙重純潔性的高要求:瓷土和釉,都使用真正的長(zhǎng)石瓷土和長(zhǎng)石釉,“使得在高溫下胎釉結(jié)合良好……花紋和圖案能夠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lái)”?。這就像中藥對(duì)藥引的要求?,或者族人對(duì)血緣和道德純潔性的要求一樣嚴(yán)格。
白地藍(lán)花,是青花瓷的特殊標(biāo)志色。這里的“青色”(藍(lán)或靛藍(lán)),與唐五代柴窯所代表的青瓷之“青色”不同。青瓷的青色(青如天),與器物的材料和造型渾然一體,并沒(méi)有從造型中分離出來(lái),它僅僅是在同一維度和平面上,對(duì)材質(zhì)和造型的補(bǔ)充與強(qiáng)化,其青色的生長(zhǎng)性象征,與模仿女體的器物造型所表征的內(nèi)容重疊。這也是對(duì)“膚如凝脂,手如柔荑”這一比喻的材質(zhì)化、器物化。而青花瓷的青色,首先就從器物造型和材質(zhì)中分離出來(lái),那是因?yàn)榘状傻某霈F(xiàn)為它創(chuàng)造了條件。南北朝時(shí)期白瓷的出現(xiàn),是對(duì)早期青瓷的一次超越,也是對(duì)泥土中的雜質(zhì)徹底清空的野心的呈現(xiàn),也同樣是強(qiáng)力煅燒和清除的結(jié)果。有人稱之為“陶瓷發(fā)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和“一次偉大的創(chuàng)造”?。白瓷的出現(xiàn)(清除了瓷土中的雜質(zhì),特別是鐵、錳、鎳等),是青花瓷戲劇上演前的一個(gè)序幕,盡管它的白色還是乳白或淡青,還有雜質(zhì),但已經(jīng)為純白色的出現(xiàn)做好了準(zhǔn)備。首先是含長(zhǎng)石的高嶺土和瓷石的發(fā)現(xiàn)和使用,使器物形體本身變成純白有了可能性;其次是對(duì)“青料”使用技術(shù)的掌握,使器物之上所描繪的內(nèi)容成為了純青色;再者是釉料的制造運(yùn)用使釉下彩成為可能。青花瓷之純“青色”和白瓷的純“白色”,以及它們能夠獨(dú)立存在,為青花瓷的圖案和紋飾等文化內(nèi)容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了條件。
青色本是一種十分曖昧的顏色,它介于綠和藍(lán)之間,非綠非藍(lán),有時(shí)偏藏藍(lán)或墨藍(lán),有時(shí)又帶綠色,有時(shí)又指黑色。在我家鄉(xiāng)(江西)的土話中,青布就是黑布,好比古詩(shī)詞中的“青絲”指黑發(fā)。而“青天”又叫“蒼(深藍(lán))天”,還叫“碧(淺藍(lán))空”,“碧草”也是青草或綠草的意思。這種對(duì)色彩命名上出現(xiàn)的詞匯和語(yǔ)義的含混性,既是對(duì)自然色系(光譜)本身的性質(zhì)缺乏深刻認(rèn)識(shí)的結(jié)果,也是對(duì)陌生色彩描述詞匯匱乏的結(jié)果。“青色”的本義就是“藍(lán)”的顏色,所謂“青出于藍(lán)”即是。而“藍(lán)”的顏色,就是“靛草”的顏色,一種能產(chǎn)生藍(lán)色的草的顏色。農(nóng)民自織的布,原是本白色,為了增加花樣,他們會(huì)將白布染成“靛藍(lán)色”或者藍(lán)白二色的青花布。但無(wú)論如何,“青色”又是一種十分重要的顏色,屬于“五色”(青紅黃白黑)之一種,對(duì)應(yīng)于“五行”(木火土金水)、“五方”(東南中西北)、“五候”(風(fēng)火溫燥寒)等?。它是東方的顏色、春天的顏色、樹(shù)木花草的顏色、自然和大地的顏色、生長(zhǎng)的顏色、生命的顏色。
圖案和紋飾,是青花瓷表面更為具象的內(nèi)容:花朵、草木葉、藤蔓等自然界花草樹(shù)木的基本元素,以及用草葉、樹(shù)葉、花瓣、藤蔓等基本元素拼成的各類對(duì)稱的幾何圖案,還有自然界的山水鳥(niǎo)獸,還有風(fēng)景中的人物,等等。其中,植物及其相關(guān)的圖案占主導(dǎo)地位。這是農(nóng)耕文明對(duì)生長(zhǎng)和繁衍的夢(mèng)想的再現(xiàn)。陶瓷工藝和青花瓷本身,通過(guò)對(duì)礦物寶石恒久不變性質(zhì)的模仿,通過(guò)對(duì)青綠色所象征的生長(zhǎng)性的模仿,通過(guò)“釉下彩”和“蕩釉”等新工藝對(duì)理想和現(xiàn)實(shí)內(nèi)容的模仿(敘事、描寫(xiě)、抒情),將農(nóng)耕文明的社會(huì)理想和審美理想符號(hào)化、固定化、永恒化,表達(dá)著充塞在農(nóng)耕文明深層的偉大夢(mèng)想:五谷豐登,子孫滿堂,福祿壽喜,六畜興旺,流芳萬(wàn)載,天祚永享。
三、社會(huì)形式:青花瓷功能的符號(hào)分析
如上文所述,青花瓷的制作,首先是一種“摶黃土”“煉五石”的“捏”的行為,然后是在器型表面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造”的行為,最后經(jīng)高溫煅燒將其“形式”和“內(nèi)容”全部凝結(jié)。實(shí)際上可歸結(jié)為兩道工序:捏造和固化。作為一種人工制作的工藝品,它無(wú)疑不是“真理”,所謂“真理是不能捏造的”?。而青花瓷是一個(gè)“捏造”出來(lái)的被固化的“真實(shí)”世界:通過(guò)“拿捏”瓷土而制造出一種精美器皿,也“捏造”出繁復(fù)而又令人著迷的器物符號(hào)。這種精致而繁復(fù)的“捏造”行為,從隱和顯兩個(gè)層面呈現(xiàn)出它的功能。身體技術(shù)層面的人類學(xué),還有社會(huì)工藝層面的仿生學(xué),乃至將其神圣化的獻(xiàn)祭行為,這些都屬“隱”的范疇。而日用品、交換品、饋贈(zèng)品、藝術(shù)品、收藏品等等,則都屬“顯”的范疇。
就制作實(shí)踐活動(dòng)本身而言,青花瓷或其他瓷器與更為古老的陶器相一致。這種摶土捏造的手藝,屬于人類最原始的“捏造”行為,是一種習(xí)得的產(chǎn)物,在漫長(zhǎng)歷史過(guò)程中,如本能一般凝結(jié)于人類的意識(shí)深處,并將人類擊打、碎裂、完型的原始沖動(dòng)投射其中,同時(shí)也將人類對(duì)收藏、容納、承載、存留、歸類等原始欲望投射其中,最終通過(guò)人類最初始的造型能力把握而指向?qū)徝澜?jīng)驗(yàn)的呈現(xiàn):將旋轉(zhuǎn)、摶捏、刻畫(huà)這些初始動(dòng)作,轉(zhuǎn)化為圓形、方形、流線形及花紋、圖案等美學(xué)形式。既是一種身體技術(shù),又是人類對(duì)自己身體的一種使用技能,還是一種審美升華過(guò)程。人類學(xué)家指出:“身體是人首要的與最自然的工具。……人首要的與最自然的技術(shù)對(duì)象與技術(shù)手段就是他的身體。”?青花瓷工藝,是農(nóng)耕文明背景下手工藝中的高級(jí)身體技術(shù)之一。它是對(duì)人類身體的基本動(dòng)作,包括咬、抓、捏、打、擲等的綜合運(yùn)用和升華,也是古典科學(xué)工藝的體現(xiàn)和農(nóng)耕美學(xué)的集大成者。
倘若僅限于此,尚不足以將瓷器和陶器的制作區(qū)分開(kāi)來(lái)。瓷器對(duì)高溫的要求,顯然是燒制工藝高度成熟的結(jié)果。通過(guò)對(duì)溫度的增加和有效控制,決定了瓷器的品質(zhì)。這就在工藝上大大增加了技術(shù)含量,也大大增加了智慧含量。青花瓷通過(guò)約1300度高溫的煅燒,將材料中的所有水分(包括分子水)都燒干。泥土中那具有生長(zhǎng)性的水被燒干,仿佛人體中的水分(汗水、眼淚、血液)也被抽干。高溫剔除了雜質(zhì)(鐵錳鎳等),土元素轉(zhuǎn)化為一種更為純粹的新物質(zhì),它仿佛是土的骨骼、土的精髓、土的理念、土的形而上學(xué)。這種新物質(zhì)就是剔除了雜質(zhì)和水分的白瓷胎。它就是全部青花瓷工藝的“仿生學(xué)”基礎(chǔ)。特殊的上釉工藝,不只是全新的和高難度的技術(shù),更為全新的藝術(shù)形態(tài)的誕生提供了條件。審美形式成了一種靜態(tài)的、永恒的、無(wú)水的、不具備生長(zhǎng)性的干貨,抽象地呈現(xiàn)在器物的表層。它的外表,再通過(guò)一種叫“釉下彩”(描繪所需要的靛青色圖案和畫(huà)像)和“蕩釉”(涂抹在圖案表面的釉,經(jīng)高溫煅燒后形成一層發(fā)光玻璃層,將描繪的內(nèi)容固化)的工藝,對(duì)一切有可能發(fā)生變化的形式予以固化。在純粹的土元素之上,再覆蓋一層細(xì)膩、光滑且透明的、凝脂一般的釉,好像在這件借助土而制造出來(lái)的器物骨架和肌肉之上,又覆上了一層精美的皮膚。如果把白色的瓷胎比作人體,那么,發(fā)光釉就是它的皮膚,青花紋飾就是它的服飾(雖然在釉之下)。它的器型就是人體的仿造物,有寬肩的、大臀的,有頭、口、肩、腰、臀、腿。但正因?yàn)樗鼉H僅具有“仿生”特征,而不是“生物”本身,所以它的皮膚和服飾的界限是含混不清、概念不明的,甚至是邏輯錯(cuò)亂的:服飾在皮膚之下,就像在皮膚之上一樣,從而隱含著某種“東方神秘主義”的氣息。
青花(透明釉下彩)的出現(xiàn),使得青花瓷的皮膚(釉本身)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皮膚,而是一種有著極高文化識(shí)別度的符號(hào)表征,賦予瓷器以中國(guó)化的藝術(shù)精神,一種特殊的美學(xué)。仿佛給青花瓷這件人工的“摶造物”吹進(jìn)了一股東方文化精神的靈氣,使得青花瓷不只是一件日用的器皿。這是對(duì)女?huà)z造人神話的模仿與再現(xiàn),是農(nóng)耕文化條件下人工制造所能發(fā)揮的想象的極致。這也是一種浸潤(rùn)著農(nóng)耕文明的美學(xué)精神:純潔牢靠而又搖曳多姿的生長(zhǎng)性,生生不息的繁衍精神,恒久不變不易的特征。這三種特征,正如錢鐘書(shū)《管錐編》開(kāi)篇在“論易之三名”一節(jié)中引《易緯》之說(shuō):“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錢鐘書(shū)并借鄭司農(nóng)之《易贊》《易論》,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以及黑格爾、歌德、席勒等西方名家著述,申述這種中國(guó)特有的簡(jiǎn)易符號(hào)之多義性,或多義符號(hào)之簡(jiǎn)易性,進(jìn)而論“不易之理”?。我們發(fā)現(xiàn),“易”這種帶有東方神秘主義特征的符號(hào)所具有的三合一特征(簡(jiǎn)易、變易、不易),與“青花瓷”這個(gè)典型的東方符號(hào)之間,存在相契之處。青花瓷的文化語(yǔ)義之簡(jiǎn)易性、多義性和相對(duì)的恒定性糾纏在一起,構(gòu)成了這個(gè)器物在當(dāng)今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中的奇異處境。所以,盡管“青花瓷”這一符號(hào)系統(tǒng)中隱含著復(fù)雜多樣的深層功能,使它具有象征性,但又正因?yàn)槠渖顚庸δ艿碾[蔽性,使其外顯功能混亂而易變。
首先是它的“使用功能”。毫無(wú)疑問(wèn),青花瓷首先是作為一種日常實(shí)用器皿被制造出來(lái)的。最常見(jiàn)的是容器:其“純功能”?是接納、收藏、盛裝。與之相應(yīng)的結(jié)構(gòu)是:一方開(kāi)口的圓柱形,四周和底部封閉,或者開(kāi)口是活動(dòng)的(加蓋加塞的器皿)。與結(jié)構(gòu)相應(yīng)的形態(tài)是:圓柱形或圓柱變體(上大下小,上小下大,兩頭小中間大,兩頭大中間小,直線形和弧線形的)。器皿日常使用中的“純功能”可以不變,而其他選項(xiàng)則可以隨意變換,比如器型可以變(也可為三角形和圓錐形),但它還是青花瓷。更重要的是,材質(zhì)也可以變,比如,器皿的材質(zhì)也可以用玻璃、塑料、木頭、金屬等來(lái)替代,但這時(shí),“青花瓷”概念已不存在。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器皿材質(zhì)五花八門,并非古典的瓷器獨(dú)大的時(shí)代。無(wú)疑,瓷在器皿意義上并無(wú)優(yōu)勢(shì),除非作為餐具。這是因?yàn)槠洳馁|(zhì)的穩(wěn)定不變性,或者說(shuō)沒(méi)有生長(zhǎng)和死亡特質(zhì),它是一種“終結(jié)物”:不氧化、不磨損、不變化,符合餐飲衛(wèi)生,所以至今依然可以是餐桌上的主要器皿。但又由于所有瓷器都有同樣的“純功能”,這就意味著青花瓷并不處于重要地位。作為日常器皿,青花瓷的使用功能并不重要。事實(shí)上,它已經(jīng)退居到了相當(dāng)邊緣的位置上。
其次是它的“附加功能”。器物在滿足人們?nèi)粘S枚鹊摹凹児δ堋敝猓€有一些“附加功能”,是其本身無(wú)論怎么變化都不會(huì)被改變的。比如,審美功能就是其中之一,還有收藏功能、祭祀功能等等。就審美功能而言,它包括材質(zhì)精細(xì)或純凈與否,造型美觀與否等外在于日常“純功能”的因素。與其恒久不變相比,“附加功能”是隨時(shí)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所以不具備永恒性。比如,青花瓷體表面是否光潔,在元明清時(shí)代,不僅是工藝進(jìn)步與否的問(wèn)題,也是審美問(wèn)題。時(shí)過(guò)境遷,今天的問(wèn)題是:為什么要光潔?亞光不行嗎?靛藍(lán)純度高,繪制圖案花紋清晰,但在今人看來(lái),模糊美也很不錯(cuò),甚至沒(méi)有花紋也很好,宋窯的柴燒就很美。還有器型的繁復(fù)與簡(jiǎn)潔問(wèn)題,汝窯的造型簡(jiǎn)潔就很美。再有,就瓷胎的精致化和粗糙化而言,粗糙在今人看來(lái)或有一種樸拙之美,而不再需要那么精致。由此可見(jiàn),器物的“附加功能”是非本質(zhì)的、易變而不穩(wěn)定的,青花瓷同樣如此,它的美學(xué)風(fēng)格,今天無(wú)疑已經(jīng)邊緣化了。器物的“純功能”是物品的最高道德,它和人類的實(shí)踐活動(dòng)無(wú)法分離,而“附加功能”的變異性,卻又決定了作為商品的器物是否具有恒久性。青花瓷在今天生活中的邊緣化,正是其使用價(jià)值的邊緣化和審美價(jià)值的邊緣化使然。
作為一種器物,青花瓷的使用功能在減弱,它被其他材質(zhì)和工藝制造的器物搶占了位置。它的審美功能也在減弱,被那些更為簡(jiǎn)潔的美學(xué)形式,比如汝窯和柴窯的瓷器器皿所取代。更為尷尬的處境還在于:如果完全復(fù)制青花瓷的工藝、器型和美學(xué)形態(tài)來(lái)進(jìn)行生產(chǎn),相對(duì)其他材料(玻璃、搪瓷、金屬等)而言也并無(wú)特別的優(yōu)勢(shì)。如果將“青花”作為一種造型元素提取出來(lái),用到別種材料的產(chǎn)品上,那么,青花瓷則又失去了其真正存在的價(jià)值,成了一堆破碎的生命殘片(比如有一種瓷土與某些金屬的混合物組成的新型材料,似乎與“瓷器”沒(méi)有必然的關(guān)系)。
青花瓷作為農(nóng)耕文明下的手工制品,它在一般意義上的使用價(jià)值、交換價(jià)值和展示價(jià)值處于“凍結(jié)”狀態(tài)。但又由于它凝結(jié)了古老的智慧和農(nóng)耕文明的潛意識(shí)內(nèi)涵,以及被歷史記憶所賦予的象征價(jià)值,使其繼續(xù)在現(xiàn)實(shí)生活和文化敘述中擔(dān)當(dāng)著某種重要角色,并也在試圖借此而獲得資本價(jià)值,它的收藏價(jià)值即由此而來(lái)。在日常生活中,沒(méi)有人去大量使用青花瓷,年代久遠(yuǎn)的制品就更不可能。事實(shí)上,在當(dāng)下語(yǔ)境中,古老的青花瓷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相關(guān)聯(lián)的紐帶正在被切斷,這些精美璀璨的泥土精靈,正在日益成為孤獨(dú)無(wú)依的幽靈。一種將農(nóng)耕文明的價(jià)值觀念和審美趣味高度濃縮于一身的器皿,就這樣成為了博物館的收藏物,或是古董市場(chǎng)上被以各種目的裹挾的幽魂。
通過(guò)審美想象,去召喚夢(mèng)想之物或者死去之物,是世俗社會(huì)一種特殊的自我救贖行為。而所謂收藏不過(guò)是掩埋和哀悼。戀物般的收藏,僅是通過(guò)對(duì)收藏對(duì)象的物質(zhì)形態(tài)的保存,來(lái)滿足人們對(duì)古老之物的依戀和膜拜,也是人類在嘗試著對(duì)自身時(shí)間焦慮和死亡焦慮的克服。至于古董商式的收藏,則是將這種被時(shí)間流逝所積淀下來(lái)的生存欲望和美學(xué)沖動(dòng),轉(zhuǎn)化為商品的文化附加值加以販賣。在一次又一次的轉(zhuǎn)手倒賣過(guò)程中,青花瓷的價(jià)值越來(lái)越高,因?yàn)檫@正意味著青花瓷越來(lái)越失去其使用價(jià)值和美學(xué)價(jià)值,越來(lái)越遠(yuǎn)離其日常生活語(yǔ)境和美學(xué)語(yǔ)境。而每一次轉(zhuǎn)手和升值,其古老的美學(xué)輝光就會(huì)暗淡一分,逐漸成為被囚禁在博物館的文化囚徒。
結(jié) 語(yǔ)
通過(guò)對(duì)“青花瓷”符號(hào)的物質(zhì)內(nèi)容、文化象征和社會(huì)功能的分析,我們或可以對(duì)青花瓷這一熟悉的陌生物,對(duì)“青花”所隱含的農(nóng)耕文明美學(xué)內(nèi)涵,有更深入的認(rèn)識(shí)和了解。
首先,青花瓷與其他陶器和瓷器在制造工藝上有相似之處,都是古人對(duì)“摶黃土”和“煉五石”神話的戲仿。在農(nóng)耕文明世世代代對(duì)泥土和生死循環(huán)的迷戀與承擔(dān)背后,一直存在著一種超越生死循環(huán)的沖動(dòng),進(jìn)而去發(fā)現(xiàn)或者發(fā)明它。在物質(zhì)層面上,通過(guò)火熔化和剔除泥土中易變的物質(zhì)以煅造恒久不易改變的器物,本質(zhì)上構(gòu)成了對(duì)泥土的否定和超越。用生的形式展開(kāi)死,用死的形式顯示生,這種兩歧性,正是農(nóng)耕文明造物的精神密碼。其次,“釉下彩”是對(duì)器物文化內(nèi)涵的固化和凝結(jié)。通過(guò)“釉下彩”“蕩釉”“煅燒”三道工序,將精神密碼外化為一種顯在的形式,這是工藝的造化。煅燒、凝固是對(duì)泥土生死循環(huán)宿命的直接超越,而想象性敘述和符號(hào)再造,是對(duì)死寂的永恒形式的二度超越。經(jīng)過(guò)煅燒、塑型、凝固、涂抹、描繪而浴火重生的,并不是泥土真正的生長(zhǎng)性和開(kāi)放性,而是一個(gè)再造的象征性符號(hào)體系。這里面還包含著對(duì)物質(zhì)的道德純潔性的極度追求。再次,器物制作過(guò)程及其造型原則超越了狹義的工藝學(xué),而指向更廣闊的人文世界。在這里,生的內(nèi)容和理想的神話被永恒固化在了器物的表面。
在這個(gè)意義上,青花瓷作為典型的中國(guó)符號(hào)之一種,無(wú)疑成為有待進(jìn)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的中國(guó)標(biāo)本。
① 關(guān)于青花瓷的起始年代,學(xué)術(shù)界還存在爭(zhēng)議。中國(guó)硅酸鹽學(xué)會(huì)主編《中國(guó)陶瓷史》中的觀點(diǎn)是,根據(jù)“釉下彩”和“氧化鈷青”兩要素,認(rèn)為唐代就具備了這種技術(shù),并稱之為“原始青花”(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342頁(yè))。而標(biāo)準(zhǔn)的“青花瓷”,一般認(rèn)為應(yīng)以元代“至正型”(1351年)青花為標(biāo)識(shí)(參見(jiàn)馮先銘《中國(guó)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455頁(yè))。
② 玻璃的起源也是眾說(shuō)紛紜,作為一種新型材質(zhì)的“現(xiàn)代工業(yè)玻璃”,產(chǎn)生于19世紀(jì)末(參見(jiàn)《簡(jiǎn)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shū)》第一卷,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出版社1985年版,第801頁(yè);W.福格爾《玻璃化學(xué)》,謝于深譯,輕工業(yè)出版社1988年版)。
③ 這種對(duì)青花瓷的描述語(yǔ)言,最初是針對(duì)唐五代時(shí)期的柴窯“青瓷”:“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罄”。明人文震亨《長(zhǎng)物志》中有記載,但他表明自己并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這種青瓷,只是對(duì)傳聞的引述,故下有“未知然否”的說(shuō)法。將形容青瓷的“青如天”,改為形容青花瓷的“白如玉”也順理成章(陳植:《長(zhǎng)物志校注》,楊超伯校訂,江蘇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頁(yè))。
④ 用于釉下彩繪的含氧化鈷元素的青料,有進(jìn)口的(如蘇麻離青),也有國(guó)產(chǎn)的(如平等青)。此外還有一種誕生于元代的“釉里紅”釉下彩,彩繪時(shí)不用鈷料,而是用含氧化銅的銅紅料。
⑤ 瓷器“china”是“China”的派生物,而非相反。景德鎮(zhèn)1004年之前名叫“昌南”,與“China”發(fā)音近似,并不證明“中國(guó)”與“景德鎮(zhèn)”和“昌南”有什么關(guān)系。一般認(rèn)為,“China”是由梵文“支那”(Cina)轉(zhuǎn)化而來(lái)(參見(jiàn)張星烺《“支那”名號(hào)考》,《中西交通史》第一冊(cè)附錄,中華書(shū)局2003年版)。
⑥ 高嶺土(Kaolin)一詞,源于景德鎮(zhèn)浮梁縣高嶺村出產(chǎn)的一種可以制瓷的白色粘土,主要分布于江西景德鎮(zhèn)、湖南衡陽(yáng)、廣東茂名等地。其主要成分為含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鋁的高嶺石。瓷石(China Stone,中國(guó)石)以景德鎮(zhèn)浮梁縣柳家灣為代表,始采于宋代,主要成分為石英、云母、長(zhǎng)石。
⑦拙著《土地的黃昏——中國(guó)鄉(xiāng)村經(jīng)驗(yàn)的微觀權(quán)力分析》(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主要研究的是農(nóng)民對(duì)土地或泥土的生長(zhǎng)性的依賴,以及由此生成的一系列文化規(guī)則。
⑧ 礦物巖石學(xué)用“莫氏硬度”對(duì)巖石硬度進(jìn)行分類。該分類法于1824年由德國(guó)礦物學(xué)家莫斯(Frederich Mohs)提出:用棱錐形金剛鉆針劃巖石表面,根據(jù)劃痕深度將之分為十級(jí):1.滑石;2.石膏;3.方解石;4.螢石;5.磷灰石;6.正長(zhǎng)石;7.石英;8.黃玉;9.剛玉;10.金剛石。自七級(jí)開(kāi)始為特別堅(jiān)硬的巖石。歸納為口訣:滑石方解螢磷長(zhǎng),石英黃玉剛金剛。
⑨參見(jiàn)拙著《土地的黃昏——中國(guó)鄉(xiāng)村經(jīng)驗(yàn)的微觀權(quán)力分析》第七章第三節(jié)關(guān)于“游戲與泥土意象”的論述。令人稱奇的是,制瓷中的“印坯”工序,陶瓷工匠稱之為“拍死人頭”,與玩泥巴作為一種“生死游戲”的判斷正好巧合(參見(jiàn)傅振倫《〈景德鎮(zhèn)陶錄〉詳注》卷一,書(shū)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93年版)。
⑩ 女?huà)z“摶黃土”傳說(shuō),見(jiàn)《風(fēng)俗通義校釋·佚文·二十六》:“俗說(shuō)天地開(kāi)辟,未有人民,女?huà)z摶黃土作人。劇務(wù),力不暇供,乃引繩于泥中,舉以為人。”(吳樹(shù)平:《風(fēng)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頁(yè))“煉五石”傳說(shuō)見(jiàn)《淮南子·覽冥訓(xùn)》:“五色石以補(bǔ)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jì)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淮南子》,中華書(shū)局1954年版,第95頁(yè)。)
? 青花瓷制作工序最有代表性,分為:取土、煉泥、鍍匣、修模、洗料、做坯、印坯、鏇坯、畫(huà)坯、蕩釉、滿窯、開(kāi)窯、彩器、燒爐等十四道(參見(jiàn)傅振倫《〈景德鎮(zhèn)陶錄〉詳注》卷一;《耶穌會(huì)士中國(guó)書(shū)簡(jiǎn)集》Ⅱ,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 還有一種“釉上彩”,又稱“粉彩”“軟彩”“雍正粉彩”,在蕩釉和煅燒成型之后,用彩色乳膠在瓷器表面繪制彩色圖案,以一種艷俗的農(nóng)耕趣味改寫(xiě)了青花瓷和釉里紅單色的美學(xué)趣味,盛行于清代“康雍乾”時(shí)代。
? 北京故宮藏陶瓷三十五萬(wàn)件,明清青花瓷可參見(jiàn)《明清青花瓷:故宮博物院藏瓷賞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 布希亞:《物體系》,林志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頁(yè)。
? 參見(jiàn)《博爾赫斯全集·小說(shuō)卷》,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yè);《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上,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446頁(yè)。
? 高豐:《中國(guó)器物藝術(shù)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頁(yè)。
? 哈里·加納:《東方的青花瓷》,葉文程、羅立華譯,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yè)。
? 魯迅《吶喊·自序》:“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jīng)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duì)的。”(魯迅:《吶喊》,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3年版,第1頁(yè)。)
? 中國(guó)硅酸鹽學(xué)會(huì)主編《中國(guó)陶瓷史》,第167頁(yè)。
? 參見(jiàn)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shū)局1994年版,第166—169頁(yè)。
? 博爾赫斯:《謎的鏡子》,《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第443、443—446頁(yè)。
? 馬塞爾·毛斯:《各種身體技術(shù)》,《社會(huì)學(xué)與人類學(xué)》,佘碧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頁(yè)。
? 錢鐘書(shū):《管錐編》,中華書(shū)局1979年版,第1—6頁(yè)。
? 物品的“純功能”,是物品基本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的原始功能,相當(dāng)于詞匯的“本義”。物品的“附加功能”,是在不改變物品基本結(jié)構(gòu)的前提下,增加附件產(chǎn)生的功能,相當(dāng)于詞匯的“引申義”。比如汽車的“純功能”是高速移動(dòng),“附加功能”是增加汽缸數(shù)以增加“馬力”,或者改手動(dòng)擋為自動(dòng)擋(參見(jiàn)布希亞《物體系》,第1—8、15—16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