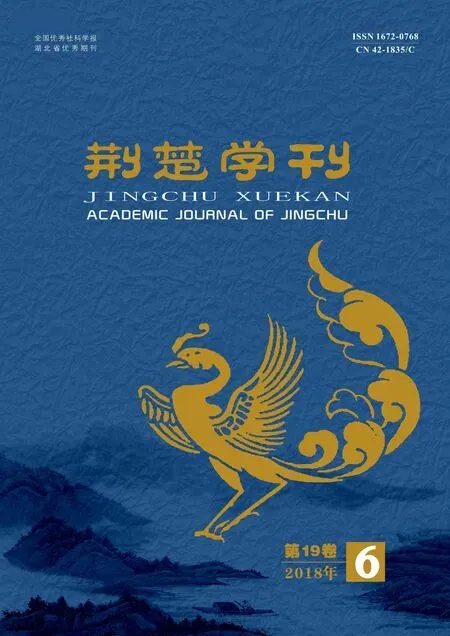身體的狂歡與消費:“抖音”短視頻的審美反思
曾 蒙
(揚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9)
2017年,短視頻蓋過了直播的熱度,在互聯網上大放異彩。短視頻App在手機應用市場上層出不窮、更新不斷,其中又以“快手”“西瓜視頻”“火山小視頻”“抖音”等App最為火熱。短視頻的第一個特點如其命名,強調短,其時長多以秒為計算單位。沃霍爾曾言,“將來,人人都可以著名15分鐘”[1]。如今,只需在短視頻軟件上發布短短15秒視頻,草根也能出名,獲得眾人的圍觀。短視頻的第二個特點是高度的社交性,在人際傳播上“具有巨大的可分享性(share-ability)”[2],正因其高度社交性,短視頻軟件都能獲得極大的用戶流量。
“抖音”作為一匹“黑馬”在短視頻領域中脫穎而出:“抖音的國內日活躍用戶數突破1.5億,月活躍用戶超過3億。”[3]“抖音”的短視頻類型豐富,從主題上大致可以分為“明星、才藝創意、旅行美食、曬娃秀寵、美女帥哥、婚禮現場”[4]等類型。其短視頻多為配音發布,熱門的配音多為節奏性強、抒情性強的歌曲,極具聽覺刺激性和情感渲染性。不管是何種主題視頻,視頻發布者大多在音樂的伴奏下以自己身體的夸張動作或任性舞蹈來表現自我。比起以往其他大眾媒介,身體元素在“抖音”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展示更為直觀。作為當今視覺時代新興審美媒介的突出代表,“抖音”將視覺時代的審美路徑彰顯到極致。將其作為視覺時代的一個鏡像,從身體這個關鍵詞入手,可以管窺視覺時代語境中的獨特審美路徑與身體狂歡、身體消費現象,并對其中潛藏的審美困境提出合理建議。
一、審美路徑的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媒介的發達帶來審美媒介在當代社會的主導、疊合和泛化現象”[5]72,使得審美媒介走向了多元化;但也不得不承認視覺元素在其中日益占據突出的地位。當今主導的審美媒介甚至可以說已經從由文字走向圖像/視覺,“音響和畫面,特別是后者構成了美學,指導著觀眾”[6]105。而審美媒介作為溝通和連結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工具,在審美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不僅具體地實現審美意義和信息的物質傳輸,而且給予審美效果以微妙而又重要的影響”[5]70。審美媒介的變遷不僅給人們帶來新的審美體驗,更塑造了一種新的審美路徑。
黛布雷以媒介將人類社會分為三個時期:書寫(writing)時代、印刷(print)時代和視聽(audio-visual)時代[7]。其認為與視聽時代相對應的是視覺(the visual)。前兩個時代也可統稱為文字時代,該時代中的人們對于文字盡管也是以看的形式來進行,似乎也是一種視覺文化,但實際上人們是在讀文字。“視覺活動的本質是視覺化(Visuality)”[8],但人類閱讀文字所產生的視覺化其本質是間接的、次生的,是發揮主觀想象的產物。這要求審美主體在“理解一個論點或思考一個意象時調節自我的速度,與之對話”[6]108,由此出現所謂“詩無達詁”的現象。因而文字時代對審美主體的要求更高,其需要懂得文字形象所潛藏的意義,否則文字符號對其而言便為無意義之物。故該時代的審美具有主動性、高雅性與精英性。其次,文字作為一種語言符號,有其能指與所指的二元區分,這種二分模式導致語言在表情達意時必然存在著某種困難或局限。一方面,語言符號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是對萬事萬物的抽象式把握;另一方面,任何抽象的把握都不能整全地反映現象世界。因此人類在使用語言時總是面臨各種言不盡意的尷尬與困難。中國古人以“立象以盡意”的巧妙形式來解決這一困難,本來語言就和自在世界存在一層能指的隔離,“立象”之后又多了一層“象”的隔離,最終語言與自在世界之間無疑變成了雙重隔離。因而文字時代的審美具有明顯的凝神靜觀特點,人往往進行著有深度的思考,追尋所指內涵與返回自在世界的過程必然需要一種沉思。
而視覺時代則突顯出與文字時代迥異的審美路徑。首先,在語言和圖像二元對立的傳統中,“語言被認為高于圖像,因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語言就是‘邏各斯’”[9]43。人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所直接目睹的現象總是不斷變化、異常復雜,視覺的地位也因此常常遭到貶低。在巴門尼德看來,“一切感官知覺僅僅提供錯覺,其主要錯覺恰恰在于它造成了一種假象”[10]。柏拉圖更是繼以“相”論將活生生的現象世界視作對“相(理念)”的模仿,視作“相”的影子,一種虛假。當代視覺文化的繁榮,正是對傳統以語言為中心的思想文化的反叛,不再是追尋所謂的“本質”“真理”而是掉轉頭直擊感性現象世界。因此視覺時代一個突出的審美特點就是直擊感性存在,解放感性,帶來一種震驚式的生理快感體驗。“抖音”正是以青春、美、身體等感性元素而爆紅,“抖音”便是直接刺激人的感官沖動,特別是激發人的笑,這種充滿笑點和感官刺激的視頻在大眾中尤其是年輕人群中大受歡迎。再次,在視覺時代,審美主體在面對不同圖像時,盡管有著選擇的自由;但一旦選定看的對象,“運動中的圖像總能抓住你的視線,把你引向某一方向”[11],人在這一過程之中更多的是被動地接受圖像。最后,圖像相比文字而言,使得人與自在的世界之間不再是一種隔離狀態,圖像往往直接刺激著人們的視覺。視覺文化對審美主體要求相對降低,文化抑或審美都不再是精英的專權、不再獨居高雅之堂。“抖音”作為新興視覺文化的代表,沒有對象的限制,只須會使用手機即可,人人可以觀看、分享、留言討論短視頻。人人也可以上傳自己的視頻,由一個看者轉變為被看者。這是一個具有高度大眾參與性的新興媒介。
審美媒介由文字到視覺的轉變,不僅帶來了審美體驗的變化,更帶來了一種審美路徑的變化。也即以何種方式進行審美,這種方式不僅包括物質媒介層面,也包括思維與心理層面。簡而言之,文字時代的審美更加高雅化、精英化、理性化、審美主體具有較大主動性和創造性,多以凝神靜觀方式進行;視覺時代的審美則更加通俗化、大眾化、感性化,審美主體呈現出被動性特點,往往被震驚、被驚艷。“抖音”中最常出現的熱門評論是“別人的男朋友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抖音中的狗也能上清華”等等,諸如此類的高居被點贊榜首的評論也正體現了這些短視頻的震驚風格。
二、身體能指的狂歡
視覺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感性文化。人類的感性可以分為認識活動層面以及肉體官能層面,前者“以感知、表象、想象、聯想為感性認識”[12],后者“是以生理欲望、原始沖動、感官快適、自然本能等為表現形式的感性生活”[12]。盡管鮑姆加通將感性提高到一門科學的層面,建立了感覺學,也即美學,但他只顧及到感性的認識活動層面而“懸擱了一個重要的感性存在——肉體,身體的作用和意義”[12]。這個被壓抑的、遺忘的身體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運動中不斷得以解放,甚至極端地強調“回到身體自身,就是回到身體直接的肉體性”[13]。同時身體作為一種重要的語言符號,其唯一性和不可復制性也極力地迎合了“小時代”人們表現自我、展示自我的欲望,由此身體也成為了當代視覺文化中最重要的審美對象和審美媒介之一。
(一)“小時代”語境與身體語言登場
“小時代”(1)是相對“大時代”而言的。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家政治將個人和國家的命運直接地、緊密地聯系起來,在這種語境之下,“小我”不具有合法性,也是要遭受到批判的。改革開放后,“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確實降低了政治資本的重要性,使得更多的個體能夠憑借自己的知識、技能和勤奮而致富和實現自我”[14]7。此外,市場經濟發展不僅促進了“個體的興起”,也促進了“社會結構的個體化”[14]358。換言之,“小我”的地位由此得到重視和保障。此外,“小時代”還與當代哲學思潮轉變有關:“從本體論走向了功能論”[15]25。前者是一種深度模式,伴隨著本體的都是沉重的、宏大的話題,如靈魂、絕對精神、本質等。而功能論也即“效益、功用和利害得失,成為衡量一切的首要的也是最終的尺度”[15]25,簡而言之,關注什么是有用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一種價值論哲學。價值是相對主體而言,這種功能論或價值論將主體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小我”的地位得以提升。生活在“小時代”的人們執著于追求“小我”的最大化,在生活中處處表現自我,展示自我。
改革開放后,在文化上這種“小我”追求大致呈現出三個階段,可謂之“三部曲”。首先體現為從純文學走向網絡文學,盡管這二者都以文字為媒介,但網絡文學卻給讀者提供了大量細分類型以及私密的體驗。人們在仙俠、玄幻、言情等等細分的類型中找到自我的歸屬感,在大量私密寫作中滿足了“小我”的窺視欲望。這種文字的解放,帶來了文化上最初的小我感,網絡文學因此也被視為“文化轉軌與文化解放的開路先鋒”[16]。其次,當圖像時代來臨時,網絡文學又讓位于各種圖片文化。比如各種表情包風靡網絡媒介,視覺化的表情包以最迅速、最直觀、最形象的方式傳遞著發送者的感情、心理、個性。再次,直播以及短視頻的興起又讓圖片比如那些表情包退出“小我”表達的時尚圈,因為圖片給眾人的小我感似乎還不夠。“小時代”中的人們對“小我”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文字與圖片都是借助外在于我自身的媒介,它們與“小我”始終隔了一層。最終,“我”便直接用自己的身體親自登場,開直播、錄小視頻,我的身體就是我的小世界的最好感性代言。因為身體不同于文字和其他圖像,身體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復制性,即便是同一個人的身體也很難做出兩次一致的身體動作。所以,當人們將自己的身體作為展現和表達自我的語言時,“小我”被塑造到近乎極致的狀態。
(二)身體在狂歡之中淪為能指的空殼
“抖音”正是“小時代”最新代表物之一。它最初火起來是源于各種各樣配著音樂的身體舞蹈,諸如海草舞、拍灰舞、喵喵舞、開車舞等新奇、時尚的舞蹈。這些舞蹈表演者以自己的身體為媒介,借著電音、舞曲配樂短時間內爆紅網絡,引發眾跟風模仿,呈現出一種集體狂歡。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青年研究者往往泛用、濫用巴赫金意義上的“狂歡”來描述“抖音”文化現象,筆者在這里所使用的“狂歡”僅從其字面含義也即縱情歡樂角度而言。因巴氏“狂歡”的特性,尤其是“顛覆等級性”在“抖音”中表現得并不醒目,相反“抖音”文化之中始終隱藏著等級的建構。
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an animal symbolicum)”,“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17]43。身體符號作為視覺時代的“時尚符號”,在使用中走向了能指的狂歡。這種能指的狂歡一方面體現了言語(2)活動的迅速生產,能指的消費。例如,“抖音”視頻中曾經火熱的一個動作橋段:逆天化妝,該視頻的第一個畫面是表演者穿著睡衣,睡眼惺忪。在配音響起后畫面隨之切換:表演者用一件衣服擋住自己并迅速將其甩開,而呈現在觀看者面前的對象立馬變得或楚楚動人,或帥氣時尚,可謂“顏值”忽然“爆表”。如果說該系列動作的首演者通過自己的身體,將某種青春活力,或人要靠衣裝、化妝等所指傳遞給觀看者。那么在該動作不斷地被大眾模仿,迅速生產出一系列的身體“言語”活動之后,這種個人性的身體言語不斷發生著“原初能指和所指的斷裂,發生了二度或三度能指的情況”[18]。身體動作的模仿于傳播過程之中淪為了形式意義和生理快感的傳播,而其所指則是貧乏性的,“因為其僅僅作為一種能夠使意義和快感在社會中流通的中介;作為對象本身,它們是貧乏的”[19]123。另一方面,這種能指的狂歡也反映出大眾對身體語言符號的外置(excorporation)過程,也即“每個人都有權在商品系統所提供的資源之外,創造自己的文化”[19]15。例如在逆天化妝系列視頻中有模仿者第一個畫面不變,但將甩開擋住自己的衣服的動作修改為抖動衣服欲找衣架掛著。這種結尾的突轉或不按套路出牌,超脫了身體動作所具有的最初含義,從而不斷帶給觀看者新的感官體驗和生理刺激。大眾的外置能力,將符號意義“見之于使用的方式,而非被使用的事物”[19]15,無疑加劇了身體語言符號能指漂移的過程。觀看者會在這些意料之外的能指中沉醉與發笑,意義在身體能指狂歡之中喪失或缺席,并最終將淪為能指不斷漂移的這一行為過程本身。正是不斷漂移的過程給觀看者帶來了新的感官刺激,滿足了其獵奇和娛樂化的需求。由此“身體作為符號的表達,其成了符號的器官或工具”[18]。
三、身體消費的悖論
消費社會中的身體在狂歡之中既是自由的,又是受束的。一方面,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運動后,“宗教與意識形態教條在界定、規訓、控制身體方面的權威性的削弱”[20],身體從靈魂束縛中走向了自由。另一方面,在消費社會中,“消費的邏輯被定義為符號的操縱”[21]114。符號無疑成為一位新神,身體作為當今消費社會的重要符號,也從實用地位走向了一場“氛圍”的游戲,也即將身體作為突出自己的符號而加以塑造與消費。由此觀之,消費社會中的身體又走向嚴厲甚至殘酷的自我控制與約束之路。
(一)身體在消費之中的自由與解放
在中西方社會中,長久以來靈魂可以說是一個中心(center)。解構主義認為中心“是一個絕對的或者說先驗之物”[22]15,是西方歷代傳統哲學建構的基石。解構主義所好奇的正是“如果這個中心被移除后會發生什么,結構會做如何改變”[22]15。而事實上,“身體在今天成為救贖之物,在這個意義上它取代了靈魂之中的道德和意識形態功能”[21]129。換言之靈魂這一中心已被移除,由于失去靈魂這一中心的控制,身體處于一種四處漂浮、游走的狀態,人似乎一瞬間一無所有;但轉而卻將自我存在的感覺完全歸之于身體,因為“至少身體好像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在現代世界中重建可以依賴的自我感覺的基礎”[20]。
在“抖音”大量的短視頻中,表演者紛紛以各種方式展現自己的身體,身體在“抖音”中是自由的。有健身房秀肌肉的,有穿著比基尼秀身材的,也有對著鏡頭眨眼賣萌的,當然,最時尚的方式是以舞蹈的動態形式來進行,各年齡層次的人群都加入到這場舞蹈的狂歡之中。在中西方文化中,舞蹈的文化意義最初都是近乎神圣的、沉重的。因為其作為人神溝通的中介,所要解決的多為關乎部族興亡的重大事情。李澤厚先生指出新石器時代的舞蹈紋彩陶盆上所繪的舞蹈“直接表現了當日嚴肅而重要的巫術禮儀,而決不是大樹下、草地上隨便翩躚起舞而已”[23]。如今的“抖音”中恰恰也流行過一段類似舞蹈,也是三五個人手牽著手一起跳舞,然而“抖音”中的舞蹈者,隨時隨地都可以翩躚起舞。盡管并排牽著手,似乎有了某種儀式之感,但這種動作行為本身的意義只是停留在行為本身所造成的視覺奇觀上——整齊劃一的舞蹈動作與青春靚麗的外貌。移除中心之后,身體在感性視覺的狂歡之中,是“典型的以形式之重,承載著精神之輕”[9]155。這種形式之重,也即形式的自由化,身體可以去做各種各樣的事,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呈現自己。這一看似自由的、我行我素的身體行為,有時甚至挑破了道德倫理的束縛,無論是對于視頻表演者而言,還是對于觀看者而言,都享受到一種極大的感官刺激和生理快感。本雅明指出“游蕩者”(flaneur)的形象:他們沉醉于四處游蕩所帶來的“動感凝視”,“游手好閑者屈就的這種沉醉,如顧客潮水般涌向商品的陶醉”[24]。而在“抖音”中,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位“游蕩者”。在一個接一個的身體動作中,人們的視覺不斷遭受著動態的震驚,不斷游蕩、陶醉在變換的身體動作形式之中。
(二)身體在消費之中的控制與約束
“資本已把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商品化了,包括人的身體乃至‘看’的過程本身”[25],在資本滲透之中的視覺文化之中潛藏著等級與束縛的內核。身體在不斷變換的形式之中看似獲得了一種最大的自由,但不得不承認人們在消費身體,給予其自由時,也在不斷束縛身體。身體在現代消費文化中如聚光燈一樣,聚集著看者的目光與凝視,造成一種集體圍觀效應,這一看的行為也將被看者推向了視覺焦點。但在看與被看之間,并不是一種對等關系,而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
實際上,“抖音”背后的看者絕大部分擁有“一雙男性的眼睛”。這種擁有并不意味著肉體上的具有,而是指心理上或文化上的擁有。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你以為自己在說話,其實是話在說你”[26],在男性話語規訓下,即使是一雙女性的眼睛也最終多少變成了一雙男性的眼睛。比如“抖音”中的那些獲得高點贊量的女性身體,大多“顏值爆表”,或青春洋溢,或妖嬈嫵媚,或苗條性感。這些身體形象正是男性話語中的理想身體,是男性不斷以話語權力去支配女性的產物。但在視頻的留言中卻不乏眾多女性人群,她們具有女性的雙眼卻對這些理想身體紛紛投出了羨慕和驚嘆的目光。換言之,她們也想變成這些理想身體,她們也幻想著自己的身體能登上舞臺的中央,享受眾人的凝視。現實中身體是天生的、自然的,然而在話語的規訓下,人們認為“身體不是自然生成的、固定的,而是可以改造的、可塑造的”[20]。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在按照社會話語權力所標舉的理想身體去改造身體。“如果說以往是‘靈魂包裹著身體’,如今則是肌膚包裹著身體……肌膚作為一種聲望的服飾與聲望的第二故鄉,成為符號以及時尚的參照”[21]130。“模式”或者說“理想身體”會讓人對自己的身體做出不斷地修改以求達到模式的標準,這不僅是對身體的控制和束縛,更是一種自我對身體的暴力行為,“身體在這一行為中簡直就是祭品”[21]143。“抖音”在給予人們一個身體自由表演的舞臺時,也潛藏著讓身體走進一間暴力牢籠的困境。對于“抖音”中每一個所謂理想身體的點贊及夸贊的留言,都將為未來的“身體暴力”埋下伏筆。總之,“消費社會既是關切的社會也是壓制的社會、既是平靜的社會也是暴力的社會”[21]174,“抖音”中身體的狂歡不僅是展現身體、表演身體的自由狂歡,更是一場控制身體和約束身體的狂歡。
四、審美的困境及出路
盡管“抖音”給予了大眾一個展現自我的舞臺,人人獲得了看似平等的表演權和觀看權,同時也促進了當下審美文化的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抖音”作為視覺時代的新興審美媒介,無疑將身體極力地推向了狂歡與消費之境。而這其中也潛藏著審美的困境:本來通俗、大眾的短視頻卻逐漸走向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化”。而且身體作為審美的對象和媒介,也在消費之中越來越走向自我控制和自我暴力的境地,淪為娛樂至上的奴仆。這一困境也是視覺時代與消費時代雙重疊加的產物,對其不能不做理性反思:“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27]。
(一)表層的審美化與娛樂至上
“當前我們正經歷著一場美學的勃興。它從個人風格、都市規劃和經濟一直延伸到理論”[28]3,但“不幸的是,在審美化標題之下,人們經常光是言及它的膚淺含義,而未能思及深層次的審美化”[28]4。當今的審美化更多的是在表層上進行,而且處處可見。大到店內精心設計的壁紙、桌椅、板凳等,小到商品包裝袋、商標、燈光色調等,都圍繞著美來進行。但這種美是最直觀的視覺注視下的美,這種注視并非凝神靜觀,而是處于動態游走之中。消費者所體驗到的美,來自生理的快感和感官的刺激。“抖音”也正是迎合了消費社會中的這種表層的審美化,身體在舞蹈中所流露出來的是肉體的感官刺激。正如許多“抖音”視頻的評論“看到你,我感覺戀愛了”“看到你的一瞬間,我連我們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糟了,是心動的感覺”等等所反映出的,這些觀看者對于美的判斷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生理快感層面。這無疑也顯示出“當代審美文化的低幼性”[15]254,其所提供給人們的正如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中的最低層次,也即生理需求。而今的消費者,其生理需求實際上在吃、喝層面多已得到滿足,但卻將生理快感作為新的“糧食”來消費,而這種“生理快感的饑餓”狀態實際上很難得到滿足。“中國當代文化的基本形態,是一種快樂原則的文化,一種欲望的文化”[29]316,快樂和欲望是交織在一起,彼此循環,互相促進的。所以當“抖音”以身體將這種快感引向狂歡時,人也陷入了追尋生理欲望的無底洞,而人們自我實現的需求與深層次的審美無疑將被娛樂至上所遮蔽和遺忘。
(二)技術崇拜與“三俗化”
“抖音”從最開始的時尚化、大眾化、通俗化,到如今卻逐漸與“快手”的審美模式趨同。“快手”視頻因其觀看者可以給表演者打賞“鮮花”“幸運星”“小金人”“666”等虛擬禮物,這些禮物可以變現。故在金錢的刺激下,“快手”視頻表演者往往做出“三俗”——庸俗、媚俗、低俗之舉。而“抖音”盡管一直未開通虛擬禮物這類讓視頻發布者賺錢的功能(3)。但其所采用的智能算法,卻也讓用戶發布的短視頻逐漸趨向于“三俗化”。該模式“就是利用編程技術解決信息如何實現精準分發問題的一種機制”,“使受眾便捷地獲得自己恰好想了解的內容”[30]。以“新浪微博”為例,其并非采用智能算法模式,只有所謂的“大V”才能獲得大量的關注。而在“智能算法”模式下的“抖音”,會給予每一位視頻發布者同等的推薦權。而且智能算法會根據用戶對視頻的瀏覽及點贊,自動為該用戶推薦該類型的視頻。顯而易見,“算法一直走在越來越懂你的道路上”[30]。但是智能算法是在缺乏人作為主體的情況下獨自做出的判斷,其可以判定人喜歡什么,但并不能判定人所喜歡的是否存在價值,是否健康。例如以智能算法著稱的“今日頭條”,在技術中立中忽視了人的監管,“旗下的‘內涵段子’客戶端軟件和相關公眾號因導向不正、格調低俗等突出問題被永久關停”[31]。智能算法下的“抖音”會越來越給受眾推薦滿足其欲望的視頻,而這些不斷被點贊的小視頻反過來又會刺激那些視頻表演者繼續發布此類視頻。由此循環導致短視頻逐漸走向了“三俗化”之路。技術崇拜突出了工具存在而忽視了人的主體性,“當人淪為物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時,毋庸置疑,這是一種非審美化的異化狀態。”[29]289
(三)出路:重申理性與因時而化
“抖音”審美文化的困境只是當代審美文化“感性泛濫”困境中的一個典型代表。這種困境說到底還是源自中心的移除。理性、靈魂、本質這些傳統意義上的中心之物,關聯著沉思之物,權威不再,由此“我們發現,取代沉思的,是感性、同步、直接和沖擊”[6]111。這種“直接、沖擊、同步和感性效果作為審美模式和心理體驗,將每一時刻戲劇化了”[6]118,這正是人類在失去沉思,感到生命之輕后所采取的措施。人們以不斷的生理刺激、感官高潮來狂喜狂悲,來承受生命之輕。然而“被一陣感性刺激的旋風裹挾之后,剩下的只有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6]118。如果不重新正視那些中心,這種由枯燥的日常生活到心理高潮的刺激仍會不斷循環。但恢復中心,重申理性,并不意味著像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無情地驅逐詩人那樣,“除掉頌神的和贊美好人的詩歌以外,不準一切詩歌闖入國境”[32]。若將“抖音”這類短視頻軟件一律強制關停,抑或只準許在“抖音”上發布傳統形式講述正能量與理性的作品,這都將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不能以審美匱乏來治療審美困境。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也有一代之媒介。重申理性的正確做法是因時而化,視覺時代這一大的語境并不可逆,但在這些不斷發生的新變化中卻能夠以新形式去重申理性,“創新是文藝的生命”[27]。同時政府應發揮好引導與監督職能,利用好“抖音”這類新興審美媒介,將傳統意義上的中心之物以新的方式,寓教于樂的形式去呈現(4)。讓“抖音”既百花齊放,又有真善美的引導,重申理性。如此,我們的文化也終將回歸正常之路,我們的審美也將走上促進人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康莊大道。
注釋:
(1) 本人選擇“小時代”而非“微時代”是從哲學思潮轉變、國家歷史進程角度來立論作為主體的“我”碎片化了。而學界對“微時代”的使用多強調的是客體,諸如文化的碎片化和細微化。
(2) “語言”和“言語”是索緒爾在其《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重點區分的一對概念,他認為前者是屬于社會的、重要的;后者是屬于個人的、從屬的和偶然的。
(3) “抖音”沒有打賞功能,只有收藏和喜歡、評論以及轉發等功能。“抖音”的打賞功能設置在用戶直播模式中,而非本文所討論的短視頻發布模式。
(4) 例如“四平警事”(四平市公安局官方抖音號),以娛樂形式做普法視頻,在抖音上發布88部作品共收獲5 024萬點贊,并吸引了1 071萬粉絲關注(2019年1月5日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