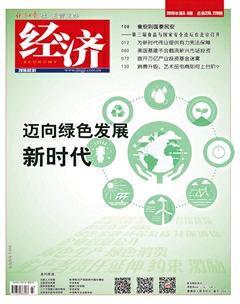狂歡下隱憂何解?

雖然產業投資基金發展得如火如荼,也能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遺憾的是,中國目前尚未形成真正的、可以任由產業投資基金發揮作用所需要的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和監管措施。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投融資研究中心副主任陳經偉的說法,如果按目前的趨勢發展,未來私募股權市場規模會越來越大,但純粹的產業投資基金規模會越來越小。
資金沉淀嚴重
據陳經偉介紹,目前產業投資基金的資金體量足夠,但真正按照產業投資基金的規定去投資,會有很多困難,最后基本都淪為投行業務本身。“如果這樣,產業投資基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我國設立的產業投資基金本應屬于金融行為,但目前卻慢慢成為了一種財政行為。“現在很多的情況是,假設今年國家發改委或者財政部設定了1000億的產業投資基金規模給某個省份,當某個省份拿到這筆錢又會平分給下面的地區,但實際下面的地區未必就有合適的企業適用這筆產業投資基金,從而造成資金浪費。”陳經偉稱。
還有一種情況是,“很多地方設立的產業投資基金并非缺錢,而是缺項目”。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說,目前各地政府引導的基金都會對投資地域和行業做出嚴格界定。比如地方會規定專項基金投資于本地企業的額度不低于總規模的80%,但除了深圳、江蘇等是產業發展聚集地區外,能夠符合國家產業投資基金政策的地區并不多,這就增加了一些地區尋找優質項目難度。“甚至有些政府將這些資金以借貸的方式放出去,或者干脆放在銀行里‘吃利息。”
的確,資金沉淀嚴重,也使得產業投資基金的意義本末倒置。在2015年底,中央財政設立的13項政府投資基金募集資金中,就有1082億元結存沒有使用,占基金總規模的30%。抽查地方6項基金發現,有66%的資金變成了銀行定期存款。
設立產業投資基金本意是撬動社會資本來參與產業發展,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比如PPP項目,還是存在明股實債、風險分配不合理等變相舉債風險。與地方政府發債相比,產業投資基金是要由一家金融機構建立,以股權的形式介入項目公司,參與施工建設,不計入地方債務。但目前的情況是,很多地方表面上是股權融資,不增加地方債務,但為了順利融資,地方財政多以土地出讓收入作為擔保,對產業投資基金回報進行兜底。
2015年6月,財政部在相關文件中嚴禁通過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將BT等項目包裝成PPP項目。在2016年6月底披露的《國務院關于201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被抽查的內蒙古、山東、湖南和河南等4個省份在委托代建項目中,約定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支付建設資金,涉及融資175.65億元;浙江、河南、湖南和黑龍江等4個省在基礎設施建設籌集的235.94億元資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益等承諾。在2017年,隨著地方債務的嚴監管模式,依托政府出資的產業投資基金進行明股實債安排,也被50號文明令禁止。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原研究員吳維海向《經濟》記者說,明股實債是通過系列文件部署,模糊股權和債權的界限,將債權包裝成了股權。而這種模糊情況的形成,在認定交易性質時會引發爭議。并且,如果明股實債被認定為股權投資,則投資人不能主張還本付息,得不到定期收益。
“而且,產業投資基金較其他收益產品來說,征信處于劣勢。因為傳統非標資產在征信方面的手段是抵押土地或者房地產等超過100%的抵押。而一般產業基金征信的措施多為被地方政府擔保或者投資公司母公司擔保,抵押物是項目本身。所以一旦出現經營失衡,很多企業存在道德風險,投資者將成為無辜受害者。”吳維海說。
特別是,“如果明股實債情況過多,會擴大地方債務,增加金融常規性的風險。”趙錫軍如是說。
發展條件欠缺
陳經偉表示,產業投資基金的本源是做一個長期資本投資和增值服務。但無論從融資渠道還是人才管理中,我國目前仍不具備產業投資基金良性發展條件。
陳經偉具體解釋說,由于我國產業投資基金發展緩慢,尤其在專業人才積累和實際操作經驗上,較國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產業投資基金在運作的過程,實際是在找對家,從而帶來更多1+1>2的格局,這其中對基金管理人的要求很高。基金管理人要有道德水準;要熟悉基金業務,有產業分析、企業分析的能力。“但目前我國產業投資基金人才具備這些能力的并不多,而人才的培養并非一朝一夕,這就制約了我國產業投資基金專業化的發展。”
另外,融資通道窄,也制約了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新時代證券副總經理潘向東表示,與國外相比,我國產業投資基金主要來源是包括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機構融資。而在國外,包括養老基金、保險基金、公司企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政府創業投資基金以及個人資金等,都是產業投資基金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而相對有限的資金難以滿足我國產業發展,還需要進一步引入大規模的民間投資進入產業投資基金市場。”
同時,產業投資基金發展的相關制度缺位加大了我國產業投資基金的風險。比如退出制度,投資方需要實現產業資本增值來獲取收益,而不是獲取實際控制權,所以產業投資基金在達到收益目標后要通過有效的方式退出。而我國主板市場存在嚴重的股權分置問題,法人股不能流通轉讓,這給產業投資基金的順利退出設立了障礙。同時,由于我國的產權交易成本高,產權交易市場也沒有形成統一,使得跨行業地區的產權轉讓難以實現。
趙錫軍補充說,目前還有很多人把PE、股權投資、債券投資基金弄混了,很多不具備投資資格的企業,也進入這個行業里面去,一些項目被搶得很厲害。實際這在根本上也違背了金融業是一個很高端、適當競爭的行業定位。“所以這個行業還需更多的機制,不能隨便注冊一個1000萬的公司就可以進入該行業。”
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認為,目前產業投資基金立法仍缺失。雖然從1997年,原國家計委曾草擬《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但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出臺正式法律法規。另外,由于產業投資基金涉及發改委、證監會、科技部多頭監管,致使行業投資領域和后續評價等存在差異,影響整個行業的健康協調發展。
調整體制盤活市場
雖然產業投資基金有一堆的問題亟待解決,但其獨特的優勢不可替代。那么如何解決產業投資基金發展條件欠缺的問題?
吳維海認為,首先國家要為產業投資基金放寬政策,要打破一些投資地域和行業的限制,比如不應該統一要求當地政府投資當地企業的額度不少于80%。要根據產業地區的活躍度情況來進行區別劃分。
其次,產業投資基金的主要目的還是以少量資金,通過杠桿效應撬動社會資本。而盤活政府投資資金的使用是目前的首要任務,比如地方政府自身不要過于謹小慎微。因為不難發現,較之一些市場金融機構,地方政府部門更在意資產的安全性,認可沒有收益,也不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風險。在滿足沒有風險的條件下,才考慮收益和國有資產增值的部分。如果地方政府能突破這一保守思維,才是盤活政府出資基金的前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投資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比較專業,但是在投新興產業方面,地方政府應該委托市場化機構來管理基金。由專業的團隊管理資金,產業投資資金的作用才能發揮最大化。
再者,產業投資基金只要投進去,就要考慮退出的問題。眾所周知,在美國,上市退出的渠道有紐約交易所、美國交易所,掛牌退出的渠道有納斯達克。但中國產業投資基金根據國情,除了可以選擇公開上市、兼并與收購,也可以選擇在較長時期內持有風險企業的股份獲得經營收益。“由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在一個較長時期仍處于世界前列,所以只要看準項目,股東也有能力長期持有風險企業的股份情況下,即使持有股份不動,基金也會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來收獲回報。這也可以認為是一條中國特色的產業投資基金退出渠道。”吳維海認為。
陳經偉最后補充說,我國未來的監管還要采取對金融工具差異化的監管規則。不能大而全,要小而精。并且,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僅有《產業投資基金暫行管理辦法》等法規是無法促進產業未來發展的,所以建議制定一部《產業投資促進法》。同時,還要有相關機制來優勝劣汰市場中的企業,促進行業良性發展。建立以產業為核心的金融投融資體系,為中國產業投資基金專業化的發展提供操作依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