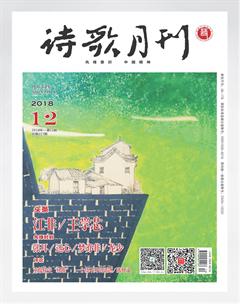山水之意(創作談)
江非
山水即自然。但這不是一個完全的真言判斷,只能是在象征或者是提喻的意味上方能如此言說。
中國的山水觀念主要完整于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所以,我們的“山水”之中必有仁、智,必有動、靜,必有時、空,必有道、德。
我把“山水”分為:原野的、荒野的、田野的和視野的。原野,給人的是時空形式。荒野,給人提供恐懼和敬畏。田野,給人的是勞動、生活和親和力。視野,給人的是景觀和觀念,是一個游覽、享樂、消費并可以拍照的對于“山水”的觀念性模仿和復制。借用馬丁·布伯的話來說,人在荒野中將稱頌“我和你”,在田野中稱頌“我和他”,在視野中稱頌“我和它”,在原野中.人,無言稱頌。或者,借用“主體性”這個觀念,“山水”有著被腹語、低語、話語和詞語所分割區別的四個層級。中國古典的“山水論”多是荒野的和田野的,是一種認識論和實踐性中的倫理學,不涉及本體論。因此,“山水”也為中國斷片、斑點和塊片特性的美學思想奠基。
現在人們所談及的“山水”,多是那種景觀性的“山水”。是一種“永恒復歸”話題下,生態社會學和地理經濟學的偽中國性和偽古典性。是資本變形性的最終影像生成。置身其中的人,已變成同樣具有資本性質的被支配和被交換物。這其實已是一片毫無“山水”的一片荒漠,一個不再揭示任何事物只有符號滑過的旁白。正如我們的當下生活中,那種既無真實判斷,又無真實評價和輿論,一種圍觀之下的純信息化的景觀性“微信”語言的自治——一種在語言本性的顛倒之中生成的話語暴力,和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新烏合之眾的即語式的“自意識形態”。這樣的“山水”僅是一種面具化審美的毫無生命連續性的瞬問姿態。
“山水”在中國古典詩歌中一直是作為三種質素而存在:本質、屬性、功能。李白有“本質”,王維有“屬性”,陶淵明有“功能”。列舉三句詩,分別是“黃河之水天上來”“清泉石上流”“悠然見南山”。以上三種,又分別是:語言在語言之中、語言在關系之中、語言在對象之中。其話語形式分別是:“是山水……”“和山水……”“像山水……”。蘇東坡是第四種,他說:“由山水……”,那是“我思故我在”出現在了山水的“形態”中,如“橫看成嶺側成峰”。
因此,山水即相遇,山水即臨即,山水即置身。
人在山水中。但山水之人不是無生命形式的赤裸之人,更不是生物學之人和牲人。山水以存在本身給人以唯一的生命與思維的純粹形式。山水即思。人思存在。山水即真理和自由用以沉默藏身的那個面相,來抵抗實在和人之話語喧嘩的那個面孔。山水即人回到面龐而與面孔的斗爭性分離。人來到“山水”之中,人投身于“面具一面孔一面龐一面相”這一例外運動之中。
世界上最大的山水是地球。比地球更具有極性的山水是太陽和銀河系。那么山水即是量子力學對古典力學的一種塑造,或者是古典力學對量子力學的一種顯現。山水即一種被拋人的深淵、孤獨和絕對的荒涼。以上所占對嗎?小對。那么,真正的山水即地球之圓和太陽之圓。山水即是“網”。山水即是王陽明和胡塞爾的“良知”和先天純粹邏輯形式。
孔子在山水之中,所以有占:逝者如斯夫;老子在山水之中,所以有占:天長地久;莊子在山水之中,所以有占:無極之外復無極。
山水:幾何學中的數與力。山水:時與空。山水:有與無。山水:身體。山水:屬與種。山水:康德的“范疇”。山水:莊子的“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山水:海德格爾的“讓思”。
山水,語占之無占:“道一德”的一致統——一個絕對事件的純粹形式;人之思維的原質。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能被人歷史的、經驗的把握的人類事件。
山水——“自然保護區”其實對應的是“罪犯一拘留所”“難民一收容所”“猶太人一集中營”。山水——“風景旅游區”則可以和“商品一超市”“面影一美容院”“墨點一微信圈”和“謊占一議會大廈”相互對應。
所以,我們的詩歌不能如此著急的去誤解“山水”。因為人類歷史并沒有已經走到黑格爾式的終結,人還小能變成歷史和政治學之中的無用之人。詩歌除了撫摸我們已經舒適的個體生活,也還需要干點別的。
所以,在目前說到“中國性”,它的核心還必須是“現代中同性”。它必須呈現“中國性”的實質:“易”的世界觀——時空同一往復共存,因而時問即為“空問一物質”;“道”的生命論——簡樸的邏輯自在主義,人同時活在前生,也活在來世,并非只是今世;以及“儒”的社會學——理想秩序集體主義——命名大道之名而取消自名,與大道同名。因此,“中國性”在此時只是一種方法論,只能作為一種方法用來反對社會的生物進化論、享樂主義的生命現世論、他人即陌路的世俗個人主義;是在反對人本主義、理性主義、功利主義、消費與消遣主義,反對所有單向性的“科學”“發展”“進步”“解放”“物”,以及“技術”“機械”“價格”“添加劑”“信息化”……從而按照“易、道、儒”的基本精神,以一種萬在共存的理念,在現世重新建立——人,并同時重建“知識分子”為大道而命名的“君子光暈”,以人之原初的澄明“致良知”,而達真正的“至樂”。從而消除人與物之問的盲目動力關系,把已經“邪惡”的“個人現世關系”重新引向天人關系、社會關系和歷史關系。那么“現代中國性”其實是把“南東往西”的對于西學的概念化看待,轉變為“南西往東”的西學對于“同學”的實質性相互理解與闡釋——是“獨善其身一默禱”、“以身作則一行動”的中國理念與“懺悔”“救贖”“超越”的西方思想相互對照。那么,西學仍是走向“中同性”的重要現實之路。“中同性”并小是指“唯一性”和盲眾性。
所以,“中國性”小能表象化。不能只是“易”的“爻”一符號化、“道”的“圖(陰陽)”一象征化、“儒”的“禮”一儀式化。詞語化的“小橋流水人家笙歌琴瑟”小是“中國性”。在“藝術一詩歌”范疇中,“中國性”的歷史使命應該是重建一種人與自身以及他物的語言關系和歷史話語結構,建立一種歷史的“語言—精神”關系。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一樣,詩在中國也經歷了三個發展時期:神學詩學、邏輯詩學和文學詩學。《詩經》并非是一部中國早期的“文學詩歌”選集,而是一部卦辭、神諭、禱詞、祭辭、釋夢辭選集,是神學詩歌的一個匯編。“詩:占,寺”,在詞源學上最早并非是“語言的神廟”,而是“神廟前的語言”,是中國最早的知識分子的代天代神之言。孔子的春秋詩學屬于邏輯詩學、修辭詩學和倫理詩學。文學詩學的出現是在西漢,在魏晉唐宋發展成熟。這時,“神廟前的語言”轉變為“語言的神廟”,人的認識論也由自然本體論轉向了歷史本體論,詩隨之進入到“誦詩以化民”的文學時代。這是任何一個民族的語言學與詩學協同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在此基礎上興起的唐詩宋詞,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小品美學,是對人的一種美學化的政治與歷史規圳。其中的文學制度即是語言制度,也是社會制度。“詩”從源頭或在本質上,在任何一個民族都是對于神秘意識和世界奧秘的闡釋,是對于時空和自我在神學和哲學上的首先認識。詩是對“是”的一個理解和對于先驗邏輯的純粹映現。這也是“山水”在詩中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