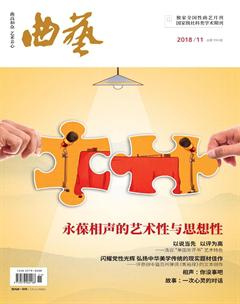文化雅韻與自覺自信
曲藝,它生于民間,長于廟堂,它孕育于先秦,萌芽于漢,興盛于唐宋,發展于元明清,在民國時期至新中國成立以來,曲藝藝術一直在努力發展和呈現這門藝術的魅力與輝煌。它的對象就是老百姓。曲藝與中國的老百姓有著天然的聯系,長時期的撂地演出,觀眾來與去,付費的多與寡,甚至付不付費的隨意性,使曲藝娛樂性強,收費低廉。古詩中描寫道: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從古時起,大地就是舞臺,人們稱它為民俗藝術,在雅與俗當中,人們把它歸于俗。
其實這種俗也挺美的。
但是在曲藝的曲種當中,有一種曲藝形式,被人們稱為雅韻的,它是評彈藝術。評彈為什么列入雅的行列中。這里請大家聽一首描寫評彈的詩歌:
芊芊素指輕輕撥動弦上的溫柔,
縷縷思緒編織出光滑的絲綢,
點點情感釀造成醉人的美酒,
吳儂軟語匯聚成涓涓細流,
千回百轉,蔓結腸愁。
聽到了,聽到了,
那個鮮活、婉轉的聲音,
從彎彎的石拱橋上走來了。
她走得是那樣緩慢,
讓數百年的時光徘徊猶豫;
她走得是那樣深遠,
像寒山寺的鐘聲一樣展臂;
輕喚亭樓,
她來得是那樣輕盈,
如密林深處飄落的一聲鳥鳴在行走。
看到了,看到了,
那個紅顏的女子的倩影,
鑲嵌在煙雨蒙蒙的閣樓。
竹為她修得一段奇俊,
水為她點染一片情柔,
石為她鑄就一方玲瓏,
茶為她捧來一縷清幽。
琴音穿過蘇州的古街古巷,
恰似水滴石穿的長久,
從古樸的瓦當間輕輕緩緩,
擊穿歲月深處郁結的凍層,
化作一曲評彈清音,
落入一顆顆期許滋潤的心頭。
于是我在想,所謂雅韻,應該有一種靜靜的美在里邊。
我們在聽名家講博大弘深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韻味潛在其中!
我查字典,雅,古代說文化高為雅。雅與文化是附在一起的。
2014年,我參加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文藝座談會,那一天習總書記大篇幅講了中國、世界的經典作品和他的體會。習總書記告訴我們:文化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精神與靈魂。文化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思想、智慧、價值和追求。
追隨文化,不是高調呼號的場面。文化帶給我們的不只是古樸或是時尚的嬌美,更多的是對生命的感悟。我欣喜地觀察到,在文化的傳承人隊伍里,如在一些大學的學習傳統文化座談會中的莘莘學子身上,我看到了一份無擾與對名利的淡薄,看到了對文化的崇尚和尊重。生命就應該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成長,去體會,去領悟。
馮驥才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說:文化,有高調的文化和低調的文化。高調為了生活在別人的世界里,低調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說:高調遲早會被更新鮮更時髦的東西取代,而低調,不會為大紅大紫而放棄一己的追求。它甘于寂寞,因為它確信這種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我曾經在很多的講座活動中,在不同的地點,在北京、在杭州、在牛津、在劍橋,聽名師講課、和同學們探討,學習中華傳統文化。記得在英國的泰晤士河邊,我向一些學者請教了有關于文化自覺的自我思考。大家說,這是一個不斷地覺醒過程。
前年,我與一些人在一起談起了文化自信,尋找文化自信的根基在哪里。今年,我高興地看到就是在一個月前,習近平總書記“7.1”講話,在三個自信的基礎上,“文化自信”的字樣躍然加入了這個隊伍。
探討文化不斷覺醒的過程,這理應是一個集體的公民意識,不能僅僅是一個國家意識或者政府意識。國家意識應該代表、影響全民意識,如果要讓整個國民都有了一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話,那就需要有一個很好文化自信的基礎。比如在大學舉辦的講座活動,就是這樣的園地。
我曾聽過一個故事:宋代有一個莆田人,叫鄭樵,寫《史通》的那個人,他說了一句話,叫“學術之末,日益淺進”,就是說學術的末端要不好好繼承的話,是日益淺白的。我們的現代文藝工作者需要對中華的優秀傳統好好研究與加以繼承。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文化發展歷史悠久,包含的內容也是豐富多樣,但文化的魅力在于有相同而能相融,更重要的在于有所不同,而能夠交相輝映,這正是文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