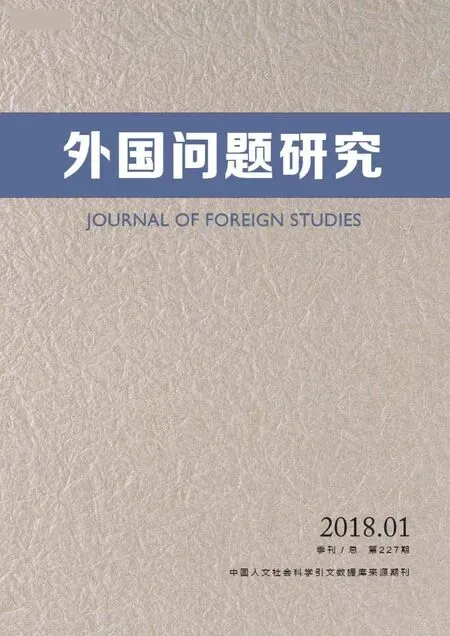日本對偽滿洲國殖民文化政策淺析
劉怡君
(1.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2.長春市圖書館 策劃推廣部,吉林 長春 130021)
一、控制輿論宣傳陣地
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中國東北之后,為了控制偽滿洲國的輿論宣傳,實行“泛日化”的殖民地文化,在偽滿洲國成立之始的1932年3月,便迫不及待地在偽滿洲國政府的資政局內設立了負責宣傳“建國精神”,普及“自治思想”,統轄偽滿洲國的輿論宣傳機構的“弘法處”。
1933年3月,日本為了強化殖民地統治的需要,撤銷資政局,將原資政局下設的弘法處業務歸并到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下設的“情報處”。掌管和控制偽滿洲國的輿論機構的“情報處”之所以設立在總務廳,是因為總務廳全部由日本人任職,是日本關東軍直接控制,監督偽滿洲國國務院的中樞機構。也就是說,偽滿洲國的最高統治者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日本關東軍司令官通過偽滿洲國國務院的總務廳對偽滿洲國實施“內部統轄”。
日本關東軍為有效地控制偽滿洲國政權,在日本關東軍內部特設立了統轄偽滿洲國的第四課,聽取偽滿洲國務院總務廳的匯報,并直接傳達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的旨意。因此,總務廳便成為日本控制偽滿洲國政權的中樞機關,掌管著偽滿洲國包括宣傳在內的各個重要部門的實際大權。而偽滿洲國總務廳“情報處”則是統轄偽滿洲國的“思想宣傳和情報收集”,①滿洲日日新聞社編:《滿洲年鑑》,滿洲文化協會,1938年,第442頁。控制偽滿洲國的新聞、出版、廣播等輿論宣傳機構,是偽滿洲國的輿論中樞。
偽滿洲國總務廳情報處不僅控制、統轄偽滿洲國的宣傳機構,而且編印所謂情報處機關報的《宣撫月報》(后改名為《弘宣》),以及《滿洲國概覽》《旬報》等印刷品進行直接日本殖民文化的宣傳和指導。情報處為擴大政治宣傳范圍,在地方的省、市、縣、旗各級組織設立情報機構,將觸角伸向了偽滿洲國各地。
1937年,日本又將情報處改建為“弘報處”,下設監理、情報、宣傳三個科。弘報處統攬著偽滿洲國輿論宣傳和文化的全部內容,與總務處下設的企劃、法制、統計、人事、地方等五個處共同構成了不可或缺的偽滿洲國的“中樞機關”。
1941年,偽滿洲國的機構進行改革,日本對弘報處的職能再次擴大,將原來其他部門對新聞、出版、廣播、通訊、監聽、文藝等的審查事宜,一律統歸弘報處管轄,成為一個帶有文化專制性質的政府組織。
1941年3月,由弘報處主持制定的《文藝指導綱要》出籠,成為日本對東北文藝實行專制統治的綱領性文件。其目的就是在偽滿洲國內,實施日本帝國主義嚴密控制下的法西斯主義殖民文化。至此,弘報處最終成為一個集新聞、出版、宣傳與文藝監管等職能于一身的文化殖民機關。
弘報處還通過偽滿洲國的映畫協會、演藝協會、文藝協會、出版協會、廣播協會等社會團體,對各個行業集中、壟斷進行控制。對此,“日本侵略者給這種文化專制概括了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叫‘官制文化’”。*孫邦主編:《偽滿史料叢書·偽滿文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頁。所謂“官制”,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法西斯主義殖民地的專制文化。
日本為擴大對偽滿洲國新聞報業的控制,1936年9月在偽滿洲國特成立了“弘報協會”,并對偽滿洲國的新聞界進行調整,以控股的方式對偽滿洲國的通訊社和主要報社進行控制。如中文報的《盛京時報》《大同報》,日文報的《滿洲日日新聞》《哈爾濱日日新聞》《奉天日日新聞》《大新京報》,英文報《每日新聞》,俄文報《哈爾濱時代》,朝鮮文報《滿鮮日報》等,并對未加入“弘報協會”的報紙進行整頓。
日本在對偽滿洲國輿論控制的同時,還對中國人民思想進行秘密偵察。在日本關東軍和憲兵隊中秘密下發的《思想政治服務要綱》中,要求掌握“民心動態”,并對“民心動態”“必須進行長期不斷之偵察”“掌握其真相”。*東北抗日聯軍編寫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編:《東北抗日聯軍史料》(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857頁。并設立“文化警察”,對不服從“教化”的中國人和所謂思想反日分子,進行嚴密監視,或以“思想犯”抓捕、關押。
特別是對學校的監視尤為嚴密,日偽特務機關在學校專門設立了秘密“稽查班”,監視教師、學生的言論和行動。很多教師、學生被莫名其妙地跟蹤、逮捕和屠殺。因恐怖政策和偵探網的實行,使家長們也不敢教育自己的孩子。
二、詆毀中華民族文化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關東軍立即組織了一個由漢奸拼湊的“自治指導部”,籌建偽政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搖旗吶喊。在“自治指導部”中的日本人指導員每人手中都持有一本《自治指導員服務心得》,“心得”強調:“對各種言論機關及集會等內部情況應特加注意,以滅絕排日思想”“對排日教材要斷然鏟除”。*姜念東等著:《偽滿洲國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4頁。
1932年3月,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后,在日本關東軍的授意下,發布“通令”“禁止東北各地懸掛中國地圖,不得用‘中華’字樣,不得使用中國教材”。“不許集會、游行、攝影、出版”等。*孫邦主編:《偽滿史料叢書·偽滿文化》,第10頁。對于體現中華民族思想意識的文藝作品、書籍、報紙雜志等宣傳品并以“反滿抗日”“低級趣味”等罪名嚴加取締和摧殘。
據偽滿洲國文教部統計,僅從1932年3月至7月,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在東北禁書650余萬冊。1934年6月29日,偽滿洲國民政部通令禁止包括我國關內的《大公報》《華北日報》《北京日報》《上海日報》及前蘇聯的《真理報》《消息報》等36種報刊輸入東北。此后查禁書刊種類逐年增加,查禁內容不斷擴大。*孫邦主編:《偽滿史料叢書·偽滿文化》,第10—11頁。
日本對偽滿洲國出版物的審查和控制更為嚴苛,1944年上半年被審查不予承認的就有170件,占總數的18.3%;被駁回的12件,所謂保留的177件,占總數的10.4%;*滿洲日日新聞社編:《滿洲年鑑》,滿洲文化協會,1945年,第435頁。被批準的出版物,其中日文占一半以上,而絕大多數為宣揚和歌頌法西斯殖民統治的宣傳品。
關于進出口的出版物,從關內進入東北的出刊物大大減少,而從日本進口的出版物卻逐年增加,比例相差懸殊,在多數年份中,“竟達到占東北當時進口出版物之80%乃至90%以上。”據偽滿洲國有關資料記載,在日本進口的出版物中,絕大多數是宣傳日本帝國主義所宣揚的“東亞共榮”“大東亞圣戰”“王道主義”等法西斯主義思想和殖民主義文化,以詆毀中華民族文化。
偽滿洲國時期,電影業也同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嚴厲控制。偽滿洲國監查機構規定,凡有損于日本政府、日本天皇、日本軍隊、偽滿洲國政權和具有反戰思想及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影片一律禁演或銷毀。“1936年,禁演的178部電影,其中涉及共產主義思想及所謂危及偽政權而禁演的有損于偽滿洲國形象的就有36部。1939年,列為禁演的43部,其中中國影片占第一位,有18部被禁”。*孫邦主編:《偽滿史料叢書·偽滿文化》,第12頁。與此同時,日本電影充斥整個偽滿洲國,僅1936年日本向偽滿洲國進口影片就有950件9410本,其中日本新興公司為31件2567本,日話公司為259件2104本,松竹公司為241件1922本,大都公司為178件1272本,ヌキノ公司為70件458本,極東公司為49件388本,太秦發聲公司為32件315本,PCL公司為29件227本,“滿鐵”公司為61件157本。*滿洲日日新聞社編:《滿洲年鑑》,滿洲文化協會,1941年,第417—418頁。此后,日本向偽滿洲國進口影片逐年增加。
日本為壟斷和控制偽滿洲國的電影事業,除抵制中國關內影片進入東北和大量放映日本影片,于1937年8月21日,在偽滿洲國首都“新京”成立了壟斷我國東北電影事業的“滿洲電影股份公司”。
1937年3月,偽滿洲國建立了“滿洲圖書股份公司”。1939年,建立壟斷東北圖書發行和圖書進出口業務的“書籍發行股份公司”。1943年,建立了控制整個東北出版事業的“出版協會”。
不僅如此,在偽滿洲國時期,日本殖民主義者為了宣傳、灌輸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并利用音樂消融中國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東北各城市的大街小巷彌漫著日本音樂。歌頌日本大和民族文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電影充斥大小影院。在整個偽滿洲國時期,日本法西斯文化籠罩全東北,泛濫成災,詆毀中華民族的文化,危害和摧殘著中國人民的精神。
三、宣揚“王道主義”政治
偽滿洲國建立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認為,要在偽滿洲國建立牢固的殖民地統治,“唯僅賴軍事行動,新興政府之施政,乃萬難成功,故必須使建國精神滲透于國民大眾”。*滿洲國通信社編纂: 《大滿洲帝國年鑑》,滿洲國通信社,1944年,第207頁。為此,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便以法西斯殖民文化為先鋒,控制偽滿洲國的文化輿論宣傳陣地,取締、摧毀中華民族文化,大力宣揚以“王道主義”、“民族協和”為主要內容的“建國精神”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殖民主義思想,消磨中國人民的反抗意志,建立起以日本大和民族為“核心”的“民族協和理想之地”,以“確保東亞之永久和平”,*山口重次:《民族協和運動と當面の課題》,《東亞聯盟》 1942年第8期。達到永久霸占的目的。
所謂“王道”,中國儒家認為,就是君王以仁義治理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在日本外務省編寫的《滿洲讀本》中,將“王道”解釋為,“一切人民之生活均得以保障”“開發求富,不為私有”和“盡使勞力為社會服務”。*外務省情報部編:《滿洲讀本》,東京:改造社,1938年,第29頁。《滿洲評論》主編橘樸在《王道理論的開展》中將其宣稱為,“王道即儒教所謂大同社會思想之實現,含政治之道理與財富之社會化,并藉此以保障民生,即經國大道是也。”*橘樸:《王道理論の開展》,《満州評論》第3巻第7號,1932年,第11—12頁。
但日本關東軍所說的“王道”,既不是儒家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代帝王所尊崇的“王道”思想,也不是日本御用學者所欺騙性的“一切人民之生活均得以保障”,“大同社會思想”的美化宣傳。而日本殖民主義者對“建國精神”內容中“王道”的闡述卻道出了侵略者的真實含義的詮釋。榷藤重義在他的《天照民族與世界維新》一書中說:“滿洲國之建國精神乃基于王道”,但“究其根本卻是始于皇道,此亦非吾輩妄言。回念建國初之皇帝《即位詔書》《回鑾訓民詔書》《日滿協定書》等,均已明確宣示日滿之不可分,天皇與皇帝之精神一體,滿洲國民之一德一心。故若言滿洲國之建國精神為王道,則此王道亦絕非古時中國儒者所倡議之王道,其與日本之皇道才堪稱為真正一體”。*榷藤重羲:《天照民族と世界維新》,東京:平凡社,1942年,第142—143頁。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和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在聯合發布的名為《滿洲國的根本理念與協和會的本質》的內部文件中直言:“滿洲國皇帝秉承天意,即天皇之意旨即帝位,以服務于皇道聯邦中心之天皇,以天皇之意旨為己心”。但是,“一旦皇帝違背建國理想不以天皇意旨為己心時,則將立即喪失其帝位。”一語道出了所謂“王道”,即為日本“天皇之道”,日本天皇之“意旨”。而“天皇之道”除法西斯侵略思想之外,亦包含著中國傳統封建之禮教。要求人們在封建禮教的約束下,達到“民族協和”“日滿一德一心”“實現王道樂土和道義世界為理想的天皇意旨”。*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66頁。
因此,日本殖民主義者極力推崇“王道主義”。在日本殖民主義者授意下發表的偽滿洲國《建國宣言》中,強調普及所謂“先王之道”的教育,以“實現王道主義”。
說穿了,所謂“建國精神”,就是以“王道主義”灌輸、教化國民,達到以日本人為核心的“民族協和”。因此,日本殖民主義者認為,要穩固偽滿洲國的殖民統治,實現“民族協和”“必須徹底普及王道主義”“傾注日本文化,排擠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彈壓赤化的侵襲”。*《現代史資料》(11卷),東京:みずず書房,1965年,第639頁。
1932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國東北“徹底普及王道主義”,成立了具有官辦性質的思想政治團體——“協和會”,偽滿洲國“執政”溥儀任名譽總裁,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任名譽顧問,偽滿洲國國務院總理鄭孝胥任會長。1933年3月,協和會制訂的《滿洲協和會會務綱要》指出:“滿洲國協和會根據王道主義,向國民徹底地普及建國精神,團結有明確信念之國民,排除反國家思想和反國家運動,以期建成民族協和理想之地”。“重建東洋文化,確保東亞之永久和平”。*山口重次:《民族協和運動と當面の課題》,《東亞聯盟》 1942年第8期。
“協和會”《創立宣言》指出:“本會目的在于遵守建國精神,以王道主義,牢記民族協和,以加強我國之基礎,宣化王道政治”。*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翻譯發行:《滿洲國史》(分論上),1990年,第124頁。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在其發表的《滿洲帝國協和會的根本精神》一文中也再三強調,“協和會”組織是與“滿洲國同時產生的一種國家團體”。
為此,不論從“協和會”的“宣言”、性質、宗旨,還是“根本精神”,都不難看出,“協和會”就是為宣傳“建國精神”,加強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偽滿洲國國家之“基礎”,“宣化王道政治”而成立的。由此可見,日本殖民主義者對“建國精神”的“王道主義”的宣傳、“教化”如此重視。
為了通過“協和會”組織“徹底普及王道主義”,大力發展和擴大“協和會”,控制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強迫人民群眾入會,要求一戶一會員。到1938年11月末,“協和會”計有省本部17個,市本部13個,縣本部76個,地區本部34個,分會3218個,會員1137883人。*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翻譯發行:《滿洲國史》(分論上),1990年,第168頁。1942年5月末,“協和會”在市、縣、旗、地區,本部已增加到189個,分會增加到4289個,會員增加到2894646人。*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翻譯發行:《滿洲國史》(分論上),1990年,第215頁。到1944年,“協和會”更加膨脹,分會增至5185個,會員達428萬余人,占當時全東北人口總數的14%以上。*王希亮:《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政治統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5頁。
“協和會”為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宗旨,大肆制造反動輿論,腐蝕與毒害東北廣大人民群眾。通過出版《滿洲協和會創立思想》《協和會的根本精神》等書籍和創辦《協和》《王道月刊》等多種刊物,對廣大的人民群眾進行毒害和奴化愚民教育。
1932年,通令全國各學校把有關黨義的學科及教科書一律廢除”,制定基于“日滿一體”、“王道大義”新的教育方針。從1933年開始,對原有的教材大加刪改和重新編寫。在重新編纂的教科書中,所謂“建國思想”、“王道政治”及“大同世界”等謬論幾乎無書不有。
日本殖民主義者的“王道主義”宣揚,深入到各個角落、各個階層,就連婦女也不放過。他們認為“男女協和,則國民力量雄厚,當然國家的效率也要增進。假如丟了婦女,則國民力量自然減少,而國家進展也要發生障礙,所以‘王道’政治丟不掉婦女”。
1942年12月8日,日本為穩固后方殖民地統治,更加強化了對殖民地人民的“王道主義”教育,指使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張景惠發布了《國民訓》。要求“國民須念建國淵源發于為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盡忠誠于皇帝陛下;國民須以忠孝仁義為本,民族協和,努力于道義國家之完成”“國民須舉總力,實現建國理想,邁進大東亞共榮之達成”。*《國民訓》,《盛京時報》,1942年12月8日,第1版。
日本殖民主義者企圖通過宣傳、鼓吹、灌輸、普及“王道主義”,麻醉中國人民的意志,摧毀中華民族文化,達到永久殖民統治的目的。但不甘屈服的中華兒女們始終不渝地與日本法西斯殖民文化進行著頑強、不屈不撓的抵制和斗爭,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捍衛中華民族文化的戰歌。東北作家羅烽、金劍嘯、舒群、蕭軍、蕭紅、白朗、梁山丁、王秋瑩、袁犀、梅娘、金音等一批文化精英,通過他們的文學作品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黑暗,隱喻光明,保衛著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表現出了堅定的民族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