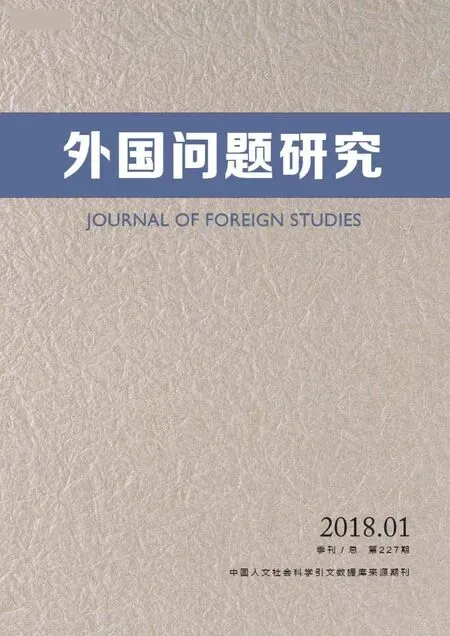以色列建國初期中東均勢安全戰略探析
蘆 鵬
(中國刑警學院 情報系,遼寧 沈陽 110854)
從國家對外關系領域看,猶太民族在1948年以色列國家獨立后,身處錯綜復雜的“三重”國際關系體系:即最外層是以色列與世界大國關系、中間層是以色列與中東域內大國(土耳其和伊朗)關系、核心層是以色列—阿拉伯世界敵對關系。1948年——1967年的三次中東戰爭時期是猶太民族實施以“生存權”為首要目標的國家安全戰略時代。由于這一時期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處于經濟封鎖,政治對立和軍事對抗的“全面戰爭”關系。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這樣的時代主題天然決定了以色列在中東地緣政治外交中可以施展 “能量”的空間和舞臺僅剩下“第二重”國際體系。建國初期,對于以色列在中東地區與“非阿拉伯”力量的外交關系問題,時任以色列臨時國家委員會憲法執委會主席的利奧·科恩(Leo kohn)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中的玄機:“以色列在中東地區與幾個非阿拉伯國家保持了積極良性的關系,這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來自阿拉伯國家方面的敵意,從而實現了戰略再平衡。”①Leo kohn,“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6, No. 3(Jul. 1960),p.330.
一、均勢戰略的內涵及實踐
所謂“均勢”(balance of power),從英文的字面意義上理解就是指“權力平衡”,即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試圖保持力量的平衡,以防止任何國家占據優勢地位。*李少軍:《國際戰略學》,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96頁。古今中外,“均勢”思想和策略源遠流長,古希臘城邦國家雅典和斯巴達的對峙,中國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三國時代蜀吳聯合抗魏,都體現了運用均勢戰略的理念。*李少軍:《國際戰略學》,第96頁。然而,“均勢”真正作為一種思想成熟,體系完備的“國際政治理論”或“戰略模型”是發展于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歐洲列強時代——三百年來,歐洲各國始終是以尋求國家利益的均衡來維持世界秩序,其外交政策以追求安全為目標。*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頁。
翻看近代歐洲國際關系史,歐洲大陸國際政治體系中出現了許多以軍事和政治聯盟為手段,以防止大陸霸權國家為目的,以戰略“均勢”為特征的各種聯盟或同盟,均勢外交戰略在這一時期可謂發展到了頂峰:1815年后,建立了神圣同盟、四國同盟。1833年東方三君主會議后形成了俄、普、奧三君主同盟。普法戰爭后,在法德關系中,結盟與反結盟的斗爭十分突出,成為國際斗爭的主要現象。隨著俾斯麥普魯士德國的崛起,歐洲大陸的均勢結盟外交進入了一個高潮期,比如1872年的三皇同盟及其1881年的恢復,1879年德奧同盟,1882年德奧意同盟及其1887年的續盟,1887年英、意、奧匈帝國的地中海協定,1887年5月西班牙語意大利協定,1887年6月俄德再保險條約,1887年12月奧匈、意、英的東方聯盟,1893你那法俄協約,1902年英日同盟,1904年英法協約,以及針對土耳其的巴爾干同盟。*李義虎:《均勢演變與核時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44頁。可見,無論是古代城邦國家對“均勢”策略的探索,還是近現代歐洲國際關系體系中對“均勢”理論和模型的升華、完善和應用,“均勢”戰略一直都是國家間處理關系,協調利益、平抑霸權、維持穩定的重要戰略手段。
均勢戰略目標的達成主要通過戰略結盟或戰略合作實現的。由于小國自身國力局限性導致的天然的安全脆弱性。因此,小國對聯盟承諾具有強烈的興趣,首先是為了軍事安全,通過制衡對立集團或者威懾侵略,聯盟增加國家的權力,因此節省了寶貴的資源。發展中小國可以因此更容易采購武器裝備,并維持一定的軍事能力。*韋民:《小國與國際關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96頁。在以色列建國初期,與土耳其和伊朗這兩個與巴勒斯坦問題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中東域內大國進行戰略合作正是上述戰略思想指導下的國家安全戰略實踐。
二、以色列與土耳其的秘密戰略聯合關系
如前所述,由于“均勢”戰略自古以來在國家關系領域都是一種平抑強權,維持戰略平衡的政治手段和外交藝術。所以,在1948年前后以色列面對整體實力強于自己的阿拉伯世界的軍事安全威脅之時,不惜一切代價獲得外部力量的支持成為以色列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任務。土耳其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世俗化的發展道路、親西方的戰略取向和非巴勒斯坦利益相關方的“超然”政治立場自然而然的進入到以色列領導層的視野,成為以色列建國初期在外交戰略領域重要的拉攏對象和借助力量。
總體來說,1948—1967年間,以色列與土耳其外交關系在雙方國家利益的相互需求的內部驅動力與外部地緣戰略環境的制約力共同作用下,呈現一種“二律悖反”的特殊狀態。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摩西·達楊”中東與非洲研究中心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奧夫拉·貝吉歐(Ofra Bengio)曾對以土戰略關系的特殊性進行過形象地比喻,他認為自以色列建國以來,以土戰略關系“表現出頗具欺騙性與迷惑性的‘雙軌制’戰略:一條是秘密的戰略軌跡,它始終存在,且表現得相當緊密和隱蔽;另一條則是公開的戰略軌跡,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低水平和缺乏實際影響力的。”*Ofra Bengio, 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p.3.
那么,如何理解以色列與土耳其在五六十年代存在的看似前后矛盾,表里不一“雙規制”戰略?事實上,奧夫拉·貝吉歐(Ofra Bengio)對以土戰略關系看似“似是而非”的判斷恰恰從本質上揭示了那個時代背景下中東地緣政治利益斗爭的殘酷性和以色列國家安全戰略環境的險惡性。另一方面,除了戰略環境的影響因素之外,對于以土戰略關系的分析也應當透過現象看本質:所謂的矛盾性和迷惑性是表象,僅僅是以土兩國在復雜的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下所采取的利益最大化的外交策略形式;而兩國戰略利益的相互需求才是真正推動兩國關系以秘密且隱蔽的方式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現實主義理論大師、美國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曾就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和行為的本質動機進行過深刻論述。他認為,國家對外關系都是權衡利弊得失的理性決策,“發展合作關系不是一方施予另一方的恩惠,而是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巨永明:《核時代的現實主義——基辛格外交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71頁。故而,從現實主義角度理解,以色列建國初期與土耳其構建的戰略合作關系依然符合“國家利益”原則。具體分析:
(一)從以土關系的表現形式看,以土戰略合作的迷惑性和欺騙性主要是指以色列與土耳其這一時期的戰略合作關系未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認,兩國戰略合作的主要手段都是秘密外交。
追根溯源,這是由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整個中東地區地緣政治格局這一大環境—美蘇爭霸和阿以沖突—所決定的,是雙方避免激化同阿拉伯世界和蘇聯勢力之間的矛盾而采取的“權宜之計”。采用秘密外交,拒絕將兩國戰略關系公開化的處理方式從根本上講,是符合以色列與土耳雙方的外交利益的。
首先,秘密外交僅僅是一種手段,以色列從土耳其方面秘密獲取戰略援助并不受到影響,如何從土耳其獲得現實的戰略利益才是以色列領導人考慮的重點。
其次,秘密外交充分考慮了土耳其伊斯蘭國家身份,解除了土耳其在中東地緣外交中的顧忌,避免阿拉伯方面的強烈反彈。
第三,與以色列合作可以幫助土耳其打通對于西方世界的交往通道,同時獲取以色列背后美國的信任和支持,提高土耳其在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影響力和戰略話語權,這符合土耳其建國以來融入歐洲,走西方發展道路的既定國策。此外,由于以色列在中東國際體系中,一直是作為長期抵抗阿拉伯激進國家的“重要力量”,同以色列發展戰略關系也有助于緩解土耳其在中東地緣政治體系中遭受的來自激進的阿拉伯國家的壓力和威脅。因此,綜合上述考慮,以色列與土耳其雙方以秘密外交的方式“低調”處理兩國關系符合兩國的戰略利益,是符合當時中東地緣政治大環境的明智選擇。
(二)從以土兩國發展戰略關系的根本動機上看,背后有著深遠的地緣政治考量,國家利益的相互需要是雙方發展戰略合作關系的根本驅動力。
在國家利益的眾多領域內,推動以色列與土耳其破除干擾、成功實現戰略聯合的根本性國家利益是二戰結束初期,雙方在地緣戰略方面有著相當程度的契合性。換言之,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中東戰略環境中,以色列和土耳其擁有的戰略合作“向心力”遠遠大于當時制約雙方接近的“排斥力”——阿拉伯與伊斯蘭因素。
首先,從以色列方面看,以色列建國初期,阿以矛盾主要體現為大規模的全面戰爭。由于阿拉伯世界近代以來落后羸弱,支撐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進行全面軍事對抗的戰略力量其實是“蘇聯因素”。因此,對于以色列建國初期的國家安全戰略而言,其實有“遠近”雙個威脅方向,“近”的直接威脅來自于拒不承認以色列生存權的激進的阿拉伯前線國家;“遠”的間接威脅來自于蘇聯東方集團。
其次,從土耳其方面看,30年代開始納粹德國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向東擴張侵的野心,南部高加索地區乃至中東事務越來越成為蘇聯國家安全戰略關注的重點。打通土耳其在其南部的戰略障礙,實現“南下戰略”是蘇聯這一時期突破德國封鎖,提升自身戰略能力的重要地緣政治取向。于是,在來自“北方”強國的戰略壓力下,土蘇矛盾不可避免:1939年9月,當土耳其外長蘇庫·索厄戈魯 (sukru Saracoglu)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要求土方采納一項旨在提高蘇聯關于博斯布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管理“話語權”的提議。*Suha Bolukbasi, “Behind the Turkish-Israeli Alliance: A Turkish View,”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29, No.1 (Autumn 1999),p.22.可見,土蘇圍繞“海峽問題”已經矛盾初顯。二戰結束后,蘇聯更是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進一步向土耳其施加壓力,并已經構成了對土耳其領土主權的現實直接威脅:“二戰后,蘇聯立刻從官方渠道照會土耳其要求參與控制海峽,并且要求從土耳其收回早在1921年友好條約中割讓出去的現已為土耳其東部地區的卡爾斯和阿爾達漢領土。”*Suha Bolukbasi,“Behind the Turkish-Israeli Alliance: A Turkish View,”p.22.總體來說,二戰結束后隨著蘇聯成為世界一極,土耳其北部受到的安全威脅開始不斷增強,“事實上,在這一時期內,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它對蘇聯因素的關注。”*Suha Bolukbasi,“Behind the Turkish-Israeli Alliance: A Turkish View,”p.22.因此,以色列憑借其自身獨特的戰略地位很快成為了土耳其地緣戰略中的重要伙伴。以色列自1948年宣布獨立之后,1949年土耳其就正式承認以色列的合法性,從而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個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之后兩國關系迅速升溫:自從土耳其承認以色列開始,兩國采取了諸多措施提升彼此關系——兩國商業貿易繁榮,開辟定期的空中和海上交通運輸路線,體育和文化領域雙方也交流頻繁。*Suha Bolukbasi, “Behind the Turkish-Israeli Alliance: A Turkish View,”p.23
(三)從以色列和土耳其這一時期戰略合作的主要內容看,以色列建國伊始與土耳其的戰略聯合主要是圍繞軍事領域展開的,由于軍事合作往往帶有極大的敏感性和保密性,這就不難理解以土關系會表現的“相當緊密且隱蔽”。
蘇伊士運河戰爭后,以色列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和武器封鎖,除了傳統法國軍事援助外,以色列還尋求獲得土耳其的援助。關于蘇伊士運河戰后以土軍事合作問題,以色列學者米迦勒·巴爾-祖海爾在其依據以色列建國之父本-古里安的口述史料而出版的研究著作《本-古里安傳》中,對于以土戰略合作給予了側面印證:
“1958年8月28日,星期四,本-古里安像往常一樣參加了每周舉行的總參謀部會議。那天傍晚,他的幾個得力助手來到他家;按助手的建議,他穿上了卡其布制服,這是他平時去視察軍事演習時的穿著。據傳,那天本-古里安要去內格夫視察新的軍事設備的秘密試用。那天晚上9點,一位國防部的助手來到本-古里安家并護送‘老人’上了車,但車并沒有像內格夫方向駛去。繞了一大圈后,車子從一個側面駛入了盧德機場。黑暗的跑道上有幾個人影,其中包括外交部長果達兒·梅厄和伊扎克·納馮。所有的隨從人員都爬上了一架在跑道邊已發動的大型軍用飛機、10點差一刻時,飛機起飛了;飛向了海上,然后向北飛去。就像兩年前一樣,本-古里安這次出行的詳情是一個嚴格保守的秘密,而且一直保守許多年。在這次旅行中,本-古里安要會見另一個國家的首腦并與之締結一項友好合作條約。”*米迦勒-巴爾-祖海爾著,劉瑞祥,楊兆文譯:《本-古里安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304頁。
由于本-古里安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力,其本人在其口述歷史中并沒有對1958年他秘密出訪國背景信息進行詳細說明。然而,亞美尼亞高加索-伊朗研究中心學者謝爾蓋·米納希安(Sergey Minasian)根據其深入研究,對1958年以本-古里安為首的以色列秘密高層代表團的出訪國身份進行了相關考證,他明確指出:“1958年本-古里安秘密出訪的國家不是別人,正是土耳其。這次行動正是以色列試圖打破阿拉伯國家對其邊界封鎖之舉,也是以色列構筑起號稱‘外圍聯盟’之秘密政治聯盟體系中的重要一環。”*Sergey Minasian, “The Turkish-Israeli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Iran & the Caucasus,.Vol.7, No.1/2, 2003,p.309.
(四)從以色列與土耳其戰略合作關系的實際表現看,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五六十年代以土戰略關系的基本特征,即“開局勢頭良好,后期齟齬不斷”。
以土關系的不穩定性和波動性特征非常符合上述以色列學者奧夫拉·貝吉歐就以土關系“雙軌制”戰略模式中有關“公開的”戰略軌跡的描述——“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低水平和缺乏實際影響力的。”*Ofra Bengio, 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rs, p.3.究其原因:
首先, 就良好開局而言,以土在五六十年代實現秘密戰略合作關系,根本得益于前面所述的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地緣政治動因,這里不再贅述。此外,猶太民族和土耳其民族悠久的歷史傳統友誼和雙方都選擇西方發展模式的身份認同也是非常重要的“隱形”促進因素。
一方面,猶太民族與土耳其民族擁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友誼,雙方關系史上不存明顯的民族沖突和歷史積怨。有歷史記載,在整個漫長黑暗,且充滿反猶主義傳統的中世紀歐洲,“奧斯曼人始終敞開大門,收容了那些在基督教歐洲國家備受迫害而逃難至此的猶太難民。接下來,猶太人對帝國的繁榮做出了貢獻,至少在早先的年代里,猶太人一直對奧斯曼帝國保持忠誠”。*Ofra Bengio, 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rs, p.72.這為以色列建國初期雙方迅速開展戰略合作關系奠定了堅實的民間心理基礎,創造了充分的政治輿論準備。
另一方面,以色列建國之初就確立了西方議會民主制度,并在國家發展方向上堅定遵循西方模式。這些都賦予了以色列作為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重要盟友的戰略地位。于是,這對于自凱末爾改革之后將世俗化和民主化作為重要國策的土耳其而言,以色列對自由民主價值的認同和對西方國家身份的定位無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認同感。某種意義上看,以色列作為西方國家的一分子,它為同樣持有民主與世俗化價值觀的土耳其提供了一條通往西方文明的“橋梁”。因此,國外有學者從“身份認同”的角度出發,以建構主義的視角對以土戰略關系進行了富有意義的評論:“土以友好關系是自然發展而來的結果,原因在于它們同是中東地區民主的、世俗的和非阿拉伯國家。”*Bulent Anas,“The Academic Perceptions of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 No.1(Spring 2002), p.8.
其次,就后期兩國齟齬不斷的外交關系而言,主要原因還在于土耳其方面。這是因為:以色列建國初期與土耳其相比,實力差距懸殊。換言之,兩國實力的巨大差別導致兩國彼此利益需求的失衡性。以色列處于相對弱勢一方,對土耳其的戰略需求較多;土耳其屬于相對強大的一方,對于以色列的戰略需求較少。冷戰時期,處于阿拉伯國家軍事包圍中的以色列對于土耳其的戰略依賴性明顯強于土耳其對以色列的戰略依賴,“以色列做了可能增強與安卡拉之間關系的幾乎一切努力。”*Ofra Bengio, 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rs, p.3.然而,一旦中東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危害土耳其自身利益和不利于土耳其繼續對以色列保持積極立場的重大變化,土耳其往往會毫不猶豫地在公開的外交層面轉變對以色列的態度。這背后最根本的制約因素就是阿拉伯因素。由于土耳其身為伊斯蘭國家身份,在對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外交關系中,土耳其實際上處于“兩難困境”。所以,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盡管土耳其把以色列看作中東地區的重要的戰略資產和對付周邊激進國家的潛在平衡力量,但是它不希望因為耶路撒冷的友好關系而將自身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至于危險境地。”*Ofra Bengio, 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rs, p.2.
由此可見,國家實力的大小決定了自身外交靈活性和主動性的多寡。總體上,以色列與土耳其關系具有天然的不平衡性。土耳其掌握了較多的戰略回旋空間和主動權,以色列基本處于被動應對的地位,“幾乎所有推動以色列與土耳其發展關系的促進因素都來源于以色列方面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講,以色列與土耳其的關系走向完全依賴于土耳其的善意態度。”*Ofra Bengio, 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rs, p.3.隨著1956年以色列聯合英法發動對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爭和1967年爆發了以色列主動突襲阿拉伯國家的“六五戰爭”,中東地區乃至國際社會掀起了抗議以色列侵略的浪潮,土耳其針對以色列的外交立場發生了明顯轉向,以土戰略合作關系從六十年代后期開始進入了低潮期,但依然以一種“低水平”的秘密地方式持續向前發展:“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1967年六月戰爭和1973年的十月戰爭中,土耳其在軍事上嚴守中立,沒有派軍隊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任何一方。戰后,土耳其依然頂住了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強大政治壓力和斷交要求,繼續保持了與以色列的外交關系”。*Ofra Bengio, 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rs, p.74.
三、以色列與伊朗的秘密戰略聯盟關系
從近現代國際政治理論和外交安全實踐來看,相對于大國而言,由于小國具有的安全資源有限,對外部安全環境又異常敏感,出于規避風險,增加戰略籌碼的考慮,小國在外交安全戰略中多傾向于“多邊外交”模式。從以色列的國情出發,建國初期的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是非常典型的“小國”,其中東地區均勢安全戰略中,除了土耳其之外,盡可能多的吸收其他域內大國加入伙伴關系,則是快速提升自身實力,短期內增強國家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由于小國外交的政策目標往往是追求生存風險的最小化,大國尋求的則是發展和戰略利益的最大化。*韋民:《小國與國際關系》,第239頁。因此,從以色列與伊朗的各自所處的國際體系地位不同和擁有的戰略資源的較大差異的層面分析可知:由于阿以長期中東戰爭和沖突的存在,中東地緣政治環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存在較大的波動性和風險性,這些綜合性變量因素天然地決定了作為小國的以色列與作為中東地區大國的伊朗兩國關系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總體上看,以色列與伊朗戰略聯盟關系的歷史發展進程呈現出“前期試探磨合,后期密切合作”的波動性特征。究其原因,關鍵在于以巴列維國王為首的伊朗決策層能夠以伊朗國家利益大局出發,審時度勢地克服阿拉伯方面的強大阻力和干擾,對以色列戰略價值予以重視和利用,巧妙實施一種“道義上譴責批評,實質上聯盟互助”的實用主義外交策略。
(一)以色列建國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與伊朗的初步政治接觸
對于以色列建國初期的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來看,在面對與以色列發展關系的第一道障礙“阿以沖突”問題上,伊朗實施的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外交策略,即從宗教感情和當時的阿以戰略力量對比態勢出發,對于以色列持有一種帶有明顯傾向性的謹慎回避態度。換言之,就是在外交道義方面支持阿拉伯國家維護巴勒斯坦主權的正當要求,對待猶太復國主義持批評立場;然而,在事關以色列生存和安全的猶太移民問題方面,又對以色列秘密保持“積極”“友善”的態度。
一方面,從兩國關系發展的消極方面看,伊朗在以色列建國問題上最初持不支持的態度。根據當時英國向聯合國提交的建議和要求,聯合國于1947年5月15日成立了由加拿大、瑞典、捷克斯洛伐克、伊朗等11國組成的“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其任務就是到訪巴勒斯坦,實地調查巴勒斯坦阿猶沖突,并對美國和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進行征詢,以獲取證明材料;如果可能,將就巴勒斯坦的未來命運向聯合國大會提交報告。*“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1947年報告” [EB/OL].http://www.mideastweb.org/unscop1947.htm,登錄時間:2017年5月22日。作為一次展示伊朗外交能力和擴大本國國際影響力的絕佳機會,巴列維國王當時委派時任伊朗聯合國大使納斯魯拉·因提扎姆(Nasrollah Entezam)作為特別委員會的伊朗代表,并在調查結束后聯合印度和南斯拉夫共同提出了旨在成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阿拉伯-猶太聯邦制國家的“少數派”的報告。而委員會其他多數國家提出“多數派”報告則表現出了更加親猶的政治立場,即主張“就目前的形勢下,英國應當結束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分別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阿拉伯國家和猶太國家,并成立經濟共同體。”*“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1947年報告”,登錄時間:2017年5月22日。與主張巴以分別獨立建國的“多數派”報告相比,顯然伊朗此刻在聯合國外交舞臺上的公開立場是傾向于反對在巴勒斯坦出現猶太國家的。1947年11月聯合國分治決議投票時,伊朗依然以反對票表明了自己在巴以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
另一方面,從兩國關系發展的積極方面看,伊朗在關系以色列核心利益的“猶太移民問題”上又大開“綠燈”。從歷史上看,早在巴勒斯坦殖民時期,伊朗就因“猶太事務”與猶太復國主義產生了某些聯系。二戰時期,歐洲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在巴列維國王的許可下在伊朗境內開設了猶太辦事機構——“艾瑞澤以色列辦公室”( Eretz Israel Office)。面對歐洲戰火和納粹大屠殺的嚴峻形勢,該辦公室猶太官員的主要任務就是協調與伊朗當局的關系,并發展同伊朗當地猶太社區的關系;同時,猶太辦事機構還在伊朗的協助下,積極將那些曾經接受過安德斯將軍及其領帶的波蘭抵抗力量(General Anders’brigades)協助而逃亡至蘇聯的波蘭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Middle East Journal, Vol.39, No.2 (Spring 1985), p.294.從二戰結束的1945年到以色列獨立的1948年間,伊朗境內的猶太辦事機構的行政官員開始越來越多的被以色列摩薩德特工所取代,他們日后的核心任務就是處理與伊朗當局的關系,并安排耶路撒冷的伊朗領事官員與猶太辦事機構的代表進行會晤。盡管雙方早期的聯系是零散的,不具有實質政治意義的,*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294.但是對于以色列建國后兩國關系的開啟仍然創造了一個良好的開局。
可見,就以色列獨立前后中東戰略環境來看,這一時期伊朗針對以色列“明拒暗合,謹慎中立”的微妙態度顯然有著深刻的地緣政治考慮:當時“阿強以弱”,猶太民族在阿拉伯國家攻勢下“命懸一線”,面對阿以沖突前景尚不明朗,以色列國家命運前途未卜的戰略“不確定性”,伊朗針對阿拉伯和以色列實施“平衡外交”的戰略決策是最符合當時伊朗的國家戰略利益的“理性選擇”。
(二)以色列建國初期以伊關系迅速升溫
盡管伊朗在以色列建國問題上曾表達過支持阿拉伯方面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公開立場,但從日后伊朗與以色列戰略關系的發展軌跡看,伊朗當年在巴勒斯坦分治問題上的“反猶立場”僅僅是伊以戰略關系發展進程中的次要矛盾和支流;真正推動兩國戰略盟友關系最終實現的根本因素還是在于那個時代條件下兩國具有戰略合作的根本利益動機,即以伊關系如何波折,“塑造以色列與伊朗兩國利益聚合性的地緣政治邏輯是長盛不衰,歷久彌新的。”*Sohrab Sobhani, The Pragmatic Entente: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1948—1988,New York: Praeger, 1989, p.170.如前所述,伊朗與以色列由于自身戰略地位的互補性和彼此戰略價值的互助性,一旦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發生變化,制約伊朗與以色列接近的外部不利因素消退,伊朗必然會按照自身戰略利益為出發點去處理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系,伊朗與以色列關系迅速升溫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以1948年戰爭為重要時間節點,標志著以伊兩國關系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具體分析如下:
1.伊朗方面
第一,身處阿拉伯和以色列外交夾縫中的伊朗,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對待阿以沖突明智地秉持“超脫”的外交立場。針對阿拉伯方面以伊斯蘭宗教名義號召伊朗對以色列采取軍事行動的要求,伊朗持消極回避的態度。1948年10月下旬伊朗半官方的德黑蘭日報曾刊發了一篇評論,很好地反映了伊朗當時針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伊朗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聯合國基礎之上的,我們之中不會有人想去挑戰這個原則。在這場與以色列的沖突中,我們將把我們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至于第二位,不會踏足中東地區一個新的沖突的漩渦之中。”*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297.
第二, 1948年中東戰爭為伊朗觀察和認知以色列的軍事能力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戰爭的結局明顯有助于提升以色列在伊朗對外關系中的戰略地位。到1949年7月時候,阿拉伯與以色列停火協議已經全面鋪開,雙方軍事平衡基本實現;從形式上看,阿以停火協議結束了1948年戰爭并確立了以色列國家領土位置。*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292.可以說,1948年戰爭的獲勝使得以色列國家生存得以確立,國家實力也大大增強。這些由1948年戰爭所帶來的新的變化和新形勢無形推動了伊朗重新“審視”以色列對于伊朗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第三,由于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構成了伊朗外交關系體系中的兩個矛盾對立面,當以色列因這場戰爭受益匪淺之時,阿拉伯國家對于伊朗的影響力實際上在無形中遭到了削弱。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戰爭期間伊朗與阿拉伯國家就“猶太難民問題”的外交立場的矛盾和態度差異方面:一方面,伊朗作為中東傳統文明古國,境內生活著數量眾多的猶太人。阿以沖突中如何對待境內生活的猶太人,直接牽扯到阿拉伯方面的敏感神經。這場戰爭中,伊朗頂住了來自阿拉伯方面的壓力,針對境內的猶太人實施了保護和寬容政策:“在中東戰爭期間,伊朗沒有針對境內的猶太人社區實施任何限制措施,甚至那些潛入伊朗境內實施秘密活動的以色列特工人員也未受到任何影響。”*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297.另一方面,戰爭期間,伊拉克由于與以色列的戰爭而遷怒于本國猶太人,大批猶太人被伊拉克當局迫害。為了防止伊拉克猶太人外逃至以色列,從1948年10月開始,伊拉克駐德黑蘭公使便向伊朗當局施加外交壓力,要求伊朗封鎖邊境,禁止其流入伊朗。這項來自伊拉克的外交要求最終在1948年底被伊朗所拒絕……盡管1949年中期德黑蘭當局迫于伊拉克更加強大的外交壓力而象征性的遣返了幾批伊拉克猶太難民。然而,這項措施很快就于當年9月在摩薩德特工和美國駐德黑蘭外交人員的共同游說下被伊朗當局廢除。*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p.299 —300.此后,更多的伊拉克猶太難民乘坐伊朗飛機飛赴以色列。
2.以色列方面
從宏觀層面看,伊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戰略價值賦予了以色列與伊朗實現戰略結盟的強大動力。傳統現實主義認為“當主要的行為體之間權利分配均等時,國際系統的穩定便可以得到充分保證,即出現‘勢力均衡’或均勢的狀態,這幾乎成為了國際關系中經典的恒等式。”*李義虎:《均勢演變與核時代》,第29頁。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以色列中東地區均勢戰略中,面對強大而敵對的阿拉伯國家集團,顯然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實力懸殊是巨大的,僅僅實現與土耳其的“較低水平”的秘密戰略合作還不足以從根本上扭轉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失衡的“戰略天平”;實現以色列“反包圍”“反封鎖”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更是無從說起。此時,作為雄踞中東地區東部的擁有數千年輝煌波斯文明的古國伊朗,無疑在以色列領導人眼中可以算作中東地區國際體系中的“重要一極”。因此,為了進一步增強以色列的戰略力量,加大以色列在與阿拉伯國家戰略對壘中的“權勢”,與伊朗發展密切的戰略關系將完成以色列在中東東部地區的重要戰略部署。從地緣戰略格局上看,以色列—伊朗戰略聯盟與前述以色列—土耳其戰略合作關系一起,共同構成以色列中東地區均勢戰略的 “東西兩翼”。
從微觀層面看,1948年戰中,以色列與伊朗在“猶太難民問題”的良好合作為雙方戰略關系發展提供了“抓手”。由于戰爭期間,伊拉克軍隊遭到以色列方面的沉重打擊,損失慘重。在高漲的民族情緒影響下,伊拉克境內開始出現許多迫害猶太人的事件。如何將這些猶太難民安全轉移到以色列成為當時以色列面臨的重大外交與安全難題。如前所述,伊朗對待猶太人的寬容態度使得以色列向伊朗方面尋求幫助成為可能。在營救伊拉克猶太人過程中,以色列事實上動用了包括摩薩德在內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戰略資源來對伊朗政治人物進行賄賂,這也是促使伊朗在此次猶太難民問題上積極幫助以色列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以色列不惜以“金錢”為誘餌,向伊朗實施“金錢外交”和“利益輸送”,以求換取伊朗對以色列新政府的積極態度:1949年3月,伊朗一個正式外交代表團訪問以色列,伊朗方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與以色列就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中被戰火損毀或被以色列沒收的100個伊朗人家庭財產賠償問題與以色列進行磋商……盡管這次訪問,事先沒有獲得以色列外交部的官方批準(也就意味著伊朗方面沒有正式承認以色列的身份),但是以色列為了獲得伊朗的承認而在賠償問題上盡最大限度滿足伊朗方面的經濟要求。*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301.
可以說,以色列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所展示的軍事能力,對伊朗展示的結盟誠意以及猶太人精明的外交手腕是推動伊朗改變立場,實現以伊關系迅速升溫的重要推動力量。
(三)五十年代開始直至伊斯蘭革命爆發,以色列與伊朗戰略聯盟關系發展定型
兩國關系經過以色列建國初期的試探和磨合之后,進入五十年代,中東地緣政治環境和世界格局的發生了劇變,以色列和伊朗各自國家安全戰略開始進行深刻調整,雙方戰略利益的交集進一步增加,伊朗對以色列的結盟愿望越來越報以積極回應的態度,以伊雙方進入兩國關系的“蜜月期”。直到1979年伊斯蘭革命巴列維王朝覆滅,雙方維持了長達近30年的秘密戰略聯盟關系。具體分析如下:
1.從伊朗方面看,蘇聯威脅因素急劇上升是促使伊朗考慮與以色列結盟的首要原因。隨著二戰勝利,蘇聯成為全球格局中的一極,蘇聯以伊朗為戰略支點南下中東的戰略需要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雙方此時在國家安全利益上的“零和博弈”最終以1946年“伊朗危機”形式爆發出來:按照美蘇英在二戰期間達成的協議,美英兩國于1945年9月率先在伊朗完成撤軍行動。而此時的蘇聯,為了達到控制伊朗,實現“南下戰略”的目的,不僅沒有撤軍,反而進一步加強其在南部地區的軍事力量。到1945年12月中旬,蘇聯利用軍隊和秘密警察力量在伊朗領土北部靠近蘇聯邊境地區扶植了兩個親蘇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阿塞拜疆人民共和國”( Azerbaijan People’s Republic)和“馬哈巴德共和國”( Republic of Mahabad)。*George Lenczowski,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 Middle Ea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7-13.五十年代,隨著赫魯曉夫上臺,蘇聯與以色列關系開始惡化,蘇聯中東政策由40年代時期的支持以色列轉向50年代開始支持阿拉伯國家;以色列也開始進行外交戰略調整,越來越表現出親西方的態度。*Gawdat Bahgat,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the Jewish State,” Israel Affairs, Vol.11, No.3(July 2005), p.518.從巴列維國王的角度來看,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以色列親西方的對外戰略調整讓其看到積極發展與以色列戰略聯盟關系有助于伊朗抵御蘇聯在中東地區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地區影響力。*Gawdat Bahgat,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the Jewish State,” p.518.
2.從五十年代中東地區局勢看, 1952年埃及納賽爾革命和1958年伊拉克七月革命掀起了阿拉伯民族“反帝反霸”民族主義高潮,這給親西方的以色列和伊朗造成了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促成兩國進一步接近。由于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中在埃及納賽爾的帶領下,阿拉伯國家第一次取得了抗擊英法以西方集團的勝利,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深深地影響了阿拉伯世界的團結和對外政策:1958年敘利亞與埃及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彭樹智:《阿拉伯國家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4頁。在埃及和敘利亞合并之時,伊拉克和約旦緊隨其后,與當月14日發表宣言,宣告兩國組成“阿拉伯聯邦。”*王鐵錚、黃民興:《中東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3頁。面對五十年代席卷中東的納賽爾主義思潮,以伊兩國“抱團取暖”共同抵御阿拉伯激進民族主義在中東地區的蔓延,這成為推動兩國實現戰略聯盟關系的最現實,最直接的政治動機。
3.從美國因素看,五十年代以色列與伊朗不約而同的先后成為美國中東盟友,戰略取向的相互認同和美國積極“撮合”,為以色列與伊朗發展戰略聯盟關系提供了強大的“粘合劑”。首先,從伊朗方面看,1953年堅持反殖民反霸權,積極推行石油國有化運動的民族主義摩薩臺政府倒臺。在美國支持下,重獲政權的巴列維國王不得不開始轉向親美國親西方的對外戰略。在伊朗對外戰略中,美國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快速上升對于伊朗改變過去的阿以“平衡外交”策略,轉而實施與以色列結成戰略盟友關系意義非凡。其次,從以色列方面看,與伊朗的情況相類似:早在1949年10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蘇聯擁有核武器之后,美國針對以色列過去在美蘇之間搞平衡外交的做法深表不滿。到1949年10月,隨著美國針對以色列“選邊站”的政治要求和外交壓力的不斷加強,以色列外交部不得不全面接受華盛頓的建議,與伊朗建立一種正式的關系成為支撐以色列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價值的意義所在。*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294-295.
4.從以色列與伊朗兩國領導人因素來看,本-古里安總理與巴列維國王就五六十年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兩國戰略安全利益的認知存在相當程度契合。這些是左右以色列與伊朗國家關系走向的重要內部主導因素。亨利·基辛格曾對領袖的個人政治影響力和素質的重要性提出了深刻且富有見地的看法,他認為“國際秩序的建立和維持歸根到底要由政治家來操控,包括對外政策制訂、外交戰略的選擇、外交策略的運用等。”*巨永明:《核時代的現實主義——基辛格外交思想研究》,第145頁。五十年代,面對風云變化的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以色列國父本-古里安以敏銳的戰略眼光和深邃的戰略思考,針對以色列對外戰略提出了著名的“外圍聯盟”( “peripheral pact”)構想。所謂“外圍聯盟”戰略構想,是指“以色列已經被由埃及總統納賽爾為代表的阿拉伯激進國家勢力所包圍,它們成為了蘇聯在中東滲透勢力的‘代言人’,并以摧毀以色列為最終目標。作為應對,以色列應當與中東北部非阿拉伯的伊斯蘭國家土耳其和伊朗,以及中東南部地區的非阿拉伯的基督教國家埃塞爾比亞建立一種三角同盟關系。”*Gawdat Bahgat,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the Jewish State,” p.522.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在五十年代提出的“外圍聯盟”構想得到了伊朗巴列維國王強烈共鳴和積極響應,他認為:“伊朗此刻也同樣需要抵御納賽爾主義者們和蘇聯在中東地區日益擴張的影響力。隨著阿拉伯團結呼聲的日益高漲,巴格達君主體制的垮臺以及伊拉克—蘇聯關系的迅速升溫,所有這些不利因素使伊朗越來越感到不安和孤立。鞏固同以色列之間的關系是應對這些挑戰的重要途徑。”*Gawdat Bahgat,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the Jewish State,” p.523.
5.以色列與伊朗在商業貿易和軍事安全等領域具有較大的互補性優勢,從伊朗方面獲得經貿利益;從以色列方面獲取先進軍事安全經驗為雙方維系長達數十年的高水平的“戰略聯盟”關系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利益基礎。以色列建國初期,由于阿拉伯國家的封鎖包圍,經濟崩潰,民生凋敝。與伊朗這樣一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且態度友善的地區大國發展經貿關系,滿足國家發展的現實經濟需求對于以色列生存同樣意義重大:以色列方面認為,在與伊朗發展關系中,經濟利益因素應當被著重強調作為刺激伊朗發展同以色列關系的重要驅動因素——以色列工業發展所需的產品和原材料,諸如水產品、肉類、蜜餞、農作物、毛皮、羊毛和毛毯等將為伊朗提供大量商機。*Url Bialer,“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301.為了在外交上應對伊朗巴列維國王即將于11月中旬對美國開展的國事訪問,1949年10月30日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就以伊經貿關系的前景制作了分析簡報,認為“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以色列無法從鄰國購買商品,以色列無疑將成為一個商品進口國家。與伊朗建立起經濟聯系有助于以色列進口自己想要的物資。以色列應當充分利用以上這些因素來促使伊朗與以色列發展關系。”*Url Bialer, “The Iranian Connection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1948—1951,” p.301.此外,以色列油氣資源幾乎空白,加之阿拉伯石油國家對以色列的封鎖包圍政策,伊朗作為世界油氣大國的戰略資源為以色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現實的解決途徑:在50年代前期,以色列就和伊朗簽署了石油供給協議,此后以色列一直積極與伊朗探討雙方的石油交易,并且取得了較為理想的結果;甚至在對阿拉伯世界造成重大災難的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后,伊朗也沒有停止對以色列的石油出口。*范鴻達:《波斯與猶太:民族和國家關系的演變》,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第35頁。
對于伊朗方面而言,以色列經過1948年和1956年兩次中東戰爭的洗禮,其所擁有的戰爭能力和豐富軍事經驗對于正在謀求伊朗崛起,實現“白色革命”的巴列維國王而言,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參考意義。在美國的鼓舞和撮合下,與以色列進行緊密的軍事安全合作,有助于提升伊朗的安全能力,符合伊朗此時的國家安全戰略利益:不可否認,五十年代當巴列維國王尋求以色列幫助伊朗建立和訓練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SAVAK)的時候,以色列和伊朗的關系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色列歡迎伊朗的主動示好,并派自己的情報機構“摩薩德”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聯合協作訓練“薩瓦克”。*Mansour Farhang, “The Iran-Israel Connection,”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11, No. 1(Winter 1989), p.87.
綜上所述,從1948—1967年,這二十余年是以色列與伊朗國家深化發展“戰略聯盟”關系的黃金時期,兩國關系無論在對外戰略還是經貿往來和軍事安全等領域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入合作,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地區雙邊關系發展的“典范”。
結 語
從1948年建國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突襲阿拉伯國家取得重大軍事勝利算起,建國初期的二十余年是以色列在阿以沖突中處于總體戰略防守的歷史時期。相對被動的戰略態勢決定了這一時期以色列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國家生存權利,防止以色列新生國家遭到阿拉伯世界全面戰爭的毀滅性打擊。這一時期,在以色列國父本-古里安的“外圍聯盟”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以色列縱橫捭闔,在紛繁復雜的中東地緣政治環境中不斷突破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干擾和壓力,在復雜艱難的政治利益博弈中,巧妙的尋找以色列與土耳其和伊朗兩個地區大國的國家戰略利益契合點。雙方國家安全實踐基本涵蓋了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與安全等諸多國家安全核心領域,成為牽引以土關系和以伊(朗)關系不斷突破障礙向前發展的強大內驅力。總之,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前的歲月里,以色列憑借同土耳其以及伊朗構筑起“地區聯盟”體系,為自身國家安全提供了強有力的地緣戰略支撐和安全保障,為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生存、發展乃至崛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