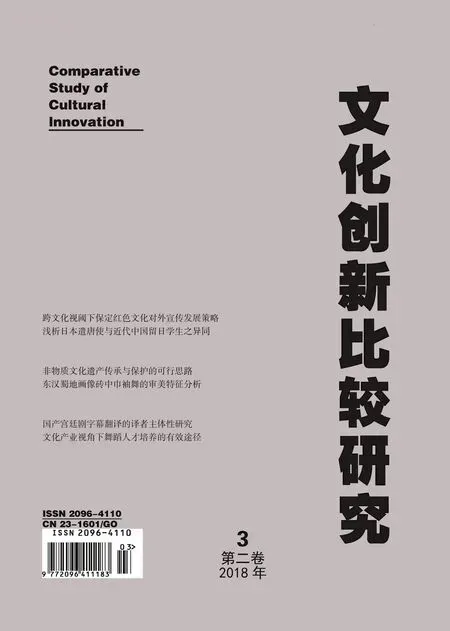《野草》中的生命哲學
2018-03-06 17:09:18王琬瓊
文化創新比較研究
2018年3期
王琬瓊
(山東大學,山東濟南 250100)
1 《野草》中的情緒轉變
《野草》堪稱魯迅大量的作品中最為異色的存在,就文辭來說,大量晦暗詭譎的意象,含混不清的象征性表達,“消失于無地”這樣陷于自相矛盾的話語,以及“水銀色焰”、“一切冰冷、一切青白”、“青白的兩頰泛出輕紅,如鉛上涂了胭脂水”,這仿佛帶著金屬質感的文字,正是最魯迅式的表達。
我將野草分為四組。
第一組中,《秋夜》作為《野草》的第一篇文章,為整個《野草》的夢——噩夢一般的——奠下基調。《野草》是一場噩夢,人們終將從噩夢中醒來,而后又復沉入噩夢,再醒,再做夢,如此循環。
《影的告別》影沒有歸處,影不被任何一方所接納,影亦不接納任何一方。“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會吞并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影認為自己不論去往哪里都將迎來終結,卻絕不愿拖累他的朋友,絕不愿“占你的心地”,最終獨自遠行。
《求乞者》主角不施與,也不祈求施與,不寬恕他人,也不要求他人的寬恕。末尾,“我將用無所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將得到虛無。”這又是極為魯迅式的闡述,《求乞者》中本是冷漠與麻木的循環,人與人之間沒有真誠,也沒有理解,只剩下瞞和騙。魯迅拒絕對這種虛偽的現象軟化,他“一個也不寬恕”,同時也拒絕寬恕身處其中,不自覺與之一同食人的自己,因而不要求施與,卻以這種不要求做消極的反抗,至少打破這冷漠的循環。縱然不能使“誠”多一點,也使“不誠”少一點,這樣的反抗,魯迅稱之為“與絕望搗亂”。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