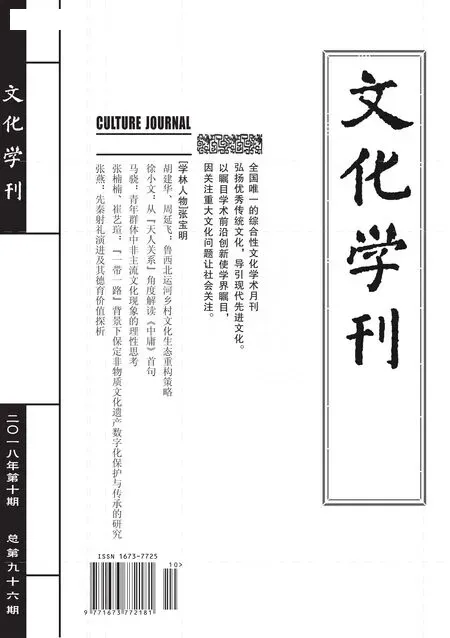康德哲學中的溯因思想研究
朱耀樺
(南開大學哲學院,天津 300071)
一、溯因推理的來源
溯因推理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時期,他曾在《前分析篇》中提出了一種“還原的推理模式”,但它當時并沒有被確立為一種邏輯推理。具體提出溯因推理這一概念的是美國的哲學家皮爾士。皮爾士最初將其稱為假設,而后更名為溯因推理,其溯因思想經歷了兩個階段的發展。
皮爾士早期主要從推理形式上對溯因推理與歸納和演繹推理進行區分,并沿用了亞里士多德三段論的形式。他認為,演繹推理是通過已知的規則和事例推斷出結果;而歸納推理則是從事例和結果推斷出規則的過程;溯因則是根據已知的規則和結果來確定事例的可靠性的過程。
二、溯因推理與因果性
皮爾士后期的思想,不再拘泥于三段論對推理的分類,而是將溯因、歸納和演繹這三種推理與科學探究的過程相關聯,分別對應假說的形成、評價和預言過程。溯因推理雖然是一個為結果尋求解釋性假說的過程,但皮爾士指出它仍是具備一定邏輯形式的推理,并將其定義為:“如果我們觀察到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C。并且如果A是真的,則A可能引起C。那么我們就可以通過溯因推理推斷出A可能是真的。”
皮爾士運用了逆向假言推理的邏輯形式,但在溯因推理中A與C的這種關系并非經典邏輯中的實質蘊含。在假言推理中,如果A→C,那么A是C的充分條件,C是A的必要條件,且非C是非A的充分條件。而在溯因推理中,我們可以用天下雨來解釋地為什么濕,卻不能用地沒有濕來說明天沒下過雨。溯因推理在形式上雖然相似于假言推理,但卻只具備其逆向的形式,其中A和C的關系具有非對稱性,且它們在時間上往往是相繼發生的,這也是因果關系的特性。皮爾士在利用三段論定義溯因推理時,也將其描述為根據已知的規則和結果來回溯解釋性假說的過程。內格爾也將其定義為:“假說推理(也稱為溯因,逆推法,假說),在于從一些事實或假說,推斷一個解釋、原因,后者可以作為一個假說的結果。”[1]
英國哲學家J·L·Mackie在The Cement of Universe中對因果性和充要條件進行了詳細區分,他指出:“一個事件的原因既不是它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條件。但它存在于該事件的充分非必要條件之中,并是其中必要不充分條件或非盈余部分,即INUS條件。”[2]通過溯因推理也可以看出,“因果關系具備不對稱性和方向性,而條件關系在邏輯上是沒有方向性和不對稱性的,或至少它不能窮盡因果關系的方向性和不對稱性”[3]。我們可以說,如果A是C的充分條件,那么非C也是非A的充分條件。但是當天下雨導致了地濕時,我們無法通過地沒濕來說明天沒下過雨,這也就是因果關系的非對稱性。可其在時間的方向性上卻面臨一個困境。如果通過原因發生在結果之前來判斷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那么就無法解釋火車頭拉導致火車跑存在的因果關系,因為二者在時間上是同時發生的。
為了解決這一困境,英國邏輯學家Von Wright提出了可控性標準的概念,他認為:“當兩個事件A與B中存在因果關系,如果我們不用B就能產生和制造出A,而B因為A而出現,即A是B的原因,而不是B是A的原因。”[4]但是很明顯,它只適用于我們可能進行實踐操作的范圍內,超出我們實踐范圍的事物,我們仍無法進行因果關系的判斷。那我們如何能把握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呢?
休謨曾指出:“因果被人發現不是憑借于理性而是憑借于經驗,但又不是僅憑經驗。”[5]“要論證思維的客觀真理性必須訴諸于實踐,而非理論。”[6]“例如火藥的爆炸能力并不是通過先驗論證所得出的。”[7]因此,休謨認為因果之間的必然聯系是無法通過經驗來證明的,因為“根據經驗得來的一切推論都只是習慣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結果”[8]。基于此,因果關系便失去了普遍必然性,因為他只是人們一種主觀習慣。也正是在休謨懷疑論的沖擊下,康德走出了“獨斷論的迷夢”。
三、康德對因果性的辯護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我們認識的對象其實是物自身刺激我們的感官所形成的現象,因果性是屬于認識主體的十二個先驗知性范疇之一。我們對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判斷其實是運用先驗的知性范疇把握經驗現象的過程。由此可見,我們認識的對象其實是我們自身感官所建立的,所以我們在此基礎上做出的判斷并不是缺乏理性的習慣。但知性與感性只有在圖型的中介作用下才能結合,康德在其“純粹知性概念的圖形法和原理體系”中指出,“要將先驗范疇運用到直觀雜多,就必須依賴于作為范疇與直觀的中介的圖型”[9]。要將先驗的知性范疇與物自體刺激感官所形成的現象相結合,就必須依賴于圖型的作用。康德認為:“當先驗的知性概念應用到每個可能的經驗時,它們的綜合是數學性的或力學性的。”[10]其中“范疇的數學性使用原則是一種絕對的必然和知覺的確定性,它包括直觀的公理和知覺預測。而范疇的力學性使用原則是一種間接且不自明的,僅僅具備一種推論上的確定性,它包括經驗的類比和一般性的思維公設”[11]。康德在經驗的類比中,對時間進行了三種樣態的劃分,即持存性、相繼性同時并存。其中,因果性范疇的運用則是力學性的,它將時間中的前后相繼作為圖型,因而因果性范疇在運用中所具備的確定性是推論上的,例如在觀察到“太陽曬而石頭熱”時,我們并未直接看到其中蘊含的抽象因果,而是通過兩個事件在時間上的前后相繼所做的判斷。康德在“知性純粹概念的先驗演繹”中也指出,“我們是通過知性范疇把握經驗現象的過程來形成知識的。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離不開理性的作用”[12]。
四、知性活動中的溯因思想
康德認為:“我們的理性是有因果作用的,或者說,我們至少是對我們自己把理性描寫為有因果作用的。”[13]他指出這種絕對的因果在知性范疇把握直觀雜多的過程中起到的是范導性作用,將知性的活動目標指向絕對化的超驗“絕對全體”。但理性并沒有直接參與到知性的建構中,而是使知性的建構沿著正確的方向最大限度地擴展經驗知識。康德認為這種傾向是人類的天性,它不會止步于得到任何東西而結束追溯的過程。例如,“物自體”這個理念并不是作為知識的建構而存在,因為我們并不是為了對物自體的本性進行探究和預測,它被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對知性范疇起到范導性作用,指引范疇的綜合統一沿著正確的方向擴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依然認為“物自體”本身是不可知的,因而理性的范導性規則是指引著我們為了認識它而不斷追尋,從而最大限度地擴展了我們的經驗知識,這也就形成了以絕對因果作為開端的因果鏈,其中包含了一段段的因果追溯。康德的“范疇的先驗演繹”已經蘊含了溯因思想,且他對因果性范疇的論證也相對最多。而皮爾士訴諸于“知覺判斷”這種“潛意識”概念為溯因推理尋找根據,受其影響也頗深。
皮爾士認為,“只有包含了普遍性的知覺判斷才能成為溯因推理的根據,并且沒有什么理智中的東西不是預先存在于知覺之中的。”[14]在康德的理論中,溯因的思想存在于知性把握直觀雜多的過程中而非知覺判斷,皮爾士與康德一樣雖然確定了因果關系的客觀必然性,并在因果性的基礎上將溯因確立為一種推理形式,但仍將溯因推理的根據訴諸于一種先天存在的“潛意識”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