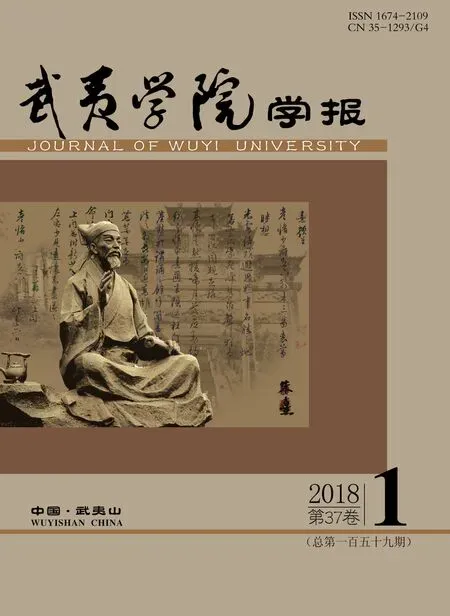泉州地方傳統藝術倫理研究
陳 佳
(泉州工商旅游學校 學前教育專業,福建 泉州 362000)
藝術是美的集中體現,倫理是經驗規范體系。雖一個有形,一個無形,一個偏直覺體驗,一個屬邏輯認知,但因兩者都來自人類文明起源的地方,且同作為以感性與理性統一為基礎的文化現象,藝術有從形而下層次的技藝、技術,逐漸提升為形而上層次的道德和教化活動的趨向,而始終維續著關聯。藝術作品被認為可以把抽象的原則轉化為具體的案例,較好地傳達道德洞見,升華道德情操和人生境界。正如羅斯金《藝術與道德》一書所言:“藝術曾經有或者將來會有三個主要的目標:第一,強化人類的宗教信仰;第二,完善人類的道德水平;第三,為人類提供物質服務。我敢斷定你會吃驚于我說藝術的第二個功能只是用來完善人類的道德水平,而通常認為藝術會毀壞人類的道德水平。”[1]相較于西方浪漫主義美學和分析哲學對藝術社會價值的孤立、狹隘的理解,中國文化中的倫理與藝術,似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相得益彰。中國傳統美學始終占主流的觀點“文以載道”“樂通倫理”,從本體論、認識論和審美論的角度,對美和善的深層次統一,藝術和道德在境界、評價上的高層次融合,進行了最堅定的辯護。福建省泉州市,因城郊清源山中之“虎乳泉”而得名,又有刺桐、溫陵的別稱。城市是文明的象征,每一座新城市都標志著一個文化新世界的開端。“世界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民族、國家、政治、宗教、倫理、藝術和科學都是以城市為基礎的。”[2]顯然,要充分挖掘泉州地方文化,就繞不開藝術和倫理的話題。鑒于藝術環境、本體與藝術本質有著顯而易見的同一性、整合性,本文即以文化廣角視野鳥瞰泉州地方傳統藝術倫理。
一、釋義
傳統,就是活著的過去,指一種時代相傳的文化體鏈,即圍繞一個或幾個被接受和延傳的物質主題而形成的不同精神變體的時間鏈條。在心理層面上,傳統藝術之所以長期受到人們的敬重和依戀,既因為人們在傳統藝術形式、題材、風格熏陶下形成的趣味使然。人們想到它的時候,常感到熟悉和親密,就像長久在外的旅客思念家鄉的歸心似箭的心境。更由于人類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在地方的傳統決定的。實質性的傳統藝術根植于中華民族深厚的倫理土壤之中,它所表達的生活智慧,具有令人敬畏和依戀的東西,散發著與現實事物相對立的神圣的感召力,對個體和群體行為產生了強大的精神推力。地方是地理、歷史和文化范疇的概念,指人類對某個區域的時空、活動,自然與人文條件的綜合認識。地方這個的自然、社會、文化、心理隔離物,使社會群體形成一個穩定的生產、生活、思維、情感方式的獨立活動方式。不同的地方,使藝術、倫理的名稱所指的事物都會大不相同。如果用布迪厄爾的“場域理論”來理解地方社會,它的邊界是經驗的,是社會分工的結果。一個相對獨立的地方社會空間具有獨立的邏輯和必然。邏輯型構上,地方,充滿斗爭又和諧統一,既是法律、宗教、政治、教化場域,也是美學場域、藝術場域、倫理場域。必然性上,如果一個地方的群體成員一再重復的情感、思維和行為準則和價值觀等,因場域中的自我和環境的特殊作用,都會異于生活在其他文化環境中的人們,且不同地方社會之間又發生著復雜的關聯。中國傳統的地方社會,與為了要完成更迭性和控制性任務而結合的現代法理社會不同,它是一種并沒有具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禮俗社會。生長于廝的藝術,不但是許多現代藝術的雛形,且意境極具美感,包孕了普世的價值與情感,持久的習俗形態和雅俗共賞的表現形式,道德教化和倫理規范,至今仍在給予現代文明以熏陶和滋養。不管人類如何標榜自身的獨立性和不可替代性,無論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或制度文化,以至于藝術和道德能相互作用,都無法從地方環境條件中根本地擺脫出來。德國學者F·拉采爾在1882和1891年出版的《人類地理學》一書,從社會學角度分析自然環境成分如何進入社會意義體系,論述了人類作為環境的產物,其活動、發展和分布受到環境的嚴格限制。自18世紀工業主義以來,歐洲哲學家們認為只有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才是健全社會的標志,將接近自然的地方文化環境,視之為抵御文明侵蝕的良方。心理學研究則將人的自我認同感與出生地、兒時的記憶、集體無意識等相聯系。美學界對藝術本質的探討中,無論是丹托的“藝術界”、韋茲的“家族相似”還是迪基的體制理論,或是維特根斯坦對藝術多維度的認識及丹納的“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說,其理論基礎也無不是把藝術設想成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的廣闊的文化語境。這里,文化,不是狄奧尼索斯式的非理性的世界,而是通過人的經驗自然而然地生成上去的。文化環境,特指文化系統產生與活動的背景,概念框架包括地理環境、歷史環境和社會環境,其結果是特定地方的人們獨有的自我認同、生活方式與思想氣候。
二、要素
地理環境是構架地方文化的第一要素。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因此,他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3]中國是一個地理疆域廣闊的大國,跨越了多個氣候地帶和生態環境。以胡煥庸用于劃分人口密度的“黑河騰沖線”理論作為地方文化的分區線,泉州所處的該線東部的文化屬性,是農耕、宗法、科舉和儒教的,早在南朝時候,學堂已很普遍。靈魂的上升,要愛智和愛善兩個階段。泉州人尊師重教,學校、私塾、書店隨處可見,戶戶“家有詩書”,自唐至清治學、中舉、入仕者數不勝數,可謂“滿街都是圣人”,又得“海濱鄒魯”之名。泉州又是交流、商業與異端的。泉州唐時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宋元時被稱為“光明之城”“東方第一大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因宗教資源多元豐富,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如今,泉州這座“東亞文化之都”正在融合中謀求著新的突破。同時,如后現代人文地理學理論認為的那樣,文化并非某種“超結構”而是一種共享的意義體系。在中國,中原的農耕文化、西北的草原文化、西南的高原文化、東北的森林文化、東南海洋文化,都是系統、動態與開放性的文化圈。因地理、歷史層面的邊緣性,文化中心在社會內擴張上,泉州成功克服了文化排他性,充分吸納了農耕、海洋和異域文化,成為閩南文化的發祥地。文化中心的跨社會擴展上,泉州又是港澳臺胞和東南亞華僑的重要祖籍地,文化影響覆蓋面大且深遠。
歷史環境是建筑地方文化的第二要素。在歷史標系上,一個泉州人實際上幸運、完整地經歷了如人類學者茲爾尼瓦斯所說“人類的成長需要的三次誕生”,即第一次是在本族文化中,受本地文化的熏陶而形成意識主體,第二次誕生于異族文化,學習外邦人的生活、思想、行為;第三次誕生,在現代文化之中,擁有了他獨特的文化擴展性和生命意義。泉州一直有著“海陸兼容”的地方文化特色,其一是,其古代文化以唐代為醞釀期、宋代為上升期、元代為最盛期。由于地域邊緣性,接納了各個時期來自于中原的優秀人才,構成了對超穩定、高純度的中原文化的繼承,以傳統戲曲、民俗、方言,茶、石、瓷文化著稱。其二是,由于政治環境、經濟制約的松散,形成了自由精神,推動了文化交流,又是“雜交文化”或“共生文化”。以“梯航萬國、帆檣如畫”的商業文化和“中國第一僑鄉”的華僑文化為特色,市舶司、真武廟、石湖碼頭、文山碼頭、航標石塔、德化古窯、天后宮、九日山石刻、祭海儀式等海洋文化景觀,與“以舟為車,以楫為馬,以海為田”的海洋文化精神,以及清凈寺、草庵明教寺、古基督教墓碑與墓蓋石,元妙觀石雕塑等為代表的多元宗教文化遺存為構成。
社會環境是孕育地方文化的第三要素。孟德斯鳩認為,居住在山地的人堅決主張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則要求由一些上層人物領導的政體,近海的人則希望一種由兩者混合的政體。泉州境內山地面積較大,又有以清源山斷裂和亭店斷裂為界的平原區,具備堅實的小農經濟基礎,宗法、鄉約勢力強大,使得法律與道德處于行政諭令、氏族組織、村落自治的三方轄制之下,對群體認同性強。思想上,以儒、佛為正統,其他為補充,相互建構與消解。因此,其倫理文化既寬容個人自由,特點是小型、精致、豐富、孤立而聯系的;又強調集體意識,是緊密、保守的,近乎自給自足的,由此衍生了具有強有力的家庭或部族結構,對群體認同性強以及高度發展的宗教儀式的系統。泉州瀕臨臺灣海峽的西岸,人口成分復雜且流動頻繁,生活上雖習慣大家族聚居,區分尊卑長幼,但每當遭遇災年,泉州人熱衷于獨立外出打拼,海洋捕撈,開拓市場,緩解環境、資源、人口的壓力。泉州灣古船陳列館所藏的遠洋貨輪,載重達到200噸,蜂尾古船模則將各種漁航、商船、戰艦按比例縮小,制成黑舟皮五青案和鄭和寶船。起航于泉州的南宋沉船“南海一號”乃遠洋貿易商船,出水數千件來自德化、景德鎮、龍泉窯的瓷器。這里,地理環境直接影響藝術材料、藝術品種。歷史和社會環境則通過倫理觀念等文化媒介,間接影響著藝術題材、內容、對象,藝術類型、表現、風格和創作。
泉州半規范文化周而復始的倫理熏陶,則是地方藝術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基礎。德者受到尊崇,失德者遭到唾棄,道德自然會成為地方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在泉州,古圣先賢的精神都能得到尊重與傳承。泉州城內拜祭孔子的名井“夫子泉”,井畔茂林修竹,游人如織。泉州人講究傳統禮儀,樂于通過語言、行為隱晦的倫理暗示,喚起人們情境性的儀式感。譬如,有事麻煩常說“費神”,對教師、知識分子尊稱“先生”,與長者交談不可夸夸其談等等風俗。通淮關岳廟,始建于宋代,主祀關圣帝君,附祀岳王,是關公信仰六大祖廟之一,每年進香人數以幾十萬記錄,是民俗倫理神圣性的彰顯。清源山老君巖的石刻雕像立足于傳神寫照,以樂天、健康的老者面貌出現,既體現出“養生”“玄妙”的主題,也反映出對“道德家”的仰慕之情。泉州本地也名人輩出,朱熹作為傳統道德的播種者,李贄作為傳統道德的批判與改良者、鄭成功作為傳統道德的捍衛者,弘一法師作為宗教道德弘揚者,他們的道德感召性,引起人們的崇拜。道德典范性,激發模仿沖動,道德超越性,容易被各階層接受。
三、弘揚
地方傳統藝術具有倫理思想的傳承性和統合性。音樂是表演藝術和聽覺藝術,也是明道正誼的藝術。泉州南音被譽為集唱、奏于一體的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四大樂種之一。現存的3000余首古曲譜,保留了自晉(公元265年至420年)起至清(公元1644年至1911年)歷代不同類別的曲目。南音形式上分為指、譜、曲、戲四科,在秉承雅樂、佛曲、道情、楚歌、吳歌、潮調、弋陽腔、青陽腔、昆腔音樂元素的同時,也散發出濃郁的儒道佛倫理氣息。
首先,南音在音樂表演上彌漫著儒家思想。演唱方式以靜態的坐唱或站唱,演唱者持拍板居中,嚴守了漢代相和曲“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的表演舊制,突出人聲的主導地位。指譜《四時景》刻畫了春播夏種,秋收冬藏的景致,沿襲了安土樂天的農耕文化心態。《梅花操》通過對梅花不懼酷寒,爭奇怒放的形象刻畫,贊頌了剛正不阿的君子節操,寄喻了儒家尊圣崇賢的精神寄托。上四管和下四管,將樂器詳細劃分了尊卑等級,以絲竹之音清脆為上,以管弦之音渾濁為下。教化和儀式的道德力,近似于禮樂倫理中心化的蘊涵,達成了組織與統一的作用。演奏者們透過樂聲交流彼此內心,終達成“八音克諧”“樂以教和”的無上境界。這里,南音表演有三種隱性的表意:人神以和,樂以調風,天人合一,涵蓋了人與神性、人性,天性的關系,像是一種人本主義的“萬物為我所用”的理想和愿景。南音依靠“樂社”傳承,學徒即為“郎君子弟”,相互尊稱“弦友”。只要有幾位弦友相聚,即可組成南音社團,并擇定、館邸、聚合、拜師、研習。南音樂師被稱為“先生”,備受尊崇。民間于道觀廟宇內設有“閑間”,平日由精通樂理、技藝精彩的先生在此演奏、授徒。用心理學的“蔓延之律”現象來解釋,無論是內向式的自娛自樂,還是人際式或團體式的交流、傳承,都是人之間的相互定性,不但加強了倫理共鳴,還獲得彼此間的某些“本質”。
其次,音樂形態貫徹了陰陽二元互補論的道家倫理思維,使其具有“安、足、靜、定”的特征。根據結構主義的概念:整體對于部分來說是具有邏輯上優先的重要性。南音樂曲稀蓬性旋律,一以貫之的溫婉、平和的旋律發展,回避了陽剛的過激和陰柔的晦暗。這種陰陽互補的理念,從生理感官上的“和”進到生理與心理的和,然后再到自然和社會的和。稀疏的旋律自然形成的大量“留白”,好似“大音希聲”理念的注腳,開辟了想象空間。曲牌體現了氣韻生動的追求和審美意趣,強調要留有空白和未確定成分的神韻,亦強調“無言之美”和審美體驗的模糊性相似。曲式結構組筑契合自然界發展的運動過程,呈示一種富于彈性的動感思維,趨同于模糊的即興性與寫意性,彌漫著若有若無的情愫。單線程旋律,究傳情,重體驗而輕邏輯,靜與緩的節奏,賦予聽者慢節奏的生命感、漸變式審美意象、頓悟式的哲學省思。南音界還每年固定舉行“郎君大仙春秋祭”祈崇五代蜀君孟昶。這種行業神祭祀活動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次數之頻繁,形式之繁縟及祭祀中犧牲之多都是空前的,只為獲得祖先神靈的歡悅和保佑,避免災禍。儀式有一套固定的程序以保證按照固定的形式和規則,完成象征性行為。香案供桌食果齊全,案桌后壁懸掛“郎君大仙”繪像。先唱“金爐寶篆”,演奏“噯仔指”,接著唱“七撩”的曲子,最后唱“倍工”“相思引”“錦板”“過枝曲”。程式化的行為意義在于:提醒參與者,創造者是誰以及演奏者應承擔的責任;教化,將非音樂和音樂行為貫穿起來,傳達一種神圣和秩序的信息,將和神仙信仰、音樂活動、道教儀式和倫理行為融合在一起。由此,構成了復合的倫理接受,其儀式側重于神靈的膜拜價值,稱為凝神專注性接受,其音樂活動側重于展示藝術價值,稱為滲透性接受。
最后,傳播讓南音完成了從藝術形式——內容拓展——新藝術形式的蛻變。作為一個誕生于漢魏時期的樂種,南音在海洋文化推動下,將番邦音樂元素加入其中,顯得更加大氣磅礴。從源流上講,元代的波斯音樂在整個亞洲和歐洲曾風行一時,南音琵琶類似波斯樂器中的薩它爾,二弦如喀曼介,洞簫像乃依;南音的袞門思維也可能源自波斯音樂體系。南音母題“陳三五娘”有許多典型的阿拉伯民間故事特征。南音音樂受印度佛教音樂影響其次。指套《南海觀音贊》的曲牌《兜勒聲》有濃郁的原生佛教色彩,三套《金錢經》中《喝噠句》該是藏傳佛教典章《哈達句》的諧音,《番家語》中的番字在閩南語中海外的意思;《折采茶》《折雙清》中的“折”字,則記錄了早期佛教音樂的語言和時值。大譜《梅花操》《走馬》從樂曲結構、節奏旋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唐代雅樂、燕樂的遺緒。而“燕樂”是學界公認的“華戎兼采”的產物。唐初宮廷設立七部樂吸納了西域高麗、天竺、安國、龜茲、疏勒、康國樂并增加高昌樂,集成為十部樂。后又把法曲與胡部合奏,用于宴樂,終于成就為燕樂。以上樂部均以中亞古國名作為樂部名稱。異域文化作為南音的組構,值得大書特書。
泉州節慶民俗藝術,也保持著這種對固有文化的接納,和對外來文化的寬容。道教節日“天香”“普渡”不乏南音表演。跳鼓,選男女二人,持鼓載舞,由南音《管甫送》或《打花鼓》伴奏。貢球出自梨園戲《鄭元和》“踢球”一節,由南音《孤犧悶》或《直入花園》伴奏。十音,起源于行伍音樂,威武雄壯,形成了與南音柔婉之風對照,北管則緣起于明清以來的江淮小調。民歌《天烏烏》《貓年年》《火螢火叉叉》《月仔月光光》《思想起》《四季春》等,形態特征一般為五聲調式的變宮古音階,平穩級進,速度舒緩,是原生城市小調和鄉土民謠的回流。舞龍、舞獅,奉瑞獸,襲舊制,是具有千年傳承史的全國性民俗藝術。拍胸舞出自梨園戲 《鄭元和》“企食”一節,雖由若干坦胸露乳的壯漢表演,坦胸露乳,手拍周身,舞以蹲襠步,詼諧歡快,但并不是鄧肯現代舞蹈那樣的自由,而是自信、整體美感的流露,乃是云門樂舞、蠻夷樂舞精神的遺緒。火鼎公婆,源自閩越先民的“火神”崇拜,舞姿顛而不狂,醉而不癡,又恪守了中庸之道。唆羅連舞蹈,口訣或來源于印度梵文,不斷重復地唱“唆羅連啊,羅連哩羅連”,再配以舞蹈烘托氣氛,突顯驅邪祈福之意。
四、超越
地方傳統藝術所體現倫理思想的超前性和反抗性的部分,則是文化彈性和生命力的體現,表明:傳統或“世代相傳”的意義絕非僅是盲目地或一絲不茍地因循前人的風格。傳統文化一直有性壓抑的傾向,許多美好的愛情故事注定是被世俗牽絆,封建婚姻桎梏所殘害,以悲劇收場的。男女主角的壓抑來自于法律的、輿論的,更來自內心倫理。甚至可以說,封建禮教以對性欲的壓制擴散到對人多種欲望的壓制。梨園戲被稱為“宋元南戲的遺響”,改編創作劇目《董生與李氏》,卻講訴了這樣的故事:彭老員娶少妻李氏。去世前,恐其紅杏出墻,密囑其鄰、塾師董四畏暗中監管。董風度翩翩,李因此嗔愛,遂誘之。董懼聲名敗壞,百般推辭。后李設計,董忿憐,終喜結良緣。主旨刻畫了讀書人掩抑曲折的情愛心理,顛覆了迂闊怪詭的封建倫理。辛辣諷刺了人性和倫理中滑稽可笑、消極落后的一面;尊重了人的欲望,呼喚著生命本真的張揚。知識男性的悲劇,并不在于“手無縛雞之力”的身體上的羸弱,而在于精神在道德壓力下的“文質彬彬”,只好龜縮在自己的世界里。高甲戲《金魁星》中的賣花婆胡氏面似修羅嚇夜叉,卻樂于助人,知恩必報,為幫秀才王贊求取功名,夜入丞相大諒府,于何小姐房中請走一尊金魁星。又巧裝相婆為小姐測字,繼而勇闖公堂,涉險救難,可謂有勇有謀。霍布士曾指出:“善分為三種,一是指望中的善,即美;二是效果上的美,即感官之美,即欲念所向往的目的。第三種,是手段上的善即有用,善是美德內容。”[4]賣花婆胡氏的“美”,即是第三種意義上的“丑妻薄地家中寶“的傳統的實用之美。人生,不但涉及自我也涉及到他人,特別是某些重要的他人,只有將他人納入自己的存在之中,才能從關系的愉快感受和重要目標的實現中,獲得人生意義的圓滿。打城戲《目連救母》劇本摘自古印度《佛說盂蘭盆經》。家庭關系之愛,既是最純粹、深刻的倫理之愛,也是人生最具法定義務的社會關系。這里,一個孝子把自己的全部交給家庭倫理,變得不可戰勝了,因為有神罩著他。佛弟子目連到地獄中見到了受苦的母親,心中不忍,十分悲哀,祈求于佛。佛陀教目連于七月十五日建盂蘭盆會,借十方僧眾之力讓母吃飽,目連乃依佛囑。目連母親得以吃飽轉入人世。目連又育了七天七夜的經,使母親進入極樂世界。珍惜生命是個體道德的基點,而肯定生命和珍惜生命,首先是愛惜生命。在道德真理面前,強權和死亡并沒有多少力量。堅持孝敬而不畏強權,不懼死亡;孝讓人勇敢,勇敢之孝可以戰勝生命的死亡。這種孝既像“慈鴉還哺,羔羊跪足”那樣符合自然界的規律,也符合人心和天地的道義。主人公與母親經歷了苦難,存在的意志、理性、勇氣去戰勝非存在的威脅。傳統道義上的孝敬,呈現恒久性、嚴謹性、程序性。故事也提供了一種超越死亡的哲學途徑即:超越功利的趨利避害,超越恐懼的羈絆,就是超越死亡。既然人類生命每一天都要被奪走一部分,只需用接納的態度且勇于承擔責任,死亡恐懼自然消失了。同時,這些傳統戲曲的創作也是在歷代統治者的保護下才得以存續的。它驗證了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觀點:封建統治者已經諳熟,統治龐大的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于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從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由等級尊卑的預設,禮仁和諧的踐履,宗法人倫的轄制所構成的封建道德,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社會關系的一種調節手段確實可以發揮有限的作用,這種倫理作用的發揮,保證了傳統文化的緩慢演進。
五、協調
地方傳統藝術還試圖在上述“道德工具論”和“道德自律論”之間尋找平衡,以期在不否定人性、人道的需求的基礎上,承認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是倫理傳統和現實生活相互干預的結果。從而避免作品中倫理思想陷入凝固和放任兩極,從而理順了審美趣味,使公眾不至于在使用和欣賞時陷入各種價值觀所營造的劇場假象之中不能自拔。服飾美是人體美的文化生成,除卻宗教性的服裝,世俗的服裝的審美要素:質料、款式與色彩,與實用性價值時常交錯在一起,是一種頗具等級權力意味的典型的遮露藝術。無論中西方,女性都是血淚史。歷史上,女性服飾一直被研究者作為性別壓迫的指代物。惠安女是惠東半島海邊一個特殊的女性族群,其奇特的服飾,被譽為“巾幗服飾中的一朵奇葩”。惠女服飾根據勞動和審美需要設計并不斷改進,以花頭巾、短上衣、銀腰帶、大筒褲為特征,俗謂“封建頭,民主肚,節約衣,浪費褲”。首先,封建頭,體現了女性面臨多重壓迫,不得不屈服于男性的話語,是倫理精神傳承的標簽。其次,民主肚,立足于勞動需要和性別特征的展示。因為腰肢的暴露,既利于勞動時伸展、排汗,又讓胸部、腰部處于若隱若現之間,抒發了女性了對自由的向往并發出性的誘惑。再次,“浪費褲與節約衣”是生存智慧。經濟上,衣服短了,布料就省了。功用上,褲子較長,是為了遮蔽常年勞作的粗腿。審美上,短衣長褲使女性身體,成為富于視覺感染力的符號,性誘惑的主導動機。最后,裝飾貫徹了集體意識,外上衣一律為藍色飾以淺色綠條、碎花或蝴蝶圖案,上衣、頭巾、褲子的尺寸相仿,貫徹了程式化的設計,既避免了因年齡、喜好而造成審美分歧,也便于勞動協作。總之,服裝文化是相對開放階級社會中一種階級區分的形式,人們試圖用某些可以看得見的符號或者信號象征體系來進行自我確證。惠女服飾釋放了女性人體美,又保持了傳統元素,是民間倫理反抗和遵從精神的象征。
“建筑不能降格為只是具有美學價值或技術價值,應是生活方式的詮釋,應幫助表達出某種共同的精神風貌”。[5]開元寺石塔,一曰“仁壽塔”一曰“鎮國塔”,合稱“東西塔”,皆取道德稱謂。泉州的大厝民居既模仿宮殿式建筑,與環境構成呈點、線、面的和諧關系。房舍間以“庭”為組織院落單元,庭、廊、過水貫穿全宅,在此基礎上又組成“巷”的組織單位,阡陌縱橫,彼此呼應,構成氣勢非凡、等級森嚴的階梯型排列。在大厝民居群中,從最簡單的形式“空地”開始,房子被分為若干組,以一棟大房子為核心,人們在此集中、議事,其他的房屋環繞中間的空地,明顯地突出中心權威的觀念。建材采用“胭脂紅”磚,稱“紅磚文化區”,呈現黑、紅兩種顏色,使建筑籠罩于暖冷兩種色調之中。繪畫技巧、線條運用、色彩組合,大都移植自中原古代的宮室、名堂、宗廟,顯現出鮮明的繼承性。同時,泉州人又是浪漫主義者,富于大膽、創新,灑脫超越精神的,那些閩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墻面、圖案設計,宅內又置書字畫于門墻廳壁,營造了一個“濃麗清新的色相世界”,灌注了俗世間的情感,充滿了盼望能豐衣足食、闔家平安,進而發財致富的美好祈愿,是一種倫理“中和主義”的象征。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泉州民居之所以常出現這種不受固有門派、風格局限的寫意創造,在于民間工匠的技藝高超,雖難免匠氣,但頗能接地氣。又因為建筑屬于多工種協作,這些建筑師的作品多可不屬姓名,不為名利倫理所累,更可自由創新、施展。
六、變通
藝術和宗教的情感、邏輯方式都同屬于一個領域。地方傳統藝術中的宗教倫理,更像是傳統倫理的典型變量,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彰顯出文化性和跨文化性的特征。梁思成曾說:“藝術之始,雕塑為先”。何朝宗,明代德化縣潯中鎮隆人,佛教徒,善瓷塑,尤善人物,如達摩、觀音、羅漢、大使、善才、城隍、童子、小鬼等。僅其名字,就頗具虔誠的宗教倫理色彩。朝宗,是指覲見、入海之意。佛典里說,佛祖在靈山講經說法,天、地、人三界菩薩列席聆聽,受佛的凈化,始有“萬佛朝宗”的說法。何朝宗瓷雕一反宗教雕塑大型化或人體等比化的趨向,專注于小型化,利于把玩收藏,反映宋元以后審美私人化的回歸。獨,“獨往而獨來,是為獨有之人,獨有之人是為至貴。”(《莊子》)這種創作風格還契合傳統的“不似似之”的原則,太似則呆滯,不似為欺人,妙在似與不似之間,既不具象也不抽象,徘徊于有無之間,斟酌于形神之際,呈現了“象外之象”的意境。渡海達摩像,光頭大耳,高鼻深目,滿臉虬須;身著袒胸寬袖長衣,拱手赤足,腳踩一蘆葦,浮于碧濤上。下視目光,緊閉嘴唇,透露出堅定不移的揚法之心。今人將何朝宗塑造的觀音尊稱為 “何來觀音”。趺坐觀音,盤膝而坐,溫良嫻雅,神態既神圣又慈祥,柔潤流暢的衣紋線條,細刻劃的頭部、身材、手腳。“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都不同的一點:缺乏超驗的部分,一切都圍繞著人倫而來。哪怕‘天理’也只是人倫之至的意思。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只有身和心,而不存在一個神性的大。”[6]此外,何朝宗雕塑從白瓷的取材到構思、創作都獨立完成,寄寓著濃烈的日常情感。何朝宗把佛、菩薩、羅漢等大神面目的尊榮性和身姿的世俗性統一起來。而塑造“小神仙”如城隍、文昌君、和合二仙時,由于其“次尊嚴”性,則大膽地突破傳統,肢體表情更生動些,好像雕塑的是心靈平靜安逸的普通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鬼神。
開元寺大雄寶殿后回廊中央,即有兩根雕刻精美的古印度教石柱,明末高僧木庵稱“石柱牡丹”,奉為開元寺“八吉祥”之一。一柱四面,兩柱八面,各附浮雕圓盆,上有故事。圓盤兩側,以竹蘭花木吉祥圖案裝飾,環繞其間。一幅曰《毗濕奴騎坐金翅鳥》,把道德起源歸結于神秘的天啟和神的意志。傳說毗濕奴有時坐在蓮花上,有時安靜祥和地躺在一條千頭蛇上。坐騎是半人半鳥的大鵬金翅鳥,手持長劍,鏟除掉世上的惡人。浮雕描繪了:毗濕奴騎金翅鳥化人形,人首鳥身,背后有翅,頸掛蛇形項圈,表情安詳肅穆。此神慣散吉祥,飛臨之處,則如天之福,興旺發達。印度教的根本教義即“吉祥”,是善與惡、理與欲、上智和下智相調和的理念;最終目標是光明戰勝黑暗,要使一切“光明分子”脫離黑暗的羈縛,而回歸明界。故事邏輯很簡單:助于我教目的之到達的則為善,凡有妨礙于我教目的之到達的則為惡。人通過崇拜,一來,可得神的庇佑;二來,可以達到神祗之境界,神祗幫他們消除罪孽,徹底擺脫人類有限境域之內的無能。周圍的紋飾如雙鳳銜瑞草、雙獅戲球,喜祿封侯:喜鵲立于枝頭之上,兩只鹿銜芝草在下,猴子摘蜂窩在左。題材已完全有喜慶文化的內涵,一反粗獷質樸的裝飾風格,植物紋多以回環曲線、連續的華麗圖案出現,是中外文化磨合的顯現。一副曰:《摩那河七女出浴》,表達了“道德根源于人生而有之的東西,是自然的天性”的思想。它講述了:克利希那化身英俊牧童,見七女于閻摩那河沐浴,一時玩心興起,便取其衣裳。眾女浴畢,苦無寸縷蔽體,便苦求。克利希幡然悔悟,方放下。這里,男女關系被凸顯出來了,男人先是淫邪的浪子,被欲望俘虜了而輕視倫理;后竟良心發現,化成圣徒,不能不說是神秘主義的解決方式。欲,本無罪!“盜衣”的情節,實際上是對欲望的愛慕之心的歌頌。另一方面,“放衣”的情節,又提倡一種理性的節制,告誡人們不要做欲望的奴隸。一副曰:《十臂人獅掰開裂兇魔身體》。法相之上,毗濕奴渾身披堅執銳,鋒芒逼人,執繁榮法螺、力量圓盤、朝元仙杖,把兇魔希拉尼亞卡西布放膝蓋上,騰出兩手掰裂其肚皮,以暴制惡。這里,看似是神戰勝了妖怪,其實是妖怪違背了人間道德的善惡準則,應該是人戰勝了妖怪。一副曰:《象鱷爭斗》,貫徹了“道德起源于至高的理念和精神”的觀念。象和鱷魚都是毗濕奴的信士,因惹動其它神袛而被貶謫,彼此爭斗不休,長逾千年。后來,象猛然想到毗濕奴大神,以鼻卷舉蓮花向毗濕奴求救。毗濕奴果然騎金翅鳥飛臨,殺死鱷魚,解救了大象。大象的勝利并非道義、武力的勝利,而是信仰和崇拜的勝利。古印度教將世界看成善與惡循環對抗的場所并預測善惡的前途,亦重視心靈凈化。印度教對道德的自圓其說極限于并非一元論的范疇。看似自相矛盾的闡釋,實際上是為了迎合多層次的需要。
七、結語
地方傳統文化是特定區域所繼承的賦有象征意義的所有文化產品的總和,相對于民族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來說,具有一定的非意識形態或泛意識形態特征。它既服從于群體的協調共存的秩序,也必須兼顧個體的自由意志和生命發展需求,并遵循著既定的生產、地理、經濟、政治發展模式。藝術的誕生、存在和生長,是不能不依賴于它所生長、指涉和服務的地域或社會的。“由于藝術是藝術化的社會象征符號系統,是社會信息的記憶方式,所以藝術成為狂越時空局限的最佳交流媒介。這種交流媒介在本文化圈內,在特定群體內,可以發揮維系人際,增強內部凝聚力、穩固性和協同性的效用;在不同文化圈外,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社會成員則可發揮情感交流、心靈溝通、文化交往,增進了解和友誼,促進文化匯通的作用。”[7]地方傳統藝術常以生產方式和生活經驗為情景,同時強調了藝術作品的審美和教化功用。它形成于城市的歷史、經濟等所積淀的文化土壤與氛圍中,是當地人生存狀態、情感方式的直觀體現。地方傳統藝術的創造和接受過程,是一個使參與者認識到自身復雜性和傳承性,不自覺地成為歷史和文化的對象,并在獲得感性愉悅的視聽覺體驗的基礎上,展開“心靈尋根”的過程,從而獲得一種重新確證、呈示和顯現自身意義的機會。藝術本體與藝術本質有其顯而易見的同一性,前者通過某種隱喻性的置換方式,把后者整合在一起,并使之成為它自身的一部分。藝術和倫理,是一個地方流淌在血管里的文化血液。藝術風格只要契合某個地方社會或群體的倫理需要,就可能會保持穩定。反之,倫理的穩定性也阻止了藝術形式和內容的變異。地方傳統藝術將以自始至終獨有的倫理價值,而具有普世的價值。泉州地方傳統藝術作品的倫理色彩,既混雜多種文化基因,是多種道德觀念的合體,又在內涵上呈現出倫理的變異性的傾向,時空的超越性、合適性,內容的獨創性、豐富性,思想上的統合性。地方文化的淪陷,意味著一個民族世代相傳的對生命過程的符號闡釋系統的徹底斷裂。提倡藝術的地方特色,決非維護狹隘的地域性,而是保護文化生態多樣性,和尋找“怎樣才能在重建中國傳統城市結構的同時保留下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問題之答案的必要。[8]
[1]約翰·羅斯金.藝術與道德[M].張鳳,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5.
[2]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M].齊世榮,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127.
[3]馬克思.資本論[M].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4.
[4]托馬斯·霍布士.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235.
[5]卡斯騰·哈里斯.建筑的倫理功能[M].申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125.
[6]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M].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65.
[7]潘澤宏.藝術文化學[M].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361.
[8]陳雯暉.記憶和建筑:古泉州的繁榮復興[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