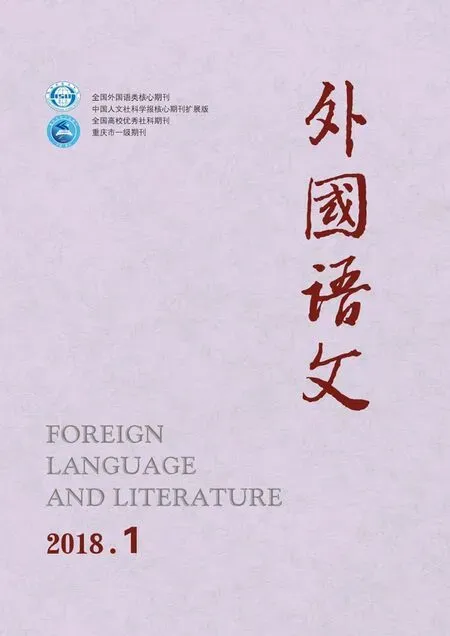情態的多維度研究
楊 曙
(華南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0)
0 引言
情態最初源于傳統模態邏輯對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探討。在模態邏輯領域,Von Wright (1951)區分了四類模態:真值(alethic)模態、認識(epistemic)模態、道義(deontic)模態和存在(existential)模態,這一分類對后續的情態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語言學的情態研究借鑒了模態邏輯的研究發展,較早關于情態的討論可見于Jespersen (1924:320-321)。在當代,情態作為一個重要的語義和語法范疇,一直是語言學各領域的關注熱點,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傳統語義學(Lyons,1977; Palmer,1979, 1990; Coates,1983; Perkins,1983; Collins,2009;Leech,2013)、語言類型學(Bybee et al.,1994; Van der Auwera et al.,1998;Palmer,1986, 2001)、系統功能語言學(Martin,1990; Halliday,1994; Martin et al.,2005)、話語分析(Hyland ,1998a, 1998b, 2000, 2005; Kosko et al.,2012)、認知語言學(Talmy,1988; Sweetser,1990; Langacker,1991, 1999, 2010, 2013)和語用學(Papafragou,2000; Maalej,2002)。鑒于國內目前關于情態的綜述性論文并不多見,本文將梳理、回顧情態在以上領域的代表性研究,以期對相對薄弱的漢語情態研究和英語情態的后續研究提供參考和指引。
1 傳統語義學領域的情態研究
情態是語義學的一個重要范疇。語義學家們對情態的定義、基本類型以及表達形式等問題進行了探討。Lyons (1977)較早從語義和哲學角度探討了英語情態的定義、基本類型和主客觀性問題。他著重討論了認識和道義兩類基本情態,并區分了主觀和客觀情態。他認為,主觀情態表達說話人的觀點或態度,而客觀情態與說話人無關;主觀情態比客觀情態出現得更頻繁,客觀情態較少見。Lyons的研究為后續的情態研究奠定了基礎,然而他的情態范疇較窄,并且沒有討論情態在具體語言中的表達形式。
在此之后,Palmer (1979,1990) 較為系統、詳細地討論了英語的情態類型和情態助動詞。他認為情態是一個語義和語法范疇,在英語中主要存在三類情態:認識、道義和動力(dynamic)情態。他詳細闡述了體現這三類情態的核心英語助動詞的語義和語法特征,并提出,英語的認識情態與說話人對命題真值的判斷有關,道義情態與說話人給予聽話人的義務或許可有關,兩者均具備說話人取向(speaker-oriented)特征;動力情態則與小句主體的能力與意愿有關,具備主體取向 (subject-oriented)特征。Palmer (1979,1990)較系統、全面地闡述了英語情態助動詞的語義與語法特征,被視為英語情態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Palmer (1990: 67)認為,英語的情態助動詞很少與情態副詞共現,而且這些共現是重復、多余的。這一觀點遭到眾多后來學者(Coates,1983; Hoey,1997)的質疑。Hoey (1997)以語料庫為基礎,對情態助動詞與副詞的共現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認識情態助動詞與情態副詞的共現呈顯著性傾向,這種共現可以加強說話人的推斷,并解決情態助動詞的歧義問題。
在語義層面對英語核心情態助動詞進行描寫的研究還有Coates (1983)。該研究把情態劃分為兩種類型:認識和根(root)情態。該研究認為,認識和根情態助動詞的語義存在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表現為三種類型:漸變(gradience)、歧義、融合(merger)。Coates指出,漸變是根情態的一個重要特征,根情態助動詞的語義在強弱度和主觀性方面存在漸變。Coates的研究創新性地運用兩個大型語料庫作為研究語料,并運用模糊集合(fuzzy set)理論來概括情態助動詞語義的不確定性。然而,她對認識情態的定義遭到Palmer等一些學者的質疑。Coates(1983:18)認為,認識情態表達說話人對命題真值的信心(confidence)或缺乏信心,而Palmer(2001:34-35)則認為,認識情態表達說話人基于已知事實的推理。Collins(2009:39-40)也指出,認識情態助動詞“must”與“I suppose” “at a guess”“presumed”的共現表明“信心”并不適合用來定義認識情態。
在Palmer等人的研究基礎之上,Perkins (1983)首次對情態助動詞以外的英語情態表達形式進行了系統描寫,并闡釋了英語情態具備眾多表達形式的動因。他認為,情態在英語中可由以下多種方式體現:情態助動詞、情態名詞和形容詞、情態副詞、實義動詞、時態等。情態助動詞是情態的無標記表達形式。說話人可以選擇助動詞以外的其他表達形式來具體化情態意義。例如,如果說話人想強調客觀情態評價,可以選擇情態副詞、情態形容詞或名詞;如果說話人想強調主觀情態評價,可以采用第一人稱代詞加情態實義動詞小句;如果說話人想主位化自己的情態評價,可以使用情態副詞或實義動詞。Perkins的貢獻在于首次系統描寫并闡釋了情態助動詞以外的情態表達形式,然而他對于情態表達方式的理論解釋在學界仍存有爭議。例如,他認為說話人可以選擇情態副詞來強化自己的客觀情態評價,然而英語的情態副詞“certainly”“definitely”明確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評價。
新近從語義學角度對情態進行的系統研究有Collins (2009)和Leech (2013)。Collins(2009)詳盡分析了三個大型平行語料庫(即當代英國英語、美國英語、澳大利亞英語語料庫)中4000多例情態助動詞和半助動詞(如have to、be to)的用法,統計了這些情態詞所表達的認識、道義或動態語義在三個大型語料庫中的分布頻率。該研究發現,主觀與客觀性有時系統地區分情態助動詞與半助動詞,例如,助動詞“must”“should”通常體現主觀義務,半助動詞“have to”則體現客觀義務。這項研究還表明,在當代英語中,半助動詞的使用在增加,而情態助動詞的使用呈下降趨勢。Leech (2013)基于美國和英國英語的書面和口語語料庫發現,在當代英語中,核心情態助動詞的使用頻率在迅速減退,而興起的半助動詞包括“be going to”“have to”的使用頻率在逐步增加,并提出語法化和口語化(colloquialization)是造成這一趨勢的最主要原因。
2 語言類型學領域的情態研究
語言類型學從語言功能的角度來闡釋語言結構,遵循功能主義的路徑。語言類型學把情態視為一個跨語言的類型學范疇,在跨語言的框架下概括情態的基本概念和分類,并從歷時類型學的角度探討情態的語法化過程。
Bybee et al.(1994)分析了情態的語法化過程以及引起語法化過程的語義演變機制。這項研究把情態劃分為四種類型:施事取向情態、言者取向情態、認識情態、從屬句中的情態,并在跨語言的基礎之上,概括了世界語言中情態的語法化過程。這一過程表現為由施事情態演化為認知情態和言者取向情態,最后演化為從屬句中的情態。該研究還指出,引起情態語法化過程的語義演變機制包括隱喻、推理、概括等。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同樣把情態劃分為四種類型:參與者內在能力與需求情態、參與者外在條件情態、道義情態、認識情態,并且采用語義地圖(semantic map)來呈現這四類情態意義的相互關系和語法化過程。該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采用語義地圖系統、清晰地呈現了情態的歷時發展過程。
語言類型學對情態的奠基之作當屬 Palmer(1986,2001)的著作。Palmer (1986)是第一個從類型學視角對情態進行系統研究的語言學家。其著作(Palmer,2001)是語言類型學領域情態研究的標準參考書目。Palmer (2001)在廣泛采納歐洲、亞洲、美洲以及澳洲土著語言的基礎上,對情態進行了定義和分類。他以“現實”(realis)與“非現實”(irrealis)區分非情態和情態。“現實”指已經實現或正在實現的情形,可以通過感官直接感知;“非現實”指僅存在于思維領域,只能通過想象獲得的情形。他把情態劃分為兩種基本類型:命題情態和事件情態。前者包括認識情態和言據性情態(evidentiality),均與說話人對命題真值的態度有關;后者包括道義與動力情態,均指未實現而有可能實現的事件。他還指出,語言的情態意義主要通過情態系統或者語氣系統(即虛擬語氣)體現。例如,英語的情態意義通過情態助動詞系統體現,而西班牙語則通過虛擬語氣實現。Palmer的研究詳細闡述了情態的類型學特征,為情態的跨語言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然而,他把言據性納入了情態范疇,盡管這一觀點在語言類型學領域被廣泛認可,學術界仍有些聲音(如De Haan,2005)認為言據性不屬于情態范疇,而應當作為一個獨立的范疇。
語言類型學領域新近出版的論文集ModalsintheLanguageofEurope收錄了16篇論文,其中有14篇論文聚焦歐洲各語言中情態標記的語義與句法特征和語法化過程。該論文集還總結了歐洲語言中情態的基本特征,例如,情態在歐洲語言中主要由情態動詞或情態詞綴(affixes)體現,旨在為情態的跨語言研究提供參考。
3 系統功能語言學領域的情態研究
系統功能語言學把情態視為語言人際元功能的重要語義資源。語言的人際意義主要由語氣、情態等系統體現。Halliday(1994)探討了情態的定義和類型,情態在英語詞匯語法層的實現方式,并提出了情態隱喻的概念。他認為,情態表達說話人對命題和提議的判斷和態度,涵蓋“是”和“否”之間的意義領域。英語的情態系統包括情態化和意態。情態化指在以交換信息為語義功能的命題句中,說話人對命題可能性和經常性的判斷,包括可能性和經常性(usuality);意態指在以交換物品或服務為語義功能的提議句中,說話人對提議的態度,包括義務和意愿。Halliday指出,情態意義的實現存在一致式和隱喻式。在功能語法中,一致式和隱喻式分別指人類識解經驗的典型和非典型的方式。在英語中,情態的一致式由情態助動詞和情態附加語體現,情態隱喻主要以小句形式體現(例如I believe,it’s possible)。系統功能語言學情態隱喻概念的提出拓寬了情態研究的范圍。
系統功能語言學派的另一主要成員Martin在詞匯語法層面探討了情態在英語和塔加路族語(Tagalog)小句層的韻律式體現方式。情態的韻律體現方式指情態意義的表達不局限于小句的某一成分,而是由多個成分共同實現,如同韻律一樣遍布整個小句,具有明顯的非離散性和累積性特征。Martin & White (2005)還在語篇語義層面探討了情態的功能。該研究把情態納入了評價系統(APPRAISAL),情態被視為使語篇具備協商性和對話性的介入資源。Martin & Rose (2007: 53-54)也指出,情態的功能類似協商,是把其他的聲音引入語篇的一種資源;情態的主要功能是對話性,是構建語篇多聲(heteroglossia)的重要手段。情態在系統功能語言學中從最初被視為表達說話人對命題和提議的主觀判斷和態度的資源,到作為評價系統中的介入資源構建語篇的對話性,這是從強調情態的主觀性走向強調其主體間性的發展歷程,也是系統功能語言學框架內對情態研究的拓展。
4 話語分析領域的情態研究
話語分析領域的情態研究著重于情態表達形式在特定語篇中的分布頻率和具有的功能,涉及到多種體裁的語篇,包括教學語篇(Holmes,1988; Kosko et al., 2012)、法律語篇(Garzone,2001, 2013; Diani,2001)、政治語篇(Simon-Vandenbergen,1997)等。例如,Kosko & Herbst(2012)發現,在教師話語中,規約性和可能性情態的使用頻率比經常性和意愿性情態要更頻繁,這表明教師傾向于更多地談論事件的恰當性與可能性。Simon-Vandenbergen(1997)指出,在政治語篇中,說話人對命題真值做出較高程度的承諾旨在使他人確信某一存有爭議的觀點,情態詞的使用旨在與聽眾建立同盟關系。
在話語分析領域最值得一提的是Ken Hyland的一系列研究。Hyland (2005)把情態納入元話語(metadiscourse)的框架之下,他把元話語定義為“在語篇中協商互動意義的自我映射型話語,旨在協助作為某一特定團體成員的作者/說話人表達觀點和與讀者進行互動”(Hyland,2005:37)。他認為,情態詞屬于交互元話語資源,交互元話語包括了模糊限制語(hedges)和加強語(booster)。前者由低值可能性情態動詞“can”“might”和相應的情態副詞或形容詞“possible”等體現,后者由“certainly”等必要性情態詞體現。Hyland (2005: 52)認為,模糊限制語的使用表明作者認同其他的聲音和觀點,從而拒絕對命題做出全部的承諾,通過允許信息作為個人觀點而非確定的事實來呈現,提供了協商的空間;加強語的使用表明作者雖然意識到潛在的不同觀點,但是選擇縮小而不是擴大不同觀點,以一種肯定的態度直面其他不同觀點,從而關閉了協商和對話的空間。Hyland(1998b,2005)還著重探討了學術語篇中的元話語資源。研究發現,在學術論文中,模糊限制語是最頻繁使用的元話語資源,旨在區分事實與觀點,表明作者認同潛在的其他觀點。
5 認知語言學領域的情態研究
在認知語言學領域,早期的研究如Talmy(1988)和Sweetser(1990)采用力動態理論(force dynamics)來闡釋認識和道義情態,最新的研究Langacker(2010,2013)從“力爭控制”的角度來闡述情態語義。
Talmy(1988)采用力動態理論闡釋了英語情態助動詞的道義情態意義。力動態理論包括兩個理論實體:動力體(agonist)和阻力體(antagonist)。動力體是體現靜止或運動內在力趨向的實體,阻力體是施加反作用力的實體。Talmy認為,內在力趨向可以映射到權勢、意愿等社會心理關系中。例如,“You must/may do your homework”可以解釋為“我施加權威力迫使你決心做作業”。在這一例句中,動力體是聽話人“you”,阻力體是說話人。動力體的內在力趨向是不愿做作業的意愿,阻力體的反作用力是說話人的權威,阻力體通過施加權威阻礙這一事件的發生。“must”的運用表明阻力體的作用力大于動力體的內在力趨向,“may”的運用則表明阻力體沒有對動力體施加阻力。
在Talmy(1988)的基礎之上,Sweetser(1990)延用力動態理論闡釋了英語情態助動詞的認識情態語義。她主張,英語情態助動詞的認識和道義情態意義并非是獨立、互不相關的兩種語義,認識情態語義是根情態語義(義務、允許、能力)的延伸。道義情態的社會心理作用力可以映射到認識情態的推理作用力上。她把認識情態闡釋為“基于論據的認識作用力(epistemic forces)促使說話人得出一定的結論”。因此,例句 “He must be at his office”可以解釋為“已有的證據施加推理作用力迫使我得出他在辦公室的結論”,例句“He may be at his office”可以解釋為“已有的論據沒有阻礙我得出他在辦公室的結論”。在認知語言學框架內對情態展開的后續研究從不同方面發展了Tamly和Sweetser的思想,然而力動態理論的核心思想一直得以延用。
認知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Langacker早期從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的角度探討了英語情態動詞的歷時演化過程(Langacker,1991, 1999),并提出了動態演化模型(Dynamic Evolutionary Model) 來闡釋情態助動詞的將來時間認識意義。Langacker 新近發表的論文(Langacker,2010, 2013)是認知語言學領域最新的情態力作。他在Talmy和Sweetser的力動態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力爭控制”(striving for control)的“控制循環”(control cycle)模型。他從“力爭控制”的角度,把所有的言語交際行為劃分為旨在力爭認識世界的“力爭認識控制”言語交際行為和旨在產生某種效果或對世界施加影響的“力爭有效控制”言語交際行為,情態相應地被劃分為認識情態和有效(effective)情態。他認為,認識情態的轄域是概念化主體所了解的現實世界,情態力是概念化主體內在的力爭對世界的認識,這種情態力不可能直接影響外部世界;有效情態的轄域是現實世界,情態力旨在影響外部世界事件的進程。認識情態是有效情態的一個固有成分,兩者都表明事件是不被概念化主體所知曉的現實,區別在于有效情態還包括外在的情態力,試圖影響事件的進程。在談及情態動詞的語法地位時,Langacker認為英語的情態動詞和時態一起形成了一個緊密結合的、語法化的情境植入(grounding)系統,實現情境植入的功能。Langacker(2013)試圖從“力爭控制”的角度闡釋認識和有效情態以及情態動詞的語法地位問題,然而,他對認識情態的界定以及把認識情態視為有效情態的一個固有成分,這些觀點仍有待探討。
6 語用學領域的情態研究
“情態是一種自然的語用現象。”(Verschueren,1999:129)語用學領域的情態研究從言語行為理論、禮貌原則、關聯理論等角度展開。首先,語用學家在經典著作中討論言語行為理論和禮貌原則時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情態表達形式的問題,情態詞被視為體現言語行為或禮貌原則的語法手段。例如,Leech(1983:121)在討論得體原則(the tact maxim)時,指出義務情態助動詞 “must”“ will”“can”“could”形成得體等級。Leech(Leech,2014:160)把可能性情態副詞如“maybe”“possibly”視為語用修飾語(pragmatic modifiers),認為這些情態副詞與表能力或潛能的情態動詞連用可以緩和或削弱說話人發出的指令或要求。
語用學領域值得一提的研究有Maalej(2002)。這項研究旨在從言語行為理論和禮貌原則的角度對英語的情態助動詞進行統一分類和闡釋。他認為,從言語行為理論來看,在不同的語境下,情態助動詞有不同的言外之力,依據言外之力的不同,情態助動詞可統一劃分為兩大類:指令承諾類、 斷言類。前者使得說話人可以讓聽話人采取某種行動或使得說話人承諾采取某種行動;后者使說話人依賴已有的證據確立對話語的信心。前者的適配方向(direction of fit)是現實世界向語言的適配,即帶來現實世界的變化以使現實世界與言語事件的命題內容相匹配;后者的適配方向是語言向現實世界的適配,即在一定程度上與獨立存在的現實世界相匹配。從禮貌原則的角度來看,情態助動詞可分為三類:說話人自己受損而聽話人受益的允許和承諾類(may,will);說話人自己受益而聽話人受損的義務類(must);既不使說話人和聽話人受益,又不使說話人和聽話人受損的斷言類。Maalej (2002)的研究給情態的分類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然而,他從禮貌原則對情態助動詞的分類仍有可商榷之處,例如,對斷言類情態助動詞的闡釋仍有些牽強。
語用學領域另一項重要的情態研究是Papafragou(2000),該研究以Sperber & Wilson(1995)提出的關聯理論為理論基礎,以英語的情態助動詞(如must、may、 can、 should)為研究對象,提出英語的情態動詞具備單一的語義特征,與不同的語用因素相結合,從而產生不同的語境解讀。該研究指出,情態動詞是依賴語境的表達形式,情態的語義沒有完全、充分體現情態動詞在交際過程中的全部意義。情態的語義內涵具體包括兩個部分:邏輯關系R(即包含或相容關系)和命題域D,也就是說,情態動詞表達某一命題p與命題域D中命題集合的邏輯關系,例如,“can”定義為內嵌命題p與事實域(Dfactual)相容,“must”定義為內嵌命題p被未確定域(Dunspecified)包含。Papafragou認同Krazer(1981)的觀點,即認識和根情態是對不同事實的分類,根情態意義的命題域包括是對現實情形進行描述的命題,認識情態意義的命題域包括說話人信念集合的命題。她指出,聽話人在聽到情態話語時,需確定情態詞的命題域類型以此確定情態的認識或根情態語義。一般而言,情態動詞的命題域或其次域必須促成一個具有最佳關聯性的話語,因此,聽話人在尋找情態詞的命題域時,常憑借內嵌命題p概念的百科信息中容易獲取的假設或語境中已有的假設,聽話人旨在重現說話人腦中的命題域類型。Papafragou (2000) 從關聯理論的角度出發,概括了情態動詞的語境依賴性,闡釋了情態動詞語義與語用推理的互動性和情態動詞的多義與歧義特征。
7 結語
綜上所述,西方語言學各領域的學者從各自的角度對情態這一古老和復雜的語義范疇進行了研究。傳統語義學關注的是情態的定義、類型以及表達形式等問題;語言類型學在跨語言的框架下概括情態的基本概念、類型以及情態的語法化過程;系統功能語言學和話語分析聚焦于情態在語篇中的人際交互功能;認知語言學著重從語言認知的角度來解讀情態語義,采用“力動態”和“力爭控制”理論來闡釋情態意義;語用學從言語行為理論、禮貌原則的角度探討情態的語用功能,并從關聯理論的角度闡釋情態話語的理解。
由于情態是一個復雜的語言現象,涉及詞法、句法、語義、語用等語言的各個層面,與語言認知、語言交際等各個方面有關,當下,西方語言學各領域內的學者對情態的研究熱情仍未衰減,新近出版的情態研究論文集包括EnglishModality:Core,PeripheryandEvidentiality、ModesofModality:Modality,TypologyandUniversalGrammar。前者關注的話題有:英語核心情態助動詞及半助動詞在當代英語中的使用和發展趨勢,情態詞的情態與言據性意義;情態在博客等新興語篇中的分布和功能。后者收錄的論文有:從喬姆斯基語段中心語(phase heads)的角度闡釋情態動詞的認識與根情態意義;從語言類型學和句法學的角度探討歐洲語言情態標記的句法和語義特征;德語語氣詞表達的情態語義和句法特征以及功能;隱性情態(covert modality)在歐洲和非洲語言中的標記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對模態邏輯和形式語義學領域的情態研究進行回顧,后續的研究可以加以關注。
參考文獻:
Bybee, J. L, R. D. Perkins & W. Pagliuca. 1994.TheEvolutionofGrammar:Tense,AspectandModalityintheLanguagesoftheWorl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ates, J. 1983.TheSemanticsoftheModalAuxiliaries[M]. London: Croom Helm.
Collins, P. 2009.ModalsandQuasi-modalsinEnglish[M]. Amsterdam: Rodopi.
De Hann, F. 2005. Encoding Speaker Perspective: Evidentils [G]∥ Z. Frajzyngier, D. Rood & A. Hodges.LinguisticDiversityandLanguageTheor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79-397.
Diani, G. 2001. Modality and Speech Acts in English Acts of Parliament [G]∥M. Gotti & M. Dossena.ModalityinSpecializedTexts. Berlin: Peter Lang, 175-191.
Garzone, G. 2001. Deontic Modality and Performativity in English Legal Texts [G]∥ M. Gotti & M. Dossena,153-174.
Garzone, G. 2013.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Modality in Legislative Texts: Focus on Shall [J].JournalofPragmatics(57):68-81.
Halliday, M. A. K. 1994.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2nd ed.) [M]. London: Arnold.
Holmes, J. 1988. Doubt and Certainty in ESL Textbooks[J].AppliedLinguistics, 9(1):21-44.
Hoye, L. 1997.AdverbsandModalityinEnglish[M]. London: Longman.
Hyland, K. 1998a.HedginginScientificResearchArticles[M]. Amsterdam: Benjamins.
Hyland, K. 1998b.Persuasion and Context: The Pragmatics of Academic Metadiscourse [J].JournalofPragmatic(30): 437-455.
Hyland, K. 2000.DisciplinaryDiscourses:SocialInteractionsinAcademicWriting[M]. London: Longman.
Hyland, K. 2005.Metadiscourse[M]. London: Continuum.
Jespersen, O. 1924.ThePhilosophyofGrammar[M]. London: Allen & Unwin.
Kosko, K. W. & P. Herbst. 2012. A Deeper Look at How Teachers Say What They Say: A Quantitative Modality Analysis of Teacher-to-Teacher Talk[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 28(4): 589-598.
Krazer, A. 1981. The Notional Category of Modality [G]∥H. J. Eikmeyer & H.Rieser.Worlds,WordsandContext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38-74.
Langacker, R. W. 1991.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 Vol.2,Descriptive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9.GrammarandConceptualization[M].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Langacker, R.W. 2010. Control and the Mind/body Duality: Knowing vs. Effecting [G]∥ Tabakowska, M. Choiński &. Wiraszka.CognitiveLinguisticsinAction:FromTheorytoApplicationandBack. Berlin &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165-207.
Langacker, R.W. 2013. Modals: Striving for Control [G]∥ J. Marin-Arrese, M. Carretero, J. Hita & J. Van der Auwera.EnglishModality:Core,PeripheryandEvidentiality.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3-55.
Leech, G. 1983.PrinciplesofPragmatics[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Leech, G. 2013. Where Have All the Modals Gone? An Essay on the Declining Frequency of Core modal Auxiliaries in Recent Standard English[G]∥ J. Marin-Arrese, M. Carretero, J. Hita & J. van der Auwera,95-115.
Leech, G. 2014.ThePragmaticsofPolitenes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iss, E. & W. Abraham.ModesofModality:Modality,TypologyandUniversalGrammar[G].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Lyons, J. 1977.Seman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alej, Z. 2002. Modal Auxiliaries: A Proposal for an Experientialist-pragmatic Account[J].EtudesLinguistiques(4):9-83.
Martin, J. R. 1990.Interpersonal Grammaticalisation: Mood and Modality in Tagalog[J].PhilippineJournalofLinguistics, 21(1): 2-50.
Martin, J. R. & . Rose. 2007.WorkingwithDiscourse(2nd ed.) [M]. London: Continuum.
Martin, J. R. &P. R. R. White. 2005.TheLanguageofEvaluation:AppraisalinEnglish[M]. New York: Acmillan.
Palmer, F. R. 1979.ModalityandtheEnglishModals[M]. London: Longman.
Palmer, F. R. 1990.ModalityandtheEnglishModals(2nd ed.) [M].London: Longman.
Palmer, F. R. 1986.MoodandModal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F. R. 2001.MoodandModality(2nd e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pafragou, A. 2000.Modality:IssuesintheSemantics-pragmaticsInterface[M].Oxford: Elsevier.
Perkins, M. 1983.ModalExpressionsinEnglish[M]. London: Frances Printer.
Simon-Vandenbergen, A. M. 1997. Modal (Un)certainty in Plitical Discourse: a Functional Account[J].LanguageSciences, 19(4):341-356.
Sperber, D. & D. Wilson. 1995.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Sweetser, E. 1990.FromEtymologyto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lmy, L. 1988.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J].CognitiveScience(12): 49-100.
van der Auwera, J. & V. A. Plungi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J].LinguisticTypology(2):79-124.
Verschueren, J. 1999.UnderstandingPragmatics[M]. London: Arnold.
von Wright, G. H. 1951.AnEssayinModalLogic[M]. Amsterdam: North-Hol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