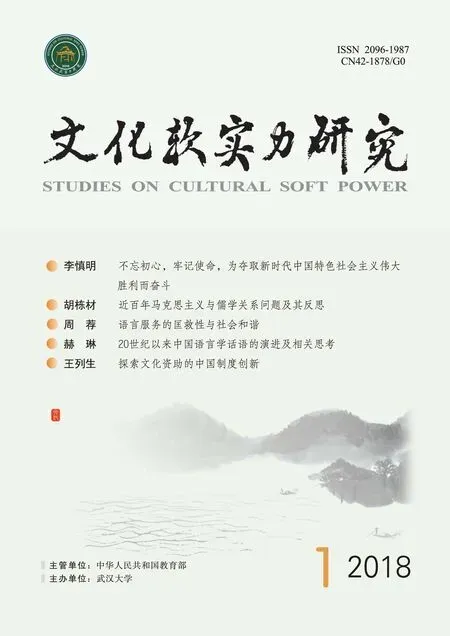20世紀以來中國語言學話語的演進及相關思考
赫 琳
一般認為,《馬氏文通》的問世,開啟了中國現代語言學之路。進入20世紀以來,西方語言學思想對我國語言學話語產生了強勢影響,逐漸形成了以模仿、借鑒西方理論為主導的研究理念和范式,其中也有所反思和校正,尤其改革開放以后,語言研究呈現多元化態勢,注重漢語事實、發掘漢語規律成為主流話語。從總體上看,百余年來,我國學者在引進、借鑒、吸收西方理論的同時,也在努力創新,不懈地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并且化用和新創了不少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術語和主張,中國特色語言學話語體系正在逐步形成。近些年來,在全國上下高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背景下,構建中國特色語言學話語體系,已經成為我國語言學界的熱門話題和孜孜以求的目標。在這樣的形勢下,系統梳理我國現代語言學話語狀況,探討其演進的脈絡,總結得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的探討只是粗略的梳理和初步的思考,旨在拋磚引玉,助力中國特色語言學話語體系建設。
一、語法學:從模仿到結合
中國現代語法學起步階段的語法研究,基本上是“模仿型話語”。1924年出版的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是我國第一部體系較完整的白話文語法著作。該書摒棄了“詞本位”的語法學體系,首創“句本位”的語法學體系,給中國語法研究帶來了新的氣息。不過,與同期其他語法學著作一樣,整體上也是套用國外語法學體系,痕跡比較明顯。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語言學者逐漸發現,簡單模仿西方語法體系存在很大問題。1936年王力發表的《中國文法學初探》,被視為反駁模仿、革新中國語法學的宣言;1938年陳望道等發起了中國文法革新大討論,促進了對中國語言學發展的反思和新探索。王力提出“要從客觀材料中概括出語言的結構規律,而不是從某些先驗的語法規則中審查漢語”*《王力文集·中國語言學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頁。,他指出漢語的特點以及中國文法的研究方法,并借鑒葉斯伯森的理論提出了“三品說”,為建立漢語句法體系做出了貢獻;高名凱主張研究漢語語法應當以口語為出發點,提出了“范疇論”;呂叔湘開創了以語義為綱描寫漢語句法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動詞中心論”“動詞方向論”等嶄新的理論;陳望道力倡“根據中國文法事實,借鏡外來新知,參照前人成說,以科學的方法、謹嚴的態度締造中國文法體系”(《中國文法革新論叢》序)。這些便構成了那個時期最具影響和建樹的中國語言學話語。
20世紀50年代,丁聲樹吸收結構主義理論編寫而成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是一部全面描寫漢語語法的專著;胡附、文煉的《現代漢語語法探索》一方面不同意傳統語法以意義為主要標準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主張在傳統語法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吸收新的語法研究理論和方法,也都別開生面。
1979年,呂叔湘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以語法分析為綱,從重要語法學術語剖析入手,對語法體系問題進行了重新審視。他認為,傳統的析句方法需要和層次分析法結合起來。朱德熙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語法講義》《語法答問》將結構主義的原則和方法與漢語的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比較適應漢語實際的語法體系*參見沈陽編:《走向當代前沿科學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25頁。。一個時期,結構主義話語成為中國語言學的強勢話語。
80年代后,結構主義理論在中國的主導地位逐漸淡化,傳統語法、結構主義語法、轉換生成語法等語法理論在中國都各有市場,其他新的理論方法也不斷被引進、借鑒,開始呈現話語多元化局面。胡裕樹的《現代漢語》首次提出了從三個平面進行漢語語法研究的思想。朱德熙、邢福義、張斌、范曉等也提出了相近的語法學思想,并開展了研究實踐。呂叔湘、陸儉明、馬慶株、邵敬敏等學者成功地運用語義特征分析法等語義分析手段來解決漢語語法問題。徐烈炯、馮勝利、沈陽等學者的生成語法研究,廖秋忠、陳平、張伯江、方梅等學者的漢語功能語法研究,都各具特色。此外,變換分析法、格語法、配價研究也成為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李臨定、張國憲、袁毓林等都有成果推出。認知語言學的引進也對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崔希亮關于語法理解與認知的研究,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對稱和不對稱》從“連續與離散”“定量與不定量”兩個方面探索漢語語法研究的新途徑,袁毓林的《詞類范疇的家族相似性》和張伯江的《詞類活用的功能解釋》為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原則解決漢語詞類劃分問題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參見許嘉璐等主編:《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頁。。有學者所稱的 “文化語法學”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申小龍繼承發展了張世祿、郭紹虞、傅東華等學者的思想,提出中國文化語言學,主張基于漢語事實,建立能夠與漢民族思維相印證的句子理論和句型體系。*邵敬敏:《新時期漢語語法學史(1978—2008)》,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34頁。
進入21世紀,我國語言學者對國外各種理論方法都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進一步的研究,并且更加注重與漢語實際的結合,注重開拓創新,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和特色術語,完全打破了過去結構主義話語的一統天下,各家理論話語百花齊放的局面業已形成。無論是形式語法、功能語法,還是認知語法、語義—語法都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可圈可點者很多。例如,沈家煊擺脫形式語法的框架,從語義、語用、認知著手,偏重于解釋性的探索,具有濃郁的理論色彩。他的研究不同于傳統的結構主義語法理論,也區別于形式語法,對以分布為主要特征的結構主義語法觀提出了挑戰*邵敬敏:《新時期漢語語法學史(1978—2008)》,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66頁。。馮勝利以漢語為基礎、以研究句法規律為目的,建構了韻律句法學體系,并嘗試將韻律句法學的理論應用于古代詩歌和文體演變的研究。劉丹青的類型學、方言語法、介詞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李宇明的量范疇及句法研究,以及陸丙甫、何元建、石定栩、徐杰、潘海華、金立鑫、郭銳等學者的語法研究,都有獨到之處。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一些學者提出的各種語法“本位論”“三平面論”“三角論”“語義語法”“意合語法”“語義指向”“小句中樞”“韻律句法”“語法與文化的通約性”“句位”等理論觀點和概念術語,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語法學話語特色。這也表明,注重漢語實際才是中國語法學者構建中國特色理論話語的重要途徑。
二、語音學:從傳統到現代化和科學化
中國傳統語言學中的音韻學,由于其深厚的歷史積淀,加上自20世紀初開始,又積極借鑒吸收了西方語言學和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因而成功實現了現代化轉型,走上了科學發展之路;與此同時,現代漢語音系學也得以產生和發展。兩者的互補,形成了中國語音學的體系特色和話語特色。
1923年,汪榮寶發表了著名的論文《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在材料上突破了漢字的束縛,在方法上擺脫了單純的考證,為擬測古音音值開辟了新的大道,成為漢語現代音韻學誕生的重要標志*參見楊劍橋:《漢語現代音韻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繼瑞典學者高本漢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擬測漢語中古音之后,趙元任、王力、羅常培、陸志韋、王靜如、董同龢、周法高、李榮、李方桂等對中古音進行了進一步擬測,林語堂、李方桂、董同龢、陸志韋、嚴學宭等人對上古音進行了擬測,羅常培、趙蔭棠、陸志韋、楊耐思等人對近代音進行了擬測,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0世紀現代漢語的語音描寫是從20年代初對“國音”的描寫和現代語音學知識的介紹開始的。1922年,趙元任發表《中國言語字調底實驗法》,最早介紹了漢語聲調的實驗研究方法,這是中國實驗語音學的濫觴之作;1930年,他發表《一套標調的字母》,創制出五度值標調法;1934年,他又發表《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成為音位學理論的經典之作*孟曉妍:《趙元任文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8頁。。1929年,劉復在北京大學建立語音樂律實驗室,創制了聲調推斷尺。王力利用浪紋計實驗了廣西博白的元音、輔音,再用浪紋計實驗了聲調,1931年完成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潘悟云、邵敬敏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語言學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4頁。。五六十年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羅常培、王均的《普通語音學綱要》,該書將語音學的一般原理與中國語言實際緊密結合起來。
20世紀80年代以后,普通話音位研究成為一個熱點。我國最早用區別特征理論研究普通話音位的是吳宗濟,他在論文《試論普通話語音的“區別特征”及其相互關系》中根據語音的聲學特性和傳統音韻學中的若干分類標準擬定區別特征*盛林、宮辰、李開:《二十世紀中國的語言學》,黨建讀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頁。,充分考慮到了漢語的實際,與國外區別特征理論的應用研究有所不同。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國外關于音系學方面的理論越來越多地被介紹進來,中國學者也越來越多地將音系學理論與漢語實際結合起來研究,并對有關理論進行補充、修正和創新。例如,王理嘉的《音系學基礎》是我國第一本系統介紹和討論音位分析理論的專著;徐通鏘、王洪君提出應該區分連續式、擴散式、疊置式三種不同的音變方式*徐通鏘、王洪君:《說“變異”——山西祁縣方言音系的特點及其對音變理論研究的啟示》,《語言研究》1986年第1期。;王洪君的《漢語非線性音系學》運用非線性音系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從新的角度對漢語進行了分析。八九十年代語音學和自然科學有諸多結合,同時與語言學其他分支學科,如社會語言學、少數民族語言學和二語教學等也開始結合,取得了新的拓展。
三、詞匯學:從字的訓詁到詞匯的全面關注
中國傳統語言學中的顯學訓詁學,主要著力點是字的訓詁,較少關注詞匯的體系和詞義系統。進入20世紀之后,隨著訓詁學的革新、語言學意識的增強和后來蘇聯語言學的影響,訓詁學優秀傳統和現代語言學思想相融匯,促成了中國現代詞匯學的誕生與發展,也形成了中國詞匯研究的鮮明特色。
晚近小學大師黃侃提出:“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頁。這已表明傳統訓詁學的新追求。
20世紀40年代訓詁學出現新氣象,傅懋勣發表《中國訓詁學的科學化》,王綸發表《研究訓詁之新途徑》,王力發表《新訓詁學》,主張訓詁學要著重研究語義變遷等詞匯學的問題,已具有現代詞匯學話語氣息。這是現代詞匯學產生的基礎之一。另一方面,在外國語言學理論影響下,“詞”的概念漸漸受到關注。第一個明確提出詞概念的是章士釗,他在《中等國文典》中分析了字與詞的區別。*林玉山:《20世紀中國語言學回眸》,載姚小平主編:《〈馬氏文通〉與中國語言學史(首屆中國語言學史研討會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頁。隨后,王力、呂叔湘、高名凱、陸志韋等學者探討了什么是詞、如何確定詞等詞匯學的基本問題。同時,《中華大字典》《辭源》《辭海》對漢語詞匯進行了系統整理,收入大量的古漢語語詞、新的名詞術語,而此時編成的《國語辭典》已具有現代語言描寫、規范詞典的性質*符淮青編:《漢語詞匯學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這些都為詞匯學的產生奠定了重要基礎。
50年代,在以上所述的基礎上,在蘇聯語言學的影響下,現代漢語詞匯學逐漸產生。周祖謨的《漢語詞匯講話》和《詞匯和詞匯學》、張世祿的《詞匯講話》和《普通話詞匯》、孫常敘的《漢語詞匯》等,構建了現代漢語詞匯學的大致輪廓,確定了它的研究對象、任務和范圍*符淮青編:《漢語詞匯學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現代漢語詞匯學的基本話語體系大體上得以形成。
70年代中期以后的數十年,漢語詞匯學有了較大發展,出現了一大批詞匯學著作,例如李行健、劉叔新的《詞語的知識和應用》、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的《現代漢語詞匯知識》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武占坤、王勤的《現代漢語詞匯概要》在詞匯體系問題上作了新的論證;葛本儀的《漢語詞匯研究》探討了現代漢語詞的確定,提出了新的分類;符淮青的《現代漢語詞匯》《詞義的分析和描寫》和劉叔新的《漢語描寫詞匯學》在理論上又有新的推進;許威漢的《漢語詞匯學引論》、賈彥德的《漢語語義學》、何九盈和蔣紹愚的《古漢語詞匯講話》、蘇新春的《漢語詞義學》《當代中國詞匯學》等,也都各具特色。
詞匯學在21世紀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詞匯學理論與應用研究逐步深入,出現了不少新的分支學科,如詞匯語義學、詞彩學、計量詞匯學、語料庫詞匯學、現代詞匯學史等;新出版了張志毅和張慶云的《詞匯語義學》、周薦的《漢語詞匯結構論》、蘇新春的《漢語詞匯計量研究》和《漢語詞義學》、張聯榮的《古漢語詞義論》、周國光的《現代漢語詞匯學導論》、楊振蘭的《動態詞彩研究》、許威漢的《二十世紀的漢語詞匯學》、周薦和楊世鐵的《漢語詞匯研究百年史》等重要詞匯學著作。與此同時,這一階段一些學者開展的特色研究和提出的獨到的詞匯學理論觀點令人耳目一新,例如江藍生提出的“類同引申說”、王寧構建的現代詞源學術語系統、符淮青的詞義描寫研究、張志毅的詞匯語義學研究、蘇寶榮結合辭書釋義的詞義研究、*參見蘇寶榮:《詞義研究與辭書釋義》(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及系列論文。蘇新春的詞的文化義研究、周薦的詞匯結構研究、趙世舉的基于語義與語法接口的詞義研究等*參見趙世舉:《關于詞義的再認識——基于語義—語法接口的詞義觀》(《中國語言學報》第15輯)、《試論詞匯語義對語法的決定作用》(《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8年第2期)等系列論文。,都是具有中國詞匯學特色的話語。
四、文字學:從《說文》學到古今兼治各科并興
我國的文字研究發生很早,成果豐碩,特色鮮明,是最具中國話語特色的學術領域之一。大致來說,20世紀以前及20世紀初的中國文字學主要是“《說文》學”,屬于傳統小學;其后則百花齊放,古今兼治,各科并興,形成了獨樹一幟、理論較為成熟的中國文字學話語體系。到了21世紀,中國文字學更加繁榮發展。
“《說文》學”在繼承中有發展,章炳麟、黃侃突破了傳統小學的《說文》學,從語言學角度研究《說文》,別開生面,成就突出,是中國現代文字學的先聲。
古文字學勃興。由于19世紀末甲骨文的發現等因素,古文字學擺脫傳統小學和金石學的束縛,實現了方法變革和視野拓展,逐步走上了獨立發展之路,成為一門較熱門的學科。這是中國文字學的重大發展。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為古文字學提供了基本理論框架,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古文字學產生的標志。隨后一批相關理論著作問世,如李學勤的《古文字學初階》、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簡論》、高明的《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等,都為古文字學的理論建設和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甲骨文、金文集成性大型著作和字典相繼推出;出版了一批甲骨金文通論性著作,例如陳夢家的《殷虛卜辭綜述》、嚴一萍的《甲骨學》、孟世凱的《殷墟甲骨文簡述》、王宇信的《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和《甲骨學通論》、吳浩坤等的《中國甲骨學史》、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和《殷周青銅器通論》(與張維持合著)、朱鳳瀚的《古代中國青銅器》等;關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專科性研究,涉及面非常廣泛,在斷代研究、文字考釋、語言研究、史料考據、內容闡釋等方面都有很多成果問世。此外,簡帛印璽等文字研究也有很大發展。一批中青年學者的研究引人矚目,例如黃德寬、吳振武、劉釗、黃天樹、陳偉等,不勝枚舉。這些都充分表明了古文字學的成熟和繁榮。
文字學理論問題研究成果迭出。出現了大量的通論性概論性著作,目前見到的最早的是1918年北京大學出版部印行的朱宗萊《文字學形義篇》。雖然它的主體內容基本上還是傳統小學話語,但體系框架體現了系統的文字學思想。有學者把它看做中國現代文字學產生的標志性理論著作。其他還有呂思勉的《中國文字變遷考》、顧實的《中國文字學》、胡樸安的《文字學ABC》、蔣善國的《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和《漢字學》、劉大白的《文字學概論》、張世祿的《中國文字學概要》、唐蘭的《中國文字學》,以及后來出版的高元白的《漢字的起源發展和改革》、梁東漢的《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裘錫圭的《文字學概要》、王鳳陽的《漢字學》、王寧的《漢字構形學導論》等,都在努力構建漢字學體系。從研究內容上看,漢字的起源、漢字的流變、漢字的性質、漢字的構形、文字改革、漢字文化、漢字研究史等重要問題都備受關注,論著不斷地大量問世,其中有很多新見和理論建樹。
現代漢字學產生。隨著文字學的發展和中國文字改革的不斷推進與深化,以及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現代漢字學應運而生。1980年,周有光發表《現代漢字學發凡》一文,首先提出了“現代漢字學”概念術語,并且進行了框架描述。他把漢字學分為歷史漢字學、現代漢字學、外族漢字學三個部分,并提出“現代漢字學研究現代漢字的特性和問題”。*周有光:《現代漢字學發凡》,《語文現代化》1980年第2期。隨后出現了一系列通論性著作,如高家鶯、范可育和費錦昌的《現代漢字學》,蘇培成的《現代漢字學綱要》,李祿興的《現代漢字學要略》等。由此,現代漢字學得以形成并快速發展,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在現代漢字體系、漢字結構理論、漢字簡化、字義理論、文獻用字的字際關系、漢字與文化研究、漢字個體解釋和字典編纂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參見潘悟云、邵敬敏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語言學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24頁。,現代漢字學理論體系不斷完善。
五、修辭學:從“搭架子”到多樣化
現代修辭學的發展、成熟過程,也就是修辭理論的建設過程。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一書融匯古今中外的修辭學話語,率先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比較完備的修辭學體系,是中國現代修辭學誕生的標志。張弓的《中國修辭學》、王易的《修辭學通詮》、陳介白的《修辭學》、宋文翰的《國語文修辭法》等在理論上都有獨到見解。
20世紀上半葉的修辭學基本上處于“搭架子”的初建階段,各家的研究多集中于一些最基礎的理論問題,主要包括什么是修辭學、修辭學的目的和任務、修辭現象的兩大分野及其統一、修辭學的范圍、語言規范等。同時,辭格研究也有一些重要成果,最早研究辭格的專著是唐鉞的《修辭格》,該書參考訥斯菲的《高級英文作文學》,把辭格分為5類27格*何九盈著:《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572頁。。楊樹達的《中國修辭學》將修辭樣式和閱讀古書的條例結合起來,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富有特色的修辭學專著。
50年代,呂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風靡全國,影響很大。一批現代修辭學論著相繼問世,如張志公的《修辭概要》、楊樹達的《漢語文言修辭學》、張世祿的《小學語法修辭》、張弓的《現代漢語修辭學》、倪寶元的《修辭學習》等。其中,張志公《修辭概要》的出版,標志著白話修辭學的創立。張弓的《現代漢語修辭學》提出了“尋常詞語藝術化”的獨到見解,建立了別開生面的修辭學體系*參見黎運漢、盛永生主編:《漢語修辭學》,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3頁。。
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力求走出“辭格論”框架,以新的視角來觀照修辭現象,創建新的體系*汪國勝、馮廣藝:《新時期的漢語修辭研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鄭遠漢的《現代漢語修辭知識》等建立了“語言三要素”修辭學體系,提倡研究言語的各種同義形式和表達方式的構成與表達作用。王希杰的《漢語修辭學》和《修辭學通論》提出了以辯證法思想為綱的修辭體系,主張以得體性為最高修辭原則、以三組基本概念有機統一作為基本框架的“三一修辭學”理論。宗廷虎的《修辭新論》建立了注重修辭現象的層次性的新的修辭學理論體系。譚學純的《廣義修辭學》提出了修辭功能的三層面,即作為話語建構方式的修辭技巧、作為文本建構方式的修辭詩學和參與人的精神建構的修辭哲學。馮廣藝的《變異修辭學》系統探討了變異修辭學。王德春和陳晨的《現代修辭學》則“運用現代語言學和有關現代科學的理論,不僅研究語言體系的修辭手段和修辭方法,而且以言語環境為基礎,研究了話語整體和言語規律”*王德春:《現代修辭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內容包括語境學、語體學、風格學、文風學、言語修養學、修辭手段學、修辭方法學、話語修辭學、信息修辭學、控制修辭學、社會心理修辭學、語用修辭學等板塊,拓展了修辭學的視野,展現出修辭學話語的新氣息。
六、方言學和少數民族語言學:從輯釋詞匯到全面調查研究與保護
關于漢語方言的研究,20世紀初,大體上還是承襲古代的研究范式,主要是進行方言詞匯的輯錄和考釋。1924年北京大學成立“方言調查會”,公開倡導對活的方言進行調查、記錄和研究,并且設計了一套以國際音標為基礎的記音符號,用它標注了14種方言作為示范,開始了有計劃的方言調查和研究*參見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從此拉開了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序幕。那時的《歌謠》周刊及其增刊發表了多篇與方言研究相關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沈兼士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趨勢》和林語堂的《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趙元任的《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是中國第一篇研究方言語法的論文,而他的《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是中國方言學史上第一部以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研究方言的專著。1956年,教育部發布了《關于漢語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各地紛紛成立了方言調查機構,開始進行大規模方言調查研究活動。除了“文革”時期之外,方言調查研究一直都是活躍的領域。既有綜合性著作出版,如袁家驊等編著的《漢語方言概要》等,又有調查方法指南,例如李榮的《漢語方言調查手冊》,更有大量的研究專著不斷涌現,例如李永明的《潮州方言》、王世華的《揚州音系》、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的研究》、顏逸明的《吳語概說》、陳章太和李如龍的《閩語研究》等*潘悟云、邵敬敏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語言學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頁。。此外,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主編的《漢語方言大詞典》、詹伯慧和張振興主編的《漢語方言學大詞典》、曹志耘主編的《漢語方言地圖集》等,是我國方言學集大成之作。
具有現代語言學意義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開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它是在我國古代民族語文研究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且受到了國外語言學理論和漢語研究的影響。自那時起,逐步形成了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基本范式。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傅懋勣、聞宥等都有重要成果推出。50年代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研究所組織的全國少數民族語言普查,把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引向了更加廣泛和深入的階段。以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學等單位為代表的學者在少數民族語言調查、描寫、識別、文字創制、重要問題研究等方面,不斷有成果推出。孫宏開、胡增益和黃行主編的《中國的語言》集成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成果,集中體現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特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對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保護研究的推動。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大力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進一步強化了語言文字事業在國家文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2008年國家語委啟動了“中國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建設”,在此基礎上,2015年教育部和國家語委又下發《關于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通知》,拉開了中國有史以來規模空前、也是世界規模最大的語言資源調查保護工程的帷幕。該工程由國家財政支持,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統一規劃和指導,各地方語委和專家隊伍具體實施。國家語委有關負責人田立新指出,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是對原有中國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建設的進一步擴充、整合,工程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收集記錄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口頭語言文化的實態語料,通過科學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規模、可持續增長的多媒體語言資源庫,并開展語言資源保護研究工作,進而推進深度開發應用,全面提升我國語言資源保護和利用水平,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安全服務”。*田立新:《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緣起及意義》,《語言文字應用》2015年第4期。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核心專家組組長曹志耘把語保工程的定位表述為“國家工程,社會化,科學性”。*曹志耘:《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定位、目標與任務》,《語言文字應用》2015年第4期。這項工程的實施,不僅表現為語言調查研究的規模擴充和全面推進,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國家、學界和社會語言觀念的轉變,是在“語言資源觀”指導下,對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保護和利用工作的全面深化,對其意義和價值的進一步提升。這也彰顯了中國在本領域的特色,已經引起國際關注和高度評價。
七、 應用語言學:從現代語文運動到廣泛關注社會語言生活
我國應用語言學主要是在19世紀末伴隨著現代語文運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最初主要關注的是語文改革、語言教學等方面。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領域不斷拓展。進入21世紀,應用語言學全面發展,擴大到廣泛關注社會語言生活。不僅關注語言使用自身,也關注語言在其他領域的應用;不僅關注人的語言應用問題,也關注機器的語言使用問題,尤其重視與語言學交叉的領域和新興領域的研究。在語言教育、語言政策與規劃、中文信息處理、語言生活觀測、網絡語言、漢語國際傳播、語言經濟學及語言產業、盲文手語,以及語言在法律、新聞媒體、政務及服務業、安全及偵查、醫療康復、廣告、心理學等行業領域的應用研究方面,有新的開拓,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不僅體現了中國應用語言學話語特色,而且在某些方面正在形成中國學派。
在語言教育研究方面,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研究與實驗不斷推進,“暫擬漢語語法教學系統”的構建是其中的一個特色;民族語和國家通用語的“雙語教學”,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教學實踐,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對外漢語教學/漢語國際教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正式起步,逐步實現了學科建構和開創性發展;外語教學在借鑒國外教學理論的同時,也在結合我國教學實際進行積極探索。
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基于我國語言生活實際,借鑒國外相關理論,在語言政策與規劃的內涵、性質、任務、對象、內容等方面的研究,不斷深化和拓展,特色鮮明,成就斐然。在書面語革新、國語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研制與推行、漢字簡化、語言文字規范化及普通話推廣、術語標準化、民族語言保護與發展、盲人手語研制與規范等領域都有中國特色理論建樹和成功應用。
21世紀以來,隨著“語言生活派”群體的逐漸形成,“語言生活”“語言資源”“語言能力”“語言和諧”等概念得到強化,語言應用研究的中國特色日漸彰顯。李宇明將“語言生活派”的學術主張概括為“就語言生活為語言生活而研究語言和語言生活”。這個群體根植于中國語言生活沃土,以解決中國語言生活問題為己任,同時也密切關注世界語言生活,推動我國語言研究和語言規劃研究發生了重要轉向:一是將語言研究轉向語言生活研究,二是將研究聚焦在語言的社會功能上。*李宇明:《語言生活與語言生活研究》,《語言戰略研究》2016年第3期。郭熙、祝曉紅認為:“語言生活派的最大特點是家國情懷。服務國家、服務社會,做政府、社會和學界之間的旋轉門,這是其旨趣所在。他們的《語言與國家》(趙世舉,2015)、《當代語言生活》(郭熙、朱德勇,2006)、《語言、民族與國家》(蘇金智、夏中華,2013)以及《中國語言生活》電子刊等學術和普及讀物,擴大了學科影響,鍛造出一種接地氣的學術品格。”*郭熙、祝曉紅:《語言生活研究十年》,《語言戰略研究》2016年第3期。十多年來,“在一批學者不懈努力和政府有關部門支持下,通過建機構、搭平臺、聚隊伍,逐步形成了對現實語言生活進行多視角、大規模、成系統、持續性實時觀測研究及發布的體系……取得了不少標志性的成果,并開始了理論創建,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入發展”。*趙世舉:《中國語言觀測研究的實踐及思考》,《語言戰略研究》2016年第5期。自2006年起陸續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綠皮書)、《中國語言政策研究報告》(藍皮書)、《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報告》(白皮書)、《世界語言生活狀況報告》(黃皮書)等,集中反映了“語言生活派”的研究成果。相關學者的研究視野開闊,不斷出新,例如,李宇明對中國語言政策與規劃、語言生活的全方位研究,陳章太對中國語言規劃理論的建構,戴慶廈對少數民族語言生活的調研,陸儉明對語言教育、語言能力等的研究,周慶生對國外語言政策和民族語言政策的研究,郭熙對華語和語言生活的研究,文秋芳對外語教育和國家語言能力的研究,王建勤對國家安全語言戰略的研究,趙世舉對國家語言戰略和語情的研究,蘇新春對教材語言和臺灣語言生活的研究,趙蓉暉對外語戰略和國外語言生活的研究,徐大明對語言資源和城市語言生活的研究,曹志耘對語言保護的研究,屈哨兵對語言服務的研究,蘇金智對語言生活的研究,郭龍生對中國語言規劃的研究,張日培對中國語言政策的研究,張普、侯敏、楊爾弘、何婷婷等關于語言資源監測的研究,黃少安和張衛國關于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等,不勝枚舉。這些大體代表了語言政策與規劃、語言生活研究的中國特色,并且已經引起國際同行的關注,開始走向世界。
中文信息處理研究,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的機器翻譯研究,雖然起步稍晚,一些核心技術落后于人,但近20年發展迅速,成效顯著。具體表現是:漢字規范化工作基本完成,漢語拼音方案被國際標準化組織接納,漢語拼音正詞法規則成為國家標準,為中文信息處理奠定了重要基礎;漢字編碼、輸入/輸出、編輯、排版等相關技術已經解決;漢語分詞規范已經制定,以“綜合性語言知識庫”和知網為代表的一批漢語資源庫相繼建成;詞語自動切分、命名實體識別、句法分析、詞義消歧、語義角色標注和篇章分析等自然語言處理的基礎問題得到全面研究和推進,一系列不斷改進的模型和方法相繼提出;機器翻譯、信息檢索、輿情監測、語音識別和語音合成等應用技術在眾多互聯網企業、國家特定領域和機構中得到實際應用。*宗成慶:《中文信息處理現狀分析》,《語言戰略研究》2016年第6期。同時,我國蒙古語、藏語等民族語言信息處理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和突破。從我國中文信息處理技術在眾多領域的成功應用和在國際某些領域競賽中名列前茅的情況來看,中文信息處理研究的中國特色和優勢正在形成。
余論:關于中國語言學話語體系建設的思考
從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百年來,我國語言學者一方面立足于我國語言學傳統,積極進行新的開拓;另一方面借鑒西方語言學理論,進行中國化的嘗試,努力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為中國語言學話語體系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從整體上看,理論創新和體系構建還比較薄弱,需要反思和繼續探索。
(一)中國語言學發展有著明顯的優越條件,需要增強學術自信
第一,我國語言學有悠久的傳統和豐富的積淀,有很多寶貴的遺產值得發掘、傳承和利用。這是我們深厚的學術根基。第二,我們有極其豐富的語言資源。中國是世界上語言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分布著300余種分屬東方的漢藏語系、西方的印歐語系、北方的阿爾泰語系和南方的南亞語系、南島語系的語言,中國語言的地域和語系分布之廣,大概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黃行:《中國語言資源多樣性及其創新與保護規劃》,《語言學研究》2017年第1期。。同時,我國漢語方言十分豐富,按照一般的說法,就有八大方言區。這是我國語言學發展的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第三,語言學越來越受到中國社會各方面的重視。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眾多領域語言需求的增加,語言學有了很多新的機遇和條件。政府和社會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必將促進語言學科更好地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中國語言學發展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正視和克服
突出的表現是理論意識和創新意識不足,習慣于對過去的沿用和對別人的借用。這種情況有很多表現,徐通鏘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于高校一直在采用自己編的《語言學綱要》是既高興又悲哀。悲哀在于《語言學綱要》不是“萬歲”的,需要隨著語言學的發展不斷變化。到現在,其中的一些基本思路他自己已經放棄了,但社會上仍不放棄*《徐通鏘先生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求索者徐通鏘先生紀念文集》,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519頁。。由此可見一斑。中國的語言研究和教學通常樂于追捧經典,繼承經典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而故步自封。由于受中國尊師重道的治學傳統的影響,學生往往一味地講求繼承老師的學問,而不敢提出新見,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創新的勇氣和意識。習慣借用的問題也非常突出,英國倫敦大學應用語言學講席教授李嵬曾公開指出:“目前,到海外參加語言學學術活動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往國外期刊投稿的量也越來越大,但多數研究的理論框架是從國外學者那里套用過來的,是用中國的豐富語言資料論證國外的語言學理論,很難看到中國學者自己的理論、聽到中國人真正的聲音”*李嵬:《中國語言學要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9月26日。。可見,缺乏創新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
與上一個問題相聯系,另一個表現是多而不精、淺而不深。應該承認,中國語言學近30年得到了很大發展,論著數量不斷上升,但內容是評介、概述、引證、套用的比重大。 “有不少發表的學術論文局限于對基本概念的闡述,缺乏結合實際的語言現象進行創新研究”。“如果說在中國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起步階段,對國外語言學理論的引介是必要的話,那么,在中國語言學急速發展的今天,一些研究仍停留于對語言學理論、基本概念低層次的重復介紹上,不結合我國語言實際和具體語料進行系統、創新的研究,那就明顯落伍了,無助于語言學研究的發展”*范繼花:《論中國語言學三十年發展之概況》,《人民論壇》2010年第23期。。同時,缺乏學術批評的氛圍,也是我國語言學界的明顯問題。
學科內部互通不暢問題也比較突出。傳統語言學界、現代語言學界,漢語學界、民族語言學界、外語學界,理論語言學界、應用語言學界,各有優勢,但大多各守疆界,缺少交流合作。很多研究學科分野分明,學科內部互通性研究、交叉融合點研究和不同理論方法綜合運用的研究缺乏,關注新問題不多,宥于學科小分支、按照傳統路子做研究的為多。據宋暉對《中國語文》《世界漢語教學》等九類語言學刊物2009年所發文章的統計,傳統研究,如漢語史、訓詁、漢語具體詞匯等研究占全年發文的72.3%,這也從一個層面反映出問題所在。至于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結合和互動更少,這就導致語言學不能很好地吸收其他學科的營養,也同樣限制了語言學的發展。
(三)中國語言學發展需要腳踏實地穩健創新
構建中國特色語言學話語體系,必須增強理論意識和創新意識,立足于中國語言實際,堅持繼承與借鑒結合,堅持批評與獨立精神,走中國語言學自己的路。張斌說,“學術不是關起門來就可以做的,介紹國外的理論是重要的,問題是不要老是跟著人家跑,最好的貢獻是把國外的理論跟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一定要了解人家,也一定要重視漢語的特點”*張宜:《歷史的旁白——中國當代語言學家口述實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頁。。徐通鏘也強調,“一定要從具體材料出發,從材料的梳理中提煉相應的理論,絕不要套用國外語言學的一些概念,湊點材料,敷衍成篇”*徐通鏘:《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頁。。邢福義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語言學研究,應該旗幟鮮明:面向世界,面向時代需求;根在中國,根在民族土壤。”*邢福義、王耿:《中國語言學要有一顆中國心——邢福義訪談錄》,《語文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10期。注重漢語實際,探索漢語特點,是構建中國特色理論話語的重中之重。
要用問題導向驅動理論創新。強烈的問題意識,是把握學術研究、學術創新內在規律的體現。問題導向永遠是理論工作和理論創新的原動力。*參見尹漢寧:《立足中國實踐 創新中國話語》,《紅旗文稿》2014年第12期。中國語言學研究,一定要從中國語言及其使用中存在的問題出發,理論創新始終都應當明確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不能憑空假設和簡單模仿。
要對理論創新有足夠的寬容度。語言的復雜性和時代的局限性,決定了任何一個理論不可能在提出的時候就保證它的絕對正確性,有目的的研究本身就是在探尋未知,需要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完善,這就需要鼓勵大膽探索并保持寬容,容忍難以避免的錯誤和失敗。只有這樣,才能有利于學者們保持創新的熱情和勇氣,積極參與中國特色語言學理論體系構建。
要注重跨學科研究。語言學需要與哲學、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政治學、認知科學、信息科學等不同學科進行對話,相互結合和相互借鑒,推動語言學創新發展。在語言功能不斷發展的今天,這一點更顯重要。
要注重提升語言學者的語言能力,包括母語能力、外語能力和少數民族語言能力在內的多語能力。這不僅是語言研究自身的需要,也是理論表達和成果傳播的需要。有學者指出,一個國家想要成功確立國際話語權,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提升理論貢獻能力:第一,“能夠明確、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態度,也就是解決‘能夠說’的問題”;第二,“動員各種資源,建立各種渠道來最大限度地吸引聽眾,并且用世界多數國家都能理解的方式進行表達,同時建立自己言辭的信任度。也就是解決‘有人聽’的問題”*中央黨校課題組:《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的經驗、挑戰與對策》,《對外傳播》2014年第12期。。要想做到這兩點,就要提高我國語言學者的多語能力。現在很多語言學者外語能力的不足,使他們無法在國際上自如地表達自己的理論觀點,制約了中國聲音的國際表達。這也是中國語言學話語體系建設需要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要注重變換視角,登高望遠,正確處理古今中外之間的關系,善于為我所用而不被其束縛。要想讓我們創建的語言學理論體系與國情相符合,被世界接受,就需要有高屋建瓴的水準和發展的眼光、世界的眼光。一是要把理論創新放在學術史的視角下,考量其價值。周有光曾提倡“厚今而不薄古”。“一個人既要知道古代,又要知道現代,可是不能拿古代來限制現代。我們要往前走,不是不要古代文化”*周有光:《對話周有光》,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頁。。這是十分深刻的。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審視自我,在更廣闊的視野下反思所創理論的科學性和普遍性,考察其是否能為人類語言學做出貢獻。如果能在這兩個視角下來審視我們的理論,并不斷修正和完善,那么終有一天具有中國特色、世界價值的語言學話語體系必將形成,并在世界上產生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