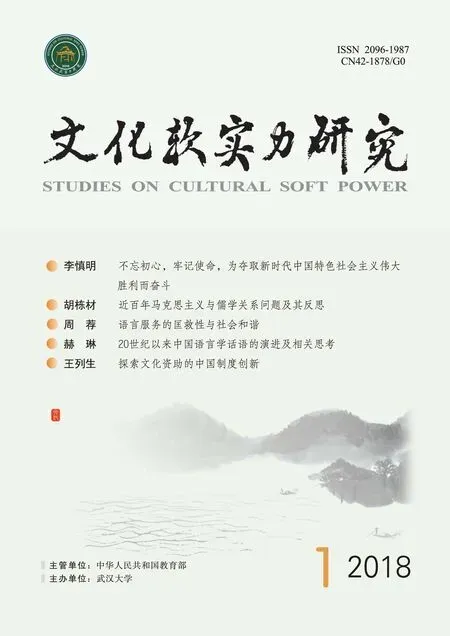語言服務的匡救性與社會和諧
周 薦
一、語言服務的匡救性,效果大不相同
如所周知,語言是人類交際交流的工具,人們每日每時都要運用此工具為達成自己的某種目的服務。人們耳熟能詳的語言服務有用同一語言所做的服務,也有語際服務,包括不同語言間的翻譯服務,自然語言與人工語言間的服務,有聲語言與體態語言間的服務,甚至人類語言與非人類之間的服務等。這些服務,有的是生活類型的,可稱生活類語言服務;有的是工作類型的,可稱工作類語言服務。工作類語言服務,有眾多的內容,其中之一,服務的目的是匡時救弊,可稱語言服務的匡救性。在人類的歷史上,無論戰、和哪種狀態,匡救性對于語言服務而言都是極為重要的,不可或缺。語言服務的匡救性,因為使用者的階級、身份、地位,因為使用的目的,因為服務對象等的不同,效果也會有所不同。語言服務的匡救性的作用,在和平年代或不甚明顯,在戰爭年代則看得異常清楚。例如,20世紀上半葉國共決戰中,國共兩大陣營的眾多領袖人物都是運用自己的母語——漢語的高手,但他們用以服務的對象、目的等截然不同,服務的效果也大不一樣。這種現象的出現很難從兩黨兩軍領袖人物各自的教養上找到原因,因為兩大陣營領袖級人物中的相當一批都曾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甚至同出一門(如同出身于黃埔軍校);而只能從他們為之服務、獻身的階級,從他們所建立的政權的基礎上尋找原因。先看下面對照鮮明的一對例子:
一個例子是毛澤東1931年12月19日所作《六言詩·蘇維埃政府布告》(收入《毛主席詩詞全集》),節錄如下:
軍閥豪紳地主,到處壓迫窮人。
利用國民政府,要捐要稅不停。
地主白占土地,廠主壟斷資本。
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參加革命。
窮人一致奮起,組織工農紅軍。
豪紳地主土地,一律分給農民。
免除苛捐雜稅,都是有吃有剩。
工人每日工作,只做八個時辰。
商人服從法令,生意由你經營。
各地工農群眾,趕快參加革命。
建立工農政府,快把地主田分。
工人組織工會,快同廠主斗爭。
大家一致努力,完成中國革命。
一個政府的布告本該是非常嚴肅的公文,但毛澤東所擬的不但用了許多俗白的詞語,而且用的是詩(實際上是順口溜)的形式,用意是非常明顯的:讓不識之無或識字不多的窮苦百姓都能看得懂,聽得明白,以達到最佳的宣傳目的。
另一個例子是蔣介石1927年4月15日發布的清黨布告*選自鄭庭笈:《國民黨各地“清黨”資料一組》,載《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照錄如下:
為布告事:
照得此次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共產黨連同國民黨內跨黨之共產黨員等有謀叛證據,請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在所在各地將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機關,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仍須和平待遇,以候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全體大會處分等因。此系阻止少數分子發生叛亂行為而已,并非變更國民黨任何政策。所有一切農工主要團體及各級黨部皆照常進行,毫無更張。務望各方面皆應安堵如常。本總司令職司討伐,以維持地方秩序為最要。如有借端擾動,有礙治安者,定當執法以繩其后也。
此布。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中正
蔣介石所擬的文告用的是當時士大夫常用的文言字詞甚至句式,典雅倒是典雅,但與當時鮮活的口語嚴重脫節,不是最基層的勞苦大眾習用的。
毛澤東和蔣介石兩人語言服務的匡救性效果截然不同,高下立判:一個是不識之無的勞苦農工人人一聽就懂,便于喚起大眾;一個是只有受過文言教育的人士才懂,受眾范圍極其狹小,普通百姓卻感到十分難懂。
下面一組例子出自孟良崮戰役紀念館的宣介材料:
一個例子是1947年5月13—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為圍殲國軍整編第74師發動孟良崮戰役時,陳毅給解放軍下達的命令:
現在要不惜一切代價,把孟良崮拿下來。誰打下孟良崮,誰就是戰斗英雄!
另一個例子是蔣介石當時給國軍下達的命令:
此為我軍殲滅共軍完成革命惟一之良機,如有萎靡猶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頓……必以誤國縱匪貽誤戰機論罪,決不寬容!
兩軍對壘,戰機瞬息萬變,容不得指揮官對下達的命令中所用的詞語精雕細刻,以使官兵感覺是否用詞高雅。從上面陳、蔣二人下達的命令中可以分明地看出:前者服務所用的詞語明白如話,任何人一聽就懂;后者服務所用的詞語不夠通俗,一般人難懂費解。戰局的結果最終如何,固然由許多因素決定,但語言服務匡救性的效果怎樣,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語言無階級性,語言服務有政治傾向性
語言無階級性,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語言使用者有政治傾向性,導致語言使用也存在政治傾向性,影響語言服務的匡救性也具有政治傾向性,這也是毋庸置疑的。在階級斗爭異常激烈的社會中,人們從不諱言語言服務匡救性的政治傾向性;在和風細雨的和平社會環境中,語言服務的匡救性既然依舊彰顯,其政治傾向性自然也就會仍以某種形態存在,我們對此也不必諱言。
語言服務匡救性的傾向性,在世界各國都是存在的,當今世界的一些政黨和組織,在對自己的問題進行報道時,所用的詞語多是有選擇性的。例如,香港《東方日報》2006年11月29日所刊文章《華府“欺人之談”泛濫》,說美國農業部11月中旬發表報告,指出2005年美國共有3400多萬人因貧窮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該報告摒棄往常慣用的“饑餓”字眼,改用據稱是更科學的“食物安全程度極低”(very low food security)來形容這種情況。這樣的欺人之談被稱作doublespeak (“曖昧語”)。再如美國民主黨維護墮胎權,從來不說“墮胎”而稱“選擇”(choice),標榜自己是“贊成選擇”(pro-choice),使反對者成為“反對選擇”(anti-choice)的人。美國第51屆第41任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的反恐戰制造了數不勝數的曖昧語,例如以“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來形容軍隊對平民的屠殺,以“另類審問技術”或“身體勸服”(physical persuasion)指嚴刑拷打囚犯,以“自殘行為事件”來描述囚犯的自殺行為。2006年3月,3名囚犯在關塔那摩(Guantánamo)灣的監獄上吊自殺,美國軍方竟形容為“非對稱戰爭行為”。最近的一個例子,海外網2017年12月4日電,據美國《僑報》消息,近日,原斯坦福大學亞裔學生、現皇后學院英語教授朱秀英在網絡雜志Entropy發文,披露自己17年前在斯坦福大學求學時,曾遭該校已故的弗利格爾曼教授(Professor Jay Fliegelman)打壓和性虐待等細節的痛苦經歷。兩周后,朱秀英又在Facebook上張貼一封公開信,質問該校英語系主管及弗利格爾曼教授的助理和同事,當時為何不出面阻止事件的發生。斯坦福大學副總監兼法律總顧問朱瓦特(Debra Zumwalt)在一封信中簡短總結了弗利格爾曼案件的調查結果,并向受害人朱秀英致歉:“我謹代表斯坦福大學,對于你因為教職員的不當行為而遭受的折磨表示遺憾。”朱瓦特的信中稱,弗利格爾曼教授曾“言行失當,有不恰當的身體接觸行為”。對此,朱秀英直言,自己遭受了弗利格爾曼的強奸,但校方的道歉信中并沒有出現“強奸”的字眼,而這么多年來強奸的陰影一直折磨著她。不難看出,從美國總統到美國的高等學府,他們用語言來為社會進行服務時,是有傾向性的。而且這種傾向性,有時甚至應該說是偏袒的、蠻橫的,對另一方毫無人性可言。
在中國,傳統的倫理上有所謂“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是為中國的古訓。“為尊者諱”,更被不少中國人視為美德。這種“隱”,這種“諱”,表現的是人在情與法之間的痛苦抉擇和心理掙扎。能夠“隱”,能夠“諱”的,一般都是“小惡”而不是“大惡”,這樣,“父”和“尊”才有可能被“隱”被“諱”。而一旦是對社會構成重大傷害、對統治構成威脅的“大惡”,無論你是“父”也好,“尊”也罷,中國社會又有所謂“大義滅親”之舉。由此不難看出,在中國,語言服務匡救性的傾向性,是有傳統的,而這個傳統是循著良、善的路徑發展下來,是為社會的和諧性服務的。
其實,不光是在古代中國,我們今天在對自己進行宣傳報道時,有時也會在遣詞用句上費心掂量: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或換以另一說法。這倒不一定是報喜不報憂,更不是文過飾非,而是著意宣傳正面的東西,以予人奮進的力量;把問題談清楚即可,不必刻意渲染己之過,而予對手以攻擊的口實,目的還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當然,這其中也存在著語言服務的技巧性的問題:有的用語機智巧妙,既能把問題講明說透又鋒芒不露;有的用語則顯得呆板笨拙,不但不能說清問題,反倒貽人口實,徒留笑柄。
三、語言服務要達成目的性,不能肆無忌憚,而須有所忌憚
人敬惜字紙,對語言更存敬畏之心,語言“塔布”或將永存。尋常百姓對語言存敬畏之心,對自己與周遭環境和諧相處十分重要;而教育語言使用者對語言心存敬畏,這對執政者來說尤顯重要。語言服務要達成匡救性的目的,語言使用者對語言心存敬畏,心有禁忌,則是必需的。
有個成語“童言無忌”,那說的是童言,未聞成人言而無忌者。成人言而毫無顧忌,那就多少有些問題了。處理人際關系時,人際關系必出問題;談論社會現象時,那就容易妄言妄議。不是說評論什么都是妄言妄議,而是有礙于政權和社會穩定的信口胡說才是妄言妄議。不是善意的批評建言,而是惡意的、有礙于政權和社會穩定的妄言妄議,是很難見容于任何一個政權及其治下的社會的。人民網2017年10月4日訊,據法新社報道,美國媒體披露,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與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一些問題上存在政見分歧,蒂勒森在一個會議上公開指責特朗普“愚蠢”。美國媒體近期普遍猜測蒂勒森有可能要辭職,也就是有可能被炒,據說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媒體報道過他曾批評特朗普“愚蠢”,罵特朗普是“蠢貨”。且不說蒂勒森批評特朗普“愚蠢”,罵特朗普“蠢貨”是否正確,身為下屬若真對總統如此出言不遜,總是不應該的。蒂勒森辭職與否還有待觀察。如果他真的辭職,那么這是否因他口無遮攔,大概也就無須多說了。端起碗來吃肉,撂下筷子罵娘,恐怕是任誰也無法容忍的。
不妄言妄議,不信口雌黃,對于執政團隊的每一個組成人員而言自然至關重要,對于代表執政團隊發聲的新聞發言人來說更是必須遵守的鐵的紀律。新聞發言人當然不是傳聲筒,他們有自己對問題的分析和研判,有他們的所思所想,也有他們感情表達的著重點,是有其一定的發揮余地的。倘非如此,新聞發言人豈不千人一面,毫無個性可言了?那樣的發言,恐怕就真的是呆板傳聲,面目可憎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但是,新聞發言人的個性是在特定范圍內正常發揮時顯現出來的,借用聞一多談舊體詩歌的話來說就是“戴著鐐銬跳舞”,目的還是使他們的發言收取最大限度的良好效果。這也正是新聞發言人的職業操守之所在。
四、語言服務與體察輿情的關系
在當下的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匡救性語言服務尤顯重要。體察輿情,在歷史上和當下都是語言服務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中國上古時代,就已有從流行語觀社會輿情的傳統。如《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在這里,孔子將《詩經》對社會的作用概括為“興、觀、群、怨”,反映出他對詩的社會作用的深刻認識。“興”,孔安國注:“興,引譬連類。”朱熹注:“感發意志。”意為詩是用比興的方法抒發感情,使讀者感情激動,從而影響讀者的意志。“觀”,鄭玄注:“觀風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見得失。”意為詩是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通過詩可了解風俗的盛衰和政治的得失。“群”,孔安國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意為詩可助人溝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礪,加強修為。“怨”,孔安國注:“怨刺上政。”意為詩可批評執政者為政之失,抒發對苛政之怨。古代的史書和筆記類的著作對采風以知民情是有記錄的,例如《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記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后代的著作就記錄了不少反映社會民情的諺語,對執政者是很好的參考。例如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二:“(童貫)進用被寵,繼西邊用兵,又以功進。于是縉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而士論始沸騰矣,至以蔡京為比。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筒:諧音“童”,指童貫;菜:諧音“蔡”,指蔡京。二人是北宋末年權奸,朝野憤恨。上述流行的諺語指除掉童貫、蔡京,天下就太平了。清嘉慶年間,大貪官和珅歸案,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諺語,流行天下。
歷史進入現代,作為社會變化的記錄儀和顯微鏡,流行語更集中反映了社會熱點問題,蘊含著人們對自身生活、社會變革與人類發展的理性思考和追求,在反思中積蓄著時代的正能量。現代一些流行的諺語(尤其是勸誡諷喻性的諺語)的采集也反映出政府對民意的重視態度。一些有失檢點的政要,某些貪官、不法者,有的因為他們自己出語不慎而露出馬腳,最終鋃鐺入獄;有的是百姓據做惡者的惡行編出諺語,司法機關尋蹤覓跡最終將其繩之以法。這些話語,憑網絡等媒體迅即流行開來,成為流行語,例如“唐駿讀博”“恨爹不成剛”“爹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表叔之表,王主任之鞋——都是天價!”“王懷忠當市長,阜陽沒有共產黨;王懷忠做省長,安徽百姓要遭殃”。據報載,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就是把采集民諺作為考察地方干部德行的一個方式的,焦裕祿式的好干部,在人民那里自有口碑,流芳千古;而王懷忠那樣的敗類,千夫所指無病而死,人民的評價也會將其送上審判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