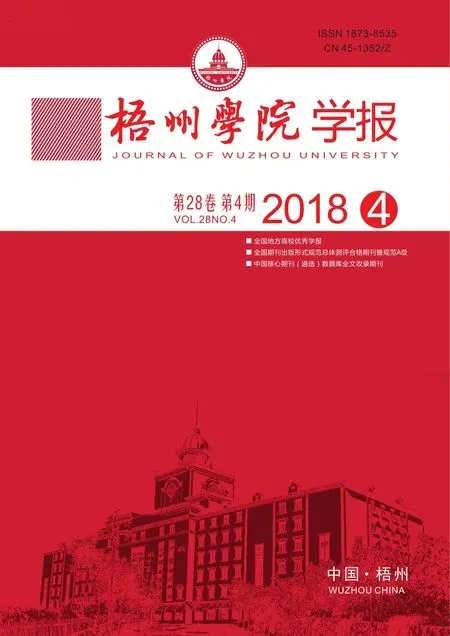論清浙西詞派關于柳永的評價
但白瑾
(廣西大學 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4)
在詞學發展史上,柳永是極具開創意義和創作風格的重要詞人。后世在詞學研究中涉及小令與長調、雅詞與俗詞、豪放與婉約等諸多問題的討論時,柳永便成為必須討論的對象。清初浙西詞派在當時“世之論詞者,惟《草堂》是規”[1]的詞學環境之下興起,以“一洗草堂之陋,而倚聲者知其宗矣”為任,崇尚以清空、騷雅為特質的姜夔、張炎一脈的詞風,與向來被認為俚俗、輕薄的柳詞在風格上截然不同。故從最基本的詞學主張來看,浙派詞人在對柳永及其詞進行評價時,應是以貶損為主,難以相容。
但綜合一些具體詞論來看,浙派“宗主”朱彝尊在論及柳永詞時并非一味貶損;浙派中期和后期盡管否定柳永詞風,但其觀察視角不一,所側重之方面也不同,結合其詞學思想之嬗變來看也頗值得玩味。本文擬以浙派前期、中期、后期對柳永的不同認識為綱,綜合各家之詞選、詞論、作品分析對柳永的認識,以期對此問題得到更清晰的觀照。
現有的研究成果中,較早討論這一問題的論文有陳水云、蘇建新合著的于2002年發表于《武漢大學學報》上的《清初詞壇的“尊柳”與“抑柳”》。該篇有一部分涉及到朱彝尊對柳永的評價,主要就《詞綜》的編選及其中對前人關于柳永評價的擇錄情況進行評述,認為朱彝尊“是以尊雅黜俗的觀點來看待柳詞的”[2]。但其并未結合《詞綜》中所錄具體作品進行討論,也未曾參照其他材料展開說明。此后,由劉漢初先生指導、林佳欣撰寫的臺灣東華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柳永詞評價及其相關詞學問題》,在整個詞學發展史的架構之下討論了柳永詞的接受與傳播問題,以清人之評價為主,兼及前人之詞論,指出了朱彝尊、汪森等《詞綜》編選上對柳永羈旅行役之詞的肯定,但對于浙派其他詞人的相關評論少有結合具體文本進行論述。故此問題仍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
一、浙派前期詞人關于柳永的評價
(一)朱彝尊
作為浙派“宗主”的朱彝尊,對俗詞、艷詞持以明確的貶損態度,故其在《詞綜》編選中,選錄前人對柳永之評語如孫敦立之“多雜以鄙語”、吳虎臣之“虛艷浮華之文”,雖非直接討論,卻也借前人之口表現其對柳永詞作重艷詞部分的不屑。
但也許是因為朱氏更強烈地反對當時以《花間集》《草堂集》為代表的詞風,在具體詞學主張中論及俗詞時,并不以柳永為例,如:
甚矣,詞之當合于雅也。自《草堂》選本行,不善學者流而俗不可醫。(《秋屏鈔題辭》)[3]
且在《群雅集序》和一些具體創作中,可以零星看到對柳永的部分肯定。先看《群雅集序》:
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制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時則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萬俟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奪倫者也。
在這里,朱氏肯定了柳永的審音、創調之功。另外,在其具體詞作中,亦有兩次提及了柳永:
錦瑟新詞鳳閣成,贏得才名,不減詩名。風流異代許誰并,是柳耆卿,是史邦卿。閑悶閑愁讀罷生,吾亦多情,那得無情。問何人解按銀箏,說與君聽,先與吾聽。(《一剪梅·題汪季甪舍人錦瑟詞》)
擅詞場、飛揚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風煙一壑家陽羨,最好竹山鄉里。攜硯幾,坐罨畫溪陰,裊裊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筍烹泉,銀箏侑酒,此外總閑事。空中語,想出空中姝麗,圖來菱角雙髻。樂章琴趣三千調,作者古今能幾?團扇底,也直得尊前,記曲呼娘子。旗亭藥市,聽江北江南,歌塵到處,柳下井華水。(《邁陂塘·題其年填詞圖》[4]
前一首詞將柳永與浙派所推崇的史達祖對舉,“史柳”之并稱,在后期浙派詞論家郭麐處亦出現,此問題有待后文討論。在這里,柳永作為“才名”與“風流”之象征出現。
后一首詞,作為名篇,歷來被評論家所征引為對陳維崧的評語。結尾句用“有井水處,皆倡柳詞”之典,即流露出歆羨之情。陽羨、浙西兩派,雖在理論根柢與創作風格處大相徑庭,但在反對柳永詞艷冶之風這一傾向上是一致的。朱彝尊贈陳維崧的這首詞中自然化用此典,也能看出對柳永之“才名”的肯定。
除了作為重要詞人,朱彝尊在當時亦以儒學著名,他無疑是在傳統道德方面較為注重的知識分子,而在所引的二首詞作當中,其公然贊許甚至歆羨柳永這一在傳統儒家道德體系中評價極低詞人之人格。且詞在朱彝尊那里已經提升到“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的地位,絕非歷來所謂之“艷科”“小道”。
以上引文,可見朱彝尊早期對于柳永其人其詞之包容。
(二)《詞綜》對柳永詞的選錄及與之相關的浙派前期詞人作品
《詞綜》選柳永作品21首,在所選詞人中數量不多。從入選作品與當時所見全部作品的比例來看,則更顯單薄。
所選作品就題材劃分,大致如下:
閨愁怨別:《斗百花》《女冠子》《雨霖鈴》
羈旅苦思:《傾杯樂》《卜算子慢》《少年游》《夜半樂》《玉蝴蝶》《八聲甘州》《安公子》《雪梅香》《婆羅門令》《西平樂》《陽臺路》《近衷情近》、《竹馬子》《玉山枕》
狀景賦形:《望遠行》《二郎神》《河傳》
承平氣象:《木蘭花慢》
從體制來看,只有《少年游》《河傳》兩首是小令,其他都是長調。
從情境來看,這18首詞作中有明確的登高、望遠之情境。
聯系浙派主要詞學主張和朱彝尊的個人生平,可作如此推想:首先,《詞綜》對柳永作品多選長調,少選小令,應是浙派宗南宋詞風的顯現;其次,《詞綜》多選柳永羈旅行役之作,尤其注意選錄其中帶有高遠景物意象的作品,除了這些作品較符合浙西詞派提倡醇雅的觀念之外,或與朱彝尊早年“江湖載酒”的經歷相關,有一種共鳴和同情;第三,《詞綜》已經注意到柳永書寫承平氣象的作品,這與朱彝尊的“歌詠太平”論或相呼應,但沒有選錄聲名更甚的《望海潮》而選取氣勢和格調偏小的《木蘭花慢》,或又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總體來說,除了與浙派主張完全相悖的俗詞以外,柳永詞中的大部分佳作被選錄于《詞綜》。可見,《詞綜》在編選過程中雖然根據浙派之詞學主張有所倚重,但對于與浙西派詞作主張不盡相同的其他佳作亦能欣賞和包容。
從數據上來看,《樂章集》中羈旅行役詞約五十余首,此處即選錄近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艷情詞約百余首,此處則僅選錄3首。亦可見朱彝尊、汪森在編選《詞綜》時存在明顯的重羈旅行役詞、輕艷詞的傾向。
此外,作為“浙西”六家之一的沈皞日其《柘西精舍詞》亦以寫羈旅苦思之情著稱,其部分作品酷肖柳永同樣主題詞作形貌,如名作《百字令·泊銅陵感懷》:
晚舟如鏡,正木蘭,漂泊山城如斗。十五年前游子路,那管羅裙消瘦。未識離情,初辭奩閣,愛醉斜陽酒。而今一夢,千條愁見楊柳。鐵舟消息依然,町花畦草,冷落苔非舊。七里堤沙雙屐健,似此閑心誰又?幾點漁燈,月稀星黑,蘆荻濤聲走。荒雞清柝,淚痕寒進襟袖。
以之對比柳永《夜半樂》:
凍云黯淡天氣,扁舟一葉,乘興離江渚。渡萬壑千巖,越溪深處。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帆高舉。泛畫鹢、翩翩過南浦。望中酒旆閃閃,一簇煙村,數行霜樹。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敗荷零落,衰楊掩映,岸邊兩兩三三,浣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到此因念,繡閣輕拋,浪萍難駐。嘆后約丁寧竟何據。慘離懷,空恨歲晚歸期阻。凝淚眼、杳杳神京路。斷鴻聲遠長天暮。
就詞之題材和主要內容來看,都是寫羈旅漂泊,都有寫孤舟漁火;就詞中的主要意象來看,山巖、酒市、斜陽、遠岸、楊柳、浪濤等意象在兩詞中均出現;就兩詞的藝術表現來看,“幾點漁燈,月稀星黑,蘆荻濤聲走”與“一簇煙村,數行霜樹。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筆似,結尾“荒雞清柝,淚痕寒進襟袖”與“凝淚眼、杳杳神京路。斷鴻聲遠長天暮”境合。即便沈皞日未曾受到柳永的直接影響,但其對與柳永羈旅行役之詞詞風相似的作品是能接受并認許的。
可知,在浙派早期,無論是在詞論、詞選和詞作中,部分詞人對柳永及其部分詞作所代表的美學風格尚能包容,且突出表現在對其羈旅行役之詞的認同上。此期浙派雖已呈現出明顯的“崇雅”意識,然尚能容納不同之詞風。
二、浙派中期詞人關于柳永的評價
(一)厲鶚與“格高韻盛”
相較于浙派前期詞人,浙派中期詞人對于柳永的評價整體不甚寬容。浙派中期詞人較前期詞人有著更明顯的崇南宋詞、輕北宋詞的傾向,這集中表現在其中期領袖厲鶚身上,如其在《半緣詞跋》中認為:長短句權輿于唐,盛于北宋,至南渡極工[5]。
從其為專收南宋詞的《絕妙好詞》作箋,也可從其側面看出其審美傾向。而在其著名的《論詞絕句十二首》中,則對柳詞提出直接批評:
張柳詞名枉并驅,格高韻勝屬西吳。
可人風絮墜無影,低唱淺斟能道無?
“格高韻勝”之說最早見于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中對《樂章集》的總評:“其詞格固不高,而音律協婉,語意妥帖,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于羈旅行役。若其人則不足道也。”[6]
這里的“詞格固不高”,聯系后文“若其人則不足道也”,顯然是針對柳永俗詞進行評價。厲鶚在此征引此句,固然有否定柳永俗詞的用意。聯系他在其他方面的詞論,則看得更加明了:“詞之為體,委曲啴緩,非緯之以雅,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也。”
顯然,柳永之詞境不符合其對“委曲啴緩”之詞境的追求,而張先“柳徑無人,墮風絮無影”則更符合厲鶚所推崇的“清空”之格[7]。所謂“格高韻勝屬西吳”,則是以張先神思興會之筆否定柳永風格之“淺斟低唱”,前者去白石、玉田之格近,后者去白石、玉田之格遠。浙西一派的“崇雅”詞學主張,在厲鶚這里有明顯強化且固化之趨勢。
(二)王昶與“褻狎”“俳優”
浙派中期詞人中另一對柳永有直接評價的是王昶,即:
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后多出于狎褻,是豈長短句之正體哉?余弱冠后,與海內詞人游,始為倚聲之學,以南宋為宗,相與上下其議論。(《國朝詞綜續編自序》)[8]
詞,三百篇之遺也,然風雅正變,王者之跡,作者多名卿士大夫,莊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彥輩不免雜于俳優。(《姚茝汀詞雅序》)
“褻狎”“俳優”,都是針對柳永艷詞發難,從而在詞格上否認其創作。厲鶚與王昶,一正一反,一借貶抑柳永提出了自己理想的詞作標準,一借批駁柳永反證其所摒棄之詞風。
若結合對柳永外的其他北宋之評價來看,不難得知,時代稍后的王昶較諸厲鶚呈現出更明顯的尊南宋而抑北宋傾向,厲鶚尚能欣賞北宋之周邦彥,即:
兩宋詞派,推吾鄉周清真,婉約隱秀,律呂協調,為倚聲家圭臬。
而王昶對周邦彥,則簡單將其與柳永并斥之為“雜于俳優”。無論是對柳永還是對周邦彥的評價,均反映了在浙派中期詞人對姜、張以外的詞風愈發不能包容,而詞學眼界也愈發狹窄的現實。后來謝章鋌在《賭棋山莊詞話》中對此現象有較客觀的分析和較合理的辯證:
予嘗謂南宋詞家,于水軟山溫之地,為云癡月倦之詞,如幽芳孤笑,如哀鳥長吟,徘徊隱約,洵足感人。然情近而不超,聲咽而不起,較之前人,亦微異矣。不獨東坡之《百字令》、《水調歌頭》無其興致,即柳耆卿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秦少游之“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出語高爽。惟白石尚有此意,余則皆不逮也。有花柳而無松柏,有山水而無邊塞,有笙笛而無鐘鼓,斤斤株守,是亦祇得其一偏矣。辛、劉之派,安可廢哉?
此論足以平數百年南北宋詞高下之爭,然若非對浙派中期詞人于他種詞作風格不包容之極有感而發,無以有此論。對柳詞“出語高爽”之肯定,即與朱彝尊、汪森在《詞綜》中選錄大量含高遠景物意象的柳詞羈旅行役之作遙相呼應。
三、浙派后期詞人關于柳永的評價
(一)吳錫麒
吳錫麒之詞論多見于序跋中,似陳維崧,多駢語,故虛筆鋪陳有余,實際立論較少。但也可零星見其之于柳永的評價,如“蓋其具體于周、柳,稟態于姜、張,以是首涂,得成超詣。”
從這里可以看到,雖然他仍是尊姜、張,但已全然不同于王昶對柳永所代表的詞風進行強烈貶斥,而是看到柳永在詞學發展中的階段性地位,甚至認為其為形成浙派推崇的姜、張一脈詞風的一個階段。
從整體詞學觀來看,其主張與浙派中期相比,已發生較大變動,故包容柳永詞在內的多種詞風已成為可能,其重要詞論《董琴南楚香館詞鈔序》言:
詞之派有二:一則幽微要眇之音,宛轉纏綿之致。戛虛響于弦外,標雋旨于味先。姜、史其淵源也,本朝竹垞繼之,至吾杭樊榭而道其盛。一則慷慨激昂之氣,縱橫跌宕之才。抗秋風以奏懷,代古人而貢憤。蘇、辛其圭臬也,本朝迦陵振之,至吾友瘦銅而其格尊……事固有因時酌宜,應物制巧者。豈得謂姜、史之清新為是,蘇、辛之橫逸為非,而必欲盡東其畝哉?
這里承認了蘇辛之“慷慨激昂之氣,縱橫跌宕之才”與姜史之“幽微要眇之音,宛轉纏綿之致”堪與并稱,與厲鶚之“非緯之以雅,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也”和王昶之“作者多名卿士大夫,莊人正士”已是完全不同的主張。故包容大體上仍屬“宛轉纏綿之致”的柳詞風格,也不在話下。
(二)郭麐
郭麐是浙西詞人中少數留下專門詞話著作的詞人,亦是在浙西詞人現存詞論中談及柳永次數較多的,在其《靈芬館詞話》第一則便談到:
詞之為體,大略有四。風流華美,渾然天成,如美人臨妝,卻扇一顧,花間諸人是也。施粉傅朱,學步習容,如宮女題紅,含情幽艷,秦、周、賀、晁諸人是也。柳七則靡曼近俗矣。姜張諸子,一洗華靡,獨標清綺,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盤,入其境者,宜有仙靈,聞其聲者,人人自遠。夢窗、竹屋,或揚或沿,皆有新雋,詞之能事備矣。至東坡以橫絕一代之才,凌厲一世之氣,間作倚聲,意若不屑,雄詞高唱,別為一宗。辛、劉則粗豪太甚矣。其余幺弦孤韻,時亦可喜。溯其派別,不出四者。
此處較吳錫麒“詞之派有二”更進一步分出“詞之為體,大略有四”,但整體上沒有擺脫對姜、張明顯的推尊傾向。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特地將東坡詞從辛、劉分出,且并未正面予以否定。
郭麐評柳永詞的“靡曼近俗”,雖仍是否定,但也與王昶所謂之“褻狎”“俳優”相別。“靡曼近俗”是屬于“風流華美,渾然天成”的花間一脈的,郭麐并不全盤否認花間詞風,只是認為柳永在這樣的背景下未能掌握好“靡曼”的“度”而近俗。而此處對“花間諸人”進行較高評價,已初現之后常州詞派論詞之端倪。
而在此則詞話后文中,其又言:
本朝詞人,以竹垞為至,一廢草堂之陋,首闡白石之風。詞綜一書,鑒別精審,殆無遺憾。其所自為,則才力既富,采則又精,佐以積學,運以靈思,直欲平視花間,奴隸周、柳。姜、張諸子,神韻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語之渾成,非其比也。
在其他詞論中,則言:
詞家者流,其源出于《國風》,其本沿于齊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兒女之情不能道也。宋立樂府,用于慶賞飲宴,于是周、秦以綺靡為宗,史、柳以華縟相尚,而體一變。蘇、辛以高世之才,橫絕一時,而奮末廣憤怒之音作。姜張祖騷人之遺,盡洗秾艷,而清空婉約之旨深。自是以后,雖有作者,欲離去別見,其道無由。(《無聲詩館詞序》)
前則云“平視花間,奴隸周、柳”,后則又云“周、秦以綺靡為宗,史柳以華縟相尚”。不論周、秦,還是史、柳;不論“綺靡”“華縟”,還是“靡曼近俗”,都是在繼續強調柳永詞與“花間諸人”相近的美學風格。且以“史柳”并稱,實際上也打破了南北宋詞風之成見,而更趨以詞人具體風格作為歸類標準。柳詞重新回歸為如明末清初云間、陽羨等詞派所論一般,作為婉媚詞風之代表。
綜之,在浙派后期詞人的評價中,柳永更多被視為婉約詞風代表作家之一,甚至是由花間詞風發展至姜、張詞風的一個過程。于其貶抑較浙派中期詞人稍輕,但仍是在尊姜、張一路的背景下被認識。
基于以上討論,大致可以看到浙派詞人關于柳永認識的脈絡。在浙派形成初期,其對詞的評判標準尚未固化,故對包含柳永在內的其他詞風尚能包容。及至浙派中期,其詞學主張已極為鮮明,評判標準已相對固定,故對以柳永為代表的俚俗詞風尤難兼容。再到浙派后期,其詞派內部已意識到長期局限于某種單一風格和標準的弊端,試圖從其他方面尋求出路,但一時仍無法擺脫長期以來崇姜、張之詞學環境所造成的成見。
自北宋以來,對柳永之評價,若為褒揚,則多談其羈旅行役之詞;若是貶抑,則多言其俗情艷冶之作。在婉約詞風之發展、樂譜聲律之創制方面,柳永未必沒有作出過無可替代的貢獻,只是,婉約之風為詞之主流,名家輩出;周邦彥、姜夔對樂譜聲律之創作更勝柳永。故即便在這些方面對其有所肯定,也依然只是能將其泛泛歸入“周、秦、史、柳”,且其在此類詞中表達直露、語言淺俗的作品往往容易受到攻擊。
故真正能代表柳永在詞學方面獨特貢獻的,真正能被后世詞學家普遍承認的,乃是其融入高遠景物意象的羈旅行役之作。即便是將其譏為“屯田輕薄子”的王國維,對其《八聲甘州》,也不得不評之以“佇興之作,格調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9]。浙派初期,朱彝尊、汪森在編選《詞綜》時尚能注意到柳永詞的這類風格,但在中期和后期,即便是在后期論詞相對多元而力求新變的情況下,柳永詞的這類風格依然被忽視。
結合后世詞論家對浙派“雖不纖靡,亦且浮淺;雖不叫囂,亦且薄弱”的評價來看,如果浙派能從柳永融悲歡離合之致于高遠景物意象中的羈旅行役之詞中尋找到自家詞風之蔽的突破口,或許不失為“拯亂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