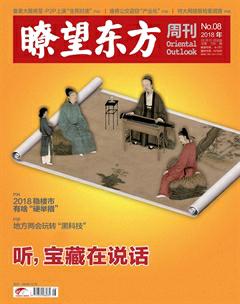蟲蟲入碗來
張燕

在科幻題材的影視作品或者小說游戲里,蟲族是經常能見到的角色,以數量取勝的蟲海戰術往往是對手的噩夢。
而在現實生活中,昆蟲的數量確實不少,從常見的影響生活的蒼蠅蚊子,到鋪天蓋地的蝗災,都彰顯出這類生物的顯著特色。
與此同時,也正是由于數量多,昆蟲也成了潛在的人類食物來源。
糧食和飼料短缺的解決方案
雖然在不少外國人看來,中國人的食譜范圍寬廣得驚人,但“四條腿的除了板凳,長翅膀的除了飛機,其他啥都吃”的人畢竟是少數,被奉為美味的炸蠶蛹和燒螞蚱只是小眾人群的“心頭好”。即使在昆蟲種類最豐富的某些地區,也不是人人都有勇氣將肥肥胖胖的竹蟲放到嘴里,大多數人對吃蟲子還是有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
不過為解決至今仍存在的大面積饑饉問題,只要咬牙閉眼不挑食,昆蟲確是一個不錯的食品來源。隨著世界人口快速增長,人們對肉類和魚類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長,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目前的飲食方式是不可持續的,聯合國就鼓勵世人多吃昆蟲作為補充。
昆蟲有很多優點,味美、營養豐富、大規模養殖成本低、污染少,還可以緩解饑荒危機。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昆蟲的地位被提升到餐桌美味和抗饑荒、減污染的高度。
這份報告估計,到2020年,全球對動物飼料的需求會增長70%。用大豆和魚類制成的高蛋白飼料價格已經飆升,而畜牧業排放的溫室氣體也已經超過飛機、汽車和其他交通運輸工具的總和。因此,昆蟲可以成為一種解決方案——它們的蛋白質、脂肪、礦物質和維生素含量都很高。
雖然人們經常被各種昆蟲騷擾,恨不得一下子將害蟲都消滅干凈。但作為食物的話,蟲子卻是怎么都不嫌多的。2013年發布的一項研究發現,如果要獲得相同數量的肉,昆蟲的飼養效率分別達到雞、豬和牛的2倍、4倍和12倍。
好在和其他事物相比,絕大多數可吃的昆蟲較容易采集。在解決全球糧食和飼料短缺問題的諸多方案中,發展昆蟲養殖業是其中之一,比如,可以使用過期食品或農業肥料喂養昆蟲,它們需要的水很少,產生的溫室氣體也遠低于傳統畜牧業。
有人暫時不想成為食蟲者,但也同樣支持建立昆蟲農場。他們認為昆蟲可以在人類的飲食中扮演重要角色,只不過應該在食物鏈上更上一層,把它們做成牲畜的飼料。大規模養殖昆蟲為飼料加工提供原料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世界不同地區已經有一些成熟的企業在從事這項業務。美國、加拿大、法國、荷蘭和南非都在建設更大的昆蟲農場,為傳統的牲畜提供高蛋白飼料。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報告,目前有超過1900種昆蟲被人類當做食物來源,全世界至少有20億人曾經吃過昆蟲,這意味著不到4個人里就有一個人吃過蟲子。
哪些昆蟲好吃
吃什么是一個日積月累的習慣問題。和昆蟲形似的蝦和螃蟹已經明目張膽地占領了人們的餐桌。
按照人們接受蝦蟹的路徑,要讓大家普遍接受吃蟲子,就要有些“拳頭產品”,讓人們知道蟲子味道還不錯。昆蟲到處都是,且“出肉率”高,絕大部分的昆蟲都是100%可吃的,而一頭牛可吃的身體部分只有四成。
在有記載的可食用昆蟲種類中,甲殼蟲算是主力之一,占了四成,蟋蟀也是人們吃得較多的一種。蟋蟀和肉牛,產出同等數量的蛋白質,蟋蟀需要的飼料比肉牛少得多。從環境角度看,蟋蟀等昆蟲糞便的溫室氣體排放比豬羊雞鴨等傳統家畜家禽低得多,一公斤蟋蟀制造的溫室氣體只有養育一公斤豬肉所產生溫室氣體的10%。
熱帶地區的人吃昆蟲相對更多,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昆蟲長得更快,在氣溫較低的溫帶地區,昆蟲數量較少,因此不值得專門捕捉。
不同地區的食蟲者的口味也有差異,除蟋蟀外,有些地方的人偏好黃蜂和甲殼蟲。黃蜂的幼蟲生吃像是味道很濃的凝塊奶油,煮熟了配上姜、醬油和米醋的話,味道像甜甜的牡蠣。
泰國人喜歡吃油炸螞蚱,墨西哥人將螞蚱拌著辣椒和青檸一起吃,澳大利亞原住民則喜歡吃木蠹蛾幼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盛產白蟻,而那里不少國家的人都將這種唾手可得的白蟻做零食。白蟻很快就會賣光,人們把白蟻煮了,然后用鹽炒一下,吃起來像是切成小塊的脆火腿。
在南非,毛毛蟲屬于高檔奢侈食品,價格不菲。雨季的時候有人凌晨兩點就起來,采集最多汁的毛毛蟲,有的被慢燉當主食,有的被快炒當零食,它們吃起來像有肉味的蔬菜。
實際上,如果按照營養成分來衡量的話,多花點錢吃毛毛蟲看上去也是物有所值。按照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研究人員的測算,每100克毛毛蟲的蛋白質含量要略高于牛肉末,鐵含量則是牛肉的10倍。此外螳螂和甲蟲中還富含牛肉里沒有的鈣。
昆蟲菜單
在電視真人秀《荒野求生》里,經常見到被譽為“食物鏈最頂端的男人”的貝爺把一只只昆蟲放進嘴里,并津津有味地稱贊“嘎嘣脆,雞肉味”。
對大多數人來說,即使能成功克服心理障礙成為“食蟲者”,也未必喜歡貝爺式的“生吞昆蟲”,精心烹制后的昆蟲會讓人們感覺好得多。
聯合國糧農組織建議餐館把昆蟲寫入菜單,廚師們把昆蟲納入食譜設計,由此提升昆蟲的地位。
喜歡吃昆蟲的英國普利茅斯大學副研究員彼得·史密瑟斯說:“如果你以一種講述見聞的有趣方式告訴人們,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吃昆蟲,相信多數人都愿意嘗試一下。”
丹麥大廚瑞尼·雷澤皮多年以來一直在他位于哥本哈根的諾瑪餐廳里宣傳吃蟲子的好處,而倫敦的阿奇皮拉格餐廳也提供幾道用蟲子制作的菜肴,例如黃粉蟲鷹嘴豆泥、墨西哥蟲卷和辣椒拌蟋蟀等。
開張于2015年11月的全球餐廳是英國第一家在多數菜肴中都加入了昆蟲的餐廳,那里的招牌菜是用黃粉蟲、蟋蟀和蚱蜢制作的漢堡,還配上了玉米片和上面撒了許多螞蟻的蒜蓉蛋黃醬。食客們說它看起來就像蔬菜漢堡,但味道和口感更好。
大廚們挖空心思,想出通過慢烤等不同的烹飪方法提供不同口味的昆蟲菜式。在歐美新開的昆蟲餐廳面臨的挑戰,不是讓人們嘗試去吃昆蟲,而是讓那些抱著獵奇心理嘗過鮮的食客成為回頭客。就這點來講,不斷開發新的昆蟲菜單和推出新的口味才能構成持久的吸引力。
或許大廚們可以環球尋找靈感,因為除創新的菜譜外,在很多國家的傳統菜和小吃中也有昆蟲食譜的存在。
比如,墨西哥就有著名的龍舌蘭酒泡幼蟲,酒瓶子里泡著的蟲子種類很多,都是墨西哥一些地方很受歡迎的食物。其中呈紅色的蟲子最受歡迎,吃起來有一種很特別的煙熏味道,很有些梅斯卡爾酒的滋味。
在墨西哥,農民們在麥田和紫花苜蓿地里用大桶抓一種美味的蚱蜢,當地人把它們稱為查普林。這是一種吃起來口感很好,有檸檬味道的蚱蜢。
在剛果,白白胖胖的蛆蟲很受歡迎,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們帶著斧頭去砍開棕櫚樹,尋找樹里面的蟲子。這些蛆蟲用葉子包起來放在火上燒烤,吃起來就像一小包油油的肉醬。
比起這些原汁原味的烹調方式來,看不出原本樣子的更容易讓人接受。比如把磨成粉的蟲子加入面包、通心粉和蛋白奶昔中。這些食品有助于吸引“入門版”的食蟲者,至于那些“生猛昆蟲”,還是先讓“進階版”的食蟲者去享受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