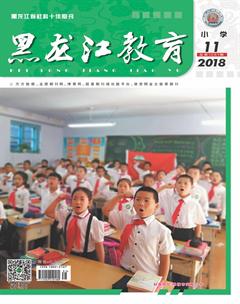閱讀本無關應試
張凌辰
現在的家長對語文越來越重視了,不但舍得為孩子購買各種課外書籍,而且還積極鼓勵孩子參加各種語文活動。這種現象在我從教二十幾年的經歷中,是前所未有的。作為一名語文老師,我感到很欣慰,但同時又有一些憂慮。因為在和很多學生及他們的家長交流之后我發現,大家對語文日益高漲的熱情并非都是來自于對這門學科本身的熱愛,而是因為幾年來的高考改革——語文試題的難度和占總成績的比重都在增加。然而,本著這種目的的“重視”能持續嗎?投入了那么多時間、精力、財力,能達到預期效果嗎?作為本次“閱讀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我很想將視角再拓寬一點,從語文學科,從兒童成長的角度,再說說“閱讀”。
一、先說說語文
最近流行一句話:得語文者得天下。聽起來很豪邁,但能不能“得”恐怕另當別論。
想要“得語文”就該先弄清楚“語文”是什么。語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語文學科知識的體系性不強,字、詞、句、段,修辭、結構、思想、情感,記敘、說明、議論、文言……互有交叉又各自獨立,大多呈散點式分布,想通盤掌握很難。語文學習好比“聚沙成塔”,聚沙耗時,成塔不易——每一座“塔”成,都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沒有捷徑。不僅如此,每一座“塔”還樣式各異,“成塔”的過程也不盡相同,很難有規律可循。
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小學語文是從識字開始的,學生很快就會認識“小船、月亮、彎、像、的”這些字,但是不是認識了這幾個字,就可以告訴他們“彎彎的月亮像小船”是比喻了呢?實踐告訴我們是不行的。因為他們聽不懂。那要在學生認識多少字之后,才能講比喻呢?也沒有固定的標準。而又該在何時教會學生理解這樣的比喻是為了生動形象地說明月亮的樣子,更是沒有具體的時間節點了。這些都要靠教師本人去把握,結果也自然差異很大。你看,這種情況是不是讓教者和學者心里很沒底?關鍵是這些問題不在合適的時段講清楚,就勢必影響到學生之后的能力發展,包括閱讀能力。
二、再談談閱讀
如果說真的是“得語文者得天下”,那么恐怕就要說“得閱讀者得語文”了。因為閱讀是所有語文題目中最容易丟分,又最不容易明白為什么丟分的題。很多學生都會在考完試后自責閱讀答得不好,很多家長也常常會埋怨孩子閱讀總錯。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問題該怎么解決。下面我就從“語文考試中為什么要有閱讀題,閱讀題是怎樣命題與評價的,什么樣的學生才能駕輕就熟地解決閱讀問題”三個方面談談我的意見。
首先,閱讀題在語文考試中是用來區分學生語文水平的,所以閱讀題必須要有一定的難度。學生可以在語文基礎知識問題中盡量得滿分,可以在作文中保證與他人分差不會太大,但在閱讀題上很可能失很多分。而這,正是此類題型存在的價值。否則,語文考試的效度就很難把握了。因此,大多數學生在閱讀題上丟分都屬于正常現象。
其次,閱讀看似一道題,其實卻包含著很多類型各異的小題。小學的閱讀題中除了純閱讀問題以外,還有一定比例的字詞句等基礎知識問題。中學考試中一般都是純粹的閱讀題,但也要從信息提取,直接推論,詮釋整合,欣賞評價等不同的方面對學生進行考察。
不僅如此,閱讀的命題和評價還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閱讀的篇目是出題人在浩如煙海的文章中挑選的,同一篇文章能夠命制的題目千變萬化,而同一題目的答題方法很可能又各不相同。因此,我們在評分標準上常常可以看到“言之成理即可”的字樣。可是,誰有權判斷其“言”是否“成理”呢?當然又是批卷老師了。雖然命題和評卷的老師也必須保持和公眾一致的標準評判,但是如果學生只愿按自己的好惡思維,而不能從他人的、出題者的、公眾的……這些角度去思考的話,他們也是無法寫出恰切的答案。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語文考試中的閱讀并不單單是在考知識,更是在考察學生的思維。所以,只有思維水平高的學生才能駕輕就熟地解決各種閱讀問題,才能在語文考試中獲得高分。
三、閱讀與人的成長
語文學科知識體系為塔型結構,而閱讀居于高層。所以,達到閱讀的高度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個是堅實廣博的基礎——字、詞、句等相關知識;另一個就是清晰明確的路徑——思維。基礎知識通過持之以恒,一絲不茍地訓練可以掌握。但思維的培養僅僅靠本文開篇寫到的那種一擁而上的重視就不行了。語文教師都明白,要教會學生認字、組詞、造句子容易,要教會他們思維方法卻很難。
很多時候,待解決的問題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培養思維的重要方法之一恰恰就是閱讀。因為閱讀伴隨著想像,伴隨鑒賞和評論,伴隨回憶,所以閱讀與思維密不可分。只不過,如果我們想通過閱讀來訓練學生的思維,就不能只看閱讀試題這一狹窄的范疇,也不能僅僅選擇讓學生讀課外書這種簡單的方式。
古人講:“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隅;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此言對通過閱讀培養思維同樣適用。當我們從讓學生更好地學會生活并且終身收益的角度去指導閱讀,培養思維的時候,就不難發現:思維的培養不僅是破解閱讀難題、提高語文水平的重中之重,其意義更遠遠超越了語文和閱讀的范圍,足以影響人的一生。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閱讀不僅是一種單純的學習能力,而是一種人生存的重要能力,它持續地作用于每一個人的整個生命周期。嬰幼兒在沒有進入正式的教學情境之前,就早已開始學習閱讀了:他們會一邊翻著連環畫,一邊或歡喜或悲傷;他們會看著菜單點出自己喜歡的快餐食品;他們會循著指示牌找到要去的地方。其實,那就是在讀圖了,他們的小腦袋瓜中的思維就在發展了。后來,他們到學校學習,能夠讀好多書,學很多知識,思維能力也在提升。再后來,他們走出學校,步入社會。有的人會越來越有智慧,越來越善于解決問題,這些人思維的發展就是無止境的,他們的人生也會越來越成功,越來越幸福。當然還有一些人,他們的思維發展漸緩甚至停滯了,因為他們沒有通過學校教育學會閱讀的思維——系統的學校教育終會結束,只有閱讀才能提供無盡的成長空間。
因此,好的教育者一定是一方面努力為學生提供閱讀的機會,不急于干涉,更不會將自己的理解強加給他們,他們會為學生留足想象的空間和思考的時間,等待學生一點一點讀懂周遭的各種信息,為閱讀更深奧的內容做好準備。另一方面,他們也會盡量向學生傳遞正確的思維方向和方式。他們會明確地表態:要想讀懂文學作品,必須要有自己的觀點。但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評判一定是片面的,還要揣測作者的、同時代的、當下社會主流的……各類人的想法,這才是完整的思維。同時,他們還會適當地傳授具體分折理解的方法。對一段文字的感受從哪里來?是“想當然”嗎?不是,應該找到明確的依據。這些依據就是文本中的字詞、修辭方法、寫作手法,對這些內容加以闡釋,就為自己的理解找到了支撐。
例如:曹敬莊先生在《索溪峪的野》一文中,曾經寫到了這樣一句話:“(索溪峪)這種美,是一種隨心所欲、不拘一格的美。” 若問學生作者這么寫的目的是什么,很多同學都會說,要表達作者對索溪峪的喜愛之情。但是這樣說太籠統了,如果能具體解釋一下才更有說服力。所以比較好的解釋是:作者把索溪峪的美寫成了一種想怎么樣就怎么樣、不局限于一種規格或格局的美。還用到了擬人修辭方法,把“美”看做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說明這種美十分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表達了作者對這種美的贊賞和喜愛。
學生能夠這樣完整地解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是一種短時間內就能具備的能力。但他們一旦學會了這種條分縷析面面俱到的思維方式,就會深深地刻在頭腦中,并且可以將其運用到閱讀以外的很多地方,他們也就走向成熟了。這恰恰是通過閱讀培養思維的最重要的意義,已然超越了閱讀本身
造物有情,賦予人類好學的天性;兒童純真,對閱讀有與生俱來的熱愛。希望作為師長的我們都能懂他們,護他們,助他們,教他們。讓他們在最該閱讀的年齡多讀書,在最需要引領的時候告訴他們該怎樣讀。那樣,他們就一定會成為語文學習中的佼佼者,也一定能成為人生的成功者。
最后,寫一首小詩送給那些愛讀書的學生:
閱讀本無關應試,善讀應試又何妨。博覽群書蘊錦繡,文采何處不飛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