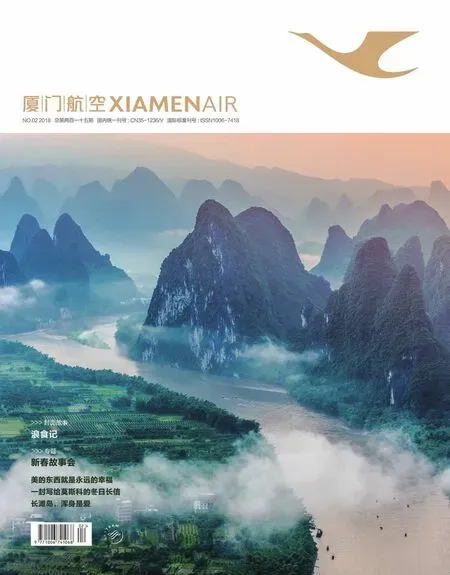『忙而喪』的一年,我依舊愛它
社會時事作家 陳方
每年的生日一過完,馬上就是新年。原本計劃2017年的生日要“隆重”一番,畢竟是40歲的生日。都說四十不惑,40歲,這是人生的分水嶺了吧。步入40,中年人的人生要真真實實開始了。這一年,看看媒 體上呈現了多少“中年危機”“中年 焦慮”的話題?保溫杯、禿頂,肥胖, 成了中年人的標配,有這些“標配” 引發出的中年危機的話題還沒徹底沉 寂下來,臨近年底,42歲的中興通 訊程序員歐建新又進入輿論暴風眼, 當他決絕地從高樓上縱身一躍,再次把 “中年危機”呈現在世人面前。帶著一 種惶恐的心情步入40歲生日。生日那天,反而平靜到連生日蛋糕也沒興趣吃。突然覺得這也是很平常的一天,感懷、念舊、回憶、期待,這些情緒性的東西都是懸浮在空中的,中年是最不討喜的年紀,你表達出來的情緒都是他人的話題,而你生活中遭遇的種種,除了自己沒人能幫你解決。

留守
這一年里自己的工作愈發讓人感覺到“喪”。身為傳統紙媒人,行業的沒落很難讓自己再感受到職業的尊榮。工作儼然只是工作,甚至連“養家糊口”的工具都算不上了,讀者流失、廣告下滑、收入大幅度下降,未來不可期,這個職業已經讓你找不到任何歸宿感。認真想一想,越來越喪。
偶爾,還有命運輪回的感覺。有一天和身為領導的同事聊天,我感慨,“沒想到自己又在輪回父母那一代的命運,身為工人,我的父母就是在我這個年紀下崗的。我原以為自己‘階層翻身’了呢,沒想到,到了父母當年的那個年紀,又面臨和父母一樣的局面。”領導苦笑,默不作答。聊天就在沉默中結束。這一年,我身邊的很多人都在堅守,堅守紙媒最后的尊嚴。說堅守是“褒獎”,說“留守”更合適吧?能走的都走了,創業,或者選擇其他行業,毫不猶豫地轉身,過去經歷的一切統統放下。很多人沒走,大家很少談論未來,或許是感覺這份工作的未來實在渺茫。前面是懸崖還是泥沼,沒人說得清。
看不清的路也要蹚一蹚。某種程度上說,“蹚路”與“念舊”是聯系在一起的,“你無法預知未來的點滴,只能在回顧過往時串起過去的蛛絲馬跡,所以你要相信,在未來,你所經歷的點點滴滴都會以某種形式串聯起來。”對過去一年的總結、對過去一年的評價基調,其實也意味著你怎樣打算接下來的一年。
已近中年的人們,似乎更喜歡用“不過如此”“不好不壞”來概括你經歷過的每一天。積極地說,這是一種放下的豁達;消極地說,卻是一種含混的湊合。
比較慶幸的是,我不喜歡湊合。與湊合相比,我寧愿“焦慮”。湊合其實是一種更可怕的狀態:焦慮,至少證明你還對未來有所期許,你對生活的感知還未曾麻木;而湊合,則是出于一種“半接受”的狀態,它就像鞋里的沙,你能感覺到不適但又不至于刺痛,就這么將就著繼續,遑論去感知生活的質感?
出路
一位朋友說,行業的沒落,并非是個人不努力所致,努力的人永遠都有出路。我還是相信改變的力量。工作已然找不到歸宿,何不自己“找點兒事做”。這一年里,自己的“副業”反而風生水起。工作之余,我和同事搭建了一個“少年寫作平臺”。
必須承認,人都是功利的,潛意識里都想選擇對自己好的那個選擇。但是,什么是最好的選擇,沒有人能告訴我們,只能靠自己邊走邊看。現在回想起來做這個少年寫作平臺的初心,三五同道,并沒有打算在應試教育的框架內有所作為——不過是看不得孩子們為干巴無趣的作文題絞盡腦汁,家長苦,老師累。干脆攘臂而起,及鋒一試。畢竟,于文字中浸淫二十余年,把參差多態的觀察和具體而微的發現形之于筆,也算我們媒體人的一技之長了。當然,這只是其一。還有一個難以啟口的原因,人近中年,總覺得應該做些什么來對抗所謂的“中年危機”。這種危機是一種“心理病”,或者說也是一種“職業病后遺癥”。浸淫媒體十多年,習慣了刷存在感,而這種存在感是通過他人的反響與回饋刷出來的,它必須帶有社會價值的屬性。于是,幾個志同道合的媒體人在業余時間創設了這個“少年寫作平臺”,我們一致認為,如果能讓孩子從小養成真實而獨立的表達習慣,在他們的成長道路上以致成年后不去說、不去寫那些“假大空”的套話,善莫大焉。
一份似乎拿不出手的“副業”,一下子找到了使命感。身為一個生性散漫的人,很多時候都不忍心看著孩子們從一個輔導班出來匆匆趕到下一個輔導班,他們現階段的“下一站”似乎永遠是輔導班。我們也時刻在自省,千萬別把這個副業辦成“輔導班”:它應該是開闊而非封閉的,在一個空間有限的物理場域內,我們聊天,討論,暢談一切有可能的未來,最后的寫作只是我們梳理自身經歷的一種表達,而非負擔。
短短一年時間,這份副業竟然生根發芽,在我生活的這座城市打開了知名度。從沒有過分宣傳,口碑卻已傳播開來。行動與改變,成了我應對“中年危機”“中年焦慮”的武器。所以我確信,改變,未來還有機會,還有成長的可能;固守,則一切皆無可能。我們不確定改變到底能帶來什么,但任何人生都會有結果,這是我們在一切不確定之中所能得到的確切保證。今天你所有為改變付出的努力,未來終得回響。
沒錯,是習慣“湊合”還是去改變現狀,一切取決于你自己。未來是什么樣的結果,完全取決于你當下的行動。你與時間進行著怎樣的交易,未來都會給你答案。
未來
每一個人近中年的人,都不再強求人生“逆襲”了吧?某一天在悟空問答上看到一個問題,“70后們如今都過得如何?”潛意識里,我也拿這個問題拷問自己。
可以說,70后是相對比較幸運的一代。沒有經歷過動蕩的歲月,接受了正規良好的教育,上升的通道比較順暢。考大學時,分數說了算;工作時,還不用拼爹;買房時,房價不太高。大多數人,只要有能力,都過得不算差。反倒是人到中年了,開始焦慮——因為中年危機,因為孩子的教育,因為以后的養老……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性,不是在年輕之時,而是在中年以后,日漸明顯。
此時,已經缺少年少的沖勁,沒有了年齡的優勢,人生的節奏開始趨于平緩,但世界卻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在改變,過了不惑之年的70后,如果不能知“天命”,怕是很難真的“不惑”了。
這一年里,和很多年紀相仿的朋友聊天,就像新聞里呈現的一樣,焦慮和壓力,是他們首要面對的問題。尤其是中產階級,很多都是吃了很多苦爬上來的,社會地位不穩定,很可能因為一次變故,就又變成貧困階層了,所以為了維持中產階級的生活,他們一刻也不敢懈怠。特別是在成家立業之后,由于自己吃苦的經歷,就努力想給孩子創造好條件,讓孩子少吃苦,只能更加努力,以至于越來越焦慮。
這一年里,很多個夜晚,在“忙與喪”的情緒中度過。“留守”在一個無法改變的行業里,自己尋求“出路”,多多少少安撫了自己的焦慮,但依舊會惶恐。同樣是因為“未來不可期”。可是未來這個東西,到底能有多少人把握住呢?如果真能把握預知,那還叫“未來”嗎?
盧梭在《愛彌兒》里說過:“所有痛苦的感覺都與擺脫痛苦的愿望密不可分,所有快樂的觀念都是與享受快樂的愿望分不開。所以,所有愿望全都意味著一種需求,而所有的需求都是痛苦的。因此,我們的痛苦正是產生于我們的愿望和能力的不相稱。一個有感覺的人,在他的能力擴大到了他的欲望的時候,就將變作一個完完全全快樂的人了。”
我能意識到自己的生活中有焦慮的成分在,好在,我算是一個有行動力的知道該如何緩解焦慮的人。面對真實得很不可愛的中年生活,不得不承認,真正考驗的是置身其中的每個人的心態。心態,甚至比你的能力更重要。比如,年末歲初這個時間的埡口上,我會盤點一下這一年我完成了多少事,而不是僅僅糾結還有多少事沒有做成。未來還長,很多愿望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