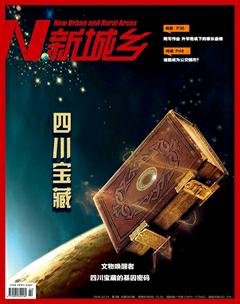戶籍管控思維難解“大城市病”
高明勇
“城市病”的主要責任不是外來人口造成的,卻要讓他們來埋單,有失公允。
“城市病”的主要責任不在外來人口
近來,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一大批城市總體規劃獲批,按照其中的目標設計,一直糾纏于各個城市的“大城市病”有望得到紓解。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中,在談及2020年發展目標時,描述是:“大城市病”等突出問題得到緩解。在談及2035年發展目標時,描述是:“大城市病”治理取得顯著成效。
根據這一時間表,未來20年左右的時間里,治理“大城市病”的頑疾將成為城市發展進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不過,在如何去除“大城市病”的方式上,卻存在很大差異,有些已經涉及到了方向層面。歷來,關于“大城市病”的解決方案,大多都涉及人口調節問題,尤其是流動人口的問題。對此,《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提出的方法是:“制定科學合理的公共服務政策,發揮公共服務導向對人口結構的調節作用。”
發揮“公共服務”的杠桿作用,這一提法相對并不多見,值得進一步期待。
與之對應的是,在“大城市病”中的流動人口問題,在一些地方文件中多有談及,街頭巷議中也是恒定的話題之一。
對于這一話題,《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一書中,美國學者蘇黛瑞提及,1995年,就有課題組下結論說,“城市居民通常都將許多問題歸咎于流動人口。”實際上,根據作者田野調查:“凡是市民們對某些問題(諸如交通問題)投注很多激情去討論的城市,他們的驚慌實際上是相對缺乏客觀依據的。”這一結論,歷經20余年仍未過時。
不僅坊間爭論缺乏客觀依據,學術研究依然如此。六年前(2011年),筆者專訪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部長、“主體功能區人口管理政策研究”課題組組長貢森時,他曾提出,到目前為止,沒有一份令人信服的調研報告能夠說明是因為外地人口和低端人口造成交通擁堵、水資源緊缺等“城市病”。
在公共服務層面,貢森的分析是:交通擁堵主要是規劃不科學造成的,一些特大城市的發展采取“攤大餅”式,而不是組團式、多中心的模式;一些流域和城市的環境惡化問題,主要是工廠布局分散和污染治理不當導致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面臨的壓力,主要是財政投入不足和公共資源空間配置不均衡導致的;大城市水土資源的超載問題,主要是經濟過于集聚或者社會文化資源過于集中導致的;外來人口低素質帶來的社會治安問題,主要是社會偏見和社會排斥的結果。
“大城市病”≠人口增多
“城市病”的主要責任不是外來人口造成的,卻要讓他們來埋單,有失公允。
上海學者陸銘在新作《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中說:“中國的很多事之所以分歧太多,就是最基本的原理被忘記了。”他認為,我們目前在城市建設的時候,一直有一個思想上的大誤區,總是把“城市病”理解為是人多導致的:人口增多,對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需求增長,供給相對緊缺。
以限制購房為例,他指出可以針對“外國人”,不能針對“外地人”。針對外國人的購房、就業是個政治問題,是要保護本國公民。而以“外地人”為限制對象的戶籍門檻,是沒有道理的。
這一判斷,與蘇黛瑞《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的分析相吻合。根據蘇黛瑞的分析,“城市病”是城市公共品供給制度的問題,而非流動人口的問題。他提出,必須瓦解舊有的城市公共品供給體制,才有可能解決城市的問題,而非“歧視”外地人。
解決這一問題,歸根到底還是要回到制度框架中解決。之前筆者專訪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段成榮教授時,他提出如何保證流動人口行使憲法賦予他們的政治權利,如何理順流動人口參政渠道,已經成為各地各級政府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課題。“目前社會管理的根基是以戶籍為基礎,例如對購房、購車資格限制的界定,對流動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入學資格的限制,這些政策的出臺,制造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是對流動人口合法權利的一種傷害。”
就是說,結合數十年來的城市研究及發展脈絡看,以戶籍管控思維為導向的城市管理模式,注定無法解決“大城市病”。因為流動人口的流入并非造成“大城市病”的根源,如果繼續沿襲老路,不但容易制造更多的社會歧視和社會摩擦,也會限制城市自身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和宜居環境的塑造。而在“宜疏不宜堵”的思路指導下,告別行政力量的簡單粗暴干預,一手建立基于價格機制的市場調節,一手建立基于“制定科學合理的公共服務政策”的公共品調節,才有可能將“大城市病”的問題歸置于法治規則內解決。
(作者系鳳凰網評論部總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