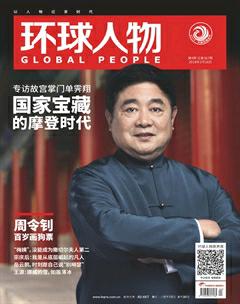阿來(lái),穿行在藏區(qū)與世界之間
許曉迪
他寫(xiě)《塵埃落定》《空山》,講述藏族鄉(xiāng)村百年史;主持《科幻世界》,關(guān)注科學(xué)與未來(lái)。
長(zhǎng)久以來(lái),人們對(duì)于藏區(qū)、藏人的想象,總會(huì)讓作家阿來(lái)覺(jué)得自己在面對(duì)一個(gè)龐大的“無(wú)物之陣”:“從年輕時(shí),我的思考原則就是不迷信。不僅是在宗教上不迷信,更重要的是,不迷信學(xué)界為我們提供的一般性結(jié)論,他們把藏區(qū)當(dāng)作一個(gè)整體,然后賦予它幾個(gè)關(guān)鍵詞——圣潔、原始、夢(mèng)幻。”在四川作協(xié)的辦公室里,他站在高高摞起的書(shū)堆前,把第三根煙放進(jìn)嘴里,“至少我的經(jīng)驗(yàn)不是這樣。”吐出一個(gè)煙圈,他將推到眉間的眼鏡,重新放回鼻梁上。
窗外車流喧嘩,這里距離成都熱鬧的春熙路商圈不到1公里。阿來(lái)告訴我,那是一條民國(guó)時(shí)代的老街,現(xiàn)在是成都最“潮”的地段,再往前走,就是大名鼎鼎、游人如織的寬窄巷子。
這是藏族人阿來(lái)來(lái)到成都的第二十二個(gè)年頭。采訪進(jìn)行到40分鐘,他從沙發(fā)上起來(lái),站在窗前接著說(shuō),每隔一會(huì)兒就換個(gè)方位,或是腆著微微隆起的肚子來(lái)回踱步,看起來(lái)就像個(gè)普通的漢族知識(shí)分子,不帶一點(diǎn)“邊地氣息”——除了因長(zhǎng)期在藏區(qū)大地上行走、游歷,可能不太能坐得住。
在城市的車水馬龍中,大自然銷聲匿跡,那些隱藏在大山深處的村莊,更是仿若虛空。但對(duì)阿來(lái)來(lái)說(shuō),那里才是他的精神原鄉(xiāng)。
從空山到機(jī)村
2005年3月的一天,阿來(lái)想為正在寫(xiě)作的鄉(xiāng)村系列小說(shuō)起一個(gè)名字,突然間,“空山”二字就跳了出來(lái)。他想起少年時(shí)代遇到的一支地質(zhì)勘探隊(duì)。他們拿出一張巨幅的黑白航拍照片,滿紙都是崎嶇的山脈縱橫交織。阿來(lái)想在其中辨認(rèn)自己的家鄉(xiāng)馬爾康,卻沒(méi)有找到。它和其他山村一樣,隱藏在大山的褶皺中,一無(wú)所見(jiàn)。
“那么具體的人,那么具體的鄉(xiāng)村,那么具體的痛苦、艱難、希望、蘇醒,以及更多的迷茫,所有這些,從高遠(yuǎn)處看去,卻一點(diǎn)也不著痕跡。”從此,這一系列故事,有了一個(gè)共同的名字:空山。
2008年,逾90萬(wàn)字的《空山》出版,以“六部曲”(《隨風(fēng)飄散》《天火》《達(dá)瑟和達(dá)戈》《荒蕪》《輕雷》《空山》)的形式,從上世紀(jì)50年代一直寫(xiě)到90年代,半世紀(jì)的藏族鄉(xiāng)村人事躍然紙上。
故事開(kāi)始于公路的開(kāi)通與汽車的到來(lái),封閉的機(jī)村縮短了與外部世界的距離,“現(xiàn)代”——從科學(xué)技術(shù)到政黨國(guó)家,從接二連三的運(yùn)動(dòng)到?jīng)坝康氖袌?chǎng)經(jīng)濟(jì)——也以勢(shì)不可擋的態(tài)勢(shì)打開(kāi)了機(jī)村人的視野。他們既享受著新生的美好,又遭遇陷落與迷失。當(dāng)舊有的秩序、倫理與生產(chǎn)方式土崩瓦解,新世界的制度與道德又風(fēng)雨飄搖,欲望、暴力、仇恨也開(kāi)始瘋狂地蔓延。
寫(xiě)作《空山》的時(shí)候,阿來(lái)一直盼望著它早點(diǎn)結(jié)束。“因?yàn)闀?huì)帶入”,他說(shuō),“我有幾十年的鄉(xiāng)村經(jīng)歷,看到那些與我有千絲萬(wàn)縷關(guān)聯(lián)的人,在嚴(yán)酷的生活中掙扎,非常難受。這些痛苦,有實(shí)際的問(wèn)題,更重要的還是情感上、心靈上的負(fù)擔(dān)。”
在躁動(dòng)而陌生的市場(chǎng)化時(shí)代,那些在少年時(shí)代曾與他朝夕相伴的朋友,一個(gè)個(gè)被裹挾其中。阿來(lái)的一個(gè)同學(xué),這邊父母要看病,那邊小孩要上學(xué),兩頭夾擊,每天被歉疚與絕望折磨;另一位同學(xué),開(kāi)著拖拉機(jī)翻到了公路下面,明明可以自救,卻放棄采取任何措施,殞命在長(zhǎng)途販運(yùn)木材的路上。
在《空山》中,一種細(xì)致而銳利的痛楚始終纏繞筆底。然而,以“空山”二字為題,卻不免生出旁枝逸出的聯(lián)想。“這名字總讓人想起王維的詩(shī),‘空山不見(jiàn)人,但聞人語(yǔ)響‘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lái)秋。”阿來(lái)對(duì)《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shuō),“在王維的語(yǔ)境中,空靈、禪意出來(lái)了,但中國(guó)的鄉(xiāng)村生活,哪里會(huì)有這些?那里只有凝重、破碎的現(xiàn)實(shí)。”
2018年,《空山》出版10周年,浙江文藝出版社重版此書(shū)。阿來(lái)便給這部小說(shuō)起了一個(gè)新的名字:《機(jī)村史詩(shī)》。
“機(jī)村”,是小說(shuō)中村莊的名字。“機(jī)”,是一個(gè)藏語(yǔ)詞的對(duì)音。它并不是標(biāo)準(zhǔn)的藏語(yǔ)詞,而是藏語(yǔ)里一種叫嘉絨語(yǔ)的方言詞,意思是種子,或根。
塵埃落定
對(duì)阿來(lái)而言,故鄉(xiāng)馬爾康就是他的根。
馬爾康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隸屬于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嘉絨藏區(qū),意為“火苗旺盛的地方”。嘉絨在行政上屬于四川,地理上屬于西藏。這里的藏人們世代過(guò)著半農(nóng)半牧的生活,在漢藏文化的邊緣地帶穿梭游走。
從童年時(shí)代起,阿來(lái)就開(kāi)始了在兩種語(yǔ)言之間的流浪:在學(xué)校,學(xué)習(xí)、使用漢語(yǔ);回到日常,依然用藏語(yǔ)交流,用藏語(yǔ)表達(dá)一切看到的東西。
1981年,22歲的阿來(lái)在馬爾康縣中學(xué)教書(shū)。他不止一次地回憶起,那段在空蕩蕩的校園里,沉溺于閱讀的孤寂日子。
“小縣城里,書(shū)店的書(shū)很少,我就給出版社寫(xiě)信,讓他們寄來(lái)書(shū)目單,我挑出想看的書(shū),連同買書(shū)的錢一起郵回出版社。”阿來(lái)說(shuō),當(dāng)金庸、瓊瑤風(fēng)靡全國(guó)時(shí),他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將海明威、福克納、馬爾克斯等文學(xué)大師的作品讀了個(gè)遍。
在老家馬爾康,現(xiàn)在還有一間屋子,堆滿了阿來(lái)上世紀(jì)80年代讀過(guò)的書(shū)。一位紀(jì)錄片導(dǎo)演看到這間體量巨大的書(shū)房,頻頻咋舌:“怎么你那時(shí)讀的書(shū),和我們?cè)诒本┳x的一樣?”
而當(dāng)時(shí)的內(nèi)地文壇,正卷起一陣“西藏想象”的旋風(fēng)。漢人馬原與藏人扎西達(dá)娃,分別憑借《岡底斯的誘惑》與《系在皮繩扣上的魂》,賦予西藏誘惑與隱秘的形象,將來(lái)自拉美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從炎熱、潮濕的熱帶叢林,移植到干燥、空曠的青藏高原。
阿來(lái)也被卷進(jìn)了這團(tuán)旋風(fēng),他開(kāi)始寫(xiě)詩(shī),之后也寫(xiě)小說(shuō)。寫(xiě)大地、群山、海子、村莊,寫(xiě)草原、喇嘛、生靈、英雄。1989年,他的詩(shī)集與小說(shuō)集出版,然而如同宿命一般,他卻在此時(shí)陷入了寫(xiě)作的迷惘:簡(jiǎn)單的激情與浪漫,膚淺的邊地情調(diào),能否寫(xiě)盡一個(gè)民族的滄桑與深廣?
尋找答案的辦法是行走。阿來(lái)走出家門,在故鄉(xiāng)廣闊的大地上漫游。此后的幾年里,他徒步走過(guò)每一個(gè)鄉(xiāng)一級(jí)的單位,從馬爾康的村寨開(kāi)始,到梭磨河、大渡河、莫爾多神山、大小金川、若爾蓋草原……走到哪兒就住在哪兒,累了躺在松樹(shù)下,讀聶魯達(dá)和惠特曼,與藏民們坐在草地上看白云疾走,喝酒,吃牦牛肉。endprint
到了1994年5月,高原上的春天剛剛開(kāi)始,阿來(lái)看著窗外的白樺林,寫(xiě)下一句話:“那是個(gè)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看見(jiàn)一群畫(huà)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這就是《塵埃落定》的第一行字。
《塵埃落定》的故事發(fā)生在上世紀(jì)40年代的西藏。麥其老土司依靠鴉片、槍支與銀元,迅速成為一方霸主。他的二兒子是個(gè)傻瓜,卻總表現(xiàn)出驚人的睿智。當(dāng)罌粟隨著漢人的軍隊(duì)第一次出現(xiàn)在西藏的土地,傻子就嗅到了不祥的死亡氣息;而當(dāng)他的聰明哥哥在戰(zhàn)場(chǎng)上大肆征伐時(shí),傻子卻將堡壘敞開(kāi),創(chuàng)造了第一個(gè)邊境貿(mào)易市場(chǎng)。然而,現(xiàn)代已經(jīng)到來(lái),傻子意識(shí)到歷史的宿命,坦然赴死,最終在汩汩鮮血中,見(jiàn)證了土司時(shí)代的終結(jié)。
《塵埃落定》中,漫山遍野的罌粟花,土司宮廷內(nèi)的刀光劍影、明爭(zhēng)暗斗,還有喇嘛、活佛呼風(fēng)喚雨、轉(zhuǎn)寄靈魂的種種巫術(shù)……這些充滿魔幻色彩的元素,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了讀者對(duì)西藏的想象。
然而,阿來(lái)并無(wú)意構(gòu)筑一個(gè)魔幻神秘的異度空間——如同大多數(shù)搜羅奇風(fēng)異俗的西藏書(shū)寫(xiě)者那樣,從他曾研究過(guò)18個(gè)土司家族史的“野心”可知,他更關(guān)心的是一個(gè)世俗的、現(xiàn)實(shí)的西藏,看它如何在現(xiàn)代性的沖擊下,承受著從覆滅、斷裂到新生的艱難轉(zhuǎn)型。
對(duì)阿來(lái)來(lái)說(shuō),這種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是全球性、普遍性的。“從普遍的意義講,沒(méi)有什么漢族、藏族的區(qū)別。從《塵埃落定》到《空山》,就是一個(gè)中國(guó)鄉(xiāng)村百年史。”阿來(lái)說(shuō),“鄉(xiāng)村的命運(yùn)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今天鄉(xiāng)村面臨的變遷是整個(gè)國(guó)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大地的階梯
對(duì)大多數(shù)人來(lái)說(shuō),西藏是個(gè)形容詞:遙遠(yuǎn)、荒蠻、神秘,可以隨意加諸于許多當(dāng)下缺失的東西。于是,荒蠻成為浪漫,神秘成為信仰,行路的艱辛成為了不起的探險(xiǎn)。在無(wú)數(shù)游客、文青、“朝圣者”那里,西藏圣潔得空洞、浪漫得乏味。
但對(duì)阿來(lái)而言,西藏是由一個(gè)個(gè)地理區(qū)塊構(gòu)成的龐大名詞,需要用雙腳一步步丈量。
阿來(lái)把從成都平原走向青藏高原的一列列山脈,看成“大地的階梯”。30年里,他一次次邁開(kāi)雙腳,順著階梯的軌跡,在高嶺深谷、山川牧場(chǎng)間開(kāi)始實(shí)際的尋訪與勘探。他走訪藏文化氣息最濃厚的中心區(qū),如山南、拉薩,也追溯河西走廊地帶的藏人歷史;跑遍了武威、麗江、敦煌、玉樹(shù)等十幾個(gè)地區(qū),也重游故鄉(xiāng)的村鎮(zhèn)。
“只有囊括不同的地方,寫(xiě)出藏文化內(nèi)部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才能破解一種當(dāng)下對(duì)藏文化的迷思。”阿來(lái)說(shuō)。
在行走與游歷中,阿來(lái)寫(xiě)出了《格薩爾王》,講述格薩爾王一生降妖除魔、開(kāi)疆拓土的豐功偉業(yè);也寫(xiě)出了《瞻對(duì)》,鉤沉瞻對(duì)這塊如“鐵疙瘩”一般的彈丸之地,如何在歷史的沖擊下漸漸融化。
“世上哪有不融化的地方?”阿來(lái)感嘆,“過(guò)去的西藏,沒(méi)有學(xué)校、沒(méi)有醫(yī)院、沒(méi)有公路,什么都沒(méi)有,只有寺院,幾十年前,像我這樣識(shí)字的人,恐怕也就是個(gè)喇嘛。”而如今,拉薩已成為燈火輝煌、高樓林立的現(xiàn)代都市,喇嘛們拿著iPhone,開(kāi)著車,穿起了漂亮的皮鞋。
當(dāng)整個(gè)青藏高原已經(jīng)不可逆轉(zhuǎn)地與現(xiàn)代文明遭逢,“沒(méi)有一個(gè)角落不被捕獲,變化必然要發(fā)生”。阿來(lái)希望“新”的到來(lái),但在這個(gè)漫長(zhǎng)的過(guò)渡期,社會(huì)的卑俗、人心的委瑣,卻使他憂慮: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漂滿了大樹(shù)的尸體;教義開(kāi)始失落,金碧輝煌的寺廟并不能護(hù)佑人們的精神世界;鄉(xiāng)民們盛裝打扮,一邊賣力地表演“民族風(fēng)情”,一邊用英語(yǔ)或普通話,與留影的游客討價(jià)還價(jià)……
現(xiàn)在的他,每年仍會(huì)獨(dú)自開(kāi)車奔向青藏高原,少則十多天,多則兩個(gè)月,車?yán)锓胖惶讘敉庋b備,包括衣服、帳篷和睡袋,有時(shí)就露宿在草原的滿天星光下。“只要是5、6月份上高原,滿山都是挖蟲(chóng)草的;一到秋天,滿山都是找松茸的;經(jīng)常也會(huì)碰見(jiàn)偷偷摸摸搞柏樹(shù)的。”
阿來(lái)把這些路上的見(jiàn)聞,寫(xiě)成了“山珍三部曲”——《三只蟲(chóng)草》《蘑菇圈》《河邊柏影》,揭示消費(fèi)至上的社會(huì)里,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商業(yè)鏈條對(duì)自然界、對(duì)鄉(xiāng)村、對(duì)弱勢(shì)群體的剝奪:“挖掘蟲(chóng)草,草皮上的傷疤會(huì)慢慢潰爛;蘑菇(松茸)完全都采光,就再也沒(méi)有了;制作佛珠手串,柏樹(shù)因?yàn)樾欧鸬挠豢彻狻!?/p>
近10年來(lái),阿來(lái)行走的足跡越發(fā)寬廣,他頻頻出國(guó),“不是為旅游,而是關(guān)乎我的思考”。在他看來(lái),現(xiàn)代性沖擊下的文化與信仰危機(jī),不只發(fā)生在西藏,“世界上的任何一個(gè)角落都是如此”。
在美國(guó)夏威夷,別人下海,阿來(lái)上山,看當(dāng)?shù)赝林说谋硌荩八麄兲就恋牟萑刮瑁樽嘁魳?lè)卻是西班牙的弗拉明戈,最早的曲調(diào)已經(jīng)失傳,文化的源頭在殖民過(guò)程中就消失了。”在美國(guó)的中西部鄉(xiāng)村,他看到農(nóng)夫們騎著高頭大馬,或開(kāi)著皮卡車出現(xiàn)在高速路邊,比城里人顯得更為自尊、安詳。森林、牧場(chǎng)、麥田,相互間隔、輝映。那里的寧?kù)o、富庶,讓他獲得了反觀中國(guó)鄉(xiāng)村的視點(diǎn)。
還有拉美大陸。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秘魯,在那些被干旱折磨的原野上,巨大的仙人掌讓他神傷,拉丁美洲被跨國(guó)資本無(wú)情掠奪,資源消耗殆盡,破碎的山河大地如同被“切開(kāi)的血管”。
阿來(lái)說(shuō):“拉美這些國(guó)家,工業(yè)化比中國(guó)要早,上個(gè)世紀(jì)六七十年代,農(nóng)民向城市轉(zhuǎn)移,離開(kāi)農(nóng)業(yè),失去土地,淪為只有勞動(dòng)力可以出賣的無(wú)根的人。中國(guó)是個(gè)后發(fā)展國(guó)家,很多我們正在面臨的問(wèn)題,可以從他們的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yàn)。”
“人是出發(fā)點(diǎn),也是目的地”
1996年,阿來(lái)離開(kāi)生活了36年的阿壩高原,來(lái)到成都,在《科幻世界》做一名編輯。談及這個(gè)話題,我們的采訪突然轉(zhuǎn)變了風(fēng)格,阿來(lái)的語(yǔ)氣不再沉重,他興致勃勃地談著科幻,談著宇宙、星系……一次采訪被毫無(wú)預(yù)設(shè)地分成了兩部分:此前的阿來(lái),是一個(gè)從現(xiàn)在回望過(guò)去的哲人;之后的阿來(lái),是一個(gè)看向未來(lái)的理想主義者。
1997年,《科幻世界》舉辦國(guó)際科幻大會(huì),阿來(lái)跑來(lái)北京“搞活動(dòng)”,操著流暢的川普,整天同各檔媒體見(jiàn)面。
那次活動(dòng)盛況空前,除了科幻作家,還請(qǐng)來(lái)了多名俄羅斯和美國(guó)宇航員。之后,又移師成都,在月亮灣度假村舉行夏令營(yíng)。宇航員連續(xù)幾小時(shí)為科幻迷們簽字,長(zhǎng)長(zhǎng)的隊(duì)伍讓人震驚。著名科幻文學(xué)作家韓松當(dāng)時(shí)在現(xiàn)場(chǎng),“目瞪口呆,就像看見(jiàn)虔誠(chéng)的教徒接受洗禮一樣”。endprint
韓松最初見(jiàn)到阿來(lái)時(shí),他只是一名站在門口,代表《科幻世界》向記者發(fā)紅包的“打雜工作人員”。隨后的幾年,阿來(lái)的《塵埃落定》出版,轟動(dòng)文壇,而他本人卻將大把的時(shí)間投入到科幻編輯的角色中:閱讀前沿科學(xué)的書(shū)籍,寫(xiě)關(guān)于科學(xué)幻想的文章,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科幻作家隊(duì)伍。他用剛剛書(shū)寫(xiě)過(guò)藏地歷史的筆,開(kāi)始講述工業(yè)文明,談?dòng)?jì)算機(jī)、克隆、空間站與外星人,讓人忘記了那個(gè)在高原上游蕩行走的阿來(lái)。
1999年,發(fā)生了一件事。這年,全國(guó)高考的作文題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而在高考前一周出版的《科幻世界》第七期上,刊登了一篇阿來(lái)的文章《長(zhǎng)生不老的夢(mèng)想》,竟與高考作文題“不謀而合”。這再一次引發(fā)“科幻熱”,阿來(lái)回憶,那時(shí)的雜志社,每天要接到大袋大袋的信件。
阿來(lái)主持《科幻世界》的10年,被科幻圈公認(rèn)為科幻文學(xué)發(fā)展的“黃金時(shí)代”。雜志的發(fā)行量,從不到1萬(wàn)增至幾十萬(wàn);一批新生代作家,劉慈欣、王晉康、何夕等從這里走出、成長(zhǎng),至今仍是科幻界的領(lǐng)軍與中堅(jiān);大量國(guó)外科幻文學(xué)被引進(jìn)、出版;而如今科幻界的掌舵人,“劉慈欣背后的男人”姚海軍,也是在阿來(lái)力排眾議的舉薦下,從黑龍江調(diào)入《科幻世界》。
“長(zhǎng)久以來(lái),中國(guó)的科幻文學(xué),相比‘文學(xué),更偏重‘科普。科幻文學(xué)是類型文學(xué),但它首先得是文學(xué),然后才是科幻文學(xué)。其實(shí),科學(xué)也好,文學(xué)也好,最終都是為‘人的。人是出發(fā)點(diǎn),也是目的地。”
在阿來(lái)看來(lái),最好的科幻作家,從來(lái)都是超越“科幻”類別的寫(xiě)作者。“不久前去世的美國(guó)科幻作家勒古恩,寫(xiě)過(guò)《黑暗的左手》,但沒(méi)人只把它當(dāng)作科幻作品,而是經(jīng)典小說(shuō);諾貝爾獎(jiǎng)里也有科幻小說(shuō),英國(guó)戈?duì)柖?xiě)的《蠅王》就是科幻小說(shuō),但沒(méi)人說(shuō)戈?duì)柖∈强苹米骷摇!?/p>
“還有現(xiàn)在的劉慈欣,《三體》是一個(gè)科幻作品,但它比很多主流文學(xué)還要好。”阿來(lái)說(shuō),“越好的作品,越難于歸類。《西游記》是什么?用現(xiàn)在的話說(shuō),至少是玄幻;《聊齋志異》是什么?鬼故事。《紅樓夢(mèng)》就是超越言情小說(shuō),《金瓶梅》就是超越色情小說(shuō)。所以好的文學(xué),恰恰是可以打破這些類型分野的。”
而阿來(lái)自己,也始終實(shí)踐著這種打破壁壘的努力:他將一只眼投向藏族歷史,另一只眼注視科學(xué)和未來(lái);用一只腳游歷嘉絨故土,另一只腳邁向世界版圖。這使他早早就跳出了深遠(yuǎn)內(nèi)陸的縣城,超越了自己的民族,將自己融入更廣袤的大地和更深遠(yuǎn)的世界之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