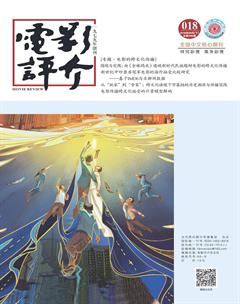困境與突圍:由《金珠瑪米》透視新時代民族題材電影的跨文化傳播
石嵩 李真甜
《金珠瑪米》作為一部少數民族題材主旋律電影,有著與以往的民族題材主旋律電影所不同的視聽元素和鏡頭呈現,突破了以往多數主旋律電影為保持自己鮮明的主旋律特色往往采用的較為固化的電影敘事方法和鏡頭語言運用方式,摒棄了主旋律電影中模式化、刻板化的特點,為民族題材主旋律電影做出了全新的熒幕詮釋和講故事方法的探索。導演楊蕊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長期以來,民族電影基本形成了比較固定的幾種類型,有漢族拯救其他民族的,有遠距離敬仰或者欣賞民族文化的,還有就是展現當代少數民族群眾日常生活狀態的,我對這種視角的固化不是很滿意。”[1]她希望借助自己平視的鏡頭語言和換位包容的自省視角,重返那段重大歷史往事。
一、 平等的敘述視角跨越傳播隔閡
金珠瑪米,在藏語中原來的含義是打破鎖鏈的人。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后,金珠瑪米就成了西藏人民對解放軍的稱呼。影片以展現當年為解放西藏奠定重要基礎的“昌都戰役”為主線展開敘述,但在影片當中,導演并沒有把戰爭的發生及其殘酷性作為重點描述的對象,而是通過主人公——解放軍華山深入藏地部落與藏人發生一系列的接觸與交往來展現20世紀50年代漢藏兩族人民的第一次碰撞與交流,更多的描繪了人性與選擇。不可否認,戰爭也是漢藏兩個民族間互相碰撞、彌合的重要形式,是描繪歷史所不可避免的一個重要環節。但是考慮到歷史題材的特殊性和漢藏等民族觀眾的接受度,導演巧妙地將戰爭放到了遠景,將人性推到近景,選擇用平等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事件,而不僅僅停留在“誰解放了誰”的層面上止步不前。
電影《金珠瑪米》當中出現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各方勢力,人民解放軍、藏地部落、土匪等等,對于每一方勢力,導演以及創作團隊都進行了精細的雕琢和清晰的刻畫。在談判遲遲沒有進展、解放西藏的美好愿望破滅以后,為了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人民解放軍毅然進入西藏,直面嚴酷的地理環境而不退縮,忍受著空氣稀薄、饑寒、勞累等痛苦,日夜兼程,連續作戰,展現了人民解放軍不畏艱苦的堅毅品質。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藏地頭人洛桑,作為一個站在時代轉折點上的部落首領,一方面, 他需要維護自己農奴主的地位,堅持自己半生以來堅定不移的信仰;另一方面,時代的洪流滾滾而來,農奴主的時代終將過去。從歷史發展宏大的角度來看,區區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的微小力量與滾滾而來的歷史洪流始終無法匹敵,農奴主階級的沒落注定讓人唏噓。所以實際上洛桑是一個阻礙歷史發展潮流、思想落后的非正面角色,但是劇中塑造的頭人形象卻深受觀眾喜愛。他身上散發著一種領主特有的干脆利落、堅強果決的魅力。“天高地闊,好惡由心”的電影主旨在他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他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符合邏輯與人物設定,即使在某些阻撓歷史進步的情節中,他的行為也是有理有據,不會使人生厭,反而為他的身份和所處的時代背景的沖突扼腕嘆息。以占堆為首的土匪勢力在壓迫之中舉起反抗的旗幟,為了自己的命運展開了激烈的抗爭,展現了不屈不撓的意志品質。
不管是在鏡頭運用還是情節安排上,導演都是以一個平等的角度去審視藏地頭人、土匪和人民解放軍,運用豐富的鏡頭語言對所有處于時代變換語境下的渺小人物進行生動的刻畫,他們的行動邏輯不是弘揚主旋律,而是基于每一個復雜境遇下的理性選擇。《金珠瑪米》從頭至尾都沒有為觀眾設定一個特定視角,而是站在歷史宏大的視角之下,平等的描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明面臨的生存與前途的抉擇,記錄了在20世紀50年代,兩群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在海拔高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所發生的碰撞與融合。平等敘事的鏡頭語言,使得影片在跨文化傳播尤其是對外傳播過程更顯得平易近人,使觀眾更有帶入感。
二、 新時代主旋律民族題材電影的類型化創新嘗試
“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要提高共賞性,讓各民族觀眾乃至全球各國觀眾都喜聞樂見,走類型化的道路或許是一種很好的選擇。”[2]在電影《金珠瑪米》中,觀眾可以感受到西部類型片的影子。據總策劃牛頌介紹,在《金珠瑪米》創作過程中,主創團隊始終堅持將人情人性擺在最高位,盡可能吸收西部片等類型元素,突出觀賞性,力爭拍出一部符合當代審美潮流、符合當今觀眾審美趣味的電影。“《金珠瑪米》既擁有主旋律電影的正能量,又富有文藝片的精致藝術呈現;既具有民族題材影片的特質,又具備西部類型片的審美趣味。”[3]影片的主題雖然是戰爭,創作團隊并沒有把鏡頭聚焦在昌都戰役本身,而是著眼于劇中每一個人物的喜怒哀樂,塑造出了一個個有血有肉、愛恨分明的人物形象。劇中主要演員們之間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也是電影的一大看點,反映了小人物們在宏大的歷史進程中真實的狀況,增強了電影的觀賞性,這也與類型片的特征相似。
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認為:“創作西藏題材影片的難度在于,必須要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闡釋歷史問題。《金珠瑪米》既為今天的觀眾講述了昌都戰役的歷史合理性,又巧妙地回避了一些早已解決的歷史問題,并未引發新的矛盾。僅憑這一點,便確立了影片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4]面對當下的市場,重大主題的少數民族電影,如何既保持民族特色,又能融入已有的類型片元素,《金珠瑪米》的創作者走出了新時代主旋律民族題材影片類型化創新的重要探索一步,楊蕊導演采用了許多的航拍鏡頭來表現藏地高原上的自然風景和人文風貌,拋開故事情節不看,儼然是一部制作精美的紀錄片,類型特征十分明顯,增強了影片的可觀賞性。
三、 少數民族電影跨文化傳播任重道遠
近年來,我國的電影事業蓬勃發展,無論是電影的生產數量、影院數量、電影屏幕數量還是電影的上座率都有了明顯的增加。“中國電影正在謀求由生產大國向創造強國的升級發展道路。這一歷史進程中,少數民族電影也日益成為引人注目的重要環節,成為豐富乃至提升中國電影版圖的文化維度與產業生長點的要素。”[5]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的少數民族電影作為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少數民族電影創作當中涌現出了一大批富有時代氣息和民族特色的作品。與此同時,一批才華橫溢的導演也與少數民族電影一同成長起來,為電影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力量。《金珠瑪米》作為一部藏族題材的主旋律電影,契合了少數民族電影蓬勃發展的趨勢,也是觀眾了解西藏歷史的一個窗口。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漢藏雙語影片在跨文化傳播尤其是國際傳播的過程當中可能遇到的傳播桎梏與不認同現象。
“鮮明的地域特色和特殊的歷史文化造就了獨特的藏族題材電影,作為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藏族電影向世人講述和還原了藏族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6]但正是由于這些特殊性,造成了藏族電影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阻礙重重。對于國內觀眾來說,首先,藏族電影的發展雖然能夠在創作拍攝過程當中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但是在后期宣傳的過程當中顯得后勁不足。一部影片的宣傳發行與前期創作拍攝同樣重要,如果好的影片沒有好的宣傳,就會陷入知名度低、院線排片量少、觀眾少、票房慘淡、流通受限的死循環。其次,藏族電影在內容上偏向于弘揚時代旋律和展示民族文化,在觀賞性和娛樂性上與其他類型片上相比略有欠缺。在《金珠瑪米》當中,導演以類型化影片的創作形式為少數民族題材主旋律電影的創作發展做出了一次開拓式的有益嘗試,提供了一種反思歷史和民族關系融合的全新視角方法。最后,許多少數民族電影在國內的主流院線無法上映或者票房慘淡,但是在國外展映的過程當中卻能頻頻斬獲大獎,如何避免類似情況的發生,也是少數民族電影工作者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至于少數民族電影在海外的傳播,更是難上加難。“影像表達通常比較多義,方向往往是可以被利用的,在一個國家的人們看來是正面的影像,可能在另一個國家人們的眼里就有一定的負面性。”[7]《金珠瑪米》是一部以男性角色占主體的電影,在一眾高大勇猛的康巴漢子的襯托下,女主角形象卻顯得有些單薄。藏族優秀女演員楊秀措飾演的央金作為影片中主要的女性角色,在片中更多的是為了男性角色的感情需要和觀眾潛在的審美欲望而非獨立個體存在,角色情感簡單化、理想化、缺乏深入的心理活動描寫就成了這個角色塑造中最大的問題。這也需要創作團隊在影片前后加入字幕或旁白進行一定的解釋說明來幫助國外觀眾理解。所以,少數民族電影工作者在創作電影的過程當中,必須站在多語境、多文化的角度下進行思考,考慮到跨文化傳播尤其是對外傳播過程中容易產生的種種誤解與誤讀的情況。
四、 換位思考、跨越差異,開拓新時代民族題材影片表達與傳播的新路徑
從電影《岡仁波齊》之后,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了西藏轉山的傳統,加上在之前看到的許多西藏電影當中,都把西藏描述成了一個距離我們十分遙遠,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方。在《金珠瑪米》這個電影之中,導演在表現一個信仰至上的西藏同時,更著意于鏡頭透視下的人性有著普通人的情感與價值觀。
觀影后有人對導演提出質疑,認為這個故事失去了藏族的民族特色,在其他地區、其他民族人的身上也有可能發生。而在導演楊蕊的眼中,藏族人民與其他民族的人并沒有天差地別的差距,他們不是每天都活在信仰當中的完全抽離了自然生活的人,而是每天腳踩大地,要繁衍生息,每天要勞動生活的普通人。我們看到的西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想象,而實際上,在時代轉折到來的時候,當生活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他們內心的困惑與搖擺、掙扎與堅持和我們并無二致。
在電影拍攝之前,楊蕊導演和全部的主創團隊為了更好地還原歷史,曾經沿著18軍進藏的路線,從四川出發,克服了艱難的自然環境,帶著主創團隊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拍攝。他們還采訪了沿途參與昌都戰役的老人們,也聽到了許多藏民口中的類似“紅漢人好,白漢人不好”的評價,試圖在最大程度上還原歷史的真相。《金珠瑪米》這個片子最終能呈現在觀眾的眼前與導演誠懇負責講述歷史的拍攝態度和全體主創人員的付出是分不開的。
對于傳播者來說,要想傳播,首先得了解它。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原總編輯張小平先生曾經在一次專訪當中說:“首先要學習藏民族的文化,要掌握藏民族文化的基本特點和它的精髓。只有充分地了解它,才能把握好對外講什么,怎么介紹這個民族,怎么介紹這個民族的文化,這個是很重要的。”[8]不管是外國人,或者是生活在西藏地區以外的中國人,都不可避免的對西藏有著刻板印象,這是傳播不暢所引起的,也是需要我們去努力克服的文化偏見,更是新時代民族題材影片對外傳播急需解決的問題。開拓新路徑,向全世界展現一個多元化、現代化的西藏,是每一位試圖描繪西藏的新時代傳播者的責任和擔當。
結語
總體來說,楊蕊導演的《金珠瑪米》跳脫出一種我們常見的主流歷史觀點,為少數民族主旋律電影的發展與跨文化傳播做出了一次全新的嘗試和突破,也讓我們關注到了少數民族電影以及主旋律電影新的可能性,以此來看,《金珠瑪米》其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不言而喻。雖然,影片的民族題材與主旋律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特殊性,這樣特殊題材的電影在跨文化傳播尤其是國際傳播方面可能遇到多重誤讀。再者,由于地理形態、風俗習慣、歷史文化所產生的陌生化隔閡使其跨文化語境接受過程中會遇到問題與瓶頸;但這都不妨礙后續民族題材影片的創作者們沿著《金珠瑪米》所開拓的新時代民族影像與跨文化傳播路徑繼續探索和發展。
參考文獻:
[1]楊雯.《金珠瑪米》:民族電影的另一種打開方式[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7-12-14.
[2]馬瀟.主旋律電影的“今世前生”——簡論改革開放以來主旋律電影的流變[J].當代文壇,2011(1).
[3][4]李博.金珠瑪米:西部片風格的西藏題材電影[N].中國藝術報,2017-05-19.
[5]李蓉.中國少數民族電影破解傳播困局的路徑[J].當代電影,2017(11).
[6]王廣飛.新中國少數民族電影筑夢之旅:西藏卷[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6:4.
[7]石嵩.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文化困境——談《滾蛋吧!腫瘤君》沖擊奧斯卡[J].藝術評論,2016(3).
[8]王曉燕.傳播西藏文化 還原真實西藏——專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原副總編輯張小平[J].對外傳播,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