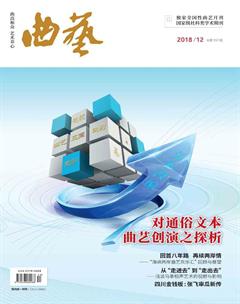英雄金筆今尚在
陳為人

王秀春的成名作《十里鋼城盡朝暉》,在1973年山西省曲藝調演中獲得優秀節目獎。《山西日報》全文刊登了這篇數來寶作品,并獎勵了王秀春一支英雄金筆。當年這也算是一件貴重的獎品。但在寫作主要靠電腦的今天,鍵盤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鋼筆。而王秀春珍而重之贈送給孫女的英雄筆,也不免有人調侃:“現在還有誰希罕鋼筆?你不如把它埋進土里,哪天還能成出土文物。”
英雄金筆成為意味深長的一個象征。
幾十年過去,王秀春那雙忽閃忽閃的大眼睛仍是我腦海中最靈動的光。人們說,王秀春的眼睛會放電,到舞臺上不用演,光憑眼神就能和觀眾充分交流。1973年的山西省曲藝調演,我太太嚴淑鶴擔任報幕員,她回憶說,王秀春一出場,劇場就是一股熱流,一股笑流,火熱的程度不亞于如今的明星出場。每次節目演完,報幕員上臺,都會遭到觀眾的轟臺,一陣陣的掌聲如雷動,根本不容她開口報下一個節目。王秀春和搭檔返場謝幕,觀眾還是不讓,有一次竟然謝幕達四次之多。
王秀春從事曲藝工作近60年,創作演出數來寶、小品等作品300多件,有近百件作品分別刊登在《曲藝》雜志、《天津演唱》《工人日報》《山西日報》等報刊和各種曲藝作品集中,數十件作品在中央電視臺及省市電視臺錄制播出。他創作并演出的《新爐長》《說話》《該怨誰》《信不信由你》等節目在曲壇大獲成功。現任山西曲協副主席、山西曲藝團團長王兆麟回憶說:“1992年,我與蔡石基、馬小平三人有幸表演了王老師的《真假之間》,那個年頭,曲藝小品比賽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我們的對手是潘長江、黃小娟、鞏漢林、崔凱,都是這樣級別的大腕。王老師的《真假之間》卻力壓群雄獲得了一等獎。”王兆麟又說:“我們當年都是初出茅廬,沒有什么表演經驗,能得一等獎,完全是王秀春老師創作的作品好,用我們曲藝界的行話說,就是‘活兒保人了。”
山西曲藝界另一文化遺產太原蓮花落的傳承人王灝偉回憶:“著名曲藝評論家常祥霖評價:‘像王秀春這樣既能創作又善于表演的曲藝家在全國恐怕也沒有幾個,是我國曲壇名不虛傳的大腕。1984年在北京香山的全國曲藝研討會上,專家們一致認可,王秀春的數來寶是中國曲壇的一朵奇葩,一大流派。”
20世紀末可說是王秀春的黃金歲月。一次次從北京載譽歸來,一頂頂桂冠落在頭上:山西省曲藝家協會主席、山西省青聯副主席、山西省文聯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說唱中心常務理事、中國快板藝術研究會副會長,……一個工廠里土生土長的業余曲藝愛好者,成長到今天的地步,很是難得。
但王秀春清醒理智地對我說:“‘死去元知萬事空,過年就77歲奔80歲去了,我總對自己說,轟轟烈烈一場,風光過,人五人六過,自己折騰得也算可以了。75年的戲劇人生過來了,你就認命吧,你就老老實實當個觀眾,坐到觀眾席上把‘戲看下去。算了吧,舞臺上的聚光燈,還能總照著你,老不熄滅呢?掌聲再熱烈,也總有停下來的時候……”
王秀春說的是實話,畢竟曲壇輩有才俊現,各領風流一眨眼,江湖后浪推前浪,前浪消逝沙灘上。誰人頭上的光環,耐得住歲月流水的磨礪沖刷?可盡管江潮浪涌起伏有時,而那一片從大地中生長出來的磐石卻能始終屹立,煥發磨洗之后的光彩。
王秀春不能被遺忘,老一輩曲藝工作者不能被遺忘。
這些潛臺詞正是我撰寫《撇捺人生王秀春》的意在筆先。
后來擔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唐達成20世紀70年代被下放至太鋼,我們編輯著一本不定期的《太鋼文藝》,也擔負著為太鋼文工團創作一些小節目的任務。因著這關系,王秀春與唐達成和我接觸很多。王秀春經常會謙恭得像小學生一樣,向我們請教一些文學方面的問題。
王秀春說:“我雖然是個搞曲藝的,但在本質上我是崇拜與癡迷文學的。常聽你和唐達成先生說‘文學即人學呀,寫出‘這一個呀,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當時我聽著不僅新鮮、好奇,而且似乎點醒了我,解除了對創作問題的蒙惑,創作的最高歸宿就是寫出具有時代典型性的人物來。之后我便著手于曲藝創作的實踐與摸索,并走出了一條‘寫人‘以人說事,以事喻理的自己的路子。當然,曲藝有它的自身規律,還不完全等同于文學。你和唐達成先生的談話經常就觸動了我。‘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句話就是聽你們說的。日后對文學和文藝理論的學習與思考,也不斷驗證著這些觀點的可行與正確。”
以曲藝的形式,如文學一樣走塑造人物的路,成為王秀春一段時間里的探索和追求。王秀春在一篇《從生活中來》的創作談中寫道:
“20多年的鋼城生活,使我真切地看到并了解了周圍大量的人和事。他們身上展示出千差萬別的人物性格和時代風貌,這些真實而原始的事例,從不同角度激發著我的創作熱情,同時為我提供了極寶貴的創作原料。數來寶《新爐長》即取材于一位煉鋼工,在試煉一爐特殊鋼中,科學加勇氣,甚至在補爐時被烤得臉、臂起水泡的英雄事例。由于感受真切,所以避開了一般化的手法。”
任何文學形式,或隱或現,都有塑造英雄人物的表現沖動,無產階級文學之表現力尤其強烈。恩格斯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無產階級文學要“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此后,以高爾基為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就開始了“大寫的人”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新中國文學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塑造反映“時代風貌”的英雄人物。塑造站在歷史潮流前面的新人形象,這是一個時代對作家提出的神圣職責。王秀春在曲藝領域,也難能可貴地進行了這樣的嘗試。
王秀春說:“還有一件事也是聽唐先生和你在一起時說的,一位大作家下農村,在農家院里看到雞在地上走過留下的印跡都是一個個單個的‘個字,便又引發了聯想,由此寫出一篇關于‘個人‘個體主題的文章。這件事對我觸動非常大,所謂過去在心中空泛的詞句‘觀察生活,提煉生活,從生活中來一下子就變得具體起來了,并且銘刻于心,長期地指引著我創作的思路和方法。”
王秀春在一個美展上偶然看到一幅工筆畫《蓮藕圖》,觸景生情,浮想聯翩:“蓮之姣美,淺出于水,其根在藕,深入于泥。”一個“深入”,一個“淺出”,形象而生動地喻明了藝術形式和思想內容之間有機的依附關系。形式即“蓮”, 內容即“藕”,形式是內容的外在表現,而內容則是形式的生命所在。“不少數來寶作品有技巧,有笑料,不失數來寶的風格,但缺少較深刻的思想、藝術深度,通俗話叫作沒什么‘琢磨頭;還有的數來寶作品,有較深的思想意義和政治觀點,但表現手法過于死板,說教性太強,政治名詞、豪言壯語連篇,無生活氣息,無藝術趣味,失去了曲藝生動風趣的特色。通俗說管這類段子稱作‘皮厚。”
王秀春把溜嘴皮耍花腔玩語言的花里胡哨,自覺升華為追求話中有話、弦外有音。言有盡而意無窮。
王秀春所創作的《新爐長》中的爐長,《說話》中的“我”,《排隊》中的疤拉眼,《該怨誰》中的大梁和小梁,及《美莉的心靈》中的姜美莉,無一不依附著某一生活原型,無一不努力地按著這一創作原則進行形象的塑造。王秀春數來寶作品特有的語言風格、表現形式,自有一種得天獨厚、俗中見雅的優勢。梅花香自苦寒來,天道不負有心人。
中國曲藝家協會快板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大同數來寶的藝術家柴京云說:“王秀春老師的作品把握住了一個平民定位。貼近生活,貼近百姓。王秀春老師的作品具有教化功能和娛樂功能。王老師的創新意識很強,他的數來寶已經不僅是兩個演員在表述一段故事,而是通過故事展現人物性格和發掘思想靈魂。所以他的作品百看不厭,常看常新,人物非常生動。王秀春老師的作品至今仍是曲藝界學習的一個樣板。”
在王秀春的身上,有著濃郁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情結。王秀春不止息地思索著曲藝與文學的關系。王秀春并不一定能把他的每一個作品都做得多好多成功,但這種對文學性的追求及努力,使他在曲藝的創作和表演上能夠獨樹一幟、脫穎而出,使他的曲藝作品比同時期的曲藝作品顯得棋高一招。
王秀春曾寫道:“‘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誰說的?尼采?是冷笑吧!”王秀春愛思考,所以按自己的思維詮釋了這句名言。人依天地而生,天地因宇宙而在,人畢竟是因為有思想而區別于萬物。人生煩惱因心生,你不去思不去想,日子就得過且過“浮光掠影”,一頭驢子是沒有煩惱的,一只母雞的愿望只不過是一把谷糠。但人是“會思索的蘆葦”,我思故我在。人的思索,不可避免地都要面對價值取向,也就是究竟追求什么樣的人生價值。然而,每個人自身力量的局限,又使得追求或不盡如人意或無功而返。不如意就產生不堪回首,事倍功半總讓人悔不當初,克爾凱郭爾說人的痛苦有兩種:一種人是因為要做自己而痛苦;另一種人是因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于是就有了要做自己,特立獨行而不得;拒絕做自己,隨波逐流而不甘。謂之進則憂退亦憂。知不可為而為之,成為伴隨人一生的“不得已”。“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人生在世,多在“不得已”中掙扎沉浮。
2018年11月5日,在《撇捺人生王秀春》《王秀春曲藝作品集》首發座談會上,現任山西省曲協主席柴京海評價王秀春:“王秀春老師從未自詡過自己是大師,但他是我心目中的曲藝大師;王秀春老師從未自詡過自己是名家,但他在舞臺上所展現的高超表演藝術是曲藝界共認的名家。”柴京海還評價說:“舞臺上能演,拿起筆能寫,課堂上能講,王秀春老師都具備了。”
王兆麟說:“我們山西曲藝團在中正天街有一個好悅來說唱劇場,王秀春老師的作品作為保留節目,歷史的記憶、歷史的經典,還一直在演出。王秀春老師筆下的人物,仍然鮮活在舞臺上,唱到現在經久不衰,生命之樹常青。”王兆麟還說:“王秀春老師的作品在我們北方曲藝學校成為范本,一直是歷屆學生的必讀教材。”
我曾多次涌起過一個念頭:擅長創作數來寶的王秀春,他寫的所謂詩,有著鮮明的“快板”特色。趙樹理在《李有才板話》的引言中開宗明義:“作詩的人,叫‘詩人;說作詩的話,叫‘詩話。李有才作出來的歌,不是‘詩,明明叫作‘快板,因此不能算‘詩人,只能算‘板人。”劇作家華而實曾為王秀春寫過一篇文章:《“寶”中之寶 人中之人》,文中說了這樣一句話:“趙樹理稱《李有才板話》中的李有才為‘板人,那么,擅長數來寶吟誦的人,可不可以稱之為‘來寶人呢?我就是這樣戲稱王秀春的。”
王秀春的成就在于他創作及表演了許多數來寶,也因此而在中國曲壇聞名。寫出王秀春數來寶的創作歷程,也許還能與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相得益彰。一個是農民中的智者,一個是工人中的智者,工人作者、農民作者,構成共和國民間話語的兩翼。一個農民智者用“板話”記錄和描繪了中國鄉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滄桑變遷,一個工人智者的數來寶,則折射出中國曲藝在轉型時期的社會主義特色。
1973年王秀春獲獎的那支英雄金筆,大概寄寓了“首選一支筆”的深意。王秀春也揮筆十年試鋒芒,書寫下不少可圈可點,或讓人捧腹大笑,或令人掩卷沉思的作品。隨著時過境遷,近半個世紀的歲月塵埃,似乎已將這支英雄金筆掩埋進幽幽的歷史深處。然而,猶如曾有生命的植物掩埋于地層深處轉化為煤藏,煤藏終究要重見天日發出光和熱。
唐代詩人韓翃有詩句:“輕煙散入五侯家”。也許正如柴京海所說:“王秀春老師自己并不知道他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我們是站在了王秀春老師的肩上。王秀春老師的創作功力始終是我們無法逾越的標高。”王秀春的創作表演技藝,已經“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潛移默化地滋養著山西曲壇的后繼精英們,安得倚天揮金筆,在萬里如洗晴空,健筆書寫曲壇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