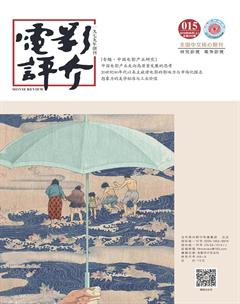想象力的美學(xué)標準與工業(yè)價值
在構(gòu)思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無意間把題目寫成了“想象力的美學(xué)價值和工業(yè)標準”。根據(jù)精神分析的方法,這個誤寫顯然表露出了我的潛意識。于是我不得不嘗試著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然后發(fā)現(xiàn),這可能不是我個人的潛意識。一般情況下, “美學(xué)價值”和“工業(yè)標準”是公認存在的,前者更是美學(xué)的基礎(chǔ)之一,即承認美作為人類的感知和思維對象,有著不同于實用、功利的價值;而美學(xué)則試圖為這種價值的判斷確立某種標準。隨著20世紀哲學(xué)美學(xué)的顛覆性進展,美學(xué)、倫理學(xué)等人文學(xué)科相繼放棄了對統(tǒng)一、終極存在的執(zhí)念,更多情況下,人們傾向于承認,美只是各式各樣的話語,因而只能在對話、博弈、反思中求得妥協(xié)和共識。只是在與藝術(shù)相關(guān)的社會活動和文化消費等領(lǐng)域里,我們才能看到各種對價值進行評估的標準,如電影、戲劇、演唱會等的票價、美術(shù)品的拍賣等等。也就是說,美學(xué)的價值在今天很多時候已經(jīng)由于商業(yè)和市場前所未有的強勢介入而被重新定義,進而明碼標價。
這個表述滿懷傷感和悲情,以至于,盡管我想表達的核心觀點是要為想象力確立標準,或至少要用確立標準的思維去衡量和評估想象力的價值,但在潛意識里,我仍然在捍衛(wèi)美學(xué)的獨立價值,即美的價值不可能用冰冷的工業(yè)標準來判斷。將美學(xué)與工業(yè)二元對立很可能是知識分子的某種集體無意識,之所以如此又并非因為具備本雅明一般的智慧,而僅是喪失對美和藝術(shù)的話語權(quán)后引發(fā)的不安與焦慮。就我個人而言,發(fā)現(xiàn)自己以知識分子自居,這樣的潛意識也令我很是不安。
從精英知識分子力場上講,為人類生存處境的終極自由理想來想,批判權(quán)力和資本是非常必要的,此所以《1984》和《美麗新世界》被奉為啟示錄般的文本。但凡是立場和命題的應(yīng)用都脫離不開具體而復(fù)雜的語境。例如,站在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和文化的角度,一味猛批權(quán)力和資本,而不反思創(chuàng)作和創(chuàng)作者的不足,則往往成為不負責(zé)任的推脫。請設(shè)想,電影創(chuàng)作者既不能與權(quán)力平等共舞,又不能引導(dǎo)資本為人文效力,要么“一朝選在君王側(cè)”,要么“老大嫁作商人婦”,無論如何都透著無能為力和無所作為。權(quán)力無處不在,否則人類社會無從運轉(zhuǎn);資本逐利而居,并不必然需要電影。唯有電影的創(chuàng)作者,作為個體離開電影行業(yè),則與電影無關(guān);作為全體退出電影,則電影不復(fù)存在。因此,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優(yōu)劣成敗,才最應(yīng)該為電影的興衰榮辱負終極責(zé)任。
這個自我批評也是我即將陳述觀點的前提。
我的觀點是:中國電影行業(yè)和文化發(fā)展到今天,想象力不足成為電影創(chuàng)新的一大障礙。為改變這一局面,需要為電影創(chuàng)作中的想象力建立美學(xué)標準,進而評估如果要投入工業(yè)開發(fā)階段,其具備多少價值。
想象力這樣一種心理建構(gòu)的過程,首先來自于現(xiàn)實。“現(xiàn)實與想象,這看似背道而馳的兩極,卻是優(yōu)秀文藝作品必須兼?zhèn)涞目少F品質(zhì)。平庸的作品往往是不夠現(xiàn)實,也不夠有想象力,從而無法碰撞出強大藝術(shù)張力。而優(yōu)秀作品,其創(chuàng)作者在對現(xiàn)實的敏銳發(fā)現(xiàn)和真實觸摸中,被激發(fā)出強烈的表達欲,并且相信他的所感所思應(yīng)當并且能夠感動他人,與此同時,他又能調(diào)動非凡想象力,組織獨特藝術(shù)語言使得他的思想情志得以凸顯。而事實上,同樣的,現(xiàn)實的土壤無論多么豐饒,也必須借助想象力才能夠生長萬物、建構(gòu)伸向天空的文明殿堂。中國觀眾需要在大銀幕上看到現(xiàn)實,但不是機械地、沒有情感投入地使用現(xiàn)實,更不是片面地、過于主觀地曲解現(xiàn)實。同樣的,中國觀眾歡迎電影的想象力,但這種想象也不應(yīng)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更不是莫名其妙的無病呻吟。[1]2017年下半年有兩部電影,《嘉年華》和《暴雪將至》,都是在國際電影節(jié)上提名并獲獎的作品。但仔細打量,它們一個共有的問題是以所謂書寫現(xiàn)實的姿態(tài)對現(xiàn)實加以高度個人化的處理。北京大學(xué)陳宇教授發(fā)現(xiàn)了這類影片在國際和國內(nèi)上角逐獎項的奧妙,認為這種電影之外的故事比影片本身還要精彩。[2]《暴雪將至》的故事發(fā)生在湖南,但是里面的主人公和周邊人物都講一口流利的北京普通話,于是看起來非常寫實的、大量被使用的長鏡頭,與真實美學(xué)的原理完全背道而馳,既沒有真實,也完全不現(xiàn)實,更遑論超現(xiàn)實?這樣的想象力實在沒有多少含金量可言。
想象力的第二種來源是藝術(shù)史上的經(jīng)典性文本。這些文本體現(xiàn)出結(jié)構(gòu)的特性,而且至今在廣泛的文藝、特別是大眾文化領(lǐng)域里保持著高度的穩(wěn)定性,其中尤其以電影電視的情形為突出。如果我們單純地相信進化論,那么,今天中國的影視創(chuàng)作者都應(yīng)該身處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影響的焦慮”,而且應(yīng)該比西方同行更深重。因為不但類型片,甚至文藝片的情致、藝術(shù)片的先鋒深邃,都近乎已經(jīng)被前人開掘得題無剩義。然而,讓我們很尷尬,現(xiàn)實情況是目前太多影視作者幾乎完全沒有受到經(jīng)典文本的影響,恰恰相反,對經(jīng)典一知半解乃至任意曲解、偷梁換柱、指鹿為馬,倒是隨處可見。隨便舉個例子,眼下的古裝劇,咬文嚼字做有文化狀,識者看來實則文法不通,名實不符。另一類典型的例子普遍出現(xiàn)在國產(chǎn)兒童動漫產(chǎn)品中,只要對國外動漫和西方兒童文藝略知一二,都會驚恐地發(fā)現(xiàn),國產(chǎn)動漫的造型、人物劇情、背景設(shè)定等等,都眼熟得可怕,同時也混亂得駭人。我們的孩子們或許不能馬上意識到這些,于是他們未來將不得不重新區(qū)分這堆視聽碎片分別屬于哪一個文化符號系統(tǒng),然后質(zhì)疑中國的影視創(chuàng)作者們?yōu)槭裁粗粫谥七@樣的怪胎——這比山寨還糟糕。創(chuàng)作者的語言和意象錯亂實際上表明,他們沒有經(jīng)由必要的學(xué)習(xí)和訓(xùn)練來獲得創(chuàng)作的基本能力之一,即不犯下文化常識性的錯誤。
還是在文藝片和藝術(shù)片這兩個概念含混、界限不明的范疇里,為數(shù)不少的國內(nèi)電影創(chuàng)作者倒是表露出了對電影經(jīng)典的熟悉和偏好——他們有意無意地在自己的作品里使用著現(xiàn)成的橋段。這很吊詭,因為,不同于類型片都是帶著相似的鐐銬跳不同的舞蹈,文藝片和藝術(shù)片最忌諱的事情就是雷同。更不用說水土不服、西學(xué)之體中學(xué)難以為用。“向某某致敬”的說辭并不足以遮蔽能力不足、學(xué)習(xí)而不甚解的尷尬。此外,還有一種現(xiàn)象也足以證明這種學(xué)習(xí)的極端片面,那就是在今天的影視創(chuàng)作里幾乎看不到對中國電影史經(jīng)典的借鑒,這意味著,中國電影的美學(xué)積淀并未得到足夠的認知和繼承。
上述有關(guān)想象力的兩個來源決定,想象力是有美學(xué)標準的。如果創(chuàng)作者們還同意藝術(shù)水準有高下之分的話,他們就應(yīng)該去思考,我的美學(xué)觀點、趣味是什么?它們是不是足夠好到可以支撐一部作品、一件產(chǎn)品?美學(xué)標準是和藝術(shù)規(guī)律、敘事模式、作品體系(包括電影史)相關(guān)聯(lián)而存在和顯現(xiàn)的,它有相對穩(wěn)定的標準或標準體系。在想象力物化為作品和產(chǎn)品后,它的美學(xué)呈現(xiàn)應(yīng)該可以衡量、比較,甚至可以量化。在未來,通過大數(shù)據(jù)的思維和邏輯,人們將可以對文藝作品和產(chǎn)品的美學(xué)形態(tài)、作者的審美趣味、受眾的接受度等等加以計算和分析。這是早晚的事情。今天的計算機已經(jīng)可以一本正經(jīng)地寫詩,這意味著,人工智能可以按照某種美學(xué)標準來完成一件相對簡單的作品。由于美學(xué)最終極的形態(tài)是理性表達的邏輯,可能人工智能在建立美學(xué)標準時反倒要比它去創(chuàng)作更加簡易。
一旦我們認為想象力有美學(xué)標準,它也就具備了工業(yè)應(yīng)用的可能性,擁有了真實不虛的價值,這種價值進入工業(yè)的考量標準應(yīng)該可以去估算、核算。所以,用逆推、倒逼的思維,用工業(yè)化的模式去推動創(chuàng)新,刺激創(chuàng)意,規(guī)范想象力,應(yīng)該是我們現(xiàn)在需要開展的工作之一。這項工作,與其等產(chǎn)業(yè)圈出手,不如創(chuàng)作界、學(xué)術(shù)圈提早鞭策。
目前中國電影行業(yè),想象力不足、不好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作內(nèi)外兩個方面。
就外部而言,首先是解決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問題。這固然是老生常談,但從想象力進入電影工業(yè)思維的角度看卻仍然很有必要。長期以來,“中國制造”的弊端,也是最為人詬病的軟肋之一,便是山寨嚴重,中國電影行業(yè)也不能免俗。2016年,迪士尼公司訴訟國產(chǎn)動畫片《汽車人總動員》抄襲其《賽車總動員》一案可為典型。假如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在《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促進法》出臺之后仍然不能成為業(yè)內(nèi)共識和紅線,奢談想象力將毫無意義,因為作者的想象力就像沒有孫悟空保護的唐僧,隨時會被人覬覦。其次是解決價值評估的問題。想象力經(jīng)過創(chuàng)作物化為具體可感知的形態(tài),如劇本、梗概、人物小傳、故事板、策劃方案等等,然后接受行業(yè)評估,被認可的成果得以進入電影工業(yè)流程。在這個關(guān)節(jié)點上,價值評估應(yīng)該成為更加科學(xué)、精密、合理的程序。如前所述,評估體系至少應(yīng)包括該成果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聯(lián)程度、與電影史文藝史的互文本關(guān)系,也必須包括該成果在整個項目的價值將以何種方式計量及轉(zhuǎn)換為價格。顯然,目前國內(nèi)電影行業(yè)在這一點上既不夠重視,也缺乏標準,更準確地說,正是由于不重視,才沒有去思考標準的問題。盡管有的劇本作者收入豐厚,但從整個行業(yè)的情況看,并沒有將想象力作為抽象的重要存在、認真對待。
就內(nèi)部而言,首先還是解決原創(chuàng)的問題。假設(shè)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得到嚴格執(zhí)行,假設(shè)電影行業(yè)有了評估想象力和創(chuàng)作的標準體系,那么現(xiàn)在的創(chuàng)作者是否能夠源源不斷地輸出優(yōu)質(zhì)的作品呢?他們的想象力是否足以支撐電影行業(yè)運轉(zhuǎn)并發(fā)展5年乃至10年的需求呢?——這意味著他們要一直保持對觀眾審美的引領(lǐng),并不斷帶給他們驚喜。客觀來看,情況并不樂觀。平心而論,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其實已經(jīng)相當自由,限制想象力的絕不是外部環(huán)境,更多時候恐怕還是想象力的匱乏。2017年廣電總局電影局主辦的第三屆中國電影論壇上,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知名的編劇都轉(zhuǎn)型成為導(dǎo)演,同時很多導(dǎo)演也身兼編劇一職,純作編劇的代表人數(shù)偏少,也偏弱。這是個非常明顯的信號,應(yīng)當引起重視。也是在這次論壇上,我們綜合各方面信息,強烈地感覺到中國電影當前的繁榮并不是必然可以持續(xù)的,有領(lǐng)導(dǎo)提出一個嚴肅的設(shè)想:如果有一天中國電影的觀眾突然流失了怎么辦?這個危險是不是存在?不久前我遇到一位二線城市電影公司的人,他說他所在的城市里面有十幾家影城,競爭非常激烈。我們要想象一下中國電影未來是什么樣子,如果電影像今天的紙媒一樣,會遇到它的終極殺手,這位殺手是什么樣子的?是游戲呢?還是VR或AR呢?電影最不可替代的存在基礎(chǔ)、立身之本是什么?這樣思考當然是超出電影創(chuàng)作的思維之外,但如果一個電影創(chuàng)作者對電影存在處境沒有這樣的危機意識,沒有跳出來看、來想的能力,那么他在未來面前是不合格的。
因此,第二個內(nèi)部問題就是解決電影教育的問題。近20年來,國內(nèi)電影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發(fā)展迅猛,目前開設(shè)影視學(xué)科方向的高校不下百余所,放諸世界范圍來看也令人矚目。但如此蓬勃開展的電影教育卻和業(yè)界普遍感覺到的人才匱乏形成對比,現(xiàn)有的電影教育、人才培養(yǎng)方式和行業(yè)需求、社會期待之間的矛盾不容忽視。這是個很復(fù)雜的問題,本文在此只想強調(diào)一點,高校以及其他教育機構(gòu)一定要為中國文化的未來穩(wěn)住陣腳,不忘初心,不負使命。一方面,要保持象牙塔的純潔性,將資本和權(quán)力的不良影響拒之門外;另一方面,要走出象牙塔去貼近現(xiàn)實、貼近時代、貼近生活。前者給想象力真正自由的翅膀,后者給想象力堅實飽滿的力量。一種理想的電影教育,必然包含著理想主義的倫理訴求。
我個人深感,如果要談清楚想象力的美學(xué)標準和工業(yè)價值,就一定要有某種程度上的精神潔癖,否則主客易位,最終要么回到美學(xué)的虛無,要么淪落為資本或權(quán)力的工具。藝術(shù)必須從美學(xué)和哲學(xué)中獲得自身存在的力量,并以此為基礎(chǔ),贏得與資本和權(quán)力博弈的資格。
參考文獻:
[1]左衡.不夠現(xiàn)實,仍缺想象[N].人民日報,2018-01-02(14).
[2]陳宇.《嘉年華》:當邏輯遇見大時代[N].中國電影報,2017-12-05(7).